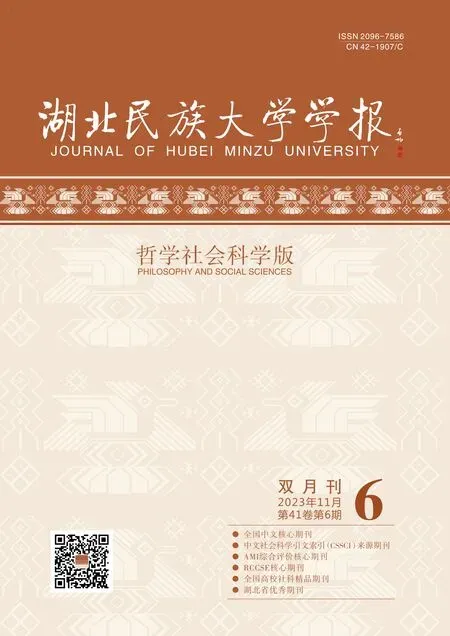论莫斯《礼物》的原创性思维
2023-03-02朱炳祥
朱炳祥
莫斯的《礼物》一书,已经成为学术史上的丰碑,是社会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之所以这样讲,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此文就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一些根本的和真正的问题提出了恰当的理解——且不论它还涉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问题。”(1)阿兰·迦耶:《礼物》“中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页。“《礼物》这本闻名遐迩的著作,是马塞尔·莫斯献给时代的赠礼……对于职业人类学者来说,它一直是促发思考的不竭源泉,就好像被物中之灵hau不断敦促,一次又一次返回这个主题,或许是要发现一个全新而确凿的观点,又或许是要进入一次对话,似乎要告诉读者些什么。”(2)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1页。然而,这本具有开拓性的民族志作品或许是社会人类学领域中最晦涩的、最令人困惑的作品。它看似通俗易懂,但却“很少有人读懂”,因为它在表面上纯粹的各种民族志材料拼接的背后,有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体系。一些人在“莫式礼物”中看到的是礼物自身的极端的含混性,另一些人却只看到了简单转让和交易相混杂的源头,又一些人看到的是某种范式,还有一些人将其解读为非市场性呈献的多种形态之一。(3)弗洛伦斯·韦伯:《多样化的礼物:迈向一种非市场性呈献的民族志》,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附录”,第140页。
如果说《礼物》一书是社会科学作品领域中的宏伟大厦,那么,这座大厦的房基则是毛利人的一个词汇“hau”所奠定的。莫斯正是从“hau”的误释开始,经过了一系列神奇的语义再释与转换,发明了一个“总体呈献体系”,进而构建出他的基于人性基石的“节制下的和平”机制,以实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本文旨在通过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理解莫斯《礼物》原创性思维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
一、从“hau”到“礼物之灵”:为了“发明”的“误释”
由于莫斯原创性思维的产生与进展是从“hau”开始的,“hau在《礼物》中所扮演的伟大角色——以及此后在人类学的经济学中所享有的蜚声——几乎完全源自这一篇章”(4)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3页。,因此,我们的考察也需要从“hau”出发。作为“第二主体”(5)“第一主体”指当地人,“第二主体”指民族志者。参见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58-71页。的莫斯和作为“第一主体”的毛利人对于“hau”的解释有着一个巨大的、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因为处于主位的被观察者和处于客位的观察者之间的立场、观点与思维范畴的差异所造成。正是在土著或本地概念(主位)和作为观察者的民族志学者的概念(客位)之间的差异中,莫斯的天才思维获得了创造空间。
《礼物》一书首先追问的问题——也同时是最基础性的问题是:“在后进社会或古式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6)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莫斯认为:这种力量就是“hau”,它导致了回报的义务,并象征了在古式社会中相关于社会“交换”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列维-斯特劳斯说:“在《礼物》中,莫斯热衷于用各个部分重建一个整体,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得不把一个让他误以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补充量增加到这一整体之中。这一补充量就是‘hau’。”(7)列维-斯特劳斯:《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9页。正是在“hau”这一关键性概念的词义上,诸理论家一致批评莫斯对此进行了主观性的“误释”。当地报告人拉纳皮里是“hau”这一词语的唯一提供者,他也是第一个解释者。他的话语原文是贝斯特收集的,全文如下。
Na, mo te hau o te ngaherehere. Taua mea te hau, ehara i te mea ko te hau e pupuhi nei. Kaore. Maku e ata whakamarama ki a koe. Na, he taonga tou ka homai e koe moku. Kaore a taua whakaritenga utu mo to taonga. Na, ka hoatu hoki e ahau mo tetehi atu tangata, a ka roa pea te wa, a ka mahara taua tangata kei a ia ra taua taonga kia homai he utu ki a au, a ka homai e ia. Na, ko taua taonga i homai nei ki a au, kote hau tena o te taongai homai ra ki a au i mua. Ko taua taonga me hoatu e ahau ki a koe. E kore rawa e tika kia kaiponutia e ahau moku; ahakoa taonga pai rawa, taonga kino ranei, me tae rawa taua taonga i a au ki a koe. Notemea he hau no te taonga tena taonga na. Ki te mea ka kaiponutia e ahau taua taonga moku, ka mate ahau. Koina taua mea te hau,hau taonga, hau ngaherehere. Kati ena.(8)转引自何菊:《多义性作者: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学写作——基于“礼物之灵”诸文本的考察与辨析》,《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50-63页。下文贝斯特的英文译文以及莫斯的法文原文亦转引自此文。这段毛利文在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亦有全文采录,张经纬等学者对这段毛利文的中文译文为:“现在,牵涉到森林的hau。这个hau并不是吹动(风)的hau。不是。我会仔细地跟你解释。现在,你有一些贵重物品给了我。我们并没有关于支付的协议。现在,我把它给了其他人,在很长时间之后,那个人认为他有一些贵重物品,他应该偿还于我,所以他就这样做了。现在,给我的那些贵重物品就是我之前得到的贵重物品的hau。我必须将它给你。如果我私自保留它那是不对的;不论它是很好的或者很坏的,这些贵重物品必须偿还与你。因为这些贵重之物是其他贵重之物的hau。如果我私自扣留了它们,我就会死亡。这就是hau——贵重之物的hau,森林之hau。这些已经足够了。”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5-176页。
这段话是拉纳皮里向民族志者贝斯特讲述的,贝斯特翻译的英文译文如下。
I will now speak of the hau, and the ceremony of whangai hau. That hau is not the hau (wind) that blows—not at all. I will carefully explain to you. Suppose that you possess a certain article, and you give that article to me, without price. We make no bargain over it. Now, I give that article to a third person, who, after some time has elapsed, decides to make some return for it, and so he makes me a present of some article. Now, that article that he gives to me isthe hau of the articleI first received from you and then gave to him. The goods that I received for that item I must hand over to you.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me to keep such goods for myself, whether they be desirable items or otherwise. I must hand them over to you, because they are a hau of the article you gave me. Were I to keep such equivalent for myself, then some serious evil would befall me, even death. Such is the hau,the hau of personal property, or the forest hau. Enough on these points.
莫斯《礼物》一书中的法文原文如下。
Je vais vous parler duhau... Le hau n’est pas le vent qui souffle. Pas du tout. Supposez que vous possédez un article déterminé (taonga) et que vous me donnez cet article; vous me le donnez sans prix fixé. Nous ne faisons pas de marché à ce propos. Or, je donne cet article à une troisième personne qui, après qu’un certain temps s’est écoulé, décide de rendre quelque chose en paiement (utu), il me fait présent de quelque chose (taonga). Or, ce taonga qu’il me donne estl’esprit (hau)du taonga que j’ai reçu de vous et que je lui ai donné à lui. Les taonga que j’ai reçus pour ces taonga (venus de vous) il faut que je vous les rende. Il neserait pas juste (tika) de ma part de garder ces taonga pour moi, qu’ils soient désirables (rawe), ou désagréables (kino). Je dois vous les donner car ils sont un hau du taonga que vous m’avez donné. Si je conservais ce deuxième taonga pour moi, il pourrait m’en venir du mal, sérieusement, même la mort. Tel est le hau, le hau de la propriété personnelle,le hau des taonga, le hau de la forêt. Kali ena. (Assez sur ce sujet)(9)汲喆对这段文字的中文译文是:“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hau,……hau不是吹来吹去的风。根本不是。比如说你有一件什么东西(taonga),你把它送给了我;你送我的时候,也不必说它值多少,我们这不是在做买卖。但是,当我把它送给了另一个人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想好要回报给我某样东西作为偿付(utu),并把这样东西(taonga)馈赠给我。可是,他给我的这份taonga是你给我而我又转赠于他的那份taonga的灵力(hau)。我应该把因为你给我的taonga而得到的taonga还给你。我要是留下了这份taonga,那将是不‘公正的’,这份taonga会很糟糕,会令人难受。我必须得把它们给你,因为它们是你给我的taonga的hau。这份taonga如果被我自己留下,它会让我生病,甚至丧命。这就是hau,这就是个人财产的hau,taonga的hau,丛林的hau。就是这样。”参见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何菊在《多义性作者》这篇考证性论文中,从“报道人与研究者:蒙蔽的可能性”“翻译者与报道人:选择性表述”“解释者与翻译者:偏移性表述”“不同解释者之间:目的性表述”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拉纳皮里、贝斯特、萨林斯以及莫斯对于“hau”的翻译中由于各自的背景、动机与目的不同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解释。她指出:“针对毛利文第八句(Na, ko taua taonga i homai nei ki a au, ko te hau tena o te taonga i homai ra ki a au i mua)的翻译,毕盖斯与贝斯特的做法一致,保留原词,只有莫斯的法语译文‘l’esprit(hau)’将hau与‘礼物之灵’划上等号。”(10)何菊:《多义性作者: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学写作:基于“礼物之灵”诸文本的考察与辨析》,《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50-63页。
“hau”这个词,无论是拉纳皮里的原话,抑或贝斯特的英译,还是萨林斯请出色的毛利学者布鲁斯·毕盖斯教授重新翻译的译文(他译为“the hau of the valuable”),都没有“灵力”的含义。但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有一处保留了毛利原文的直译(le hau des taonga),另一处则译为“灵力”(l’esprit),并且明确地强调:“‘hau’指的是事物中的灵力(l’esprit)。”(1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他论证道如下。
这份资料很值得讨论,毛利人虽然还浸润在诸如“秘屋”之说等尚不精细的神学和司法精神之中,但其思想有时也会令人惊讶的明晰。在上述对“hau”的描述中只有一点模糊之处,这便是第三者的介入。但是,要想很好地理解这位毛利人法学家,只需这样说也就足够了:“taonga以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都有hau,即一种精神力(pouvoir spirituel)。你给了我一份taonga,我又把它给了第三者;然后那个人又还我一份taonga,这是我给他的礼物中的hau促成的;而我则必须把这份东西给你,因为我所还给你的东西,其实是你的taonga造成的。”(12)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他还在一个注释中进一步说明他赋予此词“灵力”词义的来源:“‘hau’这个词和拉丁文的‘spiritus’一样,兼指风和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它指的是非生物和植物中的灵魂与力量。”(13)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页注释第25。这样,“hau”的“礼物之灵”的概念含义就产生了。
当莫斯再度对“hau”进行解释,他又将“礼物之灵”的语义转换为“人之灵”。他说:“对财产—护符的考察使我们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至少在理论上,从毛利人的法律和宗教的角度而言,‘taonga’与个人、氏族和土地息息相关;‘taonga’是毛利人的‘曼纳’的载体,承载着其所具有的巫术力、宗教力和精神之力。”(14)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由事物形成的关联,乃是灵魂的关联,因为事物本身即有灵魂,而且出自灵魂。由是观之,馈赠某物给某人,即是呈现某种自我……顺理成章,我们就能够明白,在这种观念体系中,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因为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15)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这里的“hau”,已经不仅是“礼物之灵”,而且是“礼物赠与者之灵”,礼物与人合一,所以在交换过程中,它总是试图回到原来的地方,同时它赋予赠与者控制受赠者的力量。“你是什么,我也就是什么;今日起我便是你,你我合二为一;我把你送给别人,等于送了我自己。”(16)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173页。这样,莫斯在不断远离毛利词汇原义的过程中,稍稍地接近了他的“总体呈献体系”的思想。
关于“hau”的释读,雷蒙德·弗斯直接批评莫斯的解释是“别有用心的误释”。弗斯说hau没有莫斯认为的那种主动精神,拉纳皮里文本事实上无法证明hau在积极地试图回到源头,莫斯混淆了在毛利人看来完全不同的几种hau的观念——人的hau,陆地和森林的hau,礼物的hau——在此基础上莫斯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莫斯没有理由认为礼物之hau就是赠与人之hau。由此推论出的,物品交换就是人的交换这一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错误命题。拉纳皮里只不过说有第三方赠予第二方的物品是第二方从第一方获赠的物品的hau。人的hau并不在交换之中。”(17)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9页。另一位毛利研究专家乔汉森则怀疑拉纳皮里这位毛利老人在谈论礼物的hau时,脑海中是否会浮现某些独特精神产物。他发现hau这个词有着丰富的语义学意义,有着同音却不同义的多种解释,作为hau的物品随着仪式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塔麦提·拉纳皮里是在介绍并解释某个仪式时,提到了对礼物的论述,这个仪式是毛利猎人在捕鸟之后对森林的献祭仪式。在这段说明性文字中报道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确立互惠性原则,这里的hau只是意味着“回礼”。(18)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1页。萨林斯的批评则是关注到因为有“第三方的加入”,hau说的是繁殖问题,是增值问题,是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利润”对hau来说,是一个比“灵”更好的翻译。hau并不是灵力,hau的载体wauir放入森林以使鸟儿繁殖,说明森林的hau就是其生殖力,正如礼物的hau就是其物质生产力。萨林斯批评莫斯关于hau之精神意义的先入之见,及与之相应的对其经济意义的忽视。他认为,“taonga交换所展现的hau的意义和交换本身一样世俗。如果第二件礼物是第一件礼物hau,那么一件商品的hau就是其利润,正如森林的hau就是其生产力。”(19)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5页。这样,萨林斯使礼物之灵非神秘化,并且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20)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对莫斯使用‘hau’概念的批判已成为民族志领域的某种常识。”(21)参见弗洛伦斯·韦伯:《多样化的礼物:迈向一种非市场性呈献的民族志》,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附录”,第142-143页。许多人类学家共同确认,莫斯的确是将hau的语义内涵以及hau的精神意志误释了。莫斯将hau作为“礼物之灵”进而作为“人之灵”,只是一种凭空想象的臆断。既然如此,从通常的学术规范来说,莫斯的研究有着致命的“硬伤”,这可是学术研究之大忌。然而,“hau”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以后,“礼物”大厦却并没有因此而崩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作为“第二主体”的民族志者的创造性来说,这种“误释”恰恰是原创性思维的一种极致表达。这个“误释”意义极为重大:如果没有“礼物之灵”的概念将“物与物”之间联系起来,进而又将“人与物”之间联系起来,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就不可能有一个“总体呈献体系”,由此进一步的建构更是无法设想。当莫斯的理论大厦需要寻找一块磐石作为基础的时候,莫斯这位著名学者也许千寻百觅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石头,他只好利用自己那“点石成金”的本领,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给予了灵魂,点化成为“灵石”,从而完成了他的创造性工作。现在,虽然真相大白,然而,既然这座“礼物大厦”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如此完美,那么无论什么人证明那块作为奠基的石头何等不堪大用,都丝毫无法撼动这座大厦了。《礼物》一书依然光芒四射,它甚至因为后世的争论反而更加辉煌夺目。这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学术现象。
二、从“礼物之灵”到“总体呈献体系”:为了“建构”的“发明”
正是从毛利词汇“hau”的历史性误读中,莫斯从“礼物之灵”中获得了重大的学术灵感,他的原创性思维由此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接着,他要来建造他的伟大工程了。于是,莫斯离开了波利尼西亚,先去了美拉尼西亚,再去了西北美洲,到达那些与西方社会“相邻”的社会进行书斋民族志考察;其后,莫斯又穿越历史时空,到达古罗马、古印度、日耳曼社会这些属于西方社会“过去”的形态中巡游。经过这种跨越时空的观察,莫斯得到了一个结论:“礼物之灵”表明了古式社会特有的“混融”现象,“礼物之灵”的观念背后乃是一个物我群己混融的世界。“归根结底便是混融。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22)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正是在这种“混融”中,整个礼物社会凝聚成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存在,即“总体呈献体系”。
所谓“总体呈献体系”,是指古式社会各个分部或次群体之间的各种复杂的社会事实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总体的”社会现象。这些“总体的”社会现象能够同时展现这些古式社会的全部各种制度:政治、经济、家庭、宗教、法律、道德乃至美学现象与形态学现象。在“总体呈献体系”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让和移交的,包括食物、女人、儿童、财物、扩符、土地、劳动、服务、圣职和品级等。莫斯将这种古式社会的交换的性质与形式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之间的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呈现在契约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其次,交换并不限于物质和财富这些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而是一种总体交换,他们首先要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其中市场只是种种交换的时机之一,市场上的财富的流通不过是远为广泛、远为长久的契约中的一项而已。第三,这种交换是一种义务,甚至极易引发冲突,但是他们往往通过馈赠礼物这种自愿的形式完成。(23)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总体的呈献不仅包含了回礼的义务,而且还意味着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义务:送礼的义务和收礼的义务。我们相信,关于上述三重义务的复合论题的完整理论,能够为波利尼西亚诸氏族间的这类契约提供彻底圆满的解释。”(24)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夸富宴”和“库拉”,是莫斯所论述的两种“总体呈献制度”,其民族志材料来源于四个地区:波利尼西亚的毛利人、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人、其他美拉尼西亚人和西北美洲。“夸富宴”是典型的赠礼制度,它充满着竞争与对抗,这是因为要确定群体之间、群体的首领之间一时的等级。莫斯认为,夸富宴只存在于等级关系并不稳定的社会中,在这类社会中,每次仪典都可能使等级关系破旧立新。在夸富宴之中,人们会发生争斗,甚至会导致参与争斗的首领和显贵丧命。一方首领为了压倒其他竞富的首领及其盟友,甚至会不惜将自己积攒下来的财富一味地毁坏殆尽。“这种呈现使首领处在一种极其突出的竞技状态。它在本质上是重利而奢侈的,人们聚在一起观看贵族间的争斗,也是为了要确定他们的等级,这一等级将关乎整个氏族的最终收益。”(25)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这种“竞技式的总体呈献”是氏族首领之间的较量,这场互竞慷慨的盛会的目的是在不同群体及其首领之间建立等级关系:赠送、摧毁财富最多的人就是最强者。夸富宴是一般性交换的古代形式:赠礼与回礼,而这些社会中事物的流通即是权利与人的流通。夸富宴是“总体的”现象:它是宗教的,因为参与其中的首领们再现了祖先与诸神;它又是经济的,即使用目前欧洲的标准来看,其交易的数额也是惊人庞大的;它又是社会形态学现象,在夸富宴上,部落、氏族和家庭乃至部族在夸富宴上集会,并造成了强烈的紧张与兴奋,在接二连三的竞赛中,人们或互相沟通或彼此对立;它还是美学现象、法律契约形式;如此等等。(26)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70页。“夸富宴”竞争对抗激烈,其逻辑以两个原则为基础:信用与荣誉。不是马上偿还,而是稍后回报,这是信用问题。回报的礼物多于收到的礼物,这是荣誉问题。夸富宴的本质在于压制对手,使对手成为奴隶,而使自己成为主人。其所毁坏礼物所显示的超功利性正是功利性的反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制度则是赠礼制度的退化与变形产物。莫斯多次提及“库拉”和“夸富宴”的亲缘关系,认为这两种制度都属于总体呈献,唯一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竞争。“库拉”只要加上对峙、打斗和破坏,也就等同于夸富宴。“库拉”是一种平等且平和而规律的互惠性双向流通,它由仪式性交易的双向循环构成,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身份关系。有规律的交换使人们建立了相互联系。特罗布里恩的库拉是一种大型的“总体呈献体系”,承载了部落间的大量贸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所有这些部落,所有这些沿海远航、珍宝奇物、日用杂品、食物宴庆、有关仪式或性的各种服务、男人女人等等,才被纳入一个循环之中,并且围绕着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上规则地运动。”(27)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库拉”是经济、法律、道德、神话、宗教和巫术的复合。这种交换与毛利人一样,同样是由事物、价值、契约以及其中所表现的人共同形成的混融。“竞争、对峙、炫耀、追逐富贵、贪图利益,这就是支撑着以上行为的各种动机。”(28)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部落间的“库拉”是更为普遍的礼物交换制度的一个案例,是这种制度中最超越和最富戏剧性的场景。它使整个部落跨出了原有疆界的狭小范围,甚至超越了它们原有的利益和权利的圈子。礼物交换制度已经渗入到特罗布里恩人经济生活、部落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就是不断地“送与取”。(29)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页。然而,“库拉”虽是平和的,但这种贵族式的贸易也是荣誉之行,库拉是循环的奖杯,奖杯象征荣誉,失去荣誉就失去了地位。因此,库拉和夸富宴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莫斯对于“夸富宴”与“库拉”这两种“总体呈献制度”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非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对于这种“游观”式的、“散点”式的观察方式,对于这种将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混融在一起的“煨中药”式的思维方式,重视“结构”研究的列维-斯特劳斯似乎既不以为然,又肃然起敬,他以一种介于严肃与戏谑之间的语调说:“这些混乱的纸张(指《礼物》一书)所具有的惊人的力量就源于此。它们还有点混乱的东西,其中各种印象主义的标志以十分奇怪的方式重叠在一起,充满灵感的博学常常被浓缩在压垮正文的批评部分,它杂乱无章地收集了各种美洲的、印度的、克尔特人的、希腊的或大洋洲的参考资料,但是它们同样都是令人信服的,真是这样吗?当读到《礼物》时,没有人不会不感到像马勒什所描绘的他在第一次阅读笛卡尔时的那一连串的激情:心在跳,头在摇,精神被一股尚无法界定、却又是绝对的确定性所侵袭,促使它参与一次关键的科学革命的事件中去。……社会第一次不再属于纯粹是资料汇总的领域:奇闻、轶事被用来进行道德化的描述或当作博学式的比较的材料,成为一套系统,人们可以从中发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等价和一致。”(30)列维-斯特劳斯:《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6页。这里所谓“心在跳”,这是惊异于莫斯这种创造的神奇性,乃至可以看作是民族学思想史上“一次关键的科学革命的事件”;而所谓“头在摇”,是因为莫斯的《礼物》杂乱无章地将各种时间与空间中的材料乃至奇闻轶事都放在一起,“印象主义”式地进行组合“成为一个系统”,这种创造性的拼接很难令人信服。他还批评莫斯对结构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解,于是只好用“han”的神话拼凑出一种交换理论。
莫斯没有做过田野工作,他的理论建立在第二手资料上,他由此出发探讨的范畴与问题都与土著人的本土理念和土著人的现实情况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莫斯的“总体呈献体系”只能是一种主观的构建,是一个逻辑的推论。莫斯将“交换”看作是大量表面上异质的社会活动的公分母,但是,他没有在事实中发现这一交换,经验观察没有向他提供交换。“在那些独立的部分、也即单独的礼物上应用一种综合它们的力量源泉,‘我们能够……证实在那些被交换的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迫使礼物们往来、被给予、被回馈的力量’。但是,困难正是从此开始。这一力量真的像一种被交换财物的物理属性那样客观地存在吗?显然不是;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力量必须主观地去理解。”(31)列维-斯特劳斯:《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9页。莫斯所身处的传统,是一个从孟德斯鸠到涂尔干的哲学传统,“依据这一传统,结论主要得自于对概念的分析而不是对事实的分析,事实仅被用作由归纳法所产生的命题的例证”(32)埃文斯-普里查德:《礼物》“英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从《礼物》一书看,莫斯采取的正是这种“概念的分析”方法。莫斯始终没有离开他的书斋,他从概念出发去罗列、整理、编排事实,他对于二手民族志材料的分析仅仅是为“概念的分析”作论据的。也正是这种对“概念的分析”的卓越能力,使莫斯“依据马林诺夫斯有关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文献,就能够揭示出马氏本人对自己所考察的制度都没有理解或理解不够之处”(33)埃文斯-普里查德:《礼物》“英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220页。。
概念分析方法使莫斯的“总体呈献体系”并不能成为一种“发现”,而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一项独特的“发明”。列维-斯特劳斯就曾指出:《礼物》“所揭示的那些事实并不是一些发现”(34)列维-斯特劳斯:《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因为就“发现”而言,两年之前,戴维已经分析和讨论了夸富宴,马林诺夫斯基两年前发表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讲的就是库拉圈的互惠性交换问题,他们才是礼物交换的发现者。“发现”是使某些已存在的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或事实变得为人所知。发现是“找到”(finding),即原先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找到它。“发明”则是对先前存在的材料、条件和风俗的新综合。发明是“制造”(making),即制造原先并不存在的东西。“总体呈献体系”之所以是一种“发明”,是因为它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主观解释结构,即“对象在意识中的构造问题”(35)瓦尔特·比梅尔:“编者引论”,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页。。莫斯综合了从波利尼西亚到美拉尼西亚、安达曼群岛和西北美洲,再到古代罗马社会、印度社会和日耳曼社会的大量例证,他将这些零散材料如剪贴画那样拼接起来、排列起来,进而发明了“总体呈献体系”。
三、从“总体呈献体系”到“节制下的和平”:为了“理想”的“建构”
莫斯发明“总体呈献体系”的意义,在于它成为莫斯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个寄托。那些至今仍然进行礼物交换的古式社会的民族被莫斯看作“都是新石器时期伟大文明的杰出代表”(36)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在这些社会中,“礼物赠予关系”是所有未被扭曲的交往行动的原型。然而,这种原型当中的某些基于“人性基石”的基本精神被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扭曲和丢弃了。现代资本社会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全部还原为纯粹物与物的关系,而这种物与物关系更倾向于赤裸裸的利益与金钱的计算。而古式的社会的“总体呈献体系”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物我关系、社会交往关系和文化象征关系,它凝结着人类的个体德性、集体交往行动、道德情感、想象与象征、巫术与宇宙论以及社会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礼物在莫斯那里“被用来作为理解人的社会性、道德义务和有机团结、交往行动和交往体系、文化象征结构以及原始经济的一种模式,而且还被用来作为理解宗教性、神圣观念或弥赛亚观念的一种话语模式”(37)张旭:《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莫斯在《礼物》的开篇即说明了该书的主旨,即对交换与契约进行考古学研究。它的基本命题是: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契约,这是与近代以来从霍布斯开始,经由洛克、卢梭、斯宾诺莎和康德,直到约翰·罗尔斯所形成的政治哲学传统相异。人类社会原初只有礼物,古式社会的基础就在于“送礼—收礼—回礼”三重义务。这个基础不是如现代社会的那种“交换”或“契约”,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礼物—交换”“准契约”的那种方式。(38)阿兰·迦耶:《礼物》“中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
萨林斯揣摩莫斯的“礼物”交换研究的用意,他说:“莫斯用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替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礼物意味着联合、团结和结盟——简言之,和平”“礼物是原始社会达成和平的方式”“莫斯发现了礼物,一个可以维护和平的机制。”(39)马塞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01页。不过,萨林斯的话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了,并非莫斯的本意。莫斯本人清晰地意识到新石器时期的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具有双重的品格:“初虽甘醇,终必荼毒。”(40)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这么说,“礼物”的理想并不美好,《礼物》一书中那个尊沃德举出的例证就是一个“和平”的反证:美拉尼西亚的一个部落的首领Buleau邀请了另一个首领Bobal和他手下的人来参加宴会,人们整夜都在反复跳舞。清晨,所有人都因为这一夜的狂欢歌舞而兴奋不已。但就为了Buleau的几句责备,Bobal带来的一个人便把他杀了。接着Bobal这一队人竟大开杀戒,把村子洗劫一空,并抢走了村里的妇女。(4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在这个例证中,礼物和仪式的交换并没有维持住“和平”,只因“几句责备”就破坏了这个机制。退一步说,即使“礼物”真的建立起来“和平”,那么这个“和平”也是极为脆弱、不堪一击的。莫斯将这个例证用在全书的最后,很可能具有“点题”之义。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礼物交换”既证明了和平,又证伪了和平。礼物的交换并不总是导致和平,这是由于礼物交换是基于“利益”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礼物交换本身只能建立联系,不能决定这种联系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只要利益均衡因某种原因被打破,和平即刻停止,战争即刻来临;同时,只要战争的利益大于交换的利益,战争也会立即发生。礼物所建立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中,这种“战”与“和”总是交替进行的。“送礼”也好,“收礼”与“回礼”也好,其出发点与目的都是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总是非常容易失去均衡而导致战争。因此,“礼物”交换并非总是指向和平一端,它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复杂的、和平与战争风险并存的机制。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斯的社会理想倾向于“和平”一方,但是他对“古式社会”的研究中,却无法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这种理想。莫斯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式社会考察来判断人性的基石以及在这块基石上来建构他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的,他没有关注与研究包括旧石器时代在内的数百万年的人类全部历史,他的视野显然受到限制,受限于距今仅仅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之内,而这一段时间仅占全部人类历史的不到1%。如果我们将视野延展到人类全部的历史,在这个宏观的视野下思考人类文明的基础,思考人类的初始状态与终极理想,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42)关于从旧石器时代思考人类文明基础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问题,我将在《对蹠人》第二辑中的《文明的基础》一书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既然莫斯的学术视野受到限制,并不是十分宽广,既然“礼物”社会并不理想,“礼物”所建立的也仅仅是和平与战争并存的机制,那么,《礼物》一书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莫斯对于新石器时代的“人性”的基本判断以及古式社会与西方资本社会的对照两个方面去理解。
莫斯通过礼物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以来人性“既不是太善良,也不是太冷酷”(43)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礼物交换中的人们是自利利他的;因此,我们理解莫斯所追求理想只能在这个基础与前提下进行务实的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礼物》的政治学理想也好,社会学理想也好,经济学理想也好,全部都是围绕着道德理想的。(44)从《礼物》一书的结论就可见之。《礼物》结论的第一节就是“道德的结论”,第二节“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论”的主线同样是“道德”,第三节“一般社会学的结论与道德的结论”又重复了一次“道德的结论”。总之,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结论,都是道德的结论。莫斯的道德并不是那种利他主义的高尚的道德,而是一种“中性”的道德。这种道德就是根源于“既不是太善良,也不是太冷酷”的“人性”。对此,莫斯对于“礼物”研究的“最终收获”说得非常清楚。
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要做交易,首先就得懂得放下长矛。进而人们便可以成功地交换人和物,不仅是从氏族到氏族的交换,而且还有从部落到部落、从部族到部族,尤其是从个体到个体的交换。做到了这一步以后,人们便知道要相互创造并相互满足对方的利益,并且最终领悟到利益不是靠武器来维护的。从而,各个氏族、部落和民族便都学会了——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的各个阶段、各个国家和每个个人将来都应该懂得的道理——对立却不必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这便是他们的智慧与团结的永恒秘诀之一。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道德、其他的经济、其他的社会实践更为可行。……善与幸福就在于此,在于克制下的和平,在于共同劳动与个别劳动相交替的恰当节奏,在于财富集中后的再分配,在于教育所倡导的彼此的尊重和互惠的慷慨。(45)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210页。
礼物是互利的,也是自利的,这是礼物的品格,也是“礼物”的真正意义所在。虽然“礼物”所建立起来的是和平与战争风险并存的机制,但莫斯希望能够实现“节制下的和平”。《礼物》所要表明的是:“如果人不能被化约为‘经济人’、不能被化约为维护个人利益的冰冷机器,那么也不应该进而走到相反的极端,强迫人成为利他主义者,否则就只能以暴力和屠戮大众告终。政治与民主的秘诀就是安排好一个生活空间,在其中人们能够‘对立却不必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46)阿兰·迦耶:《礼物》“中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页。这是莫斯建立在“人性”基石之上务实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虽然,莫斯的民族志材料无法证明这一理想;但是,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于莫斯的原创性思维来说,无论材料对于他的理想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学者的莫斯的学术情怀以及他的理想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
莫斯从事非西方部落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在西方文明陷入整体性的危机时刻。在这一背景之下,“莫斯的人类学考察到底是出于西方文明发展到成熟的顶峰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还是出于对西方文化深深的自我怀疑和悲观主义?此外,他将礼物交换研究从‘人类学的经济学’提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层次,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古式社会的礼物经济和社会形态可以作为矫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一个参照?”(47)张旭:《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的确,莫斯无论是对于“hau”的误释,还是特意发明了一个“总体呈献体系”,事实上都是为了他的学术理想和社会改造理想的建构。莫斯将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制度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商品交换”制度进行对照,并且将“总体呈献制度”作为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古式社会的制度来进行时间定位。“礼物”制度尚未形成个体契约、货币流通的市场、确切意义上的销售,特别是尚未形成使用经过计量与命名的货币来估算价格的观念的社会。(48)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页。莫斯认为这种制度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类在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中所共有的,它至今仍然存在于他所描述的那些民族中。莫斯对于他的研究目的说得很清楚:他对原始和古式社会中的礼物的分析是为了给“我们的法律危机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某些问题”找到答案。礼物现象,是“我们外围的社会”和“前于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现象,“这种道德与经济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深刻而持久发挥着作用。”莫斯既要从西方“外围社会”又要从西方“刚刚经历过的社会”(西方过去的社会)中寻找一些他对于理想社会思考的某些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将来也会存在的,而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但却是被扭曲了的那些基本的社会事实。(49)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年代,经济学中心主义把一些普遍性动机都归诸想象的“经济人”,经济学家们远未能找到理解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解决方案,仅仅是把他们自己的推理投射到他者的行为上,而这些推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从韦伯著作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史研究,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中汲取概念的经济民族志研究,以及受涂尔干学派启发的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学不约而同对社会流行的经济学观念进行了批判。(50)弗洛伦斯·韦伯:《多样化的礼物:迈向一种非市场性呈献的民族志》,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附录”,第163页。莫斯承续着这一批判传统,特别承续着他的老师涂尔干着力解决而尚未妥善解决的问题,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他相信在总体呈献中找到了‘我们所能观察和设想的最古老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同时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趋向’的一种制度,即兼具自愿与义务的给予。”(51)弗洛伦斯·韦伯:《多样化的礼物:迈向一种非市场性呈献的民族志》,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附录”,第168页。莫斯要探寻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而人们往往把当今的制度、习俗视为既定的,不知道在历史上、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人们都曾经有过并且仍然有着不同的观念、价值和制度。在莫斯的著作中,在他所论述的古式制度和西方现有制度之间总是有一种含蓄的比较或对照。他所要探寻的,不单单是如何理解那些古式制度,还有这种理解如何能够有助于理解、甚至改善我们的制度。(52)埃文斯-普里查德:《礼物》“英译本导言”,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1-222页。《礼物》试图寻找一种社会问题解决的政治上的方案。这就是说,莫斯是在批判西方社会制度的目的下到古式社会中去寻找救世理想与救世方案的。
莫斯的理想的对立面是他所身处其中的西方现代社会的那种既有观念。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与赠予的习俗制度及其道德情感的人性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瓦解了。在莫斯从事礼物研究的时代,“商品的法则”和“资本的逻辑”摧毁了一切“前现代”的人类社会的伦理生活法则,消解了“礼物”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意义,使得现代人在本质上定位在“经济人”“劳动力”“消费者”和“欲望机器”之上。现代社会就是由这些数目庞大的原子化的相对冷漠的“现代人”所构成。莫斯在涂尔干社会学的基础上,通过礼物研究所反思的是:只有超越和克服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视野的局限,才能重新发现“礼物社会”及其整体性社会生活实体的意义。“莫斯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过于抽象而非人性化的资本社会所谓的‘现代性原则’就是各个彻底分化的社会领域中的‘冷酷的理性’,而古式社会的‘经济—道德’与‘法律—契约’原则应该被重新引入现代社会中以补救它‘理性化、太理性化’的弊端。”(53)张旭:《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礼物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混融的整体性,与此相反,在西方现代的“资本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欲望与情感、成功与失败等,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和计算,都要由金钱来衡量,由资本来推动。“礼物社会”和“资本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礼物社会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社会实在,而资本社会则是一个社会系统高度分化和理性化的社会。莫斯对古式社会的礼物交换习俗研究质疑了这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生产模式的道德与法律的人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莫斯发掘古式社会礼物赠予、交换和回赠的习俗中物我群己混融的总体性的社会实在的意义,并以此来抵制韦伯以及后来的卢曼所描述的工具理性化的抽象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冷冰冰的、非人性的、理性的抽象社会关系,为现代社会引入“礼物社会”的道德、情感、法律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的人心人性的基础。就此而言,《礼物》中的“礼物社会的考古学”对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的“社会整体实在”及其道德与法的人性基础的探究,可以视为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世界宗教伦理”系列研究)中所阐发的社会各个领域彻底“理性化”和彻底“分化”的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深刻的反驳。(54)张旭:《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42页。由此看来,《礼物》一书所展示的理想虽然因为视野所及仅在于新石器时代而受到限制,但其却具有鲜明的基于现实基础的另一种务实的理想,这种理想在于在于彰显了莫斯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去进行现有资本社会改造的责任及愿望。
四、结语
一部民族志作品,是一种“呈现—解释—建构”的形式。(55)关于民族志是一种“呈现—解释—建构”的形式,参见拙著《地域社会的构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7-37页。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看到,莫斯取自当地人的重要概念“hau”并没有“礼物之灵”的含义;由“礼物”所构建起来的“总体呈献体系”,仅仅是莫斯的主观“发明”;“礼物”因其基础是“利益”关系,故而它也不能成为一种“和平机制”的理想,甚至“节制下的和平”也做不到。然而,正是《礼物》所展示的社会批判力量以及莫斯作为学者的学术道德责任,才相关于学术研究的本质及其特征。人们往往以为,人类学的研究就是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即描述事实、发现规律的研究,这在莫斯创造性思维的冲击下无疑已经成为一个认识误区。其实,创造性研究仅仅是人类学家思想的成果,而不是客观规律发现。于此,本文的目的绝不是指出莫斯的“礼物”理论是何等的“正确”,主观理念与客观事实是何等的“符合”,而是要揭示莫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在构建“礼物”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那种原创性思维的爆发力、破坏力与创造力,这种爆发力、破坏力和创造力在以下三种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第一,“材料”与“解释”的关系。对于经典民族志的阅读,培养了后来者的一种坚固的理念:只有材料与思想(观点)完全吻合的民族志,才是最上乘的民族志。经典民族志者总是将他们的研究做“圆”,以便可以概括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这种“思想”与“材料”完全吻合的作品往往被看作是具有学术严谨性而加以推崇。普里查德的《努尔人》成为经典的例证。对于一些人至少“是受牛津影响的那些人来说,该书成了所有民族志研究的典范和原型。其言简意赅的描述和高度的抽象备受人们的推崇和仿效”(56)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王晓燕、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页。。不过,那些努力追求“自圆其说”的作家,往往刻意舍弃、掩盖乃至隐匿与他的观点不相符合的证据材料。对此,即使我们避开学术伦理的批评,仅就文章的观点与材料的关系而言,也是不足为榜样的。“自圆其说”的作品主要是一种因果性解释,“如果根据由前提条件与普遍规律而确立的因果律,把文化解释为时空框架上发生的事情,那么,事情的本质、有意识的体验与在体验中主体的自我理解就会消失”(57)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社会科学的认识只是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世界的认识,只有现实世界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构成研究与理解的对象,“对象”只是研究者从无限世界中抽离出来的符合他们需要的有限部分,研究者基于这种有限部分构建了因果关系,故而,这种因果关系仅仅是在主体意义模式中被联结起来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韦伯曾经将事实比喻为汪洋大海,将研究者所攫取的事实比作小岛,“既然对现实的哪怕最小的断面做出详尽无遗的描述也绝不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怎么可能对一个个体性的事实做出因果的说明呢?决定着某一个体性的事件的原因,其数目和种类始终是无限的,而且没有任何蕴含在事物自身之中的特征可以把它们的一个部分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考虑”(58)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莫斯的开创性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hau”的语义中并不包含“灵力”的含义,“hau”与莫斯的“礼物”大厦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性联系。然而在对材料的解释中,从“hau”到“礼物之灵”,莫斯依仗他那天才灵感一步就从此岸跨越到彼岸。在这里,怎样跨越过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到达了那一边。这使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者那种原创性思维的突破力,强大到可以击破任何既有的学术规则的围栏。
第二,“解释”与“重新解释”的关系。莫斯将“hau”误释为“礼物之灵”,完成了第一步天马行空式的跳越;接着又将“礼物之灵”重新解释并发明了一个“总体呈献体系”,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跳越,它同样是民族志者个体的主观创造。“解释”活动本身并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单纯的认识行为,而是解释者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创造性的一种基本特征。人类学家总是处于一种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受到不同的时代社会条件的制约。在进入研究之前,他从他的禀赋出发,选择性地接受了时代思潮和传统中的某些思想或观点,形成了一种“预理解结构”。文化符号对人类学者说什么取决于人类学者能够站在什么高度向这些文化符号提出的那些问题。因而,理解总是生产性的,是别有新解。一个符号的意图从来未被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符号从某一文化和历史环境传到另一文化和历史环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中抽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作者或同时代读者预见到。(59)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9页。莫斯由“礼物之灵”拓展到“总体呈献体系”是他从时代的高度向在他之前的“礼物”研究提出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如果简单说来就是,莫斯由关注“送礼”和“还礼”的交换关系,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再由人与人之间的个体交换关系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进入整个一个群体内部所有成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以及此一群体与彼一群体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以此来反思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莫斯的这种思维创造的特点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空间关系,或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的心理形象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时间关系”(60)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何瑞福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于此,“总体呈献体系”就被发明出来了。
第三,“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关系。任何研究都带有作者强烈的目的性诉求和学术理想,即使那些自称为只是进行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研究也同样。人类学者的研究目的各有不同:普里查德为殖民帝国去研究努尔人,列维-斯特劳斯为了探索人类心灵结构而去搜集整个美洲的神话,费孝通则为了救国、富国和强国而研究中国乡村。莫斯对于“hau”的误释误解,以及对于“礼物之灵”重新解释为“总体呈献体系”,都是为了他的一种目的性建构而服务的。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构理论模型与理想模型。“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模型。”(61)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8页。莫斯希望借助于“礼物”交换建构一个人类社会倾向于“节制下的和平”的理论模式,这个理论模式就是他的务实的理想模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属于“主体民族志”研究的一个侧面,关注的是民族志者主体(第二主体)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要研究等问题。我们从马塞尔·莫斯的经典例证中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启示:为了学术“理想”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建构”,为了这种建构又可以对材料进行那样的“拼接”与“发明”,为了这种发明还可以对当地人的述说进行如此的“误释”!当知道了学术研究竟然这样的神奇并且具有如此的奥妙以后,我们也许会深深赞同格尔兹关于著名人类学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存活下去,“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高明,也不是方法正确,而是他们的写作能力高明”(62)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的看法;也同样地会深深地赞同理查德·罗蒂关于“语言的偶然”与“自我的偶然”(63)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的观点;于是,我们就会从崇拜学术大师转向去寻觅自己内心的“出自独智”的学术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