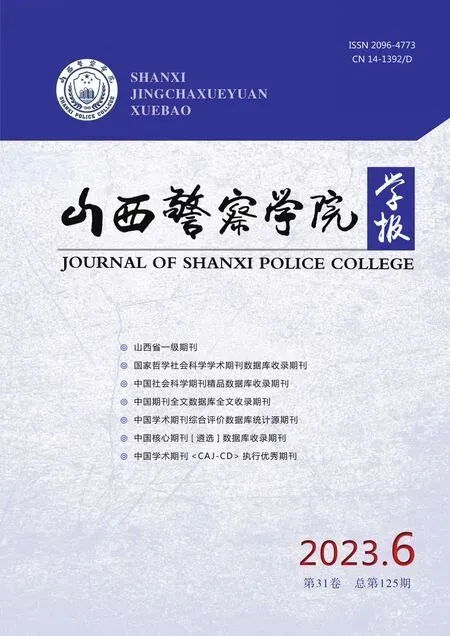从“军府”走向“郡县”:清代新疆治理变迁
2023-02-26沈秀荣
□沈秀荣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有清一代,经过康雍乾三朝经营,清廷最终戡定西北边疆,重新恢复并推进了国家对新疆(1)新疆,古称西域。关于西域的范围,并无明确界定,“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军事势力,政治势力,使节僧侣商贾之足迹,而有远近广狭之不同”。清代,西域改称新疆,地理范围为天山南北路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参看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导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页;齐清顺:《西域、新疆和新疆省》,《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地区的治理。自乾隆朝设伊犁将军府施治,至光绪朝仿内地设行省,清代对新疆地区的治理主要经历了由“军府制”向“郡县制”的政制变迁。
一、三朝经略:新疆复归中国版图
史书称新疆“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洲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1自汉代以来,新疆因其重要战略地位而受瞩目。“汉取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唐开安西、北庭,以制诸蕃;元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灭宋、金而有天下。”[1]1明初,天山北路为蒙古旧部厄鲁特所据,称瓦剌,天山南路为元裔政权叶尔羌汗国。明末,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强大,首领顾实汗袭据青海地区。绰罗斯部巴图鲁浑台吉蚕食近部、声势日壮。(2)《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和硕特固始汗于明末袭据青海,又以兵入藏,灭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绰罗斯特则据伊犁,兼挟旁部,与喀尔喀邻,势俱张甚。”引自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5页。清初康熙年间,绰罗斯部噶尔丹继父兄之位,自立为准噶尔汗。噶尔丹先袭取青海和硕特部,兼有厄鲁特四部,随后夺取天山南路的回部。于是,准噶尔部并有天山南北及青海地方,成为清代西北的强大部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汗噶尔丹率兵向东进占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投奔漠南蒙古求救,清廷施以赈济,将科尔沁地方借与喀尔喀部众游牧,并着意调停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纠纷。噶尔丹势盛,不愿和解,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以追讨喀尔喀为名,引兵越过呼伦池,威胁清朝北边。康熙皇帝亲至边外迎战,清军于乌兰布通大败准部,噶尔丹败归科布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又出兵举衅。康熙皇帝再次亲征,击退噶尔丹。其时,噶尔丹因与清朝交战长居漠北,难以顾及新疆地区,其侄策妄阿布坦便招集部众,据有伊犁之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兵败。策妄阿布坦主动向清军投诚,朝廷以为策妄阿布坦驯服,将阿尔泰山以西划归其部众游牧。
康熙朝三度用兵,扑灭强敌噶尔丹,将漠北喀尔喀部收为清朝藩属,又北得科布多、西得哈密,作为进一步经营西北的根据地。十余年后,准噶尔部势力大增,又生异动,复为清朝西北大患。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阿布坦率众侵扰哈密,清廷派兵至巴里坤,于哈密附近募兵兴屯,以为防范。次年,策妄阿布坦派兵袭入西藏,杀拉藏汗,致藏中大乱。清廷派兵入藏,平定西藏乱局。康熙六十一年(1722),因准噶尔部求和,清廷便退兵休战,只在哈密、巴里坤、吐鲁番、布隆吉河等地驻兵,防范准部东扰。
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对清廷无宾服之意,屡犯边境。雍正七年(1729),清廷派出北、西两路大军,征讨准噶尔部,但战事不顺,双方僵持不下。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决定休兵,遣使议和。次年,噶尔丹策零遣使报和,双方休战。对此,孟森先生称“雍正之于准噶尔以征讨始,以约和终,是为西陲未竟之局”。[2]629
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身死,准噶尔部陷入内讧,呈分裂之态。达瓦齐虽继立为汗,但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萨拉尔等先后率众出走降清。“于是准部爪牙心腹尽至,且指画准部形势如在目睫。”[3]156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经过多年筹谋,清廷决定采用准噶尔降将的计策,分两路出师,征讨准部。阿睦尔撒纳、萨拉尔等人分别担任两路大军副将,各自率领部众作为先锋军作战。“时两副将军皆准夷渠帅,建其旧纛先进,各部落望风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尔藏多尔济及旧回酋和卓木先后迎降。于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潼酪,献羊马,络绎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3]156达瓦齐奔逃回疆,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执献于清军。可以说清军兵不血刃便克定准噶尔部。但当年十月,阿睦尔撒纳因不满清廷封赏,叛而作乱,准部又陷兵祸扰攘之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兵分两路,会攻准部大本营伊犁。其时,准噶尔内部自相攻伐,又有天花痘疫横行肆虐。清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终于平定准部之乱,尽收天山北路地方。
至于天山南路,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初定准部时,由于回部早已服属准噶尔,清军便一并收复,不再另举兵,并释放被准噶尔长期羁禁的和卓后裔,命大和卓博罗尼都归定回疆,小和卓霍集占留居伊犁,分别统率天山南北的教徒族众。阿睦尔撒纳作乱时,小和卓参与其间,逃归回疆煽动大和卓率众抗清。清军派出回部招抚使欲行招抚,但使臣被杀,于是抚议决裂,再起兵戈。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兵败外逃被杀,清朝收复回部之地,统一天山南北。
关于清代经营西北的武功,晚清疆臣纂修的《新疆图志》概括道:“洎我圣清御宇,长驾远驭,九有方夏,悉主悉臣,惟准噶尔崛强西陲,负固不服。自康熙迄雍乾三朝之间,王师载驾,天戈所指,扫穴犁庭。于是一讨准噶尔,再俘达瓦齐,三歼阿睦尔撒纳。鲸鲵既翦,属土归命,是为北疆底定之始。既而回酋霍集占兄弟煽众为乱,移师南向,迭克名城。二竖穷蹙,授首荒外,传檄而下,兵不衄刃,是为南疆底定之始。”[1]2清代为巩固国防,经略西北,历经康雍乾三朝,积时七十余年,终于告成大功,收复天山南北,定制施治,保民安堵。孟森先生论称:“高宗之取新疆,武功之盛逾于前代……除元以外,清之武功为极盛矣”。[2]651
二、大一统下的“因俗施治”:清代中期的新疆治理
统一天山南北后,乾隆皇帝谕曰:“准噶尔荡平,凡旧有游牧,皆我版图”,[4]942宣示了清朝对新疆的主权。由于新疆地处边陲,幅域辽阔,族群众多,宗教复杂,清廷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施政原则,在新疆施行有别于内地省区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理方略。曾问吾先生将其概括为“设军府、驻重兵以震慑之;兴屯垦、讲牧政、筹经费以辅助之,更封以爵位,锡以俸禄,以羁縻其首领;尊其宗教,允其自治,以抚慰其百姓。此是乾隆朝所制定实施者,历嘉、道、咸、同,奉行不渝”。[5]186总体上,清朝对新疆的治理程度较前代深刻,统治策略显现出治理能力和技巧的成熟。在清朝统治之后五十余年,新疆基本保持了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土地日辟,户口日昌,边鄙不警,边民乐业”。[5]209
(一)以军府制为主导的地方政制
清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主要以军政合一的军府制管理新疆地区,如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西、北庭都护府,并册封地方首领以行羁縻。清朝吸取了前代的治边经验并加以发展,在新疆实行以军府制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按照族群人口分布情况分行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这种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政治体制在清朝治理新疆前期有利于稳定地方局势、促进地方发展。
新疆初定之时,清廷于伊犁建军府,设伊犁将军,乌鲁木齐设都统,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其余各城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或领队大臣。(3)《新疆图志》记载:“我朝初定西域,建侯行师,立军府于伊犁。其建置规模,考之前史,大抵于唐为近。” 参看(清)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二十四《职官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1页。关于军府各级军政大臣建置,参看马大正:《西出阳关觅知音:新疆研究十四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9页。将军、都统、诸大臣为军府高级官员,办理各地军政事务。“诸大臣之在北疆者领于乌鲁木齐都统,其在南疆者领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犹唐之有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伊犁将军总统南北军政,自都统、参赞以下,并受节制,礼制最崇。”[1]481
新疆东部地区,汉民、回民杂处,与内地联系较紧密,被视为“旧有之地”。清廷在乌鲁木齐以东地区推行内地的郡县制,设镇迪道,受陕甘总督与乌鲁木齐都统的双重领导。比之前代,实行郡县制的地域有显著扩张。(4)有关清代新疆州县建置进程,参看郭润涛:《新疆建省之前的郡县制建设》,《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天山南路先行归附清朝的哈密、吐鲁番以及天山北路游牧的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等实行札萨克制。清廷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册封各部族首领,命其全权管理本部族内部事务,朝廷不征赋税,各部按期朝觐纳贡,但须受到驻地的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的监督。天山南路的回疆、伊犁的回人聚居地区(5)准噶尔时期,曾令一批回疆居民赴伊犁种地纳粮,称“塔兰奇”。清朝统一新疆后,又陆续将回疆六千余户居民迁往伊犁屯田,并设伯克管理天山北路的回疆居民。实行伯克制。伯克制是回部旧有官制,清廷加以改革,废除伯克世袭制度,将伯克的任免权、监察权收归中央,规定伯克品级,将其纳入清朝官制体系,实行伯克回避制度,准许伯克分批朝觐进贡,并保留伯克的养廉地、养廉户、养廉银等特权。
(二)巩固边防:驻军建城、设卡置台
为巩固边防,清朝派重兵镇守新疆,分北路、东路、南路三路布防。北路,伊犁地区为总汇重地,地旷人稀,又与哈萨克、布鲁特相接,因而驻兵特多,由满洲八旗兵、索伦兵、锡伯兵、察哈尔蒙古兵、厄鲁特沙毕纳尔兵驻防。东路,乌鲁木齐地区居南北冲要,由满洲兵、绿营兵驻防,以资震慑。南路,朝廷以为“回部索习农功,城村络绎,视准部数千里,土旷人稀,形势迥别。自全部输诚内属,设立驿站、卡伦之外,其城所在,固无事多兵驻守矣”,[6]588故回疆无驻防兵,抽调北路、东路满洲兵、绿营兵为换防兵,轮班防守。(6)《新疆图志》记载:“国朝底定西陲,兵制迄今凡三变。初,乾隆时之荡平南北路也,以伊犁为总汇重地,乌鲁木齐居中外冲要,分设旗、绿各营,携眷移戍,谓之驻防。南路回疆及塔尔巴哈台则更番轮戍,三年一易,谓之换防。驻防、换防之绿营,皆自陕、甘移调者也。其驻防之满洲兵,则移自热河、西安、凉州、庄浪等处,察哈尔蒙古兵则移自张家口外游牧,索伦、锡伯等兵则移自东三省,厄鲁特沙毕纳尔兵则拔自新附兵。换防之满洲兵,北路塔尔巴哈台则自伊犁调拨,南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则自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等处调拨。卡伦之兵领以侍卫,满洲驻防隶于佐领,绿旗隶于营官,回兵则令各城伯克经理,而以驻扎之将军、都统、大臣总辖之。”参看(清)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五十《军制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0页。驻防兵额约四万名,(7)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军事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北路最多,东路次之,南路最少。“东北两路,皆在天山之北,可见当时驻兵制度,重视山北,而略于山南。”[5]190
为便于屯驻军队,清朝政府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修建城堡,(8)“当时所著各城堡,并无严格区别,一般较大者称城,较小者称堡,其实皆为土城,主要用于屯驻八旗绿营军队及其家眷,功能基本相似。这些城堡后来变化较大,有的发展成为城市,有的则废弃不用。”引自齐清顺、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如乌鲁木齐地区的迪化城、巩宁城,伊犁地区的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宁远等九城。在素称“城郭之国”的回疆地区则多在旧城旁另筑新城,如喀什噶尔徕宁城,乌什永宁城。不少新城逐渐发展成当地的军政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
新疆底定后,清朝“于其严疆要隘,毗接外藩处所,酌设卡伦,以资捍卫”。[6]438卡伦有常设、移设、添撤三种,由八旗兵驻守,朝廷选派侍卫担任卡伦官员,受伊犁军府管辖。卡伦的主要职能包括防止越境游牧、稽察行人出入、防守矿场禁区、维护治安等。相邻两座卡伦的官兵每天须按照规定路线巡查会哨。每年春秋两季,由伊犁将军派遣官兵分别从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出发,按规定路线巡查辖区内的卡伦以及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区域。(9)参看于福顺:《清代新疆卡伦述略》,《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清朝在西北用兵时为供应军需、传递军情,在交通沿线设立军台。统一新疆后,清廷仍重视建设军台系统,以保证新疆与内地的交通、通讯。有学者指出,“新疆各地遍设军台,而不像内地各省那样改为驿站,与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以军事治理为主的军府制度,驻各地官员皆为军事系统的武职官员有直接关系”。[7]184乌鲁木齐地区因行“郡县制”,“府厅州县平移公文,例不便擅交军台递送”,[8]便在军台之外另设驿站。各军台由绿营派遣驻兵,天山南路的军台除绿营兵外还选派当地回民当差。军台配备马匹车辆等,负责传递公文、接待往来官兵、运送官物、解送罪犯、维护治安。主持民屯的地方官员在军台附近安民屯垦,逐渐形成村庄城镇。据学者研究,“这些由军台发展而来的城镇,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规模总体较小。但是,在历史上,这些城镇却起到了凝聚民众,促进经贸往来的积极作用”。[9]诗曰“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长征”。(10)引自(清)萨迎阿《哈密》诗。全诗如下:“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储粮饷设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斯途合送迎。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长征。瓜田万顷期瓜代,好向伊吾咏太平。”引自(清)钟方撰:《哈密志》卷十三《舆地志十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军台除保障官方通讯,还有利于地方商贸往来及人口流动。
(三)屯垦开发,以边养边
屯田是清朝经营新疆地区的一大要政。它最初只是一项军事措施。由于内地运粮至西北困难重重、耗费巨大,为解决军队用粮问题并节省军费,清军在哈密、巴里坤、吐鲁番、辟展等地兴办兵屯。统一新疆后,考虑到“驻防大军,分据要害,然驻兵需饷浩繁,疲敝国力,耗中事边,势难持久”,新疆“武定功成,农政宜举”,[5]193清廷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开发新疆,以边养边。屯垦类型分为兵屯、回屯、犯屯、旗屯、户屯。兵屯,由绿营兵丁承垦,多在天山北路,南路较少。回疆农户迁往伊犁地区屯田,称回屯。犯屯,也称遣屯,指内地发遣罪犯屯田,除哈密一处外,皆设在天山北路。旗屯,指驻防伊犁的八旗兵屯种。招募内地人口前往天山北路开垦,称户屯、民屯。
其中,户屯规模最大。乾隆皇帝以为“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而“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4]786于是“国家以殖民为务”,“专于户屯措意”。[1]487为了鼓励移民实边,官府提供内地民人赴边所需车辆、银粮,提供农具、种子、牲畜、建房银两,开垦的土地六年后才升科纳粮。民屯政策吸引了大批内地民人赴天山北路开垦。时人记载“内地民人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10]据统计,到嘉庆末年,天山北部“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的自耕农(国家在册农户)已有20余万人,开垦土地108万亩以上”。[11]
清朝新疆屯田之策以天山北路为重。相关研究指出,经过清朝中期的屯垦开发,“天山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已经基本改变新疆历史上长期以天山为界、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为天山北部、乃至整个新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新疆长期以天山为界南农北牧生产格局的基本改变,也为清朝政府把治理新疆的重心放在天山北部及新疆政治军事经济重心的北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证明,清朝政府大力开发新疆天山北部地区的政策完全正确,不仅对当时新疆地区的政局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新疆地区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7]149
(四)限制宗教,坚持政教分离
清季,新疆地区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天山以北游牧的蒙古部众信仰藏传佛教。天山以南的回部信仰伊斯兰教。“在边疆地区,这两种宗教有着巨大的传统影响和社会势力,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边疆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施政不能不考虑宗教因素。”[12]429清朝为维护统治,对宗教采取限制的政策。
清朝一向尊崇黄教,以怀柔笼络敬信黄教的蒙古诸部和西藏,使其诚心内附。天山北路的佛教寺院多毁于战火,战事平定后,清廷主持重建佛寺,以便蒙古部众礼佛,并从北京特派喇嘛主持寺院。对待伊斯兰教,清廷态度更为慎重。一方面,尊重伊斯兰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允许回众诵经礼拜、按照教规处理纠纷,并册封归顺清朝的和卓后裔、保护和卓墓地。另一方面,“鉴于回疆长期以来存在着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的激烈斗争,进而导致察合台后裔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鉴于大小和卓返回南疆以后,即发动叛乱,以宗教为旗帜对抗清朝政府的事实”,[13]268清朝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政策,禁止宗教头目阿浑干预地方事务或担任官职,规定伯克有权举荐阿浑人选并对举荐之人负担保责任;对阿浑看经定罪的宗教法加以限制,废除部分旧有酷刑,对重大案件适用《大清律例》;限制宗教势力的盲目发展,打击非法宗教活动,严禁陕甘地区的伊斯兰“新教”在新疆传播。学者指出,“尽管清朝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以是否有利于其统治而发生变化,但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在评价清朝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政策时,决不能忽略这一点”。[13]280
三、兵燹民瘼:晚清新疆的变乱与善后
嘉道之际,清朝国力日见衰颓,吏治腐败、财政支绌等沉疴痼疾开始发作,地方局势屡有动荡。在新疆地区,清前期治理所积压的矛盾与弊端也开始暴露。当时多有驻疆官吏以地方为利薮,勾结伯克,苛派回户,横征暴敛。“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将军窎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括,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值,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3]186朝廷官员如此做派,官民矛盾一触即发。而流亡在外的和卓后裔在外国势力的煽动、扶持下常常乘隙潜回作乱。以至回疆地区自“嘉道以还乱事尤炽,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竟使清廷穷于应付”。[5]209
(一)道咸年间回疆多乱
道光初年,流亡浩罕的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在浩罕势力支持下,利用回疆民众对清朝官员和伯克失职、腐败的怨愤,纠集人众组成武装,多次侵入喀什噶尔。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之众攻陷喀什噶尔,并相继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占据回疆西四城。清廷紧急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领军进剿,并从陕、甘、黑龙江等地调兵配合作战。几番激战后,清军克复西四城。张格尔战败逃走,后被生擒,押赴北京处死。耗时十九月余、用帑一千余万两后,(11)关于此役军费支出,参看赵珍:《清道光朝南疆战事军费奏销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清廷最终平定张格尔之乱。
然而,时隔仅两年,回疆又生变乱。原在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清廷要求浩罕交出张格尔的亲眷,浩罕以“回人经典,无献和卓子孙之例”为由拒绝。于是清廷决定断绝与浩罕的贸易往来。道光十年(1830)九月,经济大受掣肘的浩罕欲以武力报复中国,招诱张格尔之兄玉素普,拥立其为和卓,啸聚数千人侵入回疆,所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清军在当地回民的支持下击退浩罕兵。此次变乱,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大城虽未失陷,但附近回庄均被抢劫一空,百姓深受其害。次年七月,浩罕因惧怕清朝出兵征讨而议和,清廷不欲劳师,遂许和,并恢复通商。
而“浩罕虽与中国议和,然夷情诡谲,非诚心修好也。依旧豢养张格尔之族人,伺隙而动。且其所属安集延城之商人在喀什一带者常数千人,秘密勾引回民,侦探军情,一有机会,复驱之而入寇。”[5]218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倭里汗等七人在浩罕纠集人众,袭据喀什,分兵进扰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廷调军进剿,连战连捷。迈买的明等溃败逃往浩罕。咸丰七年(1857),倭里汗又率众潜入喀什,攻城作乱。清军复调兵平乱,克复回城。
自张格尔之乱始,玉素普之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之乱等数次变乱对新疆,尤其回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清军扑灭了历次变乱之火,但回疆多乱的局势对清朝的统治提出了很大挑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令清朝财政难以负担。
(二)善后以求久安长治
张格尔之乱使清廷认识到必须整饬新疆的治理问题,根据形势调整政策,以求安内制外。道光七年(1827)底,张格尔之乱基本平定,清廷任命直隶总督那彦成为钦差,赴喀什噶尔,代长龄办理善后事宜。那彦成曾在嘉庆年间出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内实干尽职,对回疆内外情势知之甚详。他坚决反对武隆阿“捐西守东”(12)武隆阿认为“西四城环通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甄,似无需更守此漏厄”,提出放弃回疆西四城,据守东四城。的弃地主张,也反对长龄于西四城分封伯克自理自守、内移参赞驻地的退守之议,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筹划新疆善后事宜。那彦成在疆一年多,“先后奏事一百四十余件,除循例公事外,其有关兴利除弊,国计边防,及整饬官兵、抚绥回众、控制外夷者,共有八十余件,均已钦奉谕旨准行,咨行各城遵办在案”。[14]
其善后安内之策以整顿吏治为重,包括:革除各城大小衙门陋规;加强官员监察制度,规定“每届年终,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将各城大臣出具切实考语,密以陈奏”,“将军、参赞大臣内有不正己、不秉公者亦准各城大臣据实参奏”;[15]4慎重选用官吏,重申回疆各城印房章京由京拣派,禁用驻防笔帖式;卡伦官员不再由京选侍卫担任,改从本地驻军官员选派;严禁贿补伯克,重定伯克选拔资格,重申保举责任、回避规定;增加官员养廉银。安内之策的另一大端是增强军事防御力量:增加回疆驻军兵额;增设喀什噶尔换防总兵;规定南疆换防绿营兵年龄不得超过四十,严禁超期换防,并抽调二千精兵,由总兵专门训练;建卡伦,增派各大小卡伦的驻卡兵力;重建满城,以便屯军防守。为改善财政、增加赋税收入并解决军需问题,那彦成奏请清查私垦地,“查出各城私垦地亩,增收粮石,以供兵糈,并就余粮作官员加增养廉盐菜银两,以节经费”。[15]19清查出的私垦地面积几乎与原登记在册的耕地面积相当。
由于张格尔是在浩罕势力支持下作乱,清朝平乱后浩罕又拒绝交出张格尔亲眷,故而针对浩罕的制外之策是回疆善后事宜的另一要端。那彦成提出的制外策略是“严禁与浩罕通商,以窘其生计。将浩罕人尽逐出境,以断其耳目。收抚各布鲁特,以翦其党羽。待其款关求贡,然后抚而用之”。[5]215有学者研究认为“那彦成整个善后措施,对浩罕始终采取强硬立场,乃在迫其收敛扩张野心。起初,颇得宣宗‘所议极是’的赞赏,然基于宣宗保守消极的心态,于收抚布鲁特政策上,未得同意那彦成的做法,致使其善后制外良策,打了很大折扣”。[16]
道光十年(1830),玉素普之乱再起。长龄以“起衅根由,显系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17]914将变乱归咎于那彦成办理善后事宜不当。道光帝下令将那彦成撤职查办,委任长龄办理续办新疆善后事宜。
长龄的善后计划分为“固守”“媾和”两点。他提出在回疆驻守重兵,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于巴尔楚克设总兵,各省绿营兵额裁撤百分之二以援助回疆增兵。(13)据学者研究,“驻兵规模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按此计划,清兵分驻喀英叶和四城达1.1万,加上巴尔楚克的共1.4万,这个数字将是道光九年的二倍,道光五年的五倍,乾隆二十四年的七倍,是个空前庞大的驻兵方案。”参看潘志平:《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第38页。由于国家财政拮据,长龄的增兵方案未能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14)道光皇帝谕称:“溯查乾隆年间勘定西陲,庙谟神算,办理周妥,六十余年久安长治,从未议及增兵,如果必须添兵以壮声威,当日诸臣早经议及,何待今日,且从古以来,未见有竭内地之兵力堵御四夷,而又能行之久远者,况回疆之极边,于居重驭轻之道大相刺谬,俨然回疆添一省会,日后何能治理,必至内外俱困,将如之何哉,此时即照该将军等所议,竟能一劳永逸,将国家有常之经费,为外夷无益之张罗,实不值如此办理,倘仍不能安靖,徒劳罔功,尚复成何事体。”见《清宣宗实录》卷199,道光十一年十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32页。但“道光帝为摆脱‘重兵久戍、去留两难’的困境,议和之心早已迫不及待”,[18]39传谕长龄“明示浩罕,以大皇帝天恩浩荡,许该夷仍旧通商,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并免其货税……送出回民一节,竟可置之不问,以示大方”,[17]1132“从前抄没安集延物件,亦可发还”,[17]1159指示长龄“总之久安长治,全在抚驭得宜,断不可徒事铺张,顾此失彼,日后转多流弊,以致内外俱困,则悔之晚矣”。[17]1143在道光皇帝“不可徒事铺张,顾此失彼”,“务须得体,不可草率”的指示下,长龄采取了对外妥协退让的善后政策,应许浩罕的议和条件:通商免税,派设商头,归还财产,释放回犯。是以军事上失利的浩罕不仅未因其侵掠行为付出代价,反而获得了各种优待。学者认为,“毫无疑问,媾和是在清朝方面全面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清廷看来,付出一些代价,由此安定南疆,又在形式上保住‘天朝’尊严,是值得的”。[18]40
《清史稿》有论:“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长龄持重于始,老成之谋。那彦成力祛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19]尽管疆臣积极谋划善后举措,图定边疆,奈何清朝国祚已衰,势难挽回,新疆偏居边陲,更有外国鹰视狼顾,一方之安宁终为侈谈。
四、因时变制:清末新疆建省与治理转型
(一)同治年间新疆大乱
清至咸丰朝,国势更危,外有列强步步紧逼,内则变乱四起。南方,太平军兴,捻军附起。西北,陕甘爆发回民事变,新疆也陷入空前的变乱。有论称,“道咸以前,回疆虽时遭变乱,然其乱波限于一隅,未及于全疆。同治间,全疆回民烽起为乱,除镇西外,各属全陷失,几不可收拾。”[5]221
秦翰才先生对此次新疆变乱情形有一概括:“(同治)三年四月,马漋在库车叛,遂拥黄和卓踞南疆东四城。六月,阿布都拉门在叶尔羌叛。马福在奇台叛,八月,金相印在喀什噶尔回城叛。马福迪在和阗叛。九月,妥明陷乌鲁木齐城,遂并踞乌鲁木齐东西各城(旋妥明称清真王)。十月,迈孜木杂特在伊犁叛。四年正月,伊玛木在塔尔巴哈台叛。三月,安集延帕夏(将军)阿古柏侵入英吉沙尔及喀什噶尔汉城。六年阿古柏攻灭阿布都拉门、马福迪、黄和卓等,遂尽有南疆地(旋阿古柏称毕条勒特汗)。九年,妥明降于阿古柏,阿古柏遂并有北疆大部分地。在上述七年期中,清廷虽数度命将出师,仅守住巴里坤,收回哈密。”[20]论者称:“总之,新疆汉回与新回,乘陕甘回乱,纷纷烽起响应之,不出数月全疆糜烂。依其割据形势可分为五系:西四城为金相印等所据,东四城为黄和卓所占,北疆及吐哈为妥明所踞,最后皆并吞于阿古柏。是发难者是中国之回民;获渔人之利者,乃亡国之安集延人也。”[5]224
阿古柏先后吞并其他势力,据新疆之地立新国。当其时,英、俄两国趁机介入新疆。早在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便与英属印度官员接触,与英国建立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与阿古柏正式订立商约。“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政权,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12]606英国与阿古柏之间的联系引起俄国的不安。同治十年(1871),俄国借口保护国境安全,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照会清廷称“俄国并无久占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绥来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1]949同治十一年(1872),俄国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但随后阿古柏又与英国订约并许给英国更优厚的通商条件,遂与俄国关系恶化。新疆局势因英、俄两国介入更加危重。如论者所言,“陕甘之回乱,引起新疆之回乱;新疆回乱,引起安集延之入侵;阿古柏独立,引起回教诸国及英俄等邦之外交关系,引起俄国之占领伊犁;叛徒势力,虽由分而统于一,然国际纠纷则益趋于复杂矣!”[5]230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清军克复肃州,陕甘回乱基本肃清。清廷以为“现在关内肃清,亟应乘此声威,将关外各处窜匪次第扫除”,[21]命将军金顺率师西进,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出关各军粮饷军火。连年用兵,朝廷财政早已极支绌,“官兵需饷孔亟”而“饷项奇绌”成了西征的最大窒碍。是以朝臣中有一派主张放弃西征,“或以谓发捻初平,宜休兵息民,徐以观釁;西域阻远,非所宜急;且强邻干预,连兵不解,尤恐牵动全局”。[1]2
内乱未靖,外患又起。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据台湾,造成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清廷有感“海疆备虚”而谕令沿海各省筹办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22]主张放弃西征,将军费移作海防之饷。此论一出,引起朝臣激烈辩论,“海防”“塞防”之争沸腾一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23]177称“我朝定鼎燕京,内外蒙部,环卫朔方,前代九边,胥成腹地,皆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秦晋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地不可弃,兵不可停”,[23]650坚持西征规复新疆。朝廷最终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光绪元年(1875)三月,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筹大局。
左宗棠制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新疆规复战略,先期整军、筹款、运粮。为节省军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左宗棠主持裁汰冗员弱兵,组成近六万人的西征大军;通过外国银行借款、各省认领协饷、户部拨款等方式筹措军费;分南、北两路粮运,采买内地粮食,输送至前线,还因时制宜向俄国购粮或令军队就地购粮。其进兵计划分作两步,先剿奉阿古柏之命驻守天山北路的白彦虎,再剿南路的阿古柏大本营。大军西进后,按计划收复天山北路、南路。至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均克复。光绪七年(1881)正月,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清廷与俄国签订《还付伊犁条约》,终于收复伊犁。
史论称,“我朝自道咸以来,一乱于张格尔,再乱于阿古柏,几蹈唐代之覆辙。然而卒以长保者,岂非祖宗之创垂能为其可继,而中兴将相匡危戡难之功为不可没哉!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1]481此次新疆大乱历时十四年,“人民丧亡殆尽,旧制因之荡然”。[1]888新疆克复不易,克复后如何经营又是一大难题。
(三)新疆建省之议决
光绪三年(1877)六月,在收复天山北路与吐鲁番之后,左宗棠提出新疆建省的倡议,奏称“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23]650皇帝诏命左宗棠“通盘筹画,妥议具奏”。光绪四年(1878)正月,天山南路平定,左宗棠重提新疆建省之议,认为“事当创始,关系天下大局,非集内外臣工之远猷深算,参考异同,则思虑未周,筹策容多疏误”,奏请下廷臣及各省督抚会议建省之事。[24]5朝廷以为“新疆应否改设行省郡县,事关重大,非熟习该地方情形,难以悬断。此时遽令内外臣工议奏,亦未必确有定见”,[25]仍命左宗棠妥议章程具奏。同年十月,左宗棠再次上奏说明新疆建省的必要性,以及调整新疆兵制、打开利源的具体情形。朝廷以“伊犁未经收还,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为由暂缓新疆建省计划。到光绪六年(1880)四月,左宗棠认为“新疆南北各城频年办理善后事宜,均有端绪”,“分设郡县,于时务相宜”,再次奏请新疆建省并提出具体的建置方案。朝旨仍谓“现在伊犁尚未收复,布置一切,不无窒碍”,[24]476命左宗棠继续筹办新疆善后诸务,建省之议留中再候谕旨。七月,清廷发出上谕,命左宗棠赴京陛见。左宗棠奉旨回京,由刘锦棠接其任,继续办理新疆善后事宜。光绪八年(1882)九月,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复奏请新疆设行省。(15)参看(清)左宗棠:《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36页。其时,伊犁已经收复。新疆各种善后举措均有成效。“设行省,实见时会所趋,舍此不足言治。”[26]218朝廷折衷定议,采纳了设省意见,命刘锦棠办理新疆建省事宜。可以看出,清朝对于新疆建省非常慎重。
刘锦棠在左宗棠的新疆建省方案之上斟酌情形,有所变通,在各地善后局的基础上设县置官,行省规模渐次具备。光绪十年(1884)十月,朝廷颁布上谕,命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任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正式建省。“于是军府之制一变而为郡县之制,监司守令在位咸秩,大小纳职悉主悉臣,自汉唐以来,未有建置若斯之盛也。”[1]498
曾问吾先生盛赞左宗棠、刘锦棠二位疆臣,称“勘定新疆,决策定计,总督军务者为左宗棠,冲锋陷阵,奏功最伟者为刘锦棠。即图谋新疆之长治久安而实行建省亦倡之于左,而成之于刘。是左刘二公,关系于新疆之得失,关系于中国西北塞防之安危,顾不重哉?”[5]245此论不虚。二臣匡危戡难,殚精图治,功不可没。
(四)建省后新疆治理转型
新疆一开行省而气象大变,政制、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政制方面,改军府制为郡县制,设甘肃新疆省,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四道下辖府六、厅八、分防厅二、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设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四道道员皆“以守兼巡为兵备道”,可以调动地方军队。废除伯克制。裁撤各城伯克,以知府、同知、知州、知县等官员代之,旧有伯克选充书吏、乡约。部分地区保留札萨克制。哈密、土尔扈特、和硕特诸札萨克在回乱中忠于朝廷,平乱有功,仍旧世袭爵位,领其封地。吐鲁番则实行改土归流,土地人口分隶于吐鲁番厅、鄯善县。伊犁仍设将军,塔城设参赞。伊犁将军统辖伊犁、塔城旗营以及蒙古、哈萨克部落,节制伊塔道。伊犁将军的权限较从前大有缩减,但“较之内地驻防,其分更崇,其权亦重”。[27]伊犁将军甚至干预伊塔道地方事务,使道员乃至巡抚难以正常行使权力。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曾说:“表面视之,则巡抚有统治全疆之责,而自内容言之,则将军、参赞隐有专理蒙、哈部落之权,人民既判,土地遂分,而政事亦因之阻格,遂有一剖不可复合之势”。[1]1979据学者研究,“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28]
军事方面,新疆驻军改为旗营与标营。旗营有旧满营、新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分驻伊犁、塔城、古城,总统于伊犁将军。内地兵勇经裁撤后编为标营,分抚标(巡抚直辖)、提标(喀什提督管辖)、镇标(阿克苏总兵、巴里坤总兵、伊犁镇管辖)、协标(塔城副将管辖),统由巡抚节制。原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噶尔,统筹南路军队,原喀什噶尔总兵移驻阿克苏,增强地方军事力量。回疆地区军队不再实行换防,改为驻防。新疆收复后,因朝廷财政无力负担军费支出,要求新疆裁兵,刘锦棠主持将标营兵力由五万余减至三万一千。光绪三十年(1904),再次为节饷而大规模裁军,兵力减至一万三千余人。(16)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4-257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军制因行新政、编练新军再次发生变化。三十三年(1907),伊犁将军长庚获准抽调八百名内地新军驻守伊犁,并招募当地壮丁加入,扩编成伊犁混成协,是新疆的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巡抚联魁也整编标营,编练新军,称新疆陆军。这一时期新疆还设立了近代“巡警”,替代巡防营,维护治安。
经济方面,由于“回乱数十年,历道、咸、同三朝,人多流亡,野皆暴骨,屯田蹂躏,荒、熟俱不可考”,[1]587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新疆政务要端。光绪十三年(1887),刘锦棠组织清丈新疆地亩,据统计,“通省南北两路三道属共查丈各等荒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万一百九十四亩四分五厘”。[26]405“南路缠民繁庶,荒地尚属无多,北路镇迪各属,已垦熟地不过十之二三。”[26]394由于天山北路乱后闾阎凋敝而田赋缺额多,刘锦棠制定屯垦政策,(17)规定“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盖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价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以二人为一户,并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斤。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共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初年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展。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征”。参看(清)刘锦棠:《兴办屯垦并安插户口查报隐粮折》,《刘锦棠奏稿·卷十二》,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394页。招徕民人垦荒,并规定每十户派一屯长,五十户派一屯正,“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功及滋事不法诸弊”。[26]394并按照民屯章程,将不愿回原籍的裁汰官兵安置在驻所附近屯田垦荒,既解决其生计问题,又扩大了屯垦规模。天山南路裁撤伯克后,旧有养廉地归官,招佃承租。新疆的农业生产在用心经营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天山北路田赋照旧征收,而南路新设郡县,重新厘定田赋,按地征收,不再抽取丁税,“其未裁伯克廉地,及拨作义学坛庙香火各官地,均科额粮”。(18)北路:“上地每亩科粮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三升,照章概不征耗。”南路:“上地每亩科粮五升四升不等,科草五斤;中地每亩科粮三升,科草三斤;下地每亩科粮一升五合一升不等,科草二斤。耗草不必加征。”参看(清)刘锦棠:《新疆田赋户籍造册咨部立案折》,《刘锦棠奏稿·卷十二》,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405页。为增加财政收入,刘锦棠设置哈密局、古城局,(19)哈密局专收由嘉峪关出口运入新疆的货税,古城局专收由包头归绥走蒙古草地运入新疆的货税。征收外来货税,货价一两,抽取税银三分。官府在各地招派商人开设牙行,征收本地货税,“只收其大宗,零星小贩,一概免征”。[5]260新疆的赋税制度与全国趋向一致,减轻了新疆人口的纳税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为促进新疆各地经济往来,刘锦棠在乌鲁木齐设立宝新局铸钱,将普尔钱作为全疆统一流通的货币。
文化方面,在建省之前,左宗棠提出“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24]466主持兴建义塾三十七处,开启新疆文教。刘锦棠主政后,继续增设义塾,并颁布奖励办法鼓励入学,但效果不彰。《新疆图志》记载:“缠民闻招入学,则皆避匿不往,富者或佣人以代,谓之当差,代官念牌牌子。所遗教习,大都内地游学,随营书识,授以《千字文》《百家姓》,以此授以对字,作八比。缠民茫然不知所谓,愈益厌苦之。师或防其逃逸,闭置室内,加以桎梏,故缠民闻入学,则曰‘凡差皆易,惟此差最难。’其入学数年者,所学亦无用。”[1]695为推行新政,新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提学使,又设劝学所作为提学使下属机构,负责各地兴学事宜,陆续兴办高等学校、两等小学、师范学堂、法政学堂等新式学堂。清末新疆教育文化领域的改革虽然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文教建设,增进了民族交流。
“夫易变者时也,因时而恒变者制也。”[1]454经过历次动乱的巨殇后,清朝决议新疆建省,通过“设行省、改郡县”在政制上推进新疆与内地的治理趋同,提高国家治理的同质化水平,加强国家整合的程度。建省,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进一步完善对新疆治理的需要,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新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新疆图志》论称:“我朝绥服新疆,建军府于伊犁,百余年间,相循未改。方其盛时,连城列郡,拥疆符者十余人,戍塞防秋,转饷常四百数十万。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承平日久,文荒武嬉,复犬羊其民而虐用之,及其既弊,则四肢堕而体解,一厦倾而土崩。天时人事,数穷运剥,往昔军府之制,已如冬葛夏裘之不可复御。于是同光再定,代以郡县,联边腹为一体,袭戎索以华风。盖自汉唐以还,官制之变,至斯而极,长治之基,未有善于此者矣。”[1]454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清代治理新疆的历史,也指出治理的转折在于由军府制转向郡县制,并极赞赏这一官制之变,称“长治之基,未有善于此者矣”。
乾隆朝统一新疆后,清廷延续“藩属屏藩”的边疆策略,将新疆列为藩部,在“众建分势”“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下构建地方政局,形成了以军府制为主导的多元管理体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多元管理体制“重在内治,而非御外,其边防能力自较有限”,当清朝国力强盛时,基本能适应边防需要。但嘉道以降,尤其同光之际,内乱与外患迭起,这种藩部管理体制面对空前的危机便显得力难支绌、穷于应付。清廷在左宗棠等疆臣的支持下及时调整治理策略,由“因俗而治”转向“一道同风”,设立行省,欲以内地之法治新疆,化多元为一元,推进新疆与内地各省的一体化进程。[29]论者指出建省“这一举措,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祖宗成法,在中国边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开启了中国传统疆土观念近代转型之路”,“新疆建省以后,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疆土观念,在日后台湾、东北、蒙藏等地的建省筹划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的版图形态,其意义可谓深远”。[29]
与新疆政治体制的变化相适应,新疆的法律秩序也经历了“复线并行”“多元归一”的转变。军府制时期,新疆的法律运行十分复杂。法律渊源方面,既有国家法,又有习惯法、宗教法;司法实践方面,北路、东路、南路的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建省后,国家统一的法制在新疆得以进一步发展。学者白京兰将这一发展趋势总结为“一体化、中华化、近代化”。(20)参看白京兰:《复线并行与多元归一:新疆法秩序的历史建构》,《克拉玛依学刊》2023年第5期。新时代治疆方略将“依法治疆”置于首位。回望历史,正确认识历史遗产,以清廷经营新疆的得失为镜鉴,实现传统治理资源的创造转化,是推进“依法治疆”的应有之义。古代法制以政制为依托,故而政制研究往往是法制研究的基础。本文的写作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