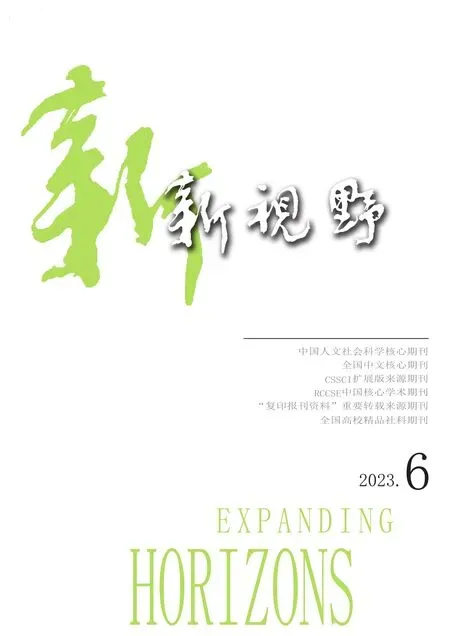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揭示中华文明的意义:以中欧早期互动为中心
2023-02-25张西平
文/张西平 陈 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我们应从长时段的宏大历史发展中,认清中华文明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就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它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通过研究中国与欧洲早期的接触与互动历史,尤其是晚明至清中期(约公元1500—1800年)的交流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在世界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
一 在东方发现文明
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开始作为全球的一个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
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过程也是西方人用刀和火耕种这个世界的过程,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的殖民史开始的历史,拉丁美洲的血管由此被切开,葡萄牙对西非海岸的贩卖黑奴也由此开始。当葡萄牙从印度洋来到中国南海,西班牙从太平洋来到中国近邻菲律宾,中国与欧洲在晚明相遇。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国南海合围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且十分强大的中国,同时中国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开始利用西方人所开启的全球化网络,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与文化。从全球史来看,从晚明至清中期的中西接触中,中国是以独立、强大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在中国与葡萄牙的新会西草湾之战中,葡萄牙船队大败。这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海外扩张过程中第一次遭到的军事挫折,也是近世中国与欧洲人的第一次小规模战争。后来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双歧岛与华人海盗及倭寇勾结,势力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无天,成为“福兴诸府沿海患”。朱纨遂命海道副使沈瀚及把总俞亨率福建兵船对双歧围剿,赶走葡萄牙人,填塞双歧港。这是明军第二次与葡萄牙人交锋。嘉靖28年(1549年)走马溪一战,第三次与葡军交锋,大胜葡军,抓葡人16名、黑奴46名、华人海盗112名,至此“全闵海防,千里肃清。”1554年,葡萄牙船长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口头协议,允许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及附近岛屿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因协助明军消灭海盗,广东镇抚默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1582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两广总督的许可,实行“自治”,澳门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
中西关系在明清之际和在晚清的境遇完全不同,目前许多人一谈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在讲晚清,实际上晚明至清中前期近三百年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时期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绝不是处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相反,晚明至清中前期的“中国看起来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地区一样‘发达’,无论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制造业与市场的复杂程度,还是以消费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3]把明清的中国一概说成是“木乃伊式的国家”完全是对全球化早期的认知偏见。
二 作为世界性货币的白银
中国在晚明至清中前期全面走进世界近代发展的历史舞台,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晚明的币制改革。白银作为明朝的官方货币经历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明朝初年,白银并不是官方货币,它只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使用,学术界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的427件契约的使用通货分析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到嘉靖年间,货币的白银化已成大势。白银的货币化是以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命: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由此白银成为明朝的官方货币。而明代赋役的改革,“一条鞭法”的实施,进一步推动赋役和徭役的货币化,以银折役、以银代赋,白银渗透了晚明生活的方方面面。万明对《万历会计录》的系统整理,从计量史学和数据资料上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白银在明代的货币化可以归纳为五点:“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化;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其三,白银形成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其四,白银形成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白银本位制;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4]
白银怎样成为了世界性货币的呢?当白银成为中国的主币后,对白银的需求大增,但国内的银矿开采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对银的需求,这时只好将目光投向海外。嘉靖年间,倭患猖獗异常,海禁更使得中日贸易受挫,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成为中日之间转口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如利玛窦所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从日本到马六甲之间的诸国,如摩洛加、暹罗、交趾支那等国家而言,澳门都可谓是印度洋上最理想的市场之一……。”[5]这些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将中国的生丝等货物运往日本,日本则以白银购买,澳门的耶稣会士再用白银购买内地的生丝等货物,日本的白银通过澳门流入了中国。据史料记载,“此次航行的船队,所有六艏帆船均在耶稣会之名下,配有已签署的耶稣会徽标,装载86筐,以及13大箱,超过52担28斤优质生丝,其中25担11斤半是在此次日本交易会上购买的,每担价格是白银1167钱,包含运费和关税”。[6]这样的贸易之所以通畅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盛产白银。活跃于日本与中国的耶稣会士罗德里格斯说:“日本国有许多的矿山,出产所有种类的金属。例如大量的铁、铜,此外还出产银、铅、锡和水银的混合物。主要的矿藏是遍布全国的银山……。”[7]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日本的白银矿产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前半期快速发展起来。从1560到1600年,日本每年生产和供应50吨白银。从1600年至1640年,每年生产和供应150吨到190吨,最高峰时的1603年为200吨。在1560至1640年的80年间,日本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8]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中国南海时,并未带来更多可以与中国交换的商品。尚未工业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亚洲的渗透,目的是为欧洲各国买到所需要的以丝绸、棉布和瓷器为核心的亚洲产品,他们通过进入亚洲的贸易来完成这一过程。他们并不是以西方的产品来和亚洲的产品交换,他们只能要么用白银购买,要么用在亚洲贸易网络所得到的钱,购买亚洲的产品。[9]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开的贸易,只是一种转运贸易。他们凭借着中国商品和市场进行中介贸易,一是输入海外物品,其中以白银为主,二是输出中国的货物,以丝绸和瓷器为主。前者因为有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后者则完全依靠中国市场的发展。但这种转口贸易,也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之间的白银流动。所以,“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的重要一翼。”[10]
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另一翼是由来到中国南海的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推动的。1567年随着明朝政府开放海禁,福建商人开始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进行商业往来,中国的商人们运来生丝、棉布和陶瓷等商品,经双方议价以白银为币成交。“1573年,两艘体势巍峨的大帆船,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港驶向美洲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历史上著名的 ‘马尼拉大帆船’航行开始了。”[11]以中国生丝和白银的交换为核心,大帆船贸易开始将中国与世界相连。“大量的中国商品经福建商船从月港载运至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转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一条跨越两洋、连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航线建立起来了:中国(漳州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维拉克鲁斯)—西班牙(塞维利亚)。”[12]
在大帆船贸易中有多少白银流向中国呢?学者统计不太一致,剑桥大学索扎教授认为,从1590年到1644年,菲律宾共输入了美洲白银1.54亿西元(4620吨)。[13]全汉昇先生认为:“在16、17、18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至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西元的时候为多。”[14]有的学者统计出1565—1644年从墨西哥到达马尼拉的大帆船数目大约为132艘,“如果我们估计每艘大帆船平均货值为110万比索的话,则总计为1.45亿比索,约合白银1.05亿两,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中国。”[15]
中国以白银为币进行贸易,直接推动了世界白银的产量。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考证,从1521年到1544年,世界白银(不包括日本及东方各国)的平均产量为90200公斤,而到了16世纪60年代,达到311600公斤,又此后20年,为299500公斤,此后的1581年到1600年,世界白银产量达到封顶,则惊人的420000公斤。[16]在这个意义上,弗兰克所说世界围着白银转,白银围着中国转,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个结论并没有错。
晚明白银的货币化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变,为建立一个以中国白银为中心的世界货币而准备了充足的条件”。[17]因此,晚明社会的变迁并不是由于西方的裹挟而发生,而是晚明自身的变化。当然西人的到来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从而使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同时全球化初期开始以中国的白银作为世界流通货币,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白银作为国家货币存在的问题是铸币权并不在国家手中,而是通过贸易流通从日本和拉美国家获得。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墨西哥的银矿,加之拉美的独立运动,19世纪世界范围的金银减产不仅减少了在中国的白银套汇交易,而且也刺激了鸦片输入。到乾隆时人口的增加,国家广泛使用的国外白银,这成为清帝国的致命伤。“由于英国人没有足够的白银,鸦片被用于交换茶叶和生丝。”从而“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白银问题”。[18]因此,如果说在16—18世纪中国尚可算作世界强国的话,“到19世纪是真正的衰落了。因为作为财富象征的黄金大量流出,白银虽然有所增长,其价值已经大大下降。”[19]因白银而兴,无论明朝还是康乾盛世,但也因白银而亡,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 中学西传:中国知识与文化的西传
公元1500—180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除了以白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外,还有以来华耶稣会士为桥梁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这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形成了中国和欧洲知识与文化的紧密互动,此时期的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与晚清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华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大航海后发现的新知识,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有些知识虽然并非近代新的知识,但作为不同的知识系统对中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秘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曙光说”,侯外庐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提出的“早期启蒙说”,萧箑父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提出的以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接合点说”。[20]在以上学者的论证中,西学东渐受到普遍重视,并作为历史研究立论的根据之一。因此,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不仅提供了新的知识,而且也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关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学术界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这里不再赘述。由来华传教士所推动的“中学西传”是中国与欧洲知识交换的另一重要方面,作为与“西学东渐”相呼应的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是中国文化首次全面在欧洲的展示。这件事与白银资本一起构成了中国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一个是在经济上,一个是在文化上。[21]此时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是哪些呢?
第一, 关于中国历史。早期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就有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例如,皮雷斯的《东方概要》到克鲁斯的《中国概说》等各类游记。但真正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的是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书将一个富饶、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在当时已经称霸全球的西班牙人,看到中国如此庞大的文明体,惊叹不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把16世纪的中国向西方作了最客观、最全面的介绍,也体现了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22]耶稣会士入华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和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开启了17世纪欧洲汉学。特别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把一个远比基督教文明悠久得多的中国历代年表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它所引起的争论甚嚣尘上,直到法国人杜赫德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的出版,欧洲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达到了高潮。如伏尔泰所说:“杜赫德虽然不曾走出巴黎,不认识一个汉字,但是,他借助教会同僚们所撰写的相关报道,编纂了一部内容最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佳作,堪称举世无双。”[23]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其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文明不仅使当时的基督教文明相形见绌,同时也提供给了启蒙思想家瓦解基督教历史观的有力武器。
第二, 关于中国社会管理。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家的管理体系采取的是中央集权之下的郡县制,而不是贵族分封制。同时,中国科举制度被详尽介绍到欧洲。来华的耶稣会在中国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这样的管理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欧洲是没有的。利玛窦详尽解释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指出:“那些执掌国家大权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举人和进士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的……他们做官不靠任何人的恩惠与情面,不要说官员,就连皇帝讲情也无济于事。”“这是区别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形式。”[24]几乎所有来华耶稣会的汉学著作都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的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办法给予了高度赞扬。托克维尔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曾说,大革命就是“在各自领域努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融合不同等级,使不同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用官吏取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25]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感兴趣应该是很自然的。
第三, 儒家典籍的翻译。一开始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例如柏应理返回法国后,在法王路易十四支持下所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是第一次将儒家原典翻译成拉丁文。内容包括:柏应理所写的《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初序》、 殷铎泽所作《孔子传》并附孔子像、《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全译本、柏应理所作的《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和《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并附柏应理绘制的中国地图。这部书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欧洲学者奉为启蒙运动时的经典著作。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收录了“四书”以及《孝经》《小学》的全部拉丁译文。法国来华耶稣会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已经成为一项严肃的汉学研究。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中国典籍的翻译成为其重要的内容:包括朱熹论著选译、《易经》选译、《书经》选译、《诗经》选译、《春秋》选译、《礼记》选译、孔子传选译、《大学》选译、《中庸》选译、《论语》选译、《孟子》选译、《孝经》选译、《小学》选译、《康熙帝御选朱批历代敕、诏、法、令、谏、言集》选译、《明代著名文人唐荆川所编文集选》《列女传》、二程哲学选译、理学著作选译等。
儒家哲学传入欧洲给启蒙思想家一个可以用自然神学来解释世界的例子。因为孔子不具有人格神的特点,但他同时又有宗教性关怀的特点,孔子的思想特别适合欧洲从启示神学向自然神学转型的思想潮流。伏尔泰谈到孔子时说:“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他只是作为贤者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26]孔子的学说就是教导人们掌握理性,认识自然。而且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倾向,回答了人“远神”后世俗生活的精神价值。这些思想自然引起启蒙思想家们的关注。特别是后期宋明理学提出的核心思想“理”,以及整个学说中的理性精神都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引起他们思想的共鸣。
第四,中国的文学艺术与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的小说、戏剧此时也被翻译成法文,例如《今古奇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观:六月雪》《赵氏孤儿》。伏尔泰读后很受触动,编写了自己的《中国孤儿》。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篇》开启了华乐西传,卜弥格对《本草纲目》的翻译、对王叔和《脉经》的翻译开启了中医西传,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学史》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智慧。根据王致诚关于圆明园建筑的介绍,英国人钱伯斯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计》,向欧洲展示了东方园林与建筑美学。这些逐步在欧洲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在罗可可时代的心里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不仅是艺术方面,就是在智慧方面也然。在这个世纪初,所谓中国货,如图书、花瓶、雕刻、墙纸、漆器、丝绒等东方物品大为流行,盛极一时。小说中宣传中国的情形,至于使读者们各个都憧憬于神话式的理性国之中……”[27]
中国典籍的西译,中国知识的西传从文献上证实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从思想上展现了东亚文明的独特性,从文化上证明了东方的多彩与丰富,乃至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认为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而在中国发现的是文明。中国的知识与文化开始成为推动欧洲思想文化变迁的力量。
四 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晚明到清中前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以晚清的中西关系推测晚明和清中前期的中西关系是对历史的无知。此时的中国非但不是闭关锁国,更谈不上落后愚昧。晚明经济的发展推动白银从民间货币变为国家货币,白银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初期具有世界性的货币。因为此时的西方各国拿不出可以与中国交换的货物与产品,只能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中国产品流通世界。即便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也拿不出产品与中国交换,这成为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此时中国的发展并非来自西方的推动,而是原生型的、内在发展的结果。西方提供了一个逐渐完善的世界舞台,二者结合使晚明至清中期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明清鼎革并未终止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脚步,此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的重要桥梁。清朝早期的外交事业是在与国际互动中展开的,《恰克图条约》的签署解决了中俄贸易问题,《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边界冲突问题,铎罗与嘉乐的来华则是康熙试图解决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宗教冲突问题。此时的“西学东渐”开拓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文化视野,天主教在康熙时期的合法化是中华文明第二次接纳外来文明的确证,尽管雍乾百年禁教,但西学东渐已成大势,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前行。[28]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从16世纪到18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是逐步丰富起来的,从最初的道听途说到以后的亲身经历,从一般的传教士到后来法国来华的科学家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在逐步深入。经过他们的介绍,一个比欧洲各国历史还要悠久的中国呈现在欧洲读者面前,一个社会生活比欧洲还要多彩的中国吸引了欧洲的读者。而当启蒙思想家们读到传教士所翻译的那些中国典籍时,他们被打动了,从伏尔泰到莱布尼茨,从魁奈到沃尔夫,即便有孟德斯鸠这样的批评者,但中华文明的悠久与制度之完善也使他对中国的评价无法协调起来。18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欧洲中国热,绝非空穴来风,它是中国知识与文化传入欧洲二百年的积累的必然结果。“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29]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使命的风尚。中国知识与文化的传入催生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对一般民众而言只是对东方的好奇,但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来说,无论是赞扬还是反对,中国的知识所包含的智慧与思想还是启迪了启蒙思想家。17世纪欧洲仍笼罩在《圣经》的神学思想之下,18世纪欧洲才出现有关地球的自然历史论,19世纪西方才出现人类和动物同属一个自然王国的概念。[30]而中国思想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对人类世俗化生活的系统论述使人耳目一新;唐朝以前中国人并不知道基督教创世神话的史实瓦解了基督教教义的普适性,中国历史年表的真实与可靠,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观。所有这些不仅在知识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为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提供了另一种文明类型,撼动了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文化。
因此,晚明至清中期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与思想在欧洲的影响是人类文明互鉴的经典历史事件。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用后现代史学否认这一时期传入欧洲知识的真实性,用“误读”来消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任何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是从自身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的,任何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都会根据自身文化所需对外来文化进行加工和改造,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但不能因为接受者对知识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对异文化的“误读”,就否认知识在传播中的真实性。同样,不能因传播者在传播知识时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对其所传播的知识附上主观色彩,就完全否认了所传播知识的真实性。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立场忽视了知识传播中接受主体自身的文化背景对知识传播和接受的影响,并且将文化之间的交流、知识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完全简缩为一个主体自身文化背景问题,将丰富的历史过程仅仅压缩为主体自己的文化理解问题。这样也就“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显然,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的。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对全球的殖民与掠夺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开始领先于中国,中国晚清后的衰落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大反转。在赫尔德那里中国只“是一具木乃伊”,在黑格尔那里,孔子毫无智慧,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度。欧洲中心主义开始盛行,16—18世纪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西方的历史教科书中已经消失。今天我们讲述晚明至清中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和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并非沉醉于往日的荣光,而是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仍有人把欧美文化说成是一个“自我成圣”的文化,外来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不足为道。这不仅在知识上不符合历史,也反映出了这种观点对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的错误迷恋,对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观念的盲目崇拜。
中国知识与文化的西传是16—18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表现。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无法揭示出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现代性意义。
五 结 语
明清之际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揭示了近300年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说明,随着白银成为国家货币,中国走上了近代化之路,这种近代化是中国内生性演化而产生的。同时通过白银在世界的流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中心。同时,17—18世纪的中学西传,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段历史为我们从文明互鉴考察中西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31]
百年弹指一挥间,确立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重新思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在全球史和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下重新确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