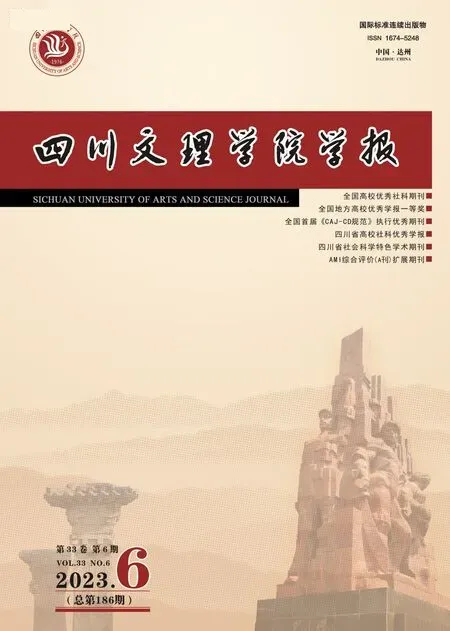忠实的抵抗
——吕叔湘翻译诗学研究
2023-02-24毛逸菲
林 忠,毛逸菲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翻译诗学发轫于亚里士多德诗学思想,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思想,当下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1]早期翻译诗学将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包含于翻译理论之内;[2]后现代主义翻译诗学[3]以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特性关照“跨学科交叉研究”,[4]不断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吕叔湘(1904-1998)是中国知名语言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5][6][7][8]他“并臻信达兼今雅,译事群钦夙擅场”(叶圣陶语)的译品、深邃的翻译思想、独到的翻译方法无疑具有研究价值与必要。然学界目前关注不够。
鉴于此,本文从后现代翻译诗学视角切入,聚焦文本内部特征和价值,解析吕叔湘文学译作与诗学策略,从忠实性、读者接受、自主权、译者发声四大议题挖掘吕译品的诗学魅力及译者个人的翻译诗学观。文中分析材料主要来自1981 年和2002 年版《我叫阿拉木》吕译本,限于篇幅不一一标注。
一、后直译主义的忠实保全
诗学路径下的翻译呼唤忠实与直译主义割席。直译主义奉字对字为信条,规避复杂与差异,其“模仿臆说”(mimetic assumptions)在文学翻译对独到、灵动的呼唤中走向失能,[9]18“完美的可译”及“完全的忠实”云云冰消瓦解。[9]42吕叔湘的译作规避直译,“用地道的汉语曲尽原文之妙”,[10]161-162堪称再现原文意蕴、精神与美质的典范。
吕叔湘曾表示:“以原则言,从事翻译者于原文不容有一词一语之误解”。[11]1英汉语言差异造成的翻译张力(translational tension),会迫使译者以文本化和语境化靠近(textualized and contextualized approximation)的形式将原文的意义积寸累尺地转渡到译文中。[12]对此,吕叔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主张翻译并非是对原作的机械复制,反对一刀切地“把hydrogen 翻成‘氢’,把oxygen
翻成‘氧’”的“翻译化学元素”式的译法,[13]31认为“逐字转译,亦有类乎胶柱鼓瑟”。[11]11可以说,他所主张的忠实绝不以实现“纯粹直译的‘他者’”(absolute literalist“other”)为目标,[9]37而意在传达衍生出“诗学意义”(poetic significance)的词语内涵。[14]21请看以下译例:
(1)It was the most modulated howl I ever howled; because it was the easiest strapping I ever got.
这是我叫唤过的最有分寸的叫唤;因为这是我挨过的最好挨的鞭子。
此例描写了主人公阿拉木因屡次逃课去马戏班而被先生鞭打时的内心活动。原文看似简单的词语却不乏幽默与内涵,不经意间便将一个古灵精怪的顽童形象刻画了出来。在该句中,吕先生选用“分寸”和“好挨”译划线部分的“modulated”和“easiest”两词,可谓突发奇想而又恰到好处。他并不拘泥于词语的字面意义,将其笼统译为“调节”“容易”,而是在剖辨原文的基础上,发挥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仔细推敲选词,使人物调皮捣蛋的孩子气跃然纸上,极能传神达意。吕先生将彻底了解原文和充分掌握本国语文视作胜任翻译工作的必要条件。[15]202的确,以臻于完美的语言功夫和对原作内涵的精准把控为依托,吕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忠实严谨的译者风范。
其次,除稳妥传递原文意义之外,译文对原作风格的移植也不容忽视。在吕叔湘看来,“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思”与“尽量保存原作的风格和精神”应当两全。[16]180吕先生译介的作品展现的多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片段,因此语言平白朴素,贴近生活,其中不乏方言土话。为重建原文本鲜明的语言风格,吕叔湘在翻译时运用大量地道汉语,无论是儿化词、方言,还是其他口语词,皆信手拈来,使译文明快上口,恰似原文。现举一例:
(2)These strength, he said in English which he liked to affect when speaking to me, ease from God. I tell you, Aram, eat ease wonderful.
I told him I couldn’t begin to become the powerful man I had decided to become until I sent Mr. Strongfort some money.
Mohney! my uncle said with contempt. I tell you, Aram, mohney is naathing. You cannot bribe God.
“者个力量,”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爱用他的破烂美国话,他说,“者个力量世赏帝那里来的。我对你朔,阿拉木,者个真伟大。”
我告诉他,我立志要变个大力士,可是非先寄点钱给强如狮先生,没法儿开始变化。
“纤?”我的叔叔满脸瞧不起这个东西,他说,“纤没有舍么用,赏帝世不受运动的。”
这是阿拉木和叔叔吉科之间的对话。原文叙述者吉科的英语使用有许多不规范之处,如ease(is),eat ease(it is),mohney(money), naathing(nothing)等。在译文中,吕叔湘采用同样不标准的汉语以保存原作对话的语言特色,比如“者个”(这个)、“世”(是)、“纤”(钱)。此外依旧使用地道的汉语口语(“满脸瞧不起”)以及儿化音(“没法儿”),在词汇和语气上贴合原文情景,惟妙惟肖地再造了原文本生活化、口语化的风格,诚如吕先生自己所言:“好的翻译应当是不但是把意思翻对了,并且把语气也译出来”。[17]332
最后,美是文学作品共同的艺术追求,译者同样肩负着继承原文美质的使命。茅盾指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18]1巴恩斯通在其著中也谈到,忠实不仅对字面意义负有责任,更对文字美感有所亏欠。[9]可以说,在文学翻译中,审美的再现是衡量译者忠实的关键标准。吕叔湘文学素养高雅,审美眼力敏锐,他虽谦虚地表示自己译著的读物只能够得上“文学”二字,但叶圣陶却评价吕译“译者的文笔也大可称美”。[19]52例如:
(3)In the spring of the year the water hurried, and with it the heart, but as the fields changed from green to brown, the blossoms to fruit, the shy warmth to arrogant heat, the ditch-es slowed down and the heart grew lazy.
春天一到,河里的水涌了起来,人的心也跳了起来;到了田里绿变做黄,树上花结成果,煦日化为骄阳的时候,河里的水就慢了下来,人的心也就懒了下来。
四字格的使用是吕译文的一大特色,四字结构音韵和谐、体现了汉语语法的对言特质。[20]落脚于中国语言这一本质,吕叔湘将清新自然的原文翻译为同样富于美质、引人入胜的汉语。此译中,他以一组对仗工整的四言格“绿变做黄、花结成果”处理原文中的平行结构,保持了原作语言的形式与节奏美,重现了其诗学语言特征。此外,译文中其他“四字组”的使用同样可圈可点,从“涌了起来”到“跳了起来”,从“慢了下来”到“懒了下来”,无不妥帖恰当,优美动人,在给读者带来极大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彰显出吕叔湘艺术家的手腕和译者的功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足以品味出吕译作既遣词精妙、传达原文内涵,语气逼肖、再现原作风格,又行云流水、保留原文美质,着实达到了他自己对诗歌等文学作品翻译的要求:“原诗的精神——诗中大意和所含的感情——非用心体贴,忠实表达不可”。[21]601
二、阐释学框架下读者接受的考量
诗学的笔触将翻译描画为一个“诠释过程”(hermeneutical process),[9]21即阅读和解释。实际上,这一论断与“读者接受理论”互为表里。因为无论是在阅读还是在翻译中,总是存在某种“艺术伙伴关系”(artistic partnership),读者占据其中一方,经由“解释性的阅读”(interpretive readings)或洋溢着想象力的翻译,取得与作者同等的“合著”(co-authors)身份。[9]21-22而译者作为原文本与译语读者间的斡旋人,需要将读者在文本生成中的操纵纳入考量,以促成“读者-文本邂逅”(reader-text encounters),[9]24从而使译文顺利融入目标语文学宝库,在新的语境下焕发生命。
细读吕先生的译文,我们便能发现熟谙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他,在翻译过程中灵活变通,对原文文化信息进行调整,兼顾意义传达与读者观照。譬如,他将原文中基督教色彩浓重的词汇“Bible text”和“ungodly mess”译为“施善书”和“不仁不义的糊涂事”,使用佛教用语“功德圆满”表达“a good workout”,采用道教词汇“入静”和“丹方”翻译原文中的“meditating”以及“dope”。此种以译入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契合读者的心理认知与取向,极大增强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亲近感。再有,吕叔湘不把“one-sided”直译为“一边倒的”或“单方面的”,也未将“free-for-all”译作“不加管制”或“自由放任”,而是分别使用“剃头担子一头热”和“格杀不论”进行归化处理,使译文透出浓浓的中国味儿,利于异语文学作品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的接受与传播。
这种在原作与译作间寻求平衡,将翻译置于目标语文化脉络之中的归化策略避免了目标语读者的抵触心理,有效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度。进一步而言,吕先生对原文信息进行的文化“转码”不仅体现了他心怀读者,向读者期待靠拢的责任感,也浸透着当年翻译工作者们维护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民族本位立场——“像吕先生这样生于世纪之交,而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坚定不移的人生‘使命感’,服膺中国旧道德的优良传统,而又把文化看作一种几乎是终极的信仰”。[22]543
三、再创造目标下的译者自主
当诗学理论将翻译与“精湛的再创造”(masterly re-creation)划上等号时,[9]88对译者以及翻译“实质上的自主权、艺术性及独创性”视而不见无疑不是明智之举。[9]5所谓的“译者-创造者”在朝着“再创造翻译”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中或增、或删、或改的种种技巧决定了翻译的质量。[9]45身为巴氏笔下的“自主合著者”(autonomous co-author),[9]105吕叔湘认为译事不能不有变通,而“未尝以辞害意,为译人应有之自由”。[11]17直面中英文字的扞格,触及抵抗与试炼的“创造性张力”(creative tension),[12]49吕先生全方位、多角度行使译者自主权,护送译出语安稳地抵达译入语,其中,变换句式结构是典型的一类:
(4)That was the thing that had kind of kept me sleeping after four-thirty in the morning when by rights I should have been up and dressing and on my way to the trains.
就因这一念,四点三十分的时候,按说我应该已经爬起来,穿衣服,上火车站,却糊糊涂涂的又睡下去了。
(5)Pandro Kolkhozian, on the one hand,seemed to be the most uncouth boy in the world and on the other—and this was the quality in him which endeared him to me—the most courteous and thoughtful.
旁德罗这个孩子,从一方面看,是世界上最野的孩子,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最有礼貌最能体贴人的孩子,我就爱他这一点。
在句法方面,汉英各有其特质与规律。概言之,英语以主谓结构为本,叠床架屋;汉语以对言为本,重视“结构平行性”。[23]吕先生是语法家,对于中英文各种句法之别,他都有深刻的认识,反映在翻译实践中便是绝不削足适履,强迫译语死守源语规律。在上列两例中,原文皆为典型的英式复合长句,句内以从句嵌套,以连接词衔接,注重以形显义。
吕叔湘发挥译者自主,对原文进行操纵还体现在人名的翻译上,以《五部独幕剧》汉译本为例,Armstrong 译作“安”姓、Johns 译为“钟”姓、I was a Sheffield 译作“我是薛家的姑娘”、I was a Thompson 译为“我娘家姓棠”、Brownlow 译作“白朗劳”、Snaith 译为“史耐思”。在吕译《我叫阿拉木》中,Sampson 译“沈普生”、Lionel Strongfort 译“强如狮”、Steve Hertwig 译“何德威”。诗学视阈下,对人名及地名的改写是颠覆人物出身的有效手段,以此方式,翻译或将逐渐脱离于原文,最终在其经典化的进程中呈现出可与原作匹敌,甚至能取其而代之的创作权威。例如在早期的圣经翻译中,基督徒译者为抹去耶稣的“犹太性”,将希腊语中耶稣的称谓“Rabbi”(拉比,指犹太教经师或神职人员)译为“Master”,从而赋予基督教圣经无可争议的独创性。在上述译例中,我们同样可以领略到吕叔湘对人名进行改写的高超技艺,Armstrong 不再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而摇身一变成了“安”家的女儿,更有“强如狮”这样颇有亮点,令人拍案叫绝的译文。无需多言,借由对人名的操纵,吕叔湘创造性地改变了原作人物的本来身份,向译文输入了“尊严、权威和自主性”(dignity,authority,and autonomy)。[9]104
吕叔湘在翻译中尊重原作但不受制于原作,灵活运用句式结构变换以及人名改写等技巧,形塑出斯坦纳所说的“忠实但自主的重述”(faithful but autonomous restatement)。[9]26这就不难理解,黄懋颐(1985)要将五部独幕剧的译文誉为“艺术的再创造”,并感叹“在创造性的翻译中,在运用语言方面,吕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24]35
四、作者身份让渡后的译者发声
在诗学维度下,任何作者在其他语言中的生存取决于“作者身份的模糊”(blurring of authorships),即原作单一所有权向另一作者——译者——的部分出让。[9]106当译者郑重地接过作者身份,他会以自身的信念、知识、身份、选择等注入译文文本,从而产生“中心偏移”(Led centrement),[2]此时“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文中得到了持续的、最新的、最繁盛的开放”,[9]17原文就“失去作者灵性”等待“译者的救赎、等待生命的延续”。[25]80总而言之,译者为自己发声在作者身份让渡后取得了合理性、有效性,他的主体意识及能动作用对文本的重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吕先生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选择与参与恰恰源于他身兼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的多重身份,来自于其特殊多重身份赋予的学术精神和人文关怀。着眼至关键的译中阶段,他所采取的诗学策略则是大量加注。译注,即译者注,属副文本范畴,折射出“译者对翻译、对原作文化的态度以及翻译活动如何受制于特定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26]78在《翻译诗学》中,巴恩斯通提到加注释是一种通过支配解读从而改变文本的有效方式,具有将语言表层意义转变为注解者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9]吕叔湘认为,“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但要注意“注释必须正确,否则宁可阙疑”。[15]205根据笔者统计,在1981 年再版的《我叫阿拉木》汉译本中,吕叔湘作注共698 条;在《英汉对照吕叔湘译文三种》中,译者注长达52 页,共计2356 条(其中《伊坦·弗洛美》81 条,《五个独幕剧》1475条,《跟父亲一块儿过日子》800 条)。这些译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丰富,涵盖语言、文化、文学常识、历史背景等,不仅能帮助读者全面细致地了解作品,也为专业研究如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等提供了学术参照。试举《我叫阿拉木》再版本为例,全书译注内容包括:1. 意义注解;2. 语法规律;3. 补充说明;4. 习惯用法;更有些注释涉及多种类目,如意义注解兼语法规律,意义注解兼习惯用法等。
作为译者发声之见证,吕叔湘的译注涵盖丰富的学科知识,既通俗易懂,又不乏科学的严谨。钱定平深感“从学英语的角度说,最主要是吕先生的注解写得极好,文字简练而解释精当”;[22]529夹杂着注解的精美译文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能够使读者“在一种‘如坐春风’的心情氛围之中学习英语”。[9]528由此可见,在作者身份界限模糊之阶段,译者吕叔湘向源语语篇输入个人态度、立场、意识后,译文跳脱出按部就班的语言符号置换,转而指向新的价值和功用。如此翻译不会遮蔽原作的光芒,而是在原作与译作的混合融汇中,原作者与译者的互动得以圆满,译者借助“双重艺术”(double art)创造出新的作品。[9]88至此,我们有理由说,以翻译为跳板,译者实现了与原作者“作者身份的恒久结合”,[9]103译者的诗学之声将在原作的来世得以传递、回响、永存。
结 语
纵然吕叔湘关于翻译的论述算不上宏富,但是,追随他的翻译足迹,梳理他的翻译文字,我们足以领会到,吕先生对内容之真与诗学之美的双重顾全,对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关系的处理,对“忠实”与“抵抗”“创造”之间张力的把握,无不与翻译诗学的精神实质相吻合。故而,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吕先生的翻译诗学进行深度阐发,以顺应当下翻译研究方法注重学科交叉性的趋势。与此同时,文章将重点放至译文自身的诗学分析及译者个人诗学在翻译文本中的体现,是对翻译本体研究的靠拢与回归,不仅避免了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仅作为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佐证而存在”,还避免了翻译学科“消融在政治学与文化学之中,并成为它们的附庸”的风险。[27]56
最后提及一点,从吕叔湘文学译作中挖掘出的译者策略、诗学态度、人文情怀不仅有助于我们越过时间藩篱,了解特定年代的翻译风尚、诗学语境和译者角色,更能为今天翻译研究涌现出的新问题贡献思路与样本,譬如翻译与语言的生长和革新、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解决“翻译腔”与“外语性”间的冲突等等。[28]总之,身处新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我们有必要拓宽视野,不能“眼光只局限于身份或性质明显的翻译家或翻译事件上”,[29]5而应加大关注以吕叔湘为代表的更多多重身份的学术鸿儒,在“翻译与传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译者翻译思想。”[30]从更丰富、更前沿的视角研究其翻译成果,从而为建设凝聚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力量的译论体系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