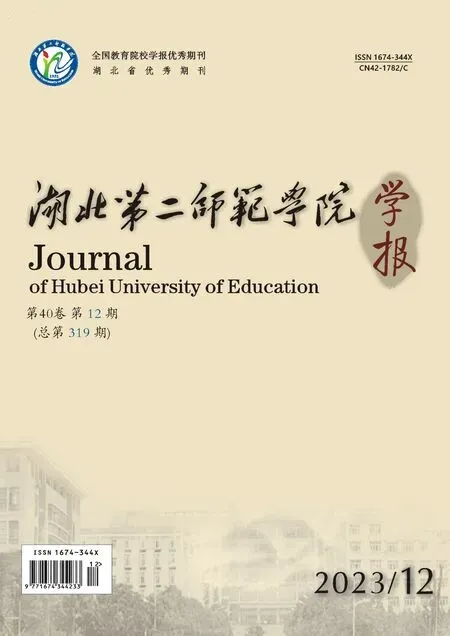论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文化隐喻与生命关照
——基于清江流域的人类学考察
2023-02-23蒋晓玲孙文波兰润生
蒋晓玲,孙文波,兰润生
(1.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上海体育学院 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
生与死,始终是人类要面临的永恒主题。在人类对自身生命存在形式和意义的无尽探索中,不同时空下的人类群体分别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关于生与死的观念,这些观念或存在于成体系的科学知识系统,或杂糅于客观记忆与主观臆想的神话、传说以及信仰体系等之中。[1]尤其是在原始农耕社会,各民族基于这些体系在对生命的探索中创造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仪式性强的礼乐文化以表征其生死观念,化为延续族群生命记忆、表达生命精神诉求和凝聚生命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并伴随着历史更迭,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于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就是这样一种蕴含丰富仪式象征和深厚文化隐喻的生命关照仪式。撒尔嗬仪式内聚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基因,它通过歌舞狂欢仪式实现土家人祭奠死者和关照生者的象征性交换,体现出清江流域土家人以喜寄哀的豁达生死观。这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的赓续,还是中华民族生死观多样性的独特表征,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存在形式和意义无尽探索中的一朵奇葩。因而,深入挖掘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的文化内涵,解读其独特的生死观念,既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利于强化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和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一、“敬”亡“亲”生的撒尔嗬仪式
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内聚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基因,以礼“敬”亡者而以乐“亲”生者文化表征仪式,它是一种以礼“敬”亡者而以乐“亲”生者的人生之礼,体现了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还表现出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生命的高度礼赞。
(一)撒尔嗬仪式中的礼乐文化基因
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一种祭奠亡者,安慰生者时高歌狂舞的特殊情感表达方式。[2]这句话向我们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一种祭奠亡灵的仪式,二是清江流域土家人祭奠亡灵的仪式也是安慰生者的高歌狂舞仪式。若将其放入中国礼乐场域中,祭奠亡灵的仪式是为礼,高歌狂舞是为乐,则撒尔嗬是以礼“敬”亡者而以乐“亲”生者的土家族文化表征仪式,它诠释了中国礼乐文化使人相亲爱、使尊卑有序的功用。之所以有此言,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可称为礼乐文明,文化称为礼乐文化,礼主要指人行为的雅化、典礼艺术和礼仪,乐则指涉诗、乐、舞。[3]李泽厚也认为,中国之礼源于“巫”,各种巫术活动经过理性化,便成为了和合氏族、规范族群、维持生存、表达情感,以及对自我生命、存在与神同一的肯定的巫术礼仪,这些巫术礼仪通常伴随着乐,尤其是巫舞等舞蹈活动。[4]
在美学视域下,以礼乐为标识的美学传统的确是中华民族极具奠基性的文化基因。在传统中国文化生态中,礼与乐经常是相生相伴的,如《乐书》中说:“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等。[5]由此可见,中国之礼乐文化不仅与传统道德观念、社会伦理息息相关,还与祭祀之事紧密相连。质言之,礼乐融于传统先民的各项文化表征仪式之中。《乐书》还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5]可见,乐表亲,礼主敬,中国礼乐文化正有使人相亲相爱、使尊卑有序之功用。流传于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撒尔嗬即为这样一种内聚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基因,以礼“敬”亡者而以乐“亲”生者文化表征仪式。
(二)以礼“敬”亡者
所谓以礼“敬”亡者,指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最为重要的人生礼仪中的丧礼,土家人通过撒尔嗬与死去长者告别并表达尊敬与缅怀之情,它不仅具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深刻文化内涵,还具有无限延续的缅怀意义和祈福意义,对于清江流域土家族的生存繁衍具有极大的心理支撑作用。“礼”与“敬”都源于“巫”。巫术礼仪即将巫术力量演化为巫术品德的仪式,巫术品德最终内化为氏族首领的个体品德力量,其外在表现便为“敬”与“礼”。“敬”即敬畏,包括恐惧、崇拜、敬仰等多种心理情感。“礼”即从原始巫术活动演化而来的与族群极为重要的行为、活动等一整套仪式规范。[4]显然,以礼“敬”亡者即为通过撒尔嗬这种礼仪表达对死去长者和祖先的敬仰,撒尔嗬与清江流域土家族的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极为密切,是清江流域土家人敬仰祖先的礼节。
研究表明,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氏族繁衍、祭奠始祖廪君的摹拟巫术。相传清江流域的土家人是上古巴氏的一支,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清同治年间《恩施县志》等古籍的记载,以及相关学者如王善才[6]、宫哲兵[7]等学者的考证和廪君、白虎崇拜在土司文化中的遗存可以确定,清江流域的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实为一体,白虎图腾即廪君所化。这则神话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巴志》、清同治年间的《恩施县志》中均有记载,称通过“石穴掷剑”“乘土船能浮”等考验,共立巴氏之子务相为廪君,带领土家先民生存,后来“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8]。撒尔嗬就是根据祀廪君的仪式演变而来,据“《夔牛图经》载:‘巴人尚武,击鼓踏歌以兴衰。……父母初丧,击鼓以道哀,其歌必狂,其众必跳,此乃白虎之勇也。’《归州府志》曰:‘巴人好踏蹄,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衰。’《湖北通志·舆地志》说:‘巴人好歌,名踏白虎事’。这些古籍中提到的鼓舞即为撒尔嗬,因此撒尔嗬又名打丧鼓”[9]。由此可见,撒尔嗬是杂糅于清江流域土家族信仰崇拜体系之中的一种祭祀之礼,如撒尔嗬中的动作“猛虎下山”“虎抱头”等就是摹拟白虎的各种形态以表达对廪君化为白虎图腾的崇敬。另一方面,在撒尔嗬仪式中还表达着清江流域土家族尊敬长者和行孝的民族心理。据访谈对象称:
“在过去啊,虽然所有人去世后都会举行丧葬仪式,但可不是在所有葬礼上都能跳撒尔嗬的。只有那些‘走顺头路’(即寿终正寝)的德高望重的人老了(在土家人语言体系中,‘老了人’即为有老人去世了的意思)才会跳撒尔嗬。这种丧葬仪式越热闹越好,否则外人就会指责其子不孝,所以这种葬礼热闹与否也就成为了衡量其子尽孝的尺度”。
由此可见,“敬老”与“行孝”是清江流域土家人内在的个人品德。撒尔嗬仪式演化了这种品德,并将其与土家族的社会规范、秩序、行为等杂糅在一起,成为族群礼数,并通过这种礼数强化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祖先和长者的崇敬之心。
(三)以乐“亲”生者
撒尔嗬仪式在以礼“敬”亡者的同时还以乐“亲”生者,表现出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生命的高度礼赞。上述有观点认为,礼指人行为的雅化、典礼艺术和礼仪,乐则指涉诗、乐、舞。撒尔嗬仪式的内容完全由诗、乐、舞三者构成。
首先,撒尔嗬仪式中的唱词内容丰富,但多以诗句构成,如“歌郎送出门,庄子返天庭,亡者安葬后,孝眷万年兴”“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生命尽总难逃,纵有精神也不牢。犹如梅花遭雪打,恰似嫩花被风摇”等,也许这些词的章句比较通俗,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诗的形态和诗的韵律吟唱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尽管当代许多唱词几经演化出了现代唱词的风格,但不可否认撒尔嗬的唱词蕴含诗的文化基因。
其次,从古籍与当代撒尔嗬的形式可以看出,撒尔嗬仪式蕴含丰富的音乐元素,古籍中记载的“击鼓踏歌”“伐鼓”“巴人好歌”的音乐形式一直延续到当代。当代长阳、巴东、恩施等地的撒尔嗬仍保留着专业人士敲锣打鼓、余者随鼓点而歌而舞的形式。而且撒尔嗬的音乐内容丰富,不仅有歌唱神话创世的《盘古出世》和《姊妹相合生后人》,还有歌唱男女爱情的《相思歌》《探郎》,以及歌唱先祖的《侍师》《摇丧》等等诸多内容。
最后,原始巫术总伴随着舞蹈,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的舞蹈内容也独具特色。它们的动作多以摹拟动物的形态为主,如牛擦痒、鹭鸳伸腿、白鹤展翅、犀牛望月、猛虎下山等,这些舞姿粗犷古朴,极富感染力和生命力。正如《乐书》所言:“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于人心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5]。乐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需求,体现的是生者的感悟,而乐又表亲,使人相亲相爱。清江流域土家人感于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感于礼敬亡者的仪式,其表达的是生者的情感需求和生命感悟,其目的在于通过撒尔嗬仪式中的乐,使氏族繁衍生息、相亲相爱。由此观之,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礼乐文化的表征仪式,尽管它以礼“敬”亡者,但其最终目的在于以乐“亲”生者,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是对生命的礼赞,它蕴含了清江流域土家人独特的生命关照。
二、撒尔嗬仪式的文化隐喻:生与死的象征交换
撒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礼乐文化的表征仪式,它通过对亡者的礼敬表达对生者的关照。可以说,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的本体意义在于生与死的象征性交换,其仪式中对丧的歌唱表征了清江流域土家族独特的豁达生命观,对丧的舞蹈又是死者“寄身”的神圣体验。
(一)撒尔嗬的本体意义:生死交换的仪式
清江流域撒尔嗬仪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本来表达悲伤的丧葬仪式中用极度欢快的形式同时体现了对亡者的礼敬和对生者的关照,因而传递出清江流域土家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别具一格的生死观。从海德格尔生命哲学的视域而言,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象征着人类生死观上的一次转化,它将个体的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群体的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和高度礼赞,因而可以说它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的一种生与死的象征性交换仪式。从清江流域撒尔嗬仪式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体现的是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生与死的独特认识。清江流域土家人认为,寿终正寝的老人的灵魂并没有灭亡,生命永恒存在,生与死只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的交换。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结,同样也是新生命的伊始。因此对待死亡应该是欢乐的,正如迎接人的新生一样,是喜事,所以办丧事就要欢欢喜喜,高歌狂舞,甚至打破世俗禁忌体现男欢女爱的生命追求。撒尔嗬仪式实质上完成了礼赞生命、迎接新生的一种特殊礼敬仪式。
从象征的角度而言,这种仪式的目的不是要消除死亡,也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在社会关系上连接死亡,亡者并未真正消逝在族群中,而是进入先祖的场域,在社会关系上仍连接着族群。因此在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生与死并非对立存在,生与死可以通过仪式的形式实现象征性交换。“在象征层面上,生者和死者没有区别。死者只不过是具有另一种身份罢了,象征终结了生与死的分离,它是终结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真实与非真实、出生与死亡之邦的乌托邦”[10]。因此,在清江流域土家族中有老人寿终正寝后,其族人总是热热闹闹办丧事,合族不悲,哀而不丧,甚至狂歌热舞,狂热与肃穆庄严不显冲突,这种看似有些不相协调的丧葬仪式,正是清江流域土家人独特生死观的体现。在这种独特生命观影响下生成的生命意识沉淀于清江流域土家人的内心深处,几千年来始终浸润着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民族文化,使得撒尔嗬成为其生与死的象征性交换仪式。
(二)“歌丧”:生者祭死的豁达情感表征
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具有生与死象征性交换的本体意义,体现着土家人别具一格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直接体现在撒尔嗬仪式的歌咏中。如前文所说,清江流域撒尔嗬仪式的乐文化内容丰富,它们广泛包含了土家人祖先和图腾崇拜、渔猎活动、生产生活、男女爱情和历史叙事等诸多内容,这些乐文化来源于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生与死感悟。清江流域土家人在撒尔嗬仪式中用高亢的歌声咏唱诸多与生者有关的歌,旨在“暖丧”和发家佑人。所谓“暖丧”是指以奔放的歌与苍劲的舞蹈陪伴亡人的最后一程,传达着生者对死者的礼敬,以及对生命的祈盼。[11]譬如《送歌头》的唱词:
“师家龙凤交我手,大家都来送歌头。你一首来我一首,水流东海不回头。新亡辞哒阳世路,孝家两眼泪直流。团转四邻来帮忙,惊动远近众亲族。亲友到屋拜灵柩,又作揖来又磕头。”
明明是在丧葬仪式上,清江流域土家人却偏偏用歌咏爱情、咏生者的祈盼,甚至咏丧葬仪式的情境,他们在仪式上尽情歌唱,任意舒展,竭尽所能来彰显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他们以歌声表征生者祭死的礼敬,不可谓不豁达。尤其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的歌中大多充满了被称为生命之歌的情歌,这些情歌正是清江土家人“情动生音”的体现。在这些歌声中,渗透出清江流域土家人的民族心理,表述着他们豁达的生死观。
(三)“跳丧”:死者“寄身”的神圣体验
“跳丧舞”作为生与死象征性交换仪式的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中最重要的环节。土家人通过“跳丧舞”的涉身体验与本民族生命信仰建立连接,身体成为生死转换的媒介,舞蹈成为沟通亡者的关键因素,因而跳丧舞的人群在仪式的狂欢中获得神圣体验。长期以来,仪式都被认为是人类情绪、情感表征的工具,也是作为族群文化对“他者”的集体性、公开性陈说,是一个民族生命观念的外显表达。人在参与艺术实践的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分被充分调动,心灵、思想和心志转入人的全身各部位,身心互动,投注、沉浸于艺中,精神领悟与身体感通真实相汇,成为整全、协调和畅的生命共同体。[12]个体的涉身体验成为仪式中神圣感获得的关键环节。在仪式的结构中,存在“阈限”和“交融”两个阶段,参与仪式的群体从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从而暂时与原有社会结构相关的价值观、情感等分离,进入阈限阶段,他们被鼓励去思考并接受仪式生成的价值观与情感,因而他们进入到由仪式构成的社会结构(即交融),从而成为“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异质的混合体”[13]。换言之,参与仪式的群体因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变得“狂迷”,暂时性获得巫术礼仪中的崇拜、敬仰等心理情感,从而在整个仪式过程中都保持神圣的内心状态。
在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这种“狂迷”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撒尔嗬仪式的开始阶段,本来是由掌鼓师和歌舞者在场上临场选择和即兴发挥,众人围坐观看,当场上有人疲惫或歌舞不好时才会有人替换。但当仪式进行到中期,这样自然的衔接被打破,掌鼓师、歌舞者、围观众人都参与其中,他们彼此展示自我,“叫啸”,一波接一波,异常“狂迷”,多时竟有上百人同时歌舞,正如古籍中所记载的一样,“其歌必狂,其众必跳”。可见,撒尔嗬仪式在清江流域土家族之盛。撒尔嗬仪式体现了清江流域土家人对生与死的独特认识,“灵魂不死,生死转换”是这种仪式生成的心理基础。尽管这种心理是原始社会共有的文化现象,但清江流域土家人的表达是与众不同的,越是歌舞狂欢,死者的新生也就越是可喜可贺,生者对死者的缅怀也就愈加深刻。可以说,撒尔嗬仪式中生者的狂欢实际上是死者新生的“寄身”,通过“跳丧舞”的涉身体验实现了生与死转换的神圣过程。
三、撒尔嗬仪式的生命关照
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体现了土家人对生命的礼赞,它蕴含了清江流域土家人独特的生命关照,生与死的象征性交换在撒尔嗬仪式的歌舞中实现。撒尔嗬仪式中歌舞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曰歌神话,二曰歌世俗,三曰歌先祖。清江流域土家人独特的生命关照都潜藏在这三种形式的歌舞中,因而它们被用以延续族群的生命记忆,表达生命精神的诉求,唤醒生命共同体意识,成为清江流域土家人的生命哲学场域。
(一)歌神话:祈求生命记忆的延续
神话,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歌唱的重要内容,它们表达了土家先民对族群繁衍、对生命记忆延续的追求。如在《盘古出世》中唱“盘古开天”“轩辕织衣巾”“神农尝百草”等,在《姊妹相合生后人》中唱“天地相合生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在《十梦》中唱“白虎坐堂当家神”等。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写照。“‘神话’、‘图腾’、‘巫术’构成中国原始文化的动态结构,其中原始神话是人与世界的‘第二面貌’。它不是历史本身,是被神化、灵化、巫化与诗化了的人类远古历史的文化方式。作为通过‘言说’的一种文化符号系统,在想象与虚构中,蕴含着文化的真实与密码。原初民的精神,一定程度上是被神化所育成、锻炼与成长的,并且影响其物质生活及其生命的过程与结果”[14]。尤其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充满恐惧和敬畏,加之人类对繁衍后代、生命延续的需要,于是,将内在的生命冲动、生命意象,偶然的自然现象、梦境、潜意识等带有神秘色彩的因素,与生命、生殖相关联,衍生出最为广泛的生命信仰的仪式。[15]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充满了强调氏族繁衍的祖神崇拜,与傩文化中的高禖仪式极度相似。“原始先民在祈求多子多谷的仪式上,琴瑟击鼓,以人的性行为诱导天地交合,使田亩受孕,把人间的男女与天地阴阳等同起来,目的是万物的生育。这一神圣的仪式就是对‘高禖’的祭祀。”[16]质言之,撒尔嗬仪式拥有生与死象征性交换的功能,不仅使亡者在族群生命方面完成了“虚幻”的新生,还在此生与死象征性交换的仪式上表达族群繁衍生息、生命延续的愿望。清江流域土家人将这种对生命延续的期望寄于歌舞中,通过仪式的狂欢,把族群生命观念与生命激情镌刻在民族记忆最深处,成为族群生命文化的内核,使得撒尔嗬成为清江流域土家族的一套文化符号系统,不断强化族群的文化记忆,在撒尔嗬仪式的神话歌唱中延续、传递、再生产生命记忆。
(二)歌爱情:满足生命精神的诉求
世俗生活与爱情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歌舞的又一重要内容,而且是歌舞最多的内容,这些歌舞是土家人精神世界的投射,表达着土家人生命精神的诉求。通常而言,仪式活动中的歌舞表达是对象征性类比关系的知觉,进而产生创造性思维,这种创造性思维实践活动的象征最初具有较多幻想和巫术色彩,其思维表达过程常是较为积极和狂热的活动过程。[15]因而,这些仪式活动往往带有人类群体主观想象的投射和情感思维的渗透,群体通过仪式活动寻求精神上的感受,使得参与意识异常强烈,使得这种精神吸引形成群体的生命感召,让人积极主动涉身其中。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一方面将世俗生活事件和爱情作为思维发生的起点,另一方面又不断对世俗想象和幻化,通过狂迷的歌舞仪式表达土家人内隐的生命精神追求。如《十绣天子城》:
“一绣天子城,绣起天子管万民,绣起凡间世上人。二绣月中梭,绣起明月照江河,要绣美月变娇娥。……十样都绣尽,绣起月亮圆纠纠,绣起桫椤在里头。”
在世俗场域高唱情歌是理所当然,但令人惊叹的是在礼敬亡人的神圣场域中竟出现情歌的滥觞,在这情感反差极大的两个场域中同样歌颂爱情,实际极为鲜明地张扬着清江流域土家族丧葬中的独特生死观。在礼敬亡者的神圣场域高歌生者,实际上是对自身生命的积极肯定,是对生命精神的诉求。在礼敬亡者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并未投递到神的界面,而是感到自身生命、存在与神同一而获得的自我肯定,天命、天道愈往下贯,人的主体生命愈得肯定。[4]换言之,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不是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和崇拜,而是就人在涉身体验的狂迷过程中产生人神一体的感受和体会,进而表达撒尔嗬仪式歌舞中对象征性类比关系的知觉的陈说,也就是对作为思维发生起点的世俗生活事件和爱情的陈说。同时,从另外角度看,情歌作为生命之歌,爱情作为生命之事,老人的死亡也意味着氏族成员的减少,而要弥补甚至增加氏族成员的途径就是激励族人婚配繁衍,延续生命。因此,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一定程度上在神圣和世俗两个层面表达着土家人生命延续的愿望。但是,土家人歌爱情,最主要的还是在陈说象征性类比关系的知觉和作为思维发生起点的人的情感,即在涉身体验的狂迷过程中表达他们对自身的肯定和对生命精神的追求。
(三)歌先祖:唤醒族群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歌先祖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它表达着土家人群体共同的生命忧患意识和民族共同发展意识,并逐渐成为清江流域土家人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仪式中潜藏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先祖”这一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中所蕴涵的族群生命意识,二是“一方有丧,八方帮忙”的共同发展的生命意识。清江流域土家人的“先祖”即为廪君所化的白虎图腾,它是关于土家人生命始于何人、何时、何地,又何以起始的一种原始的文化行为与心理现象。“图腾文化体现了‘人类集团’的‘共同性’即‘集体统一性’。一定意义上,原始人类的精神、理念,是靠图腾崇拜的意绪及其象征仪式来加以维系的。血族借此将自己的氏族与别的氏族区别开来,从而团结、保护自己,初民所依赖的就是图腾。图腾作为氏族的保护神,将一个族群的原始初民团结在自己‘祖神’的旗帜之下。它是初民血亲意识的初步萌起”[14]。正是出于人类对自身生命存在形式和意义的探索,追根溯源,原始初民较早地产生了“共同先祖”这样一种人文意识和情感,它与氏族群体以及每个个体的生命意识相联系,希望确认自己的生命起源,并将其转化为关于生命存在形式和意义的依据。
在图腾崇拜的仪式中,“初民‘意识到’而且有一种主观的心灵冲动,便努力寻找与笃行其‘先祖’是谁,并对其深表感激和绝对崇拜,以便在‘先祖’保护神的庇护与禁忌中,共同面对无情世界的灾难。图腾的基本文化素养,在于唤起氏族迷信‘先祖’而向心的群体生命意识”[14]。因此,作为群体生命意识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廪君这一“共同先祖”的身份认同,撒尔嗬表现了清江流域土家人的生命忧患意识和民族共同发展意识。当举行撒尔嗬仪式时,远亲近邻,甚至平时有仇怨者都“不请自来”,齐心协力帮助料理死者料理后事,并衍生出“人死众人哀,不请自然来”“打不起豆腐送不起礼,打夜丧鼓送人情”的民间丧葬风俗。仪式的一重大功能便是社会团结。在仪式举行过程中,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密切关注其共同的行动、更知道彼此所做所感时,就会更强烈地体验到其共享的情感而产生集体兴奋,欢呼的人群变得狂热,通过有节奏连带的反馈强化,参与仪式的人群产生了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以及维护群体的道德感。[17]在撒尔嗬仪式中,土家人在共同的行为心理下,通过歌舞实现心灵共睦,变得兴奋而狂热,使群体更加团结,且“唤醒”了象征群体的符号——先祖廪君,他们因迷信“先祖”而产生的群体生命意识得到强化。这种群体生命意识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融入到土家族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一种深厚且稳固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成为清江流域土家人的凝聚向心力,实质上是土家族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
四、结语
对于人类而言,死生亦大矣。一个强调生命存在与意义的民族,必然拥有渊远的祖先信仰体系和深厚的文化血脉。撒尔嗬正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渊远祖先信仰体系和深厚文化血脉的表征,它以高歌狂舞的形式礼赞人的生命,使涉身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情感投入到歌舞中,融汇到撒尔嗬仪式里,彰显和突出清江流域土家人别具一格的生命关照。在撒尔嗬仪式原始古朴的歌舞狂欢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张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脉搏。这对于人类关于自身生命存在形式和意义的无尽探索,以及对生与死的永恒主题富有哲学意味的认识与思考,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尔嗬的独特文化内核。撒尔嗬内聚中华传统礼乐文化基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又与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相依相偎,在弘扬民族精神、表征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现代文化场域中仍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以及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