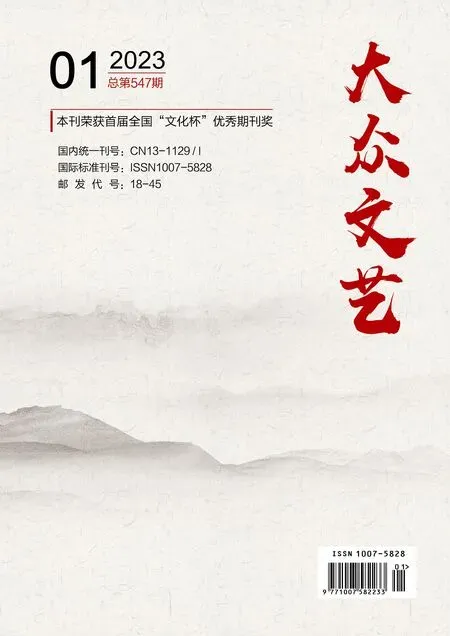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诗经》三种英译本的副文本对比研究
2023-02-22王聪
王 聪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300)
一、引言
副文本(paratext)是一种周边文本或服务性文本,是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正文本”,副文本是读者最先接触的部分。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根据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的观点,副文本是“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1]。副文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根据与正文本的空间位置可以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两类。内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封面、书籍护封、插图、前言、后记、序跋等;外副文本包括书籍外的一些资料,如对作者的采访、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作者身份、作品时代背景等。
近年来国内外副文本研究呈上升趋势。这些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副文本的价值。如Kung(2013)认为副文本包含重要的线索,可以提供文本中不存在的信息或者隐含信息[2]。彭文青(2021)认为“副文本体现了作者的翻译意图和价值取向”[3]。应用研究倾向于用副文本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Neveu(2017)以《拉方丹寓言》为例分析副文本对作品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副文本有助于提升阅读体验[4]。姜智芹(2022)对余华作品英译的副文本进行剖析,发现译作的副文本有利于提高作者的知名度、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5]。
目前,部分研究者开始聚焦《红楼梦》[6]、《西游记》[7]、《论语》[8]等中国古代经典英译的副文本特点。其中《诗经》英译是关注的重点之一[9][10][11]。不过已有研究大多涉及理雅各、许渊冲的译本,极少讨论亚瑟·韦利的译本。因此本文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从副文本角度对《诗经》的三种英译本进行对比。这些译本包括1993年出版的许渊冲韵体译本、1876年理雅各的韵体译本,以及1937年亚瑟·韦利的非韵体译本。研究问题如下:
(1)三种译本的副文本有何异同?
(2)哪些原因可能导致副文本的差异?
二、《诗经》英译本的副文本特征对比
副文本包括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侧重分析《诗经》英译本的内副文本。副文本形式多样,本文选择护封及封面、排版、序言和注释进行对比。
(一)书籍护封及封面
书籍护封及封面不仅起到美化和保护书籍的作用,也是读者最先获取的信息。在所选的三个译本中,许渊冲译本和理雅各译本是精装版,既有书籍护封也有封面。亚瑟·韦利译本是平装版,只有封面。下面分别从文字、颜色、装饰、图案等方面对护封及封面进行对比。
许渊冲译本的书籍护封上部标有丛书名“TH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OF CHINESE CLASSICS/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中间有中英文书名“BOOK OF POETRY/诗经”和语种说明“汉英对照/文白对照”等字样,语种说明位于书名的正上方。护封英语全部大写。从字号上来看,“诗经”二字最大,最为引人注目。封面的底部注有译者姓名、编校者姓名以及出版社名称。封面底色以黑色为主,红色为辅,并配以金色花纹,这样的装饰显得高贵典雅。护封上不仅有详细的信息可供阅读,同时视觉上较为美观,能够吸引读者。
许渊冲译本的书籍封面底色为白色,书脊中部标有中英文书名“诗经/BOOK OF POETRY”,“诗经”二字最为醒目,正下方有出版社名称“湖南出版社”,书脊最顶端和最下端都有花纹作为装饰,字体和花纹均为金色。
理雅各译本的封面设计较为简朴,封面以单一的蓝色为底色,书脊处有英文书名“THE SHE KING,OR THE BOOK OF POETRY”、译者姓名“JAMES LEGGE”以及出版社名称“TRUBNER&CO.”。封面的文字全部大写且字体为金色,与纯色封面结合更能凸显重点信息。封面简单而不失雅致,读者容易识别主要信息。
亚瑟·韦利译本为平装版,因此没有书籍护封。该版本的封面内容较以上两种译本更为丰富。封面主要包括英文标题“The Book of Songs”、译者姓名“ARTHUR WALEY”、英文丛书名“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和一幅古画。古画的底色为暗黄色,画中是一对身穿古代服饰的夫妇,妇人手中捧着一朵花,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该画可能代表《诗经》的主题之一——爱情,也可能反映译者关于古代中国的艺术审美。封面底色以黑色为主,古画的暗黄色为辅,字体为白色。除书名外,所有文字全部大写。在所有的文字中,书名“The Book of Songs”不仅字号最大,而且首字母大写,从而区别于其他信息。
简言之,许译本的书籍护封以及封面突出英汉对照的特点,理雅各的封面较为简洁,强调书名、作者等重点信息,亚瑟·韦利译本的封面信息较为丰富,凸显该书的爱情主题和英文书名。
(二)排版
下面以《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文为例,比较三种译本的正文页面排版。
许渊冲译本的汉语与英语译文对照排版,两种语言各占一页。汉语在左,英语在右,其中汉语既包括该诗的古文原文,也包括现代汉语的整篇释义。汉字为简体中文,采用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现代汉语书写方式。字号方面,除标题外,所有文本均采用同样字号,并无突出的字符。古文原文在页面左侧,采用逗号、句号、感叹号等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每个分句均为四个汉字,每句各占一行,全诗共三个小节,每节以空行隔开。古文原文右边是对应的白话文,句句对照。可能是排版的原因,文中没有关于具体字词的注释。英文全诗采用逗号、句号、感叹号等现代标点符号,每行与汉语对应,每个小句的首字母大写,偶数行缩进四个字符。
理雅各译本采用古文原文和英文译文对照排列,一页中同时存在古文原文、英文译文和英文注释。古文原文为繁体中文,字号偏大,右侧竖排(即采用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的古代书写方式)。原文用句号标记句读,前后小节另起一行,没有现代汉语译文;小节上方标有“一章”“二章”“三章”等字样以便分节。原文正下方是与之对应的英文译文,译文采用左对齐的方式,从左至右横排,每行首字母大写。译文采用逗号、句号、分号进行断句,每一小节前用阿拉伯数字进行分节。译文下方是与诗节相关的大量英文注释。注释左右横排,且中间分栏,排版方式与词典排版类似。此外,注释中英混排,一句中经常出现两种语言,汉语字、词为繁体形式,字号较大,更为突出,数量较少;英语字号较小,文字较多。
亚瑟·韦利译本没有古文原文,译文横排,文中采用逗号、句号、感叹号等标记句读。每一小节以空行进行区分。奇数小节前有“THE FEASTERS”(欢宴者)字样,偶数小节前有“THE MONITOR”(告诫者)字样,这种对话形式以重章的方式反复咏叹,或者告诫自己与他人要勤勉努力,或者劝人及时行乐。译文的风格类似西方诗歌,排版形式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易于被目标读者接受。
综上所述,许渊冲译本的排版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进行双语研究;理雅各译本的排版有助于读者对古文原文的字、句等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亚瑟·韦利译本更像一本独立的作品,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更加通俗易懂。
(三)序言
序言是位于作品主体之前的文本。
许渊冲译本的前言共9页,包括《诗经》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与影响,以及英译情况。序言首先对《诗经》进行简介,并对《诗经》译本进行简要评述。在文中译者提出了自己的译学观点:“诗歌要集各家之所长”。以《周南·卷耳》为例,余冠英和钱钟书对同一首诗有不同的解读,所以译者在河南译文中(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人间春色第一枝》)采用余的说法,在湖南译文中(湖南出版社的《诗经》)采用钱的说法[12]。许渊冲的译文体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的“三美”准则。
理雅各译文的序言主要阐述《诗经》的翻译历程、不足之处、翻译动机、翻译难点、致谢等。序言共182页,分为五章。序言的第3章对《诗经》的格律、诗学价值、译本进行探讨,其他章节分别讨论《诗经》的编撰历史、作品反映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因素以及翻译参考的国内外文献。
亚瑟·韦利译本的序言共27页,包括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第一版前言解释了未翻译15篇诗词的缘由,他认为“这些诗都是对政治的哀叹,与其他诗歌相比,显得枯燥乏味,内容腐败、毫无意义”[13]。第二版前言说明了修改过程并进行致谢。韦利提到诗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对儒家思想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指出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诗经》,但是它依然保持自身的魅力。
(四)注释
许渊冲和亚瑟·韦利的译本未使用注释,而理雅各的译本出现大量的注释,且注释的篇幅远远超过译文。准确来说,理雅各的译本是学术翻译的典范。在正文中,理雅各几乎逐字逐句地对古文原文进行解释。以《桃夭》为例,注释对诗中的“夭夭”“灼灼”“之”等汉字或词语进行释义。为方便读者阅读,各种注释非常详细。理雅各解释说:“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丝毫不会对长长的注释在意;但是,可能会有第一百个读者,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14]。
三、三个译本副文本的差异原因
分析表明,《诗经》三种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差异较大,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源于译者身份、时代背景和假定目标读者的不同。
许渊冲(1921~2021)是一位从事文学翻译60余年的翻译大师,精通中、英、法三种语言,是英、法译诗的翻译奇才,被誉为“英法诗译唯一人”。他在六十余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翻译了众多的中国古代诗歌。许渊冲的译本更注重双语对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译本意在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一名英国传教士,他是19世纪著名的西方汉学家和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家。他在八年的时间内对《诗经》进行了三次翻译。作为传教士,他知道必须熟悉中国的儒家经典、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而后才能传教。此后,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翻译与研究,涉及《论语》《大学》《中庸》(第一卷)、《孟子》等作品。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国著名的翻译家,是继理雅各、李约瑟之后,少有的闻名于海外汉学界的英国人,他属于英国汉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亚瑟·韦利偏爱短小精悍的英诗,因此他的《诗经》译本以简洁明快著称。但是他在翻译时不太注重原文,更倾向保留自己的风格,这种翻译方式依赖于译者对《诗经》的主观解读,是译者眼中中国古诗的西方呈现。
除译者身份外,时代背景也是造成副文本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许渊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期,文化“走出去”逐渐向“走进去”过渡。他的译本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则是英帝国在亚洲迅速扩张的时期,英国为了侵占中国,试图向中国输送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传教,而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让传教能够在中国顺利进行。这正是理雅各重在解读古汉语原文、挖掘其中中国思想的主要原因。而亚瑟·韦利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想象之中。据说当被问及为何不去中国时,亚瑟·韦利回答道:“我要把中国的唐朝形象一直维持在我的脑海里”。
此外,根据副文本分析的结果,我们推测许渊冲的假定目标读者是国内的英语学习者,他的译本能够帮助他们进行双语学习;理雅各的目标读者是具有一定汉语基础且对汉学有深层研究的西方学者,这些为数不多的西方汉学家通过学习他的译本,汉学造诣能够有所提升。亚瑟·韦利的目标读者是西方的普通读者,有助于激发西方大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结语
正如热奈特所说,副文本“围绕在文本周围,使它得以延伸,正是为了让作品得以‘呈现’,是为了使作品现身”[1]。本文对许渊冲的韵体译本、理雅各的韵体译本和亚瑟·韦利的非韵体译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三个译本在封面、排版、序言、注释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认为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译者身份、时代背景和假定目标读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