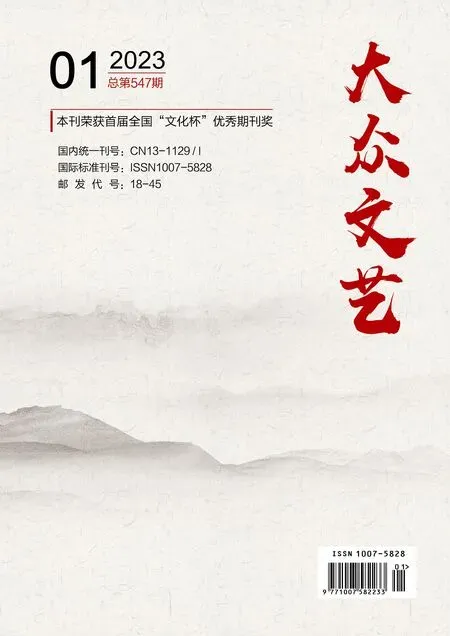本雅明“辩证意象”的语图维度再阐释
2023-02-22庄懿
庄 懿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二十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发生促使了人的思维的转变,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他将语言视作一个封闭的系统。本雅明并不赞同索绪尔将语言视为外在于人的系统的观点,于是他从卡巴拉教派的神秘主义入手建构语言哲学,探讨语言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回归原初语言来重现事物的真理,实现最终的救赎。在神学—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本雅明以非中介的辩证法来解放真理,使之从主客二元对立认识论的遮蔽中呈现出来。“辩证意象”就是本雅明提出的有力的认识和批判工具,它蕴含着对时间和历史的颠覆性理解以及语图的辩证关系,构成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和W.J.T.米歇尔对艺术作品乃至各种图像问题思考的根基。
本雅明的“辩证意象”体现过去记忆与现在视觉所见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于贝尔曼正是从这一点入手,试图通过视觉细节中的断裂、差异和重复来接近人类的思想样态与生命情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本雅明认为语言是“辩证意象”之地,“辩证意象”以文字与图像相遇的形式呈现,意义或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生成,这启发了米歇尔提出的图像转向论以及“元图像”概念,让图像言说自身,从而实现对语言言说图像的传统的颠覆。借助米歇尔、于贝尔曼与本雅明思想之间的重叠和错位,或许能为“辩证意象”概念的理解提供更加全面的观照。
一、“辩证意象”的根基:本雅明的语言哲学
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认识论,使人类以同一性、精确性来控制一切事物,主体从而凌驾于客体之上,甚至渗透到语言领域。[1]在以主体理性为基础的符号语言中,自然事物的意义是由理性主体赋予的,理性主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而在图像语言中,自然事物的样态能够呈现其本质而没有被主体的认识需求所遮蔽,客体具有优先性。类似地,本雅明通过统一事物的本然状态来呈现事物样态的丰富性,推崇客体优先性,将图像语言视为打破主体统治地位的关键。
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语言与人的思维和存在方式间的深切关联,语言不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本雅明建构了一种容纳历史哲学的语言神学,缅怀并追寻原初的纯语言。纯语言不是本质存在,而是通过碎片的重组和并置从而不断接近的可能性,迥异于形而上学中至高无上的理念。
本雅明批判索绪尔以棋盘与棋子之间的关系来类比语言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2]在本雅明看来,索绪尔的语言观是唯名论的,语词与事物之间联系随意且偶然,本质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索绪尔关注整体语言的社会性,个体语言并不具有实体性。罗兰·巴特进一步指出了社会性的语言结构对个体言语的压抑,处在语言之中的人难以脱离语言来批判或思考语言。但是与索绪尔不同的是,罗兰·巴特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倾向,把语言学纳入符号学,从而揭露符号本身的历史性。本雅明则是抑制主体以保障客体优先性,最终目的是抵达自行生成和显现的非同一性的真理。他为命名集式的语言找到神学根基,指出了语言以对应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建构力量。语言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整体,也不是语词、话语、文字等具体事物的集合,而是存在于语词、文字、声音、图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张力中。
本雅明早期的语言哲学是在神学的框架下展开的,整体逻辑可以用“起源即目标”来概括,即人如何从起源堕落,并重新寻找救赎回归原初的起点的过程。“起源”不是指生成,而是“在变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的历史性范畴。起源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总体,而可以被视作一种变动不居的节奏。[3]本雅明探讨的是如何打破线性的历史进程,反对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断裂、差异中寻找爆破的可能性。于贝尔曼将本雅明的“元语言”中的“元”理解为正在形成的危机。[4]因此“元语言”实际上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已经失落了的原初语言,另外一个是在试图迫近过去时在瞬间的爆破中抵达的原初语言。
在本雅明看来,语言最初是由上帝赋予人的一种天赋。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是通过“说要有——便有了”来创造万物与人类的,上帝以名称这一创造性语词的方式来使人类得以存在。[5]在上帝的命名下,万物的存在得以与上帝的创造性语言同一,分有上帝的神性,直接在场。上帝的语言直接显现了事物本身的真理与知识,是无中介的、纯粹的和完满的绝对真理。被上帝命名的人类和事物就是知识本身,二者是统一的。在伊甸园中人类的语言是完美的,能够完满地传达精神实体、语言实体以及神性的启示。但是在人类亚当和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之后,得到了有关善恶的知识,否定并放弃了名称。这时人类语言的名称是外在的知识,成为对上帝语言的拙劣模仿,传达外在于自身的事物。人类堕落之后,作为表意符号的语言混乱不堪,通过外在的认识判断来获取事物的真理在本雅明看来是徒劳的,名称作为高贵的神性的表征沦为被奴役的工具。
于是本雅明着手考察如何将人类语言擢升为纯语言。这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起源既体现的是主客间最原初的同一关系,又是一种有待完成和实现的状态,不断地以流动的节奏引领着救赎的实现,在四分五裂的经验碎片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而人类必须探求新的方式来抵达主客同一的源初关系。本雅明并不是走中立调和的路线,而是以爆破和毁灭一切的“辩证意象”来接近真理。
本雅明的语言哲学中的时间错位,为“辩证意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辩证意象”发生于当下,以过去的记忆拉开与当下体验之间的距离。在这双重距离与时间错位中,一种本真性的综合得以实现。“辩证意象”既是人认识事物与自身关系的工具,又是人类批判自身的工具,因此是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本雅明预设了语言与精神存在的同一性,语言既是突破紧张关系时参照的起源,也是想要达成的目标,尽管目标的实现可能发生于断裂、爆破的瞬间。“辩证意象”的产生基础就是这样的一种与精神存在同一的语言得以实现的瞬间的可能性。
二、“辩证意象”的运作原理:星丛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辩证意象”将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体验以星丛的方式关联在一起,从处于当下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中爆破出来。这种星丛式的运作原理,早已在本雅明的语言哲学中有所体现。在《译者的职责》中,本雅明论述了诸种语言之间的亲缘性,是由不同语言之间互补的表意擢升出来的总体性,而这种总体性就是纯语言的特征。纯语言或者上帝语言,既是原初世界的起源,又是堕落的世俗语言要求得救赎的目标,本雅明将目标的实现置于动态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翻译这一直接中介来达成。纯语言是对事物真理和上帝旨意的直接显现,是通过翻译使原作和译作互补并调和而成的抽象总体性,与“星丛”概念的运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论批判”导言中,本雅明详细地论述了理念、现象与概念之间星丛式的关系。语言是与精神内容对应同一的透明性容器,理念的表达即语言的自我表达。对于真理而言,表达是首要的。这是一种从《论原初语言和人的语言》中延伸出来的观点:人在语言之中传达着他自己的精神存在。[5]语言不是传达的媒介,而是传达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传达的事物本身,因此真理不需要像认识一样借助中介建立起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与认识和真理之间的差异相对应的则是概念和理念之间的差异。本雅明指出了概念起着中介的作用,通过对现象进行分解、收集和整合,使现象消解为星丛结构连接点的元素,从而参与理念的存在。理念只有在“概念对物的元素的组合中表达自己”[6],将现象吸纳入自身之后进行再现。因此概念作为现象和理念之间的中介是极为重要的,在同一个过程中既拯救了现象,也表现了理念。
本雅明的星丛构型方式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主观意图的介入,使真理成为一种中性的“由理念构成的一个无意图的存在”和“意图的死亡”[6]。因此真理是无法通过认识以一种占有的方式捕获的,主观意图也无法与其发生联系,而只能通过理念这一表征来接近。[7]通过概念这一中介,理念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它们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是星丛式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要素与要素之间是一种并置的关系,现象借助概念这一中介抽离出原本的逻辑语境,以要素的形式浸润在星丛之中,而理念在这些要素的排列中以星丛的形式得到显现。
本雅明对“辩证意象”生成的论述,正是借助了这一逻辑,将过去经验与当下的体验、图像本身与图像的可读性星丛式地并置在一起,让“辩证意象”如集体无意识般自行显现,从而具有了短暂易逝的乌托邦色彩。以星丛的构型生成的“辩证意象”使人对精神与事物、语言与图像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认知与反思,这又是通过“新颖”(novelty)赋予人们震惊体验来实现的。尽管本雅明是用意象化的方式来拯救现象与理念,但这个过程离不开语言的参与,语言是与“辩证意象”的生成相互缠绕的,服务于“辩证意象”的读解,是承载并呈现“辩证意象”的媒介。于贝尔曼认为,理解“辩证意象”等同于阅读辩证意象,这是因为阅读不是去解读图像本身,而是用文字对图像进行批判性的再加工。“本雅明关于图像的可读性应被理解为图像本身的一种本质的时间运动(可读性不压缩图像,因为它生自于图像),它不是图像的解释。”[4]真理就产生于图像与语言之间的时间距离当中,生成于图像和批判性阐释图像之间的张力当中。
借助米歇尔的理论,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图像本身与图像可读性之间的张力或者说辩证距离。受到“辩证意象”的启发,米歇尔进一步发掘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与图像互渗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个类似于“辩证意象”的批判工具——“元图像”。图像是由原初的形象(image)转变为经过人为扭曲的具有实际用途的图像(picture)的过程,通过将实际的图像元素进行拆解和重组,以接近甚至抵达原初的图像。形象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而是类以家族相似的识别逻辑形成的克隆关系。[8]原初的形象并不是现象的本质或者经过抽象的一般形式,而只是与图像相似。这些相似性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亲缘家族,原初形象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相似性的交织,它既是自身,又是他者,是在场的缺席,缺席的在场。与米歇尔相比,本雅明“辩证意象”更具有整体性,探寻的是总体救赎的可能性,因此语言与图像并不是中性的元素,而是蕴含着爆破一切的批判性力量的。米歇尔的“元图像”则是彻底后现代的,试图拆解一切总体性,与异质、多元的社会融为一体。图像的价值和作用不必被放置于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而是社会本身[8]。
三、“辩证意象”的实现:从寄喻到新颖
本雅明对元语言的追寻,是试图在打破线性时间进程的同时寻找新的救赎方式,来接近语言的原初状态。他将“辩证意象”视作通向起源的认识论工具和批判武器,考察不同时期的“辩证意象”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就像十七世纪寓言是辩证意象的准则一样,到了十九世纪新颖(novelty)便成了辩证意象的准则。”[9]
十七世纪的巴洛克悲苦剧的呈现样态是星丛式的,体现了理念是一个历史性的、开放的和充满张力的场所,文字、声音和图像的混合使用使得语图关系的重要性得以显现。悲苦剧以不具备任何美感的废墟形态拯救艺术本身,这体现在其寄喻性结构当中。传统的理论家往往将寄喻视为一种“描述性图像”[6],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忽略了寄喻性直觉本身所具有的原初力量。他们误解寄喻的原因在于,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的文字遮蔽了寄喻的表达特性。本雅明认为,寄喻不是一种描述方式,而是表达本身,是和语言、文字一样的表达。[6]更准确地说,寄喻是陈规与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寄喻符号内在于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又极具创造性、生机勃勃和自由。[6]寄喻符号不是被赋予和被规定的,更偏向于象形文字,能够以图像的形式直接与神义建立联系。
一方面,寄喻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体现于它迥异于象征的特性。与象征相比,悲苦剧中的寄喻不断地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滑动,与明确的意图或者固定的意义发生冲突并试图征服它们,从而实现不断的自我更新。不仅如此,悲苦剧的意义产生于声音与文字之间的断裂。[6]词语没有固定的所指,不再是人类进行对话或交流的工具。另一方面,寄喻符号本质上依托于人图像式的思维方式,只有这种无须任何规定的直观,才能极具爆破性和生命力地自行生发出神圣的力量。无序而又尚未定型的图像还是人类思想样态呈现的形式,寄喻所使用的文字是图像式的,因此能够真正进入到本质当中。[6]巴洛克式寄喻的特点就在于文字的图像性,图像就是和鲁内文相似的碎片,直接沐浴在神灵光芒的照耀下而不被任何理念、意指或意义所遮蔽,因此隐晦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怪诞的废墟状态。寄喻这种充满歧义性的碎片形式并不妨碍理念的生成,相反,正是在这黑暗的废墟中散落四处的碎片上闪烁着理念的光芒。因此,悲苦剧的语言打破传统悲剧语言的规范性,以不断变化、跳跃和流动的形式模仿悲苦的情感。
更进一步地,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明显和积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模仿的是神造的自然,但是本雅明指出这种神造的自然实际上是堕落的、衰败的和消逝的,过度世俗化的实物本身并没有任何美感可言,因此不会绽放出光芒。这种不断重复的语词和无言的画面结合在一起,以展示一种忧郁悲伤的情感。[6]人通过与物同一,去理解和感知物,才能够从物那里对自己的本性进行反思。破碎的语词和无声的画面显示出没有主体的语言摧毁主体的统治,试图恢复自然的历史。语言的“沉默”不是指不发出任何声音的缄默不语,而是太多的声音和话语造成了一种表面上的虚无和颓废,其内在却是对生命的真切感知和有力表达。
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辩证意象”不再是通过寄喻中的语图关系实现自我生成,而是通过传统经验与当下体验之间的时间错位造成的新奇感生成的。[4]本雅明摆脱了语图互渗的维度,而是以一种彻底意象化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反对回忆永恒过去、当下稍纵即逝、期待美好未来的进步历史观。而在全新的历史观指引下的“辩证意象”是暧昧的(ambiguity)[10]“辩证意象”存在于不同时期的集体意识当中,[8]但它强调的是当下的体验,主体在辨认和感知到集体无意识的瞬间,也就获得了救赎的潜能。因此“辩证意象”既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也是批判自身和实现救赎的工具。
“辩证意象”的救赎性,恰好是米歇尔所缺乏的。他看到了本雅明“辩证意象”作为方法论的有效性,于是在调和语图冲突的层面上提出了“元图像”概念。他摒弃了“辩证意象”散发的忧郁绝望的气息,解除“辩证意象”蕴含的整体性。尽管他明确指出过图像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辩证意象”,以蒙太奇的方式将各种要素并置在一起,与当下直接发生关联,但他并不强调并置所有元素之后会生成真理,因为物质载体与图像之间是关系性的,这就消解掉了主体的作用和意义,也就消解掉了“辩证意象”的救赎性质。图像成为主体本身而产生了生命和欲望。这种自我指涉的元图像,可以是任何事物。[8]那么米歇尔的“元图像”也就与本雅明的“辩证意象”彻底分道扬镳。
结语
本雅明早期的语言哲学以神学的方式考察了人类语言与历史的起源,力图通过弥合现象与理念、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来恢复一种原初的总体性。以语言哲学为基础,星丛理论构成本雅明认识和批判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在传统经验与当下体验的错位中接近历史的总体性面貌。以讽喻的表达方式到对新颖的追求为特征的“辩证意象”,使人从乌托邦的幻想中看到一丝救赎的希望。借助迪迪-于贝尔曼和T.J.米歇尔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辩证意象”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及其救赎的潜能,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辩证意象”概念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