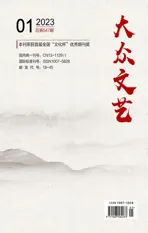从语用学角度探析《涑水记闻》中的人物语言
2023-02-22侯妙
侯 妙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涑水记闻》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一部优秀史料笔记,共16卷,主要记录的是自宋太祖开始至宋神宗朝围绕皇帝、官员所发生的事件,内容广博—涉及北宋朝廷政治、军事、外交(与辽、西夏等)、社会经济、逸闻趣事等等,语言简洁灵动,其中有颇多篇幅记录他们之间的言语。作者通过深厚的笔力,令许多人物跃然纸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聪明、节俭、有时却暴躁霸道的宋太祖,果敢、有魄力的文彦博,机智、办案慎重的钱若水和向敏中,雷厉风行的张咏,好学、淳谨、有时“掉书袋”的陆参,正直、体恤民情的姚坦,宽厚清廉的王旦等等。此书对于研究相关的历史、文学、语言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涑水记闻》大约到南宋初年宋高宗时期才得到整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传要录》记载“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冲令编类进入……于是冲裒为十册上之”[1]1693,其后流传的版本较多又几经散落,有两卷本、十六卷本、八卷本等等,本文研究所选文本为权威的中华书局点校版(2017)。
围绕《涑水记闻》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有史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
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学科,“牛津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55年正式提出第一个语用学理论”[2]1,其后,随着“会话含义”等理论提出,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顾名思义,“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是语言的运用,言语行为、合作原则、修辞、语用身份磋商等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
一、言语行为
“言”与“行”常常是紧密联系的,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就是“言”和“行”,它于1962年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可简要概括为“说话就是做事”[3]28。言语不只是简单代表语言层面的信息,它背后常连带着行为信息。在《涑水记闻》中,有许多言语行为案例,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博弈、事件的推进以及会话策略等丰富的信息。
枢密直学士张咏在益州为官的时候,有剽悍的群盗劫掠、滋扰百姓,而钤辖却并不作为,于是,某天,张咏召来了钤辖,主要通过精彩的言语行为,一步步督促钤辖踏上了前去讨贼的征程。第一步,他将州牌印交给钤辖,这样的举动令钤辖不明所以,于是问他原因,他答:“今盗势如此,而钤辖晏然安坐,无讨贼心,是必欲令咏自行也。钤辖宜摄州事,咏将出讨之。”[4]137张咏是一州长官,是钤辖的上司,讨贼是钤辖自己的职责,他怎么敢让长官直接去做,而自己坐在长官的位置上?长官的这一番话是对他不作为、不履行自身职责的严厉谴责,钤辖听了这番话,还哪里敢再不有所行动,于是惊讶说道:“某今行矣”[4]137,把出发的时间定到“今天”,而张咏并没有结束对话,他继续追问:“何时?”[4]137问钤辖今天什么时候出发,其实他的用意是不让钤辖拖延。钤辖的回答为“即今。”[4]137听到了满意的答复,张咏便吩咐左右准备酒具在城西门上为钤辖送行,说:“钤辖将出,吾今饯之。”[4]137这里的话与行动是一体的。这样一环环的言语行为、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效督促了钤辖尽快前去讨贼,不给他拖延、反悔的机会。临走之前,张咏答应了对钤辖充足的兵粮供给,顺便还震慑了钤辖,若钤辖无功而返,便要砍他的头,不给他留后路。张咏的一番话产生了效力,那位钤辖不仅出战,而且最终平定作乱的盗贼。
在是否任命狄青为枢密使这件事情上,皇帝因为左右臣子不同的谏言,有所反复、摇摆,后来,皇帝确定了要任命狄青为枢密使的想法,在忽然宣布了相关事宜之后,从前以为自己劝谏成功、对此事持反对意见的宰相庞籍是处于错愕状态的,反应过来之后,他对皇帝说:“容臣等退至中书商议,明日再奏。”[4]101这是迂回策略,他想想办法阻挠,而皇帝说:“勿往中书,只于殿门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之也。”[4]101皇帝的言语还表达了行动,指挥臣子不要转移地点,就在殿门内讨论这件事,他就坐在这里等着。皇帝的话,直接阻断了臣子想要迂回、拖延的做法,皇帝就坐在殿里等,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要太慢,这也表达了皇帝要求快速得到答复、解决这件事的决心。不久后,果然,这件事情办成功了。这也意味着皇帝的言语行为为目的达成起到重要积极作用。
相对于皇帝的言语行为,臣子的言语行为更为含蓄,常常会采用间接言语行为。所谓间接言语行为,即“人们在言语交际中经常使用间接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意图”[3]33。
皇帝因为周怀政事件发怒,要追究太子的责任,这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周围的官员都不敢说话,而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李迪等皇帝怒意稍稍平息之后,便从容上奏,说:“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4]159
他并没有直接否决皇帝的想法,而是巧用疑问语气,让子息单薄的皇帝理性地意识到其中的不妥当,言下之意是东宫的地位不可动摇。他这样的间接言语行为可以缓冲皇帝的怒气,为自己的劝谏成功起到良好作用。
二、合作原则
著名的合作原则理论于1967年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为了更好地开展会话,需要双方进行合作,他提出了四个准则:数量准则,即“信息适量,不多也不少”[5]78;质量准则,关注的是所说内容的真实性,即所说要为真;关系准则,关注的是关联性,即问答要有关联;方式准则,关注会话方式,要求语言清晰明了。[6]82
前面提到的张咏与那位钤辖的一问一答,比如“钤辖惊曰:‘某今行矣。’咏曰:‘何时?’曰:‘即今。’”[4]137二人的语言,也体现了对四个准则的遵守。张咏询问钤辖的出发时间,钤辖给出了简洁明确的回答,符合数量准则。钤辖最终按他承诺的时间出发了,他的话,也符合了质量准则。二人问答紧密相关,符合关系准则。二人语言言简意赅,不拖泥带水,也符合方式准则。
而在《涑水记闻》中,还有一些人物语言,表面上看违反了上面提到的准则,这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一)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傅永吉在平定由王伦带领的反叛宋朝的部队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皇帝很高兴,为他升官,见到皇帝之后,面对皇帝对他的夸赞,他并未居功,而是向皇帝夸赞陈执中,说自己也是因为奉行他才有幸获得成效。由此,皇帝认为陈执中也是位贤才,心中有了打算,接着,皇帝问:“执中在青州凡几时?”[4]72这是问陈执中在青州总共做了多久的官,而傅永吉的回答是“数岁矣”[4]72,从合作原则的角度看,他的回答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量的准则,对陈执中在青州的为官时长进行了刻意模糊,并未给出较为具体、精确的回答。没过多久,皇帝就对宰相说:“陈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4]72皇帝由“数岁”得出了“久”的结论,要将其召回,询问陈执中在青州为官的时间,是想为将他召回多一份有力理由。
(二)对质量准则的违反
某天,当宋太祖在后园弹雀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一位臣子称有急事想要见宋太祖(“急事”具体为何,此时并未明说),于是宋太祖急忙见了他,经过会面之后,宋太祖认为他上奏的是常事,因此发怒,问他这么做的原因,那位官员回答说:“臣以为尚急于弹雀”[4]8,认为这件事尚且比弹雀急。听了这话太祖更生气了。这位官员被宋太祖拿着斧柄打掉了两颗牙齿。分析这位官员与宋太祖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在宋太祖的角度来看,这位官员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他所禀报的事情并不是“急事”而是“常事”。而在那位官员看来,他所上奏的事情要急于宋太祖的玩乐。二人的标准不同,宋太祖是将其与国家重大急事对比,官员是将其与弹雀这样的玩乐事件对比。那位臣子称有急事,这样的言语达到了令皇帝迅速见他的目的,后来说认为上奏的事情比弹雀急,也表达了他认为国事比“弹雀”这样的玩乐活动更重要(以国事为重)的坚定立场。这件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太祖性格中暴躁霸道的一面。
北宋名臣向敏中在西京的时候,以没有查获出赃物为疑点,而怀疑一则案件另有隐情,在他的追问下,自诬为凶手的僧人说出了自己不是凶手的实话。在进一步探查这则案件中真正的凶手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向敏中秘密派的官吏在一家村店里吃饭,店里的老妇人听闻他是从府中来,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是那里的官吏,与他展开了对话。老妇人向他询问那僧人的情况,他回答说:“昨日已笞死于市矣。”[4]152
老妇人因此叹息,提出了一则疑问“今若获贼,则何如?”[4]152这是一则试探,其中也隐含着信息:老妇人知道真正的贼人不是那位僧人。为了打消老妇人的顾虑,官吏回答说:“府已误决此狱矣,虽获贼,亦不敢问也。”[4]152大致意思是:这案件官府已经误判了,所以即使抓获了真正的贼人,也不敢再问了。这里官吏话语中的“误”,也表明官吏明白老妇人前一句话的含义并且也透露出“认为僧人是贼人”是误判的观点,说此事不会再追查是为了让老妇人放下顾虑。老妇人听了他的话,放下心来,说出村里的少年某甲是真凶。最后,官吏抓住了真凶,并查获了赃物,那人服罪。在官吏与老妇人的对话中,官吏说了假话,在书中,作者还特别用了“绐之”[4]152来提示,官吏说的关于僧人已被处决等话都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表面上看,这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然而正是因此,才一步步打消老妇人的顾虑,进而从老妇人口中得知真正凶手的下落,他们对话在一步步为探寻真相提供线索,二人一问一答,环环相扣,是在合作着的。
西夏李元昊为了攻占金明寨,也曾使用了说假话、呈现假象的计谋,假装自己的士兵是因为被北宋将领李士彬威名所震而不敢作战,这样做是为了麻痹李士彬,助长了李士彬的骄傲自大,从而为自己攻占金明寨埋下了重要的一步棋。
宋太祖见到谋反的潞州节度使李筠的长子,迎头一句“太子,汝何故来?”[4]9李筠长子听了,用头击地,说:“此何言,必有谗人构臣父耳!”[4]9宋太祖称呼李筠的长子为“太子”,是故意讥讽、试探他。从李筠长子的回答来看,他也听出了宋太祖的言下之意,“此何言”先否定了宋太祖给他的称呼,表示并不敢当,接着为自己的父亲开脱,他的话违反了质的准则。他称呼自己的父亲为“臣父”,由此,也可看出,那时候他是认可宋太祖皇帝权威的,并不敢僭越。
(三)对关系准则的违反
有位录事曾向一位富民借贷而不成功,在审理富民家小女奴失踪案时,伺机报复,“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4]28,富民屈打成招。案子呈上,州官审查,都以为是事实了,而只有当时的推官钱若水对此表示怀疑,数日对此案不判决,他不愿草率为人定罪。那位录事便坐不住了,“诣若水厅事,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留熟观其狱词邪?’”[4]28那位录事用心险恶,他的问句中,透露出已经认定富民为凶手,认为应判其死罪的信息,而且还想要挟若水,问若水“是因为收了富民钱财,所以才想为富民开脱死罪吗?”这样的话,是想用办案徇私、收受贿赂等帽子逼若水“缴械投降”,而若水很聪明,并未掉入他的言语圈套及要挟,他并未直接对录事问句的信息给出是或不是的回答,违反了关系准则,转移了话题,先稳住了录事,如果他锋芒毕露,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怀疑,他的查案之路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且还可能令案件中的人身处险境。后来经过努力探查,钱若水找到了失踪的女奴,案件得以侦破,富民父子等人的冤屈也得以洗刷。
在外交中,双方在对话时,为达到己方的目的,有人有时也会运用一些语言技巧,《涑水记闻》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宋朝与夏国在边境问题谈判时,夏国的臣子薛老峰说:“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寨基。”[4]230意思是,夏国打算以安远、塞门寨基来与宋朝交换绥州。宋朝派去谈判的官员韩缜询问:“其土田如何?”[4]230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其四周的土田也归宋朝。薛老峰回答说:“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者乎?”[4]230大致意思是怎么有给人衣服而把领袖留下来的呢?他并未正面回答宋朝使臣的话,而是用了这样一个反问句,从最表面上来看,会话之间关联并不十分紧密,但其实通过推理,薛老峰是将土地比作了衣服、领、袖,这句话背后,常规的意思就是夏国会将寨基旁边的土地也给宋朝。韩缜相信了他的话,以为夏国会将寨基旁边的土地也给宋朝,他向宋朝廷上奏了,密院下达了“令追绥德戍人……不尽者焚之”[4]230的命令(与韩缜不同,经略使郭逵早就担心对方欺诈,有所防范,并未施行当时以为谈判成功后密院下达的命令)。结果等到交地的时候,夏国一方说,所献的只有寨基,不包括它四旁的土田。这时候夏国才明确暴露出真实的想法以及行动,薛老峰之前的话是误导。在会话中,一方刻意不直接回应对方的信息,以及运用反问语气,令对方误以为谈判成功。
薛老峰对韩缜的回答,还体现了“语用模糊”,“所谓语用模糊是指在言语的交际过程中引起话语理解不确定性的、模糊性的语言现象。”[7]217。虽然顺应一般的思路,他的话隐含的意思即为夏国会将寨基旁边的土地也给宋朝,但他并未明说,也并未直接承诺,他的反问句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可以被解释为只包含字面意思、与韩缜的问句无关(这样此句就违反了关系准则)等等,他的回答是模糊的,令对方误解。刻意选用这样模糊的表达,实际上也为今后己方的行动提供了一定可辩解的空间。
(四)对方式准则的违反
陆参在当县令的时候,曾判一诉状,在上面写道“汝不见虞、芮之事乎?”[4]63这令诉讼的人和县衙其他部门的人不解,后来,没办法只得再去问他,原来,他话中说的是来自《诗·大雅·绵》[8]192—194中的典故,意在呼吁讼者礼让。这样的语言用在状子上,对于诉讼者和一些相关部门来说,是晦涩难懂的,不利于立刻执行、理解,在那样的场合下,文件的语言应该选择准确、易理解的。
(五)小结
人们之间的沟通是灵活的,在会话中,人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进行适时地调整,这是一种圆通的处理方式。有时,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可以隐藏自身的真实目的、避免直接冲突等等,更有利于会话的展开以及目的达到。
三、巧用预设
“预设也叫前提,是指言语交际双方都已经知道的常识,或者听到话语之后根据语境可以推理出来的信息。”[5]116
宋太祖刚刚去世,关于下一任皇帝继位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牵动着朝臣们的神经,那时候的晋王在继隆等人的协助、催促下,及时进入了皇宫。在寝殿,宋后听到继隆到了,首先问的是“德芳来邪?”[4]20即,“德芳(宋太祖第四子[9]6272)来了吗”,可见宋后关心的是宋太祖第四子是否到达,而继隆的回答却是,晋王到了。宋后见到晋王的反应先是“愕然”[4]20,然后“遽呼‘官家’”[4]20,这里的细节十分精到。之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4]20希望晋王可以保她们母子之命。那句“官家”是对皇帝的尊称,那时候晋王还未正式继位,宋后已经做出了他为皇帝的预设,从宋后的话可以看出,她已经认可了晋王,即宋太宗继位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也是她在那样紧张的形势下选择自保的一种方式。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当时几方势力在博弈下惊险的“刀光剑影”。
四、讽喻
兖王耗费巨资造了假山之后邀请官吏们欣赏,众人皆赞美,只有姚坦与他人不同,低头不看,而益王强迫他看,随后,二人展开了对话,“坦曰:‘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4]35
在对话中,姚坦首先说出“血山”和反问句,这吸引了对方注意,令对方重视、惊讶、好奇,引发对方询问缘由,他再进而说出百姓在压榨下的惨状,目的是进行规劝,他的这一套策略是循序渐进的,王的“惊”和“问”就已经表明在会话中,姚坦策略的第一步已经成功。在接下来说明缘由时,语言很有力度,描述了他见到官府收税时百姓的血淋淋惨状,为“血山”这一论点提供充分论据,令对方无从反驳,姚坦的话语表现出他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权贵奢侈享乐行为的不满,“血山”讽喻出当时一些权贵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对普通百姓血淋淋压榨的基础上的。书中还提到,那时候宋太宗也造了假山,急忙命人毁了它。这也反映出姚坦那番话语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五、语用身份磋商
目前,学界对语用身份磋商的研究较少。“语用身份是特定的社会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运用甚至虚构。”[10]语用身份磋商在交际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交际中的一方有时会主动发出信号。
前面提到的材料中,枢密直学士张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宋太祖对李筠长子进行了一定震慑,他们的会话都体现了语用身份磋商。
枢密直学士张咏在对话一开始,以官职“钤辖”称呼对方,而自称为“咏”;宋太祖见到李筠长子,称呼其为“太子”。在现实中,他们相较对话的另一方,都是处于优势地位,甚至绝对优势地位(宋太祖),可在会话开始,他们却对对方的语用身份有一定的抬高,张咏更是在表面上将自己的语用身份放至低于对方的位置。
在这样的话语中,实际社会地位与语用身份的不对等、对对方语用身份的抬高,透露出了他们对对方的不满以及震慑(虽称呼李筠长子为“太子”,但宋太祖话语中的“汝”,也隐含了对其的不认可、不满),有趣的是,会话中的另一方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对此做出了反应,那位钤辖表示,他今天就出发去平定盗贼,背后隐含的是他不敢认同张咏的语用身份,也认识到自己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及对张咏心理期望的顺应;李筠长子不敢接上位者在话语中给予他的语用身份(太子),对此进行了拒绝,选择了与自己实际身份对等的语用身份(臣子)。
在这里,我们不禁思考,材料中的会话一方为什么要主动发出信号,进而令会话展开语用身份磋商?这样的表达较为含蓄,但以退为进,力度也较强。张咏虽然表面将自己的语用身份放低,甚至在话语中表示要与另一方在现实中互换工作,但是从当时的社会常识、环境等方面来看,这对于另一方来说是一种较大的震慑。宋太祖一声“太子”,令对方惶恐到用头击地,不怒自威。
紧接着宋后的“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4]20之语后,《涑水记闻》还记载了对方的反应:“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4]20—21这里也生动地体现了语用身份磋商。在紧张的形势之下,宋后选择了认可晋王称帝,称其为“官家”,而将自己放在了顺服地位,“吾母子”的说法,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凸显了自己的弱势地位,希望能保自己和孩子的命。晋王的回复,隐含的意思就是已经接受了宋后提出的这一“身份”,也约等于给了对方一个“保其富贵”的承诺。在这一场语用磋商中,宋后机智地给出信息,引导展开语用磋商,晋王自然、含蓄地接过了宋后给予他的语用身份,三言两语间,二人达成了一致。
在语用身份磋商中,双方你来我往,背后隐含了多方面的信息,对话双方出于自身目的或利益等,会对其语用身份进行动态调整。根据当时的语境、现实的情况等,作出合理判断,选择合适的语用身份,有助于事半功倍。
结语
《涑水记闻》中许多人物语言都十分精妙,文章主要从语用学角度分析了五个方面:一、言语行为;二、人物对四个合作准则的遵守与违反;三、巧用预设;四、讽喻;五、语用身份磋商。分析研究了其语用策略、人物立场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等情况,以期对古汉语、历史研究等贡献一份力量。同时这也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探索研究古汉语的思路和方法,这一方法有时甚至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1]40,巧妙的语言艺术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它对于当代依然“时新”。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应用语言艺术,对于当今人类文明和谐发展,依然会起到较大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