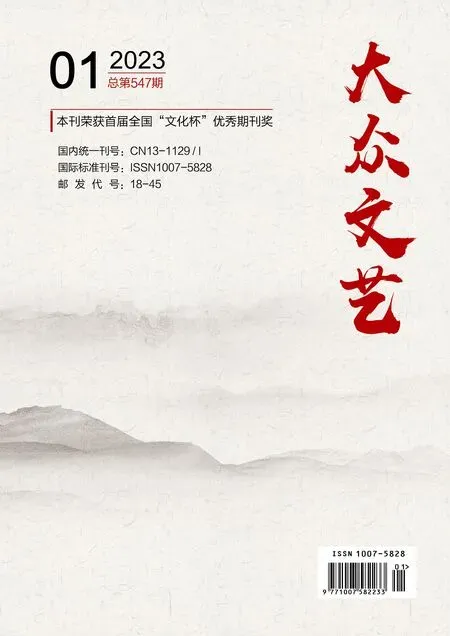网络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作者性表达
2023-02-22张强
张 强
(龙岩学院,福建龙岩 364012)
引言:纪录片的作者性问题
继《人生第一次》之后,秦博和他的团队又给观众带来了更为沉重、更具现实冲击力的网络纪录片作品《人生第二次》。较之前者,后者在制作和表达上都有了不少升级。如果说《人生第一次》给观众呈现的是一次勇往直前的冒险的话,那么《人生第二次》就是在描绘经历了跌跌撞撞之后的回眸,后者以一种更为清醒和笃定的姿态来表述生活中的疾风骤雨。《人生第二次》的总制片人张昊这样总结其创作主题:“与过去勇敢告别,在一片‘废墟’、一无所有上去重建、重启、重逢,涅槃”。[1]《人生第二次》的总导演秦博在本作之前作为总导演或首席编导参与了两季《人间世》及《人生第一次》的制作,获得了如潮好评。作为当今国内社会人文类纪录片的中坚力量,秦博将他的纪录片实践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诸多层面,让观众看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从艺术角度来看,该片在形式上以一种颇为风格化的方式完成了故事的讲述。具体来说,导演通过声音形象和叙事方式的个人化处理,让该片具有了丰富的作者性维度。
在电影的语境中,作者的概念一直备受争议。实际上,早在1913年,类似的术语“作者电影”(autorenfilm)就已出现了。[2]我们所熟悉的“作者论”(auteurism)的出现和确立多半要归功于《电影手册》杂志在1950年代的影评实践。他们将电影的导演指认为作者,于是一种电影观念就此诞生。不过,在谈论电影作者时,我们往往针对的是故事片,纪录片经常处于尴尬的缺席地位。可是,似乎也从没有人将纪录片导演排除在作者论体系之外。如果用作者论的眼光去审视纪录片的历史的话,许多我们熟知的纪录片导演都可被称之为作者型导演,而有一些以拍摄故事片知名的导演也拍摄了一些带有明显个人标签的纪录片①。因此,以作者论的视角去审视纪录片创作,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如果以作者论的视角讨论《人生第二次》的话,我们又会面临新的问题:谁才是真正的作者?作为一部系列纪录片作品,《人生第二次》的导演团队除去总导演秦博外,还有张涛、谢抒豪等十人。那么,这是一部秦博的作品还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文本?为了避免可能的争议和混乱,笔者在谈论到具体的文本时所使用的作者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和泛指,而并非具体的导演。当影片中出现一种创作者的主观性介入时,可以说,作者性显现出来了。
一、声音表达的作者性
诚然,“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一种构造物。”[3]作为一种“构造物”,纪录片的表达就难免主观色彩。对《人生第二次》而言,声音表达的作者性处理手法是随处可见的。通过对旁白和独白的灵活使用,该片在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上都显得相当丰满。
(一)旁白:一种批判的视角
在一般的纪录片当中,旁白(解说词)常常是一个外在于故事主体的声音形象。在《人生第二次》的“姊妹篇”《人生第一次》当中,旁白不是传统纪录片中不见其视觉形象的“纯声音形象”,而是较为创新的引入了“故事讲述人”的视觉形象。这些“故事讲述人”均由不同明星担任。在这里,明星的功能是双重的——既是一个视觉消费对象,同时兼顾了旁白的功能。这样的设定与其说出于叙事的考虑,倒不如说出于宣传和包装的目的。
《人生第二次》褪去了这种商业上的包装,让声音形象回归自身。纵观《人生第二次》的八集内容,只有第四集《拒》和第五集《是》以外在于故事的旁白来结构故事。除了对画面的内容进行解释和补充之外,旁白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一个评价和批判事物的视角。通过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在《拒》当中,旁白就在恰当的时机输出着作者的观念。本集的故事聚焦于争议不断的医美行业。镜头内,一个个被打上马赛克的“人造人”言辞铿锵地表达着自己整容的理由时,旁白适时而出:“前赴后继的人们,以现代医学为手段,以血肉之躯为材料,用近乎自残的方式,生产着美”,针对整容现象,旁白道出了原因:“景观社会,‘颜值经济’当道,催生了庞大的医疗美容市场”。这些旁白看似中立,但通过“自残”这样的字眼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者对“人造美”所持的批判态度。为了让此态度更为凸显,导演引入了一个对比性人物——16岁女孩冯婷——来解构畸形的美容产业。冯婷因病致使左脸畸形膨大,已到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程度,她才是最需要“整容”的人。通过这样一个“正面”人物的对比性呈现,导演最终传递出“修复重建始于内在,就像原野上的大树,绝不会因为外在的疤痕,丧失内生的力量”的价值观念。
总之,作为一种常规的声音表达形式,旁白在本片中建构起了一种批判性视角,进而传递出作者所想要表达的观念。
(二)独白:一种心理性和作者性的表达
独白成为了《人生第二次》的主导性声音形式。除了上述的《拒》和《是》两集之外,其余六集皆采取了独白的声音形式,从而使得观众能够更为深入地接近人物,去体会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声音形象既是可听的,亦是可见的。借助人物的独白之口,该片在艺术表达上获得了探究人物内心隐秘的更多可能。我们不再只是外在地观看人物,而是跟着人物的自白而进入其内心世界,于是,一种更富抒情性和心理性的表达便出现了。
《圆》一开场,我们便听到了一个丢失孩子的母亲的独白。从这段独白中,我们获知了故事的基本背景,同时,也通过母亲那颤抖的、带着强烈思念意味的声音而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怆痛。后来,找到孩子的一家人来到奶奶坟前祭奠时,母亲的独白再次出现,讲述了奶奶因为寻找孙子而不幸死去的往事,令人唏嘘不已。独白的情感色彩和心理性特征在此处显露无疑。
在最后一集《立》当中,我们常常能通过人物口中那极具文学性的独白感受到在平淡生活中涌动着的超越性力量。来自两位主人公——黄妹芳和李婷——的内心独白将她们对所生活城市的感受和自身的遭遇以极其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感染着每一位观众。四十多岁的黄妹芳依然在深圳的底层打拼,对年龄和时光的焦虑常常表露在她的独白中。朱自清散文《匆匆》中的时间感慨和黄妹芳的人生状态高度吻合,因而常出现在她的独白中。时间随时都会溜走,但未来不见得就如自己所愿。另一位主人公李婷,二十出头,正是拼搏的年纪,未来有很多可能,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深圳而去了东莞。对她来说,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故事最后,她也算实现了自己阶段性的人生目标,找了一份在办公室敲键盘的工作。她的内心独白不悲不喜,淡然地诉说着一切,听上去,竟颇有王家卫的味道——
“我不再拧螺丝,螺丝也不再拧我。车间和办公室只隔着一扇门,但是我却用了三年。现在的我敲着键盘,键盘也在敲我,键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这种文学性极强的内心独白使得该片在对人物内心的探索和表现上更显深刻,常见于故事片当中的手法在此时加强了观众对人物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恰好就是这样的主观性极强的独白,构成了一种叙事介入,使得作者的位置鲜明地暴露出来。显然,我们不能把这种人物独白看成是来自于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应将其视为人物和作者的一次“合谋”。正是在这种“合谋”中,作者性和人物的表达融为一体。
二、叙事方式的作者性
在秦博的作品序列里,叙事视角常常充满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出于“炫技”,而是和故事本身的内容和意义紧密关联,从而形成了每一个故事所独有的叙事特色。这些各具特色的故事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内蕴相当丰富的当代中国影像档案库。
(一)平民性:普通人与典型性
纪录片脱胎于电影发明初期的所谓“风光片”“新闻片”等类型,天然地和我们的社会现实相关。它几乎不可能像故事片那样凭空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出来,现实性是它的底色。因而,对普通民众的观照始终是纪录片的基本责任。不论是两季《人间世》《人生第一次》亦或《人生第二次》,一种平民性的视角始终贯穿其中。导演所选择的人物都是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再也不熟悉不过的面孔,这些面孔是如此陌生而又熟悉地出现在荧幕之上。《人间世》系列以医院为主要表现空间,以具体的人为叙事的切口,直接而凛冽地给我们呈现出了普通人面对病魔时的种种无奈、叹息和泪水。《人生第一次》以12个人生重要节点为轴,展示了每个生命个体的生老病死。《人生第二次》则将视角放在了生活中人们可能遭遇的种种危机面前,绘制了一幅虽然山重水复却终会柳暗花明的当代平民生活画卷。
在《人生第二次》里,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遭遇了生活危机的普通人。有渴盼被拐的孩子回家的母亲;有遭遇家庭变故的留守儿童;有因意外而瘫痪的年轻小伙;有因疾而致面部畸形的少女;有出狱后重新面对生活的男人;也有家庭幸福但为了一个城市户口而拼命努力的底层打工人。他们平凡,却也不凡,他们都在为生活而努力拼搏着。这种平民性的视角让影片特别富有生活气息,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在这许多人物所构成的坐标系内,如果说平民性构成了坐标系的X轴的话,那么,典型性就是坐标系的Y轴。出现在《人生第二次》当中的所有人物,都可看作是某种社会议题的典型代表。《圆》当中的王子强代表了无数为打击拐卖犯罪而奔赴一线的人民警察;《纳》中的何华杰代表了许多因意外而遭受身体损伤却仍坚韧不拔的人;《立》当中的两位主人公更是万千在一线城市拼搏的“打工人”的代表。通过这些典型人物,“人生第二次”这一片名所蕴含着的“改变”“重生”等涵义才有所附着。
可以说,正是平民性的定位和典型性的聚焦使得本片乃至于一系列秦博导演的纪录片作品具有了浓烈的现实质感。这种对时代变换中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成为了秦博导演作品的重要风格。
(二)多视点:一种多元的社会观察
《人生第二次》中,多视点叙事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叙事手段,而在其八个故事中,最具典型性的或许是第一集《圆》。该集的故事围绕一桩多年未决的拐卖案而展开,导演采取了三个人物的视点来展现这一故事。这三个人物是这出人间悲剧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母亲(占绪莲)、孩子(卫卓)和警察(王子强)。通过这些不同视点而牵引出的叙事网络,我们获得了体认故事的更为全面的视野,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拐卖事件给不同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多视点叙事的手段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上映于2020年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金刚川》,该片也采用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点为我们呈现了志愿军为了一座大桥的畅通而同美军展开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故事。应该说,虽然两片题材和类型不同,但在叙事手法上却异曲同工。在纪录片当中,这样的多视点叙事为我们呈现了现实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提醒我们,单一的视角可能会流于片面和主观化。
《圆》的多个视点构成了一个回环式叙事,也即每一次叙述的重新开启在时间上是一次回溯,同时又开辟出一个新的视点。而在其他几个故事当中,多视点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以回环的方式出现,而是在线性的时间进程当中各自发展。《缺》的故事虽然包含了诸多人物,但叙事视点主要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中学体育老师柏剑以及两个受帮助的孩子尹可心和金浩然。柏剑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爸爸”,他独自一人照顾着一群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问题。尹可心和金浩然是本片着重表现的两个对象。镜头除了表现他们在“梦想之家”的学习和锻炼之外,也跟随着他们来到了各自的原生家庭,让观众看到了赤裸惨淡的现实。这三个人物的视点叙事交织在一起,编织起了一个关于爱和奋斗的童话。
多个视点有时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的视野。在以医疗美容为题材的《拒》当中,导演刻意树立了两个从事医美行业的医生形象:韩啸和崔海燕。前者明言,做医美纯粹为了钱,后者则说,希望引领医美行业健康发展。同为医美行业的从业者,两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两个医生的视点之外,是众多“顾客”的视点。镜头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整容的理由。与这些以“近乎自残的方式”来获得美的外形的人相比,崔海燕接诊的冯婷是本片着重表现的对象。与其他人相比,她是更迫切需要整形的那个人。冯婷视点的引入使得片子从一种虚浮的商业主义氛围转向接地的生活层面,让观众看到了这个行业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与多视点相比,单视点叙事可以使叙事信息更加集中,因而更能凸显核心人物。《纳》和《非》便采取了单视点的叙事模式。《纳》记录了一个受伤瘫痪的年轻小伙何华杰的“成长”自立之路。全片以何华杰第一人称的自白展开叙述,在这样的个人化视角之下,他为了克服身体残疾而付出的努力便更富人性意味,观众也更能直接地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挣扎。同样地,在表现出狱人员毛徽融入社会的《非》当中,单视点叙事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单视点叙事能较为集中地呈现出具体对象的外在和内在的变化,而多视点叙事则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社会观察视野。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被灵活地运用在了《人生第二次》的不同故事当中,创造了丰富的叙事意义。
结语
《人生第二次》在哔哩哔哩和央视网上线之后,收获了如潮好评。目前,其在B站的播放量已超过4893万②,豆瓣电影也给出了高达9.1的评分,这一切足以说明该片的成功。该片在声音表达和叙事方式上做出了突破和创新,并以饱满的人道主义关怀和颇富作者性的表达手段,揭露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在充满酸甜苦辣的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这提醒我们,中国故事不只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也不只是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还有更多更多平凡人身上涌动着的别样风景。
注释:
①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徐童等纪录片导演就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贾樟柯等主要拍摄故事片的导演亦执导了数量不等的纪录片。
②数据截止至2022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