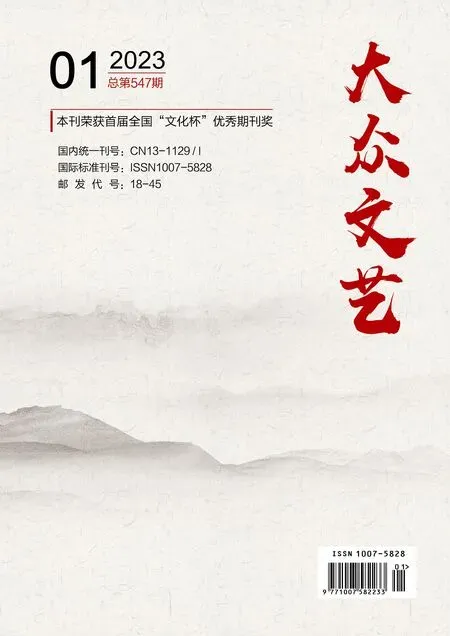台湾女性家园书写中的“父亲缺位”现象探究*
2023-02-22陈瑶王静
陈 瑶 王 静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因受到历史、地理与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女性文学具有较为鲜明的风格,呈现出集中的区域文学面貌。交错出现的殖民倒影、不断变迁的文化认知和独特的人文风情等共同汇成其文学创作的隐藏底色,并在行文中展露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家园书写作为台湾女性文学的诸多笔触中纷繁复杂的一笔,成为这一类别文学中尤为重要的主题。回顾总结台湾女性文学的创作历程,不论是五十年代作家集体性的旧地追忆、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的寻根之旅,还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家园坚守,作为贯穿文本的精神内核,家园主题一直以来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
在书写家园之时,作家多以怅惘怀念、博观多思的姿态抒发情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家园意象所指较多,从表层的家庭及其环境描写再到对精神原乡的追寻,或对文化传统的游离和回归,无不在家园意象范围之内。或迁台怀乡之异地书写,或失根飘零的文化困境,或历史洪流下的追寻安置之所,皆是女性文学对家园的多重定义。
一、模糊与消隐:“父亲”角色的意外缺席
在家园主题的书写中,有关“父亲”的描写不在少数。作为家园的代表性符号,“父亲”往往贯穿于家园文本之中,或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抑或是作为权威的隐喻,与之相联系的是更广大的权力与文化背景。但是,在这一主题之下,大量台湾女性文学却同时呈现出“父亲”的缺位状态——有的作为背景预设,有的则直观显露于文本——此种现象绝非偶然。
论其定义,“父亲”缺位不但可意味着“父亲”因客观原因消失在子女生命进程,也可指“父亲”角色本身在精神符号上的不成立。后者或与子女感情疏远,或较为漠视亲情、未尽父亲之责,都为“缺位”的部分表达。台湾女性文学作品在家园书写中易将角色置身于“父亲”缺席的前置条件下,或成为不幸的隐喻,或成为有意的漠视,而隐含其中的大多数思考则颇具批判性。表面上看,在书写家园之时将“父亲”隐去的行为如同似是而非的断裂,显示出对抗的倾向;然而“父亲”作为意象,本质是在家园书写中承担几重影响的出口,许多将父亲形象安排到缺席地位的文学作品折射出各异的文化心理。
部分“父亲”缺位现象与历史痕迹一同浸润着文本,在对“父亲”的怀念之中寄寓台湾独特时代背景中的感伤之情。如袁琼琼《两个父亲》,“我”在为迁台眷属建造的小天地眷村中无忧无虑地生长,生父袁一的猝然长逝使得“我”模糊了岁月的界限,将幼时的无忧无虑同眷村独属于“外省人”的成长经历一同封存:“父亲没有机会老去,我于是便不再长大,我把我自己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伴他”。①有作品将“父亲”比附家园进而将其延伸至文化传统,以“父亲”缺位意指与传统文化之疏离,进而在怅惘之中追忆地域特色,表达对传统民俗的人文认同。萧丽红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借女孩贞观的生活勾勒出台湾农家一派桃花源式的田园风光,其中贞观与故乡的联结和父亲的角色有着密切的关系,主人公离乡之触发点,恰恰来自父亲去世带来的诸多改变;而其返乡的故事,暗指一种返归地域文化、重拾民俗传统的尝试,透露出强烈的依恋之情。此外,也不乏借“父亲”缺位现象来反思性别关系的作品,通过“父亲”的消失来呈现女性生存状况中残酷的一面。此类女性书写进行了较富批判性的尝试,如李昂在《杀夫》中以主角林市幼年丧父作为背景展开悲剧性的描写,如影随形的“丧父”氛围深刻影响着叙述语调与角色心理,父系社会中失去了父亲庇护的她同母亲一道沦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给林市终生造成了深深的恐惧。林市举刀向夫的行为不仅代表了对性别统治结构的反抗、重新成为林市自己的渴求,也表现出林市对社会和性别双重压迫的激烈抗争。
除此以外,“父亲”缺位现象绝非仅仅意味着在家园书写中寄托个人情感,更意味着通过对民族精神内在的深入观察、两岸文化精神的隐含关联,来表达对当时社会与思想的深度探究。在“父亲”缺位基础上展开的国族想象是该类的典型,即父亲缺位只是契机,是作者们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不得不通过打破秩序核心展开的对民族和国家的多重审视。如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即讲述了中美混血儿莲儿前往美国寻找父亲的故事。莲儿本想有完整的“家”,甚至对外貌神似她父亲的表弟彼利产生了依恋,却发现祖国大陆才是归家之处,她在祖父母家中始终是一个“异乡人”。在美国衰败石头城景象和祖国百废待兴处境的相互呼应下,美国“生父”——同情且敬佩中华民族的生父彼尔——对他的寻找和莲儿生命的寻根重叠,但莲儿却发现:根在祖国。莲儿寻找异国长眠的生父生前痕迹的过程中,反而对当时劫后重生的中国充满苦难挣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民族的苦难、伤痕和动荡被一一辨认,巨大的情感力量由此迸发,正如她脱口而出的那句“我当然是中国人!”在充满怆痛的民族历史面前,外出游子们的心灵对民族则愈发展示着眷恋的柔软,有关家国的认知也不断清晰。
从以上维度看来,台湾女性文学紧密关联着时代,作者们以多维度的视角对“父亲”意象展开解读,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又表现出较为眷恋的情感。
二、思潮、历史与文化:“父亲”为何缺位
台湾时局历数次变更,文学现象也因时代动荡淘澄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台湾女性文学家园书写中“父亲”形象的消隐,其背后杂糅着文化传统、历史变迁、人文政策等多重因素。
以“五四”时期的文学为例,学者戴锦华曾评价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啻是发生在整个文化和观念领域的一场辛亥革命——一场规模大、效果显著的象征性弑父行为”②,这一时代的思潮饱含着对“父”及父系社会庞大体系的批判反思,对父亲批判化的处理倾向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女性书写中的叙述参考。联系台湾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自受“五四”影响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后才诞生这一情况,“父亲”缺位现象和对父权话语系统的批判通过大批迁台女作家的继续书写,将历史语态进行了自然移植,成为台湾女性文学家园书写中常见的文学表达。林丹娅所撰《台湾女性文学史》中这样评价道:“(迁台)女作家们的到来与继续创作使中国‘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经验在台湾得到活的传承”③。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书写在展开家园书写时,常对父权背后所指代的文学观念、社会思潮和封建秩序等方面展开反思,这一视角中的台湾女性文学继承了五四时代的创作经验和写作理念,具有较强的叛逆精神。现代大陆作品中那些挣脱父亲管制的、睁开双眼探索人生的女子们仿佛在台湾女性文学中得到了再生:丁玲《梦珂》中告别父亲而自由地探索诸多生命命题的梦珂仿佛又在台湾文坛出现了,在台北天空下以或倔强或忍耐的面目继续着故事;五四时期昂扬的思潮在台湾继续存留,即使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其精神未曾流落。女性文本中对“父亲”意象的缺位和批判处理,蕴含着书写传统的时代特征。
台湾近代有被反复侵占的历史,殖民倒影在台湾文化中留下了潜在的创伤性语调。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国家都曾殖民“台湾”,并或多或少地采取强制性文化手段施加思想影响。尤其到了日据后期,台湾人民多识得日文而非汉文,因语言隔离被迫留下了强制性的文化断裂;台湾光复后许久,当局文化审查制度较为严格、大量五四作家作品不得引介等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的“文化断层”,令作家在书写文学传统时常有“文化传统何以成为传统”或“何为文化传统”的迷茫;相应地,在书写“父亲”意象以及背后更大的所指时有“父亲是何真正面貌”的不确定游离。与此同时,另一种文化焦虑也对“父亲缺席”现象作出了解答。中国近代历史可看作一部在“睁眼看世界”思潮中寻找放置自我位置的历史,近代中国被侵略、被殖民的恐惧连同对自我的怀疑映射了否定性看过去的趋势,这种无意识的焦虑和痛苦加重了“怀疑父亲”的凝视,而不断变化的主流文化认同也为此种“怀疑”厚植了土壤。
历史的痕迹因此在台湾女性文学书写中表达得十分深刻。两岸分离、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等一系列事件让文学主体的分裂和危机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文学书写中“父亲”缺席的叹息如同“失根”的叹息一样沉重,女性文学对家园意象的处理也饱含了处理文化传统的尝试。琦君《云居书屋》写作者幼时伴着父亲在杭州云居山上书屋度过了一段宁静悠长的岁月,“我”的父亲生前再三嘱托要看顾好这满屋古籍经典,“我”却因战事损毁、奔走赴台而无法顾及,便有“回首当日与图书共存亡的誓言,不禁放声痛哭”④,文化之殇同失根之苦伴随着父亲留在了渺远的大陆,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楚流荡在字里行间。在文化传统以外,女性作为“他者”的心态常常隐没于看似寻常的文本间,以流寓心态辗转的女性在家园书写中消弭“父亲”之位,其行为凸显着失根的迷茫和寻找原乡的精神危机。《桑青与桃红》通过描绘主人公在重庆、北平、台北与美国四处空间流转的经历,彰显出强烈的无根之感,流浪于无依之地上,桑青分裂出与之性格截然相反的桃红,在混乱的生活中表达出身份的迷思。面对此种民族的历史性事件,作为女性个人的悲剧同时代的命运结合成为更深的家园思考,桑青之漂泊,同样映衬出家园风雨飘摇的处境,而以“父亲”缺席的形式表达,也恰映衬出主人公对旧家园复杂的感情——既受恩于其给养,却无法抑制地逃离。因此,在令“父亲”缺席的过程中,女性作家们对新家园的怅惘和旧家园的眷恋转为复杂的文化心态,伴随着殖民带来的文化断裂和历史文化焦虑慢慢浮现,其本身即代表着历史、文化多种矛盾的文学表达。
联系台湾女性文学特殊的文化语境,承接过往的诸多文化政策,上文从五四以来的“弑父”思潮、历史殖民传统和近代文化焦虑等方面考察了“父亲”缺位现象的动因及书写表达。不难看出,在以上因素影响之下,“父亲”缺位的设置类似于一种文化反思与文化探索,作家们在家园书写中最重要的一环“精神家园”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并在书写之中表达个人观点,她们对“父亲”及其所属展开的审视、思索、批判与重新接纳引人探究。
三、重拾自我:不再作为“女儿”之后
“父亲主题的嬗变潜藏着女性自身的心灵蜕变历程,是折射女性意识的萌芽和觉醒过程的一面镜子。”⑤前文提及,台湾女性文学之中,“父亲”缺席常作为行文背景,为故事的展开与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前提与动因。在分析过这一主题的呈现类型与内层原因以后,接下来将重点讨论“父亲”缺席实际所服务的故事前景中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有意的创作安排下,家园书写中与“父亲”主题相紧密联系的女性——“女儿”形象,作为被影响的客体存在,扮演了与“父亲”意味相承接的更为重要的角色,各异的书写往往有同样的目标:重建女性的精神家园。
法国哲学家拉康有“以父之名”的论述,意味着“父亲”这一符号具有家庭与社会的两重性:一方面,在亲属关系网织成的家庭内部,“父亲”被视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作为孩子的直系亲属扮演着陪伴者、引领者与榜样的角色身份;另一方面,在孩子从家庭关系网逐渐进入社会,即渐渐意识到社会规范、规则与随之带来的对于行为的约束以后,个人性逐渐被社会性所占据,孩子成长为了社会的一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父亲”进一步成了社会符号体系的代表,其象征着法权、父权和语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回观“父亲”缺席的主题书写,其一方面直观地表现为与父亲脱离、摆脱“女儿”身份、解放亲族关系的尝试,一方面又意味着女性脱离父权与社会规约、建构自我与主体性的倾向——作为父母亲族结构下的角色、社会一般认知以及子女自有特质的重合,通过“父亲”缺席,“女儿”试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离家出走”,她们获得一种流动的能量来置换出个体成长的空间,并开始搭建特殊的自我身份与精神家园。
就亲属联结下的父女关系而言,在涉及此主题的部分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中,肉身性的背离或断裂往往以两种姿态与心理呈现:一类女性角色主动地离开父亲,走上离家的道路,却在痛苦与抗争中疗愈失家之苦,在碰撞中体会未知:如心岱《空城计》中书写了“逆女”艾萨姬的故事,她虽受父亲娇溺且无忧虑地成长,却仍然在十六岁选择欺骗父亲离家出走以摆脱父亲施加的影响,“她宁愿不是父亲的女儿……她只有伤透父亲的心,才能使自己茁壮”⑥,她对亡故父亲的爱从未消失,却主动让自己和父亲都成为一座空城,借以孤独地开辟内心生天。一类女性角色则是被动地与父亲分离,然而在父亲缺位后逐渐实现了自我成长:如林海音《城南旧事》写女孩英子在北平的童年往事,却在终章对威严父亲的眷恋随着父亲的去世成为隐痛的苦楚,带来了审视性的转折,正如那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⑦,在父亲去世后,英子开始正视自己的成长。此外,这种与“父亲”的分离也会使得女儿们因缺少情感依托而在性格上走向极端,於梨华《小琳达》书写了女孩琳达父亲草草自杀后,琳达对历任家教——尤其台湾留学生燕心似爱似恨,她对这些生活在父亲自杀场所的老师们的感情令人难以辨认,在喜怒无常间表现出因父亲缺位展示出的矛盾人格:渴望爱却又拒绝爱,她用说谎和对外来者的敌意武装自己,琳达的人格因此分裂出截然相反的两面。
脱离了家庭,抹去了认知中的“女儿”形象以后,女性更易成为社会性的存在,进而肉身性的分离得以被扩写成与以“父亲”为代表、象征的社会符号体系的背离。纵观台湾女性文学,其中不乏将“令父亲缺席”后女性与社会接触的种种自我建构从单一接纳到多变批判予以刻画,以此让女性自我从单一、平面的抽象概念发展到立体的“人”。常常,这种社会性的接触首先让女性的地位与身份暴露得异常尖锐而残酷。李昂《她们的眼泪》讲述了收容所中林玫君等年纪轻轻便沦为私娼女孩子们的不幸遭遇,她们有父亲赠予的美丽名字,却因父系社会的漠视步入歧途。她们一派天真无知,直到在电视台的镜头前、处在社会的轻蔑凝视中才意识到自己的异类而抽噎落泪,这是一张定格的画面,在女孩子们的眼泪中,她们照见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社会处境与命运。在此种清醒却尖锐的认知基础上,女性以自我视角展开书写,进行着个人化情感的表达,同时对女性自身展开定位,即如何走出自我实现之路。朱秀娟《女强人》便讲述了女子林欣华的打拼事业史:欣华父亲早逝,高中毕业便拒绝了母亲和朋友等人的劝导自主进入贸易公司工作,从打字员职务做起一步步学习、施展才华并破除了种种商场中潜在的歧视,最终抓住台湾经济腾飞期实现事业繁荣。欣华毫无庇护地进入社会时,坚决拒绝了嫦秀等人相夫教子等传统命运的安排,一家一家公司不懈面试,直到成为“震洋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展露了女性的自我实现、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历程。
以“父亲”为基底,划其“缺位”的具体文本为肉身性的亲属关系与家庭外的社会关系,只是为了凸显文本主题的层次。实际上,“父亲”缺位的两重意味并非具有截然的区分度,而是交融在不同的文本之中:离开父亲,进而在社会中体认自身,随之锚定社会性的位置,以实现自我的成长、成人。以简嫃作品中的女儿形象为例,《女儿红》辑中所写女性多为孤独城市丛林间游走的挣扎者,在社会中寻找自我,在多面角色扮演中思考并学会理解、放置自身;文本也涉及女性独立和家园父系束缚等诸多问题。《哭泣的坛》写贞静女儿孑然一身面对社会的恶意,因寡言的性格为家庭漠视、在工作中饱受男性羞辱而自杀的惨剧,给家庭与社会抛出永恒的诘问;《亲吻地板》写女公关强人裹着厚厚伪装在工作中厮杀,谎称拥有家人陪伴庆祝升职的夜晚,却在晚间独身自处,以听小提琴曲、擦地板寻找认识本身存在;《女人刀》中有言振聋发聩:“她的父亲开启她对刀的癖爱”⑧,因“她”幼年目睹混账父亲对操劳母亲的谩骂,母亲回击时掷出的剪刀开辟了她的觉醒之路,对极具攻击性力量的“刀”的偏爱成了她生命的执着,她也终成为深刻思考两性统治结构的职业女性。
通过作家悲悯且富于观察力的笔触,台湾女性在“父系缺位”状态下对旧家园从怀疑到批判和进一步的思考,于社会的碰撞中逐渐成为更完整、更笃信自身价值的一批,以困惑、悲哀作点缀,以昂扬、勇气作点缀,成为女性本身,逐渐实现自我认同并追求自我实现。
结语
本文以台湾女性文学家园书写中的“父亲”缺位为主题,从其面貌、成因、内涵及精神特质作简要叙述。诞生于五四文学思潮、台湾特殊社会背景与文化心态中的缺位的“父亲”在文本中以多重方式呈现,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动因,在家园书写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借助“父亲”缺位,女性作家在台湾土壤中生出的家园情结,因她们的记录、书写与再创作得以反刍和重塑。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台湾女性文学借书写缺位的“父亲”对“父亲”文化符号后的隐喻如父权社会、传统秩序等现象展开延伸思考,在此过程中寻找放置社会和历史的路径;另一方面,女性文学试图借“父亲”的缺席重新体认自身,进而建造全新的精神家园,这也成了区域文学中独具魅力的思想现象。
通过对“父亲”这一存在进行重构与再理解,在回忆与想象间,女性文学重塑精神中勾连至深的彼岸,侧面诉说着血浓于水的联系,使“父亲”形象在异地进行接纳与迁移。作为区域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它同时彰显了两岸文化精神之黏连——此种黏连还将继续。
注释:
①袁琼琼.两个父亲[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40.
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
③林丹娅主编.台湾女性文学史[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64.
④琦君.烟愁[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15.
⑤黄发有.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J].晋阳学刊,1996(01):81-86.
⑥毕朔望选编.台湾小说新选[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46.
⑦林海音.城南旧事[M],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64.
⑧简媜.女儿红[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