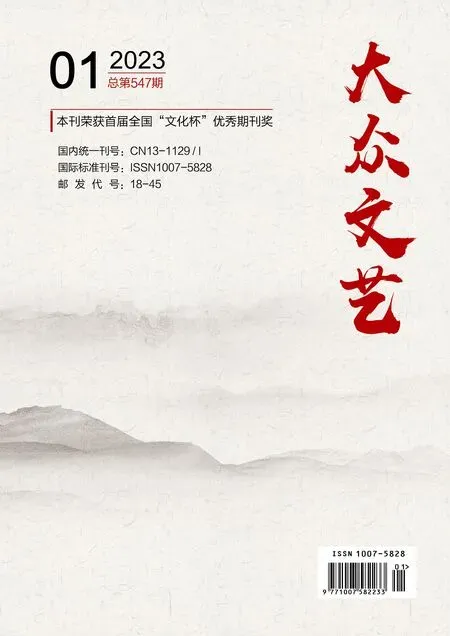古典音乐独奏教育之“神童热潮”反思
——以《音乐神童加工厂》为例
2023-02-22强文青
强文青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上海 200030)
古典音乐界似乎向来有着某种神话标签,“音乐神童”便是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5岁作曲的莫扎特似已成为每个独奏学生与家长心中的“神童典范”,人人心向往之;近年一个个音乐界冉冉升起的“神童”新星也无不给学生和家长们的野心点燃了希望之火——如德国小提琴家大卫·格瑞特(David Garrett)4岁学琴,7岁登台,13岁成为DG唱片公司史上最年轻的签约艺术家;华裔小提琴家李映衡(Christian Li)4岁学习小提琴,10岁摘得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Mehuhin)少年组桂冠,成为该比赛创办以来最年轻的一等奖获得者,12岁成为迪卡古典唱片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全球签约艺术家;新加坡小提琴家蔡珂宜(Chloe Chua)两岁学习钢琴,四岁转学小提琴,八岁时与李映衡并列梅纽因青少年国际小提琴大赛第一名。
各大权威音乐比赛的获奖选手及大师班学员逐渐向低龄化严重偏移,“神童热潮”已悄然而至。放眼音乐教育界,琴童的启蒙年龄也同样日渐低龄化,许多年仅六岁的琴童却有着高达四年的琴龄;家长们前仆后继,试图不惜金钱和心力地将孩子推上独奏训练之路。舞台的光晕固然绚烂,而光线背后的隐秘角落是否真的为野心勃勃的琴童和家长所了解呢?
面对古典音乐教育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唯有明确初心,了解独奏教育的完整体系,结合冷静分析和思考后再启程才能避免成为万万人中的无端牺牲者。
一、舞台背后——独奏教育的隐秘角落
《音乐神童加工厂》(Producing Excellence,2016)①原名为“Producing Excellence”,即“被生产的卓越”;与其中文译名《音乐神童加工厂》同样颇有讽刺意味。作者伊莎贝拉·瓦格纳(Izabela Wagner)女士是一位出身波兰音乐世家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小提琴独奏教育学生的母亲。瓦格纳女士将其深厚的学术基础与详细的社会学民族志研究手法结合进本书的写作中,她访谈了十几位古典音乐家、几十名独奏学生,建立339位独奏学生样本的基础上,她在音乐与社会学难得的双重视角下完成了这本著作。瓦格纳女士将理论分析与故事讲述巧妙结合,带领音乐界“局内”与“局外”人共同审视与思考这西方古典乐界精英独奏家的漫漫成长之路。
在本书中,读者们终于得以一览古典音乐界的传统又典型的精英独奏家培养图景及其在此成长道路上台前幕后所涉及的一切可能的人、事、物,瓦格纳女士甚至带领读者走进音乐家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一路以来所面对的掌声、汗水、失败与挑战。那些在舞台上闪耀着的身着黑色燕尾服与华美礼裙的无数音乐家们在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第一次被如此真实而完整地呈现。无论对于已行或将行至漫漫独奏路的琴童、家长、教师、音乐相关从业者、普通音乐学子抑或是对古典音乐界有着兴趣的圈外人士而言,本书的宝贵视角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然将其看作“劝退之书”或“逐梦指南”便因人而异了。
二、追逐“荣耀”或“音乐本身”?
我们常将音乐训练与运动员的体育训练类比起来——同样的高强度且持之以恒的积累,外加不可缺少的智能或体能天分。古典音乐演奏训练尤其如此。
小提琴独奏在整个音乐教育中属于“高等教育”,要求更加严苛,对琴童的天赋要求尤其高。但现在,这样的“音乐神童”却正在被批量化地训练出来,在这样的训练中,音乐教育正在失去她本来的意义。而这一意义丧失的音乐教育体系正逐渐缺失掉音乐的本心,沦为“工业化”生产演奏家的庞大“音乐工厂”。
我们常常提起“初心”,而对于演奏这种十分脆弱的职业道路,想要走上此路的人们究竟是抱着何种“初心”出发?倘若这“初心”并非发自琴童内心,而仅仅来源于琴童家长近乎偏执的“野心”,试问如此脆弱不堪甚至虚幻的“初心”又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一种竞争激烈、狭窄、又密度极高的人生呢?
在书中,瓦格纳女士也直言,多数琴童的独奏教育旅程是以琴童身后有野心的家长为起点的——不是“我喜欢”而是“家长希望”。尽管无论普通父母或音乐家父母都矢口否认自己对孩子的乐器选择施加影响,强调这是孩子(通常不满五岁)的天赋及自我选择,但不同处在于音乐家父母常因自身的资源积累及极富音乐氛围的家庭为由带领孩子走上独奏道路,而中产家庭的普通家长将艺术学习视为通识教育的优化与素质拓展部分。
尽管学习目标、挑选老师的手段、资源、与老师的配合方式都略有不同,但在“孩子必须在5-6岁之前开始学琴”这一点上所有家长达成了高度共识。目标明确之后就要参加心仪老师的试奏会或大师班争取与老师进一步合作的一些可能。巧的是每个进入独奏班的孩子都曾被贴上‘神童’或‘天才’标签,那些喜不自胜的家长很快会意识到这些标签不过意味着某种基础性入场券。
巴黎著名制琴师艾蒂安·瓦特洛(Etienne Vatelot)曾言:“天才很罕见,‘天才’的父母我倒是常常遇见。”古典音乐独奏教育界最常见的图景是——许多野心勃勃的父母怀揣着培养音乐神童的愿望将年幼的孩子推进了“音乐神童加工厂”。
艰难的独奏教育之旅正式启程,一切刚刚开始。
三、三方协作——赌上全部的竞争游戏
独奏教育的初期,由于家长需要扮演助教角色(辅助练琴),家长地对孩子的调教(乐器与心智)与投资(金钱与时间),对三方协作尤为重要。老师与家长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孩子的进取心,以“不能浪费天赋”为由竭尽全力压缩其他时间(社交、娱乐甚至学校教育的时间)进行相关器乐训练。
瓦格纳女士的田野调查样本中几乎所有小提琴手都承认曾有抗拒练琴的阶段,这之后他们逐渐习惯并能在自我进步中尝到快乐。这种快乐一旦形成,硬性任务就变成了自发的需求——正如古今中外的独奏家先辈们那般。
在合作中,家长们(无论是否是音乐家父母)与教师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是否能适当协调好这些决定了独奏学生是否能走过磨合期。通常这一磨合以家长的自我调整和妥协于教师告终——如家庭地理位置逐渐随着教师迁移也是配合的一方面。“跨国迁移”“多国籍”等特点让专业的独奏学生逐渐与兴趣班的业余小提琴学生区别开。
现代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曾直言:“竞赛只属于赛马,而非艺术家。”而这种竞赛对于独奏教育却如氧气般稀松平常。加入独奏班并卷入种种比赛竞争与社会审视的过程中,独奏学生与家长们逐渐明白了独奏教育有别于普通器乐学习的四大特点:独奏家职业的憧憬;大量的心血与金钱;偶像激励式的全身心职业训练;家长、制琴师、录音师等其他参与者的多方协同。
直到琴童接受并适应这一切,开始直面独奏世界的激烈竞争(包括独奏班残酷的内在等级),独奏教育第一阶段社会化的过程才初步完成。
四、难度升级——交替闪烁的危机与希望
第二阶段通常始于琴童对家长音乐方面参与的排斥。
随着琴童长大,他们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开始疏远父母,却由于特殊的成长与训练环境仍然与世隔离着。独立意识初具的他们惴惴不安地怀疑着自己与父母的决定——走上独奏之路是否正确。他们独自走过这段进步困难而敏感多疑的日子,不断修复可能破碎的自我,并依旧维持难度升级的高强度训练,同时学会面对独奏课与普通文化课加剧的矛盾。
这一阶段放弃的孩子并不少见。而坚持下来的学生们开始了他们的理想名师寻求之路并迅速进入职业接合模式。师生通过磨合逐渐更加符合对方期待而走向积极合作,这一阶段对学生心理素质有着极高要求,他们在纪律与自我中摇摆,在个性与顺从中游移。
在这充满变化与挑战的第二阶段学生们迅速成长,不断调整自己,直到他们在老师的音乐资源圈中成熟,并懂得如何进行职业与私人社交。最终他们会以强烈的单飞愿望终结独奏教育第二阶段。
五、初探现实:我们是无法独自存在的独奏家
随着琴童成长,更加成熟独立的独奏学生们愈发感到独奏课程进步缓慢时与老师消极合作便开始了。相比于老师的课程,老师的资源更加重要。学生们开始就如何独立进入独奏市场进行全方面积累,这一教育到了最后阶段不断增加的次要行动者们(指挥、伴奏者、录音师、音乐学家、作曲家、制琴师、赞助者等)的支持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昂贵优质乐器的获取、网络力量支持、独奏世界的人际关系与职业生涯等独奏教育社会化末端的现实问题浮出水面。所有这些影响因素如今甚至比真正的演奏技术更强烈地影响着初入市场的年轻演奏者们的职业生涯。
到此阶段的学生们急需一场重要的国际比赛为他们铺平市场道路。而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胜败如常的心态和直面失败的勇气。正如瓦格纳女士在书中所言,整个独奏世界都建立在信念和憧憬之上,一旦憧憬坍塌,布满荆棘的独奏教育之路便无法继续。然而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独奏家凤毛麟角,此时的年轻演奏者买要认清现实,并调整自己的规划,保持健康的心态努力便是此时最大的成功。
六、无路可退的独奏困境
众多样本的田野调查后,瓦格纳女士总结出独奏教育所需的非音乐特征:临场应变力、社交与自我推介力、外貌、随叫随到的学习态度、生活适应力及身体耐力、心理承受力、适当顺从与适当个性、语言学习力等。所有上述的非音乐特征有时恰恰是拉开独奏学生差距的关键所在(毕竟几乎所有独奏学生的演奏技巧都已极为成熟)。
瓦格纳女士以一位典型的成功独奏家成长历程为例,总结式回顾本书用众多田野调查样本所剖析的古典音乐独奏培养系统特点与规律,最后用历史视角对比古今独奏界,在更大的格局上用一切照旧的独奏界引发读者深思:未来的独奏界与演奏家们是否会一直照此规律更替?不公正现象是否有望改变?培养模式是否会被科技革新呢?
又或者,引起琴童及家长们更具体的问题反思——我是否适合?我真的准备好付出一切走这条独奏之路了吗?如果失败,我能够合理调整与接受吗?我为什么要开始,又期望抵达何处呢?
七、古典音乐教育界“神童”生产狂潮之时代“竞速病”
如今音乐教育界的低龄化竞速现象和“神童”狂潮似乎也正如时代病症般向社会各领域蔓延。一切都在变快,人类的耐心正在消失,不愿等果实自然成熟而选择使用催熟药剂,背后的代价果真要让年幼无知就被迫做了选择的孩童付出整个人生来承担吗?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曾在《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②一书中批判教育仅仅以技能训练的外部效果作为评判依据,认为此种做法忽略了过程中心灵的成长,以结果导向,本末倒置。以此审视古典音乐独奏教育中“神童狂潮”追求速度和名次,并以此为学习的出发点和驱动力;其本质正和杜威批评的心智孤立化不谋而合。试问一切材料都只是外物时,心灵如何真正进入问题领域并有所成长呢?
王承绪与赵祥麟曾在《西方现代教育论著》③中对著名教育家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n Heard Kicpatrick)的当代教育理论进行过阐释,指出教育的内化环节其关键恰恰在于投入时间去“经历”与反思,只有花时间去亲自经历并真正从内心认知与接受了某些知识,才算真正完成了学习的内化,这种经过时间和精力打磨而出的认知上的接受度恰恰决定了我们的内化程度——而这恰恰是当代艺术教育最缺乏的。
急功近利地“拔苗助长”是否真无代价?为达“超前学习”的目的,是否必然舍弃部分学习中本有的过程性以及心智成长,使用粗暴却高效的灌输式教学法?刘云杉教授在其《拔尖的陷阱》④一文中直言,僵化且视野狭窄的训练法,会损伤知识的系统与全面性,学生的天赋与创造力就是“超前学习”的惨痛代价。
若音乐教育只剩下拔苗助长式的竞速与机械化的技能训练,那么对这些被批量生产的毫无灵魂的拥有某些标准化技艺的孩子而言,丝毫不能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成长的音乐不是已然失去了最大意义吗?
结语:拥抱舞台之外的广阔世界
当今世界被效率和功利驱逐,耐心尽失的社会使得艺术界与教育界也难以免俗。天才当然有,但当艺术教育沦为生产卓越才能的某种“工业工厂”,我们如何能期待在这种工业气息浓重的“神童加工厂”中批量且快速“生产”出来的艺术家真正从灵魂上与内化了伟大的作品呢?又该如何保证在这条古典音乐独奏教育的赛道上失利的大多数琴童与家长能够不迷失于此,而付出整个人生为代价呢?
或许瓦格纳女士对于古典音乐独奏界所有绚烂背后的不公、泪水、压力、严苛的训练与渺茫的胜算过于真实地揭露,以及对独奏教育旅程中随时可能跌入的“竞速”与“功利”陷阱的强调都让《音乐神童加工厂》这本书稍显残忍,甚至成了圈内笑称的“劝退之书”。而“欲速则不达”这一并不复杂的道理,却常被我们这个超速旋转的时代隐去。
著名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他者的消失》⑤中反复强调知识、智慧的内化对于时间、实践和反思的需求之不可省略性。而今此种时间的过程性被侵蚀,其结果只能如同韩炳哲在《倦怠社会》⑥中所言——习惯了以优越成绩为自我衡量标准的学生把自我困在社会疯狂的竞争之中,这种竞争不只存在主体之间,甚至以无休止的自我竞争形式存在于主体内部,高压高速的竞争之下主体只能越陷越深,最终被失利时的自我责备吞噬。若这一切仅仅是始于千万个琴童家庭在“神童”光环中迷失,岂不是整个音乐教育界的一大悲哀?
真相固然残酷,但无论是常规教育,还是独奏教育,抑或是其他专业领域,通往精英教育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从无捷径可言,而这无关乎天赋。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天赋’也仅仅指克服困难的毅力与努力(如练琴的定力),而非某种不劳而获的能力。毕竟,对于教育与成长来说,面对困境时陷入“功利”与“竞速”怪圈而丢失初心远比任何困境可怕得多。
笔者以为,本书不仅不是“劝退之书”,反而是忠言逆耳的“逐梦指南”。正如瓦格纳女士所言,若你是出于热爱而准备开启独奏教育之旅的人,若你深谙本书的“逆耳忠言”也仍愿意相信音乐的美好,那么尽管向星辰大海出发吧,这本书便是是你们的启程赠礼。
愿所有即将或已经踏上音乐教育之路的学生与家长们能够不为光环所晕眩——看清初心,保持热爱,正视成败,去坦诚、理智且勇敢地追逐灵魂的成长,拥抱真实的理想主义。
注释:
①伊莎贝拉·瓦格纳.音乐神童加工厂[M].黄炎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王承绪,赵祥麟.西方现代教育论著[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刘云杉.拔尖的陷阱[J].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42期.
⑤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⑥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