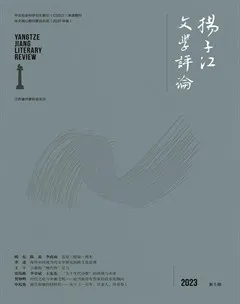传奇,抑或现实
2023-02-19刘小波
刘小波
阿来的写作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是对现实生活和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注。阿来多年来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尘埃落定》从历史出发,书写土司王朝的解体,关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遭际。《机村史诗》以机村为样本,书写乡土地方的裂变和农民的命运流转。《蘑菇圈》系列书写物质欲望膨胀带来的生态危机。《云中记》通过阿巴回村的所见所闻,串联起整个云中村的历史,穿插叙述了村子地震之前的状况以及地震之后的救援工作、灾后重建、移民搬迁等事件。《寻金记》承袭这些主题,并有所延伸,作品书写了以大金子为具体指代对象的物欲带给人的诱惑和对人性的戕害,同时也涉及很多更深远的问题,尤其是到了下部,金子失而复得,小说又开启了新的思考。
总的来看,阿来的小说对人性有着深度的揭示和发掘,并在人性书写的基础上有所延展,进入他的生命书写层面,具有显著的“亲生命性”a,体现出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和温情的人道主义光辉。阿来对地方有着很深的情结,几乎在同一块地方展开了自己全部的文学想象,作品有着显著的地方特性,大量的地方性知识蕴含其中。他的作品呈现了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同化、地方性消失殆尽的状态。与物质的地方消亡相伴随的,是文化的灭亡,是传统的消逝,作家只能用文学吟唱出一曲传统的哀歌。阿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历史的魅影始终在小说中浮现。人性、地方、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既是小说中多维呈现的主题,也是解读其作品的基本路径。
一、人性,或人性的延展
阿来的作品秉持着文学的基本母题,即对人性的深度发掘和揭示。无论是写历史的《尘埃落定》,写乡村生存状态的由《空山》 《荒芜》等组成的《机村史诗》、写汶川大地震的《云中记》,还是写民族史诗的《格萨尔王》、写生态问题的《三只虫草》 《蘑菇圈》等,都是从人性的基本立场出发,最终也都指向人性深处的某种隐秘性的一面,诸如欲望、贪念、自私、狭隘、偏执等。《尘埃落定》中土司间的战争及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纷争与仇杀,体现出了人性深处无法遏制的贪欲。《云中记》为逝去的同胞安魂,但是作品也写到消费苦难的种种现象。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是作者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云中记》中家具厂拖欠工资,刺绣姑娘因绣错花要被解雇等现象,以及很多受难者摇身一变,开始发灾难财、试图借着对苦难的消费而赚取高额利润,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现代化的批判又提升了一个层次。说到底,这些事件都指向资本,指向现代化进程本身,作家将时代反思和人性批判深度结合了起来。
《寻金记》仍是阿来这种写作伦理的集中展现,围绕着一座金矿、一块“狗头金”,偷盗、抢夺、杀戮、欺骗、贪欲轮番上演,人性之恶全部呈现出来。小说首先直接呈现了一种贪欲,这是因着财富的抢夺而引发的系列血案,是“人为财亡”的直观呈现。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更加能够体会人们对金矿的开采、保护、抢夺意味着什么。虽然具体的背景隐藏了,但是人性并没有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寻金记》书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对金子的争夺,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并无本质区别。在盗金者那里,大金子的价值被形象而直观地呈现出来,被置换为“三个老婆”和“几十亩地”,这成为他们用生命去交换的理由,很多时候盗金者其实是十分清醒的,无论他们怎样精心地谋划,也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无法抵挡此种诱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些人似乎都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人性中的贪欲则是最根本的。
在书写人性之恶的同时,阿来仍然对那些高贵的人格有着无比的尊重与推崇。《荒芜》中,机村在历史的洪流中也在发生着剧变,但是人性的淳朴与善良并没有受到绝对的冲击,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居民都是如此。当地居民收留了来自外地的驼子,驼子在翻身当主人之后仅仅是出于上面的要求而展开工作,主要还是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即便当地人指责他,他还是用温和的方式开展工作,虽然历史开了很多玩笑,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小说写到驼子的妻子在头人被打倒后还悄悄将头人的东西送回去,这并非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一种人的基本良知,感恩、回报、善良。《云中记》中的阿巴也是如此,他是云中村的祭师,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师,他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告慰亡灵,抚慰生者。《寻金记》也多次提及一些人有着自己的坚守,他们对善恶有着坚定的认知,即便是亲人,也无法认同恶的行为。作品中提及的土匪追风马的母亲,她对儿子加入匪帮无比愤怒,甚至还断绝了母子关系,有着自己的是非观与善的坚守。在小说中还出现了苦行僧形象,这些人形容枯槁,但是内心极其强大,有着坚定的信仰,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对土匪行为不认可的母亲、依靠自己辛勤劳作的人们、修行洞中的苦行僧,都是人性坚守的范本,清贫的生活、瘦骨嶙峋的身躯和伟岸的灵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人物形象,则是人性淳朴的体现,秉持着做人做事最基本的操守。
在人性书写上,深度开掘与描摹是阿来一贯的坚持,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揭示,但是,阿来的人性书写有很大的延伸,扩展到一种生命性的书写上,这就是阿来的“亲生命性”,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慈悲,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辉。《云中记》是典型的表达生命主题的作品。一直以来,阿来的书写都有穿透表象而直抵内里的功力。《云中记》是一部灾难主题的作品。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年,作家阿来出版《云中记》,首先肯定是为数万逝去的生灵安魂。这场大灾难夺去了无数生灵的性命,需要有人为之安魂,为之铭记。小说关于灾难的书写并不全是苦痛的记忆,虽然阿巴回村之后到每家每户去安魂,勾起了有关逝者的记忆,包括自己的亲妹妹、胖老师等,哀思油然而生,但是作者也写到了生命的坚韧和不屈,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重组了家庭,那些因伤致残的个体,慢慢恢复了生存的活力。小说主体上是写灾难,演奏安魂曲,落脚点却是现世的人们,如何抚慰他们才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十年过去,活着的人们有着怎样的生存现状,是作家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寻金记》有着很明顯的历史魅影,但人性书写是其基本的脉络。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对人性恶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里面。《寻金记》多次写到死亡,更写到死亡以后的尸骨无存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小说有不少地方描写了这种惨绝而血腥的场面。这是一种警示、也一种悲悯,是对突然消失的生命的沉痛哀悼。小说在一些细微处也以一种悲悯之心写到了人们生存的艰辛,尤其是几位女性的出场,虽然笔墨不多,但是都具有震慑性,动荡的时局让人们的生存显得尤为艰辛,不得不采用了各种铤而走险的方式。悲剧是人的贪欲,也是时代使然。作品写出了人的卑微与渺小,死亡在转瞬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如同草芥,正是这样的书写,体现了作家的一种“亲生命性”,是对逝去生命的不忍、同情,是对生命的向往和尊崇。《寻金记》主要围绕人物来展开,小标题便有着一定的暗示性。明面上,军队主导的金矿开采是为了大后方建设、为了抗战,实际上是各种势力借机扩充自己的利益而已。寺院、军队、匪帮、堂会、百姓等力量在这里交汇。法王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跟踪和伏击,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一次次重复。在这样的局面之下,牺牲的就是最卑微的个体,从金麸子、哨兵,到开店的百姓、匪帮的成员,堂主的替身,一个个先后殒命,还有那些在一次次械战中丧命的士兵、喇嘛、土匪。这些生命的逝去无疑是令人悲痛的。而这些贪欲的根源,也都被一种“荣归故里”的朴素愿望阐明了。每位盗金者都有他们迫不得已的理由,生命的无奈可见一斑。
和《云中记》对生命的安魂有着同样的主题,《寻金记》先后写到数十人为此事件丧生,除了有名有姓的偷盗大金子的人们,还有几股势力在为争夺金矿进行武斗时丧命的无名之辈。当然,作家设置了特殊的年代,从历史的角度来为人性解围。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个体似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以生存,被迫铤而走险,即便他们自身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除了肉身的生命书写,阿来也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阿来作品中有明显的生态主题的表达,而这种生态包括自然界的,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态。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对生命性问题关注的进一步放大,从人类拓展到万物众生。“博物”与“博爱”天然地连在了一起,希望遵循自然界本来的面貌,这也就是阿来作品中的生命性主题。《寻金记》写到的悲剧也和无止尽的金矿开采有关,都是从根源上来阐明问题。从单纯的人性揭露,到一种亲生命性的书写,让阿来的写作有了更加深厚的底蕴,也有了更多的亲和力。
二、地方,或地方的超越
长久以来,阿来的书写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小说中出现的地方几乎都有据可查,都和生养他的那块故土有关。阿来深受影响的文学传统也是地方文化的承袭。巴蜀大地上的灿烂文化给了阿来无尽的文学养分。可是地方性正在逐步消失,阿来无时无刻不对此保持一种担忧。《机村史诗》书写森林的乱砍滥伐、土地的荒芜、村庄的消失,《蘑菇圈》 《三只虫草》书写地方的物产被无止境开采,直到消失。《云中记》书写云中村的消失,乃是书写地方的消失,当外界的资本力量出现在村子的时候,消费苦难、消费地方的行为必然发生,也注定让地方被同化,地方特性逐步消失。村庄、植物、动物的消失,直至文化的消失、传统的消失。外界的同化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比如《云中记》中出现了两套语言体系,央金突然回到村庄,按照外界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
《寻金记》多次写到了当地人的传统,同时也不断写到外界对此的开化甚至同化管理的问题。虽然作品一直在试图保留那一丝的地方性,无论是语言、信仰,还是传统、山神崇拜、劳作方式,但是,地方被同化是必然趋势。《尘埃落定》 《空山》 《蘑菇圈》 《云中记》 《寻金记》无一不是写地方性的消逝问题,同化是必然,民族性、地方性何去何从?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消逝,还是一种地方文化和传统的彻底沦陷,地方性消逝,更能让外界的不良风尚引进来。
阿来的书写集中在巴蜀大地,尤其是康巴藏区,这是一种怎样的地方路径,具有一种苍生的关怀和人类的胸襟。《云中记》书写地震灾区,《寻金记》向前追溯,依然还是集中在这片土地上。很多场景直接使用四川方言来描绘,具有一种现场感,这是从某一个地方,从更深处来书写全局。
阿来的文学传统也和地方有很大的关联。继《云中记》之后,阿来推出了《寻金记》,这种小说命名的方式很自然地和四川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如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淘金记》 《困兽记》 《还乡记》、马识途的《夜谭十记》联系起来,而《寻金记》与《淘金记》更是“形神兼备”。很显然,阿来对四川文学的传统有致敬的意味,也有突破表达的渴求。这种历经多代作家建构起来的传统,无论怎样挖掘,都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的“金子”。除了题目上的相似,《寻金记》和《淘金记》在内容上也有不少相近的地方。《淘金记》描写的地方是四川的一个普通乡镇——北斗镇,镇上的各色人等都有自己的生存门道,其中不少是金厂主,这些地方上的恶棍,趁战争给后方社会带来大变动,兵荒马乱成为他们发横财的机会,抗日救国也仅仅是他们的幌子,其目的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腰包。小说中写到的“向一个原先产金旺盛的山墩,一对富孀母子家的 ‘发坟,苍蝇逐臭似的一齐进攻,而又相互间剧烈地勾心斗角。他们的心机复杂得不下于道格拉斯飞机厂里的新机器,而得心应手的作者,却跟高悬在这些可恶的可怜虫上边的一个命运似的,稳稳地作了他们的主人”等内容,一种讽刺和批判的味道跃然纸上。阿来则要内敛一些,再进行时局书写的时候,更加隐晦,也更显深刻,与沙汀、艾芜那种显露的讽刺手法稍有不同。同样是写时代的黑暗,并不仅限于一种无节制地控诉。
承襲这一主题之后,阿来又进行了怎样的续写呢?虽然不能轻谈超越,但阿来的《寻金记》与《淘金记》相比,的确有不少更精进的书写和更深入悠远的思考。至少从地方这一层面而言,有一定的超越。阿来延续着“金子”主题,描摹试图将一块金子据为己有的各色人等。在哈克里金矿上工作的金伕和哨兵共同盗走了一块六十多斤的“狗头金”,随后引发了一众人等的追逐,也接二连三地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之丧命,“人为财死”的主题凸显出来,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而故事的另一条线则是代表着官方调查员对此事的调查,直到小说结束,调查员也没有见到大金子的真身。阿来和沙汀关于“金子”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相同的人性批判意味和讽刺意味,这些金厂主们是十足的恶棍,为了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媚上欺下,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小说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度描写。阿来依旧书写由人性之恶带来的各种膨胀的物欲、贪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次血案。
三、传统,或传统的消逝
传统与现代的对举是阿来小说的常见结构。对传统的漠视或是所有问题的症结,阿来对此多次表达过担忧,“在肤浅地热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并不是念动‘天人合一的咒语就可以遮掩掉我们文化基因中对于环境问题的漠视,比如黄河流域生态的全面衰败并不是这几十年间才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关的还有,在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支配下,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冷漠或拒绝”b。在阿来看来,虽然我们对传统有着表面的热情,但实际上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是冷漠的。阿来多次在作品中描绘了传统认知结构中的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如今正在逐步消亡。比如《鱼》写到人们开始吃鱼、钓鱼了,而这曾是人们的禁忌,在曾经的习俗中,鱼是一切不洁的宿主,而现在打破了传统的禁忌和崇拜。其他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这一点。《天火》中外来力量以“破四旧”的名义对敬畏神灵的传统进行了肆意破坏。《空山》中提到了色嫫措湖的神话,色嫫措湖是机村的神湖, 机村过去干旱寒冷、光秃秃的一片荒凉, 后来色嫫措湖来了一对金野鸭, 从此机村生机盎然。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但是在一个功利与仇恨成为动力、政治极度疯狂的年代, 金野鸭的神话传说被斥为封建迷信, 当机村的森林着火之后, 指挥部决定炸开湖泊引水灭火, 湖底却塌陷了。吃鱼、“破四旧”、神湖的消失等等,其实都象征着传统的消逝。
《荒芜》也是对此的全面呈现。就连土地这一人类最依附的东西也变得无足轻重了。驼子一生都在坚守着最基本的信条,开垦土地、种粮食,但是这样的传统一次次遭遇了冲击,“科学经验”让他们的小麦因施肥太多而歉收,“油锯”让一片片的森林消失,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严峻后果;人们放弃地里的庄稼,去挖松茸、卖木头。传统的耕种方式和生活习惯遭到了冲击,“科学经验”“油锯”“卖到日本餐桌的松茸”等等都是直接和传统相对的事物。阿来在小说中思考问题一向很深入,与一般的歌功型文学不同,他独特的身份以及对第一手资讯的掌握,让他能够准确获取事件背后的东西,并通过小说表达出来。《云中记》实际上是写一个村庄的消失,通过一个村庄的遭遇,阿来写出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写出了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冲突,也写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面临的各种困惑,最终落脚点仍是现世的人们。《云中记》也是一种对立的模式,虽有对话的成分,但还是将这种传统的消失写了出来。在《云中记》中,舅舅阿巴与外甥仁钦其实是最能体现这一冲突的对象,仁钦读过大学,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而阿巴还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思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更像是互相包容,彼此都留下了一些敬畏。特别是,阿巴回村属于移民回流,仁钦的工作是劝返,但他情愿被撤职,也没有强迫自己的舅舅,这其实也流露出作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但是阿巴和仁欲之间依然还是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云中记》多次写到传统与现代对立下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移民村,阿巴他们只能被叫作老乡,此外,他是家具厂的工人、少数民族人、村里的祭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乡干部仁钦的舅舅,等等,这一系列的身份让阿巴每每陷入困惑,因为很多身份有着相互抵牾的地方,这些身份的纠缠让阿巴无法安放自我,与他一样备受身份煎熬的人还有很多,仁钦也是如此,他是党员干部,但同时又是云中村的后代,所以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也比较为难,从这一角度出发,阿来从传统的裂变中写出了人存在的各种困境和困惑。《云中记》还写出了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的复杂和艰辛,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灵魂的冲击。机耕道、拖拉机、水电站、录像厅、旅游开发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和象征,山泉水、传统石磨、马、“告诉”、祭师、喇嘛庙等等,又是传统生活和文明的代表,这块土地似乎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剧变,云中村人身上曾有的特殊味道消失了,就连他们的语言,也受到了外来力量的侵袭,加入了很多不属于自己的新字与新词,形成了两套语言体系。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还体现在移民工作的艰辛上,很多村民对现代化的进程是不理解甚至有抵触心理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才会围绕搬迁的问题发生特别激烈的争执,移民搬迁工作极为艰辛,也可以说干部们的每一项工作都很艰辛,因为村民对很多东西不相信,这种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艰难的表征。比如小说写到干部劝大家搬迁时,村民说相信国家,不相信科学,这是很有意味的细节,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相遇,愚昧与科学在这里交锋。在很多村民眼中,现代文明扰乱了山神,甚至灾难的发生都与此有关。干部们出于好心,将村民集中安置,可在村民那里,这却是一种背井离乡的行为,这些矛盾冲突考验着所有人。小说对现实问题深切关注,如灾难之后的被迫迁徙,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冲突,对活着的人们带来更大的考验。
《寻金记》同样如此,小说还是对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冲突与交融关系的深度透视。小说写到了军队对金矿毫无节制地开采,引来寺庙喇嘛的惊慌和不安,但是他们抵御的方式是古老的、传统的,“咒语”对上现代化的武器,胜负已然分了,这是传统的东西面临现代冲击的一种写照。小说中还出现了采集高原植物标本的美国探险家,而采集标本、测量雪山、绘制地图的行为被当地人看成是“偷走国家宝贝”的行为,下冰雹毁坏庄稼也和外国人使了法术联系起来,书写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是阿来一直以来的写作母题。
上述种种问题,都是因传统文明遭遇现代化冲击而产生,明面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生态的问题,指向自然的生态问题,其实也有精神世界的生态问题,生态的荒漠化也是文化的荒漠化,生态问题,或许也是存在的困境。总的来看,阿来对传统怀着很深的敬畏之情,对传统的消亡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不过,阿来对传统和地方文明并非一味认同与迁就,还是有一种理性的思辨,有取有舍,对民间的认知模式有明显的引导和梳理,比如他将匪气、义气与人性应尊崇的基本道义进行了区分,将民间信仰和一些打着民间旗号的东西进行了区分。传统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消亡,需要留下点什么,写作的意义可能莫过于此。
四、历史,或历史的魅影
历史的影子始终在阿来笔下浮现。《尘埃落定》书写土司王朝及其退场的历史,《格萨尔王》书写民族发展的史诗,非虚构作品《瞻对》书写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对历史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考察。《荒芜》涉及的历史更多,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土司管理制度、解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都曾对村子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只不过人们更多还是和具体的人和事产生了关联。《寻金记》也是历史主题。阿来的历史表达并不采用正面强攻,而是惯用迂回策略,用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流转来书写历史的进程。
《寻金记》的故事有较为明晰的时间线索,是较为明确的历史书写,涉及边地开发、金矿管理、川军抗战、四川匪患等等历史事件。川军、匪帮、堂口、寺院等多种力量,围绕着金矿来展开。在书写盗金故事的同时,小说将历史一点点还原出来,地方割据势力的建立,现代国家与古老部落的较量,战争的风云无时不在,直到反复出现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前线与后方。《寻金记》中历史的魅影时时闪现,作家用清晰的时间来标注故事的时代背景,但是他仅仅从背景的意义层面来书写历史,关注点还是在于那些被困在时局中的个体。这既有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更多的还是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其人生道路的抉择往往是在历史的外力支配下形成,具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被迫性。阿来将历史书写和人性的剖析结合起来,将“丑恶年代”里丑陋的人性表露無遗。
阿來在写作深处对大的历史还有一定的警觉,不少地方是对历史的回溯,对那个兵荒马乱的时运、时局具有深刻洞察,那是对无论贪者、恶者还是有望者、有志者都无法相互长久善待的境遇,物欲的事体与人性的悲剧,在笔法细致环环相扣的历时性、共时性叙述中,让一个个筋疲力尽的人的故事,成为步步惊心的传奇,串联起声声入骨的浩叹。至于下部,将讲述进入新的社会大金子失而复得的故事。在历史选择的铁律与小说方式的微妙间,作品显出审美的无穷张力。
阿来关于历史的书写不是用新历史主义的腔调和解构主义的色彩进行戏谑,也不是抱着重塑历史的野心来书写革命和传奇,而是一种生命书写的延续。他努力去寻找生活在历史缝隙中的生命个体,关注他们的命运,关注作为人的历史主体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尘埃落定》书写改土归流的宏大历史进程,在文本中除了关注到土司家庭的生活,也透过叙述者的视角关注到了仆人这些本不起眼的人的生存状态。《云中记》并不是站在时代的进程中去回溯灾难,而是对遇难同胞的悼念和安魂。《寻金记》通过历史上对财富的争夺,其实也指向了一种对当下财富观的思考。
当然,阿来的历史书写也有一种“民间”的意味,《寻金记》的整个故事采用了全知视角来展开,大致的故事就是“盗金”和“抢金”,整个故事如同一位说书人在向听众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所有的细节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真实史料的支撑,有历史的成分,更多的还是经过了民间流传以及“说书人”的杜撰、提炼和加工,成了一种民间传奇。最终大金子神秘消失,代表着政府的调查员,也没能见到大金子的真身,愈发加深了这种传奇性。《寻金记》书写了在西南大山中的金矿上的大金子被盗走,从而导致了一个接一个生命的消逝。作品讲述了一个隐喻颇深的寻找故事,这种寻找主题很多时候超越寻找之物本身,乃是对物欲与人性的深度描摹和批判,人性深处的很多特性并不随着时代发生根本的改变,年年岁岁景致大体相同。《寻金记》书写的是动荡年代的贪欲,据悉下部还将书写金子的失而复得c,作品的时代背景更近,依然还是这些主题。
这些似乎都是文学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有不同的演绎,这并非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彰显了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同时,作品通过召唤逝去的东西,来反衬现实,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确立当下生活的意义。抚慰在世和活在当下的人们,才是作品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小说书写的故事集中在云中村,主要是围绕曾为云中村祭师,现为移民村家具厂锯木工人的阿巴展开。地震之后,云中村整体搬迁,阿巴也是其中一员。《云中记》中的央金后来的悔悟,让她能够继续跳出优美的舞姿,很难说不是一种理想寄托。相关的书写具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后面关于阿巴的书写理想化色彩更加强烈。在大地震发生四年之后,阿巴回到云中村,为逝去的村民安魂,祭祀山神。他回村之后便着手准备祭祀山神的东西,最终举行了一个人的祭山仪式。小说的章节基本上是以阿巴在云中村所停留的时间命名,安魂之后,阿巴并没有离开,而是在云中村过上了曾经的近乎返璞归真的生活,到最后,他走向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在多部作品中,阿来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块净土,这是灵魂的栖息之所。
在经历了多年的创作累积后,阿来的小说有着太多太丰富的主题,几乎每一个细节的设置都有作者对现实、对历史、对未来的思考。这是作家的视野和胸襟所决定的。但阿来并不是单靠主题制胜的作家,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学的警醒和自觉,他对文学性始终怀有敬仰。比如小说涉及对历史进程的反思,阿巴的父亲,生在了不允许有祭师存在的年代,而到了阿巴这里,祭师被称为了宗教从业者,是合法的存在,但是祭师的事业却没有多少人关注了,甚至村民都不再信奉曾经信仰的苯教。再比如阿来的小说常常采用非自然的叙事手法,这实际上是对未知事物的虔诚。在《云中记》中依然使用了很多非自然叙述手段,如阿巴创造了神迹,创造了一片世外桃源,这种非自然叙述的根源还是对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敬畏,也是其作品深刻性与丰富性的体现。
《寻金记》的故事性很强,甚至滑向了一种“故事会”的文风,悬念迭起、疑窦丛生,通俗性很强,这或许是作家有意而为之:“在这部小说中,我尝试了新的小说写法,故事、人物,都是传奇的写法。”d研究者也因此看到了“他叙事转捩的可能”e,但即便如此,阿来依旧没有丢掉文学性的坚守,他十分注重语词的锤炼和细节的把握,同时也注重主题的翻新,而主题已经预示着最高的技法。《小说选刊》评价《寻金记》时说它“活色生香,台词明艳”f,这正是阿来追求文学性的结果。多年来,阿来不断改变着行文风格,努力避免自我的复制,文本也显现出一种多样性,但恒定的主题又是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心的表现。
【注释】
a孟繁华:《一部绝处逢生的杰作》,《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b阿来:《为了明天而记录昨天》,《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增刊(特刊2卷)。
c《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
d肖姗姗:《〈寻金记〉亮相〈人民文学〉新年首刊 阿来:尝试全新写法,现实足够传奇》,https://cbgc.scol.com.cn/news/2818305。
e张译丹:《从〈寻金记〉看阿来叙事的丰富性与转捩点》,《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
f《小说选刊》编辑部:《卷首语》,《小说选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