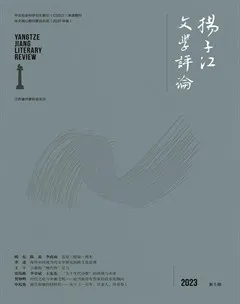论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
2023-02-19李商雨
李商雨
2022年7月,韩东出版了诗集《悲伤或永生》a,这部诗集所选诗歌跨度四十年,清楚地体现了韩东诗歌的总体风貌:从1980年代初到2021年,韩东的诗歌和诗学在根本上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逐渐演进、逐渐丰富充实,并且其发力点逐渐清晰集中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表征了四十年来当代新诗“崭新传统”b逐步确立的轨迹。研究这部诗集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对韩东诗歌的诗学研究,也是通过韩东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的一种重要诗学演变路径进行梳理。本文认为,韩东的诗歌体现了当代新诗始终朝向诗歌本体的一面,是汉语诗歌非历史化写作结出的硕果,其中所体现的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显示了新诗既可以保持诗歌高度纯粹,又可以拥有处理诗与现实关系的能力。这种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感觉力,充分体现了在21世纪的今天,汉语新诗在此“崭新传统”下,可以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本文以“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概括韩东诗歌的总体诗学特点,在此过程中,也讨论四十年来汉语新诗在非历史化写作的向度上的新的可能性。所谓“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是指诗人在写作时以一种平等、无分别的“世界意识”对待和处理日常生活,捕捉日常生活在心灵中瞬间生成的感觉,并用语言准确地在诗歌中呈现。这种感觉是诗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瞬间的直接意识,它不含分析、比较的过程。此感觉连接了诗人个体的身体和具体的日常生活,从而让诗人个体与日常生活达到物我合一的境地。以此方式生成的诗歌,使得诗歌回到诗歌的本体,因而在最大程度上赋予诗歌以感性自由和审美价值。日常生活感觉力具有无限性,诗人感觉的敏锐、细致、清晰和精微的限度决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可能达到的高度。
一、韩东诗歌的诗学发展脉络
对于中国当代新诗而言,韩东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诗人。他从18岁开始学习写诗,到2022年已经四十三年c,这四十多年,韩东不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历史,而且还参与其中,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他与朋友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起创办的民间诗刊《他们》,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这份刊物体现出的诗学观念,影响了几代写作者。尽管韩东声称最初“创办《他们》时,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的发言”d,但是刊物本身却显示出,这是一份具有明确诗学主张的刊物。《他们》所刊发的诗歌明显体现了这个诗人群体共同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即他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让“诗歌成其为诗歌”。e他们所看重的是诗歌的本体性,而不是诗歌的功能性;他们的写作追求的是新诗的美学现代性。
韩东作为《他们》的灵魂人物和“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他从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开始,从来都没有偏离过自己的艺术理想。可以说,他用四十年始终不渝地追求的就是诗歌的真和真的诗歌。这“四十年,对于一种新诗传统的建立不算短时,但对原则上面向无限的深入而言耗时也不为多”,然而毕竟“一个确实而不无丰富的崭新传统”已经建立起来了。f如今,回顾这四十年的中国诗歌,透过纷乱的现象和杂音,还是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当代诗歌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有许多诗人立足于诗歌的本体,一直未尝中断对诗歌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一个“不无丰富的崭新传统”。这个传统由若干诗人建立,而韩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对韩东诗歌的判断,应立足于四十年来的诗歌史事实,只有透过各种纷乱和杂音,才可能辨认出韩东诗歌的价值。这四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第三代诗歌”时期,起点在1980年代初,高峰阶段在1980年代中后期;第二,是当代新诗发展的混乱期,时间从1989年到1990年代末,这一时期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但“第三代诗歌”的主要代表性诗人依然在写作g;第三,是网络新媒体时期,时间是21世纪以来。韩东的诗学最初是在对其前辈诗歌的反思中确立的,具体来说,是在反对杨炼《大雁塔》h一诗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诗学。
在1990年代,韩东置身当代新诗发展的混乱期,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诗学上延续了1980年代的思想,并写下了《甲乙》等著名诗歌i。值得注意的是,韩东这个阶段写的《小姐》一诗,触及现实问题,这首诗在韩东的整个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韩东也在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但此后韩东并未沿着《小姐》这首诗的写法,而是一如既往地追求诗歌的纯粹。
进入21世纪,韩东的诗歌迎来了一个大的转变。2002年,韩东写出了《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亲爱的母亲”》《雨》《细节》《记忆》等诗歌。尤其是《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是韩东诗歌的一个界碑,这首诗里“感觉”的要素得以直接出现,并在他此后的诗歌中,越来越重要,它与日常生活一起,共同构筑了韩东诗歌的美学根基。可以说,“感觉”和“日常生活”两个要素的交融,使得韩东的诗歌逐渐真正地走向了“物我合一”的境界,他的诗歌因此更加具有审美感性特质。《悲伤或永生》中收录的诗歌,其分界点在2002年,这一年将韩东的诗歌分为“此前二十年”和“此后二十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东的诗歌写作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能说是其写作的深入,而且是无限的深入。感觉的要素在此前并不突出,或者说,并没有成为韩东写作的发力点j,但此后他创作的诗歌显示,韩东越来越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感觉的捕捉,并在诗歌中将其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具体的诗歌作品来看,韩东对感觉的关注在当代诗人中应该是最早的一位。他早期流传度最高的诗歌《有关大雁塔》,就已经有了感觉的成分,从那时起,韩东将他对大雁塔的书写与生命的真实联系在一起。他说:“艺术作品中,善的标准是虚假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k这里的“真实”就是生命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却是以感觉的方式存在的。他在回忆《有关大雁塔》這首诗的写作时说,当时他“仅仅从美学角度而非在‘历史感上肯定了这一古建筑的价值”l,所谓的“美学角度”,即非历史的角度。大雁塔对他而言,是美的而非历史的存在。他不相信杨炼在《大雁塔》一诗中对大雁塔所作的历史化处理,杨炼建构的大雁塔的形象,乃是一个伦理范畴内的善的形象,而非美学范畴内的美的形象。对他而言,从美学的视角看,大雁塔只有经过写作者本人的目光进入作者的心灵,并以某种视觉化形象存在,它才是真实的和美的。在韩东看来,“大雁塔不过是财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形式简朴、精神内敛。m这个形象,就是日常生活给予韩东的“感觉”,这是真实的大雁塔和真实的生命:大雁塔及其天空,与韩东的自我融为了一体,成为一个具有现象学特质的形象。这首奠定了韩东诗歌美学基础的诗歌,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因素:日常生活、瞬间感觉。这里的“感觉”,韩东在整首诗里将之化为一个语言的整体存在,所以读者读到《有关大雁塔》时,那种简朴的形象是通过诗歌独特的、带有强烈节奏感的语言整体呈现并传递到读者心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实现了生命信息的交流。
通常的看法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当代诗歌实现了从1980年代追求“纯诗”向1990年代“不纯诗”的转型,“历史的巨兽”再次进入诗歌。n当然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唐晓渡认为,“如果说先锋诗写作在90年代确实经历了某种‘历史转变的话”,“其确切指谓应该是相当一部分诗人的‘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和‘个体诗学的成熟”o,而不能就因此认为1990年代当代诗歌整体实现了历史转变。准确来说,1990年代诗歌是当代新诗在诗学上的混乱期,引发这种混乱的根源是两种诗学的对冲:也即将诗歌写作历史化的历史诗学和坚持从美出发的生命诗学,前者注重诗的历史化,讲究诗与历史的对位,后者则坚持诗歌写作的非历史化,立足于诗歌作为艺术的感性,追求生命的真实。
在1990年代诗歌发展的混乱期,韩东依然延续了其1980年代的诗学原则,继续在日常生活和“感觉”的方向上探索。2002年之前,他写作的着力点主要是日常生活,虽然也会注意“感觉”,但“感觉”尚未像后来那样,成为其写作的着力点。写于1991年的《甲乙》虽然是韩东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但这首诗主要是以异于他本人以往的、具有法国“新小说”特点的客观笔法来写日常生活,却很少直接涉及感觉。而且,他的这种写法并未持续下去,很快,他就回到了之前的轨道。联系到1991年(1990年代初)这个时间点,韩东的这首诗更像是非历史化的美学姿态的自我表白。他在1995年写的《小姐》一诗对现实的触及,较之以往较为罕见,结合后来二十多年的写作来看,这首诗像是一次实验,它表明韩东在思考诗歌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或者说,他在尝试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2002年,韩东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标志性的诗歌即《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这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的变化,一直影响了此后二十年。但变化是相对的:一方面,它依然延续了之前二十年韩东诗歌写作的根本特点,即诗歌所处理的题材依然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其独具标识性的语言去书写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这种“日常生活+瞬间感觉”的诗歌生成模式并没有变化;另一方面,在此种生成模式中,韩东开始将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的感觉作为其写作的发力点,“瞬间感觉”作为其诗歌中的第一要义被前景化了。
在韩东大量的诗歌中,“瞬间感觉”被视觉化了,成为一种现象学式的直观,其笔触所及,都是为了清晰呈现日常生活中的感觉,而且,他的人生经验也被感觉化了。可以说,“瞬间感觉”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感觉,它表征了一种当代新诗的崭新的生成模式,既具有方法意义,也具有本体价值——它让诗歌回到了诗歌自身,让诗歌获得了更纯粹的“具体性”,让“诗歌成其为诗歌”。p可以这样认识韩东的这一写作变化:他在诗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使它在“原则上面向无限的深入”q,这是其诗学的深化。如此一来,韩东的诗歌更加彻底地回归到“诗歌本身”r,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让当代诗歌回到了新诗最初的原点;同时,他也开始将自己的笔触伸向“现实”,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如何更好地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好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新诗未曾解决的问题。韩东在这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写作中,探索出了一条几近完美的路径。他在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作出的探索,昭示了新诗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诗集《奇迹》s中的作品,是这一探索结出的硕果;《奇迹》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收录在《悲伤或永生》一书中,本文对后者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收录于《奇迹》中的诗歌的研究和价值判断。
二、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的生成
在《悲伤或永生》的诗学演进脉络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方向:2002年以前的大部分诗歌,主要是以写日常生活为主,虽然说韩东笔下的日常生活也包含了“感觉”和“语言的感觉”t,但是“感觉”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并没有在这之前的诗歌中明显地显示出来;而这之后,“感觉”在其诗歌中的成分日益加重。在这部诗集中,从第二辑“重新做人”往后,韩东的诗歌逐渐形成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生成模式,它近乎是一个公式:“日常生活+瞬间感觉。”这种模式是一种关于诗歌“怎么写”的方法,二十年来,韩东的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生成的。u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生成方式,等于是让韩东的诗歌回到了新诗的最初起点。这个起点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别于历史诗学的、新诗追求美学现代性的传统的起点。有论者近几年提出一个新看法:中国新诗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胡适《尝试集》的传统,一个是郭沫若《女神》的传统。和郭沫若开创的传统不同,胡适开创的传统是反抒情、反个性(非个人化)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胡适所强调的那种叙述性、生活流几乎成为之后诗歌创作的潮流”v。在此,本文在认同胡适作为新诗最早起点这一判断的前提下,对此说法还有其他补充。胡适虽然是新诗的最早起点,而且从其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一文中对新诗作出“具体性”要求来看w,这一起点其实是新诗非历史化写作的源头;但是从胡适在该文中所举的案例——比如《伐檀》《石壕吏》,以及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若干诗歌——来看,胡适虽然提出了“具体性”,但“并未真正意识到它重要的诗学意义”,即他在“服从现实的训导”下,没有重视诗人“真正的个体感受和意识的解放是詩歌获得具体性的前提”。x也就是说,胡适在对新诗作“具体性”要求的同时,没有真正洞悉“具体性”的实质,因而他并未完成对新诗美学现代性传统的构建。
直到1930年代,废名在北大讲新诗的时候,在谈论胡适诗歌的基础上,提出新诗应该有一个感觉的发生机制。废名认为,诗歌仅有“具体性”是不够的,还得包含其他的东西。废名在讲稿中并没有集中表述这个问题,但读者很容易看到,讲稿处处在显示他是以瞬间触发的感觉来评判诗的。在废名看来,诗应该是瞬时性触发当下感觉的产物。他说:“关于我所谓诗的内容在这里我还想补足一点,旧诗绝句有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的,这首诗的内容又正是新诗的内容。”y他又谈到,“诗的情绪”,是“触发当下”的瞬时感觉、意识。z可见,废名对新诗内容的规定,是诗歌的日常生活具体性加上诗的瞬间感觉。本文认为,新诗中早期的非历史化写作传统的形成,是由胡适和废名共同完成的,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新诗对美学现代性的追求。
韩东在2002年以后的诗歌,相较于之前,并非单独专注于通过叙事等手段单纯地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更加着意于呈现写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感觉。由此,“感觉”的因素在韩东的诗歌中的比重加大了。以《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为例来看,这首短诗其实就写了听歌的感觉:“唱歌的人在户外/在高寒地区/仰着脖子/把歌声送上去/就像松树/把树叶送上去/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坚硬的松木/一排排的。”这首诗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是“日常生活”,第二是“感觉”。前面四行是叙述日常生活,后面五行是写日常生活情境下触发的瞬间感觉。
韩东曾谈过诗歌中的“感觉”:“谈到感觉,很多人以为是放纵、放逸,那是错误的。围绕感觉的源泉,有很多强制性的限制。为那一点点飘忽不定的自由,必须做到训练有素,以便承接。”@7韩东强调的感觉是一种被限制的感觉,它虽然被加诸“很多强制性的限制”,但也是为了“那一点点飘忽不定的自由”。很显然,这自由,是生命的自由,也是艺术的自由:这自由是美的同义词,它产生于写作者“训练有素”地将感觉与具体的日常事物相结合。实质上,韩东所说的“感觉”很明显是现象学的直观。如果我们从皮尔斯(C.S.Peirce)的说法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何谓“感觉”。皮尔斯在谈论现象学的“第一性”概念时为“感觉”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感觉(feeling),我是指某种意识的一个实例(instance),而这种意识既不包含分析、比较或者任何过程,也不存在于任何可以使一段意识区别于另一段意识的行为之中……感觉是意识之某种成分的一个实例,这种成分就是它自身实际所是的那一切,而与其他任何事物无关。”@8皮尔斯指出,“感觉”是“不包含分析、比较或任何过程”的,它是直接的被动的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它“不认知或不分析”@9,只是被动“呈现”。
结合韩东的诗歌不难看出,韩东所说的“感觉”,就是这种在皮尔斯的现象学范畴内的“第一性”#0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心灵有关,但又具有非常明显的身体特征。早在1995年,韩东就谈到“第一性”的问题。他说:“第一性”具体“指的是那种由诗人身体引发的,出自他内部的东西,是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到的东西。”#1韩东说的“第一性”,虽然并不能完全等同或契合皮尔斯的“第一性”,但是透过表述还是可以看出,前者非常接近后者,将之放在皮尔斯的范畴论中来理解是完全可以的。在韩东的这首诗里,后半部分显然就是“第一性”的感觉,它是听歌的人对唱歌的人所唱的“圣歌”的感觉,并将这种感觉视觉化:“就像松树/把树叶送上去/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坚硬的松木/一排排的。”韩东将这一视觉化的感觉用以解释他听到的“圣歌”,这种解释不包含任何的分析、比较,也不包含任何过程,它就是将自己瞬间的心灵影像进行直观化呈现。
在此,韩东这首诗和他在2002年以前的诗有了显著的区别。这首诗里包含了两个根本的因素:日常生活和瞬间感觉。在诗集《悲伤或永生》中,从这首诗开始,他此后的诗歌除了和以往一样重视日常生活,感觉的成分也明显加大。他在诗歌中,会用很大的篇幅来写(呈现)他心灵中的瞬间感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和瞬间感觉这两个因素,构成了韩东诗歌写作的两个主要对象,并由此而成为他的诗歌的生成方式。我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个因素,都是让诗歌变得“具体”和感性的根本因素。日常生活本身的具体可感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感觉的视觉化,则是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感觉的视觉化,是让诗歌更加感性的途径。诗歌的“具体性”,就应该是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感觉。而且这感觉本身就包含了生命的信息,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生命以此方式在诗歌中被视觉化。如果说,艺术是一种雕刻的手艺,那么,在此过程中诗人只需要用最合适的语言清晰地呈现日常生活中的心灵的瞬间感觉,这个过程即在雕刻时光和生命。在此意义上,写作的精确性,就是用最合适的语言,清晰地呈现诗人瞬间的感觉,而不是用语言准确地对事物作几何学意义上的叙述。这是诗歌获得自由的最具终极意义的理解:“现代诗的本质是自由,困境亦然”#2,這“自由”就是经由被限制的语言呈现的生命的瞬间感觉。所以,韩东为文学的语言也勘定了大致边界:“有一种文学语言是示意性的,传达意思即可,此外它要求灵活和节奏(舒服和活泛)。准确性和逻辑之类不在考虑之列。”#3
感觉作为一种直接意识,成为韩东诗歌的书写对象,从新诗史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98年,臧棣就谈到1990年代的诗歌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从之前对情感的书写,转向对意识的书写。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审美转向:从情感到意识。换句话说,人的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开始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动机”#4。这是汉语新诗的写作语境。
就韩东而言,他在诗歌中将被视为直接意识的“感觉”作为写作对象,客观而言,其目的就是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让“诗歌成其为诗歌”#5,这是新诗写作从功能回归到本体#6,立足于诗歌本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韩东诗歌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未曾改变的根本所在。也可以说,四十年来,韩东一直未曾改变的是他对诗歌本体性的追求,是让“诗歌成其为诗歌”,将这个问题拓放到百年新诗史中,可以将之视为新诗对美学或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从胡适和废名共同构建的新诗传统,到韩东的写作,其根本点体现为诗歌写作立足于“审美”或可感性的“美”这一前提。这一追求自身的内在逻辑是立足于生命的真实和写作的非历史化。
《悲伤或永生》中第四辑“奇迹”收录了作者写于2015-2019年间的111首诗歌。这一辑中的诗歌相比较2002-2014年的诗歌,更进一步、更集中、更突出地显示了“感觉”作为书写对象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对“感觉”的捕捉,体现了诗人的敏感,这与写作者的天赋相关联。“在写作中,敏感是第一义的,判断等而下之”#7,这敏感是对感觉的敏感,屏蔽了认知和判断,它意味着在写作中,“感觉”的能力是一种可以使“感觉”在诗歌中趋于无限精微的天赋。这就是我们谓之的“感觉力”,或感觉的能力。
以第一首诗《白色的他》为例,这首诗共14行,只有前3行是写日常生活,余下11行则完全是视觉化的感觉。这首诗的前三行是:“寒风中,我们给他送去一只鸡/送往半空中黑暗的囚室/送給那容颜不改的无期囚犯。”如果剔除了后面的感觉,这首诗就可以结束了。但他接下来所写的,是通过想象,将探望囚犯这件事展开,并在想象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出瞬间的感觉:“然后/想象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孤独地啃噬。他吃得那么细/每一根骨或每一片骨头上/都不再附着任何肉质/骨头本身却完整有形/并被寒冷的风吹干了。/当阳光破窗而入,照进室内/他仰躺在坍塌下去的篮筐里/连身都翻不过来了。/四周散落着刺目的白骨/白色的他看上去有些陈旧。”需要注意的是,“想象”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想象”只是这首诗实现可感的“具体化”的手段,这首诗的重点在最后一行。“白色的他看上去有些陈旧”是这首诗的落脚处,韩东让它落脚于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可分析、不含比较的,也不包含任何过程,因而它不是判断,只是生命的某种品质的呈现。这种品质具有瞬间性,它在时间上无限短暂。正是对这无限短暂时间的感觉的呈现,诗歌达到了生命的最大的真实。
韩东在这一阶段#8将诗歌的纯度提升到了其写作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就像工匠打磨钻石一样,语言的意义就是让他变成一个雕刻打磨的匠人,为的是更精确地呈现生命的瞬间感觉并让诗闪光。在对待写作的态度上,韩东说:“三十岁的时候我推崇天才,四十岁仰慕大师,如今我只向匠人脱帽致敬。”#9但是,韩东的这句话,应该在日常生活的感觉层面去理解。韩东一直都在做着让日常生活回到“具体性”的原初状态的工作,他写作时所面对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原初状态。
1983年韩东创作的《有关大雁塔》这首诗,所写的就是这种“原初”感。他在1988年写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一文,要求诗人写作应该摆脱“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这三个角色,只有如此,“中国诗人的道路”才真正“从此开始”。$0韩东看似在说诗人的三种身份,实际上也可以将之视为在谈论日常生活。诗人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如何让其还原到最原初的状态,是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应该具有的训练有素的能力。日常生活作为写作对象,诗人只有去除掉其本身所包含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理性认知,去除掉这些具有分析性的、知识性的成分,才可能获得那种最直接的不含分析、比较和过程的瞬间感觉,才可能获得和抵达最真实的生命,而在美的意义上,才可能让具体的日常生活获得最大程度的感性。
如何观照日常生活,韩东最近提供了一种方法:以“世界意识”去理解作为写作对象的世界。以此“意识”理解的世界,可以让世界在诗歌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审美感性自由,也让人的生命最大程度地抵达真实。韩东说:“所谓的世界意识,即是你对置身的存在有了某种如实的认同。你就在世界上,在世界中,既不在它的中心,也不在世界边缘,自自然然地在那里,在世界上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放松了。”$1韩东这里所说的“世界”,可以和本文的“日常生活”画等号。“世界意识”,就是“日常生活意识”,世界的边界,就是日常生活的边界。他又说:“世界意识则是一种平等意识,从中心撤离,但并无边缘,到处都清晰可见、可感……世界意识是世界性的‘诗歌精神得以确立的必要保证,世界性的诗歌精神有赖于价值标准的一致、经验对象的同步以及审美判断上的共识。”$2通过这些话,可以明显看出韩东的阐述和皮尔斯的现象学有着高度的吻合。
“世界意识”在诗歌中,就是皮尔斯说的“第一性”,其中的“意识”就是皮尔斯说的“不包含分析、比较或者任何过程”的、“不认知或不分析”的直接感觉,它让日常生活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正是在这种“世界意识”的观照下,诗歌拥有了“一种世界性的诗歌精神”,而这正是“这代汉语诗歌写作者孜孜以求的,也是其写作的一个前提”。$3这个“前提”,对每一位写作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它是落笔之前写作者所做的“清除”工作。韩东说:“诗不应该和某种特殊观念联系在一起,让它成为可直接感受的东西,从写作之初,我就是这么设想的。当然,对诗而言的感受力需要经过训练,是训练而不是接受理论或观念指引……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清除,清除我们关于诗歌理解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俗见或者高见(这是一回事)……单纯而富于经验的人可瞥见诗之真相。”$4韩东这里所说的“感受力”,就是感觉的能力,它需要首先清除掉诗人头脑中的种种知识、理论和见解,腾空自己才能实现。
以上可知,随着诗歌写作的深入,韩东的诗歌已经在真正意义上回到了“诗歌本身”,回到了诗歌作为艺术应该具有审美感性特质这一本体上来,并在这个方向上,诗歌获得了它的纯度。由于写作者在让诗歌变得纯粹的过程中,需要以其自身的敏感来捕捉瞬间的感觉,并对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提出高要求,因此,诗歌的纯度在一定意义上与写作者的才能是相匹配的。感觉的精微和对感觉呈现的能力(韩东谓之“语言的感觉”$5)决定了诗歌艺术价值的天花板。因此,我们尝试这样描述“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作为一种诗歌的生成方法,它是当代汉语新诗在实现自身审美现代性向度上的直接、有效途径,以此生成的诗歌具有非功利性的特质,从而使得诗歌保持了最大可能的“纯度”。这种高纯度的诗歌不同于以往的纯诗,它对视觉化的要求和对声音的要求一样,将之作为诗的本体性特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视觉化意义可能还要大于声音的意义。因此,诗歌中呈现的感觉的清晰程度是判断一首诗的审美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由此生成。
三、从“怎么写”到“写什么”
作为一种诗歌生成的方法,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首先解决了当代诗歌“怎么写”的问题。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当代诗歌是存在巨大缺憾的。“怎么写”只是一个美学问题,但“写什么”是个伦理学问题。借用王国维评论《红楼梦》时的一个说法:“《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6王国维所说的“美术”,指的是“艺术”。不但小说,伦理学对于诗歌同样重要,如果一首诗没有伦理价值,只是单纯地具有美学价值,这当然是可以的,但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没有伦理价值,这个时代的诗歌就会是暗淡的。正如文学史上为人称道的《古诗十九首》,如果没有伦理学作为其背景,而单单是由美学支撑,它的价值也是未可知的。那些抚慰孤单心灵的清风,照耀精神世界的光亮,揭示人生困厄的言辞,对应的正是诗歌中的伦理学。
在当代新诗史上,美学和伦理学孰轻孰重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是百年新诗的最大困境。汉语新诗的现代化这一命题,本然地包含了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以21世纪初为例,当“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等一时间风头无两的时候,2006年,林贤治《新诗:喧嚣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7,明确对当代新诗提出伦理诉求。当时诗坛围绕诗歌的伦理问题展开了论争,论争的焦点,乃是诗歌要不要介入现实,以及美学和伦理学孰先孰后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新诗受困于历史化诗学,过度注重诗歌的功能性,偏离诗歌的本体性,诗人在写作时往往优先考虑历史,在“历史意识”的观照下处理写作题材,由此生成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和伦理意义。这在朦胧诗和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而在1980年代,“第三代诗歌”则注重诗歌的本体性,优先考虑的是诗歌的审美因素,如以韩东等为代表的《他们》诗人群,其写作的出发点即是回到“诗歌本身”。这一诉求的前提当然就是诗歌的历史化偏离了“诗歌本身”的诗歌史事实,因此,《他们》诗人群便是以注重日常生活、平民意识、口语化语言等为出发点生成非历史化的诗歌。此外,还有观念化较强的写作,如“非非主义”。“非非”诗歌的生成具有很强的结构主义特点,以语言作为其写作的美学根本,他们不关心诗歌的功能性。杨黎就认为,诗歌就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8。
中国当代诗歌其实一直在伦理学和美学之间左右摆荡,在非此即彼中走向极端。当然,在199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诗人也意识到诗歌应该不但要在“写什么”,而且还要在“怎么写”上实现自己写作的“有效性”。只是,对他们而言,“怎么写”只是“写什么”的手段,“写什么”才是他们认为的实现诗歌“有效性”的途径。如此一来,这种写作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也因此其诗学内部包含着深层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美学和伦理学的割裂。
以欧阳江河为例,他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反词”写作。$9这种诗学实质是在结构主义诗学影响下的诗歌历史化的新形式——它仅赋予诗歌写作以新的形式,诗歌的词语在“反”掉其自身累积起来的既有的各种意义之后,重新给词语注入历史含义。也就是说,欧阳江河的这种方法是在面对历史化诗学审美缺失的事实面前,想方设法发明了一种“反词”理论,以此让其写作既有伦理学意义,同时也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个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并沒有让诗歌获得审美感性;因要在诗歌里实现历史伦理学的终极目的,诗人只能在感性缺失和历史表达之间以高度智力化的语言来做一种机械而僵硬的平衡运动。等于说,欧阳江河仍然没有解决诗歌写作的美学和伦理学割裂的难题。正像王光明指出的:欧阳江河所写的情景是“想象的、虚拟的,材料也往往不是经验的细节,而是带隐喻的意象”,也许他的写作“更能满足理论批评家的口味”,但却背离了新诗开创者胡适所希望的“诗要用具体的做法”的初衷。而实现这种具体性的前提只能是“真正的个体感受和意识的解放”%0,但欧阳江河朝向了反方向。
2009年,陈超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自19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的想象力维度转化问题。%1这篇文章展开的核心动力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2“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关键在于:第一,是诗人个体的主体介入历史;第二,写作者应该有一套“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很明显,这个诗学理论依然打着明显的历史化烙印,和欧阳江河类似,希望写作者能够通过“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来增加诗歌的审美性。具有认知特征的“历史意识”的理性和抽象性,并不能让个体感受和意识实现真正的解放,并不能让诗歌获得真正的审美特性。陈超绕来绕去,却还是落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思维的窠臼中,他倡导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为一种诗学,依然未能解决新诗在审美与历史之间割裂的矛盾。
从诗歌写作的实践看,韩东从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通过诗歌探寻生命的真实,他的写作始终是非历史化的,其出发点与历史没有任何关联,而全部是“诗”的,是从诗本身出发,而又让诗歌回归诗本身。在1980年代初的诗歌语境中,韩东这样做的意义是:诗歌作为艺术,它首先是诗歌,即让“诗歌成其为诗歌”,只有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才有“写什么”的可能性。通过四十年的写作实践,韩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艺术理想。他说:“一代人执着于‘怎么写,这没有问题,但‘写什么却被一再忽略。……‘怎么写一头独大是有其背景的,因为对‘文以载道的反驳。反驳和思想上的厌离让我们付出了代价。”%3韩东所说的“背景”,就是中国当代诗歌在历史化诗学的主导下长期过于注重诗歌功能性,诗歌过度伦理化的诗歌史语境。
1980年代初“第三代诗歌”兴起的背景是朦胧诗,1990年代“民间写作”的背景是“知识分子写作”,21世纪初“废话写作”的背景是“打工诗歌”“草根写作”等。这些“背景”的存在,促使许多诗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怎么写”的问题上穷尽所能。但是,韩东意识到问题所在,他开始思考“怎么写”和“写什么”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诗人已经开始思考了,诗歌写作的美学问题,就是“怎么写”的问题,伦理学问题就是“写什么”的问题,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以诗歌的功能性为先导,没有处理好“怎么写”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韩东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对一个‘怎么写已经具足的人而言,‘写什么自然更重要。”“有志于文学的初学者关注‘怎么写,但如果你弄笔十年以上再纠结于此就没必要了。‘写什么理应再次成为重中之重。”%4这等于是为诗歌写作中的“怎么写”和“写什么”规定了先后的顺序:诗歌必须先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在此问题解决之后,写作者必须关注“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就包含在韩东早期的诗歌写作实践中,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立足于日常生活,探求生命的真实。“日常生活”本身为写作者提供了“具体性”,但还不够,还必须将日常生活的“具体性”落实到“真正的个体感受和意识的解放”,也就是诗歌必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感性自由。这也正是本文所论述的“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的价值所在,它使得写作者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地“解放”自己,从而让诗歌本身获得绝对意义上的审美感性,实现艺术的自由。
韩东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有关大雁塔》这首诗歌的生成过程:当时他在陕西财经学院教书,大雁塔就在学校附近,每天都能看到。即,“大雁塔”就是韩东的日常生活。但大雁塔给他的感觉并不是如杨炼《大雁塔》一诗中的那种“金碧辉煌”,而“不过是财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5这个“灰影”,是大雁塔在韩东心灵中的感觉,这种感觉并没有历史,也没有政治或文化,因此,它不含有任何的认知、分析或比较成分。作为写作者,将这种感觉在诗歌中呈现出来,就是让大雁塔获得它的审美性;作为日常生活的“大雁塔”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它的“具体性”,《有关大雁塔》也因此成为一首纯粹的诗——诗的“纯粹”由此而来。
1988年,韩东在一段介绍自己的文字中说:“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6虽然在讲语言,讲“诗到语言为止”,但如果不将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和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感觉纳入其中,就很难准确理解它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在韩东那里,语言、日常生活、感觉是三位一体的。语言所赋予诗的纯粹程度,主要还是由日常生活和感觉所决定,将这三个要素处理好以后,诗歌才能真正获得审美的感性。也是在1988年,韩东还写了《三个世俗角色之后》。%7这篇文章体现了韩东作为诗人的审美自觉,他要求从诗人的意识层面自觉地以彻底的感性态度观照日常生活和生成诗歌。从最近关于“世界意识”的表述中,可见他几十年如一日思考和实践着诗歌艺术何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的审美感性,而这恰恰就是一个诗人如何首先成为一个诗人,而诗歌又如何“成其为诗歌”的问题。
以上都是讨论韩东关于“怎么写”的论述。解决“怎么写”并不是韩东的终极目的,他认为“重中之重”的事情还是“写什么”。放眼中国当代诗歌史,甚至整个百年新诗史,韩东的写作实践可能是最具独特性和最有价值的写作实践之一,极少有这样的诗人,既解决了审美感性——即美学——的问题,也在此基础上成功实践了伦理学,这里面所包含的艺术法则是不容辩驳的。而韩东在这种艺术法则的前提下,将笔触伸向伦理学领域,除他以外几乎无人做到。他近些年的诗歌,写到了父亲、母亲、恋人、朋友、陌生人、小商贩、普通的劳动者,当然也写到了自己;除此,他还写到狗、猫、马、猴子、苍蝇、蛆虫、黄鼠狼等非人类生命;另外,他也写到身边的事物以及童年的记忆,比如医院、墓园、雨、雪、老房子,甚至也写到国外的一些生活场景。总的来说,这些诗歌早已不仅仅是“怎么写”的问题,而是在此基础上,涉及到了很多重大的主题和人類的基本情感,包含了韩东本人的生活和生存经验,它们已经进入了“思想”的领地。比如生死、亲情、爱情、友情、存在、时间等等。
在以上题材中,写作者本人的自我身份非常独特。他观照这一切的方式是以“放弃自我”的方式实现的。“放弃自我”包含在“怎么写”的命题中,同时又对“写什么”发生作用。韩东说:“在自我的扩张之处我们并不能碰到诗,诗是诗人们放弃自我的结果。”“诗歌总是选择那些忘我的人、忘我的片刻,从来如此,它选择空无、躯壳和虚怀,由于它的倾注那么饱满深入因而不可能挑选拥塞狭隘之处。……其次需要腾空自己,像腾空一个房间,不抱任何成见。每一次都这样,每写一首诗一句诗都这样。”%8由此可见韩东写作的非个人化倾向:泯灭主体,物我合一;同时,这也是他“写什么”的一部分。和他所说的“世界意识”放在一起看,他的诗歌虽然深入到伦理领地,但他对自己笔下的人和事却不是以悲悯的目光去看的,更不是如“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那种方式,以个体主体的介入方式深入伦理的。在《悲伤或永生》中,有不少诗歌是写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如《卖鸡的》《工人的手》《致煎饼夫妇》《长东西》《青年时代的一个瞬间》等。这些诗歌可以作为韩东处理诗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的样本。虽然所写的对象都是平凡的人物,他却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悲悯,写作者在诗歌中所采用的是众生平等的视角,既不批判,也不诉苦,只是像工匠一样,用当代汉语将世间的这些清晰地呈现出来。韩东说:“诗何以伟大,因为其中容不下怨恨。怨恨会极大地败坏一首诗,至少在我这里这是真理。”%9将这句话中的“怨恨”一词换成“悲悯”,意思也是一样。平等、无分别地处理一切题材,体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意识”。
结语:韩东诗歌与当代新诗的现代性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于百年新诗史中,新诗一直都面对现代性的实现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长期以来,“历史”因素与诗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关系之中,相应的历史化诗学让新诗形成了一个功能主义传统。在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反省和反抗,构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和重大特色”^0。而在1990年代,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型,一些诗人再次让“历史”以强劲的姿态进入诗歌,由此形成的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就延续了新诗的功能主义传统。在21世纪,网络新媒体兴起并普及以来,新诗发展呈现出新的景观,但也有人认为,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以《他们》为代表的诗人群在这一时期对现代性的追求处于未完成状态。^1然而,本文通过对韩东诗集《悲伤或永生》的诗学研究,发现中国新诗已然寻找到一条通往现代性的宽阔道路。
韩东的诗歌代表了当代有抱负的诗人在追求现代性之路上所作出的殚精竭虑的探索和实践。韩东说:“就我个人而言,探讨过语言和诗歌的关系(‘诗到语言为止),进行过形式或文本实验,在中西影响的对峙、交往中有过身份焦虑,在艺术方式和身处存在的分裂、互动中也曾惊疑不定……此刻,在六十岁这个时间点上,我特别愿意将诗歌定位为艺术,写诗则以作品为目的。”^2这些话深刻道出了韩东本人四十年来的探索之路。尤其是他“将诗歌定位为艺术”的说法,表明了韩东是将诗歌的艺术性而不是社会性作为追求目标的。客观上这也是对一百年前由胡适等人共同构建的新诗的传统的呼应。
“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是对韩东诗学的总结性概括,它意味着诗歌写作第一要义是要求诗人注重诗歌的审美特性,从诗歌的无用性和非功利性出发,去书写个人所置身的世界。正因其无用和非功利,诗人得以以平等、无分别的心态、意识观照日常生活,并将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作为诗歌的可视化的现象材料来源。在此基础上,诗人也可以处理人的生存、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文化等问题,这就使得由日常生活感觉力所生成的诗歌,并不单纯地成为“纯诗”,它也有能力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使得美学和伦理学可以做到完美兼容。
对韩东诗学的研究,并不是要求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必须统一为“韩东模式”,只是将他的诗歌作为典型的分析案例,借助对韩东诗学的探讨,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新诗实现自身的美学现代性,必须尊重诗歌作为诗歌这一基本逻辑前提,将诗歌作为艺术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介入现实的工具。诗歌应该既有高度审美性,同时也有能力解决诗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对韩东《悲伤或永生》的研究表明,诗歌的纯粹来自它自身的感性解放,它涉足伦理学领域的能力,也表明了这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纯诗”,它的伦理学价值是其艺术价值的延伸。韩东的诗歌,意味着当代汉语诗歌未来的可能性。
【注释】
a韩东诗集《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1982-2021)》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出版,收录韩东诗歌356首。本文以下简称《悲伤或永生》。
b“崭新传统”的说法来自韩东的一篇文章。参见韩东:《一个备忘——关于诗歌、现代汉语、“我们”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c韩东说:“我十八岁开始学习写诗,至今四十三年。”参见韩东:《一个备忘——关于诗歌、现代汉语、“我们”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depr#5韩东:《他们文学社(南京)》,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52頁、52页、52页、52页。
fq$1$2$3^2韩东:《一个备忘——关于诗歌、现代汉语、“我们”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g关于这个说法本文有两点说明:1.尽管西川称,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参见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见闵正道主编:《中国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通常认为,1989年6月肖开愚在民间诗刊《大河》里的一篇短文中表达了诗歌写作的转变意识,这种转变是诗歌朝向“历史”的转变,因而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开端。2.当时一些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将自己的诗歌命名为“90年代诗歌”,这显然是不妥的,在1990年代末诗坛所发生的大范围的激烈的观念冲突表明,将“90年代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划等号是不准确的,因此,更为妥当的说法是在1990年代,当代新诗处于一个混乱期。
h参见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287页。
i本文所引所有韩东的诗歌作品,皆选自韩东:《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1982-2021)》,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后文不再一一指出。
j韩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感觉”的问题,他对这个诗学概念的关注具有人类学或现象学的意义。他曾在老木编的《青年诗人谈诗》中说:“我觉得真正的艺术还是有的。回归?原始的感觉?我说不清楚。”参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民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24-125页。
k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民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24页。
lm%5韩东:《有关〈有关大雁塔〉》,《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156页、156页。
n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o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见王家新编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
s参见韩东:《奇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该诗集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t韩东说:“有时,你的感觉并不重要,语言的感觉才比较重要。”这里,韩东讨论了“感觉”和“语言的感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感觉”,而“语言的感觉”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参见韩东:《五万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
u《悲伤或永生》共收录了韩东四十年间所写的356首诗歌,但是他在前二十年所写的诗歌仅收录95首,只占了总数的大致四分之一。因此也可以认为,韩东对后二十年的诗歌极为重视。
v姜玉琴:《从〈尝试集〉到〈女神〉:两个不同的新诗传统——兼论有关新诗的起点和奠基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5期。
w胡适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参见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文集 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x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yz废名:《谈新诗》,王风编:《废名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页、1618页。
@7#2#3#7#9$5%3%4%9韩东:《五万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8页,8页,22页,10页,53页,4页,3、4页,63页。
@8@9[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28页。
#0皮尔斯在康德十二范畴的基础上,分别对范畴重新进行了数学的和现象学的推导,将范畴分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尤其是他所作的现象学推导,对我们研究文学艺术有极大帮助。他认为,第一性是绝对的自由,它是“首先的(first)和短暂的”;第二性的特征是“它在性”,它异于第一性;第三性“与中介有关”,“包含着至少三个因素:连接着的对象和对象之间的联系”。(参见[美]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赦长墀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26页。)皮尔斯将现象的成分概括成简单的三个词:品质、事实和思想。其中,“品质”的表现形式即是作为一种直接意识的感觉。而就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关系来说,第一性是根基,第二性必然包含第一性,第三性必然包含第二性。(参见[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6、30页。)
#1林舟:《清醒的文学梦——韩东访谈录》,见韩东:《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4臧棣:《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6早在20世纪80年代,唐晓渡就指出了新诗长期以来存在的痼疾。唐晓渡用“本体”和“功能”来描述新诗的问题,他说:“所谓‘本体,在这里与‘功能相对”,“二者的不平衡一直是新诗发展中带有悲剧色彩的纠结之一。对后者的过分强调(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然)使诗一再悖离自身,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走向反面。……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反抗,构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和重大特色”。(参见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可惜的是,在1989年以后,以“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又一次以“历史意识”的形式摆荡到功能主义的一边。“知识分子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点乃是一种在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具有启蒙主义特征的历史诗学,这种诗学在21世纪初被批评家陈超发展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8《悲伤或永生》还收录了2020-2021年所写的36首诗,韩东将其编辑为第五辑“解除隔离”。这里所说的这一阶段,当然也包括了这一时间段。
$0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4韩东:《创造的任务》,《上海文学》2022年第3期。
$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徐调孚、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7林贤治:《喧嚣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94页。
$8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2009年版,第155页。
$9参见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虛构这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0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参见陈超:《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所谓“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陈超说:“约略指的是诗人从个体的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宽阔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参见陈超:《后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6韩东:《自传与诗见》,《诗歌报》总第92期,1988年7月6日。
%7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7页。
%8韩东:《关于诗歌的两千字》,《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0页。
^0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参见胡友峰、余海艳:《〈他们〉:未完成的诗歌“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