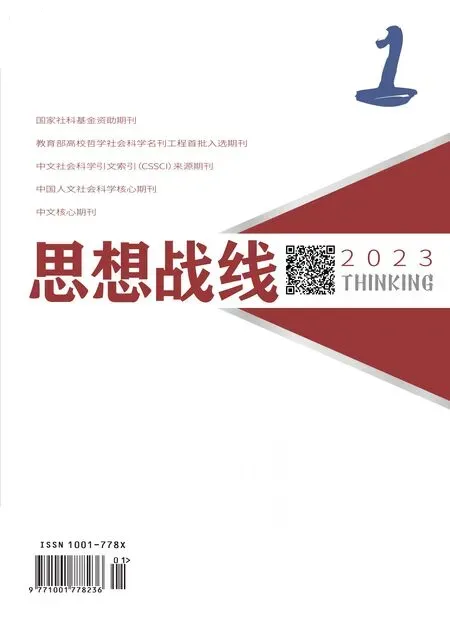文化遗产景观实践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023-02-16桂榕
桂 榕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下称精神家园建设)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关涉中国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议题。文化遗产景观实践(下称遗产景观实践)是反映中国各民族通过文化遗产实践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概念。而精神家园建设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范畴,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和社区文化建设等多层面内容。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事实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保护工作开展近20年,以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景观实践已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并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方式。目前,此领域的实践总结与理论思考还较为有限,故笔者从精神家园建设实践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在参考借鉴国际学术界关于遗产景观实践的相关成果基础上,提出遗产景观实践概念;并从遗产景观实践之于精神家园建设的适用性,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内涵和特性、类型和领域,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原则,保障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策略四个方面,分析遗产景观实践与精神家园建设的内在关联,以及如何通过遗产景观实践促进精神家园建设。
一、遗产景观实践之于精神家园建设的适用性
(一)遗产景观实践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
文化遗产景观概念的出现,源于近些年国际上遗产与景观两个领域在概念与实践层面的不断交融,反映了文化遗产在景观实践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遗产景观正在成为具有共享理念、整合力量和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图景之现状。景观一词发端于人文地理学,现已成为跨学科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地理学对语言、意义和表征作用的重视,景观开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1)Denis Cosgrove,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p.15.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观从物化概念发展为文化分析的理论工具,(2)Sharon Zukin,Landscapes of Power: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6~18.被认为是权力的代理者和社会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3)Stewart,Pamela J.and Strathern,Andrew(eds.),Landscape,Memory and Histor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Pluto Press,2003.并由于与共同体意识、归属感、历史、权力、认同交织在一起而被认为能体现国家性和时代性。近些年来,随着与意识形态的相关讨论不断深化,景观被认为涉及正义、道德和法律,(4)Kenneth R Olwig,“Editorial:Law,Polity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Landscape”,Landscape Research,vol.30,no.3,2005.具有社会共享理念和社会整合的力量,提供了消除科学、研究、政策和实践中存在分歧的方法。(5)Graham Fairclough & Heleen van Londen,“Changing landscapes of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in Tom(J.H.F.)Bloemers,Henk Kars,Amsterdam Arnold van der Valk et al.(eds.),The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Paradox: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 Landscape and its European Dimension,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653.从遗产角度来看,西方学术界将遗产视作构建和维持身份认同的合法化话语,(6)Laurajane Smith,Uses of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55.特别重视遗产所蕴含的强化共同体认同的情感和意识形态作用;公共遗产概念正在成为整合公众参与、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社区遗产实践的理论工具。(7)Angela M.Labrador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Introduction:Public Heritage as Social Practice”,In Angela M.Labrador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Heritage 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4~7.以1992年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标志,景观与遗产两个范畴正式交叠。2004年生效的《欧洲景观公约》(8)《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欧洲委员会网站Council of Europe,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module=treaty-detail&treatynum=176。将景观概念延展到日常生活层面及生态退化区域,景观研究由此体现出更多社会导向和应用价值,并发展成为跨文化对话的领域。总体上看,“遗产景观”和“景观遗产”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领域中不被严格区分的专门概念。就遗产和景观的概念内涵和社会效应而言,文化遗产更多被整合进了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景观知识框架中;在某种程度上,遗产景观正在成为诸多国家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工具。由此,笔者以遗产景观实践一词,对遗产景观所具有的在意识形态观念、认同情感、权力话语、社会价值等领域的主体能动性特征和实践属性进行特别的强调。
(二)针对精神家园建设的实践环节问题
自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9/29/content_2758816.htm。以来,学界关于精神家园及精神家园建设的讨论持续推进。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各民族共创、共建、共享等内在特质,(10)来 仪,杨莹慧:《再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及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精神家园建设旨在培植和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1)严 庆:《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民族》2017年Z1期。实现从政治凝聚到心灵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铸牢。(12)青 觉:《从政治凝聚到心灵认同:新时代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国家的分析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是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现路径是要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3)闵言平:《坚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民族报》2020年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007/1142203.shtml。精神家园建设可以说是各民族为促进民族文化创新交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开展的一项文化建设活动。(14)郝亚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推动民族文化创新交融和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可以说是文化建设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环节。如何为民族文化创新交融营造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环境、氛围和具体实践场域,又如何在民族文化创新交融过程中选取利用各族群众认同度高、传播力强的文化遗产,进行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是精神家园建设实践环节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为各族群众提供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情感体验、观念传播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是首要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活水之源、文化之基,(15)杨文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遗产景观实践,正在成为营造具有中华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和民族文化创新交融社会氛围的公共文化景观,以及整合精神家园建设的物质(文化载体与媒介)、精神(文化象征意义)、行为(文化实践活动)三层面的重要力量。
(三)契合当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下,中国正处于以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下称“两创”)阶段,遗产景观实践已成为群众性的主要文化实践形式。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1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17)《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通知》(文旅非遗发〔2021〕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fwzwhyc/202106/t20210609_925092.html。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中国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近二十年,该项工作已成为政府部门、知识界和民众共同造就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文化事业和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18)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属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各民族重要的非遗普遍被纳入政府非遗保护体系,这意味着地方性文化通过遗产化而具有了公共性,以此能有效促成各族群众间的相互认同、激发民众的民族国家情感。(19)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整体性保护”“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的遗产实践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20)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可以说,朝向人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的局面业已形成。随着非遗保护日渐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国家遗产保护管理体系逐渐完善,国家、市场和民众共同营造的遗产景观,已融汇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正在成为精神家园建设的情感基础设施,体现出与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的文化政治特性,以及参与城市规划、文化产业与遗产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特性,彰显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观念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可见,遗产景观实践具备精神家园建设所需要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主体性民主性,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文化实践角度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的可行路径。
二、遗产景观实践的内涵、特性、类型和领域
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性,涉及文化遗产具体类别或项目的保护传承、经济开发及社区文化生活、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多个层面。不同遗产景观实践类型相互交织构成难以分割的实践系统,融汇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
(一)遗产景观实践的内涵和特性
对遗产景观实践内涵和特性的把握,关键在于对景观的认识。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景观。人类学家Ingold,T.以任务景的概念强调景观是在人的生命行动的时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1)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vol.25,no.2,1993.Tilley,C.强调景观是一种居住和体验的模式,须在人的生命活动实践中被体验;(22)Christopher Tilley,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Places,Paths and Monuments,Oxford:Berg,1994,pp.25~34.Hannes Palang等认为,景观作为人在特定环境下社会生活的一种表达,是整体的、相对的和动态的。(23)Hannes Palang and Gary Frys,Landscape Interfaces:Cultural Heritage in Changing Landscape,Springer,2003,pp.262~309.地理学家Wylie,J.主张,对景观的理解,可从接近/远离、观察/居住、眼/土地、文化/自然四组紧张关系着手。(24)John Wylie,Landscap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2.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到,景观是具有价值意义和媒介传播功能的符号表征,也是根基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过程,可被视为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代码和社会关系文本。基于文化遗产进行的景观实践,既包括具体可视化的物质景观生产,也包括抽象的精神文化呈现。从实践指向的对象和内容看,既包括物理空间、物质实体等客体自在之物,也包括文化象征符号、媒介工具、情感基础设施等主体建构出的功能和价值,还涉及人的思想观念和反身性能力,即人的本体层面。从遗产景观实践的具体行为表现看,涉及以文化遗产为内容和对象的命名、标记、保护、传承传播、利用等建设性实践,以及清除、清洁、重塑、改建等破坏性实践。可以说,遗产景观实践的特性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力及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方面。
具体结合精神家园建设来看,遗产景观实践以物质文化遗产和物理空间为依托,同时涉及非遗、表征、地方性知识、社会环境等非物质层面,涵盖符号表征(文本、命名、地图、标记等)、社会现状(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情感观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身份认同、价值意义等)等层面,涉及各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文化认同、文化服务、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等诸多方面,体现遗产景观实践的精神内涵、发展动态过程,以及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为方便理解,可将遗产景观实践归纳为两类主要的行为:一是围绕景观作为社会情感基础设施所开展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如政府部门主导的景观规划设计、宣传教育与社会治理等;二是围绕景观作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历史重写本而开展的各类群众性遗产景观实践。
(二)遗产景观实践的类型
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按其目标定位和内容形式,可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民俗生活类,即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世代传承发展的标志性民俗事项,如节日、传统礼仪等;二是展演与旅游体验类,即面向文化持有者之外的游客和观众开展的各类文化休闲类景观设计和展演,如舞台表演、影视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三是社会教育传承类,如“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等以保护传承非遗为目的的实践。根据遗产景观实践所依托载体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实体类和传媒类,前者指附着于广场、传习馆、博物馆、图书馆、古建筑遗址等文化地标类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实践;后者即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网络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各类实践,涉及众多媒体形式,如网站、数据库、社交网络平台(微信、微博、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应用软件、广播电视等。总体看,遗产景观实践涉及环境、物质与非物质多层面,内容涵盖十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国家文物体系中对社会开放的那部分。
尽管分类多样,但在实际运作中,不同遗产景观实践类型往往存在相互配合、交融、转化的情况,并由此成为相互嵌合的实践系统。根据遗产景观实践的运作特点和效应,又可将其划归于惰性和活跃性两个基本范畴:如民俗生活类实践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较为紧密,蕴含较多尚未“两创”或“两创”程度较低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系统中相对稳定而基础的部分,属于惰性实践;而展演与旅游体验类、社会教育传承类和传媒类实践,受社会政治环境、科技力量及个体因素的影响较明显,“两创”程度较高,时代特点明显,属于活跃性实践。实体类实践的内容形式和特点往往复杂多样,涵盖惰性和活跃性两种情况。相对应的,活跃性实践相比惰性实践更易受外界环境因素和实践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多重效应和不稳定性。景观实践类型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类型
(三)遗产景观实践的领域
尽管景观实践类型互有交织,但在不同力量主导的具体领域,遗产景观实践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对象各有侧重。服务于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的遗产事业领域、市场主导的遗产经济领域和民间社会主导的遗产生活领域。在政府、市场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共同驱动下,围绕民族文化遗产开展的保护传承和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遗产生活三大领域,在推进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及社会主流文化相互整合、创新交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主导的遗产事业领域,早期侧重文物保护,当下特别强调非遗保护传承和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已从博物馆、古建筑遗址等特定领域和行业的遗产保护,拓展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文化公园的区域性整体保护,通过不断的探索,确立了通过融入百姓生活、激活遗产当代价值的实践定位,形成了较完备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和与文化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有机结合的遗产事业发展格局。政府作为社会文化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此领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领域的遗产景观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社会教育传承类、展演与体验类的遗产景观实践较具代表性,如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的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等的建设;“非遗进校园”、传统戏剧曲艺汇演等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镇的建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民族赛装文化节等民族文化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推进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和民族文化创新交融,是遗产事业领域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典型范例。《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将非遗保护工作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遗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要将非遗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遗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2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974.htm。综合来看,遗产事业领域的遗产景观实践,不仅具有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广度,还体现出从社会实践到思想教育层面的深度。
在市场主导的遗产经济领域,遗产景观实践集中于文化遗产相关的产业领域,涉及诸多业态和商业模式,如遗产旅游、文化创意、出版影像和文艺演出等。消费是遗产经济领域景观生产与实践的主要驱动力。这一领域的遗产景观实践除具有消费经济的普遍特性外,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政治意涵在日益凸显。以最为普遍的遗产旅游为例,《“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了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部署。(26)《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文旅政法发[2021]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ghjh/202106/t20210602_924956.html。正在规划建设的长城、大运河、长征等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将发挥对内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对外展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27)《三部门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8/content_5698069.htm。指明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任务。同月,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的指导意见》,(28)《〈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的指导意见〉出台》,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mzzj.yn.gov.cn/html/2022/gongzuodongtai_0613/42985.html。指出要依托景区平台,完善景区创建与地方发展协同互惠机制,拓展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渠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民间力量主导的遗产生活领域,遗产景观实践以开展基层社区文化建设、满足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为主要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民俗生活类实践。随着网络传媒的普遍使用,特别是藉由自媒体和社交软件的信息传播、交换、共享,遗产生活领域的实践表现出越来越普遍的传媒类实践的特点。民族医药知识、民间歌舞艺术、传统技艺、礼仪庆典等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社区民俗和文化休闲活动等实践形式得以传承发展。倡导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特色村镇街区的建设,是一种典型的以当地百姓为中心、由当地民众赋予文化遗产意义并享有遗产保护传承权益的遗产景观实践。这种遗产景观实践充分发挥了遗产持有者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激活遗产当代价值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此外,民俗生活类景观实践还能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基于地方的深厚文化根脉和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在促进精神家园建设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
三、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原则
确立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原则,须立足精神家园建设与遗产景观实践两者的内在关联。从本体论层面看,遗产景观实践与特定的人和地方关系密切,既依托物质性存在,也强调人的社会参与,应体现遗产景观作为公共象征符号、大众传媒工具、情感基础设施的属性和价值。从方法论层面看,作为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遗产景观实践须为精神家园建设提供理论工具和认识载体,应体现自身所具有的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文化政治内涵、传媒属性和认同情感价值,展现精神家园建设的动态过程和精神气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精神家园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重写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角,也是遗产景观实践的具体担当者,应重视各族人民在精神家园建设进程中的鲜活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文化生产与教育传播、个体生命体验与习性锻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文化创新交融等具体表现及其内在逻辑,体现各族群众的主体性及民主性。结合精神家园建设要求,遗产景观实践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以建设营造精神家园的相关场所设施、符号体系和情感氛围为基础
从文化遗产景观作为社会情感基础设施的角度看,遗产景观实践以景观的规划设计、宣传教育和社会治理为基础面。民族文化遗产景观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设施,承担着符号象征、媒介宣传与氛围营造等任务,其运作原理如Thrift所谈及的情感感染,即通过景观规划设计,将技术和媒介用于制造情感反应和情感关系的广泛社会公共空间中,使其变得类似于网络管道和电缆等保障城市生活的各种基础设施。(29)Thrift,N.,“Intensities of feeling:towards a spatial politics of affect”,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86,no.1,2004.这意味着要重点关注各族人民如何通过日常公共的遗产景观实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如何通过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形象塑造与情感传染,提升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和精神家园建设的参与感、成就感,以及如何共建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简言之,遗产景观实践的目标要求应体现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蕴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30)闵言平:《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中国民族报》2021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103/1144643.shtml。决定着遗产景观实践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构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从遗产景观作为国家情感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看,应综合反映国家、社会及个人三层面的价值追求,使遗产景观实践的目标方向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追求相统一。
在国际上,自《欧洲景观公约》面世,许多国家已将遗产景观视作关乎身份认同、个人和社会福祉的关键要素。在中国遗产景观的规划设计、建造命名、地图绘制、宣传教育等具体实践环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形式,充分发挥遗产景观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体系和融通各族群众情感观念方面的积极作用,彰显其作为国家情感基础设施的价值属性。鉴于社会民众对遗产景观符号的解读及实践意义的感知是主观的和多样化的,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那些凝聚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情感的文化遗产,如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建筑、纪念碑、国家文化公园及重要节日庆典,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首要身份认同,使各族群众获得共同的遗产景观价值意义,体现各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特点。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平衡各族群众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和愿望,在从规划设计、宣传教育到社会治理的整个遗产景观实践过程中,综合考虑不同主体类型的社会阶层、知识水平、权力话语等背景性因素和遗产景观实践类型方式的不同,尽量吸纳各族群众不同类型主体的代表参与。此外,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丰厚,民族地区的遗产景观实践还可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充分利用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精神家园建设协同共进。
(二)以彰显人民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为核心
文化遗产是一代代人不断传承累积的文化财富,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遗产景观实践自然就是一个不断重写和叠加的历史过程。Meinig,D.W.最先将景观视为重写本(palimpsest)。(31)Meinig,D.W.,“Introduction,”in Meinig,D.W.(ed.),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Geographical Essay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7.由于每一代人都在利用他们的景观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身份,这使得景观成为不断叠加的重写本。而精神家园建设同样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的重写本。作为重写本书写主体的各族人民,其所书写的社会历史总是嵌入在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中的。从个体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以促进精神家园建设为目的的遗产景观实践,应关注各族人民在共同体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意义表达,应体现各族人民在实践过程中的生命融入、价值传承及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在国际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32)《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Article/Index/detail?id=15716。《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3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7_81309.html。等重要遗产文件都强调要重视遗产所在地居民的文化传统和民俗生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3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20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15769。确立了非遗保护以社区为中心的总原则,明确文化持有者及其社群是遗产景观实践的核心主体。当前,世界各国通过制定遗产政策和市场驱动,通过识别、保护、管理、活化利用、创新发展等各种遗产景观实践方式,使文化遗产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文化组成和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并使遗产景观实践定位到以人为本、涉及人权和民主的层面。2022年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3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特别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新创造,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3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及其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37)《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通知》(文旅非遗发〔2021〕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fwzwhyc/202106/t20210609_925092.html。专门指出,开展“非遗在社区”工作是一项主要任务,要关注随外来人口迁入并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非遗项目,将非遗保护传承与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相结合,建设非遗特色村镇街区等。综上可见,国家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社区为依托的活态遗产景观实践,人民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彰显人民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应成为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的核心原则。
(三)以实现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为目标
在遗产景观实践中,某一民族或地方社群的遗产景观实践似乎与服务于精神家园建设的公共遗产景观实践存在目标价值方面的张力。对此,需要首先辨别具体民族或地方社群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公共遗产价值,那些遗产价值仅体现于社群内部的小众文化遗产,本身就不属于公共文化遗产范畴。(38)桂 榕,刘虎飞:《仪式的超越表征研究——以河口瑶族度戒仪式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除此之外的所谓遗产景观实践的价值张力,通常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某一民族或地方社群的遗产实践虽然具有公共遗产价值潜力,但因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制约而难以融入社会。公共遗产景观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让遗产跨越地方社会的限制,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从而促成遗产的社会共享。就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而言,要求进行公共遗产的价值塑造,使遗产成为社会每个人的遗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遗产。这就需要解决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制约而难以融入社会的问题。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动非遗小镇建设、发展遗产旅游、建设完善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等涉及人民遗产景观实践层面的一大原因。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遗产化带来的遗产脱域和认识偏差而导致遗产景观实践的无意义或价值虚空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在遗产化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极端状况,即因同质化和虚伪化而失去文化遗产本身的独特价值。针对此,Brumann,C.曾提出本质遗产的概念,并以日本京都的町屋为例指出,遗产化不仅包括建筑本体,更应包括遗产精神层面的内容。(39)Christoph Brumann,“Outside the glass case:The social life of urban heritage in Kyoto”,American Ethnologist,vol.36,no.2,2009.国内有学者提出建成遗产的相似概念,强调遗产化概念应侧重遗产与人的精神联系。(40)吴美萍:《从战后重建到预防性保护——比利时建筑遗产保护之路》,《建筑师》2018年第4期。史密斯提出,遗产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个体层面的遗产构建,也有学者将此过程称为个人层面的情感依托。(41)[德]克里斯托弗·布鲁曼:《文化遗产与“遗产化”的批判性观照》,吴秀杰译摘,《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结合服务于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来说,应倡导超越景观符号的外在物质性,关注每个个体在遗产景观实践时的价值认同和意义建构,注重其对遗产价值内化于心的诠释和体认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激发具有爱国情怀和公共道德意识的情感共鸣,以此消解遗产景观实践目标在个体、地方社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层面存在的价值张力。
此外,公共遗产景观实践还会促成个体层面的遗产景观意义生产与共同体观念成长的有益互动。通过遗产景观价值的分享与传播,除了原有遗产景观的价值和生命力得到激发外,还会凝聚众多分享遗产景观价值的主体,这些分享主体体现了遗产实践的价值互享,并使逝去的传统价值成为再现的价值,地方性价值成为更大范围的价值。(42)高小康:《传承与分享:非遗价值评估研究》,《文化遗产》2020年第5期。这在传媒类遗产景观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典型如非遗传承人通过短视频平台与粉丝群进行遗产演示传播和交流互动。通过跨越时空和民族边界的传播分享,这种传媒类的公共遗产实践会增进不同个体间、不同社群和民族间的遗产观念交流,催生更广泛的共识。由此推而广之,会促进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遗产景观实践观念的提升,从而对精神家园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
四、保障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策略
如前所述,遗产景观实践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如何确保通过三大领域的协同运作,实现遗产景观实践的目标价值,是保障精神家园建设景观实践策略的核心内容。作为支撑性和激励性的保障策略,须整合政府、市场、民间社会及科技传媒等各方力量,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着手。
(一)通过政策优化机制改善社会环境
精神家园建设作为国家当前重要的文化建设任务,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运作管理机制,特别是运用“两创”思维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宣传教育,为各族人民共同参与遗产景观实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实践者、遗产经济从业者和民间各类社会团体组织成员能共同参与到建设国家情感基础设施和书写历史重写本的实践中。过往的遗产景观实践业已说明,只有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遗产景观实践的活水之源、文化之基,以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为遗产景观实践的内生动力,推动各族群众走向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公共遗产景观实践,才能打破民族间地区间的文化区隔,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文化财富,从而促进民族文化创新交融,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针对精神家园建设实践环节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在继续宣传使用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符号资源的同时,还应不断选取利用各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更多语境化的认同标记和更为丰富的文化语言景观、公共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还应大力宣传和鼓励通过旅游休闲、社会教育、艺术交流和商业开发等多样化的文化利用和公共遗产景观实践,不断发掘、丰富和发展各民族立足当下、朝向未来的遗产价值,为民族文化创新交融、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与精神家园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
(二)通过目标价值评估提升社会效能
对遗产景观实践目标价值进行评估和反馈,是保障遗产景观实践对精神家园建设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种激励性手段。从经验事实看,通过基于56个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开展多主体、多类型、多领域的长期遗产景观实践,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正在不断交流、整合、凝聚,并最终成为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然而,对此实践过程及其社会效能的研究还很匮乏。Stephenson,J.基于新西兰两个社区的遗产景观实践研究提出的景观实践价值模型,展示了人们如何通过遗产景观实践,在价值观层面实现重叠共识,较好地阐释了景观实践主体与空间(形式)、时间(过程)的理论联系和实践理念。(43)Stephenson,J.,“The Cultural Values Model: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Values in Landscape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vol.84,no.2,2008.该模型对我们理解和评价中国遗产景观实践的内在机理和社会效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以遗产景观形式、遗产景观实践关系和实践过程为理论指标,建构针对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价值评估体系,既有助于评析估量遗产景观实践对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社会价值,解读个体、社群集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的遗产景观实践意义,也有助于探寻提升遗产景观实践社会效能的途径和方法。
(三)通过新媒体科技应用发掘潜力
新媒体时代,科技传媒已成为助力遗产景观实践的重要手段。它贯穿于遗产景观实践过程的生产、管理、传承、传播、体验和诠释等各环节,以及遗产景观的“两创”、数字化建设等众多方面,以影视节目、社交媒体等为代表的大众话语,正在成为遗产价值观念传播的主要平台。相应地,传媒类遗产景观实践正在成为社会广泛应用的普遍类型。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创造了可以和他人共享的遗产景观,形成了一种传播推广遗产知识和社会理念的新方法,(44)Graham Fairclough,“A prologue”,in Elisa Giaccardi(eds.),Heritage and Social Media:Understanding Heritage in a Participatory Culture,Routledge,2012,pp.16~17.遗产景观实践也因此扩大到了一个更普遍和包容的个体化层面,体现出中国遗产景观实践的人民性和民主性。此外,新媒体时代,遗产景观实践更多表现为对符号、电子图像和拟像的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通过允许跨媒体互动,开辟了遗产景观实践的新局面,技术和媒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更广泛的受众情感反应和情感关系的设计。通过不同媒体和技术的结合,创造了各民族交流互动的社会基础设施、空间场所,支持并促成人们解释、表达和交流遗产景观实践价值观的新方式;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遗产景观实践,还促进了民间社会对遗产实践的理解,并以日常文化生活和表演等各种形式展现出来,为各民族共同开展遗产景观实践创造了一种新型社会环境。可以说,传媒科技已成为当下发掘遗产景观实践潜力、推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还需持续推进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五、结 语
通过对遗产景观实践概念及其实践内涵和特性、类型和领域的概述,对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原则的阐释,对保障精神家园建设的遗产景观实践策略的解读,针对精神家园建设而提出的遗产景观实践全貌得以基本呈现。遗产景观实践这一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的概念,可以较全面地展现各族人民进行精神家园建设的物质基础、文化资源和社会状况,并阐明公共遗产景观实践对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作用。究其本质,遗产景观实践既强调文化遗产景观的物质性及在此基础上作为情感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强调实践主体阐释意义、表达权力话语和书写历史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可以说,作为整合贯穿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的重要力量,遗产景观实践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生活实践角度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的新视角和新途径。立足当下,朝向未来,在遗产景观实践与精神家园建设领域,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面临当下传媒科技极大改变遗产景观实践的途径、方式、格局的情况下,该如何营建良好的文化遗产生态?该如何进一步发掘遗产景观实践促进精神家园建设的优势和潜力?针对多民族、跨民族的遗产景观实践,该如何开展跨学科的深度探讨?而本文仅是初步的思考,且为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进一步的探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