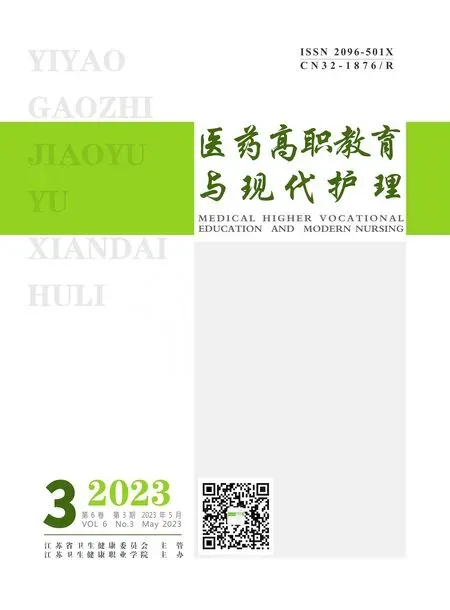论叙事医学对高职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
2023-02-13冯运红龙艺沈洋李小平
冯运红, 龙艺, 沈洋, 李小平
近年来,医患、护患关系问题突显,社会及医学界对医学人文精神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医学人文教育不容忽视,而作为医学人文精神不可或缺部分的共情,是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的人文素养。针对高职院校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基于叙事医学的共情能力培养模式,既可以打破高职院校传统的重专技轻人文的教学模式,又可以培养护生人际沟通和人文关怀的能力,并对构建护患共同体、和谐护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 共情的内涵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价值
共情,亦称移情、投情、神入、同理心等。它来自于德国术语“Einfüglung”,最初被用于描述个体对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共鸣,因此它发端于美学,后续研究与发展涉及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文学等相关领域。Robert.Vischer在其博士论文《论视觉上的形式感》一文中提出,人把自己投射到自然界之中,将内心感受投射到自己喜欢的人或事物之上的这种现象,是人通过意识活动将思想和感情加诸于对象,使对象具有一定的情感和审美色彩,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亦称“移情说”,是西方共情理论的发展基础[1]。Titchener认为,共情是通过自身的想象去体验他人的经历,即将客体人性化,感觉自身融入到他人或者其他事物的内部中去[2]。而Rogers则认为共情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即站在别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认同和理解别人处境和感情的能力,他将共情相关理论和概念从心理学领域外延至医疗卫生领域,认为共情是医者传达患者感受如同传达自己的感受一样,同时又不被这种感受所束缚,失去自我意识的能力[3]。随着共情理论在医学领域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它已成为构建和谐医患、护患关系的一剂良方。张玉芳等[4]认为共情是良好护患关系的切入点,是护患沟通的精髓所在,一切高效护理的基础。罗彩凤等[5]认为共情与护生的职业态度呈正相关,共情会影响护生的职业态度,加强护生的共情教育能够培养其积极的职业态度。王鑫星[6]对护生共情进行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操作性定义:指护生在临床情境中,站在患者立场感知其心理与情感变化,给予必要的理解与帮助,以减轻患者心理痛苦、缓解患者消极情感状态的能力。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视角,从共情的概念与内涵出发,探讨共情在不同领域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是在最初的美学领域,还是在医学等其他领域,大多学者都认为共情是一种能力。已往研究表明,在医疗护理领域,共情作为一种能力,是培养护生职业认同感、建立良好医患、护患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在注重护生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的同时,也要致力于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使共情充分融入到医学护理教育中,以培养护生良好的专业素质与人文精神,从而全面提升我国护理人才的综合素养。
2 叙事医学融入护生共情能力培养论证
2.1 叙事医学与共情之关系
“叙事医学”一词首次由美国学者Charon于2001年提出[7],并对“叙事医学”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认为叙事医学是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指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并为之感动,提出通过精细阅读和反思性写作的叙事训练可以提高叙事能力。Charon认为叙事医学能够拉近医患距离,医护能在叙事反思中与患者共情,并相互信任、尊重与理解,从而达到高效沟通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8]。韩启得院士认为叙事医学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遵循叙事规律践行的医学;而叙事素养是指认识、吸收、解释疾病故事的能力及易受疾病故事感动的同理心[9]。他强调了叙事素养在叙事医学中的重要作用,而“讲故事”和共情则是构成叙事素养的充分必要条件。李平甘等[10]研究指出,叙事医学是以叙事能力为基础,同时具备对医生、患者、同事及公众高度复杂叙事情境理解力的医学实践活动,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有助于提高医生的职业素养、人文精神及共情能力。叙事医学是现代医学促进医学人文回归的重要手段,而共情则是叙事医学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在叙事医学中,共情可使医者切实体悟“救死扶伤”“除人类之病痛”中的医学人文精神,真正达到“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境界。医学的叙事可催化护患的共情,护患的共情可促进患者疾病的转归,而患者疾病的转归,一方面可有利于和谐护患关系的构建,一方面有利于护理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认同感与积极的职业态度。因此,将叙事医学融入到高职院校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之中势在必行。
2.2 叙事医学融入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科学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医学界强调更多的是医学的专业化、技术化甚至市场化与商业化,技术至上的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医学人文精神倡导的漠视以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淡化,使医患、护患关系僵持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中人文主义缺失的现实困境,不少学者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人不是一个机器或者机器部件,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兼具躯壳与灵魂的实体,作为医务人员,不仅要关心患者的疾病状况,更要关心或同情患者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学者分别从本体论、生理学、进化论及遗传学等维度对disease和illness进行了区分。有学者认为disease是器质性或精神性功能障碍,illness是对功能障碍的主观意识,而这种意识可能成为决定适当行为的社会价值观,而有学者认为illniss就是患者对病情的直接感受,通常在特定疾病的临床诊断之前发生,因此,在医学逻辑中,illniss先于disease出现[11]。患者无论发生何种疾病,除了生物学障碍之外,还会经历与“疾病”状态相关的“病态”效应或存在性焦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这些担忧和恐惧,呼吁现代医学必须重视医学人文的回归。而叙事医学作为人文回归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运用其相关理论重构医学人文主义精神,重塑医疗护理中的人文关怀,是增进护患沟通、缓解护患矛盾的重要途径。在医学教育领域,叙事医学教育在国外已成为人文医学教育的研究热点。将叙事医学教育融入到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培养中去,既能拓宽叙事医学在医学教育中的研究领域,又能为培养高水平护理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叙事医学融入护生共情能力培养意义重大而深远。
2.3 叙事医学融入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培养的可行性
“医生的嘴,护士的腿”,整天穿梭于各个病房之间的护理人员接触患者最为密切,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心理状态等更为了解,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的机会也更多。护理人员良好人文关怀能力的塑造,离不开护理教育阶段对其共情能力的培养。叙事医学融入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培养,在理论上已得到众多学者的有效论证,在实践上亦被证实其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2011年,在护理教育领域,我国已有学者将叙事医学教育理念引入到护理教育之中[12],以培养医院临床护士与院校护生的共情能力。叙事护理教育已被研究者运用于《基础护理学》《老年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护理心理学》《护理学导论》《社区护理学》以及护理人际沟通、护理人文关怀、护理伦理学等护理学课程中。不论是郭瑜洁等[13]的“关怀叙事”教学模式,还是高晨晨等[14]开发的叙事护理素材,其叙事护理教育形式无外乎以下4种形式:听故事与讲故事、阅读经典文学作品、鉴赏文化艺术作品及书写反思性日记。不难发现,以上4种教育形式皆受叙事医学的两种特色工具——精细阅读与反思性写作的启发。以上研究表明,在我国,叙事护理作为一枝独秀,成为叙事医学的一个分支,运用叙事的相关理论与工具,为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培养独辟蹊径,有利于护理人员人文素养的强化及其人文关怀能力的提高。
3 叙事医学融入高职护生共情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
3.1 精细阅读医学史,为培养护生共情能力奠定良好契机
医学人文不仅涉及医学,还涉及到文学,通过文学文化知识来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精细阅读与疾病相关的诗歌、小说甚至名人传记能带领我们深入医疗探讨之中,能使我们融入患者的情绪、价值观等当中去,与患者共情,深刻体会患者生理与心理上的疾苦与不适。但是针对高职院校医学生来讲,大部分生源来自农村,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加之农村学生父母自小对孩子教育不够重视,农村学生对课本以外文学作品的阅读少之又少,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和基础。教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欲想在短暂的三年时间内培养出兼具医疗水平和人文修养的高职医学生实属不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医学生想要讲好医学故事,传播好医学声音,传递好人文关怀,彰显医学人文精神,必须读史明史——医学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医学史。由于高职院校学制的特殊性与局限性,国内各高职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的寥寥无几,或者仅为选修课程,其学生覆盖面窄,学时数微乎其微,远不能达到使学生聪慧明智的效果。
3.1.1 品鉴西方医学史,与海外经典共情 众所周知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其医学誓言医者皆耳熟能详,但对于他的医学故事和成名之路知者甚少。传说他的祖先是医神阿斯克雷庇亚斯和大力神海个利斯的后裔。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信,从控制鼠疫到为名人诊治疾病,从彻底放弃神道医学到对医学伦理学的贡献,从《希波克拉底文集》到希波克拉底誓言,他的每一个故事皆能启发医者对生命、对医学及人文的深层次思考。名扬于世的画家达·芬奇,我们为之熟悉的恐怕就是他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名画巨作,但这些巨作背后的故事以及隐藏的科学素养,大部分学生尚无所知。作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达·芬奇,不仅是画家,还是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解剖学家。他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凭空想象和空穴来风。文艺复兴的浪潮使人们冲破了宗教的枷锁,从对人体裸体形态之美的欣赏到对机体内部的研究,达芬奇拿起刀子解剖起来,他把所有的发现画成了几百幅图画:心脏、消化道、生殖器官、上颌窦、神经系统、子宫内胎儿的情况等;他绘制的人体比例图《维特鲁威人》,也诠释出他对解剖学的科学贡献[15]。达·芬奇超群的艺术创造力除了依靠其天赋异禀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还依靠于他对真理和科学的执著追求,解读他的故事,有利于培养医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医学素养以及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3.1.2 品读中华医学史,与医者仁心共情 我国医学史的发展亦悠久而丰富。《诗经》中就记载和描述了多种药物知识,反映出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可谓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史记载;而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医学史性质的专著。在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大师名家在其医疗实践中,无不彰显出优秀的医疗伦理传统美德。药王孙思邈《备急千金方》中强调作为一名优秀的医者,既要有精进的医术,又要具备良好的文史、哲学知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须“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勿自虑吉凶、勿避崄巇,不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皆应“一心赴救”。从三国时期董奉的“虎守杏林”到明代吴庆龙的“梅树满谷”,从费长房的“悬壶济世”到韩康“卖药言不二价”,从古至今,我国不乏医技高超、医德高尚的千古名医,他们治病救人于水火中的美名佳话流传至今,激励着无数的医者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时刻不忘保持一颗“救死扶伤”“一视同仁”“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行医”的初心。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传统的医学史,各种名医事迹不胜枚举,将医学家们动人的行医故事娓娓道来,既能增加高职院校护生学习医学的浓厚兴趣,又能将医疗道德修养在其临床实践之前强化于心,培养其医学人文精神,提高其人文素养,为其共情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契机,待其进入临床实践工作后,能够体贴入微、感同身受的解患者生理与心理之疾,为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2 反思性中文叙事,为构建护患共同体搭起共情桥梁
3.2.1 在经典叙事中体验反思,彻悟共情 反思性写作作为叙事医学教育的第二大工具,在培养护生共情能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Larocco[16]、Miller等[17]研究认为反思性写作可以有效提高医学生的共情能力;Charon提出的“平行病历”(parallel chart)就是将文学叙事引用至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一种具体的反思性写作方法,是一种培养医务人员临床叙事能力的有效形式[7]。平行病历又称叙事医学病历、平行人文病历或影子病历,是临床医学病历的补充。叙事护理在我国叙事医学中独树一帜,在其叙事护理教学中,在平行病历的基础上延伸发展了平行护理病历,也称护理叙事日记。朱红珍等[18]研究中,要求护生把护理病历以外的诸如患者疾苦、心理体验以及护生自身感受等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然后再将其在叙事分享会上分享给老师和其他护生,让老师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让护生能从彼此叙述的故事中深刻感悟健康、病痛、生死等的真谛,在培养护生良好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同时,有效提高其共情能力和人文素养。
平行病历的评价可归纳为“四有标准”:有意思、有意蕴、有意味和有意义[19]。怎样才能让平行护理病历达到以上“四有标准”呢?首屈一指的是要提高护生的叙事能力和写作技巧,打破教科书和专业术语的束缚,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叙述患者的病痛经历以及与患者沟通交流中的所感所悟。书写平行护理病历不仅仅是简单的叙述和记录,它是护理人员对患者遭遇的真实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的外化表现。无论是经典的影视题材《雨人手足情未了》《第六感生死缘》《闻香识女人》,还是书籍《霍乱时期的爱情》《错把妻子当帽子》与音频《死亡如此多情》,无论是“生命伊始的相迎”“成长途中的相伴”“流金岁月的相依”“桑榆到晚的相守”“临别之际的相送”,还是“唯美的精神甜点”“演绎关怀的舞台”“有节律的关怀会谈”等叙事护理素材[14],从对英文教材的唯美中文翻译,到具有艺术气息的教学情景设置,无不体现中文之美。中文的艺术之美首先从文字上让读者或听众便获得视觉与听觉上的认同,从而进一步想要去了解故事的具体情节和感受其人物的喜怒哀乐。通俗易懂又具美感的语言能使护生真正懂得“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者情怀,也能使学生在感受与运用中文之美的同时,不断培养和提升自身与患者的共情能力,使其认识到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3.2.2 在中文演绎中求其友声,升华共情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写好平行护理记录,引起护患、师生、生生等多方共鸣,是一门艺术。作为护生,首先要完成反思性护理记录,在与病患充分沟通交流、实施整体护理之后,切身体验其生理病痛和心理疾苦,再把自己从中的真实体验与感悟,用恰当而具美感又不失叙事护理原则的语言书写出来,这里的美感强调的是中华文字的意蕴和优美,让人耳目一新的吸睛之笔,能吸引听者或读者用心倾听与感悟,并被其彰显的人文关怀与素养所感染。作为护生,书写完平行护理记录后不是将其立即封存,而是反复细读并分享给其他护生;作为教师,要为护生搭建形成“友声”和共鸣的平台,在护生完成个人反思性写作之后,开展小组或集体反思。一方面,护生在反复阅读自己的叙事作品时,会发现故事的主角除了病患,还有护生自己,患者以“性命相托”,医护便“生死相依”,护生以主角的身份贯穿护理的全过程,更能感同身受病患的疾苦,建立起护患共同体;一方面,护生将其分享给老师和其他同学,使故事中的医疗、诊疗、护理细节再现,护生本人可以进一步审视护理工作中的护理效果与护患关系,进行二次反思;同时,教师可以带领护生,通过对其叙事故事细节的分析与探讨,将“人文关怀”“医乃仁术”“医者仁心”等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实际的案例简单而深刻地凝炼出来,使护生对医学及医疗护理行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对人文主义精神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达到集体学习和反思的效果,使护患、师生、生生皆共情,护生的专业技能、文学素养及人文素养等皆能得到提升。
4 结语
将叙事医学融入到高职院校护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中,从中西方医学史和中文叙事的视角强化护生精细阅读与反思性写作的能力,不仅有利于护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外医学的发展历程和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利于培养护生的共情能力和人文综合素养,构建护患共同体,进一步促进医学人文精神回归医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