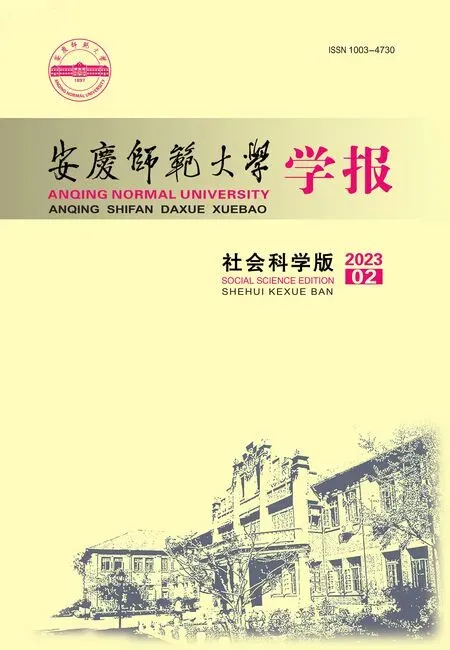从黄梅戏小戏看戏曲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2023-02-07张莹
张 莹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地方戏曲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戏曲的发展与民俗活动息息相关,而且戏曲中“保留有民间民俗文化的传统和烙印”[1],还有学者将地方戏曲归入“游艺民俗”[2]261。但同时学者们也意识到“关于戏曲语言文化的研究,对现代语言学来说,尚是一个有待开发深入的重要领域”[3]。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分为本戏和小戏。小戏一般被认为是黄梅戏的早期形态,主要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考察黄梅戏小戏剧目语言,从语音、词汇、语法入手分析戏曲语言与民俗文化、基础方言的关系,梳理黄梅戏小戏的语言及其演变,对于保护语言文化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戏曲语言是民俗文化的产物
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2]1,“是特定的民族、时代、地域的产物”[2]7,一般分为“生活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2]3。安庆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着黄梅戏小戏的语言。安庆被称为中国竹乡,盛产竹子,因此该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竹子息息相关。以小戏《打猪草》为例,该戏围绕少女陶金花偷摘了金三矮子家的竹笋展开,其中反映了竹子对当地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性。当地群众日常以竹笋为食,其中的唱词“笋子年年兴,一家人吃饭,全靠一园笋”就反映了这一饮食文化①本文中引用的所有小戏均出自安徽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1958年编,安庆室文化局1998年重印的《安徽省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第九集、第十集。。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也多用竹子制作,如金三矮子拒绝给陶金花竹笋时的两句道白:“那一根,不行不行,那是我家婆留着打澡盆箍的”,“不行不行,这是我舅娘做浆布篙的”。可见,“澡盆箍”“浆布篙”这两种生活用品就是用竹子制作的。生活中还有以制作竹制品为生的手艺人“篾匠”,如:
(1)金三矮子:没有关系,从小我妈给我学过夹匠。陶金花:篾匠!
金三矮子:手艺没到家叫夹匠,一夹就好着。(《打猪草》)
《安徽民俗》中记载“篾匠”是“篾工”的俗称,“多出自皖西一带,潜山、舒城尤多”[4]35。从地理位置上看,潜山属于安庆市,舒城与潜山临接,因此黄梅戏小戏中的“篾匠”可以看作是安庆地区行业民俗的体现。
正因为在安庆地区,竹子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黄梅戏小戏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与“竹子”有关的歇后语。如:
(2)a.竹子无节——大通(《登州找子》)
b.澡盆炸了箍——彭泽(同上)
另外,安庆位于长江下游,曾经是下游的一个重要港口,船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黄梅戏小戏中也有不少与船有关的歇后语,如:
(3)a.船头上架菜刀——池州(《登州找子》)
b.桅杆上挂灯笼——登州(同上)
安庆的太湖、望江地区有“还年”习俗,即“在除夕那天祭拜祖宗,灶神和土地神等的仪式活动”[5]。黄梅戏小戏中就反映了这一传统的“还年”习俗。如《二百五过年》中讲述了年关将至,智商不高的丈夫外出卖纱被骗,夫妻二人只好借鱼、肉、柴、米、香纸过年的故事,其中就涉及到“还年”习俗,如:
(4)a.说好话。你两个人还·年·吧。(《二百五过年》)
b.把东西拿来。我两个人还·年·说好话,莫说坏话。(同上)
黄梅戏小戏中的“还年”还有特殊用法,请看《打哈叭》中的一段夫妻间的对话。
(5)哈叭:你叫我出来做么事?
陈氏:我叫你出来打主意。
哈叭:我家祖宗三代都是母·鸡·还·年·。
陈氏:你家爹爹?
哈叭:奶奶。
陈氏:你父亲?
哈叭:妈妈。
陈氏:你呢?
哈叭:是你嘛。
陈氏:是我当家,你要听我吩咐,你到隔壁伯伯家去,借点米来,煮饭吃。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我家祖宗三代都是母鸡还年”应是指哈叭家里祖孙三代都是女性当家。这一解释似乎与“还年”习俗毫无关系。但《安徽省志·民俗志》已经指出“母鸡还年”这一说法其实与性别禁忌有关。由于“男尊女卑”“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观念,祭祀活动一般“只限于男性参加”,“人际交往时,家庭内一般都是由男性出面,主持接送”,“女性绝不轻易出头露面。否则,就会被讥为‘母鸡还年’”[6]。由此可见,黄梅戏中的“母鸡还年”是安徽地区对女性当家的蔑称。
综上所述,民俗文化影响着戏曲语言,地方戏曲语言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的产物,而且可以通过民俗事象来考证语言材料。
二、戏曲语言是民俗文化的载体
学者已经认识到“通过方言的研究可以透视方言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心理等”[7],“民俗事象无所不在,它必然也直接反映在方言词汇里”[8]。地方戏曲是重要的民间口头语言艺术,有其特定的基础方言,下面我们就来探讨黄梅戏小戏语言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如:
(6)a.正月里,正月八,爹娘将我嫁婆家,请先生,日子查,请屠户佬忙把猪来杀,请轿夫忙把轿子扎,吹长的,是喇叭,吹短的,是唢呐,吹吹打打小女子到婆家。来在婆家门,忙把轿子下,两代牵·娘·来牵奴家,先拜天和地,后拜二爹妈,拜过祖先新房踏,先吃交杯酒,后吃交杯茶。(《打哈叭》)
b.驼子三巧:兄弟三人都没有接·老婆。(《陈广大上门》)
(7)陈氏:一心心反·穿·罗·裙·嫁别人。(《打哈叭》)
上面的例子反映出传统的婚嫁习俗。例(6a)反映了男女结婚时包括择吉日、迎娶、拜堂等的一整套程式化的操作程序。安徽“各地迎娶的方式通常有三种:迎亲、送亲和等亲”[4]51。例(6a)反映了送亲习俗,即“男方家不派人去接新娘,女方家自备鼓乐、彩轿向男家送女儿”[4]51,而例(6b)中的“接老婆”,则反映了“迎亲”或“等亲”习俗,即结婚时男方派人(新郎或新郎的兄弟、叔侄)去接新娘子。
例(6a)中的“牵娘”则是传统婚礼中的重要人物,必须是夫妇同在、儿女双全、福寿兼备、并且会说吉利话的女性亲戚长辈,负责搀扶新娘上下花轿,一般男女双方都要请两位牵娘。“牵娘”这类承载民俗要素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为“民俗语汇”[9]。
例(7)中的“反穿罗裙”则反映了妇女改嫁的习俗。
再如黄梅戏小戏中有大量的“粑”,反映了安庆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粑”指一种饼状食物。目前安庆地区较为常见的为“蒿子粑”,由米粉、腊肉、蒿子制作而成。但是在黄梅戏小戏中,我们可以看到“粑”可以由小麦粉、荞麦粉、米粉等多种原料制作,甚至还有鸡肉做成的鸡粑。如:
(8)a.小麦粑吃多了,肚子内发烧,我不把茶给你喝。(《卖斗萝》)
b.荞麦粉磨上一斗多,大粑做了几十个,小粑做了一百多。(同上)
c.没得米磨粉,怎能做粑吃?(《打哈叭》)
d.杀鸡,做粑,鸡粑带酒,样样都有。(《打猪草》)
这其实是传统节日“三月三”在安庆地区的遗留,吃蒿子粑以纪念死者、祈求平安。
“三月三”是“我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节日之一”[10]225,“上古时称之为上巳节,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据传,三月上巳到水边洗澡,能洗去污浊,除去旧年不详。人们也趁此机会举行一些娱乐活动”。而且“事实上它已成为青年男女互相结交的节日。汉朝以后,三月三与求偶探友的关系在汉族地区虽已消失,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仍保持着古风,至今盛行不止”[10]224-225。如壮族的“三月三”现在又称为“歌墟节”(或“歌圩节”)。“三月三歌圩是一个集祭祀、社交、择偶、娱乐、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性节日”[11]。
我们可以看到,黄梅戏小戏中还完整保留着“三月三”这一中国传统节日民俗。如:
(9)a.年年有个三月三,先生放学我转回还。一来回家看父母,二来是回家调换蓝衫。(《蓝桥汲水》)
b.杨三笑:你三月三可曾祭坟的?白氏:是祭坟的。(《钓蛤蟆》)
c.去年间三月三夫带我一阵,一为祭扫二带游春。(《郭素贞自叹》)
小戏《蓝桥汲水》讲述了魏魁元与蓝玉莲井边相会的故事,与“三月三”男女求偶的旧俗吻合,男主人公魏魁元在三月三这一天回家换洗衣服,则是上巳节沐浴风俗的反映;小戏《钓蛤蟆》中记录着“三月三”祭祀的风俗;小戏《郭素贞自叹》中记录了“三月三”祭祀与踏春游玩的习俗。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戏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小戏语言发掘民俗文化。
三、戏曲语言是方言的活化石
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功敏指出“小戏唱词、念白的语言风格,都充盈着浓郁的安庆方言特色”[12]517。而方言是发展变化的,有“老派”和“新派”的区别。通过黄梅戏小戏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安庆方言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而探索语言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词汇、语法。黄梅戏小戏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显示出安庆方言的特色。
下面先来分析黄梅戏小戏语言中所反映的安庆方言语音特色。请看上文例(2)和例(3)所示的歇后语,重述如下:
(10)a.竹子无节——大通(《登州找子》)
b.澡盆炸了箍——彭泽(同上)
c.船头上架菜刀——池州(同上)
b.桅杆上挂灯笼——登州(同上)
歇后语是汉语口语中特有的熟语形式,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根据前后两个部分所用修辞手法的不同,可以将歇后语分为两类,喻意歇后语和谐音歇后语。其中,例(10a)为喻意歇后语,其后一部分是对前一部分的解释,利用竹子的形态特征构成;例(10b-d)为谐音歇后语,其后一部分是借用同音字来表意,前后两个部分都构成说明的关系。
例(10b)中,歇后语的前一部分“澡盆的箍炸开了”导致“盆拆”(即“盆被拆”)的结果。根据班友书的考察,黄梅戏中“盆”与“彭”同属定字韵,阳平,都读作[phən];而“泽”与“拆”同属结字韵,为入声,都读作[tsε][13]。因此,安庆方言中“盆拆”与“彭泽”语音相同,形成谐音。“彭”读作[phən]还反映出安庆方言中没有后鼻韵母的特点。
例(10c)中,“船头上架菜刀”的目的是“吃舟”。根据班友书的考察,黄梅戏中,“池”和“吃”同属起字韵,前者是阳平,后者为入声;“州”和“舟”同属求字韵,阴平[13]。因此,安庆方言中“池州”与“吃舟”语音相似,形成谐音。
例(10d)中“桅杆上挂灯笼”形成的是“灯州”。根据班友书的考察,黄梅戏中,“登”和“灯”同属定字韵,阴平;“州”和“舟”同属求字韵,阴平[13]。因此,安庆方言中“登州”与“灯舟”语音相同,形成谐音。
通过分析例(10b-d)所示的谐音歇后语,我们可以看到黄梅戏小戏语言中保留着安庆方言语音的特色。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黄梅戏小戏中看出其语音变化的痕迹。例如:
(11)昨天去晏·了,嗬啥,今天要赶早,呀子伊子呀。(《打猪草》)
例(11)中的“晏”表示晚的意义,这是老派安庆方言语音的遗留。根据鲍红的考察,在老派安庆方言中既有“晏”,又有“晚”,二者语音不同,“晏晚”语音为[ŋan],而“晚”的语音则与普通话一致为[uan][14]。而《黄梅戏唱腔赏析》中所收录的由严凤英演唱、王文治和时白林记谱的《打猪草》唱段中,该句唱词已经变为“昨天起晚了,嗬舍嗟!今天要赶早”[15]。从“晏”到“晚”的变化过程中,既可以看出黄梅戏小戏语言中所带有的安庆方言语音特色,同时也可以看出黄梅戏语音逐渐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下面以“吃”为例探讨黄梅戏小戏语言中所反映的安庆方言词汇特色。
黄梅戏小戏中,“吃”的组合能力较强,能和“吃”组合的词语可以是固体、气体、液体,如例(12)和例(13)所示。
(12)a.伢,把楼上的干菜割点,打几个鸡蛋把哥哥吃·。(《砂子岗》)
b.火在这里。你吃·烟,我到后面去拿被条子。(《瞎子闹店》)
c.一天要吃·三顿酒。(《打纸牌》)
(13)生意做成了,我家吃·茶烟,可好吧?(《卖老布》)
不过,从黄梅戏小戏中已经可以看到,“吃”的使用范围有了缩小的趋势。“吃”的用法正在向普通话靠拢,能与液体、气体搭配的,已经不再限于动词“吃”。如:
(14)a.此茶我不喝·哇。(《卖疮药》)
b.我没有打酒喝·。(《打豆腐》
(15)a.打火抽·筒烟。(《打猪草》)
b.我的哥不吸·烟福福气气。(《辞院》)
根据鲍红的考察,安庆方言中“除了可以说‘吃饭’,也可以说‘吃烟’。如:这人几好多好,不吃烟不喝酒。”[16]可见,在安庆方言中“吃”仍然可以和表示气体的名词组合。不过“吃”已经不和表液体的名词组合,即不能说“吃酒”而需要说“喝酒”。安庆方言同样显示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综上所述,从“吃”组合能力的变化中,可以看出黄梅戏小戏词汇使用中的安庆方言特色,及其逐渐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黄梅戏小戏的语法中同样反映出安庆方言的特色。下面我们以“把”字句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季艳[17]、刘玉倩[18]的讨论,安庆方言中的“把”具有动词、介词、量词和助词等多种词性。黄梅戏小戏中的“把”同样具有上述多种词性。
第一,动词“把”。动词“把”在黄梅戏小戏中可以表示多种词汇意义。最常用的有下述两种。一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动词“给”。比较:
(16)a.你老人家吃得好就把·几个钱。(《借妻》)
b.你老人家吃的好就给·几个钱。(同上)
另一种则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致使动词“使、叫、让”。比较:
(17)a.倒把·我蓝玉莲不好开言。(《蓝桥汲水》)
b.倒叫·我蓝玉莲不好开言。(同上)
“把”相当于致使动词时,用法与“使、叫、让”一致,其后必须带上表示受事的名词,如:
(18)a.倒把·我二八女脸带红光。(《罗凤英捡柴》)
b.自幼爹娘把·我学会了艺。(《纺棉花》)
c.自小我母亲把·我包脚,我怕痛,所以我没有包脚。(《钓蛤蟆》)
“把”相当于普通话中动词“给”时,用法较为复杂。这类“把”可以单独使用,如例(19)所示;“把”后也可以带上宾语,如例(20)所示。
(19)a.把·就是大方客,不把·就是滴滴鬼。(《打猪草》)
b.好好,我把·,我把·。(同上)
(20)a.肚子饿了,把·两个我吃吃。(《闹花灯》)
b.请大姐把·点水我解口干。(《蓝桥汲水》)
c.一百把·郎做买卖,一百把·郎做盘川。(《剜木瓢》)
如例(20)所示,“把”的宾语可以是数量短语(如例(20a))、指物的名词短语(如例(20b))、指人的名词短语(如例(20c))。
动词“把”还可以像普通话中的动词“给”一样①关于现代汉语口语中动词后“给”的词性,学界还有争议。这里采用朱德熙的观点,将其看作动词。,用于动词后,形成“动词+把”结构。比较:
(21)我没有好东西送·给·你,这短褂子送·把·你,做做抹布也要得。(《剜木瓢》)
这类结构在黄梅戏小戏中大量存在,如:
(22)a.卖纱,卖·把·我嘛。(《二百五过年》)
b.一一说·把·为夫听。(《闹花灯》)
c.我这裤子脱·把·你穿。(《剜木瓢》)
d.如今我送点么事给她,把这袜子给·把·她。(《剜木瓢》)
e.卖与·把·富豪家富豪不要,贫穷人想娶奴并无分毫。(《烟花女自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黄梅戏小戏中,“把”可以用在大部分动词后,却不能用在动词“把”后,即不存在“把把”连用的现象。如例(22d)所示,虽然小戏中的动词“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给”,但小戏中允许“给把”连用。更有意思的是例(22e),“卖”后已经有了“与”,而且“与”和“给”为同义词。但“与”后可以再加上与之同义不同音的“把”,构成“与把”连用。
朱德熙已经讨论过现代汉语口语中这类“动词+给”结构。朱德熙指出现代汉语口语中不存在与“卖/买+给+N’+N”平行的“给+给+N’+N”,“这是因为两个连接出现的‘给’字融合成为一个”[19]。并进一步指出“‘我给他一本书’可以看成是‘我给给他一本书’的紧缩形式。‘我给给他一本书’实际上不说,这是因为两个相连的‘给’融合成为一个了。可是有的方言里有这种说法”[20]。邢福义指出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①《绿化树》讲述的西北地区的生活,作家张贤亮在西北地区生活多年。其中的例子“给给小郎郎不用”是一句带有西北方言特色的歌谣。以及乌鲁木齐方言中有此用法[21-22]。王东也观察到“‘给给’连用的现象多集中在西北官话(如甘肃兰州话、宁夏中宁方言、宁夏黄河湟水沿岸方言)和晋语(内蒙古晋语区、山西文水方言、山西平定方言)中”,属于中原官话信蚌片的河南罗山方言中也有此用法[23]。不过,王东也注意到河南罗山方言中“给给”连用时有两种读音,老派多读为[kei13tɕi54],新派多读为[kei13tɕi54][23]。显然,不论新派还是老派都将两个连用的“给”读为不同语音。这恰好说明读音不同是“给给”共用的前提。换句话说,连用的两个汉字语音融合的条件是二者必须语音相同。黄梅戏中不存在“把把”连用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另外,黄梅戏中同义不同音的“给把”连用现象其实是安庆方言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由于安庆“位于吴越方言、楚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北方方言等中国几大方言区的交汇处”,安庆方言“受到了多种方言的影响和滋养”[12]517。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安庆方言中引入动词“给”,进入“把”“给”混用期,此阶段“把”与“给”能够替换使用。该发展阶段在黄梅戏小戏中的反映就是在同一个剧目中“把”与“给”的交替使用,如例(16)所示。这就造成黄梅戏小戏中既存在“动词+给”结构,也存在“动词+把”结构。当选择“动词+把”结构,而主要动词为“给”时,“给”“把”不同音,不会发生语音融合,于是形成了“给把”连用现象。
第二,量词“把”。当“把”做量词时,既可以是名量词,如例(23)所示;也可以是动量词,如例(24)所示。如:
(23)a.坐在两把·椅上。(《闹花灯》)
b.随手撒把·沙。(《打猪草》)
c.我抓了一把·糟吃着。(《打豆腐》)
d.我这个人大概后来是还有点把··功名。(《瞧相》)
(24)a.助我一把·水桶上肩。(《蓝桥汲水》)
b.王小六,你也来掷一把·。(《打豆腐》)
第三,介词“把”。当“把”做介词时,一般用于动词前。如:
(25)a.我把·你好有一比。(《闹花灯》)
b.就把·猪菜寻。(《打猪草》)
c.同年嫂嫂真有情有义,把·我看得很不轻。(《剜木瓢》)
d.我把·你称给撇掉。(《纺棉花》)
e.你把·拳打给我看看,我能破得开。(《打豆腐》)
(26)a.大嫂子,把·手接着。(《纺棉花》)b.没有,把·纱子抵嘛。(同上)
(27)a.我卖着钱来家,你把·我买个红灯笼,大爆竹噢。(《二百五过年》)
b.你卖着钱来家,我都给·你买。(同上)
(28)我家兄弟把·我家里走。(《苦媳妇自叹》)
例(25)中的“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介词“把”,表示处置;例(26)中的“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介词“用”;例(27)中的“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介词“给”;例(28)中的“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介词“往”。
第四,助词“把”。“把”做助词时,一般附着在数词或者量词后,表示“有零头”[24]。如:
(29)a.把鸡杀上百把·两百只。(《借妻》)
b.你怎么晓得我的鸡斤把·半,半把·斤啥?(《骂鸡》)
c.说句把·闲言语也是有之。(《胡延昌辞店》)
从“把”字的用法中,我们已经看到动词“把”逐渐替换为“给”的发展趋势。同样反映出黄梅戏小戏语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综上所述,黄梅戏小戏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反映出安庆方言的特色,可以看作是方言的活化石。崔军民等学者已经指出“语言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生态语言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处于动态平衡之中”[25]。黄梅戏小戏中的语言从安庆方言向普通话发展的趋势,其实是方言和普通话在竞争中相互影响并最终达到新的语言生态平衡的过程。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作为文化载体的这些语言同样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消亡对于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26]。因此,研究黄梅戏小戏的语言及其演变,对于保护语言文化生态平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论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王蒙的散文《我的另一个舌头》中说:“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27],实际上就道出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戏曲语言和文化之间同样关系密切。第一,地方戏曲语言是民俗文化的产物。从黄梅戏小戏中可以看到,戏曲语言与安庆地区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如黄梅戏中的歇后语就是安庆地区生活民俗的体现。第二,戏曲语言是民俗文化的载体。黄梅戏小戏中记载着安庆地区的婚嫁、饮食等风俗,甚至还保留着中国传统节日的“三月三”风俗,因此,可以从小戏的语言中发掘民间的风尚习俗。第三,戏曲语言是方言的活化石。黄梅戏小戏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都体现出安庆方言的特色,同时反映了安庆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趋势。
总之,从黄梅戏小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戏曲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民俗文化影响着戏曲的语言,另一方面戏曲语言中也反映着民俗文化。这也反映出黄梅戏小戏既是安庆地区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安庆方言研究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