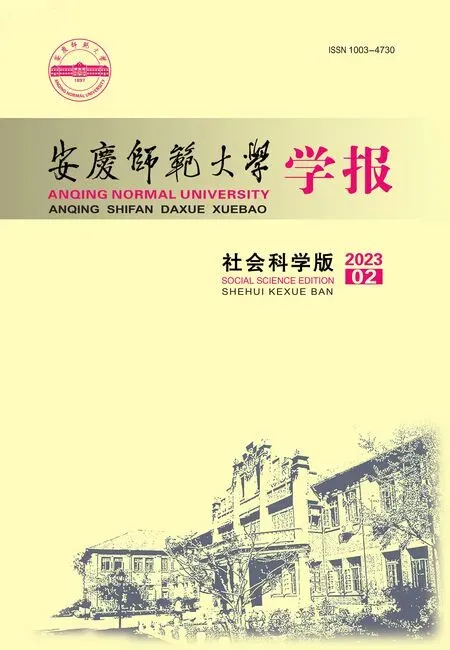杂糅与共生:皖南圩区“马灯”人物考论
2023-02-07崔龙健
崔龙健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根据民间传说,皖南圩区“马灯”兴盛于清末,一直延续至今。但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的记载,长期无人关注。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始于世纪之交,学者们分别从民俗学、音乐学、体育社会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学科视角展开考察,出现多学科研究趋势。既有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详尽考察了该民俗事象的仪式环节、表演程序[1]和音乐特征[2],以及村落语境中的民俗体育文化功能[3],还进一步讨论了在创意经济时代的保护和开发问题[4],但尚未就其人物做专门研究。在皖南圩区“马灯”人物方面,目前主要存在两个认识上的不足:一是民间口耳相传、地方志文献和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对少数人物的记载不明确,或有讹误;二是没有弄清人物杂糅共生的机制和原理,进而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呈现这一地方特色民俗事象。因此,本文拟在考证人物的同时,进一步揭示这支“神角”队伍之所以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以释疑解惑,加深对皖南圩区“马灯”的了解和认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该地方特色民俗文化。
一、相关人物考证
皖南圩区“马灯”人物中,有四名“神角”身份存疑,或名字有误。按照地方通常排位,前三位人物在地方志中被记载为“太宝、陈军师、李进皇”[5]690,其中“陈军师”常被学者们根据方言音译作“陈进士”[2]或“陈经师(玉皇大帝的传令官)”[1];“李进皇”则被音译作“李靖王”[1]或“李敬王”[6]。还有在民间被误作“郭艾”者。目前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大抵以讹传讹,都不正确。
“太宝”者应为“太保”。通常为“马灯”中的第一位“神角”,有“头马”之称,在队伍行进和场地表演时,走在“马灯师傅”之后,在民间流传中一直无实名,以致其身份存疑。从概念的视角看,太保为古代官职名,周以降与太师、太傅同位“三公”,至宋元时期词义泛化,“借以称各色人物”[7]94,如庙祝、巫师、仆役和绿林好汉等,故而代指具体人物不详。又从服装来看,“太保”所穿为经过改良的“马灯”专用戏曲服装,常见的有两种:一种为彩绣龙箭衣,加靠领,头戴红底金边文生巾;另一种为黄团龙蟒,加靠领,头戴黄色大板巾。经对照戏曲行头,此二种服装搭配都不合常规。正常情况下,彩绣龙箭衣加靠领“用于身份高贵的王侯、武将”[8]168,戴文生巾者则为“儒雅的公子、相公和清秀、潇洒的秀才、书生”[9]111;又,黄团龙蟒“专为帝王使用”[8]22,象征尊贵和皇权,通常为文老生行头,应头戴皇帽,但此处头戴大板巾“为随侍元帅、按院的校尉、中军和士兵(龙套)专用”[9]113,且“凡穿蟒的人物,加用靠领(三尖领),即表示此人是武将”[8]24。这样看来,“太保”所穿服装有自相矛盾之处:其一,既为武将,何故头戴文生巾?其二,既为帝王,怎能头戴龙套专用大板巾?两相结合,既为武将扮相,为何又是帝王形象?然核对戏曲人物图谱,鲜见这般行头装扮,实难断定“太保”身份。
关键性线索在“二马”身上。即被误作“陈军师”“陈进士”“陈经师”者,所穿服装为绿蟒戏服,头戴方翅纱帽,挂黪三髯,看上去像是绿色文官扮相,实为袍带老生扮相,在以扎靠武生、老生、武净和刀马旦为主的皖南圩区“马灯”中较为显眼。幸运的是,这一人物穿戴扮相有据可循,与《清昇平署戏曲人物扮相谱》中记载的京剧《沙陀国》中程敬思的扮相基本一致。但程敬思何许人也?其为唐僖宗时吏部尚书,出自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虚构人物,原型为代北起军使陈景思。至于陈景思其人其事,在正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黄巢已陷京师,中和元年(881年),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发沙陀先所降者,与吐浑、安庆等万人赴京师。行至绛州,沙陀军乱,大掠而还。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将,乃以诏书招克用于达靼。承制以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10]卷四《唐本纪》。
该史实记载又牵出另一位人物,即李克用。其为唐末西突厥沙陀部人,本姓朱邪,其父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而被赐姓李氏,后反唐兵败逃入鞑靼。黄巢攻入长安之后,陈景思以诏书召其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率沙陀兵镇压黄巢。因破巢之功被唐僖宗封为陇西郡王。乾宁二年(895),唐昭宗又拜其“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10]卷四《唐本纪》,故后世以“李晋王”称之。这一人物身份与方言称呼、行头扮相完全相符,可以确定“二马”程敬思之后为晋王李克用,而非“李进皇”“李靖王”“李敬王”。
再联系前后人物关系,基本可以确定“太保”者为晋王李克用麾下“十三太保”之首的大太保李嗣源。根据《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七回讲述,程敬思奉诏北上搬救兵,出大潼城至野狐岭,遭遇山贼劫掠,只剩一人一马,正当寻思自缢时,幸而遇见大太保李嗣源,不仅帮助其夺回被劫财物,还得以引见李克用[11]16-19。何也?据正史记载,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沙陀人,十三岁时丧父,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十七岁时因舍命保护李克用脱险而深受其信 任,“掌 亲 骑”[12]卷三十五《唐书·明宗纪》。天 祐 十 四 年(917),因击败契丹军有功,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检校太保[12]卷三十五《唐书·明宗纪》。同光四年(926),即皇帝位,更名李亶,为后唐明宗[10]卷四《唐本纪》。从沙陀王义子到检校太保,再到后唐第二位皇帝,李嗣源的多重身份正好解释了“太保”马灯服装混搭的合理性。
另有民间误作“郭艾”者实为郭暧。之所以如此确定,因其与金枝前后脚出场,属于皖南圩区“马灯”中常见的“夫妻档”。据记载,郭暧为唐代宗时汾阳王郭子仪幼子,娶妻升平公主[13]卷八十三《列传·诸公主》,即为皖南圩区“马灯”中金枝人物原型,出自传统戏剧剧目《打金枝》(又名《满床笏》)。剧中故事则源于唐代赵璘所撰文言笔记小说集《因话录》: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帷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14]卷一《宫部》。
这一情节经戏曲改编,长演不衰,为考证皖南圩区“马灯”人物提供了确证。
二、“神角”队伍结构
三国、隋唐、两宋时期的传奇英雄人物,构成皖南圩区“马灯”人物主体。在人物选取和排序上,受到传统习惯、师承渊源和人口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存在一些差异。“神角”数量也不一致,一般视本村青少年男子人数多少而定,以单数为主,有17匹马、19匹马、21匹马和23匹马之分。但《芜湖县志》记载多达37位人物,其中有33位为“神角”,从前往后依次为太保、程敬思、李晋王、杨宗保、穆桂英、杨六郎、杨令婆、韩信、萧何、杨再兴、岳飞、薛应龙、薛丁山、樊梨花、程咬金、徐茂公、罗成、秦叔宝、李元霸、裴元庆、周瑜、鲁肃、姜维、孔明、貂蝉、吕布、黄忠、马超、赵云、张飞、刘备、关羽[5]690。地方志中未记载的有韩世忠、梁红玉、薛仁贵、郭暧、金枝和夏侯渊等。此外,在太保之前有招财、进宝两童子和“八家云”;刘备和关羽之间有甘糜二夫人、车夫(丑角)甲乙和马童,但这些人物不在“神角”之列。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神角”队伍有明显拼凑的痕迹,但实际上有其内在逻辑性。
(一)开头:太保执令旗
“头马”为太保李嗣源,手执方形红底白边黑字令旗,带有传令兵的角色功能定位,故又被称作“报马”。至于李嗣源执令旗的缘故,还要从京剧传统剧目《沙陀国》讲起。《沙陀国》,一名《雅观楼》《解宝收威》,经谭鑫培改编为《珠帘寨》,取材于孤本元明杂剧《紫泥宣》和《残唐五代史演义》第七回至第九回。剧中,程敬思前往李克用处搬救兵,但李克用心存曾遭谪贬之怨恨,迟迟不肯发兵。李嗣源从旁相助程敬思,一同请求李克用出兵,险些被李克用处斩。遭此一遭,李嗣源便至后堂曹月娥、刘银屏二妃处喊冤叫屈,戏文曰:
母后有所不知,今有长安程敬思恩公前来颁兵求救,爹爹不发人马到还罢了,反将孩儿推出去斩,多亏程恩公讲情才得活命,特到后堂请二位母后前去讲个人情[15]92-93。
曹、刘二妃念及程敬思当年搭救之恩,前往堂前劝解李克用无效。只得怀抱令旗合令箭,传令亲自挂帅,并将令旗交予大太保李嗣源,命李克用为前站先行,至辕门听点发兵。如此一来,皖南圩区“马灯”由李嗣源执令旗做开头,便有了传令发兵之寓意。
(二)中间:两宋、隋唐、三国群英会
“神角”队伍主体大致包括北宋杨家将人物、南宋岳家将人物、唐代薛家将人物、隋唐传奇人物和三国英雄人物。其间排序基本遵循由近及远的规律,兼以父为子先、夫为妻先的原则,反之亦可,但须全部排序风格保持一致,同时期的则以民间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参照,从弱到强进行排位。
北宋杨家将人物,在“马灯”中出现的,通常有两种人物组合。第一种为顺序人物组合,杨六郎在前,杨宗保和穆桂英在后;第二种为倒序人物组合,杨宗保和穆桂英在前,杨六郎继之,杨令婆在后。无论怎么排序,杨宗保和穆桂英的顺序基本不变。这四名英雄人物皆出自杨家将精忠报国的系列传奇故事,以杨业、杨延昭父子为代表的杨氏家族抗辽保宋戍边事迹为原型,北宋时已开始流传,南宋时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说书问世,元时有《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等杂剧演出,明时出现纪振伦(号秦淮墨客)校阅的《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简称《杨家府演义》)、熊大木编著的《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等小说出版,此后关于杨家将的戏曲流行起来,并且从村野走入宫廷,有240 出的清代宫廷连台本戏《昭代箫韶》应运而生,“清末京剧成熟之后,杨家将戏更成为舞台上盛演不衰的剧目”[16]80。根据这些演义、话本和戏曲可知,杨令婆即佘太君,名佘赛花,原型为杨业之妻折氏,为杨门女将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有百岁高龄率杨门十二寡妇出征杀敌之壮举。其子杨六郎,即杨景,原型为杨延昭,智勇双全,在杨家将“七子去,六子回”的金沙滩血战中独自杀出重围,后有巧摆牤牛阵等传说故事。杨延昭娶妻后,周世宗柴荣之女,生子杨宗保。杨宗保少时随父征辽受伤落马,为穆桂英所救,后前往穆柯寨借用降龙木,与穆桂英定下婚约,得穆桂英相助,大破辽人天门阵。杨宗保和穆桂英为虚构人物,但学界亦有诸多考证,有人认为原型为杨文广和其妻慕容氏。穆桂英作为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巾帼英雄,有辕门救夫、战洪州、中年挂帅等传奇故事,在戏曲舞台上为观众所津津乐道。
关于杨家将的两种人物组合实际上皆为双数,故第一种人物组合中还有一个人物,便是杨再兴。杨再兴在“马灯”中的位置,一在杨六郎之前,这可能是一种讹误,按照排序原则,此位置应为杨业,但“马灯”中鲜有杨业人物出现;一在杨令婆之后,岳飞之前,处于过渡位置,既为杨家将,又为岳家将。何故?据《宋史·列传》记载,杨再兴原为游寇曹成部下,后降于岳飞,跟随岳飞抗金,在郾城之战中“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17]卷三百六十八《列传·杨再兴》,而后在小商桥遭遇金兵,因寡不敌众而战死。可见杨再兴确有其人,不过《宋史》并未记载其家世,以致争议颇多。但在清代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说岳全传》中,杨再兴被虚构为杨六郎后人,第四十八回有云:“我乃杨景是也。因我玄孙再兴在此落草,特来奉托元帅,恳乞收在部下立功,得以扬名显亲,不胜感激!”[18]304是故,杨再兴被赋予了杨家将和岳家将的双重身份,这在“马灯”中得到充分体现。
南宋岳家将传奇人物,除了杨再兴,在“马灯”中出现的还有岳飞、韩世忠和梁红玉。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战功累累,后为主和派秦桧构陷“谋反”而冤死。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身上刺有“尽忠报国”四字,其心日月天地可鉴,故其死令人唏嘘不已。秦桧死后,岳飞冤案得以昭雪,“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17]卷三百六十五《列传·岳飞》。韩世忠和岳飞同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忠勇有加,名震敌国,娶妻梁氏,明清戏曲小说中唤作红玉。梁氏随夫从军,立下赫赫殊勋,在建炎四年(1130)黄天荡之战中,亲执桴鼓助战,和韩世忠一同抗金,江防被金军突破后,上书请治丈夫韩世忠失机纵敌之罪,从此名震天下。《说岳全传》第四十四回“梁夫人击鼓战金山金兀术败走黄天荡”重新演绎了这一历史情节。
继之为唐代薛家将传奇英雄人物,分别为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薛应龙。长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着薛家将传奇故事,以薛仁贵及其子孙后代戍边保疆的事迹为创作原型,至清代形成故事系统,莲居士编撰的《薛家将》和《杨家将》《呼家将》构成我国通俗小说史上著名的“三大家将小说”。薛仁贵其人在新旧唐史中均有传记,东征西讨,战功赫赫,留有“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典故。薛仁贵长子薛讷镇守边疆,屡立战功,但在薛家将系列故事中,以薛讷为历史原型虚构出薛丁山。薛丁山随父平定西凉途中,与西凉寒江关总兵樊洪之女樊梨花结为夫妻,其间爱恨纠葛引出的“三休三请樊梨花”故事,最为脍炙人口。樊梨花人物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其人聪慧勇敢,且忠于爱情,挂帅封侯的巾帼英雄形象于是深入人心,名流千古。樊梨花曾收义子薛应龙,大破西凉大将杨藩的白虎阵时,封薛应龙为四路接应使,协助攻打白虎关,平定叛乱。后来樊梨花带兵攻打玉龙关,番将苏宝同布下金光阵,薛应龙私自打阵丧命,“阴魂不散,飘飘荡荡,到凤凰山与神女成亲,复归神位”[19]258。
其后为程咬金、徐茂公、罗成、秦叔宝、李元霸、裴元庆等隋唐传奇英雄人物,以瓦岗英雄为主。这些人物或有历史原型,或为传奇小说虚构,形象丰富饱满,在民间流传甚久。明清时期,有关系列小说在正史、野史、话本和民间传说等素材基础上加工而成,以清代鸳湖渔叟校订的《说唐演义全传》为集大成者,深受读者喜爱。
排在最后的三国英雄人物,以蜀汉英雄人物为主,主要有周瑜、鲁肃、姜维、孔明、吕布、貂蝉、黄忠、马超、赵云等。从排面上看,吕布、貂蝉之前为谋士,之后为“五虎上将”。其中,周瑜和鲁肃为孙吴谋士,曾力排众议,推动孙刘结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奠定三国鼎立格局。吕布和貂蝉的故事,以及蜀汉英雄人物的故事,人所皆知,不再赘述。三国乱世中,英雄辈出,他们的事迹很早就成为艺术表现的题材,直至元末明初由罗贯中博采众长,创作出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该小说以蜀汉刘备集团为创作中心,与“马灯”人物取向是一致的。
(三)结尾:“刘关张”三结义
“神角”队伍通常以张飞、刘备和关羽为结尾。刘备作为蜀汉先主,居中主位,张飞和关羽一前一后,或分居两侧,但关羽作为主神殿后。不管如何取舍人物,如何变动顺序,此三位“神角”必不被舍弃,而且关羽作为主神殿后的位次始终不变。
皖南圩区“马灯”如此尊崇这三位“神角”,与他们的忠孝节义有很大关系。据《三国志》记载,“先主(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20]卷三十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由此可见三人关系非同一般。此后民间附会衍生出桃园结义的故事,《三国演义》便将此故事作为开端,就结义经过做了具体描绘,并增添结义誓词曰: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21]3!
经过小说的艺术渲染,“结义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义’”[22]291,在现实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统治者借此来巩固江山,下层民众效仿来团结力量”[23]。
三、内在文化逻辑
皖南圩区“马灯”以太保执令旗,点兵召将,共同维护以刘备为代表的仁义君主。这样便非常巧妙地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故事系统的古代传奇英雄人物,捏合成了一支合情合理的、有血有肉的、忠君爱国的“神角”队伍。但表象之下,隐藏着该种民俗事象的精神内核和皖南圩区民众的价值取向。
(一)英雄崇拜
从精神内核上理解,“马灯”首先体现出圩区民众集体的英雄崇拜情结。目前已知的二三十位“神角”人物,涵括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受人喜爱的蜀汉、隋唐传奇英雄人物和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三大家将英雄人物。这些传奇英雄人物及其故事,至今为圩区民众所津津乐道,尤以勇敢多情的巾帼英雄穆桂英、聪明睿智的千古奇才诸葛亮和忠义勇武的完美化身关羽备受推崇。这样大规模对古代传奇英雄人物的崇拜,在传统民俗活动中较为少见,这也体现了皖南圩区“马灯”的特别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重的英雄崇拜情结,可能源于皖南圩区民众对超越凡俗的现实需求。一方面,皖南圩区多发洪涝自然灾害,生存环境并不友善,往往破圩之后尽成泽国,“埂内的屋料、杂树、棺材、人畜尸体,被大风吹飘在水面,触目皆是”[24]102,而且洪水过后满目疮痍,甚者秋收无望,饿殍遍野。另一方面,皖南圩区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经此兵燹,其地经济社会近乎崩溃,“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25]卷二十一《豁免皖省钱漕折》。加上灾难伴随着瘟疫,给皖南圩区民众的生存带来巨大挑战。面对这些苦难遭遇,在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而无法应对的时候,人们自然寄希望于超越凡俗的力量,于是产生对英雄的崇拜心理。
但这种英雄崇拜不是盲目的,它有很强的选择性和目的性。中国古代历史漫长,其间传奇人物辈出,有历史文献记载的亦不胜枚举,但皖南圩区“马灯”不过二三十个“神角”人物,数量极其有限,这就需要人们带着目的去筛选。亦如前文所述,这些被选取的皖南圩区“马灯”人物,不管是有历史原型,还是为后人虚构,都具有强烈的故事性,而且这种故事性能为民间教化提供正面素材。
当然,故事性不是“马灯”人物选取的决定性因素,它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明清演义小说和戏曲的影响尤为关键。“马灯”人物及其故事情节,很多并非出自正史记载,而是源于在宋元话本、杂剧基础上再创作的明清演义小说和戏曲,“五马破曹”“穆桂英挂帅”和“云长扫堂”等无不如此。再说程敬思这个人物,其人其事鲜为人知,在民间的影响力远不及其他“马灯”人物之所以能够入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戏曲《沙陀国》的广泛流播。其他人物也是如此。
只在个别情况下,出于英雄崇拜的实际需要,会对人物形象进行重塑。譬如吕布,在正史记载和文学创作中均非正面形象,给后人以有勇无谋和不忠不义的深刻印象,至今背负着“三姓家奴”的恶名,千百年来“将其作为一个负面形象来批判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6]。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严重背离了忠孝节义思想主题,理应无法入选成为“马灯”人物,但是话本、小说对吕布形象的描绘,丑化中又让世人看到其骁勇善战和英俊潇洒的一面,“人中吕布”形象深入人心。除此之外,皖南圩区“马灯”对吕布形象的塑造,还在于推崇他和貂蝉的伉俪情深。在三国系列故事中,貂蝉为司徒王允义女,为报答其养育之恩,遵照其连环计,周旋于董卓和吕布父子之间,成功离间吕布反目刺杀董卓,为国除害,此后嫁给吕布为妾。于是,“吕布戏貂蝉”这般英雄和美人之间戏曲性的爱情故事,一经搬上戏曲舞台,“在以金戈铁马为主的三国故事中,别具情致,每为观众所称道”[27]69,引起人们对英雄配美女式美好爱情的无限向往。正因如此,吕布和貂蝉一道入选皖南圩区“马灯”人物。
(二)多神信仰
皖南圩区“马灯”体现的第二个精神特质是多神信仰。在皖南圩区“马灯”这一个空间场域中,除了设坛供奉“马明大王”和道教诸神之外,还同时尊崇二三十位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故事系统的“神角”,两相叠加,足以说明皖南圩区民众并非崇信单一神灵,而是秉持对多神的信仰。
皖南圩区民众的多神信仰,从地方志等资料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皖南圩区既是移民社会,更是圩田水利社会,除了建有各地普遍存在的城隍庙、岳王庙、包公庙、文昌宫等,供奉城隍、岳飞、包拯、张亚子等神灵外,还建有八腊庙、将军庙等祭祀驱蝗神刘猛,建有祀山殿、祠山庙等祭祀司山神张渤,建有三神庙、杨泗庙、龙王庙、水府庙、晏公庙等祭祀各路水神。另外修建祠堂等祭祀治圩有功的官绅,如当涂知县朱汝鳌和云骑尉周溶、南陵知县钟瀛和沈尧、太平府知府陈云等,“这些祭祀之神都是圩民心目中保佑圩区风调雨顺,为农业、渔业兴旺发达而消灾消难的庇护之神,深得圩民信奉”[28]259。
多神信仰的形成,源于风俗文化的继承和积累。皖南圩区开发的历史悠久,“今青弋江、水阳江下游一带的当涂大公圩、宣城金宝圩、芜湖万春圩等圩的前身均始筑于三国时期”[29]412,至皖南圩区“马灯”兴盛的清末时期,已经历1 600 多年。期间虽然遭受多次自然灾害和战争的侵袭,但其风俗和文明整体得到延续,并且随着几次移民高潮的产生,不断融合外来文化,使本身趋于多元。长期的继承、积累和发展,才得以形成多神信仰的局面。
这种多神信仰现象在皖南圩区的存在,得益于民众的情感认同。多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基因,普遍存在于地方风俗文化之中,这对于皖南圩区作为移民社会来说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少了排斥和斗争。不仅如此,“圩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同时也达到和睦乡邻的作用”[28]259,也会促使相互理解和包容,甚而接受对其他神灵的信仰。如清光绪年间,福建旅芜商人在陶塘西岸捐资建造天后宫,祭祀海神妈祖,将东南沿海一带的信奉移至内陆,未曾遭到故意排斥和恶意损毁,“又保丰圩南坝有天后宫,光绪十年重修”[30]卷四十《庙祀志·庙坛》。
信仰多神,虽各有缘由,但也极易造成信仰混乱,为求共存必然要找出同一性。从表面上看,皖南圩区“马灯”人物均为古代传奇英雄人物的代表,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从更深层次来看,“马灯”人物及其故事背后,隐藏着忠孝节义思想,为封建时代维持圩区社会秩序所必需。所以,这些“神角”人物看似不相关联,但也存在共通之处,这便是他们得以在同一个空间场域共存的基本前提条件。
(三)主神意识
皖南圩区“马灯”有两个主神系统:第一个是象征“马灯”外在的主神系统,以“马明大王”为主神,这是“马灯”区别于其他灯种的一个显著标志,但它的功能也仅限于此;第二个是显示“马灯”内在的主神系统,通过融合鬼神观念、道教思想、文学故事、戏曲元素和民间信仰等,另外创造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神灵体系,并以关羽为主神。这两个主神,前者被供奉在灯堂,只有一个牌位,完全是静态的,鲜为人知;而后者作为“神角”行动,有活生生的载体,是动态的,更为人所关注。问题在于,将“马明大王”作为主神祭祀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将关羽作为“神角”人物的主神信仰是何原因呢?
首先,关羽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极高。一般认为,关公信仰源起于南北朝时期,其时仍以人的形象存在,隋唐时期由人入神,进入武庙配享,但地位无足轻重,宋元时期在民间形象重塑的影响下,从宋徽宗开始封王加爵,由神侯到神王,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明时进爵为神帝,位及人神之首,与孔子同尊,清时进一步抬高,“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31]615。皖南圩区各地也都建有关帝庙,地方志均有记载。关公信仰在民间可谓盛极一时,从南到北,“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32]卷三十五《关壮缪》。
其次,关羽集多种信仰和崇拜于一身。为了扩大影响力,儒佛道三家兼容吸收关公信仰,将关羽纳入各自的神灵体系予以加封,儒家尊其为关圣、关夫子,佛家封其为护法伽蓝神,道家奉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故有楹联曰:“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33]13这就能够解释为何皖南圩区民众既称关羽为“关公”,又称其为“大菩萨”。有清以降,关公信仰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其职能趋于泛化,尤以农民奉为“御患灭灾、保佑风调雨顺的神灵”[34]3,这是皖南圩区“马灯”中其他人神无可比拟的。
最后,关羽是“忠义”的楷模和化身。“忠义”二字是关公信仰的核心,最为人所称道,关羽也因此成为全民信仰的万能之神,“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酆,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过夺命黑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35]273。又因为“关公的神性、神格以及行为、功用与封建的伦理道德相一致”[36]63,被宋徽宗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神明。千百年来,能享此恩宠和殊荣的人神,可谓凤毛麟角。
四、结 语
皖南圩区“马灯”拥有一支由二三十位中国古代传奇英雄人物组成的“神角”队伍。这些人物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残唐五代史演义》《薛家将》《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有的有历史原型和正史记录,有的是文学创作虚构,横跨三国、隋唐、两宋千年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故事系统,体现了皖南圩区“马灯”人物杂糅的一面。
但是,皖南圩区“马灯”打造了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空间场域。通过挖掘人物故事性,结合鬼神观念和戏曲元素,以太保执令旗作开头,以“刘关张”三结义作结尾,中间以故事系统和时间先后为序,汇集三国、隋唐和两宋群英。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支由太保领衔,不同时期的传奇英雄人物共存,以维护刘备为代表的仁义君主这样的“神角”队伍。在突显忠孝节义的价值取向中,出自不同故事系统的传奇英雄人物成为一个共同体,得以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