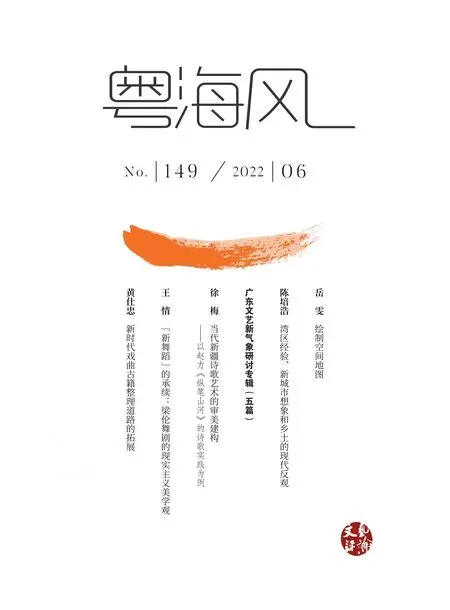新时代戏曲古籍整理道路的拓展
2023-01-21黄仕忠
文/黄仕忠
在20世纪初通过王国维、吴梅等人的努力,戏曲才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后逐渐进入到学术行列。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做法,则经历了不断尝试与修正。
清末民初,吴梅等人帮助刘世珩编校《暖红室汇刻传剧》(共出30余种),开始系统整理戏曲,精校精刻。但当时的做法,主要采用“择善而从”,没有校记,所以改变了原貌。在整理者看来,戏曲本身水准不高,以他们的学养帮助“完善”,已经是一种积极的提升。其后董康覆刻《盛明杂剧》《杂剧三编》,校勘和雕刻极其精美,时称“新善本”,也间有以意改订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吴梅编《奢摩他室丛刊》,整理朱有燉杂剧,始用铅字排印,更是做了较多“修订润色”、代为“完善体例”。
与此同时,影印方式也开始使用。如董康影印了日本藏本《苏门啸》《杂剧十段锦》和“元本”《琵琶记》(珂罗版)等,郑振铎影印了长乐郑氏的传奇丛刊。但董康影印本《琵琶记》另加了凌氏刻本的插图而不加说明,导致读者产生误解。这些处理,都是当时常见的现象。
1938年,因日军侵占江南,脉望馆旧藏“古今杂剧”散出,经过郑振铎的努力,书为民国政府购得。学界亟望得见,最好的方式是影印。但战时条件不具备,所以张元济选择其中的孤本,请王季烈主持整理,于1941年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收录剧本140余种,代表了当时杂剧整理的最高水准。但现在看来,也仍然改动较多;同时在赵琦美批校与原抄本之间作取舍时,有时首鼠两端。
吴梅、王季烈等名家整理本,一是有意将剧本所用俗字规范化,符合文人著述的标准,二是当时对戏曲俗语词研究滞后,尚未有高水平的工具可用,误解、误改的现象较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戏曲古籍的整理出版,也依然遵此二途。其间也有经验教训。郑振铎先生主持《古本戏曲丛刊》,计划编成十集,他生前只编成了出版了四集。在具体出版时,因受当时政治观念影响,所选版本涉及某些民国人物时,版面多有处理,例如清除印章,却去其题识等(如北大藏明刊《惊鸿记》原有叶德辉1250字长跋,被弃去,致作者问题的重要讨论一度被湮没)。在影印中,存原貌与便于读者阅读之间,更重后者,所以多有修板现象(其他古籍影印也是同样处理的)。后来人们用别本去比较影印本时,因发现有差异,便误以为是不同版本。
此外,如20世纪50年代一度反对“烦琐考证”,故当时整理的戏曲剧本和曲集、选集,大都没有列校记。
改革开放后,戏曲古籍的影印与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喜人。
一是影印方面,百花盛开。《古本戏曲丛刊》十集终于全部完成出版,另有许多套大型的戏曲影印丛书,以藏者、收藏单位、以国别为类,文献来源遍及海内外。以往的修板现象逐渐被抛弃,而美中不足的是,有很多大套影印丛书,对所收文献版本、庋藏源流不作介绍说明,读者利用不便。
二是大套曲集和许多戏曲家的曲集得到整理出版。例如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汇集了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大大推进了宋元的阅读利用。
但已经出版的戏曲古籍,由于整理者缺乏古籍标点整理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
首先表现不明版本。例如不知道原刊本、改题修板印本、过录本、覆刻本、微卷、影印本之间的区别,只是想要尽可能“多收版本”,以为多引版本便是认真负责,所以既有将微卷、覆刻本当作独立版本用作校本的,也有将改题印本作为新版本与原本并列的。还有因过录本清晰,遂认定比原刻本更优。
其次,不明“原本”与用来标点的“工作底本”的关系与区别。拿到一个复制本便开始标点。但有很多影印本因图片印刷模糊,再复制、复印后不够清晰,难以辨识,便称“底本漫漶”,直接加上“□□”。其实遇到这种情形,必须查原藏单位的藏本,这是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有些整理者不知道这是必须的,有的是知道,怕麻烦而不做,导致谬种流传。
再次,机械理解“不改底本”,保持原貌。结果一方面把原本某些特别异写字保留,而另一方面又让台湾版繁体字库自动改变了古籍中的原字。古籍整理的“必须改”“可改”与“不可改”的界线,其实是需要有较多的古籍整理实践才能掌握的。
至于句断错误、误读古字、不明俗写异体字等,则尚是较深一层的内容,此不赘言。对于新时代的古籍整理及传承,我以为需要通过以上的回顾、反思,来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规划。
第一,将影印本、扫描本和整理本的作用与功能区分开来。
影印,就是要保持原书的原面貌。我在日本复制古籍,收藏单位复制时把封面、空白页全部都复制。而我们在影印出版时,通常是直接从正文开始的。事实上有许多信息是在书前书后不起眼的地方的。
如果影印还有其限制,则彩色扫描本,应当要有这个“求全”的意识。学者都很感激中国国家图书馆把数万册古籍放到了网络上,开放下载,大大方便了利用,也大大便利了研究,我本人也是受益者。但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也是国家的脸面,应当做得更好。现在海外都放的是高清的彩色图片,国图放的是黑白还原的图片(现在开始有少量彩色版了),最难堪的是中间加一个“图”字的水印,生生地给“剠了面”,实在有损于国家的脸面,也与我们一直强调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相背离。
绝对“保真”的功能交给影印本、扫描本,它们主要存原貌,并满足专家从事版本研究、必须利用原本才能展开研究的需要。此点确立之后,我们对“整理本”的要求,也应当有所调整。整理校点本,放弃担当“保真”功能,而真正做好面向更广泛读者的作用。一是便于阅读,可省读者心力,二是便于检索利用。需要做好的是标点整理本身的事情,而不必纠缠于“存真”。任何出版都会改变原貌,不可以通过整理本去完全了解古人的面貌。放下这个担子,可以集中精力把该做的做得更好。
第二,我们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古籍整理理论与规范。
以戏曲和俗文学而言,我们有意建立一门“俗文学校勘学”。它与以经学为主要对象的“经典校勘学”有重叠,但又有明显区别。因为俗文学的主体是快餐消费型的,并不为“传世”而设,从写作到出版都与经籍著作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对象的特性来设计一整套的操作模式。
同样,古代四部文献,其实因为对象不同,也应有相应的整理校勘规则。我们才能在乾、嘉学者建立的经典校勘学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第三,认真研究,古籍整理究竟能够做成什么,实际上不能承担什么。
此话看来有些虚,其实有现实针对性。因为现在古籍整理的水平参差不齐,错误不免,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影印本就好了,也避免错误。其实,既然真正的专家精心整理也不免偶存错误,那么没有经过整理,一般学者根本读不下来,即使能读,速度极慢,难以找到文脉。更重要的是,这整理本不仅本专业专家可读,其他领域的读者也能阅读利用,大大拓展了传承接受的可能性。
再如我们编《全明戏曲》,在开题时,有专家提出希望尽可能地“全”,例如把明人的评点也应全部收录。记得中华书局的顾青总编说了一句:“总集只能承担总集的功能,一部总集不可能承担所有的功能。”于是遂定。因为如果评语都收,但有评语的却是书坊修订本,与作者原貌相差很大,无法让评语对应文字。所以这里也引申出一个话语:《全唐诗》的意义主要在“全”,在于收录了所有诗人的诗,但名家的研究,则不应当据《全唐诗》,而应当利用历代笺注者所做的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