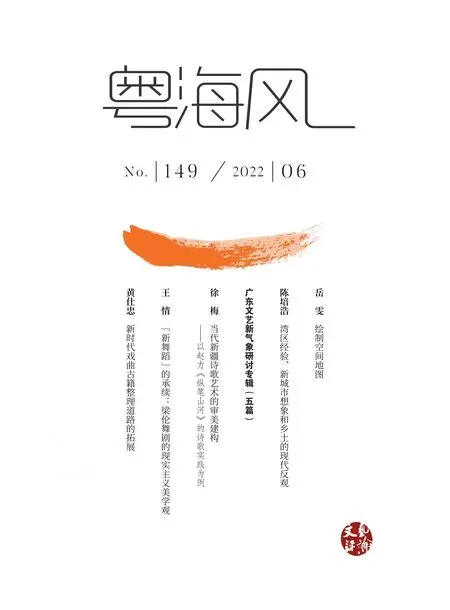食在人间便知味
——论《燕食记》中的“常”“变”逻辑
2023-01-21张云鹤
文/张云鹤
葛亮近年出版的《瓦猫》可以视为他“匠传”系列小说的开端,在长篇新作《燕食记》中,更是直接投笔于匠人匠心及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从小处、细处的“食”切入,以一间岭南百年老字号茶楼——“同钦楼”的变迁展开三代粤点师傅手艺相传的故事。从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从家族兴衰到江湖过往,从钟鸣鼎食到小摊小店,统统都融进一个“食”字。
整个故事以粤港茶楼文化研究者、采访者的“我”为主要视角,从“同钦楼”现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闭店传闻讲起。“同钦楼”的行政总厨“莲蓉王”荣贻生,20世纪20年代出生于广州“七大名庵”之一的“般若庵”,在广府大户“太史第”度过童年,后随母逃至湛江避祸,无意间拜师原“得月阁”莲蓉大师叶凤池,后由广州辗转至香港,因打得一手好莲蓉撑起了业界龙头“同钦”的名誉。其徒弟陈五举,本是荣师傅认定的唯一传人,却因个人情感“背叛”师门,入赘到由沪来港的戴家,继承了上海本帮菜的餐馆生意。师徒二人在时代和命运的裹挟下各自历经曲折,终于在一场饮食大赛中相见并和解。整部小说以食物为底,调动起感官的参与,人物和故事在弥漫的烟火气中徐徐展开,多个人物、多条线索相互交织,结构保持了一贯的精致典雅,语言轻疏温婉又细腻绵密,叙事从容克制但该泼墨时又洋洋洒洒,戏曲、园林、瓷艺、茶艺、市井风情等都跃然纸上。可见,葛亮早已将田野与案头功夫揉进饮食文化的各色风味中。
“匠传”不仅成为作家葛亮身上的一记标签,这一题材也成为一种新路径,使作家和读者共同切近传统文化更为厚重的本原。从《朱雀》到《燕食记》,葛亮始终在作品中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且“把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1]。这种文化精神在《燕食记》中装进“食”这件巨大的容器中,饮食成为一种文化密码,蕴含着日常且深刻的“常与变”的辩证逻辑。
一、以“常”为本
“食”为民之本,是于人而言首要的“常”。何为“常”?《荀子·天论》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这即是说,自然界按照固有秩序运行、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德经》第十六章也指出:“复命曰‘常’,知常曰‘明’。”[3]即回到本原是万物运行的永恒规律。“常”可以说是“本”的某种外化和表征,呈现为一种常规的、固有的、本真的秩序或状态。民以食为本,充饥止渴来维持生命运作,研究吃食以满足“饥饿的舌头”,是作为人日常且固有的本能。
“燕食”出自《周礼·天官·膳夫》,意指人的一日三餐;《礼记·礼运第九》又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4],即原始的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食”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本原。《燕食记》表明,即便是战事频仍、节衣缩食的年代,人们过节依然要备全粽子、猪肉、鸡蛋、水果,“在这溽热的南国,市井苍凉,节日倒还如她的根系。根深而蒂固,皆自民间”[5]。同时,人也有着味觉上的欲望和本能,会被美味所打动,会对某种味道产生独特的感知和记忆,普通人如是,好厨师的味蕾更是如此。《燕食记》中的主人公荣贻生之所以走上打月饼这条路,说来便要归功于童年时在太史第吃到的“得月阁”双蓉月饼。少年阿响(荣贻生小名)一口咬下去便感到浑身一阵战栗,两眼放光,脸上露出由衷的微笑,这味道“够记一辈子”。即便这双蓉月饼绝迹多年,阿响一尝便知是“得月”的月饼。等荣师傅自己成为“莲蓉大师”,每年熬出莲蓉后第一口必须亲自品尝,“与其说是信任自己,不如说是信任已经因年老正在退化中的味觉”[6]。
此外,饮食中蕴含着另一种“常”,即做菜如做人,都有所谓的规矩和“分寸”。首先,各个菜系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谨严的法度。荣师傅教徒弟制饼时,告诉徒弟“饼皮八钱,馅料四两二,皮薄馅靓。多了少了都不对,老祖宗的规矩”[7]。陈五举一向温厚寡言,而面对徒弟露露在本帮菜的鱼汤里加椰奶,一下便动气正色道:“一菜一系,根基是不能动的。有些能改,有些不能改。像你这样,一个菜就伤筋动骨了。”[8]而在那做菜的“三分做,七分蒸”中,“到头来,还得看自己的那‘三分做’,这才是做人的基底”[9]。对于做人而言,有规矩为“常”,合规矩为“本”,做人的规矩更是《燕食记》的主要体现之一。慧姑深谙“不可逾矩之道”,向来谨小慎微,无论是在般若庵还是太史第,从不多言,不越界,才得以在变动的时代保全自己和阿响。而在母亲的教诲下,阿响自年幼时便懂得做人的道理,在太史第后厨帮忙时,即使是难得美味的一碗蛇羹摆在面前也绝不“偷食”。
师父们挑选徒弟,看的便是这种“分寸”,既有做菜的“慧根”,还有细节中透出的心性和德性。荣师傅暗中选中的徒弟陈五举,随师学艺时绝不“偷师”,谨从师父的言传身教,因为在陈五举看来,偷来的用起来也不安心。随后因个人情感离开师门,陈五举更是立誓“师父传给我的东西,我这后半世,一分也不会用”[10]。他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诱惑之下显露过身手。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说:“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11]从叶凤池到荣贻生再到陈五举,师父们传授的不仅是手艺,也是沉稳而正派的心志。炒莲蓉跟做人一样,在于一个“熬”字,必须慢慢炒,心急浮躁炒不好;炒的时候要缓缓地唱“莲蓉歌”,学会了往后还要唱给自己的徒弟听。《燕食记》中,从母到子、从师到徒,心性和德性都在代代相传,无论时移世易,他们都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基底,保有自己特有的“倔强”,由此才立起了自己的整个人生,也撑起了手下的事业,这也便是钱穆所说的“性道合一”。
《燕食记》中还有一种“常”——人的本真性情感,通过饮食这一介质得以呈现。首先,师徒之间因“打莲蓉”而产生联系,即便陈五举离开师门入赘到戴家,数十年来,每逢年节都会去看望师父,师父不见,就在门口等上一两个小时才离开;到了饮食大赛的决赛场,师徒终于重逢,而在最后的炒莲蓉环节,荣师傅有意认输是为成全,陈五举却早已将比赛输赢置之身后,一心只挂念师父的手伤,不顾其躲闪上前轻轻按摩师父的肘腕,然后重新替师父炒起莲蓉。如果说师徒情因“背叛”而伤痛拉扯,《燕食记》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则不掺任何争吵、误会,透明而纯朴,“以淡笔写深情”(王德威语)。月傅和慧姑,两个般若庵里年龄相仿的女孩自小相互依靠。慧姑为了月傅在庵内稳居地位,为其操持素筵打出名声;危险来临时,月傅以身抵抗,将婴儿以及自己的全部家当托付给慧姑,阿响便由慧姑一手抚养成人。阿响儿时在太史第与七少爷要好,即便后来七少爷精神疯癫,阿响始终都极尽所能地关心照应,每次去看望都要带上点心和酒菜。叶凤池通过自己手打的月饼向慧姑传达心意,并答应以戒烟瘾为条件与慧姑结婚,多年来即便因腿骨里残留的弹片疼得在床上打滚甚至晕厥,却再没碰过大烟;遭遇日机轰炸时,一起出逃的慧姑因落下了月傅留给阿响的物件和书信,在返身回家的半途被炸身亡,叶凤池撑着一口气待阿响归家交待完后事,便也随慧姑而去。
《燕食记》中,既有浓烈的烽火硝烟,也有平淡的人间烟火,而“烟火”中那朴素而又深沉的“人之常情”,始终是人类世界的永恒主题。普遍情感是人最为切身的体验,是人得以存在和自我实现的力量本源,“人作为人而言,首先是有情感的动物……对人而言,情感具有直接性、内在性和首要性,也就是最初的原始性”[12]。作为原始性本能的饮食与情感,足以与时间和空间相抵抗,不因外物而转移,根深而蒂固,见微而知著。
二、因“变”则“通”
如果说葛亮笔下的市井风情、人间烟火是一种“常”,时代洪流则毫无疑问是一种“变”。20世纪20年代以来,时代风云夹带着革命、战争、改革等洪波席卷岭南,浩浩荡荡的情势之下,迁徙失散、孤独飘零以及突如其来的变故等,对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而言已然寻常。饮食承载了岭南地区深刻、浓厚的民族记忆和家国情感,成为文化气性的一种深刻隐喻。
时代剧变之下,每个普通个体、每个小家小户都被裹挟着前进,被未知的变数所捉弄,被残酷的命运所挤压。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朝野更迭,般若庵里本与世无争、欲望淡泊的月傅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月傅以心上人陈赫明将军之名,做了一道菜起名为“待鹤鸣”。《诗经·小雅》中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13],“鹤鸣”本为清亮高亢之音,形容一片欢愉喜庆的景象,如今却成为诀别之音,使得两人永无相见之日的悲凄显得绵长。月傅和慧姑两姐妹自小亲情同手足,也因月傅与陈将军的瓜葛自此失散,“那么仓促,甚至没有一个体面的告别”[14]。少年阿响的意中人司徒云重本是广府最大瓷商“益顺隆”老板夫妇的独生女,抗战时期夫妇俩因“通共”被杀,司徒云重多年未有音信;阿响和七少爷随团劳军多年,抗战胜利后终于回到安铺小家时,阿妈早在日机轰炸中意外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岭南地区人口流动频繁,苏浙移民、华侨归国迁居香港渐成趋势。20世纪60年代,戴家偷渡到香港白手起家,为了在香港立住生意,陈五举的妻子戴凤行怀孕期间坚持掌厨,因破伤风母子身亡。后来,由于传统茶楼改造,戴家原在湾仔的铺面被买下,不得不搬去观塘开店,生意大不如前,当地的“地头蛇”还因抢生意前来寻滋闹事,大打出手。
葛亮擅于通过个人命运、日常生活来呈现历史的变迁以及时代的更迭,从《朱雀》到《燕食记》,葛亮总能抓住某个细处,将时代的风云跌宕融进一个个平凡又飘零的生命际遇。在《燕食记》中,本是世外清净之地的“般若庵”以及无欲无求的尼姑月傅,命运却与陈炯明之弟陈赫明那短暂的戎马生平产生勾连,这也是阿响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慧姑母子栖身于湛江一个叫做安铺的小镇,遇到了原得月阁莲蓉大师叶凤池。而这个叶凤池,不仅精于厨艺,更有着满腔的政治抱负:年少时入“三点会”,随领导者之一刘芝草各处结社起义,以抗清廷,起义失败后来到安铺避身,却依然和民间组织的“音线”保持联络、了解形势;正是叶凤池特殊的声望地位和细密谋划,保住了远在广州、身处危险而不自知的阿响一条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戴家“十三行”餐馆将粤派点心与上海本帮菜相互融合,并且随周围环境推出“碟头饭”、卤水、外卖等,可以看出香港本土文化的包容与混杂;戴家唯一的小儿子戴得逐渐成人,却偷拿自家餐馆的钱出入夜总会,沉迷于娱乐场的灯红酒绿,更反映出当时香港风化业的兴盛。葛亮笔下的时代和历史,不是宏大的、爆裂的、歇斯底里式的,却恰恰通过普通人于大时代之下的飘零、变故、流徙、失散,折射出战争和历史的裹挟性和残酷性。正如阿响多年后和司徒云重再次重逢,司徒云重平淡地说:“都是乱离人,谁能碰得到谁呢”[15]。
葛亮笔下的“变”当然不止于此,即便作为个体的人被抛掷于时代的洪流中,被动而无所依凭,却仍靠着一股韧劲闯出自己独有的一条路,这种创新性和变通性同样通过“食”得以丰富呈现。20世纪70年代,随着机器代替手工,西饼逐渐占领市场,同钦楼的饼品生意大不如前,荣师傅便在小厨房里琢磨出一种双馅“鸳鸯”月饼,再次创造了香港“一饼难求”的盛况。饮食大赛上,陈五举更是在各地菜系相互迁就、融合混杂的“四不像”趋势之下,反其道而行,中规中矩地立足于本帮菜传统,加入一些细微的创新和冒险,最终从比赛中脱颖而出。陈五举的师兄谢醒虽不得志,却基于当时香港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传统茶楼格局与歌舞厅相互打通,饮食、娱乐双管齐下,打造出那个时代独具风格的“中式夜总会”。《周易·系辞下传》中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6]这句话点出了宇宙亘古运行之“道”:生生不息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自然规律,有新生才能有长久,这是极为朴素却深刻之“道”。“穷”可以激发出人的意志,推动个体通过“变”从而把握住生命的自主性,化被动为主动,摆脱困局,转危为安。
陈五举面对徒弟露露偷学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并加入自己的花样,竟也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拒绝的“偷师”是否一无所长:“偷来的,一般人学到了师父表面的皮毛,只是形似,内里难得其神。而悟性高的,偷了其表,但因为无人往深里教,便多了自己许多的琢磨与想象。走得好的,倒成就了自己,独树一帜。”[17]而在饮食大赛的最终决赛中,陈五举更是大胆借鉴露露的招式,在豆腐布丁里加入椰汁,可见,陈五举对于自己的犹豫和怀疑已经有了答案。葛亮在采访中表示:“我更想表达的是,文化传统之间融合的品性。看上去是菜肴或点心的创制,背后是传统文化的特性,稳中求变不断融合的特性。”[18]葛亮将这种“变”通过饮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正表明,融合和变通并非抽象空洞的大道理,它贴近每个个体的切身生活经验,寓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
三、以“常”应“变”
说到“食”,汪曾祺曾在散文中介绍过豆腐、栗子、昆明菜、蒙古手把肉、北京豆汁儿等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食物和吃法。他提到,儿时读《板桥家书》时对于其中“炒米”的描述分外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19]这么一句话,便道出了“食”不仅是一种“常”,同时也标记着地方性之“变”。从普遍意义而言,饮食是民生的根本,而对于不同地域甚至是不同家庭而言,饮食却又有着不同的做法和讲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不足与外人道”的习俗和风气,也便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燕食记》中对于饮食文化、尤其是岭南饮食文化的介绍可谓不惜笔墨、洋洋洒洒,舌尖上的味蕾都被调动起来,就连人物和故事本身都带有了味道记忆。岭南地区的饮食除了“茶”,便离不开“一盅两件”。每逢重大节日、婚嫁喜事,更是对“唐饼”十分讲究,且无论是饼食还是糕点、小食、蜜饯都各适其适。初春时鲜美的“黄沙大蚬”是广府年节的必食之物;清明年后的“礼云子”,一种岭南田间的小螃蟹之卵,稀缺矜贵,口味鲜美;而到了秋末冬初“三蛇肥”的时节,豪门大户可以一直摆宴到农历新年,蛇羹那清凛的膏香足以捕获所有人的眼界和胃口。对于生活在珠三角地区的乡下人而言,每到潮汐来时,会捉禾虫来入食,禾虫可用于焗蛋、煲汤、制酱。上海本帮菜的精华则在于那“自来芡”:“成菜无须勾芡,全靠这道菜的主料、辅料的佐料在适当火候,几近天然地合成浓厚细腻、如胶似漆的粘稠卤汁。”[20]同时,本帮菜变化多样,博采众长,“荤可浓烈入骨,素则清浅若无,像是捉摸不透的美娇娘。”[21]一方地域的饮食风习渗入到当地人的骨子里,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当地人一眼即可区别出茶楼里潜伏的日本特务。
可见,饮食本身便蕴含着“常”与“变”的共通逻辑。《北鸢》中,“洋医生”叶师娘与文笙的母亲昭如两人在饥馑的夜晚烤栗子时,聊到很多名菜如徽州的毛豆腐、臭鳜鱼、杭州的臭苋菜、豆腐乳等都是“意外”中的造化,昭如在此一语点道:“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22]关于“吃”中蕴含的“常与变”的辩证博弈,在那时便有先声。而在《燕食记》中,这一主题植根于岭南的一对师徒,通过具有代表性和地域特色的岭南饮食文化,体现出“常”为“本”、“变”则“通”的文化逻辑,而更重要的逻辑智慧是:以“常”应“变”。这个“常”便是顺势。
其实,无论是《北鸢》中的主人公卢文笙还是《燕食记》中的荣贻生,以及与年轻时的师父相像的陈五举,这些人物都有较多共性:天性聪慧又老实本分,安静寡言又自有主意,欲望淡泊又积极有为,说到底,都是顺势而为。《北鸢》中,儿时的文笙便懂得“放风筝,其实就是顺势而为,总不能拧着它的性子”[23]。而在《燕食记》中,慧姑带阿响从广州一路流落到安铺,面对安静懂事的阿响,慧姑感怀道:“这孩子,虽是食下栏长大,却始终是见惯了太史第的锦衣玉食。如今,跟了自己的生活,还是顺顺妥妥的,像是生来如此,无一丝勉强。”[24]母亲让少年阿响“走一趟”广州打听大少奶奶的消息,阿响便去;回到安铺小家后,叶凤池让阿响带着秀明返回广州,阿响照做;在广州得月阁,韩师傅的大弟子因地位之争而发难,荣贻生不想让一直帮衬自己的韩师傅为难,便去往香港,这一去便是多年。徒弟陈五举同样如此。入赘戴家掌厨“十八行”时,外地菜系在香港逐渐兴盛并呈混合杂糅之势,一次,来客提出想吃“一道本帮做法的广东点心”,陈五举便顺势而为,无意间创制出的“水晶生煎”“黄鱼烧麦”“叉烧蟹壳黄”等点心反而成为自家招牌,在港岛独占一“味”。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了普通人的饮食结构和时间安排,陈五举也追随茶餐厅做时兴的“碟头饭”(类似盖浇饭)以顺应打工仔的下钟需求,小餐馆生意逐渐红火。葛亮笔下的这些主人公,无论被加之何种命运,都坦然接受,从无怨言,顺势而为,却恰恰得以安身立命。
因此,并非只有另辟蹊径才为“变”,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智慧。这种“顺势”并非毫无脾气和秉性,而是对于自己的本心有着清晰的判断和认知,这种生命意识使他们明确做出选择,之后甘愿承担所有后果。少年阿响认定了要打莲蓉、做月饼,面对阿妈的反对,他说:“现在阿响长大了,想的是安身立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是没有命。”[25]这句话是铿锵有力的。或许可以说,这种“顺势”是一种“无为”,“无为”不是大脑空空如也,也不涉及抽象的反思、推理,而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生命意志和直觉。这种驾轻就熟、自在自如的顺势、无为是建立在“有为”基础之上的,是自我的一种和谐状态,正确的行为和选择可以自发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将自己的本心融入到更高的宇宙秩序之中,由是自我可以包容万象、体纳万物,可以承担所有的命运和后果。
故事最后,师徒和解并再次做出“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26]“鸳鸯”月饼不仅是不同食物品类的融合,更是一种圆满、和谐状态的隐喻,犹如《易经》乾坤二卦阴阳相互感通、相互转化、对立统一,构成生命世界的本质以及宇宙万物的本原。葛亮通过岭南地域的饮食文化传达出一种更为普遍和总体的真相,即饮食看似稀松平常,却以最为务实的方式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与大时代之下的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而无论时移世易,其内里总是凝聚着“一股子精气神儿”,中华传统文化那最为朴实、最为本真、最为智慧的“常”“变”逻辑正蕴于其中,这也正所谓“历史的真知恰恰在民间”。
注释:
[1] 陈思和:《〈北鸢〉:此情可待成追忆》,《书城》,2016年,第10期。
[2]《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8页。
[3] 饶尚宽译注:《老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页。
[4]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0页。
[5] 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75页。
[6] 同 [5],第175页。
[7] 同 [5],第33页。
[8] 同 [5],第492页。
[9] 同 [5],第36页。
(1) 三点定位采用三角形算法计算出待测点的位置,依赖于AP位置信息和信号传输信道损失。不同环境下的信号传输损耗不同,适用于WIFI环境稳定、干扰较少和单楼层的建筑空间。
[10] 同 [5],第47页。
[11]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2]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3]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94页。
[14] 同 [5],第80页。
[15] 同 [5],第355页。
[16] 杨天才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7页。
[18] 舒晋瑜:《葛亮:日常盛宴里饱含人间冷暖》,《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17日。
[19] 汪曾祺:《人间草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0] 同 [5],第396页。
[21] 同 [5],第397页。
[22] 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23] 同 [22],第201页。
[24] 同 [5],第162—163页。
[25] 同 [5],第183页。
[26] 同 [5],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