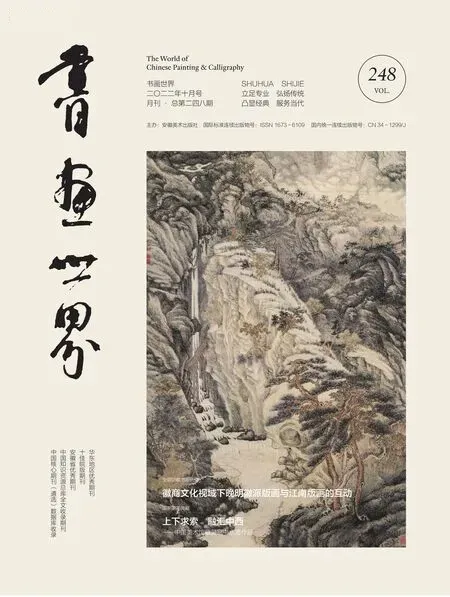张旭草书《肚痛帖》的历史意义
2023-01-06朱子敬
文_朱子敬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张旭,唐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字伯高,官至金吾长史,故世称张长史。喜饮酒,往往大醉后挥毫作书,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世人称之为“张颠”,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等人称为“饮中八仙”,与怀素并称为“颠张醉素。擅长楷书、草书,尤以大草称著。其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
《肚痛帖》(图1)高34厘米,宽41厘米。真迹不传,有宋刻本,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全帖6行,仅30字,内容是张旭记述肚痛时欲服药的生活琐事,属于便条信札类的作品,非刻意为之。

图1 张旭 肚痛帖(宋刻本)
有学者认为,此帖是后梁乾化年间(913—914)僧人彦修的临本。依据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彦修的《草书帖》石刻,北宋李丕绪题其书尾说:“乾化中僧彦修善草书,笔力遒劲,得张旭法。惜哉名不振于时。”他还把彦修草书模刻上石,而在碑阴下段一并刻有此《肚痛帖》。
所以该帖释文最后3字多有争议。
释文一:“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汁,旭。临本。”
释文一认为张旭原帖真迹的原文仅有28字,最后一字是“旭”,而“临本”二字则是彦修临摹张旭真迹之后另外的标注。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释文二:“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汁,非临床。”
释文二中“非临床”不符合当时的语境,正确与否可以研讨,但是并不影响此作的书法史学价值。
此作点画清晰,线条畅达而缠绵,变化多端,颇具张力。用笔准确,以中锋为主,提按顿挫,变化丰富。开头“忽肚痛”三个字,写得还比较厚重、端稳,字与字之间不相连接,体势凝练,形神饱满。从第四字开始,每行一笔到底,字字相连,轻盈灵动,越写越快,意象迭出,到 “如何为汁,旭。临本”则豪情万丈,酣畅恣肆,癫狂之意呈现出来,将草书的抒情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数行,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清张廷济《清仪阁题跋》云:“颠素俱善草书,颠以《肚痛帖》为最,素以《圣母帖》为最。”可见张旭《肚痛帖》草书的艺术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赏析此帖对我们有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一、使用篆籀笔法丰富了大草的用笔技法
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讲草书是“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又说“草贵流而畅”。这说明草书依靠用笔的使转完成字的结构,而使转则需中锋圆润的线条方可完成。这种用笔方法源于篆书,被称为篆籀笔法:书写时逆锋起笔,中锋、裹锋行笔,有转无折,书写的线条圆融浑厚,筋肉丰实,骨力雄强。篆籀笔法行笔时要求提按相济,虚实相变,线形饱满、浑厚而富有立体感,富有弹性,每一笔都要做到圆劲饱满、筋骨内含、力贯首尾。张旭在《肚痛帖》中,用笔多为篆籀笔法,线条圆劲、浑厚,表现出对中锋古法的创造性运用。这种技法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如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等书家的草书用笔都师承了张旭的这种用笔技法,并将其发扬光大。颜真卿《刘中使帖》,用笔纵横矫健,线条强劲秀拔,转笔处圆浑流畅,一气呵成。董其昌称其“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尤其是怀素的《自叙帖》,“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把篆籀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有别于“二王”笔法体系的用笔技法。可以说张旭开创了以篆籀笔法入草书的先河,丰富了草书的用笔技法,确保了大草纵逸、连绵而多变的线条质量。
当然,草书创作中每个字都不能一味圆转,有时也出现转中含折、顿挫分明的用笔,如《肚痛帖》首行“堪”的收笔、第二行“不知”中“不”与“知”的连笔处,都体现出转中有折的用笔。细观此帖,每个字几乎是方圆兼备的,如第四行的“俱”字偏旁的折笔和右边的圆转用笔也不失方圆互用,最明显的“服”字偏旁的方折与右边的圆转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强化线的连绵多变,丰富了大草的表现手法
书法是抽象线条的艺术。书法之所以有神奇的表现力,是因为其线条具有极为复杂的属性,诸如质感、力感、流动感、立体感、节奏感等。张旭《肚痛帖》以意为先,师法自然,表现了其为人豪爽豁达、卓尔不群的性格特点。该帖中线条畅达,其明显的艺术特点就是加强了线条的运用。书家将点、画连成线条,并赋予线条极大的可变性和抒情性;在创作中尽情放纵,一味挥洒,强化了线条的流动感、方向感和质感,使线条游于规矩之间,狂而不乱,在有意无意之间,自然成形。如第三行、四行、五行,线条连绵不断,如枯藤缠绕,千回百转,变化多端,神秘莫测,表现出张力十足、生机勃发、酣畅淋漓的艺术美感。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些都极大限度地强化了线条或灵动或雄浑,或厚实或飘逸的美感,使这些如奔蛇走虺、刚健遒劲的线条在自然流动和变幻莫测的组合中抒发难以言说的胸臆。从文字的语言实用来讲,大草已经大大削弱了汉字书写的实用性,也大大增加了汉字可识的难度;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而言,它增强了书法的丰富性和艺术性,更能够表现出书法抽象性线条艺术的特色。
三、运用节奏韵律增强了草书的感染力
节奏韵律主要的特点是某种艺术元素有序重复,在书法作品中,可以是几个字作为一个单元重复出现,也可以是作品中粗细、轻重、断连、长短、松紧、疏密、曲直等艺术元素间隔而有规律地重复出现。这些都能构成一定的节奏韵律。此帖点、画线条的运用中大量采用几个字为一组的组合元素,通过或拉长字形或压缩结体,或粗线组合或细线组合,或密排线条或疏排线条,从而形成一定的节奏韵律。如首行“忽肚痛”与第二行“是冷热所”、第四行的“冷热俱有益”在视觉上构成粗线条的节奏,而“不可堪不知”“致欲服大黄汤”和“如何”等组成细线条的节奏。这种粗线与细线间隔有规律地反复展示,形成了一定的节奏韵律,给人以大小、粗细、迟速等不同审美印象,并且会产生强弱、轻重、刚柔等视觉感受,似无声的音乐有此起彼伏之感,丰富了草书的表现手段,增加了欣赏的愉悦感,加强了大草的艺术感染力。
四、动势的表现增加了大草的生命力
伍蠡甫先生在《中国画论研究》中说“我国书学讲求由字而行,由行而全篇——由部分到整体都须得‘势’”,认为“‘势’,乃导源于‘心’对‘物’的感受”。得势则生力,无势则力弱。张旭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尤其表现在大草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他强化了线条的速度感,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笔势和字的动势,削弱了作品中静止的个体字“形”,加强了字“势”的动态连贯,用笔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呈现出满纸云烟、势不可遏的艺术效果。“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正是这种笔“势”的强化,使线条在重新组合、变换中表达了汉字的“象”与“形”的动势,将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达书家思想情感的艺术境界,真正诠释了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功用。张旭《肚痛帖》草法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是用传统技法表现个性创新的典范。张旭在倾注满腔激情的同时,又能凸显出草书气势连贯、自由畅达的特点,展现了以自然天性为追求的创作形式,形成了博大清新、纵逸豪放的浪漫主义书法风格。
五、尾首呼应使作品的结构更加完整
作品的结构是作者谋篇布局的具体表现,指作品各部分之间的组合形式,在书法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作品的开头、过渡、层次、呼应、结尾等,也就是作品创作过程的“起承转合”。《肚痛帖》的开头几字行笔较慢,线条迟缓而粗重,随后提笔并加快了行笔动作,完成了由慢到快的过渡。整幅作品中行笔快和慢、按和提、重和轻的交替运用,把作品中的前后关系和轻重关系联系起来,使作品层次分明,又有呼应,尤其是开始的“忽肚”与结尾“临本”遥相呼应,如小说作品中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发展到高潮一样,引人遐思。该帖正是通过点、画的变化和组合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该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气势连绵,意象迭出,通过起承转合的方式获得“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的艺术效果。
当然,张旭草书《肚痛帖》的创作技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的内容。它包罗了草书中的万象,尤其是在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借鉴。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和想法,相信还有很多的历史意义需要我们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