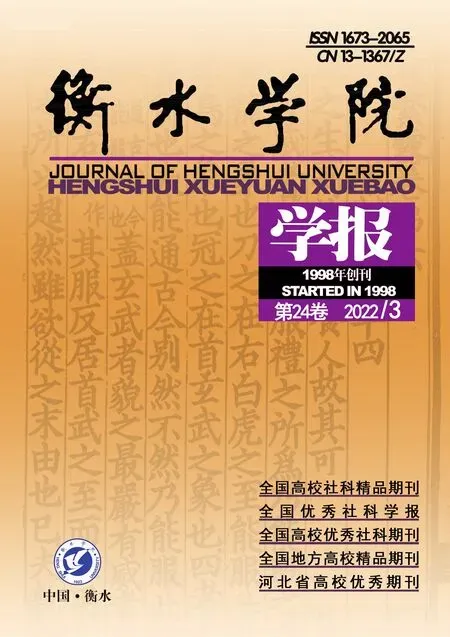“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2023-01-06保罗那比尔PaulNapier
保罗·那比尔(Paul Napier)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
“公子友如陈”:《公羊传》与“亲亲”“尊尊”儒家思想
保罗·那比尔(Paul Napier)
(上海交通大学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上海200240)
中国传统思想偏向于不直言抽象原则,而是通过论述具体事件来表达普遍真理。据此理,本文将以庄公二十五、二十七年《春秋》经:“冬,公子友如陈”之经文为例而阐释出儒家思想基本性之“亲亲”“尊尊”对立面概念结构。通过仔细分析公子友之性格、政治背景以及历史角色,将讨论“亲亲”“尊尊”与一系列对立面概念之亲密关系,即“质”与“文”,“阴”与“阳”,“仁”与“义”,“内”与“外”等因素,然后考之于先秦典籍,既指出其张力以及互相排除关系,又解释其相辅相成而互相依赖之本质。最后,将“亲亲”“尊尊”与其对应概念系列置于妥当哲学背景下,论述为先秦儒家思想之普遍思维形式之一,有客观重要性于人性、道德、社会、历史以及政治思想。以期能够揭露《春秋》公羊学连贯一致逻辑结构之一隅。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亲亲;尊尊;仁义;质文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为其偏向于重视论述具体事件、行为以及过程,不直言抽象真理或原则。与其阐释某一抽象概念系统,其不如描述具体事件以说明其道理。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讨论孔子编《春秋》的原因时,曾经直接解释此理,引用了董仲舒之说以论之,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1]4314-4315
换言之,孔子将抽象真理视为“空言”,为不足以表示其“道”之媒介,认为与其直言其抽象是非好坏,不如通过描述人类具体历史事件而达到“深切着明”之推论境界,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为“天下仪表”,以春秋具体历史过程为体现普遍道理之途径。显然,此等思想方法大异于西哲方法论,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思想传统当中,哲学与历史站在不同的领域,讨论不同的对象,然中国传统思想并非如此,常论“道”于历史形式下,其历史典籍始终具有浓厚哲学性之内涵。推此理,乃涉及儒家思想之基本本体论,用加拿大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之言:“儒家哲学意味着一种事件哲学,而并非意味着实体哲学。”[2]简言之,儒家思想不主张任何纯粹超越自然界之绝对权利,亦无所谓“exnihilo”(“由无”)宇宙创造论。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一种内在宇宙论,而不主张任何完全超越具体有限现象界之因素。因此,先秦诸子百家偏向于阐释人类具体行为于具体实践当中,不推论任何绝对超越性之理念,不由超越之永恒性而解释内在之时间性或具体性。《春秋》经之公羊学派不为例外,而且可视为此类“事件的本体论”之典型。公羊大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归纳春秋学之方法,曰:“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3]50显然,董仲舒认为所谓“经验方法”站于春秋学之中央,人人皆要“五其比,偶其类”,即将相似之事件对比而排列,将相似之道理对比而合并,才能达到“王道”之境界。由此观之,可谓人之达于“王道”,则无法通过纯粹抽象概念之快捷方式。
基于以上之方法考虑,本论文将以公羊论述方法诠释《春秋》经具体事件之一,即“公子友如陈”,通过其谨慎分析而阐释先秦思想“亲亲”“尊尊”对立面之思想结构。笔者希望既能够揭示《公羊传》如何诠释具体历史事件,又可以指出其所蕴含之义理,由此而“抽象”与“具体”两端皆有,“哲学”与“历史”两者并提。如此进行讨论,可略述儒家思想之独特两极性逻辑结构,指出一系列格外重要而对应之二分法(“具体”与“抽象”,“实践”与“理论”,“历史”与“哲学”,“个体”与“全体”),最后阐释公羊学对此两极性结构之融合以及扬弃。
一、“公子友如陈”之历史原委
庄公二十五年《春秋》经曰:“冬,公子友如陈。”[4]315经文所谓“公子友”,其为鲁国大夫,亦称呼为季友、季子,为鲁桓公之幼子,时君鲁庄公之同父异母弟弟,《公羊》视其为贤臣榜样。为何?因后公子庆父连年做大乱于鲁,此时公子友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对鲁国存亡、君位继承做出了莫大贡献。春秋时平常由“伯仲叔季”冠字为男子美称,公子友之别称为“季友”,可见“友”该为其字,《春秋》称人之字为褒义,书之以显其贤能。
“陈”指陈国,妫性,侯爵,相传为虞舜之后裔,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至于经文之“如”字,《春秋》有辞法规定:诸夏诸侯前往他国访问曰“朝”,大夫曰“聘”。然而,《春秋》亦以鲁为“内”,即以鲁国代表现实早已衰败而名义犹存之天子集权系统核心,以此别内外、序尊卑,宣扬基于天子君位之“大一统”意义。因此,《春秋》对鲁国之辞法始终有所特别,以此显示其别于列国之身份。庄公二十七年,何休《解诂》言之,曰:“《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4]322公羊家以《春秋》为蕴含“素王”孔子所推之王道,故“《春秋》当新王”意味着孔子所推之王道必统一天下,继承早已衰退周朝之天命。孔子为鲁人,《春秋》经亦为鲁国之旧史,故《春秋》以鲁为“内”可谓理所当然。至于其内涵大义,乃其意味着《春秋》以鲁国为理想化之“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之中枢”[5],为“大一统”所托而宣于天下之空间性枢纽。由此观之,鲁国为《春秋》经所“内”明明与公羊莫大之原则“《春秋》当心王”与“大一统”直接相关。因为《春秋》三世用异辞,庄公时为“所传闻世”,所以《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即以鲁国为中心,为“内”,而诸夏为疏远,为“外”。因此,《春秋》辞法之以别内外,虽有前后相异之处,然无论鲁国诸侯大夫出访外交《春秋》皆书为“如”,与天王辞同,表示《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6]之义,强调天子“无外”之道理。何休《解诂》确认,曰:“如陈者,聘也。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书者,录内所交接也。”[4]315隐公十一年《解诂》亦曰:“《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4]110由此观之,“如”辞出现蕴含三义:其一,公子友以大夫之身份“聘”陈;其二,言“如”为“尊内”之辞,表示“王者无朝诸侯之义”;其三,《春秋》以“如”辞王鲁直接显示“《春秋》当新王”“孔子为素王”以及“大一统”之基本性原则。至于公子友为何“如陈”,刘尚慈认为其为庄公二十五年春“对‘陈侯使女叔来聘’的回访”[7]161,即因礼尚往来,公子友回报陈国大夫女叔来聘而前往陈国访问。
庄公二十七年《春秋》经又曰:“秋,公子友如陈。”然此时亦增加三字:“葬原仲。”[4]318即今公子友又如陈,然而此次《春秋》经书之为“葬原仲”。为何?“原仲”为陈国世卿,即世世袭职之卿相。“原”为氏,“仲”为字。《左传》将原仲作为“季友之旧也”[8]236,即公子友之旧友。孔广森《通义》解释大夫称字为:“大夫没称字。”[9]82查于《礼记·玉藻》而见:“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10]819,可以为证。至于世卿,隐公三年何休《解诂》曰:“世卿者,父死子继也。”[4]61至于世卿之是非,《春秋》视世卿为严重弊端,因若卿大夫世世袭职,乃政权不可不逐渐集中于私家手中,大夫不可不日益嚣张,僭越君上而掠夺权威,早晚会导致国家君权分散分裂,“大一统”之道衰落。《春秋繁露·王道》言世卿,称之为:“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3]263此其所言也。后来晋国因世卿权势膨胀而分为三晋,君主政权因世卿政权而分裂,可以为“移权之败”之典型,然此并非仅限于晋国之赵氏、魏氏、韩氏,诸夏列国皆如此,此乃普遍历史趋势。因国灭乃《春秋》所恶,国存乃其所乐,大一统乃《春秋》所乐,权力分裂乃其所恶,故自然反对世卿之风。隐公三年《公羊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4]60-61为《春秋》烦恶世卿之传例。
庄公二十七年《公羊传》解释经文,曰:“原仲者何?陈大夫也。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难也。”[4]318-319“通”之义为“陈述”,“季子”乃“公子友”,何休《解诂》曰:“不以公事行曰私行。”[4]319所以“通乎季子之私行”可翻译成“陈述公子友之私人行动”。《春秋》正例,内大夫书卒不书葬,外大夫卒葬皆不书,原仲为外大夫,所以徐彦《疏》曰:“欲言大夫,不合录葬,故执不知问。”[4]319表达今书外大夫葬不合乎常例,必有其殊理。“内难”之“难”指公子庆父、公子牙所发动之鲁国政乱,“辟”表示公子友躲避国难而奔于陈国。至于大夫能否出境,春秋时期,大夫并非无权出境私行,然其特权具有限定条件,可见于《礼记·曲礼下》:“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10]124明明以大夫出境办私人之事为可行,独以请许可于君主为必备。此等较为自由之特征,显然不同于《左传》之“诸侯非民事不举”[8]235-236之说,然其亦有其理于春秋时期社会当中。大夫受允许才能出境办私人事情,反映政治等级制度之内往上递加严格的职责以及要求。同时,“诸侯非民事不举”不仅意味着君主之要求严格于大夫,也反映了君主在位而无纯粹私人之事情,就君主而言“家”与“国”融为一体,其凡事凡物必须以国名行,否则便是懈怠公事。可见,国君位置既有特权与利益,也有限制与束缚。虽然现实君主极少合乎理论理想,然不可反驳,其仍被历代公羊家当作最高榜样。
无论如何,公子友非君,其为鲁国大夫,《公羊传》为何言“不以公事行曰私行”?因为《公羊》以为《春秋》经依托外大夫原仲之葬为借口,避讳直言公子友躲避鲁国内乱。为何避讳呢?《公羊传》有例:“为贤者讳。”公子友平定鲁国内乱,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谓贤者,所以《春秋》经避讳其“辟内难”,不直言其躲内乱,不忍使其嫌于胆小耻辱。《公羊传》继续,曰:
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内难者何?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庄公之母弟也。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胁公。季子起而治之,则不得与于国政;坐而视之,则亲亲,因不忍见也。故于是复请至于陈,而葬原仲也。[4]319-320
可见,鲁国内乱细节颇为复杂。庄公临死欲立庶子子般为太子,然而庄公弟弟公子牙不以为然,违背君命,提倡立庄公庶长子公子庆父为国君。《公羊》言:“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胁公。”[4]320何休《解诂》曰:“通者,淫通。”[4]320表示二公子皆通奸于庄公夫人哀姜之罪。至于“胁公”,徐彦《疏》曰:“语在三十二年。”[4]320查于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纪录鲁庄公临死之言:“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4]321据公子牙言,“一生一及”为鲁国历代继承君位之次序,何休《解诂》描述为:“父死子继曰生,兄死弟继曰及。言隐公生,桓公及,今君生,庆父亦当及,是鲁国之常也。”[4]321从鲁国立国,周公为第一国君,考公生,炀公及,幽公生,卫公及,厉公生,献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懿公生,孝公及,惠公生,隐公生,桓公及,庄公生,几乎完全合乎此理。由此观之,因“一生一及”为鲁国之常,而公子庆父为鲁庄公弟,公子牙靠此理而提倡庄公应该传位给公子庆父。《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载此说,曰:“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1]1532虽然如此,刘尚慈以“一生一及”为偶然现象,认为“并不是鲁国的宗法继承制度”[7]178,主张鲁国真正的继承制度为嫡长继承制度,公子牙言“一生一及”为借口,根本不可靠,属于小人强词夺理之类。另外,鲁国之继承次序并非完全合乎“一生一及”之秩序。孝公传惠公为“生”,惠公传隐公又为“生”,连续两次传“生”,可见结构不完备,公子牙之言该为政治性之借口,刘尚慈之说可从。
无论如何,公子友忠诚坚持主张立子般为鲁君,正如《公羊传》所言“季子起而治之”,其顺庄公临死之愿而铲除国害,赐死公子牙以平鲁国。庄公三十二年《春秋》经书:“公子牙卒。”[4]339《公羊传》曰:“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4]339解释可见于庄公三十二年《春秋》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4]344庄公薨后,公子友立子般,然而十月公子庆父杀新君子般,立庄公另一庶子公子启为鲁国闵公。闵公在位不久,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弒其君闵公,欲自立为鲁国君。结果,齐桓公率师讨贼而平鲁国之政乱,公子友又“起而治之”,逼迫国贼公子庆父自缢而死,帮助闵公弟弟从陈回鲁而立为鲁僖公,对于平国乱以及促进君位继承的合法性做了巨大的贡献。庄公死后,公子友起而治鲁国之患,赐死公子牙,讨国贼公子庆父,故《春秋》以公子友为贤德良好、贡献无比、鲁国忠臣之表。
不过,今庄公犹在世,公子友尚未显其德,尽管后来公子友起而治国乱,庄公二十七年时他还处于较为无权薄弱之政治位置。孔广森《通义》曰:“时季子未执国政,其位与势皆不得治之。将坐视其乱,缘亲亲之心,所不忍见。”[9]88推此理而可见《公羊传》之连贯前后古今,未来与过去之理。“当下”实为个“无”,只看当下而无法知道事物真正面目,所以《春秋》断事一直根据人之总体行为,未来以及过去之贡献或罪恶。由此观之,可说《春秋》为未来贤能避讳目前无奈,以公子友之后好讳其当下避难。然而,《春秋》不仅归纳未来、当下、过去以判断是非,《公羊传》又曰:“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4]340由此而揭示《春秋》之非常重要褒贬规则,乃其“缘心”而判断好坏是非。
凡人类行为有客观之事实,亦有主观行为之动机,相辅而成为综合真理,不可一缺。不过,人常偏见于一方而失其中庸,拘泥于一面而乱其全体。若过度客观,则人会机械判断是非于表面,若过度主观,则人会愚蠢纵放,见好心为唯一重要事,而忽视客观因素。尽管如此,《春秋》于判断是非,总要强调人心好坏。查于公子友之案例,显然《春秋》以公子友为贤臣,为贤者讳,故不书其赐死之事。同时,从纯粹客观角度来观察公子友之罪,不可反驳其甚恶而可恨,公子牙为公子友之母弟,兄杀弟为大罪,何能当为贤者?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曰:
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酖之?行诸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4]343-344
显然《公羊传》已经意识到此问题,并且斟酌之极深,尽观其多层面。略列之:“诛不得辟兄”,乃公子友不原谅公子牙之罪,而此表示“君臣之义”;“行诸乎兄,隐而逃之”,乃公子友为公子牙显示体谅,不进行过度残酷之惩罚,掩盖其所能掩盖者,而此表示“亲亲之道”。《春秋繁露·王道》直接言及此案例,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明失亲亲也。鲁季子之免罪。……明亲亲之恩也。”[3]233董子所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乃指僖公五年《春秋》经曰:“晋侯杀其世子申生。”[4]343《公羊传》曰:“何谓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4]343何休《解诂》曰:“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4]343时晋献公杀其嫡长子申生,大违背亲亲之道,《春秋》书“晋侯”以显著其“失亲亲”,而公子友之所以“免罪”,即不受《春秋》经之贬斥,而是受其表扬,是因为其“明亲亲之恩”,即不进行过度惩罚。《春秋》之重“亲亲”明而易见,然“亲亲”并非绝对而无条件之价值,不可以纵放“亲亲”而失去“尊尊”之义,两者处于连贯而相成之结构内。鉴于《春秋》经书“公子友如陈”之原委,可见此两层(“君臣之义也”与“亲亲之道”)之复杂互相关系,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排斥。其实,由此着手,则可见其属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心概念,涉及一大系列对立范畴,即“仁”与“义”, “质”与“文”,“阴”与“阳”,“君”与“臣”,“亲亲”与“尊尊”。只能从这个角度考虑才能揭露《公羊传》连贯一致的思想逻辑。
二、儒家社会道德:“亲亲”“尊尊”与“仁”“义”
“亲亲”与“尊尊”是先秦思想之普遍概念以及命题,从周代宗法制度衍生出来而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各派各家。其间,可说儒者偏向于视“亲亲”为最基本的概念,而公羊派释《春秋》之义亦然。战国时期孟子于《告子下》篇直接联合“亲亲”与“仁”两概念,曰:“亲亲,仁也。”[11]380汉朝刘向《说苑·政理》将“亲亲”以及“仁”之义理内涵延伸而包括“内”在其内,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12]由此不仅可见“亲亲”与“仁”密不可分,若有“仁”乃重“亲亲”,而犹可见“亲亲”从内而扩散到外,从个人的主观内在动机而发展到四方。最重要,凡此类概念,“亲亲”“仁”以及“内”,皆有其妥当而对应之反义概念,即“尊尊”“义”以及“外”。故人偏向于“亲亲”,则重“仁”“内”;偏向于“尊尊”,则重“义”“外”可谓理所当然。至于“仁”之具体含义,《韩非子·解老》将“仁”定义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13]换言之,“仁”是主动喷涌而出的人人自然爱人之基本特征,最简单体现于《三字经》之典型“人之初,性本善”说法,为中国历代人性思想做基础。正如“仁”之“欣然爱人”性质,“亲亲”亦可见为主动从人之基本实质产生出来的倾向,此义可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言:“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1]2584,将“仁”“亲亲”与“人情”以及血缘关系联合起来。最有权威之儒家思想对于“仁”之构想在于孟子之《公孙丑上》篇。于此,孟子将“仁”阐释为“不忍人之心”,认为从人之“四端”“扩而充之”,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1]113。归纳之,孟子之说不仅意味着“仁”“亲亲”与“内”当作儒家思想之基本人性理论(《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1]113),其亦意味着“仁”“亲亲”与“内”当作儒家思想之基本社会组织基础(《孟子·公孙丑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11]113)以及政治思想核心(《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1]112)。
儒家思想虽然将“亲亲”“仁”与“内”视为人性、社会以及政治之基础,然正如“阳”于“两仪”之际不能完全离乎“阴”而存在,此系列“阳性”之概念亦不能离乎其对应之“阴性”概念而独立自由。其实,类似于《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14]6,“亲亲”一直与“尊尊”相关,而两个范畴相互对立。故若从“亲亲”之境界迈进周围社会,工作办事始与较为疏远之人沟通,乃已迈进“尊尊”之境界,要服从上令而指导下属,认真扮演某一具体之社会角色,而此具体社会角色必以“尊尊”之道为正。简言之,越近“尊尊”之界,“亲亲”之影响越衰弱,所以《礼记·中庸》将“亲亲”与“尊尊”之张力,“仁”与“义”之矛盾视为生“礼”之来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5]28由内到外,即由“仁”到“义”,意味着进入社会以及政治制度后,人人皆不可不遵守“义”之条件,顺从“义”之组织。《春秋繁露·精华》曰:“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3]159解释“义”为属于社会交往等级上下内在逻辑之类,凡社会成员得其正位而“义”道备。于是乎,若欲归纳“亲亲”与“尊尊”之正确关系,必须求之于两仪之间,即正如“阴”与“阳”无法两方皆盛,两方均衰,“亲亲”与“尊尊”,“仁”与“义”之关系犹如此,故不如说一面之兴为其对立面之衰。董仲舒书此理特清于《春秋繁露·天道无二》,曰:“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3]776推其理于仁义之道,可谓“仁”与“义”不得两起,“仁”越杀而“义”越盛,相反亦然。归纳之,“亲亲”与“尊尊”存在于一个连贯而统一之结构内,两者密不可分,又不可完全融为一体,用董子之言两者“不得两起,故谓之一”。由此可见,“亲亲”与“尊尊”不仅体现“两仪”之“相反之物”结构于有限现象界当中,反映阴阳之“不得两起”固然趋势,其又来源于统一万物之本体泉源,由此而可“谓之一”,可视为统一之全体表达于两极性形式之下。中国思想各派虽皆书此统一万物之原则以异名,如“道”“太极”“元”“玄”,然所言者无论以何名起之始终为一,而先秦各家各派似乎皆以此两极性有限界逻辑结构以及一元本体来源原则为基本性前提。由此观之,可谓“儒”“道”“法”“墨”之外表虽相异,其内涵实相同,故皆“同归而殊途”[16]358。
庄公二十七年,何休《解诂》引用《礼记·丧服四制》曰:“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揜恩。”[10]1469徐彦《疏》诠释,曰:“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断’字,盖以所见异。”[4]320依此解释,《礼记》之义该为:在内“事恩断义”,在外“事义断恩”,正好表达“仁”(或“恩”)与“义”之二分法,“亲亲”与“尊尊”之“不得两起”结构。如此将“亲亲”与“尊尊”对立起来,乃知“亲亲”“尊尊”不仅反映《周易》所始推之“两仪”宇宙本体思想,其又为中国思想传统的独特调和个人与社会、家庭与政治、部分与整体关系之基础性理论。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不将“宇宙”与“政治”、“本体”与“现象”、“自然”与“社会”分开来,故同一逻辑结构可用来阐释两方,用西哲语言言之,既为“本体论”(ontology)又为“伦理学”(ethics)。《礼记》以“亲亲”“尊尊”为人类社会道德之不可变革的核心结构,《丧服小纪》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10]871《大传》又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10]907显然,“阴阳”与“亲亲”“尊尊”均具有两极性,所有正如阴阳两仪之相互交往而产生万事万物,当作宇宙之基本结构,“亲亲”“尊尊”与“仁”“义”之相杀相盛当作整体社会制度之基本结构,导致礼制社会之同异、政治等级之上下,规定整个多元而五花八门之人际现象界。《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简洁言之,曰:“亲亲之教,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17]
三、儒家历史思想:“亲亲”“尊尊”与“质”“文”
上已见公子友之诛乱臣、行义道而杀其母兄,但《春秋》因其扬“亲亲之道”而褒之,看其不行酷罚而谅之。由此可见“亲亲”“尊尊”之基本社会道德内涵,对应于“仁”与“义”之本性,表达人伦之两极性矛盾以及张力。同时,又略见“亲亲”“尊尊”之宇宙内涵,对应于“阳”与“阴”之本性,“不得两起”之内在本体关系。故“亲亲”“尊尊”之两层重要内容已显著。所以,“亲亲”与“尊尊”不仅对应于“阳”与“阴”,当作联合“宇宙”以及“社会”、“本体”以及“现象”之两极性概念对立面;其又不仅对应于“仁”与“义”,当作人性、社会以及政治之基本结构元素;其亦对应于“质”与“文”两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之两个重要思想范畴,由此而涉及更多道德与历史现象。据桓公二年何休《解诂》曰:“质家右宗庙,上亲亲,文家右社稷,尚尊尊。”[4]131可见“亲亲”对应于“质”,主质乃重视家庭以及血缘之宗庙;“尊尊”对应于“文”,主文乃重视国家行政以及祭祀社稷。在这一方面,“亲亲”与“尊尊”,“质”与“文”似乎略对应于“私人”与“公开”境界,表示人人生活当中之不可避免的张力以及对立①虽然,现代之“私人”与“公开”两个概念并非完全对应于先秦中国思想所推之“亲亲”与“尊尊”思想,因为现代“私人”与“公开”对立面直接由启蒙运动思想遗产而来,基于个人之独一无二身分、人类权利之概念、“社会契约”理论等,即一系列独特西方现代思想概念以及逻辑,大异于先秦汉朝儒家思想所推者。最基本之缘由,该为先秦中国思想并非具有启蒙运动以来之“个人”范畴,故当时人先为某一家庭、血缘、氏族之成员,而后为“个人”。。
然“质”“文”之含义并非限制于此,除此之外,其亦涉及儒家历史思想,将朝代变换融入其复杂而多元的对应范畴系统。邹衍先将“质”“文”与历史发展逻辑结合起来,主张朝代因其继承弊端而不断互相替换,故朝代之弊端由其或从“质”或从“文”而起。后朝不可不继承先朝之弊端,面对于此而行改革以补其不足,随着弥补先弊而同时产生其自己之新弊端,而此类代代交替之历史过程可推以无穷。由此观之,“质”与“文”为两极性之朝代本质结构,凡朝因先弊而起后病,由此而得出历史之“质”“文”循环结构。历史全体不断摆动于“质”“文”两极之间,而此之际产生出历史之独特发展逻辑。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汉武帝时,邹衍之教兴于王朝,其曰:“臣闻《邹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18]显然,邹衍之教不仅为抽象理论,其亦为直接面对当时政治实践之构想,主张政策必随时而变,不可拘泥于任何死板思想,推崇汉儒必举新政策以对待当时所面对之新挑战。汉时“质”“文”对应于哪一朝代为急切政治命题,而群儒不一,或以商为质,或以周为文。不过,争论始终反映汉朝如何正当继承先王之天命,如何宣扬汉朝之合法性而使人间之政治系统以及礼仪制度合乎宇宙以及历史之两仪结构。于是乎,朝代之“质”或“文”不仅为纯粹政治性之问题,且亦是如何调和政治与宇宙、人类与上天之问题。《白虎通·三正》直接论“质”与“文”于阴阳之范围内,曰:
王者,必一质一文何?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19]368
可见,《白虎通》并非将“质”与“文”之替换视为纯粹历史性或政治性之问题,而是将“质”与“文”视为宇宙根本两极性逻辑之表现,由此而将王朝之或“质”或“文”视为反映更广泛、更全面之本体原则。由此其引《尚书大传》之文,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19]368又引《礼三正记》之文,曰:“质法天,文法地也。”[19]368直接将人类朝代礼制与“天地”,即宇宙性之“两仪”原则,联合起来。推此理,历史性之朝代替换虽由具体人类所作所为推动,然具体人类所作所为亦必视为体现本体道理者。此一本体道理为宇宙之两极性“两仪”替换结构,出现于人类历史当中而为“质”“文”之交替过程,因其“不得两起”而可以无穷循环。《史记·平准书》明显推论“质”与“文”之宇宙性含义,将其用以阐释“物”之盛衰,曰:“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1]1442可见,司马迁将“质”“文”当作表示宇宙之固定循环发展逻辑者,故“质”“文”虽可用以解释朝代之替换,然其功能并非限于此,而朝代之“质”“文”替换又为宇宙自然兴衰循环逻辑之个体表现之一。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又解释王朝历史交替以“质”“文”,曰:
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3]454
董仲舒之逻辑于此虽有所不满,尤其于其“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之说,然至于儒家历史思想之“质”“文”思想方面,关键在于其认为每个王朝具有特定的“制”,或“质”或“文”,将“质”对应于“天”“阳”以及 “亲亲”,将“文”对应于“地”“阴”与“尊尊”,以为每一后来朝代必须顺从此结构而依次出现,建立一个连贯历史循环理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之历史系统细节颇为复杂,此一“四法”说亦有人主张其非董子本人所著,目前无法仔细展开,只能指出本文将历史当作一个“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之反复节奏,由“质”到“文”而由“文”到“质”,不断反复运动于两极之间,具体体现出老子著名“反者道之动”[14]110之运动。于是乎,正如两仪“不得两起”,“法天”与“法地”之朝代“不得两起”,“商质”与“夏文”互相替代,一端偏向“亲亲”,一端偏向“尊尊”,在历史过程当中反映出“亲亲”与“尊尊”、“仁”与“义”于社会政治里的复杂互相排斥运动。《史记·梁孝王世家》据此理而言及继承制度之结构,将“及”对应于“亲亲”“质”“天”“阳”,而“生”对应于“尊尊”“文”“地”“阴”,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1]2091由此可见,汉代又将继承形式之或“及”或“生”视为表达更普遍之两极性原则,显然将“亲亲”与“尊尊”当作一种连贯、无所不包的中国传统思想历史结构之一。
四、儒家君子论:“文质彬彬”
公子友所面对之具体政治局势,其亲戚作内乱之痛苦挑战,其“国”与“家”、“君”与“兄”、“亲亲”与“尊尊”之矛盾以及张力,并非为某一偶然事件,而是体现了一个极为广泛与深刻的思想逻辑以及生活哲学。公子庆父、公子牙杀君乱国,犯大罪,而公子友必罚之,然行义道必损仁道,故公子友虽行惩,亦“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由此而勉强达于“仁义皆存”之道。由此观之,若从公子友之特别政治行为着手,可以将其具体实践之抽象原则提炼出来,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普遍思想方式的表达之一,无论在宇宙、社会、道德、政治以及历史思想当中,到处可见同一相互排斥的对立面逻辑关系,即董仲舒所言之“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根本结构。
不过,两者并非独有相互排斥之关系,传统儒家思想亦常常推崇“亲亲尊尊兼得”当作为人之最高理想,将此难能可贵之理想视为“君子”之妥当境界。换言之,达到君子之境界,乃仁义相成,质文皆有,“亲亲”与“尊尊”不相互损害。《论语·雍也》载孔子言,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0]86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文质并见”为君子之极,表达扬弃“质”与“文”之否定性关系之理想。若能达于此,乃“质”与“文”彻底相互融合,两者不再互相排斥,故《论语·颜渊》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20]181据孔子说,为君子而“质”“文”两端必须并存,甚至基本上可以回归为一。可说,正如阴阳两仪回归为“太极”而“太极”当作两仪真正来源以及统一,正如《系辞上》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16]340,那么“质”与“文”之互相排斥两者终于统一于尚未分裂的简单状态,回归于统一天地,至高无上之“太极”。由此观之,质文并存既代表“君子”之最高文明成绩,又代表“道”之最基本“自然”状态,故“天”与“人”融合于“文质彬彬”状态当中,个体体现全体,君子体现大“道”,《吕氏春秋·大乐》所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名,不可为形,强为名之,谓之太一”[21]是也。可说,正如两仪归一于“太极”,儒家为人、社会以及政治最高理想表达“质”与“文”两端融为一体之境界。由此而其普通相互矛盾不再有效:“自然”与“文化”、“真理”与“历史”、“人为”与“主动”、“宗教”与“政治”终于融为一体。
鉴于此,可推理于《春秋》经之“公子友如陈”之说,即“亲亲”与“尊尊”、“质”与“文”、“仁”与“义”皆对应于公子友之两个行为选项,及“起而治之”或“坐而视之”,可言为积极或消极之行为态度。若前者,“则不得与于国政”,即违背行政之“义”;若后者“则亲亲,因不忍见也”,即损害“仁”之道。孔子之最高理想为“仁义兼得”,不得以仁害义、以义害仁,认为君子不可以一端损害另一端。由此而可见公子友之行为其实有道理,即公子友于鲁国内乱进退两难,或“起而治之”,由此以义害仁,或“坐而视之”,由此以仁害义,故请赴陈国以避难,请避难以避免犯罪。人无法得于君子之道,则必退而避之,正如《论语·泰伯》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0]116由此观之,公子友之行为不仅可体谅,其完全合乎儒家思想最高美德!《春秋》岂不以公子友为贤,为公子友讳?
五、儒重“亲亲”之道
“亲亲”与“尊尊”相辅相成,不可一缺,当作《春秋》经之最高道德理性。公子友所面对者,乃为一种经典“悲剧性”矛盾,即其无论选哪一方面,或免贼兄之罪,或酷刑之以使乱臣贼子惧,或扬“亲亲”,或兴“尊尊”,皆必导致非完美后果,必重两仪一方而使人失中,终于无法达于完善平衡。但《春秋》仍然褒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凡人类之美德出现于有限而非完美之环境当中,只能迎事而起,故不可不有所不足,有所缺点。因此,在暴力乱世当中人之完美“君子”状态不可不失调而有所损害,或以仁害义、以质害文,或以义害仁、以文害质,由此,儒家传统思想以及《公羊传》一向偏向于重视“亲亲”,将其视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其缘由可以追溯于周朝之宗法政治以及社会制度。于宗法社会制度当中,社会结构尚未发展到相当复杂之程度,分工尚未到成熟状态,氏族以及家庭尚为当时之最高社会组织单位。人人皆自视为某种氏族成员、某种家庭成员,为父或子、伯或仲或叔或季,并非先自视为某一国家之公民,更非自视为纯粹之私人个体。氏与氏之际当外事,家与家之际亦当外事,血缘关系显然为最明显的人际关系,人人当自然而然地从家庭内事着手,将氏内之主动而自然的恩情关系拖到外在的、更疏远的社会关系。因此,宗法时期民间儒家思想不可不将“亲亲”当作社会组织制度之中央以及核心,不可不把“仁”和“内”视为所有后来社会道德之基础。《礼记·大传》描述“亲亲”基础以及核心如何散发于整个社会体系,曰: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10]917
其言简而易懂,“亲亲”乃整体社会结构之本,人人应当着手于“亲亲”,由“亲亲”之核心扩张到周围的“尊尊”而最终达到礼乐完备之制度。如此“由内而外”,推己及人,当作典型儒家思想特征之一,明显于《孟子·梁惠王上》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1]26表示“由内而外”之道德思想方法,反映儒家特别偏重“亲亲”之道。《尚书正义》孔颖达《疏》简洁描述此原则,曰:“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亲亲之心,以至于疏远,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于政令也。”[22]笔者不可增一字。
以上已描述“亲亲”并入复杂概念体系,与一系列重要范畴对应起来了,故知孔子之言“仁”,亦具有对于“亲亲”之含义。由此而见《论语·八佾》曰:“人而不仁,如礼何?”[20]32则其言“仁”而意义不可与“亲亲”无关,即若不尊重人之欣然爱人之亲亲趋势,人无法参与礼仪制度,反之,礼制不可忽视人之亲亲本质而成立。《论语·八佾》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0]32此言为何重视“亲亲”?原因在于“亲亲”之广泛意义,其复杂概念性之共鸣,即“质”“仁”“天”“内”“本”,皆为朴素、本质、主动而自然之因素,皆反映出基础性的、未受人为思考的生活元素,行礼“俭”,丧服“戚”,皆包括在其内。公羊派亦如此。隐公五年徐彦《疏》曰:“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4]86表达《春秋》重“质”于历史朝代替换制度内,作为《春秋》以“缘心”而断狱之理论基础。董仲舒继承《公羊传》家法,其自然又重“亲亲”而将其融入他整体思想系统。《春秋繁露·观德》曰:“四时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则先亲亲。”[3]615列出“四十”“十二月”与“德”为对应境界,描述为严格等级制度而将“春”“正月”“亲亲”排于第一位。董子虽不直言之,但由以上所描述观之,不妨增加“天”“质”“仁”以及“父死子继制”于其中。
不可反驳,重“亲亲”为传统儒家思想之基本特征之一。然而,不仅儒家自评如此,非儒者亦将其当作儒家思想特征之一而进行批判。《商君书·开塞》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23]可见,商鞅为法家偏向于视“亲亲”为树立偏爱而自私之因素,为某种必须受约束的野蛮人类趋势,不宜宣扬于社会中,不如以法治遏止。然尽管其“亲亲则别,爱私则险”说大异于儒者,其以“亲亲”“尊尊”为相互对立之根本概念与儒者完全相同。《墨子·非儒下》曰:“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24]436以“重亲亲”为儒者常识,又烈讥之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24]437。于墨派眼里儒者“重亲亲”为大罪,墨家由此建立“兼爱”理论以抑制人人之主动“亲亲”偏向。《老子·第十八章》又言之,曰:“大道废,有仁义。”[14]43将“大道”视为“仁义”之否定,“仁义”视为“大道废”之可憎后果。以上可略见法、墨、道三派之批评儒家“重亲亲”之言。三者虽然有所不同,其言亦不一定无问题,然均将“重亲亲”视为儒家思想之精髓,足够证明“儒重亲亲”为先秦诸子共同确认之观点。
六、“文质彬彬”与“重亲亲”之张力以及扬弃
偏重“亲亲”不可不导致弊端,即放纵人人私行倾向,使各家管内不管外,社会分裂成相互隔离之原子而无所普遍有效组织结构。即使连春秋学者也承认纯粹“重亲亲”之不足。其实,在政治方面,“尊尊”始终要高于“亲亲”,而人一进入政治境界,“亲亲”之心不可不衰退,因在有限现实历史社会当中两者“不得两起”,一方盛而一方衰,一面兴而一面颓。文公二年《谷梁传》甚至曰:“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25]简洁表达“亲亲”不得自立为绝对全面而无所不包之真理。
由此中国传统思想之无比重要特征凸显,即其偏向于避免用抽象、绝对、普遍、永恒原则讨论人类实践生活。可见,人类生活皆处于阴阳之际,生于两仪之间,如此彻底有限之人类生活无法达于无所不包、不改不变之具体实践原则。人只能通过阴阳之调,“亲亲”“尊尊”之交而试图达于某一平衡以及和谐之状态,由此而将生两仪之“太极”体现在阴阳交错之中,使包含一切矛盾之“大道”出现于有限境界之内。公子友为人为政,尽顺此理。庄公二十七年其遇“内难”,此时不掌权,无法“起而治之”,亦无法“坐而视之”,进退两难,故其退隐如陈,逃无法影响之鲁国内乱,《春秋》因其后好而讳之。反之,庄公死后,此时公子友当政,有作有为,故起而治国乱,虽杀母兄,犹扬亲亲之道,勉强行“义”而不害“仁”道。可见,公子友之行为不反映任何绝对“重亲亲”或“重尊尊”之道,不主张任何普遍实践原则,而是应时而变,按事而作,或行“仁”,或行“义”,或进,或退,或“起而治之”,或“隐而藏之”,皆按具体条件、要求以及局势而下手。于是乎,尽管两仪之际无所“常道”可言,包含两仪之“太极”支配一切有限相交,虽无名无声,犹为一切具体现象之无形源泉以及本体。故中国传统思想之唯一普遍以及绝对道德标准并非主张某一具体内容,而为一种形式结构原则,即两仪之具体平衡、阴阳之复杂和谐、仁义之相辅相成。由此,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人在各方各面皆要始终追求平衡以及和谐,尽量使“仁”与“义”、“阳”与“阴”、“亲亲”与“尊尊”融为一体,相成为一,此乃著名之“中庸”所在。
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是,传统儒家思想于“亲亲”“尊尊”持两种不同态度:其一,偏重以亲亲为本;其二,承认独重亲亲之不足,推崇“亲亲尊尊兼得”之说。或问:此非为矛盾乎?其实,传统儒家思想,包括“从殷之质”的《公羊传》始终不将“亲亲”当作绝对价值或不可批判之心理态度、或社会道德原则、或历史发展逻辑。事实上,在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当中,“亲亲”与“尊尊”相互排斥,处于复杂而多层面的两极性关系,而于此有限境界当中皆有其功能以及特权,皆有其坏处以及缺点,必须相互补足,不可一方全缺。于是乎,《春秋》虽重“亲亲”以断狱,重“仁”以褒贬是非,然此并非等同于盲目而狭隘地“崇亲废尊”或“崇质废文”。
要了解“亲亲”为何既可以当作“亲亲”“尊尊”之际的基本因素,又能为平等两端之一方,就必须回归到孔子之言。《论语·八佾》曰:“绘事后素。”[20]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其文曰:“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15]63故可以“绘事后素”为“绘画之事后于素”之义,以孔子为言“素”该当作绘画不可或缺之白色基础。推此比喻,“素”该对应于“质”“亲亲”与“仁”,而“绘事”对应于“文”“尊尊”与“义”,先“质”而后“文”乃为为人妥当结构。如若相反,乃“质”“文”皆废。朱熹阐释此理极为敏锐,由此而解决上矛盾,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白可以受采。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也。虽有文,将安施乎?”[15]63。由此可见“质”既为“文”之相对因素,又为“文”之必然基础,正如“亲亲”既为“尊尊”之相对对立社会因素,又为人之绝对本性。当作前者,乃其价值相对而范围有限;当作后者,其价值绝对而范围无限。从宇宙角度看,“质”始终为本,为必须先立之本体,为“受采”之“白”;从历史角度看,“质”乃为两极端之际之有限因素,不断处于彼胜此败、彼进此退之二分法当中。由此观之,可谓“质”之双重功能类似于董子之“天”概念,既当宇宙整体又当宇宙部分。笔者认为此双层功能实为中国传统思想逻辑之关键所在,学者彻底展开之而或可达于儒家思想系统之精髓,然此一命题远远超越本文之范围,要等后撰文阐述。
[1]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Ames, Roger T., Hall, David L..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15.
[3] 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50.
[4] 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 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44.
[6] 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31.
[7]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9.
[11]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169.
[1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131.
[14]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译[M].王弼,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6] 孔颖达.周易正义[M].王弼,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7] 王肃.孔子家语[M].王国轩,王秀梅,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45.
[1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2809.
[19]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0]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1] 吕不韦.吕氏春秋集释[M].许维遹,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35.
[22] 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75.
[2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2018:51.
[24] 吴毓江,孙启治.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5] 范宁,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1.
“Prince You Went to the State of Chen”:and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Love for His Kin” and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Paul Napier
(Dong Zhongsh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ends not to speak out about abstract principles, but to express universal truths by discussing specific events. Based on this reasoning, this essay, taking for example “In winter, Prince You Went to the State of Chen” in Zhuang Gong’s 25th and 27th year fromillustrates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pposite to the basic nature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love for his kin” and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Prince You’s personality,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role, it first elucidates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officials” and a series of concepts opposite to them, namely “content” and “form”, “yin” and “ya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ner” and “outer”, etc. Then, it examines these concepts from the classics of pre-Qin Dynasty, not only to point out their tension and mutual exclusion, but also to explain their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dependent nature. Finally, it places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 and their opposite concepts in a proper philosophical context, describing them as one of the universal thinking form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which is of objective importance in human nature, morality, society,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Dong Zhongshu;; Gongyang theory; love for his kin; respect for his elders and superiors;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ontent and form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6
保罗·那比尔(1986-),男,英国爱丁堡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青年学者支持计划”(HS-SJTU2021C01)
B234.5
A
1673-2065(2022)03-0044-10
2022-03-01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