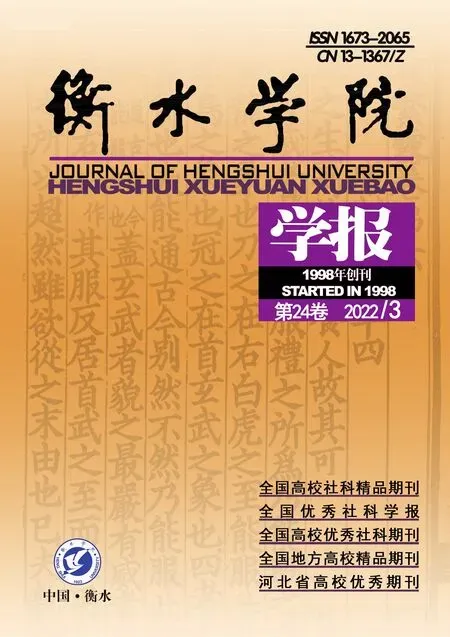“君子不器”的角色伦理分析
2023-01-06李祥翔
李祥翔
“君子不器”的角色伦理分析
李祥翔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前辈学者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器”的内涵和功用出发,将“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只有一种功用;另一类则对“君子”进行深入分析,将“君子不器”与君子的道德属性联系起来。第一类理解没有全面考虑“器”和君子的特征,第二类理解则不免抓错重点甚至有过度解读之嫌。因此,两类理解都有所不足。“器”是指人像特定的器物一样,只能承担某些特定的角色,消极地发挥角色功用。“君子不器”则是指君子有能力承担无限的角色,根据所处的关系和情境选择最恰当的行为。
君子不器;伦理;道德;角色
“君子”一词在儒家典籍中随处可见,儒家学者或是称赞君子高尚的品行,或是描述君子具有的特征,使得君子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但其中也不乏晦涩难懂的语句,如《论语》中的“君子不器”。何为“不器”?“不器”又与君子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无法在《论语》中直接找到答案,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本文在忠实于经典原著的基础上,试以儒家角色伦理来分析“君子不器”一语的含义,并且从中总结出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
一、“君子不器”旧解之不足
“君子不器”一语出自《论语·为政》,原文非常简短,只有“子曰:‘君子不器’”[1]17六字,孔子交谈的对象、针对的问题、说话的场景,我们全都不得而知。相关信息的缺失增加了后人理解这句话的难度,但是历代学者依然不惧艰难,针对这句话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提出新的理解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前辈们的理解,这既能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灵感,也能避免我们重蹈前人的覆辙。
“君子不器”这句话中有两个概念,一是“君子”,一是“器”,前辈们的解读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而展开。具体研究方法通常是对其中的一个概念进行重点分析,再将分析的结果与另一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如果对前辈们的理解进行归类,也可以按照研究的重点所在,将其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重点放在对于“器”的分析上。前辈们先是解读“器”的内涵与特征,然后确定“君子不器”一语中“器”字强调的是器的哪个方面,再反推出“不器”的含义,最后将这种含义与君子联系在一起。那么,“器”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呢?“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器’字最初都出现在‘卣’(盛酒的器具)、‘簋’(盛食物的器具)、‘盘’(盥洗用具)等祭祀用器的铭文中,这说明‘器’最初就是指这些具体的器具”[2]86。后来,“器”的所指不断扩大,从祭祀用器扩展到生活用器,后来更是成了一切“形而下者”的通称,即用来指一切有形有相的具体事物。但不管是祭祀用器、生活用器还是形而下者,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种器物都有着一定的功用,如房屋可供居住,笔可用来写字等。前辈们抓住了“器”具有特定的功用这一点,认为这就是“君子不器”中“器”字强调的重点所在。如包咸认为“器者各周于用”[3]112,熊埋认为“器以名可系其用”[3]112。前辈们由此认为,“器”的功用是有限的,一种类型的“器”只能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而不能用于其他,如舟车各有不同的用途,那么“不器”自然就是指没有特定的用途,“君子不器”也就是指君子不应像器物那样有着特定用途,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这种观点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被众多学者所认可。如朱熹认为“君子不器”指的是“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4]58。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将“不器”解为“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5]34,进而将“君子不器”翻译为“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5]34。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不器”解为“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1]17,进而将“君子不器”译为“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1]17。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将“君子不器”简单地译为“君子不是器具”[6]32,随后将此句详解为“这句话今天可以读作人非robot(机器人),即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械……人应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6]32。李泽厚对“君子不器”进行了现代性阐释,但他依然在强调君子的多才多艺,并未突破前人的理解。
第二类,不再将“器”作为解读的出发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君子”上面。清代学者李光地在《论语劄记》中解读“君子不器”为:“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谓。如子路之治赋,冉有之为宰,公西华之治宾客,以至子贡之瑚琏皆是也。君子之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颜子视听言动之间,曾子容貌辞气颜色之际,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勋德业在焉,此之谓不器。若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不器,是犹未离乎器者矣。”[3]112可以看出,李光地对于前人的理解提出了批评,认为如果将“不器”理解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为只要讲用途,讲作用,‘不器’就仍然是‘器’,二者的差别就不是本质上的,而是数量上的,也就是有一种用途还是多种用途而已”[2]87。在对前人提出批评之后,李光地开始思考“君子”有何特征。在他看来,“君子之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君子最大的追求在于成就自身的道德,技艺、行动、事功都只是次要的副产品而已。因此,子路、冉有、公西华、子贡等人虽各有所长,但依然是“器”,只不过是“瑚琏”这样特殊的“器”,颜、曾二人“不器”而德行完备,因此比子路四人更接近“君子”。可见,李光地将君子的道德属性引入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当中,而这一思路在当代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王大庆称赞李光地的睿见,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与其说是主张多才多艺,不如说是倡导提高道德水平和境界”[7];董卫国则从德才关系的角度指出“君子不器乃是强调德性修养的重要性……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的人,其技艺和能力未必能够给他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带来真正的福利”[8]。
上述两类解读既合理又有不足。第一类解读,虽然深入分析了“器”的内涵和特征,但这种分析是否全面尚有待商榷,同时这类解读未深入考虑“君子”本身有何属性,因此不免走上了歪路。第二类解读,对“君子”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君子”的道德属性,但是要么缺乏对于“器”的深入分析,片面强调君子的道德属性,甚至以道德否定功用,使得最终理解偏于一隅;要么是过度解读,甚至将自身的理解强加于孔子原意之上,成了“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因此,要想正确理解“君子不器”,我们一方面要全面理解“器”与“君子”二者的特征,在它们的相互规定中确定“君子不器”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要忠于儒家元典,避免将不属于孔子原意的个人思想掺杂在对原文的解读中。
二、器:承担特定角色
“君子”与“器”这两个概念对于“君子不器”的理解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原文中“君子”的相关属性是通过对“器”的否定而获得的,所以要想正确理解“君子不器”,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对于“器”的全面理解出发。
《论语》一书中,除“君子不器”外,共有四处谈到“器”这个话题,分别在《八佾》《公冶长》《子路》《卫灵公》四篇中出现,且都出自孔子之口。因此,要正确理解孔子所说的“器”到底有何含义,这四处涉及“器”的语句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考。
《卫灵公》篇中涉及“器”的语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处与“工”相联系的“器”,杨伯峻认为是“工具”的意思。联系下文来看,孔子以“工”与“器”的关系比喻自身与贤大夫、仁士的关系,如此一来,“器”在此处的含义就是被人利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公冶长》篇中,孔子称子贡为“器”,但同时指出子贡是“瑚琏”这种尊贵的礼器,而非工具。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即孔子口中的“器”含义多样,不可一概而论。
《八佾》中涉及“器”的语句是孔子对管仲的指责:“管仲之器小哉!”[1]31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有时他会对管仲提出器小、不俭、不知礼等指责,有时他又会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劳。通过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我们可以初步获得孔子口中“器”的一些特征。首先,孔子指责管仲为“器小”,言外之意就是人应该成“大器”,而不应当成“小器”。可见,虽然“君子不器”,但“成器”本身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成大器”也是值得称赞的。其次,管仲对于华夏文明实有贡献,但几乎只集中于政事与军事方面。在礼节与生活作风方面,管仲实在无甚过人之处,“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31其三,孔子有时用“仁”来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1]149,但在《论语》中,孔子从未称管仲为“君子”。概言之,管仲仅在特定的方面有所作为,而于其他方面则无所建树。因此,管仲是“器小”而非“不器”,不得被称为“君子”。
然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作为“瑚琏”的子贡是怎样的。结合《论语》中的其他内容来看,子贡有着一技之长,尤其是在货殖方面,如“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1]57,“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114。但子贡也有缺陷,如“不受命”[1]114等。可见,子贡与管仲极为相似,都是既有某方面的特长而又存在缺陷。因此,在孔子眼中,二人都是“器”。但是,二人又有所区别。管仲几乎是只擅长军政之事,而子贡在从政之外又擅长货殖,还位列孔门十哲中的“言语”科;并且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虽不以礼闻名,但不可能不知礼。相比之下,子贡较管仲为佳。因此,二人虽同为“器”,但一为“小器”,一为“瑚琏”这种珍贵的礼器。结合孔子对管仲和子贡二人的评价,可见,在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如果在其他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那么就是小小的“器”,很可能是斗筲等器;如果在其他方面仅略有缺陷,那么就是珍贵的礼器。至此,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一个趋势,即孔子认为一个人的缺陷越少,可应用的场合越多,他的器就越大、越精致。
最后,我们看一下《子路》篇中涉及“器”的语句:“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1]141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读“器之”:“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4]139在这句话中,“器”是作为“备”的反义词而出现的,而“备”又有全、尽之意,如杨伯峻就翻译“求备”为“求全责备”[1]141,因此,朱熹此注应为确当。如此,“器”的含义就不仅仅指个人只有某一方面的功用,还可以指个人具有特定的材质。
以上通过对《论语》中所有涉及“器”文字的分析,初步把握了“器”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孔子使用“器”字的原则。但还不能断言“器”只有特定的功用与材质这两种内涵,还应结合其他文献,继续挖掘“器”的内涵。
如前所述,“器”字最初主要是指卣、簋、盘等礼器,后来才逐渐扩展到生活用器乃至一切具体事物。虽然“器”的覆盖范围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把握“器”的内涵,我们就应当从“器”的原初含义入手。“卣”在《尔雅·释器》中被解释为“器也”,郭璞注云“盛酒尊”;“簋”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黍稷方器也”,也就是说,“簋”在古代是用来盛放食物的方形器皿;《礼记·丧大记》中“沐用瓦盘”,《正字通·皿部》中:“盘,盛物器,或木或锡铜为之,大小深浅方圆不一。”以上就是传统文献对于卣、簋、盘三种“器”的注解。如果仅仅由此展开分析,具有特定的功用确实是“器”最明显的特征。但是笔者以为,仅就这三种器物来分析“器”的含义是不妥当的。首先,从《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代祭祀活动的礼器多种多样,并非只有卣、簋、盘三种礼器,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独属于这三种礼器而不见于其他礼器的特征。其次,《说文解字》中对于“器”的解释是“皿也”,段玉裁注云“器乃凡器统称”。在许、段二学者的解释中,“器”都是各类器皿的统称,而非三种礼器的统称。最后,只在这三种礼器的铭文中,最早出现“器”字,的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器”字最初仅仅是指这三种礼器。第一,我们不能排除今后有其他铭文出现的可能;第二,即使没有其他铭文出现,也有可能是因为镌刻铭文的器物没有遗留下来而已;第三,即使最初的确只有这三种器物镌刻了“器”这个字,但我们依然不能认定最初只有这三种器物可被称为“器”,因为器物制作者并不需要在每一件“器”上都注明这是一种“器”。综上,笔者以为不应当仅仅通过对于卣、簋、盘的分析来把握“器”的内涵,而应该将“器”的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大。既然卣、簋、盘三种器物都是礼器,我们不妨通过对于各种礼器的分析来把握“器”的内涵。笔者通过对《礼记》等儒家经典礼学著作及当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将“器”的特征总结如下:
首先,如前人所述,每种“器”都有着一定的功用,如卣之盛酒、簋之盛黍稷、盘之盛物与沐浴。其次,“器”都有着一定的形状与外表。虽然有些“器”可以在外表上有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始终在一定的范式之内,正如盘之大小深浅方圆虽不定,但总不会如鼎一般有腿,或如卣一般有提手。孔子看到本应有棱的觚却“失其制而不为棱”[4]88时,感叹“觚不觚”,正是因为觚这种“器”本不应有此种外表。再次,“器”的应用场合有着严格限制。几乎每一种“器”都只能在特定场合中出现,而不能广泛地应用于所有场合。祭祀活动需要“陈尊俎,列笾豆”[9]491,笾、豆两种“器”此时必须出场,而在诸侯相朝时,则“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9]281,彼此之间只以郁鬯来相互敬酒,笾、豆两种“器”在这种场合下是不能出场的。从次,“器”的使用是被动的。孔子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183从这一话语中可以看出,虽然钟鼓等“器”可以在很多礼仪活动中出场并承担功用,但它们功用的发挥却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礼仪活动整体。礼仪活动需要钟鼓起到某种作用,它们才能发挥相应作用,如礼仪活动需要钟鼓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发出何种响声,它们就只能依样照办。也就是说,“玉帛钟鼓在此活动中是被动的,它们该如何发挥作用,并不能完全自我决定,而是由其在礼仪活动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担的功能所决定”[2]88。最后,“器”有时需要彼此搭配使用。而它们之间的搭配方式有着明确规则,例如,鼎、豆、壶三种器就经常被组合到一起使用。根据考古发现,“这种‘鼎、豆、壶’的礼器组合方式,在良渚时期随葬的陶器中经常出现,并已趋于规范化”[10]。而据《礼记》记载,不管礼仪活动的规模大小,鼎俎的数量都是奇数,笾豆的数量都是偶数,“鼎俎奇而笾豆偶”[9]302。如此一来,在礼仪活动中,不仅“器”的搭配对象是确定的,就连每种“器”的数量也都是确定的。可见,“器”与“器”之间搭配关系是清晰明确而不可随意更换的。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器”有着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涵盖了外表、功用、应用场合、搭配关系等不同方面。但如果将这些不同的特征概括为一个总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器”只能承担特定的角色。在祭祀活动中,每种“器”都被分配了固定的角色,“器”只能被动地将这个角色承担起来而不能任意突破自己的角色,否则就是越俎代庖。每一种角色都有着一定的外表,“器”的角色是固定的,外表自然也是固定的;这个角色在某种场合需要起到某种作用,“器”就需要在这种场合发挥这种作用;这个角色需要和其他角色以某种方式共同参与表演,一种“器”就需要与另一种“器”以某种方式搭配到一起。“器”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它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角色的控制。
既然“器”的特征只能承担特定的角色,那么被称为“器”的人也只能承担特定的角色。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情境,人也会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这就对人的能力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但像“器”一样固定了自身角色的人却只具有特定的能力,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发挥各种能力;只能应付某一类事件,无法灵活地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只能生活于某一种情境之中,无法适应各种复杂情境;可以被动完成一些任务,却无法主动承担责任;只能与某些人打交道,无法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可否认,承担特定角色的人可能会具有某些优点,如相比“乡愿”更加正直、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成器”“成大器”在汉语中带有褒义,但他们最多可以获得直、仁等称赞,与儒家理想中近乎完美的“君子”实在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三、不器:承担无限的角色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只具有一种功用”这个含义仅是“器”字所具有的众多含义中的一种。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将“不器”仅仅理解为不只有一种功用或者不固定功用。在语言哲学的“语境原则”看来,在准确理解语词的意义时必须要考虑语词所在的语境。虽然“君子不器”一语并无上下文,但是“不器”毕竟是儒家对于“君子”的规定。因此,《论语》乃至儒家思想对于“君子”的描述和要求就是我们在理解“君子不器”时的语境。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一百多次,但并非每一处表述都与“不器”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只需要对其中部分表述进行重点分析即可。“不器”是对于“器”的否定,而“器”是固定自身的角色而不知变通,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器”的含义,但可以合乎逻辑地推理出“不器”一定与角色有关。因此,《论语》中同时涉及“君子”及角色的文字就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角色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安乐哲认为,在儒家的视域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置身于自己角色和关系的动态环境之中。“我们活着,并非只是在肉体意义上的一个生命;我们做的一切,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毋庸置疑是关系的、协作的”[11]中文版序言1。我生活着的与具体的他人的关系为我们带来了各种相应的角色,我就是我的所有角色的一个结合体,而不是孤立存在、不与外界往来的“单子式”的个体。“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是在所有这样‘角色’及其关系中度过的”[11]194。因此,我自己是谁以及我该采取何种行动,一方面取决于与我建立起关系的他人;另一方面要取决于我所处的情境,即没有最正确的行为,只有最恰当的行为,如“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12]214。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不能决定自身所处的关系与情境,因此也就无法自由决定自己的角色。同时,关系为人们带来的角色是相互的,我是某人之“子”,那么他就是我之“父”;我是某人之“臣”,那么他就是我之“君”。因此,如果我不认可自己的角色,那么我实际上同时否认了与我处于同一段关系中的他人的角色,这种行为往往会伴随对他人的伤害,是一种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反抗自己的角色。在儒家看来,能否根据自身所处的关系和情境认识到自身的角色,进而主动承担起角色责任,可以作为君子、常人与小人区分的标准之一。
君子可以根据所处的关系和情境认识到自身的角色,进而主动承担起这个角色应当承担的责任,当关系和情境改变时,君子也会随之改变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器”的重点正在于君子这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取相应行为从而承担无限角色的能力,而不在于君子的功用在量上有多少、在程度上有多高。如《论语》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1]133孔子在耕种与园艺这些功用上不如他人,但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12]214,真正具有“不器”这一品质。因此,孔子才是真正的“君子”。这种事例在《论语》中不只一处。孔子曾明确称三人为“君子哉”,分别是子贱、南容与蘧伯玉。据《吕氏春秋》,宓子贱曾任单父宰,“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13],其治理的方法就是将任务委派给适合的人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即“任人”而不“任力”。据《论语》,南容能够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41。而蘧伯玉则能够做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61。可以看到,孔子眼中的这三位“君子”都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境的不同承担各种角色之人。他们不仅不固定功用,而且不固定行为、不固定态度、不固定外表等。任何与角色相关的要素在君子看来,都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的。也正因此,他们才能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是只能承担某一特定角色。
常人无法像君子那样随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将其承担起来,但只要被告知自身的特定角色是什么,那么常人就可以尽力把该角色应有的责任承担起来,即“成器”;有时常人对于角色的承担还可以很出色,即“成大器”。因此,管仲能够在军政方面有所作为,即是“成器”,但他对于礼仪一无所知,多次失礼,军政之功难掩失礼之过,所以只是“小器”。君子如果善加利用常人之“器”,那么就可以将常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使常人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君子用人时皆量才而任事,即“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此,孔子对于“成大器”之常人亦赞赏有加,只是不称其为“君子”而已。如“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161。史鱼不管所处情境如何,始终不改本色,虽然不能成为君子,但可以被赞为“直”。
小人承担角色的能力最为低下,不但不能像君子一样承担无限的角色,甚至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承担有限的角色,有时甚至会反抗自身的角色。如前所述,关系为人们带来的角色是相互的,彼为君、父则我为臣、子。小人行事肆无忌惮,若不认同自己为臣、为子的角色,就会以各种手段逃避角色责任,甚至弑君杀父,妄图颠覆彼此的角色。在驱使别人时,也不能量才任事,而是求全责备。总之,小人不但不能承担自身的角色,甚至对于如何承担角色一无所知。所以,孔子对于不热心于修齐治平之道反而想学稼圃的樊迟很不屑,甚至訾曰:“小人哉,樊须也!”[1]133
综上所述,“君子不器”不是指君子不只有一种功用,重点也不在君子的道德属性。“君子不器”的真正含义,是指生活在关系和情境中的君子不像具体的器物一样只能被动承担社会分配给他的特定角色,消极地发挥特定的角色功用;而是总能够主动分析自身所处的关系和情境,正确认识到自身的角色,并且能主动将属于自己的角色责任承担起来。“君子不器”的外在表现,就是君子不管在什么情境下都可以选择最为恰当的行为、从容应付各类棘手的事件、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在各种情境中游刃有余,从而使自己可以适应任何关系,可以生活于任何情境之中。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吴先伍.“君子不器”读解[J].晋阳学刊,2020(6):86-90.
[3]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6]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9.
[7] 王大庆.“君子不器”辨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4-138.
[8] 董卫国.德性与知识的融通——孔子“君子不器”思想辨析[J].孔子学刊,2012(00):165-173,9.
[9]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0]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
[11]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M].孟巍隆,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12]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6.
An Eth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Jun Zi Bu Qi”
LI Xiangxi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There are two kinds of understanding about “Jun Zi Bu Qi” ( A man of high virtue and high ability shouldn’t be like an instrument whose function is limited to one aspect) among previous scholars: one i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Qi” , that “Jun Zi” shouldn’t be good at doing only one thing, while the other 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Jun Zi”, connecting “Jun Zi Bu Qi” with the moral attribute of a “Jun Zi”. Those who stand for the first one do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 and “Jun Zi”, while those who hold the second inevitably misunderstand the key points or even over-interprets it. Both types of understanding are insufficient. “Qi” means that people, like certain utensil, can only assume certain specific roles and play their role functions negatively. And “Jun Zi Bu Qi” indicates “Jun Zi” has the ability to assume unlimited roles and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and situation he is in.
“Jun Zi Bu Qi”; ethics; morality; role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11
李祥翔(1997-),男,山东济南人,在读硕士。
B222.1
A
1673-2065(2022)03-0085-06
2021-06-27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