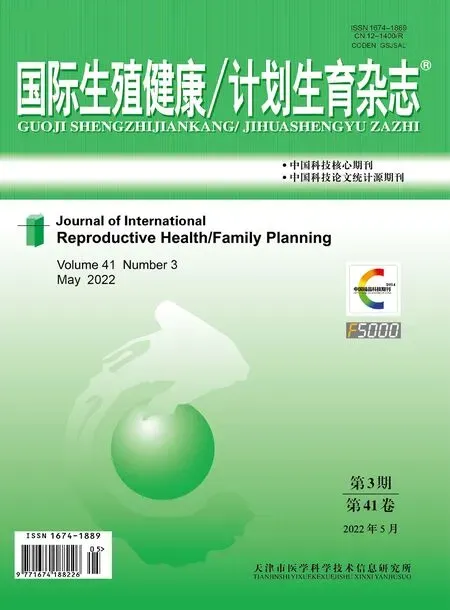单个核细胞在生殖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2023-01-05高景悦于璇臧朝雯邓晓惠
高景悦,于璇,臧朝雯,邓晓惠
单个核细胞(mononuclear cells,MNCs)是指血液中具有单个圆形核的细胞群,可通过Ficoll-Paque密度梯度离心法去除多核细胞和红细胞等不同密度的细胞组分获得。既往通常将收集MNCs作为研究单核细胞、淋巴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及树突状细胞等免疫细胞特性的前提步骤[1],随着细胞疗法的发展,MNCs中丰富的免疫细胞种类、干细胞特性、多细胞群间的协同作用以及相对容易的收集方法使其在治疗炎症相关疾病及损伤性疾病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空间。根据来源不同,MNCs主要分为脐带血单个核细胞(umbilical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UCBMNCs)、骨髓单个核细胞(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BMMNCs)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NCs)。在生殖系统领域,MNCs在治疗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宫腔粘连以及反复种植失败(repeated implantation failure,RIF)方面已开展了相关研究。现就MNCs在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MNCs临床应用特点
1.1 UCBMNCsUCBMNCs是不成熟的免疫细胞、造血干细胞/祖细胞、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和内皮祖细胞等组成的细胞群体,其来源广泛,提取分离过程无创且安全,不存在伦理问题。与BMMNCs相比,UCBMNCs中不成熟的免疫细胞抗原提呈能力及反应性低,具有低免疫原性。移植同种异体脐带血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的发生率低,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2]。UCBMNCs在心肌缺血、皮肤损伤、肾损伤及神经系统疾病中均展现了良好的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作用。
1.2 BMMNCsBMMNCs 富含造血干细胞和MSCs,还有组织特异性祖细胞和基质细胞等,可分泌多种促进损伤组织修复的生长因子,在治疗疾病方面较单一种类干细胞能够发挥更好的协同作用[3]。在临床研究中,用于移植的BMMNCs多来源于受试者自身,获取方便,可有效避免GVHD的发生。尽管自体BMMNCs移植在心肌缺血损伤、肢体缺血、股骨头坏死及神经系统病变等疾病中均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有研究表明,供体年龄增加可通过影响自噬对BMMNCs的旁分泌作用产生负面效果,从而限制了损伤组织的修复[4],提示BMMNCs的治疗效果可能因供体年龄增加而降低。此外,BMMNCs采集步骤较为复杂,操作对供者创伤较大,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1.3 PBMNCsPBMNCs富含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还有少量造血干细胞、内皮祖细胞及MSCs等干细胞群体,但干细胞比例小于0.1%。经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动员的PBMNCs中干细胞比例明显增加,且具备成体干细胞的特点。与BMMNCs相比,PBMNCs的收集方法操作较简便,对供者创伤小且更安全[5]。获取的便利性也便于PBMNCs的重复收集,增加细胞数量,以利于临床应用。
2 MNCs作用机制
在生殖系统疾病中,MNCs治疗作用的发挥可能与抑制细胞凋亡、促进损伤组织的干细胞分化和增殖、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和调节局部免疫微环境有关[6-8]。而细胞归巢和分泌与旁分泌作用可能是其发挥以上作用的基础。
2.1 归巢作用MNCs在发挥作用前需要先归巢至受损区域。趋化因子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 1,SDF1)及其受体CXCR4在归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体内出现缺血或炎症部位后,组织损伤处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alpha,HIF-1α)生成增加,诱导SDF1的表达,SDF1释放入血后,表达CXCR4的MNCs在SDF1浓度梯度诱导下归巢至组织损伤区域[9],从而发挥作用。在早衰的卵巢组织中可以发现经静脉移植的MNCs[10],可能归因于MNCs的归巢作用。体外实验表明,放线菌素相关抗菌肽可增强MNCs对SDF1的趋化反应。Klyachkin等[11]将经放线菌素相关抗菌肽预处理后的MNCs注射至小鼠梗死心肌组织周围发现,与移植未经处理的MNCs的小鼠相比,移植预处理MNCs小鼠的心肌组织微血管形成数量更多,梗死组织瘢痕更少,心脏功能得到了更好地改善。提示经放线菌素相关抗菌肽预处理后的MNCs从病灶周围向梗死灶归巢的能力增强,从而更好地发挥组织损伤修复作用。MNCs移植途径主要包括损伤部位局部注射移植(即原位移植)、静脉移植和动脉移植,不同移植途径可影响其在受损组织的归巢。在浓度相同的前提下,MNCs卵巢原位移植较静脉移植对POF小鼠性激素水平的改善效果更好[10]。提示促进MNCs的归巢更有利于其发挥治疗作用。
2.2 分泌与旁分泌Leal等[12]研究发现,MNCs移植到脑组织7 d后几乎无法在受损组织中检测到MNCs的存在,但损伤组织的恢复并未随MNCs的消失而停止。而血清中抗炎因子水平的升高则提示MNCs可能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参与局部组织损伤修复。研究发现BMMNCs裂解物与BMMNCs对神经的保护作用相似,提示BMMNCs可能通过可溶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发挥作用。生物微胶囊可以为移植细胞提供与受体免疫系统的物理分离和保护作用,同时允许低分子质量营养物质和氧气自由穿过半透膜,是研究旁分泌效应的良好工具。Kieling等[13]将BMMNCs包裹在微胶囊中移植入急性肝损伤大鼠腹膜腔内,发现大鼠存活率提高,提示BMMNCs可能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诱导受损肝组织的修复。对UCBMNCs进行体外培养,可于培养液中检测到抗炎因子、促血管生成因子、神经营养因子及具有趋化活性的蛋白质[14],表明UCBMNCs能够分泌具有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PBMNCs体外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且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hCG)刺激下子宫内膜容受性相关细胞因子白血病抑制因子(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LIF)和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分泌增加,经hCG激活的PBMNCs可促进胚胎植入[15]。以上研究均提示,分泌与旁分泌作用可能是MNCs发挥修复损伤和参与局部免疫调节作用的主要机制。
3 MNCs在生殖系统疾病治疗中的进展
3.1 POFPOF指育龄期女性因卵巢功能减退导致以不孕及绝经前综合征为主要表现的疾病,目前治疗方式多为激素替代治疗以改善相关症状,尚无有效方法恢复卵巢功能。近年来细胞疗法成为治疗POF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注射UCBMNCs至POF大鼠卵巢50 d后血清雌二醇(estradiol,E2)水平升高,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和黄体生成激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水平降低,卵巢中未闭锁卵泡数量增加,并且大鼠紊乱的动情周期得到改善[16]。王毅峰等[10]对比相同浓度的UCBMNCs原位和静脉移植2种途径的效果,发现2种途径均可提高POF小鼠血清中E2、抑制素B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降低FSH和LH水平,减少卵巢组织内细胞凋亡。且静脉移植30 d后在卵巢中依然能发现UCBMNCs的分布,提示经静脉移植的UCBMNCs同样可以到达疾病部位。与原位移植相比,静脉移植对激素水平的改善作用较弱,提示在相同细胞浓度的情况下,不同移植途径对卵巢功能的改善效果存在差异。损伤部位有效细胞浓度的降低可能是静脉移植治疗效果较原位移植差的原因之一。与原位移植相比,静脉移植更易被患者接受,其成本低、创伤小且操作方便,临床应用中可能更具优势。但在目前POF的细胞疗法研究中,原位移植仍是首选。超声引导下经阴道后穹窿穿刺或腹腔镜手术将MSCs原位注射至卵巢中,POF患者血清FSH水平下降,围绝经期主观症状改善,且随访期内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17-18]。若考虑静脉移植,MNCs在其他器官的滞留及影响、对损伤组织的恢复效果及安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除UCBMNCs外,有研究发现PBMNCs也能促进早衰卵巢功能的恢复。El Andaloussi等[19]将PBMNCs通过尾静脉注射至POF小鼠中,观察到PBMNCs可促进小鼠动情周期的恢复,甚至是生育力的恢复;卵巢干细胞相关标志物VEGF、集落刺激因子1、Notch4和抑制素B表达水平增加,提示PBMNCs可能激活卵巢中的干细胞。Huang等[6]将来源于雄性大鼠且经GCSF动员的PBMNCs联合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 plasma,PRP)原位移植至POF大鼠双侧卵巢中,在移植后5 d、10 d 及20 d 均发现了血管生成标志物CD34、抗苗勒管激素及VEGF水平显著升高,卵巢新生血管及原始卵泡数增加,大鼠发情周期得到恢复,并通过检测Y染色体性别决定区(sex determining region of Y,Sry)基因确认了PBMNCs存在于卵巢。这可能是通过促进促凋亡基因B细胞淋巴瘤2相关X蛋白(B cell lymphoma 2 associated X protein,Bax)表达下调和抗凋亡基因B细胞淋巴瘤2(B cell lymphoma 2,Bcl-2)表达上调,减少颗粒细胞凋亡,从而改善了卵巢功能。研究显示联合治疗比PRP或PBMNCs单独治疗效果更佳,提示临床或可采用PBMNCs联合PRP疗法治疗POF。
3.2 宫腔粘连反复严重的宫腔粘连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不利于胚胎着床,可导致不孕症和不良辅助生殖结局。ΔNp63是p53家族中的一员,其上调与低增殖和低分化有关。Zhao等[7]发现BMMNCs与转染了ΔNp63腺病毒的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共培养,能够显著下调子宫内膜上皮细胞ΔNp63 mRNA水平,上调细胞增殖与分化相关标志物如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CCND1)、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雌激素受体α(estrogen receptor α,ERα)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水平。鉴于近年来发现的生物支架在宫腔粘连治疗中的积极作用[20],Zhao等[7]采用自体BMMNCs搭载胶原支架对5例重度宫腔粘连患者进行治疗,发现患者子宫内膜上皮细胞ΔNp63表达下降,CCND1、Ki67、ERα 及IGF1表达增加,并且患者子宫内膜腺体数量及细胞密度增加,局部血流增加,内膜增厚;4例患者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1例患者自然妊娠,最终5例患者全部获得活产。这提示BMMNCs可能通过下调ΔNp63表达促进子宫内膜重建与功能恢复。尽管5例患者均获得了良好的妊娠结局,但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及非随机的试验设计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令人期待的是,该团队注册了一项预计纳入144例受试者的多中心、随机、单盲对照试验,探究搭载胶原支架的自体BMMNCs对严重宫腔粘连患者的治疗作用,以期为MNCs在宫腔粘连中的临床应用提供高质量证据。
3.3 RIF目前认为子宫内膜容受性降低是导致RIF的重要原因,内分泌系统及免疫系统在调节子宫内膜增殖分化、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及促进胚胎植入方面有重要作用。PBMNCs含有丰富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NK细胞等免疫细胞。LIF和整合素αvβ3是评估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标志性分子。研究发现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与PBMNCs共培养的培养液中LIF及整合素αvβ3水平均明显升高[21]。辅助性T细胞1(helper T cell 1,Th1)/Th2细胞的平衡对胚胎的成功种植至关重要。正常情况下,母胎界面Th2细胞占优势,主导免疫耐受的形成。自体PBMNCs宫腔灌注后,RIF患者宫颈管内分泌物中的Th2型细胞因子IL-6水平升高,Th1型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降低。RIF患者经宫腔灌注PBMNCs后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提高[22-23]。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参与了胚胎着床过程中免疫耐受的发生。CRH体外可抑制PBMNCs表达Th1型细胞因子,上调Th2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宫腔灌注经CRH激活的PBMNCs可提高RIF患者的临床妊娠率,推测可能是CRH促进了PBMNCs表达Th2型细胞因子,从而推进母胎界面的免疫耐受的形成,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24-25]。以上研究提示PBMNCs可能通过调节Th1/Th2细胞免疫平衡改变子宫内膜局部免疫微环境,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改善RIF患者的妊娠结局。
hCG同样参与了胚胎着床过程中免疫耐受的形成。宫腔灌注hCG预处理的PBMNCs可提高RIF患者宫腔液中与胚胎种植相关的细胞因子Eotaxin、VEGF及IL-8水平[26]。Yoshioka等[27]的研究发现,宫腔灌注与hCG共培养的PBMNCs(hCG-PBMNCs)可提高有4次及以上胚胎种植失败史患者的新鲜周期胚胎植入率。但当年龄超过40岁时,hCG-PBMNCs对胚胎植入率无明显影响。Qin等[28]的Meta分析表明,于胚胎移植前2~3 d宫腔灌注与hCG共培养48 h的PBMNCs,RIF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可升高,hCG的剂量及PBMNCs的浓度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但该Meta分析纳入的7项研究中仅有1项为高质量的双盲随机对照研究,且不同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高,结论存在一定偏倚。RIF定义中胚胎植入失败的次数并不统一。研究发现,对于胚胎种植失败4次及以上的患者,hCG-PBMNCs能够改善冻融胚胎移植周期的胚胎植入率、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但对有1~3次胚胎植入失败史的患者妊娠结局无明显改善[29]。Okitsu等[30]发现,仅当胚胎移植失败次数在3次或更多次时PBMNCs才能改善RIF患者冻融胚胎移植周期的胚胎植入率和临床妊娠率。同时该研究指出了PBMNCs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可能存在中性粒细胞污染,以及PBMNCs可能产生过量的Th1型和Th2型细胞因子。因此,该研究仅推荐将PBMNCs用于3次及以上胚胎移植失败的患者。以上研究提示,PBMNCs对3次及以上胚胎种植失败患者的妊娠结局有改善作用,对于仅有1次或2次失败史的患者,效果尚不确定。
3.4 其他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相比,人工授精的成功率始终较低。鉴于PBMNCs在RIF中的良好结果,Joao等[31]探讨了PBMNCs对人工授精结局的影响,结果发现PBMNCs并未提高人工授精的妊娠率和活产率,这一结果似乎也印证了部分研究中宫腔灌注PBMNCs对单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妊娠结局无明显改善的结论。
4 结语与展望
目前MNCs在治疗不同生殖系统疾病中的研究进展及侧重点各异。MNCs治疗POF的研究仍处于临床前阶段,原位移植临床操作的不便性、静脉注射疗效及安全性不确切等问题均限制了其临床试验的开展。BMMNCs可改善宫腔粘连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及妊娠结局,但仍需更多研究探讨治疗机制。新型生物支架联合MNCs是治疗宫腔粘连未来可深入探究的方向之一。hCG-PBMNCs对RIF的治疗效果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但需要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指导临床,并且探究可能的机制。外泌体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与血管生成、抗炎、抗纤维化有关[32]。与MNCs相比,外泌体无细胞相关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安全性更高,且无伦理问题。研究表明,从凋亡PBMNCs分离提取的外泌体可促进机体组织损伤的修复,已被证实在心肌损伤、神经损伤及皮肤损伤等组织损伤中发挥修复作用[33]。MNCs来源的外泌体有望在生殖系统疾病中成为新的治疗方法。此外,MNCs联合基因疗法也已获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转染了载有神经营养因子基因的重组腺病毒的UCBMNCs可促进脊髓损伤的恢复[34]。未来或可将重组腺病毒技术联合MNCs治疗用于生殖系统组织损伤,以期获得新的治疗思路。3种MNCs的临床应用特点各有优劣,关于3种MNCs在疗效方面的比较研究暂未开展,未来可探究不同种类MNCs对生殖系统不同疾病的治疗效果及相关作用机制。而且MNCs在应用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治疗不同生殖系统疾病时的移植途径及浓度对效果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