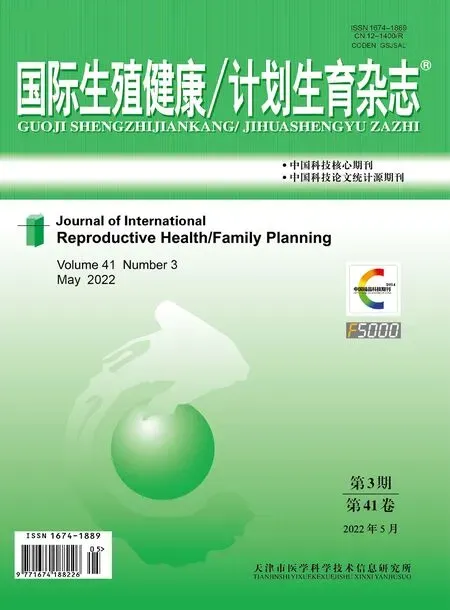蜕膜自然杀伤细胞在反复妊娠丢失中的作用及相关治疗
2023-01-05王璐李洋杜伯涛
王璐,李洋,杜伯涛
2017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将反复妊娠丢失(recurrent pregnancy loss,RPL)定义为连续发生2次或2次以上的妊娠丢失[1]。作为妊娠早期并发症,RPL发生率约为1%~5%,而连续3次及3次以上的RPL患者再次妊娠后胚胎丢失率为40%~80%。近年来多项研究发现,母胎界面免疫环境异常可能是导致妊娠丢失的重要原因。其中,蜕膜自然杀伤(decidual natural killer,dNK)细胞作为妊娠早期母胎界面最丰富的免疫细胞群,在RPL中的作用和治疗价值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就dNK细胞在RPL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及相关治疗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dNK细胞在正常妊娠中的生理和作用
1.1 dNK细胞的来源母胎界面由滋养层细胞、蜕膜基质细胞、免疫细胞以及来源于这些细胞的可溶性因子等构成[2]。其中dNK细胞约占母胎界面免疫细胞的70%,是妊娠早期最重要的免疫细胞[3]。关于dNK细胞的前体细胞及其具体分化过程仍无统一定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3种观点:外周血募集、造血祖细胞分化和外周血CD16+NK(CD16+peripheral natural killer,CD16+pNK)细胞转化。2008年Carlino等[4]证实CD16-pNK细胞与蜕膜基质细胞相互作用时,可表达高强度的CXC趋化因子受体4(CXC chemokine receptor 4,CXCR4)。CXCR4通过与CXC趋化因子配体12(CXCL12)结合被招募到蜕膜。随后,研究发现存在于蜕膜中的CD34、CD122和CD127造血前体在体外与蜕膜基质细胞共培养时可分化为dNK细胞[5]。此外,CD16+pNK细胞在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迁移到子宫组织中,并局部分化获得dNK细胞表型[6]。
1.2 dNK细胞的独特表型和表面标志物pNK细胞根据CD56表达的不同可分CD56dimCD16-表型(占90%)和CD56brightCD16-表型(占10%)。与pNK细胞不同,dNK细胞表达CD56+/brightCD16-和CD56+/dimCD16+。在表面标志物方面,dNK细胞除可表达许多典型的NK细胞标志物(NKG2A、NKG2D和NKp46)外,还可表达组织驻留的标志物(CD49a、CD69和CD94)。这种独特的表型和标志物构成了dNK细胞分布和生物学功能的基础。
1.3 dNK细胞的作用
1.3.1 子宫螺旋动脉重塑 为了满足母胎界面稳定和胎儿的生长需要,绒毛外滋养细胞(extravillous trophoblasts,EVT)重塑子宫螺旋动脉。在重塑过程的最早期,内皮细胞空泡化,个别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肿胀[7]。dNK细胞分泌趋化因子促使大量免疫细胞与蜕膜细胞聚集到螺旋动脉周围,如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可能通过母系表达基因3(maternally expressed gene 3,MEG3)途径介导VSMC的初始破坏,促进血管壁变薄、管腔扩张及血管阻力减小[8]。随着重塑过程的推进,dNK细胞和EVT诱导的细胞外基质的破坏介导子宫螺旋动脉重塑过程中血管平滑肌层的破坏和丢失,最终重塑动脉的VSMC发生凋亡。
1.3.2 参与母胎界面免疫耐受 第一,dNK细胞能够识别来源于母系和父系的异种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C,HLA-C)入侵EVT,并刺激分泌IFN-γ,提高CD14+dNK细胞表达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1,IDO)[9]。IDO是降解色氨酸的关键酶,其介导的色氨酸分解代谢产物L-kynurenine可以促使CD56brightpNK细胞向低毒性的dNK细胞转化,从而为建立母胎界面免疫耐受提供了良好的免疫环境。第二,在妊娠早期,蜕膜巨噬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15(interleukin-15,IL-15)激活dNK细胞,使其与蜕膜巨噬细胞协同抑制T细胞活化和妊娠早期免疫反应[10]。第三,CD16+dNK细胞亚群通过分泌IL-10选择性抑制IL-2、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FN-γ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等细胞因子的合成[11],从而抑制母体对同种异体抗原的免疫反应,参与母胎界面免疫耐受的调节。
1.3.3 对滋养细胞侵袭起双向调节作用 一方面,滋养细胞表达的HLA-C、HLA-E和HLA-G可与dNK细胞抑制性受体(LILRB1、KIR2DL4和CD94/NKG2A)相互作用,促进滋养细胞侵袭。dNK细胞还可以通过产生趋化因子与滋养细胞相应表面受体结合,如IL-8与CXCR1、IL-10与CXCR3,以达到促进滋养细胞侵袭的作用。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证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和VEGF-C分别与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1,VEGFR-1)和VEGFR-3结合后可抑制滋养细胞的侵袭[12]。dNK细胞通过控制EVT侵袭深度、维持EVT侵袭的稳定,保护母胎界面免疫微环境。
1.3.4 记忆功能 与初次妊娠女性相比,在多次妊娠女性蜕膜中观察到更深更早的血管内滋养细胞浸润,提示dNK细胞在多次妊娠中胎儿、胎盘的有效发育存在“训练”或“记忆”免疫[13]。研究者在多次妊娠妇女蜕膜组织中发现了以NKG2C和LILRB1高表达为特征的蜕膜“记忆”NK细胞,称之为PTdNKs细胞。其中,NKG2C与HLA-E、LILRB1与HLA-G相结合在IL-5的介导下可诱导分泌更多的IFN-γ和VEGF-A[14]。PTdNKs细胞的记忆功能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先天记忆,且已被证明是对外界环境或病毒感染的反应,以及对细胞因子诱发的记忆。
2 dNK细胞在RPL中的病理和作用
基于dNK细胞在妊娠早期母胎界面免疫微环境中独特的生理作用,其在相关病理妊娠尤其是RPL中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
2.1 亚群和表型的改变2020年El-Badawy等[15]通过刮宫收集蜕膜标本,发现RPL患者CD56dimdNK细胞的百分比显著高于CD56brightdNK细胞。在不同的CD56dim亚群中,CD56dimCD16-dNK细胞是主要亚群,其次是CD56dimCD16dim和CD56dimCD16brightdNK细胞。而且这些CD56dim亚群的数量与既往妊娠丢失时间相关:当CD56dimCD16-亚群数量增加、CD56dimCD16dim亚群数量减少,既往早期妊娠丢失数量增加;当CD56dimCD16dim亚群数量增加、CD56dimCD16-亚群数量减少,既往晚期妊娠丢失数量增加。研究推测,这种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反复早期妊娠丢失的患者中,高细胞毒性CD56dimCD16brightdNK细胞过度激活,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介导CD16的表达丢失,导致CD56dimCD16-dNK细胞增加、CD56dimCD16dimdNK细胞减少。而反复晚期妊娠丢失的妇女中,CD56dimCD16bright的dNK细胞毒性较低,CD16丢失较少,从而CD56dimCD16dimdNK细胞增多、CD56dimCD16-dNK细胞减少。因此,CD16表达的丢失可能与妊娠持续时间相关,CD16丢失越多妊娠持续时间越短。
2.2 受体表达和细胞活性的改变既往研究指出,与健康人群相比,RPL患者的dNK细胞受体表达水平发生改变,影响dNK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第一,RPL患者dNK细胞高表达CD161+。CD161+的高表达可增加NK细胞分化过程中对促炎细胞因子IL-12和IL-18的反应,并在刺激后使NKp30、CD160、CD25(部分高亲和力的IL-2受体)和CD69产生增多[16],进而增强dNK细胞活性。但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反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RPL患者dNK细胞中CD161水平低于正常妊娠女性。在妊娠早期,滋养细胞可通过CLEC2D(NK细胞受体CLR的编码基因)与dNK细胞的CD161相互作用,抑制dNK细胞的细胞毒性,促进母胎界面免疫耐受的建立。RPL患者CD161表达水平下降可导致dNK细胞毒性增强[17],从而导致RPL的发生。第二,KIR可分为激活性和抑制性受体。在RPL患者中发现,dNK细胞表达的激活性受体KIR2DL4增多,抑制性受体KIR2DL1降低[18]。说明激活性与抑制性受体比例失衡可过度激活dNK细胞的活性,使妊娠所需母胎界面免疫环境失衡。第三,在RPL患者的蜕膜组织中观察到NKG2D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19]。推测可能是RPL患者的dNK细胞在与激活性受体NKG2D相结合的作用下,激活性信号过度传导,刺激dNK细胞异常激活,活性显著增加的dNK细胞可杀伤自身其他细胞甚至胚胎,引发RPL。此外,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RPL患者dNK细胞受体ILT-2、ILT-4 的mRNA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妊娠女性、ILT-2分布密度低于正常妊娠女性、ILT-4在蜕膜局部表达水平低下[20]。ILT-2与HLA-G结合后促进dNK细胞分泌炎性因子和血管生成因子,受体ILT-4多表达于免疫细胞表面。这说明dNK细胞受体ILT-2和ILT-4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dNK细胞功能,其水平低可导致妊娠早期母胎界面免疫环境紊乱,影响妊娠结局。
2.3 细胞毒性和功能的改变Li等[21]发现RPL患者的dNK细胞CD49a水平较低,穿孔素、颗粒酶B和IFN-γ表达水平较高。CD49a可抑制dNK细胞早期黏附和向滋养细胞迁移,并通过下调穿孔素、颗粒酶B和IFN-γ的表达来限制细胞毒性。这表明RPL患者中dNK细胞的细胞毒性高于健康人群,高毒性的dNK细胞的正常血管生成功能减弱,促炎功能增强,滋养细胞的耐受能力明显降低,这破坏了母胎界面免疫微环境的稳定,导致RPL的发生。另外,当dNK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数量发生改变,会影响dNK细胞的促滋养细胞侵袭和血管重塑功能。一项研究通过检测细胞因子分泌谱发现,RPL患者蜕膜组织的IL-8和IP-10水平高于正常妊娠的对照组,而VEGF水平低于对照组[22]。接着Transwell实验证实RPL患者dNK细胞与转染微小RNA(miR-133a)模拟物在滋养细胞HTR-8/SVneo共培养时诱导HLA-G表达降低,dNK细胞与KIR2DL4结合时的分泌能力下降,细胞因子的减少可能会影响滋养细胞的侵袭和子宫螺旋动脉重塑。这为RPL致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dNK细胞亚群、受体表达水平及细胞功能异常之间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最终可能导致RPL的发生,这就为此类RPL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
3 dNK细胞相关的RPL治疗研究进展
3.1 丙种免疫球蛋白与脂肪乳静脉滴注丙种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G,IVIG)是一种被动免疫治疗,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最终改善免疫异常RPL患者的妊娠结局。IVIG主要影响辅助性T细胞1(helper T cell 1,Th1)/Th2细胞比值,促使平衡由Th1细胞向Th2细胞转变,上调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细胞)水平,进而发挥免疫保护的作用。研究发现IVIG还可以通过增加NK细胞抑制性受体表达,抑制NK细胞的溶解活性,减少NK细胞数量并降低其细胞毒性,进而改善RPL患者的妊娠结局[23]。但IVIG在临床应用中不良反应较多且价格较贵。近年来,静脉滴注脂肪乳成为IVIG的一种替代方案。Lédée等[24]研究将IL-15/成纤维细胞生长诱导因子14(fibroblast growth factor-inducible 14,Fn-14)比值作为dNK细胞活化的标志,高IL-15/Fn-14比值提示IL-15过度激活dNK细胞;将IL-18/肿瘤坏死因子样弱凋亡诱导剂(tumor necrosis factor-like weak inducer of apoptosis,TWEAK)比值作为Th1/Th2免疫调节平衡的生物标志,IL-18/TWEAK比值越高,提示局部Th1越多。结果发现经过脂肪乳治疗后RPL患者IL-15/Fn-14和IL-18/TWEAK比值显著下降,CD56+dNK细胞的动员减少,在妊娠初期过度活化的dNK细胞的比例也趋于正常。说明脂肪乳通过减少dNK细胞募集和下调Th1促炎细胞因子抑制dNK细胞的过度活化,调节dNK细胞功能并促进滋养细胞侵袭,平衡母胎界面的免疫耐受。
3.2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G-CSF是一种由免疫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多项研究发现G-CSF受体可存在于胎盘、细胞滋养层细胞、合体滋养层细胞和蜕膜基质细胞等母胎界面的细胞。G-CSF通过募集dNK细胞下调IFN-γ和IL-18等细胞因子的产生,降低dNK细胞的毒性,诱导母胎界面免疫耐受[25]。现临床上G-CSF的给药方式分皮下注射和宫腔灌注2种,宫腔灌注多用于慢性薄型子宫内膜患者,而RPL患者多选皮下注射。Kamath等[26]分析了13项研究共1 050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其中522例给予皮下注射G-CSF治疗,528例给予安慰剂或不接受额外治疗,结果表明在2次或2次以上移植失败的患者中,皮下注射G-CSF可提高临床妊娠率,降低流产率。但该研究没有关于活产率的报告,并且数据有限存在偏倚风险,有待大量研究进一步证明G-CSF的确切效果。
3.3 糖皮质激素不同糖皮质激素对NK细胞的作用存在差异。地塞米松可增强由IL-2和IL-12刺激的dNK细胞增殖,提高CD16+dNK细胞占比,CD94/NKG2A的表达水平增加,改善dNK细胞的线粒体功能,增强dNK细胞活性。强的松通过减少dNK细胞数量、下调细胞因子的产生,减少dNK细胞的募集。一项针对强的松治疗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的Meta分析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强的松能显著提高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有效降低流产率[27]。但仍有研究认为强的松治疗并不能改善反复移植失败患者的妊娠结局,关于强的松具体作用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3.4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MSC是一种多源性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基质细胞,多用于自身免疫性相关疾病的治疗。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MSC可以通过细胞间相互作用和分泌多种细胞因子,抑制NK细胞、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活性,发挥免疫调节作用。Rezaei Kahmini等[28]对有流产倾向小鼠在妊娠第4天或第5天腹腔注射脂肪来源的MSC,然后分离孕鼠蜕膜细胞,分析dNK细胞不同亚群的比例以及IL-10、IL-4和IFN-γ的水平。结果显示,治疗前有流产倾向小鼠CD49bright+dNK细胞比例增加,IFN-γ的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小鼠,而IL-4和IL-10水平无明显差异。经MSC治疗后流产倾向小鼠CD49bright+dNK细胞群减少,IFN-γ的表达水平降低,IL-4和IL-10的表达水平升高。提示MSC可以通过改变dNK细胞的不同亚群比例及其细胞因子水平,调节Th1和Th2型细胞因子的平衡,维持母胎界面的免疫微环境稳定。但文献中并未提及有流产倾向小鼠模型的妊娠结局,还需大量研究进一步证实并评估其安全性。
3.5 枸橼酸西地那非(sildenafil citrate,SC)SC可通过抑制环磷酸鸟苷(cyclic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的降解增强一氧化氮的血管扩张作用,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改善子宫血流灌注,临床上多用于因薄型子宫内膜而导致妊娠失败的患者。目前还发现SC能通过产生细胞因子和改变Treg细胞的比例来降低NK细胞活性。Kniotek等[29]研究发现,健康女性月经周期第16~25天的外周血单核细胞经SC处理后,TGF-β和IL-10的水平显著升高,IL-12的水平显著降低。IL-12是Th1形成和增殖过程中重要的细胞因子,通过增强有细胞毒性的细胞因子分泌促进NK细胞活化,增强NK细胞的杀伤毒性。TGF-β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可协同IL-10降低NK细胞活性。因此,SC可以通过提高抗炎细胞因子、降低炎性细胞因子分泌水平,进而降低NK细胞活性。该团队另一项研究将24例健康女性和23例RPL女性的pNK细胞转化为诱导蜕膜NK(idNK)细胞(与dNK表型及功能相似),经SC处理后观察idNK细胞抑制性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的变化,结果发现与健康女性idNK细胞相比,RPL患者idNK细胞中KIR2DL1表达降低[30]。说明SC可降低RPL患者抑制性受体KIR2DL1表达,减弱idNK细胞毒性。但目前关于SC是否影响dNK或idNK细胞功能及其受体的研究较少,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证实。
3.6 西罗莫司(Sirolimus)西罗莫司是一种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rapamycin target protein,mTOR)抑制剂,通过抑制IL-4和IL-2分泌阻止B细胞和T细胞的增殖,同时还可促进CD4+CD25+Foxp3+Treg细胞的生成,抑制外周血中Th17细胞的分化。Ahmadi等[31]研究发现,与不接受西罗莫司治疗的反复种植失败患者相比,接受西罗莫司治疗的反复种植失败患者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后的妊娠率和活产率提高。此外,西罗莫司还是一种自噬诱导剂。滋养细胞自噬可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2,IGF-2)的分泌,进一步抑制dNK细胞分化[32]。因此,西罗莫司能通过诱导滋养细胞自噬和抑制免疫反应降低dNK细胞的活性及毒性,对滋养细胞自噬水平低的免疫性流产有一定的治疗价值。
4 结语与展望
目前仍未找到RPL的特异性病因和特效的治疗方案,但免疫因素与大多数的妊娠失败密不可分。dNK细胞作为早期妊娠母胎界面中数量最多的免疫细胞,可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及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参与母胎界面免疫耐受的建立,重塑子宫螺旋动脉,促进滋养细胞侵袭,维持妊娠的稳定。当dNK细胞的数量过度增加,活性和毒性提高导致功能异常,破坏了母胎界面的免疫微环境,可导致RPL。但dNK细胞通过哪些信号通路和受体引起数量及功能的改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以期为RPL的机制研究和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