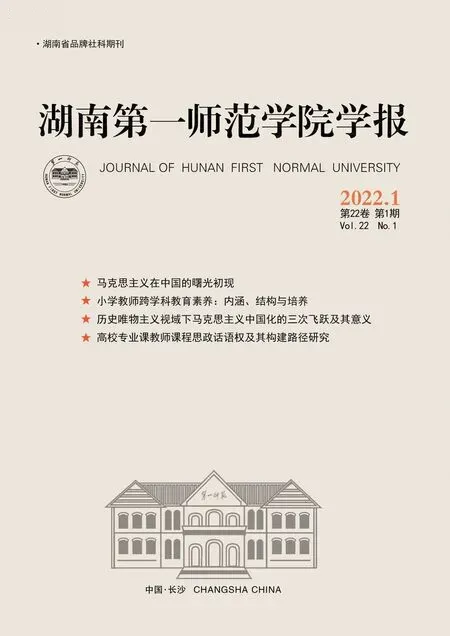数字生活中儿童“童年消逝”的隐忧与应对
2023-01-05代苗雪戴兰芳
代苗雪,戴兰芳
(1.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培训部,安徽 合肥 230022;2.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湖南 长沙410205
一、童年的价值及其消逝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只有一次。童年对于儿童个体成长意义重大,许多教育名家都曾给出阐释。萧伯纳说过:“童年时代是生命在不断再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类正是在此种不断的再生过程中才得以永恒生存下去的。”[1]夸美纽斯将儿童看作为“上帝的种子”[2],他们在这一阶段具备着促进自身得以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以及保持这种发展的无限潜力,亦即童年是通往“和谐发展”人生的必要前奏。卢梭则在《爱弥儿》中鲜明地确认了儿童童年的价值,他宣称儿童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独自存在[3],儿童应当具备独立于成人世界的精神世界与个性需要,使重视儿童并尊重儿童的诉求得以用适当的确认……儿童的童年之于人最基始的意义在于“儿童创造了成人,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童年的价值应当在人走向成长、成熟与成才的过程中获得社会各方的关切与保障。换言之,儿童的童年有充沛理由应当得到坚定的守护。然而,这种具有强烈现实意义指向的诉求,却依然有着难以革除的愿景性——因为,现实中许多儿童的童年境遇并不乐观,其童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我们的儿童依然笼罩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忧之下:童年正在消逝!
童年消逝,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媒介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于1982 年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所提出的。在整本书中,“童年”主题贯穿始终,旨在探究它在媒介变迁过程中的起源、发展及消逝,并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视角来进一步阐释现代儿童“童年”的境遇。他强调,电视媒介的应用普及使其承载的“大众文化”不断下移与沉淀。如此一来,所有的大众文化(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流通与共享,“图像革命”正在或已经进行,信息传播方式以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具体和通俗易懂为主要特点,儿童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通往成人世界的“通行证”,进而窥探成人世界[4]。许多儿童几乎是以一种被迫的方式提前介入和参与到成人世界所充斥的战争与暴力、性爱与伪善、虐待与杀戮;儿童过早习得大人的穿着与装扮,响应并践行成人的美学主张;追随与盲从大人的处世法则,变得愈加“娴熟老练”;“老态龙钟”的小大人越来越多,等等。这种由信息媒介传播技术的普及应用所带来的童年与成年之间界限的模糊,使得现代意义上美国儿童的童年正在不断消逝。由此,波兹曼无奈地发出“失乐园”一般的哀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5]。
显而易见,“童年消逝”这一概念并非针对的是生理年龄意义上的生物群体或个体的某个生长阶段或者发展周期的不复存在,并不只是片面地感叹“童年”在成长过程中“时间”要素的纵向流逝,而是基于“精神、文化与价值”层面的视角切入,透过儿童在通过接触媒介来窥探成人世界后所发生的负面变化,诸如儿童的个体属性“语言、行为举止、趣味、精神面貌与道德水平”等等一系列趋离儿童本色的负面变化,来作为判定儿童的童年何以消逝的标准。在这种话语体系里,童年的概念进一步被明确地界定,其基本的范畴与样式日渐清晰。
波兹曼关于“童年消逝”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当下的中国儿童的境遇。因为,我们的儿童正快速地步入到一个以网络为主要媒介编织而成的数字生活世界中,他们不断地穿梭于网络的虚拟镜像世界中,浸染在现实情境与虚拟网络的模糊界限里,在享受着网络世界的视听盛宴中自我陶醉。与一开始处于电视时代的美国儿童相比,中国的儿童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更为通畅、深入与广泛的渠道去接触“成人世界”,网络媒介所承载的大众文化的体量、种类与传播力是电视媒介远远无法比拟的。如此一来,若秉持同样的立场从“精神、文化与价值”层面来审视当下的中国儿童,则会发现许多童年的“语言、行为举止、趣味、精神面貌与品质”等等一系列标示儿童底色的个体属性在网络镜像的负面冲击下正产生的深刻蜕变,儿童的童年价值正被剥离,越来越趋离于完满童年的理想愿景,童年消逝的隐忧日益沉重。
二、数字生活中儿童“童年消逝”隐忧的具体表现
对儿童而言,其完满的童年时光应当是充实而有意义的,儿童对其支配的时间有效利用,以彰显出其童年的时间价值;儿童的精神生活应当是内容丰富且又积极向上,身心愉悦,富有真实的童趣;儿童的道德品性也应当符合其成长相应阶段的规律,始终保持昂扬向上而非坠落下滑,以展现儿童符合其年龄阶段应有的童真……然而,在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构筑起的虚拟镜像下,儿童童年的时间价值、童趣与童真等要素似乎正在慢慢地受到侵蚀与剥离。
(一)“过度操作”的网络媒介侵蚀儿童的时间价值
时间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纵观人类发展的进程,生命本身一度只与时间有关,人的生命的本质与价值只能从时间里把捉[6]。为此,在“时间”的视域下探讨儿童的童年不失为一个理解儿童的突破口。童年正是人由儿童在走向成人过程中阶段性的时间标注,指向儿童生命本质与价值的完满童年“生活大厦”的营造也自然就离不开儿童对其自身所支配时间的利用——将童年的时间价值发掘到最大限度。对儿童的完满童年而言,时间价值的凸显则应当表现为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能够成就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事物当中,避免将过多的时间投入到不符合其自身实际发展需要的事物当中。然而,审视处于网络镜像下的当代儿童,网络媒介的过度操作正侵蚀着儿童时间价值的发挥。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接触和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慧游戏机等网络媒介进行社交、听音乐、游戏等活动,“数字原住民”的规模正不断地壮大。根据共青团发布的《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69 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7]。儿童的“未成年属性”决定了其身心发展的未完成性与不成熟性,这导致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对于这种新事物普遍缺乏自制力,导致其时常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据某调查显示,各学龄期青少年网民每周上网时长为26.7 小时,其中,小学生网民每周上网时长为14.4 小时;中学生网民每周上网23.7 小时;看视频和玩游戏是其上网最主要的目的,有些学生甚至整日沉浸在网络世界中,以致荒废学业[8]。时间是儿童童年的基本附属品之一,能够让儿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对于其本身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这也是童年完满的一种必要的保障。但是,理想的童年状态下,这种时间支配必须是有意义的,即时间必须花费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将时间的内在价值尽量延展。反观当下,许多儿童依然在无节制地操作网络媒介工具,耗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这与建构完满有意义的童年的理念背道而驰,使儿童在无形之中陷入一场危机,透支了童年的时间支票,剥夺了其童年时间的应有价值。
(二)“饶有趣味”的虚拟世界催使儿童的精神沉溺
童趣,是儿童完满的童年精神生活的体现,是儿童天性中喜好游戏、追求纯真快乐的本性[9]。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儿童的童趣主要来源于自然,它是与自然紧密贴合,在真实的自然情境中不断地接触、探索与体验其中蕴含的乐趣,获得身心的愉悦。以往,陪伴儿童的是一串串可用肢体表达的诸如“抓知了、跳绳、赛跑、摸泥鳅、穿过田野与丢沙包”等亲近自然的活动情境,儿童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亲近自然的体验中尽情寻找童年的乐趣,自然地稀释着儿童成长的精神烦恼,精神生活丰富又充裕。而如今,在“互联网+”的号召下,以“长宽高+时间”为代表构成的现实空间的事物已经渐渐向以多维虚拟性为特征的网络空间大挪移,使得两个空间的重合度变得越来越高,并由此催生出很多带有“趣味”的新生事物——如“线上游戏、影视与音乐等等”,不断吸引着儿童“流连忘返”[10]。儿童获得“童趣”的主要场域逐渐由现实中的自然世界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其中,以最能展现和释放儿童童趣的载体——游戏为例,正如胡伊青加在《人:游戏者》一书中所主张的:人都是游戏者,儿童更应是游戏的存在。但在网络镜像下,游戏的虚拟化改变了儿童接收游戏的来源与方式,虚拟化的游戏以其承载的“趣味性”不断受到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儿童的青睐。比如,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凭借其简单易上手、充满趣味、黏性强等特点,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小学生爱不释手,使得一些学生整日沉溺在游戏的虚拟世界当中[11]。当儿童对这种从虚拟世界中获得“趣味”所建立的依赖感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足以使其蜕变成难以革除的“精神沉溺”,引发诸如“因玩‘王者荣耀’被骂,13岁学生从四楼跳下”、“有学生与队友组队开黑40小时,险些丧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事实上,游戏的虚拟化超脱于现实自然情境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割裂了儿童精神生活与自然的某种联系,导致许多儿童离现实中真实的游戏越来越远,不再有单纯的游戏存在,最终催使儿童不断地趋离于真实的“童趣”,其损害的正是儿童完满童年本应内嵌的生活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儿童童年的消逝。
(三)“纷繁莠杂”的网络讯息加剧儿童的童真迷失
童真是儿童质朴善良的道德品性的彰显,融合着同情心与怜悯心的真性情,是其简单、直接思维的表露[9]。正如洛克所言,人出生时如若一块白板,具有天真又纯洁的心灵[12]。这也就意味着,童真应当是每一位儿童都与生俱来,难能可贵的品质属性。完满的童年离不开宝贵的童真,也不可能在一种缺失童真的状态下孤立存在。换言之,宝贵的童真构成了儿童完满童年的基本要素,也有充分理由以童真的缺失程度当作判定标准来检视儿童童年的完满状态。对儿童个体而言,童真的迷失便预示着其完满童年的消逝。然则,处于网络镜像中的儿童的童真时常遭受“纷繁莠杂”的网络讯息的威胁,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不断加剧着儿童的童真迷失。现实中,在互动、共享、开放与多元的网络媒介平台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媒介数据与内容,暴力、色情与低俗等有害信息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几乎随处可见。网上“纷繁莠杂”信息接收和传播的隐蔽性,网络虚拟世界里人际关系的随心所欲,信息交往的畅通与随意性,以及无需承担责任和免遭惩罚的特点,很容易使我们的儿童深陷其中。心理学家班杜拉就曾指出,儿童的童年时常是在模仿中度过的。对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认知能力有限,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儿童而言,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很容易让其产生类似的模仿举动,包括行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他们会模仿,会习得,并建立起与其不相协调的错误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在此引导下付诸错误行动。“在距离独立生活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知道了金钱和权力的重要,他们在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社会矛盾,甚至不知道社会是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了战争、暴力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精神发展上的畸形化,磨损了其纯洁的善良品性”[13]。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必然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进一步加剧儿童的童真迷失。
三、化解儿童“童年消逝”隐忧的应对进路
网络镜像下的许多儿童,其童年正如一块日益风蚀沙化的绿洲,童年的边缘正在慢慢缩小。童年消逝的隐忧代表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关乎童年价值的危机。对此,还给儿童自然天成的童年,捍卫童年的底色,或者说阻止童年的消逝,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对此,基于现实的考量,厘定“童年消逝”的网络责任,可以从网络媒介环境、外部监督、媒介素养教育以及回归“自然”生活等角度着手应对。
(一)构筑“净化网络媒介环境”的首要防线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宏观来看,“污浊、混乱、有害”的网络环境并不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也有悖于现代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而具体落实到儿童发展的维度,审视网络镜像下儿童童年消逝的遭遇,负面的网络环境已然阻碍了儿童完满童年的实现,催使儿童沉溺于虚拟世界,在“纷繁莠杂”的网络讯息中迷失童真。站在儿童的立场,儿童的完满童年的实现离不开一个“风清明朗”的网络时空环境。尽管,对于净化网络媒介环境的呼吁其实早已成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识,但现实情况依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有必要重申“净化网络媒介时空环境”这一立场,切实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一同构筑起捍卫儿童完满童年的首要防线。针对儿童童年消逝的实际情况,净化网络的治理工程必须以整治网络媒介内容为重点,以剔除和改造容易对儿童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产生负面价值导向的“污浊、混乱、有害”等网络资讯与数据;必须以控制和切断不利于儿童发展的网络文化、资讯等数据的源头和传播渠道为切入点,防止相关负面资讯大肆传播;以继承、创造与弘扬网络优秀文化为主抓手,引导儿童积极认同、汲取优秀网络文化的营养价值,等等。从长远来看,净化网络的治理工程确非一朝一夕之易事,而是需要依靠全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与持续推动。这其中既依赖于网络主管部门的有力监管、网络文化产品和内容(包括游戏、视听、网络出版等作品)创作者的正面引导、传播与载入平台的有效审核,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与正面舆论的确立。
(二)强化儿童操作网络媒介的外部监督
作为尚未完全独立的个体,多数儿童并不具备可以规划和节制自己使用网络的时间和频率意志力,缺乏抵抗虚拟世界的精神沉溺的行动力,更欠缺分析、甄选“纷繁莠杂”的网络讯息的辨别力。这表明,儿童的未完成性与不成熟性的阶段特征决定其并不具备足以抗争来自网络负面干扰的力量。为此,落实与强化儿童操作网络媒介的外部监督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一举措的核心要义在于“监督”,即基于一种“儿童自制力、审辨力薄弱”预设前提,引入适当的外部力量的强制干预,对某些对象实施不确定性的监督。首先,坚持儿童使用网络媒介“适度、适时、正当”的基本原则,不可任由其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等媒介工具进行无节制的操作,要善于引导儿童使用网络的动机,在观察中制止其不合理的网络行为,并通过说服教育、适当惩戒等形式予以及时矫治。其次,严格划定儿童不宜使用网络媒介的时空场域。例如,严禁儿童携带非正当用途、具有娱乐性质的网络媒介工具进入课堂;强化与落实“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络经营场所的规定等。再者,探索采用更多的技术性手段实施监督。以手机游戏为例,可以建立起对于未成年人用户的审查与识别机制,提高儿童进入游戏的准入门槛,落实手机游戏注册实名制,并且对于未成年人用户的游戏时间加以严格的限制。而其他的如视听、交友等软件和平台也可以参照制定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督手段,从技术上入手,防止其过度操作而沉溺其中。但“外部监督”如同治水所采取的堵塞之策一般,依然只是辅助手段,并不能起根治效应。
(三)推动和改进儿童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网络社会的语境下的儿童是社会公民的一种主体存在,其以主体身份知悉、参与并融入网络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儿童童年的生活选项。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成人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单靠媒介工具种类单一限制来阻断与控制住儿童对外部信息的汲取和知晓,或者说采取对某些信息的强制封锁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儿童“纯真”心灵和天性[14]。儿童自身也不可能“因噎废食”割裂网络赋予的身份角色从而排斥和拒绝一切网络生活。儿童美好的网络生活既需要为其提供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更重要的是应当推进儿童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使其具备和表现出较高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目的在于造就出具有较强批判能力、能独立思考媒介信息的优质网络社会公民[15]。对儿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一大意义在于,提升其自我认同能力,即使其能够区分虚拟和现实、个人和世界的关系,认识媒介价值和自我价值,懂得自我价值不应为媒介所主导。在理性正确对待网络媒介信息的基础上,降低对网络媒介的依赖程度,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与抵制意识,合理规划好自己使用网络媒介工具的频率。深入推进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这是对儿童在网络镜像下化解童年消逝隐忧的内在要求。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同样需要整合各方力量,依托学校、社会、家庭多方协同推进,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为此,学校应当依托课堂积极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培育儿童媒介素养课程,将正确的媒介素养观念教导于学生。社会要创设良好的媒介环境,以良好的媒介氛围感染学生。家庭同样应当肩负起相关的引导责任,言传身教,自身要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在教养中提升儿童媒介识读能力,让儿童切实强化自身的媒介素养。
(四)善于引导儿童回归“自然”生活
网络并不可能成为儿童童年生活的全部,指向其完满童年的生活也不应当完全蜕变为网络虚拟世界的集合,他们需要在网络之外寻求到更为广阔的精神生活世界,回归到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活中去。在“自然”中观察、想象、体验生活,寻回童趣,守护童真,表达自我,这是捍卫童年的应有之义。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儿童回归“自然”生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儿童自然地与生长着的自然万物“交流”,弥补网络镜像下现代儿童的“自然缺失症”。这种“交流”并非是卢梭笔下所强调的在“大自然”中生存与生活,而是善于利用有限的生活条件或者尽量创设条件来引导儿童去接触自然,聆听自然的声音,捕捉自然的呼吸。来自大自然的游戏、风土人情、隽丽美景与诗情画意等都是对儿童最真的自然陶冶,是丰富儿童童年生活的自然成分,是培育其完满童年精神的宝贵载体;二是引导儿童对健康的自然生活理念的践行。我们必须为儿童创设良好的环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更多的健康有益活动,让其从户内走向户外,由线上走向线下,充分地让学生体会到童年的快乐。比如,保障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合理地控制学习负担,让学生真正的有时间玩耍与嬉戏;开展形式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能够体会到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快乐,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家长应当重视亲子关系的建设,身体力行,增强亲子双方的交流与对话,多与学生接触沟通,尊重学生合理的成长需求,创设条件让学生多亲近大自然等等。通过创设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使其逐渐转移和稀释对网络媒介的过度依赖,以一种自然的形式化解这场童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