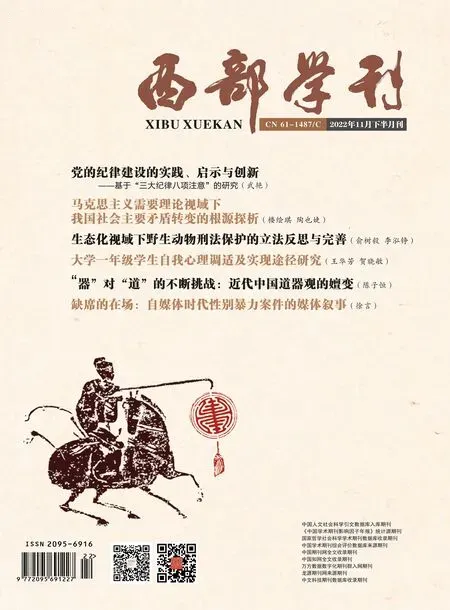“器”对“道”的不断挑战:近代中国道器观的嬗变
2022-12-31陈子恒
陈子恒
随着西方事物在近代大规模传入中国,时人对西方事物的认知以及是否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并展开了激烈的探讨,不但在一段时间内对社会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学术思想史财富。其中有一定价值但较少有人展开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中国道器观的发展嬗变,笔者尝试初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器之辨”
自“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提出“道器之辨”后,“道”与“器”这一对概念就相伴而行。“道器之辨”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展开的讨论不计其数。笔者仅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中的“道器之辨”之演变做一简要梳理。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提出了“道先器后”说,而“忽然而生”之说难以有力保证和维护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2]。这样的道器观无论在学理基础上还是现实作用上均有难以弥补的缺陷,因此其活力亦非常有限。
及至宋明,朱熹兼取张载的气本原论和二程的理本论,形成了理本体论哲学范式,将描述“道器”关系的形上形下之分用于区分“理气”,道器关系不再是时间生成上的先后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即“道体器用”说。之后,理学愈加存理遗人,而心学及至阳明后学也逐渐沦为空谈心性[2]。
适逢明清巨变,知识分子反思宋明理学之弊,王夫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卓越的创建。他从现实出发,强调“器”的优先性,有器方显形上之道。“治器”、践行、事为都是人的动态历史过程,故而“道”也处于动态变化中,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因时而万殊”,“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3]王夫之的道器观开启的是一个开放、求新、尚变的价值取向。他对道器的区分,不是时间上、空间上和逻辑上的区分,而是从人的生存和践行活动出发给予的命名区分。“器”在生存论范式下其真实性得到肯定,并取得优先的地位,而“道”则在人的“治器”实践活动中显现,并随着这一活动过程而趋时更新,故王夫之的道器观可概括为“治器显道”说[2]。可见“器”的地位在王夫之这里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
船山①之后,对“道器之辨”的诸多阐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学诚的“道器合一”说。章学诚在还原六经②原貌的同时,形成了“道器合一”的观点,并与“六经皆史”联系起来。六经是载道之书,先王之道借由六经所载典章事迹而使人知,六经是载道之器[4]。“道”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时代,“道”的含义也不同,所以需要后世随时撰述以彰显道的不同样貌。“道器合一”是“六经皆史”的重要理论基础,厘清道器关系为“六经皆史”说提供了有力论据支撑。其说之影响不仅在于治史,更在学术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道器之辨”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虚入实的过程:孔颖达“无形生有形”之说将道器关系引入虚幻,让人难以捉摸;朱熹以“理”与“物”论“道”与“器”,将“道器之辨”由虚幻引入抽象,视“道”为“体”,“器”为“用”,更重“理”即“道”;王夫之则更重视人在生存与践行活动中与“器”的种种关系,强调“器”的优先性即强调人“治器”之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治器”方能“显道”;章学诚在“六经皆史”说中强调“道器合一”,治学的目的是明道,但治学本身及其对象都是“器”,道器不能分离。由此可见,“器”之地位愈加得到肯定与重视。但必须指出,这样的道器观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相对独立情况下的发展脉络,与之后在西方大规模的冲击和影响下的近代道器观不可简单直接并而观之。
对晚清道器观影响最大的是朱熹和王夫之(章学诚或可归入其中)的两种观点。前者被视为儒家正统,多作为较保守方的思想武器;后者多作为提倡改良、变通方的思想资源。不少涉及晚清道器观的论文,仅提及“道本器末”论的巨大影响,而忽视“治器显道”说和“道器合一”说的影响。虽然它们影响有大小之别,前者长时间被视为“正统”,但若仅强调前者且忽略后者,难免有失全面。
二、晚清道器观的多元发展与复杂面向
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为晚清的道器观打下了最为标志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晚清道器观与此前最大的不同也是其自身最显著的特点为,除了相同的将“道器”与“体用”“本末”等放在一起讨论外,还加入了“华夷”“中西”与之紧密相连,“道器”几乎是与“中西”绑定出现,被一并论及的;提及的这几组成对的概念也往往一并出现。但当时论者对这些概念似乎并未有意加以区分,常常一并混用;且不同论者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也因不同语境而异。因此,笔者也难以直接抽象地将它们区分开来,只能具体语境具体分析。
若谈到“西器”,魏源无疑是必须提及的开山鼻祖般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谓是开倡导学习西方技术之先河,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可以看到,魏源论述的重点在西方先进的技术即“西器”,而较少论及与“器”相对应的“道”,因而也较难由此论及道器观。
魏源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也是少数人。在面对西方冲击之时,或受传统华夷之辨③观念的影响或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恶,不少人对西方及其事物持拒绝、排斥甚至仇视之态度。比如,一些保守的地方精英排斥外来事物。豫师,一位在清同光年间出任西北都护的学者,醉心于宋儒之学,并公开表示自己“生平最恶洋字”,家中无一物来自泰西④。与他同时代的刘恩溥,是一位在19世纪末颇为活跃的官员,同样“痛恶洋字”。不过,他家中有一个帽架是由欧洲进口的马口铁所制。由此可见,欧风美雨的浸染是无孔不入的,哪怕是最保守的士大夫的深宅内院也无法幸免[5]。由此看到,纵使主观意愿上排斥抵制外来事物,但客观上西器无处不入;可以说,随着欧风美雨的日趋深入浸染,很难有人能够绝对置身西器之外。于是,关于“中西”与“道器”的种种讨论日益盛行开来。
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可谓是反映当时道器之争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却遭许多士人反对。随之而来的争论所关涉的观念冲突,除了是否应“以夷为师”的中西冲突之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士人是否应学习器物制造的道器冲突。原本是儒家六艺之一的算学之所以会沦为“机数”⑤而遭抵制,也与这种中西、道器冲突密切相关。既要维持道高于器的理念,又要让士人学习西方所长的器物,这是争论双方都非常关注却又无法调和的问题。综观此次天文算学馆之争,道高于器的传统理念是让士人学习“西器”的观念障碍。这一观念既不能被颠覆,也无法被绕过,使得这次天文算学馆之设,最终演成纷纷争论。西方到来使中国人感受到了“器”的威力,“器”之于“道”,一如“西”之于“中”,原本皆处于次要地位。而随着中国的数次失败,“西”与“器”的地位逐渐相互增强。朝廷为了应对西方而提倡“西器”,而士人又将“西器”视为末艺,这种错位充分体现了近代西方冲击中国所产生的复杂性[6]。此后,“器”对“道”的冲击与挑战亦日益猛烈。
通过此案例,或可看出当时“洋务派”与“保守派”在道器之争上的大致样貌。若要给19世纪末的道器观一个整体性的概括,笔者想用“中道西器”“中体西用”以及“道高于器”或大概不错。但整体并非全部,有主流也并不代表千篇一律,这其中的不同音,或许更加值得被关注。
首先是郭嵩焘。分析他的道器观,要注意他中西相通的理念和中西在“道”上对抗之焦虑,与当时中西相别之观点互动又竞争[7]。他继承古代儒家“道”的概念,以此作为其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继承发挥王夫之的“道器论”,将之作为中西方文化观的理论指导。在肯定西方国家有“器”的认识基础上,指出西方“道器”兼备,从而更胜于同时代人视西方“有器而无道”的观点,并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道器一元论,提出道器多元论[8]。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是康有为。他在《物质救国论》中强调物质的重要性,认为救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包括工商经济、科学技术和军备国防。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并未否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仅靠“物质”当然不能救中国,但“物质”是立国的前提和基础,自由、民主、道德、精神统统离不开“物质”[9]。康有为有心要将对西方的学习由“精神”重新拉回“物质”的层面。然而康有为此说提出后并不为时人乃至不少后人所认同,尤其是受到梁启超的“冷遇”,以至于《物质救国论》一书的出版也一延再延。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或许与当时的主流有些格格不入,但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也是我们观察晚清道器观发展嬗变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综上,晚清道器观所关注的道器关系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如何对待西方事物以及如何学习西方,因而前文所提及的好几组成对的概念往往一并出现。呈现多元发展的情形,并有着诸多复杂的面向,并不能以“道本器末”或是“中道西器”“中体西用”一言蔽之。晚清的“道器之辨”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讨论最为激烈的,不仅是不同派别之间,同一派别的不同人之间的观点都会有所不同;留下的丰硕而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发掘和深耕。
三、民国时期趋于统一的道器观
及至民国,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开展,此前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一系列讨论正逐一成为现实。有识之士将主要目标放在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民主国家上来,而对“道器之辨”的关注和讨论则日趋减少。
因为“器”所指的可大致理解为(西方的)器物和技术,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布开来。相比于上文所举出的此前刘恩溥的例子,这时西方器物和技术早已更深更广地融入了时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当中无法避开甚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人们会渐渐认为它们的存在不言自明甚至是理所应当,并不会过多产生怀疑、思考和讨论。虽然抵制洋货的运动时有发生,但人们所抵制的并非器物本身及其科学技术,而是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民族主义内涵。
此时“道”所包涵的内容,可以大致理解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这时它们已经逐步在中国实现和推广开来。此时道器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它们确实处在不同层面,或许在时人观念中也会有高低之分,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关注点。人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并推广它们,如何更好地让它们共同服务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的是梁启超在1922年《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提出的一段著名论述。其将五十年中国思想的进步描述为线性进化的三期,从一开始在“器物上感觉不足”,到甲午以后“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最近两三年间”的“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0]。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进化”意味且明显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论述。该说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态度演变的描绘,不乏精到之处,然值得讨论之处亦有许多,已有不少研究对此有过精彩的探讨,便不再展开了。笔者想要探讨的是,这样的论述反映了当时怎样的道器观?
仔细分析梁启超的这一论述,可知三阶段的“不足”与进步均参照西方,此叙事脉络暗设着“趋西”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还预设着文化比制度比器物更接近西方文明某种实在的“本质”,如此认知逻辑也蕴含着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倾向。尽管身处变局的近代国人眼光日渐趋西,道高于器的思路却相对稳定,人们相信文化的面相要比制度、器物更能界定一个文明的核心内涵,和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道高于器”的观念有着相关联的逻辑。以较长时段观之,中国人原本视“道”高于“器”的认知结构并没有被颠覆[7]。但同样要看到,这样的论说至少肯定了器物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也并未轻视器物,相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关注并重视着物质文明的发展。
可以说,梁启超这样的认识很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之后人们直接关于道器关系的讨论并不多见。虽然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大地上陆续涌现出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彼此之间也多有争鸣,但他们的争论大多集中于“道”之上,即不同“道”之间的争论,而较少提及“器”以及道器关系。且这些为数不多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学术史、哲学史的角度对前代特别是古代的“道器之辨”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学术性文章。例如,在《东方杂志》上先后刊登过的缪天绶《宋学重要的问题及其线索》[11](1927年)、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12](1928年)、何炳松《程朱辨异(一)》[13](1930年),其他有纪玄冰《“依照说”与“道器论”》[14](1943年)、罗香林《道器双溶,理行并入:文理学报发刊词》[15](1946年)、韩少苏《道与器》[16](1946年)等。它们大都是从哲学出发探讨抽象意义上的道与器,和“中西”已无太大联系,反映出的道器观也基本不离由器至道是逐渐深入的发展过程或是道高于器这样的观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梁启超“三阶段说”的继承与再发展。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道器之辨”已日趋平息,民国时期的道器观到梁启超提出“三阶段说”已基本趋于统一,其后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说也基本不离梁说的思路框架。如此看来,民国时期的道器观似有些乏善可陈,这不免让人生疑,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思想的碰撞不应该十分激烈吗?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道器观或许已渐渐演化成为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科学主义。由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道器观与科学主义有着怎样的相互联系?第二,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人们视科学及其器物为时髦,纷纷追捧,此时的道器观又发生着怎样的转向?期待之后的研究能对此进行解答。
结语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哲学当中的“道器之辨”,可以得出两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朱熹的“道体器用”说或“道本器末”说,以及王夫之、章学诚的“治器显道”说或“道器合一”说,二者共同成为晚清道器观的重要思想来源。“道本器末”或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流,但绝非传统道器观的全部,我们需予以重视。
对中国古代传统道器观具有一定继承性的晚清道器观,面临的大变局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注的道器关系的核心问题成为了如何对待西方事物以及学习西方,因而“道器”几乎是与“中西”绑定出现被一并论及的,“华夷”“中西”与“道器”“体用”“本末”这几组成对的概念往往一并出现。总体而言呈现多元发展的情形,并有着诸多复杂的面向,并不能以“道本器末”或是“中道西器”“中体西用”一言蔽之。与当时思潮主流存在着不同的两种观点——郭嵩焘的“道器多元论”和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各有其价值,值得我们更多予以关注。
由于晚清道器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道”的逐一实现,民国时期的“道器之辨”已日趋平息,道器观到梁启超提出“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说已基本趋于统一,其后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说也基本不离梁说的思路框架。这时的道器观又与之后的科学主义产生了联系,其相互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探索。
综观明清至近代,虽然主流观念中视“道”高于“器”的认知结构并没有被颠覆,但“器”对“道”也确实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器”之地位同样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肯定和重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道”“器”各自的内涵,还是“道器之辨”、道器关系或是道器观,都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和更新的。道器观的嬗变,是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重要缩影。
注 释:
①船山:即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其字而农,号姜斋,人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
②六经: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仪礼》《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③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
④泰西:旧泛指西方国家,出自明末·方以智《东西均·所以》。
⑤机数:汉语词汇。释义为谋略;权术、权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