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鸡娃”教育的失败品
2022-12-29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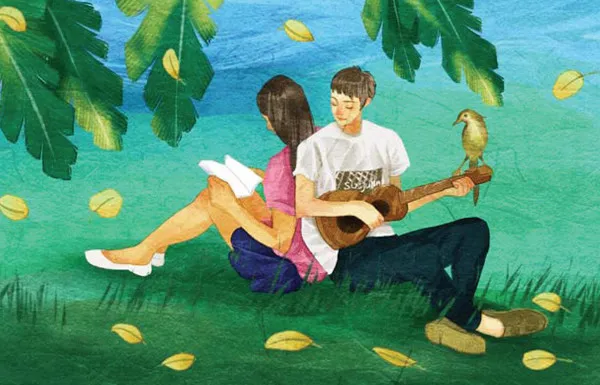
2010—2020年这10年,每年的高校毕业人数从575.4万飙升至创纪录的874万。人才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大,整个社会深陷“内卷”教育和“鸡娃”大战之中。孩子们过早地承受学习压力,各种心理问题悄然滋生。
我被父母逼成刷题机器
高一那年,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同年暑假,我开始了“十年级申请十年级”的美国高中申请。
申请好的寄宿美高需要考托福,考SAT(美国高考)。我连续考了两次托福,成绩都没有过100分。在美高申请中,托福105分是一个坎。跟我旗鼓相当的朋友们一个个迅速刷到了110分,而被父母寄予厚望的我却栽了大跟头。
妈妈跟我说:“你就是没有人家能坐得下来、吃得了苦。人家一天能刷3套听力,你呢?”爸爸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你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投入产出比是最划算的,你现在每一点付出都能改变很大部分的未来。”
10月份,我离开了就读的公立高中和朋友,开始在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和家间两点一线奔波。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像出了某种状况。当我坐在电脑前刷题的时候,我开始什么也听不进去,看什么都脑壳疼。有的时候我把手机收起来,坐在电脑前也只能发呆。晚上在家复习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妈妈悄悄地端一杯牛奶进来放在我旁边,因为那时候的我,坐在电脑前,什么也听不进去。后来,我对此连害怕的感觉也丧失了。
我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我有一个很温柔的朋友,总是能带给我很多力量。无论我多么迷茫,他总能找到开导我的方式。有一天我到他的教室门口,一如既往地请同学帮忙找他。隔着窗户玻璃,我看到了他疲惫、无奈的眼神。
我知道不该再找他了。
下午回到家,母亲说:“你该振作起来。”
我想我可能是一个负担吧。我在夜里动不了,却又睡不着,眼泪毫无知觉地流下来。我就想,我也许不该存在吧。
每次想死的时候,我就费劲地写信,写到我不想动了或者不想死了为止。然后把那张纸塞到一个硕大的信封里,再把信封压在桌面的一本字帖下面。信封上写着:请勿开启于夏(我的化名)生前。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活不到16岁。我记得16岁生日那天是周日,父母送我到学校宿舍,送我进去之前又因为什么骂了我好一阵。我回到宿舍,藏进厕所失声痛哭,一遍遍对自己说“太不容易了”。
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
我在网上搜了几种抗抑郁药的名字。中午学校放学,坐车回家自习之前,我就到学校旁边的药店去问,有没有阿米替林,有没有多虑平。
一家店坚决不卖给没有处方的人;另一家和我说,我们没有这两种,但是有另一种,不然你去问问你的医生。我说我先买吧,回头我问医生。
我用攒了好久的一百多块钱买下了那一盒我已经记不清楚名字的药,看完说明书,然后开始吃。后来我把药一直藏在书包的夹层里。
2017年5月,我终于收到了美国高中的录取通知书。8月份的时候,我开始了为期3年的美国高中生涯。
那年11月的感恩节假期前夕,在合唱节上,我认识了E。他是一个华裔和希腊裔混血的本地男生,安静、稳重。
当我和他在短信里玩笑似的讲起我申请美国高中的经历时,他忽然说了一句“对不起”。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因为你经历的一切比大多数人都艰难。”
那时候我已经快忘记申请高中时的挣扎了。那天隔着手机屏幕,我泣不成声。我发誓我要一直对他好。
“爱也许是一种救赎吧。”
母亲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不配被爱
圣诞节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家。我妈告诉我,第一学期玩没有关系,但十年级第二学期就要开始准备SATⅡ(SAT科目测试,部分顶尖美国大学有硬性要求),然后要开始学习SAT。我妈好像还批评了我12月没考好。我的耳边又充斥起了“你应该去学习了”之类的话语。我不停地劝慰自己,熬到我回学校就好了。
当我终于拉着行李回到学校宿舍时,看着空荡荡的走廊,我又恍惚了起来。我知道,有些东西好像没有好。我的老朋友啊,它又回来了。
我开始不想上课,我变得很容易哭,而哭的原因可能只是宿舍同学的一个眼神;考差一次之后我可能一整个晚上都不想动,哪怕第二天还有另一个考试;我就算独处的时候也会变得十分烦躁,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也变得十分煎熬,甚至和E打电话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这种变化让我心慌。我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那的老师说我很可能得了抑郁症,但是她不能诊断,建议我付费看外面的心理咨询,并告诉我学校愿意提供车。但我却下不了决心。
每当老师问我有没有自残倾向的时候,我都说没有。我的确不忍心在我的身体上动刀子,我的手是弹琴的手,比我这个人本身还宝贝。我不希望未来的我,某一天恢复正常的我,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我常常对E说:“你值得更好的女孩子。”有的时候,出于无法名状的对自己的恶意,我甚至希望他离开我。
我隐晦地和母亲说过,觉得自己可能心理有那么点缺陷。我妈忙说你别胡说,你没有,你不是,你可好了。母亲的态度让我觉得有缺陷是一件天大的坏事,是不配被爱的。
某天晚上,我把社交媒体上的所有好友一个一个删掉,把手机关机,一个人跑到学校的角落里,在黑夜中的草丛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后来我才知道E找我找疯了,他最后联系上了我的室友,我的室友也差点疯了。那些被我删除的美国朋友也提心吊胆,生怕我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后来E让我保证,永远不会伤害自己。我保证了。所以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也常常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扯个稀巴烂,把事情闹得很极端。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真是个浑蛋。但那时候的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一个学姐S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她也是E的朋友,常常和我说话,告诉我她理解我,也和我讲她的抑郁经历。她说她愿意开车送我去医院,避开学校的咨询部。因为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喜欢一言不合就送人休学回家。
但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或许我是担心接受心理咨询之后,真的会被贴上抑郁症的标签。
在公益活动中找到自我价值
在美国的第二年,我的状况开始急转直下。
开学之后的第二个周末,E来学校见我一面之后,就匆匆要走。我恳求他多陪我一会儿,他却说要做作业。
第二天,他找我谈话,说要分开。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手臂的肌肉摆动,特别不真实。
分开之后,我除了晚上会大哭之外,反而没有了其他抑郁的症状。我好像憋了一口气,无论做什么都非常拼命,甚至拿到了一个在市里实习的机会。我好像竭尽全力要向人证明自己没有心理问题。
第二年的春天,抑郁症如期而至。这年正好是申请大学的关键时期,我不敢再拖延,选择去校外看心理医生。我提前告诉了父亲,他沉默了几天,同意了,并且说会为我支付医疗费用。
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我尽量减少工作量,心态放缓,并跌跌撞撞地撑过了4门AP考试(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心理医生也建议我找精神科医生进行药物治疗,但我决定“再观察一会儿”
接近夏天的时候我和E又走近了一些,却没有再在一起。他虽然年纪比我小,却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时候的他已经要毕业了。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给他送了一束红玫瑰,给S送了一束黄玫瑰。我想,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送花了。
夏天的时候,我回到家,情况再次急转直下。在床上连续躺了几天之后,我稍微好转,拉着我爸带我去看病。我妈知道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念叨着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怎么这么脆弱。
她说:“你整天抑郁症抑郁症的,我听得都要抑郁了。”“什么抑郁,不就是讨厌这个家,想要逃离这个家吗?你不能总想着逃离这样的事情啊!”
我爸跟我说,他看到了当年我写的那些遗书。他说还好没给我妈看到,不然她要疯掉。我跟他坦白说,我想自杀的时候,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妈。每次我妈劈头盖脸地指责我时,我都希望自己原地消失,再也不要出现。我会想死,但我不想伤害我妈。我爸就沉默了。
当我拿到写着抑郁症的诊断书以及欣百达(一种抗抑郁药物)的药方时,我不悲也不喜,有的只有尘埃落定的安心。好像我3年没名没分的抗争终于有了意义一样。
2019年暑假,我和一些年龄、经历相仿的病友,在深圳举办公益音乐会“熹·Glimmer”,演奏了一些我们自己作的曲子。
创始人汤、贝,还有我,我们都在美国的高中就读。第一场演奏会是依靠留学中介平台举办的。我们通过中介找到了二十来个演奏者,然后在写字楼附近宣传,招来了一两百名观众。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演奏的是汤重新编曲、中岛美嘉演唱的《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
汤讲起他和这首曲子的渊源,引用歌词“我的脑袋里总是想着一了百了,也许是因为我对活着这件事太认真了吧”的时候,我心中有一根弦好像被触碰了一下,就在台上无声地哭了。
后来,我身边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有抑郁症。母亲告诉我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因为“我很轻”,我这么说会让别人觉得我有很大的问题,不堪重任。后来她大概接受了我有抑郁症的事实,但她还是时不时告诉我要振作起来,要有意志力,或者焦急地追问医生要不要给我停药。
2020年,我们策划的第二届公益音乐会在8月就要上演了。下一年还会有第三届。之后还会有第四届、第五届。
我们中的不少人将要上大学了。春天的时候,我拿到了很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汤和贝也都去了美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学。
我曾在知乎上看到,自称抑郁症患者的人很多都是在消费抑郁症,而真正的抑郁症患者总是不敢说出口。这就是为什么16岁的我放眼四周孤立无援,也是为什么20岁的我想要发声。从前,我不会想到我会坚持做一件非营利的公益活动一辈子。
如果可以重来,我再也不会选择在黑暗中独自前行了。但人生不能重来,就给后面的人点一盏灯吧。毕竟,不知有多少人曾想过一了百了,但是在这世上,我们其实还可以相互救赎。
(摘自台海出版社《少年抑郁症:来自17个家庭的真实案例》 编者:真实故事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