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高粱》谈当代小说的时代意义
2022-12-29许子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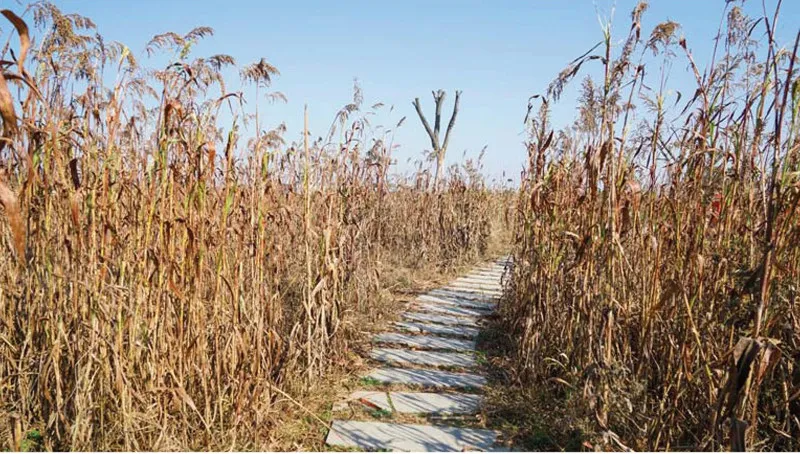
人生就是没有“多年以后”,所以要靠小说给予虚拟的机会。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被评论界认为是1978年(或1949年)以后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描写“土改”的《生死疲劳》曾获第二届“红楼梦奖”(又名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莫言自己最喜欢的则是《丰乳肥臀》。莫言的小说,有不同风格探索、不同艺术成就。我个人还是认为《红高粱》是他的代表作。
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为新人新作《透明的红萝卜》开讨论会,莫言的军官身份一再被介绍,他坐在一边,几乎一言不发(怪不得叫“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故事基本写实,又偶尔写特异感官——农村小男孩能把红萝卜看成有着金色外壳包着银色液体的透明物体。小说里的铁匠和石匠,同时喜欢一个叫菊子的姑娘。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中国当代小说作家突然发现现代主义的魔幻和现实主义的乡土也有结合的可能。
那是1985年,《红高粱》已经写好,尚未发表。
《红高粱》中的现代派技巧
《红高粱》中的现代派技巧,具体来说就是后设的叙事技巧和暴力审丑美学。我曾有专文讨论《红高粱》的两种后设叙述。一种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叙事者,包括读者,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局,然后回述当年的事情。
一般小说有点像现场直播的球赛——故事顺着时间发展,读者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是《红高粱》里有个细节,戴凤莲出嫁坐轿,路遇土匪,轿夫余占鳌等把土匪赶跑以后,男主角就去掀轿子的布帘,碰了一下新娘子的脚。这不仅不礼貌,而且基本上属于“性骚扰”。就在读者紧张期待故事会怎么发展时,小说突然插了一句:“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
这就等于足球将进未进之际,突然有旁白说“这场比赛的胜负,就在这一瞬间决定了”。这等于是从现场直播变成录像回放。虽然观众读者喜欢现场直播,但录像回放也有特别效果。回放的时候,才看得清楚比赛(事件)当中,哪些事情看上去热闹,其实无关紧要;哪些时候以为不重要,其实是关键时刻。在这种关键时候,就会出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句型:“多年以后……”
生活中每天每月会碰到很多事情,再争取一下?还是放弃?这时多么希望有个事后的声音角度,告诉我们“多年以后”……人生就是没有“多年以后”,所以要靠小说给予虚拟的机会。
后来,不少当代中国小说家都使用这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年以后”叙事策略,目的就是要写顺时态中的“后见之明”。提前出现的结局会使读者从关心“后来怎么了”转到“怎么会这样”。
《红高粱》的“后设角度”还直接体现在人物称呼上,男女主角大部分时间不叫余占鳌、戴凤莲,而是“我爷爷”“我奶奶”。既突出了叙事者与人物的血缘关系,又将“奶奶”之类的乡土符号和诸如“个性解放”等现代语言巧妙并置。小说里的典型句式是“她老人家(我奶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文学评论家季红真认为,这是家族、宗法、乡土语言和现代城市语法观念的混合。
《红高粱》接受现代派影响的另一特征是暴力审美。《红高粱》里面写罗汉大爷被剥皮那一段,令读者印象深刻。《红高粱》以后,寻根派的小说常有撒尿之类的动作描写,也不忌讳暴力血肉细节。一般来说,通俗文学常常写海滩、月亮、玫瑰、烛光,“严肃文学”则渲染各种刑罚暴力,如莫言《檀香刑》、余华《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
《红高粱》为何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
革命历史题材中,抗日本来应该是重头戏。可是在20世纪上百篇中国小说名作里,描写抗日的作品不多,这个现象值得研究。一到抗日题材,就是民族矛盾、“非人即鬼”,故事只能侧重于写抗争的手段工具,往革命通俗文学方向发展,比如《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直到今天,抗日戏依然是影视屏幕当中的主要填充材料,但是也依然要靠“手撕鬼子”之类的特殊手段才能吸引观众。在抗日题材方面的任何突破,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有张军钊《一个和八个》等,都非常艰难。
《红高粱》写丑,写暴力,用现代派的手法寻根,却写出了陌生化的抗日小说。文学评论家雷达曾撰文称赞《红高粱》“它与以往我们的革命战争文学都不相像……在审美方式上它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更新”。
在《红旗谱》等“红色经典”里,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模式主要是穷富与国共。再细一点,则有6种力量——穷人、富人、祠堂、学校(常常是地下党教员),还有国民党、共产党。《红高粱》里除了这6种力量以外,加了(或者说还原了)第七种土匪。
在《红高粱》当中,抗日的主力居然是土匪和他带领的普通民众。国民党冷支队长有兵力,可是打完伏击战以后才赶到收军火,坐享现成。有个长得很秀气的任副官,小说中的“我父亲”猜他八成是个共产党。任副官教兄弟们唱革命歌曲,成功训练出余司令土匪大队的纪律性。余占鳌的叔叔强奸妇女,余占鳌就逼迫叔叔,要把他枪毙掉——这种驯化改造土匪队伍的情节在不少文学作品里出现过。
余司令的队伍能够在《红高粱》中成为抗日英雄,浅一点说,就是打破了抗日题材一向黑白分明、缺少人物性格矛盾、一向只在手段上做文章的创作局限,所以现在土匪参加甚至主导抗日,余占鳌的性格身份处境比较复杂。深一点讲,“五四”以来,晚清侠义文学传统在中国内地失落很久了。“五四”文学本身也并不包含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王度庐等人的武侠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本名查良镛)、梁羽生的新派武侠也进不了内地,所以民众只能在杨子荣、阿庆嫂他们身上回味昔日的江湖气味。
莫言能够理直气壮地把家乡的先辈讴歌成“那么英雄的王八蛋”,或者“那么王八蛋的英雄”,在潜意识的层面是有山东豪杰水浒底气的。晚清文学有狭邪、科幻、侠义、谴责四大类,“五四”以后似乎只有谴责现实类在发展。其实狭邪文学仍然暗暗存在并演化(从“青楼家庭化”到“家庭青楼化”),而侠义传统的复兴,《红高粱》功不可没。这才是莫言对传统文学的真正传承。侠义精神的复活,加上后设叙事技巧,再加上对城市的道德批判,就有了政治反省、文化寻根和西方现代派技巧三者碰撞结合的客观效果。
但这不一定是作家的主观把控。作家本人其实更多是从他20世纪60年代初的儿时饥饿记忆出发,借点西方技巧,考虑中国政治,又歌颂家乡土地。儿时的饥饿记忆,是莫言创作的真正动力。就《红高粱》而言,莫言说:“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