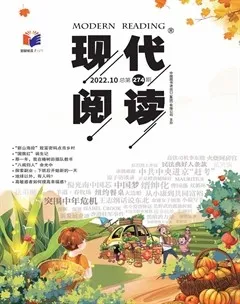事实不是你所经历的,法律不是你认为的
2022-12-29黄文伟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光明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正在开庭审理李雪莲的案子。
王公道说:“你说去年,你们的离婚是假的,秦玉河的律师说是真的,你们各执一词。”
电影中,李雪莲为了达到分房子的目的,与丈夫秦玉河决定“假离婚”,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想等分到房子后再复婚。然而,半年后,她发现秦玉河已经另与他人结婚。李雪莲气不过,便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双方是假离婚。开庭后,法官王公道根据他们确实办理的离婚登记,判决李雪莲败诉。对李雪莲来说,明明是假离婚,为什么法院不认可呢?李雪莲百思不得其解,又因为一句秦玉河说她是潘金莲,从此走上了十多年的申诉路。
当法律应用到现实生活,所有准备打官司的人,都应当有这样一个意识:在法庭上用于裁判的“事实”不是你所经历的客观事实,除调解外,司法裁判结果的作出是要建立在法官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之上的。法律事实并非凭空形成,除了那些不必举证的事实,其余事实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且是能够用经司法审理认可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如果证据不能证明事实,即便事实有可能存在,也不能成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正如西方法谚所云:“在法庭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无法证明自己的离婚是假的,法官王公道的判决,应该是根据证据作出的,合法有据。但是,李雪莲无法认同法院的判决。原因之一就是李雪莲“只相信客观事实,不懂得证据事实”,她无法理解“法院为什么不确认双方存在‘假离婚’的客观事实”,如果法院能确认这一事实,再判李雪莲败诉,李雪莲或许心里会有所释然。在初经挫折之后,她的请求也只是希望秦玉河承认是假离婚,她对秦玉河说:“明明就是假离婚,你怎么就不能说句真话说它是假的呢,秦玉河我告诉你,(你说了)我就不告你了。”
法律的应用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过程,证据事实与真实的客观事实可能有一定的距离,但法律评判只能以“证据事实”为准。案件的发生都是在若干时间以前,时间的不可逆性也决定案件的客观事实不可能重演。由于回避等程序性制度的设置,法官不可能是案件客观事实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见证者。案件的裁判其实就是法官运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去确定案件中那些法官必须知道而又不知道的事实。法官所能凭借的只能是“证据”——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来再现案件的事实,由于客观不可能再现,这种再现本质上只是法官对事实的一种想象而已。当事人虽然清楚,但是,人类理性的天然局限让其再现的事实可能有偏差,而且,由于切身利益被卷入其中,从而导致当事人可能会有意歪曲地再现事实。“事实不是你所经历的”似乎违背常理,却是法律应用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经历的事实来推断法律后果,但法官不是你。
从理论上来说,客观事实不管是否有人认识到,答案始终是二选一:存在或者不存在。而证据事实则是能够得到证明的或者不能得到证明的。在真实世界中,证据事实只是你的主张。作为一种主张,它不是过去发生的既定事实,不是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证明的问题。对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士来说,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但是,很多普通当事人对此还相当陌生,甚至根本无法理解。
一个医疗纠纷,当事人饱含情感地诉说医院的疏忽、失职与过错,强烈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人可能淡淡地表示:“如果仅仅根据你说的情况,医院确实是有责任的,但认定事实不是只听一面之词。”这时,有的当事人会极其愤怒。
无论是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还是法院审理案件,都要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并审查证据才能认定事实。同样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你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服法官。
你借给张三1万元,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无法拿出证据证明,你的事实主张就无法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怎样证明呢?证据事实并非凭空而来,仍然源于你所经历的事实,是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一种证据是不是客观遗留,例如借条是不是真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客观遗留不是事实的本身,根据客观遗留所推YIaV2zpUquCe8qaLCoGoep+fUUhVgQgBgYvtIF5EZx0=定的事实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看法。例如,仅凭借条就能推定出借款的事实吗?肯定会有不同看法。这就需要你有对手意识,能够有效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质疑。以借条为例,仅凭借条,对方可能说你们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却无借款事实,所以,你事前还得准备好能证明借款关系实际发生的证据,如转账凭证、收条等。一旦你能有效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质疑,法官就很有可能认同你的推定,你的事实主张就可以构成一个作为法官判决依据的证据事实,法官就会以此适用法律。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中,由于关键证据缺乏,就不能认定辛普森有罪。
最后,再看一个段子。
三男子去女方家提亲,家长提议:“说说各自情况。”
A说:“我有1000万元!”
B说:“我有一栋豪宅,价值2000万元!”
女方家长很满意,就问C,你家有什么?
C答:“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在你女儿的肚子里。”
A、B听后无语,走了。
在法律人看来,A、B选择走人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法律思维提醒我们要注意:C的话是真的吗?有证据证明吗?
我们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要备好证据证明;而对他人主张的事实,也务必要看一下是否有证据证明。
除了“将事实当成经历的事实,而不是证据证明的事实”,李雪莲的问题还在于“将法律当成自己认定的法律”。她“只相信自己认定的道理”,这道理在李雪莲心里就是法律。
“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然后和那个畜生结回婚,然后再离婚。”李雪莲这样一个执念在法律上是无法实现的。假设李雪莲能证明双方的确存在“假离婚”的协议,法院也不会按照李雪莲自己认定的道理进行判决。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要件,具有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律效果,而双方的假离婚协议,秦玉河不履行,法院也不可能强制秦玉河履行,否则就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
在法庭上用于裁判的“事实”不是你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证据事实”。同样地,在法庭上用于裁判的“法律”也不是你认为的法律,而是在法庭上经各相关方博弈之后最后由法官所认定的法律。大多数人可能不会犯下“李雪莲式”的错误——只相信自己心中的道理,但也经常以为自己理解的法律就是法律,他们没有注意到法律条文的含义不是唯一,在不同人看来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当你使用超市自助寄存柜,你可能认为自己与超市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事实上,针对不同案情,不同法官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公报案例“李某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中,法院认为超市与顾客之间构成借用合同关系而不是保管合同关系。
现实生活中不时出现的“同案不同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官面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不同的法律理解,或者面对同样的法条推理出不同的解释。对于很多学法的人而言,这并不是很自然的思维过程。正如律师界的一句流行语所言:“一般的律师试图说明法律是什么,优秀的律师则论证法律为什么应该是我说的样子。”
法律适用选择难题的存在,说明法律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在法庭上博弈的空间所在。我们应如何通过这种不确定性争取合法权益呢?
法律的不确定性首先源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这主要由语言模糊性的普遍存在引起,即使法律追求确定性——提供确定性的判断以规范和调整社会秩序也无法完全避免。对法律的适用实际上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如此一来,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和对法律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很可能就有不同的解释。看到“蔬菜”这一词语,你在理解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1883年美国的一项关税法案规定对“外国蔬菜”要征收10%的进口关税,曾引发一场“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的争议,进口商约翰·尼克斯认为是水果,美国海关却认为是蔬菜。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直到1893年,美国最高法院才作出判决,认为西红柿是蔬菜而不是水果。今天,如果问“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估计看法还是莫衷一是。
法律不一定就是你认为的,打官司,不能只说自己想说的和爱说的话、只顾自己的法律解释,必须有对手意识,要反驳对方当事人对你不利的法律解释,最重要的是影响法律适用者的解释,争取让法官认同你认为的法律。没有对手意识,就谈不上真实世界的法律思维。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有个著名的观点:“犯罪人不是根据法律规定去犯罪的,恰恰相反,法律是根据犯罪事实来规定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需要将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对接,法条的真实含义是在其适用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观点进一步扩展开来,也可以说,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生活而展开,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生活来立法,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生活解释法律,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里发现法律的适当含义。用当前的社会生活事实解释法律正是我们说服法官的可能性所在。
用当前的社会生活事实解释法律,进一步讲就是结合案件事实和社会生活需求来解释法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什么是财物呢?1997年修订《刑法》时,几乎没有人将虚拟财产认定为“财物”,今天,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财产保护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需求。如果能结合这种社会生活的需求来论证“虚拟财产是财物”,我们就能影响法律适用者对财物的解释。什么是社会生活的需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人类的众多社会结构——国家、民族、法律、教会、贸易,甚至货币,都是想象的产物。人们相信某种秩序,不是因为它真的是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带来美好生活。可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社会生活的需求。我们要说服法官,影响法律适用者的解释,就要善于结合案件事实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论证法律为什么应该是我们说的样子。
当然,法律不是你认为的,说服法官认同你的法律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法律适用者,特别是法官的解释,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不过,你也不必为此过分紧张,法官并不能任意地解释法律,大多数情况下,你所认为的法律与法官理解的法律是一致的。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也要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合理预期,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卡多佐所言:“当与束缚法官的规则的数量和压力进行比较时,法官的创造力便微不足道了。”
(摘自法律出版社《真实世界的法律思维:61堂出乎意料的法律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