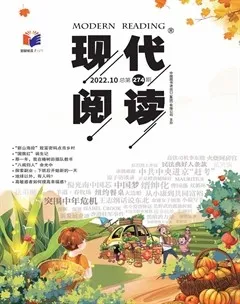伊莎白•柯鲁克的“贫困生情结”
2022-12-29谭楷



伊莎白·柯鲁克,加拿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作为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她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3年,就在伊莎白第二次回到重庆兴隆场(今壁山区大兴镇)时,她结识了大兴小学校长巫智敏。这以后的21年,伊莎白5次回到兴隆场,巫智敏都会陪同,加之频繁的书信往来,两人成为相知甚深的老朋友。
如今,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红光满面,声音洪亮,说起伊莎白时仍滔滔不绝。
巫校长说:“我最佩服伊莎白的远见,她很会发现问题。她写的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意见,我也拜读过,写得非常好,有真知灼见!她善于调查研究,喜欢自己选点。她总是边提问边录音边记录,细细问一次,就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全都问到了。你要是没有准备,或者胡说八道,她就会把你问得非常恼火。
“她生活上非常艰苦朴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和丈夫柯鲁克就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困难时期,他们又要求降工资,跟中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她现在住着1955年的老房子,家具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张窄窄的钢丝床,睡了几十年了。一件睡衣,都打上了补丁。
“到了基层,她不喜欢一吃饭就是一大堆陪客,一桌子珍馐美味。我陪她和美国学者柯临清去下面调查时,我们悄悄地在场镇上转悠,钻小饭馆、吃豆花饭、喝素菜汤。每个人才吃十来块钱,她吃得很香,很高兴。
“她不喜欢坐车,上我们大兴镇的茅莱山,那么陡的山坡坡,年轻人爬上去都要出一身大汗,她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坚持要自个儿朝山上爬,一路上还嘻嘻哈哈。哎呀,那精神之好,腿脚之灵活,真叫我们佩服。
“她还特别能为别人着想。她在写《兴隆场》时,就考虑到,写一些重要人物,如果真名真姓地写,会给这些人的后代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就用化名来替代。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她的地方。”
作为大兴镇和伊莎白交往最紧密的朋友,巫校长长期管理着“伊莎白·柯临清助学基金”(简称“伊柯基金”)。1999年6月18日,在大兴镇,伊莎白、柯临清与主管教育的副镇长签下了相关协议。
柯临清不仅是伊莎白在学术著作方面的亲密合作者,也是深受伊莎白影响的人。她目睹了大兴镇居民曹红英和伊莎白40年后重逢相拥而泣的场面,感动不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在中国流行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
在签下协议之后,柯临清说:“伊莎白跟我说过,她早已把四川、重庆当作自己的故乡,视这里的乡亲为娘家人。五六十年来,这份情义无法表达。她和我商量过了,我们决定要为兴隆场做点实事。帮助贫困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大兴镇挑选了吴开荣、周露霞、杨元依等1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作为“伊柯基金”的第一批受益者。
回到北京后,心细如发的伊莎白突然想到,当助学金交到孩子们手中时,孩子们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再翻看协议,她越看越不安。
伊莎白立即给巫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道:
我留意到在我们签订的协议里,规定了获奖的学生必须考出高于平均成绩的分数才能继续获得资助,这合理吗?贫困学生也许要帮助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种地或做家务,所以要求他们超过平均成绩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压力。我们想,你能否请人专门留意一下孩子们的身体和他们的课外负担?……
紧接着,在第二封信中,伊莎白谈道:
他们(受资助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必须拿高分,但是柯临清和我都只关心他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及他们的身心是否健康。这10个孩子在家都有繁重的家务,我想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都不太好,他们并不需要奋力争取好分数……
巫校长反复阅读伊莎白的信,禁不住连连感叹:“伊莎白对贫困学生的关爱,真是细致入微到难以想象!”
伊莎白还要求,每一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都要给她写信,谈学习和生活,谈心中的快乐和苦恼。她每年春节都会给孩子们寄去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还会写上鼓励的话。
伊莎白的英文信,要请人翻译成中文,细细念读确认无误之后,再寄出去。10个孩子,哪怕每年只给每个孩子回四五封信,也有几十封。这些信要翻译妥帖,工作量不小。参加译信工作的,有伊莎白的同事、学生、朋友。后来,璧山区档案馆整理这些书信时,发现译信人中还有著名的英语教育家陈琳、靳云秀。可见伊莎白动用了一切力量,为贫困学生送去了暖心的帮助。
伊莎白还给巫校长写信说:“现在的物价涨了,如果孩子们的学费有变化,请及时告诉我,我随时增加助学金。如果孩子们考上高中和大学,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请一定告诉我,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巫校长说:“‘伊柯基金’先后资助了3批学生,第一批10名,第二批19名,第三批17名。最先得到资助的10名贫困中小学生中,有3位女生考上大学后,继续得到‘伊柯基金’的资助。她们现在也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摘自天地出版社《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