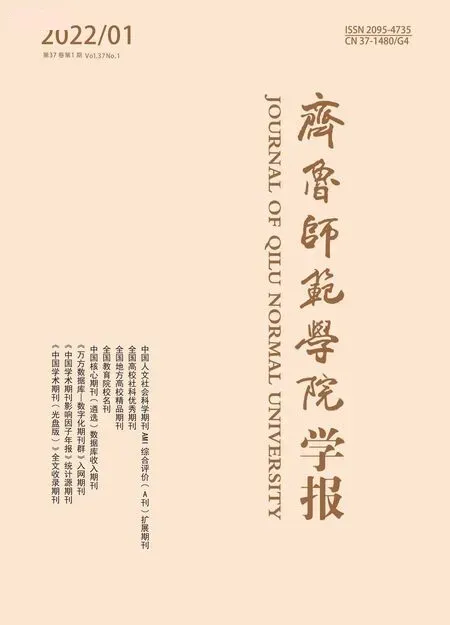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中《弗兰肯斯坦》与《裂缝》的比较研究
2022-12-28张书勉
张书勉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玛丽·雪莱的代表作,自1818年问世以来,便受到了广泛赞誉,“被文学界评为最杰出的哥特式浪漫主义小说、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1]67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发表了《裂缝》。该小说为莱辛在耄耋之年推出的一部力作,以较强的神话色彩吸引了评论界的关注,收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这两部杰作虽相隔近两百年,但都意蕴丰富,发人深省。前已有许多研究者从神话原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等角度,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阐释与解读。但是,笔者关注到,针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却较为少见。基于两者共有的、浓厚的生态主义女性色彩,及其作者共有的身份——玛丽·雪莱和多丽丝·莱辛均为公认的女性主义作家,笔者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弗兰肯斯坦》与《裂缝》的异同及其成因。“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2]5420世纪70年代末,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çoise d’ Eaubonne)的两部著作中:《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Écologie et Féminisme - Révolution ou mutation)。其中,德奥博纳呼吁妇女行动起来,发动一场生态革命。她强调尊重自然、解放自然,并预言:一种男女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关系即将形成。此后,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倍受关注的焦点。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包括以早期生态女性主义文本《寂静的春天》而闻名于世的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女性与地球生命:80年代的生态女权主义大会”的组织者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en)、凯伦·J·沃伦(Karen J.Warren)等。生态女性主义虽然被划分为不同流派,但具有共同的基本内核,各个流派均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自然和女性都受到男性的统治与压迫,都已沦为了“优越”的男性眼中需要为男性利益奉献、牺牲的“他者”。于是,“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认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3]57女性只有和自然携起手来,反抗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物种多样性,才有可能构建一个万物平等、男女平等的新秩序。而由此衍生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则正如有的相关研究者所言:“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4]109通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对两部文本进行对比研究,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弗兰肯斯坦》与《裂缝》都对男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颠覆,而后者所呈现出的效果则更加彻底。两部作品都倡导男女之间应当平等互助,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和谐相处。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今社会,两部小说无处不在的尊重女性、尊重自然的主旨,为人类谋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
一、女性与自然:和谐共处
美国生态主义女权者苏姗·格里芬提出:“我们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5]77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对《弗兰肯斯坦》与《裂缝》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完美注脚。在这两部小说中,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是平等、和谐和互相尊重的。
在《弗兰肯斯坦》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始终尊重、欣赏自然。在小说第二章即伊丽莎白刚出场不久,维克托便这样评价道:“伊丽莎白总是徜徉在诗人笔下那些虚幻的景物之中,并醉心于我们瑞士住地周围那雄伟奇丽的风光……所有这一切都让伊丽莎白赏心悦目,赞叹不已。”[6]35在寄给维克托的信中,伊丽莎白写道:“湛蓝的湖水,白雪覆盖的群山,一切依然如故。我想,我们这个温馨祥和的家,还有我们知足常乐的心田,也都是被这些同样不可变更的法则支配着。”[6]74在她眼中,大自然令人着迷,其法则是“不可变更”的,而人类生活在其法则的支配下,是可以过上美满生活的。在与维克托的谈话中,她感慨道:“只要我们有一颗爱心,彼此以诚相待,我们就可以在你的故乡——在这块宁静祥和、风光绮丽的土地上获得安宁和幸福——还有什么力量能搅扰我们平静的生活呢?”[6]117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蕴含在她朴实的语言中。在她与维克托成婚前夕,维克托因怪物的威胁而心神不宁,她便主动引导他欣赏美景:“瞧我们的船开得多快,瞧那天上的云朵……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快乐,那样恬静!”[6]261想必伊丽莎白也曾在大自然中寻得心灵的安宁,才会借大自然之魅力开导维克托。小说中另一位女性人物萨菲正巧在一个春日出现在费利克斯家门口,对于他们一家来说,她的到来“如同阳光驱散晨雾一样”[6]152。玛丽·雪莱将萨菲的出场和天气状况联系在一起,大有情景交融、女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之意。
同样,《裂缝》中象征着女性的“裂缝族”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她们居住在海边的岩洞,倚靠着“裂缝山”,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鱼、海草、水果为生。且听她们的自述:“我们是海洋人,海洋生养了我们。”[7]7“我们就是那道裂缝,那道裂缝就是我们。”[7]9她们像生病的海豹一样躺在岩石上,而她们的歌声“是一种哀恸,听起来像风在叹息和低语。”[7]35美国女作家格里芬(Susan Griffin)提出:“女性与自然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强调女性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相信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生物学上的关联,认为月经使女性与自然过程(月亮圆缺)保持着有规律的联系,使得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接近大自然,更能体验这种关系以及与女性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怀。”[8]94而小说中,月亮、红花、裂缝和生育、月经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们(裂缝族人)从月亮的蛋里孵出来。”[7]34“每个人都知道月经来潮和那道裂缝流出红色液体的一致关系。”[7]87在接触“喷射族”之前,“裂缝族”的生育正是靠月光完成的。这一切都表明《裂缝》中女性已和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与《弗兰肯斯坦》中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相比,《裂缝》中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变得更加亲密。《弗兰肯斯坦》中虽有大量关于大自然的描写,但囿于其中的女性多为扁平人物,如巴巴拉·约翰逊评论其中的女性“千篇一律,乏味得很”[9]7,女性和自然的直接互动并不多见。伊丽莎白虽作为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但她只是欣赏、赞美自然,并没有达到与自然相依为命、同生共死的程度。《裂缝》则不然。该小说详尽地展示了“裂缝族”是如何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直接依靠自然的。除此之外,自然也慷慨地给予“裂缝族”应有的庇护。无论是在受到象征着男性的“喷射族”死亡威胁的时候,还是在去探究“喷射族”之际,《裂缝》中的女性都视海滨和山为她们的保护伞,而裂缝山上的裂缝“带着令人畏惧、令人恐怖的气息”[7]133,也的的确确吓退了“喷射族”,让“裂缝族”暂免其害。“噪音”——大风事件在惩罚“喷射族”时,也有意绕开了“裂缝族”的洞穴。
二、男性与自然:纷争不已
在《弗兰肯斯坦》与《裂缝》中,男性和自然的关系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迥然不同。在女性与自然深度交融、难舍难分之时,男性正在掠夺、征服、进而统治自然。自然面对被男性贬低、边缘化的处境,也被迫予以回击。
《弗兰肯斯坦》中的男主人公维克托自幼便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然而,“欧洲科学的整体模式是父权的、反自然的和殖民的。”[3]59他虽然获取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却对自然规则,尤其对生与死,毫无敬畏之心。在他看来,“被夺取了生命的,原先优美而有力的躯体也只是蜕变成了蛆虫的食物而已。”[6]56他相信“生与死的界限是虚幻的”[6]59,意欲“率先打破这一界限,让万丈光芒普照那黑暗中的冥冥世界。”[6]59他无视两性生殖的自然规律,利用人类尸体造出了一个新生物,并赋予它生命,要求它对他“顶礼膜拜、感恩戴德”[6]59,甚至还炫耀:“天下做父亲的,有谁能像我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此结草衔环,感激涕零?”[6]59但是,“在父权社会里不存在对于‘他者’的尊重,作为男权理性的客体的他者,只有在它能够使主体受益的情况下才被予以考虑。”[3]59维克托创造新生物的目的就是奴役它,从不认为他和它地位平等,值得被尊重。因此,当他发现这个新生命是个怪物,无法为自己提供所谓的益处时,便不顾生养契约,毫不留情地遗弃了它。
在被怪物报复后,维克托对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却把不幸归咎到科学研究上。寻根溯源,他对自然蔑视的固有观念才是根本原因。“生态女性主义对‘女’之自然属性的超越,来自于其异常丰富的所指……‘女性’已成为一种文化隐喻,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或尚处于边缘地位,是饱受男性/人类/资产阶级/西方/白人等占统治地位的压迫者的欺侮的弱势群体。”[10]153怪物虽生理性别为男性,但由于被人类社会排斥,所以和女性、自然一同沦为边缘化的“他者”。它终日生活在大自然中,和大自然结成紧密同盟,对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情,堪称自然的代言人。维克托的残酷、冷漠使它饱受折磨,于是,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成为嗜血恶魔,夺走了多人的性命,其中包括维克托的未婚妻、弟弟和女仆。它把北极预设成复仇之路的终点,将维克托引至这个受人类玷污最少的极寒之地。在那里,它对他和人类社会的愤恨最后一次爆发。这何尝不是自然缘于对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愤恨呢?而维克托注定的死亡,也是自然规律对他漠视死亡的惩罚。
《裂缝》中的“喷射族”是男性的象征。“喷射族”像拓荒者一样热衷于探险,以狩猎为生,“野性十足,精力过剩。”[7]45他们直接破坏自然,试图让自然臣服于自己脚下。他们的首领名叫霍沙,这个名字与野性、征服、毁灭联系在一起,让人联想起“狼的吼叫,熊的咆哮。”[7]175霍沙组织的狩猎引发熊熊大火,烧毁了树木。在狩猎时,一些猎手引发了爆炸,惊扰了动物,打乱了森林的生活秩序。猎手还趁着在大风来临前,大肆猎杀因惊惧而四处逃窜的动物。他们砍伐灌木丛和野草,甚至连娱乐活动——一种年轻人发明的、名为“裂缝”的游戏都需要燃烧尸骨以产生浓烟,凡此种种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大自然面对“喷射族”赤裸裸的挑衅,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噪音”——大风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持续的烈风把“喷射族”的男孩们卷到空中,再扔进河里,夺走了无数生命,并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居住地,切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风在这些似乎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的人们心中植入畏惧。”[7]150在此之前,“裂缝族”误把大自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朋友”[7]150,虽说是“朋友”,但因为“理所当然”,所以毫无尊重的意识。现在,“‘噪音’这场大风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有人是多么无助。”[7]150这场重灾是大自然对“喷射族”摧残自然的回应,这虽为他们敲响了警钟,但其并不知悔改,仍被征服欲牢牢支配。在小说的结尾,霍沙还想去登陆另一片海滨,尽管海上的风暴已让他和他的朋友吃尽苦头——他摔断了腿,他的朋友丧了命。
蕾切尔·卡森认为:“‘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11]263无论是处于原始社会的“喷射族”,还是处于18世纪的维克托,都没有摆正男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误以为自己站在等级制度的顶端,把自然看成附属品。当然,他们的这些妄想无疑最终都被自然的力量击得粉碎。
三、男性与女性:由“控制”到“平等”
伊丽莎白·格蕾在《失去的绿色天堂》中提到:“自然界被贬低,源于在性别心理方面自然界与妇女联系在一起。”[12]32在《弗兰肯斯坦》与《裂缝》中,自然界被轻视,其中的男女关系无疑也是不平等的。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必会遭到女性的反抗,这在《裂缝》中,女性的还击更为激烈和卓有成效。
《弗兰肯斯坦》中的男主人公维克托将伊丽莎白视作只属于他一人的礼物,经常无视她的感受。他隐瞒自己被怪物追杀的事实,迟迟拖延和她的婚期。在成婚当天,他已预感到怪物会取走她的性命,却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只字不提。他的自私不仅导致伊丽莎白的死亡,还导致女仆贾丝婷被冤死。他明知是自己造出的怪物杀死了威廉,却为了面子不肯说出真相,使法官的矛头对准贾丝婷。在贾丝婷受审时,他也没有为了还她清白而作必要的争辩。他从未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爱惜她们的生命,反而无情地践踏她们的生命权。更为致命的是,维克托为了满足自己成为造物主的欲望,竟然直接跳过女性,亲手制造怪物,而“这种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和占有的欲望,包括对于女性生殖能力和自然繁殖能力的控制和占有,有力地揭示了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3]59
《裂缝》中,鄙夷是“喷射族”对待“裂缝族”的主基调。“喷射族”的年轻人曾把一个“裂缝族”姑娘群奸致死。他们不顾她的反抗,绑住了她的手脚,“发出胜利的欢呼”[7]50,任由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本能到处弥漫。”[7]51事后,他们虽感愧疚、嫌恶,但只认为自己“有意杀死了安宁、放松和宽慰的感觉”[7]52,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感觉”,而是对鲜活生命赤裸裸的剥夺。他们也从未站在“裂缝族”的立场上进行反省,故而此后更变本加厉。在林中远征中,“喷射族”明确表示远征的目的是逃离婴儿的嚎哭,认为“裂缝族”的生育是“让人不愉快的景象和声音”[7]216。在失去了婴儿的女孩们痛哭流涕时,“男孩们表现出他们的厌恶。”[7]216甚至连流传下来的、主题为“喷射族”丢下冒险活动来照顾孩子的歌曲都是讥讽性的。“喷射族”对“裂缝族”的不屑一顾和严重伤害,由此可见一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遗憾的是,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弗兰肯斯坦》中的女性大都温顺怯懦,地位低下,生活均以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男人为中心,有的简直堪称为“家中的天使”。她们的反抗程度轻微有限,且无济于事。伊丽莎白力证贾丝婷无罪,但仍未挽回她的性命,因为后者在法官和教会的逼迫下,不得不担下不属于她的罪名。在维克托拖延婚期时,伊丽莎白虽做出了对当时的女性来说的大胆之举——写信表示自己可以接受取消婚约,但这仍未唤醒维克托的良知,她最终也命丧黄泉。正如西尔维娅·鲍尔巴克所言:“我们在《弗兰肯斯坦》中的女性身上竭力寻找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懑情绪,却徒劳无功。”[13]423
与《弗兰肯斯坦》中的女性相比,《裂缝》中“裂缝族”的抗争显得更加系统、成功。“裂缝族”一直努力争取和“喷射族”平起平坐的地位。她们强调自身不可替代的能力:“我们裂缝人生养了全人类,包括裂缝人和怪物。如果没有裂缝人,世界会怎样?”[7]16在“裂缝族”被“喷射族”伤害时,“裂缝族”的首领马罗娜态度强硬,坚定捍卫族人的利益。她极力称道女人的牺牲与奉献,痛斥男人的不负责任,抗议男人总是欺压使唤她们,并且多次反问道:“难道你不关心我们,霍沙?难道你不为我们着想?”[7]200在裂缝山被“喷射族”炸毁后,她尖叫着控诉他们的罪行。这些较为有力的反抗多少也引起了“喷射族”的重视。他们畏惧“裂缝族”的抗争,霍沙也最终承认马罗娜是对的,接受她的批评。“喷射族”开始尝试理解“裂缝族”,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趋于缓和。
四、结语
从上述对比分析中,似乎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都谴责了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也认同自然对男性的打击报复。这正是两部作品的共同点,体现了其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女性及自然命运的深切关照。玛丽·雪莱生活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盛行时期,其夫珀西·比希·雪莱即为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而自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地位崇高,赞颂自然、回归自然是常见的文学主题。尤其是偏远、荒寂的场所,及其与生俱来的怪异氛围,因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官感刺激,故常成为浪漫派作家叙述故事的场景。玛丽在《弗兰肯斯坦》中选取遥远而鲜为人知的地点制作怪人,并把人迹罕至的北极作为终结故事之处,应是这种写作理念的直接体现。玛丽热爱自然,以女性特有的直觉敏感和洞察力,隐隐担忧由男性主宰的科技进步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同时,玛丽向往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她的原生家庭和婚姻都不甚融洽。其父对她态度冷漠,其夫沉溺于理想主义的世界里,深深伤害了她;其母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虽早逝,但她领先时代的女权主义思想已深深影响了玛丽·雪莱。在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下,玛丽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她的生态主义女性思想在《弗兰肯斯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莱辛向来关注自然和女性。在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辞中,她就对津巴布韦森林被毁深感痛心,也提到恶化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作为女性写作的杰出代表,她对男权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莱辛说:‘拒绝对妇女的支持,绝非是我所愿。……谈到妇女解放的话题——我当然支持妇女解放,因为在很多国家,妇女仍然是二等公民。’”[14]87在《裂缝》中,她呼吁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强调男女之间应互相学习,互帮互助,关爱自然,和谐共生。
这两部作品的不同点在于,与《弗兰肯斯坦》相比,《裂缝》更加强调自然和女性的本质性联系,更加彻底地否定了男权文化二元论,这主要体现在女性与自然及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上。究其成因,盖是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造成的。玛丽·雪莱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重视科技的发展,而忽视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被禁锢在男权社会中,全部生活通常局限在家庭内部,女作家更是一个招致非议的职业。为了避免引起轩然大波,玛丽·雪莱匿名发表《弗兰肯斯坦》,她对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不满,只能隐藏在文中维克托和伊丽莎白看似美满的感情下,而科幻小说的形式也更好地帮助她间接表示自己对于男性蹂躏自然的不认同,以及对人类与自然能否和谐共处的担忧。尽管如此,当玛丽·雪莱作为《弗兰肯斯坦》作者的身份暴露后,玛丽也只得以妥协的方式,强调其写作动机源于丈夫,并两次对作品加以修改,以换取可怜的话语空间。《裂缝》发表于2007年,那时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历三次浪潮,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社会氛围也更为宽容,这也极大松动了绑在女作家身上的道德枷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与科技进步,自然环境逐步恶化,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自然与人类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男性需要停止对自然和女性的“侵略”,才能拯救人类与地球。而世界文学也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诸多文学流派的嬗变,这就为作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写作形式,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于是,莱辛便在《裂缝》中虚构了一个史前世界,以极富象征寓意和充满解构色彩的写作手法,明确强调生态女性道德观,直接批判了男性优于女性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尽情表达自己对男性、女性、自然之间理想关系的深思。
我国古代素有“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思想观念,推崇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而在当今世界,随着科技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成为普遍现象,男性对女性及自然的压迫性统治虽已减弱,但仍未被完全推翻。德奥博纳在其作品中大声疾呼:“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3]57《弗兰肯斯坦》与《裂缝》提醒着人们:自然界和人类本是互相联系、和谐统一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男性并不优于女性,人类并不优于自然。只有尊重女性,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善待自然,才有助于人类迈向“天地与我齐一,万物与我共生”的理想境界,这也正是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