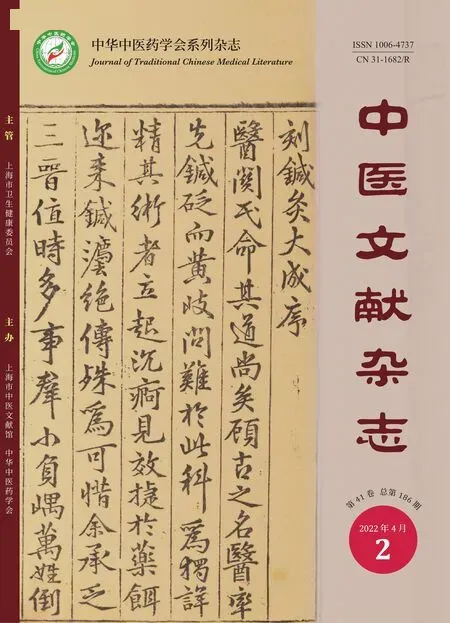《伤寒论》研习问题举隅
2022-12-27高一明
高一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200011)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本文讨论的《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按《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目录分类,特指以宋本《伤寒论》为代表的文本,不包括《金匮要略》(书目正文项下第三项“伤寒金匮”并列)。《伤寒论》的研究,至今问题重重。裘沛然称其现状为“学术多歧、一是难衷”。导致这种现状的关键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考据的问题,二是医理阐释的问题。
文献考据问题
1.版本
《伤寒论》并非单一版本,而是众多版本,非常繁复。目前已知的有《金匮玉函经》、唐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淳化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康平本《伤寒论》、康治本《伤寒论》、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白云阁本)、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刘昆湘本)、涪陵本《伤寒论》等。宋本《伤寒论》是宋治平二年(1065年)宋代政府校正医书局组织高保衡、孙奇、林亿校正的,是目前用于《伤寒论》研究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版本。宋本《伤寒论》已佚。目前,我们所见的宋本《伤寒论》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仲景全书·伤寒论》。全球现存5本,分别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仅著录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而没有明代赵开美的《仲景全书》。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由刘渡舟牵头,以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明代赵开美复刻的《仲景全书·伤寒论》缩微胶卷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版本)对宋本《伤寒论》进行了校勘,成书《伤寒论校注》,可以看作目前最权威的可用于宋本《伤寒论》及《伤寒论》研究的文本。事实上,当代的绝大多数《伤寒论》研究者,至此才得见宋本《伤寒论》的真面。1923年,恽铁樵主持影印的赵开美本《伤寒论》实为1856年日本安政本为底本的伪本。
宋本《伤寒论》底本是节度使高继冲于开宝中(约972或971年)进献的。而高继冲本的由来,历来研究并没有公认的说法(这应该是宋本《伤寒论》最大的问题所在!是文献学学者仍需持续研究的内容)。据裘沛然《壶天散墨》中的观点,高继冲本可能是由唐代十五卷本的仲景方蜕化而来。而唐代的十五卷本,是在隋唐时期传抄节录晋代王叔和编次的三十六卷本或《七录》所著录的三十四卷本。仲景书原有“医论” “方症”两个部分,后人传抄,可能只节录辨证处方的部分,而把医论的大部分略去(删略部分,今尚能检出一二,如周礼贾疏引“神农能尝百草则炎帝者也”等,今本已佚)。晋代王叔和编次仲景书为三十六卷,依据有二:其一,《太平御览》引高湛(另有“张湛”一说)《养生论》谓王叔和编次仲景书为三十六卷,高湛距离王叔和的时代很近,所见应是王叔和原本;其二,晋代皇甫谧距离仲景的时代最为接近,他所看到的《伤寒论》本子当较后世所流传的要真确得多,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汤液经,据汉志,为三十二卷。即王叔和当时编次的仲景书至少大于《汤液经》的三十二卷,与三十六卷卷数接近。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也有专门章节讨论“高继冲本《伤寒论》校注与考证”,但不若裘沛然观点明确。
以上是《伤寒论》版本的大致流传情况。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结论:目前研究以宋本《伤寒论》为主要版本。宋本《伤寒论》的底本是高继冲本,高继冲本及由此上溯至隋唐、晋代的文本,乃至《伤寒论》真正的源头,即《伤寒论》的祖本,至今未确定。宋本《伤寒论》的流传是据明代赵开美的复刻本,而后者在清代《四库全书》编撰时已无著录,目前所见五部,为何在《四库全书》编撰时未被收入?其后又是如何重现的?即宋本《伤寒论》明代赵开美复刻本的流传亦不清晰。也就是说,即使是目前公认最为权威的宋本《伤寒论》,其源、其流,亦是疑义纷纭。
2.书名
《伤寒杂病论》又名《伤寒卒病论集》(宋本《伤寒论》所载张仲景自序即是此书名),《伤寒论校注》称:“《伤寒卒病论》之‘卒’字据宋·郭雍之说当是‘雜’字的俗讹之字,故《伤寒卒病论》当为《伤寒杂病论》。”这是目前较为普遍、公认的《伤寒论》的全称。但也有不同意见,且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当时无杂病之概念可言。不会出现《杂病论》之名称。古代医书均见‘卒病’之名而不见杂病之称。如《肘后备急方》……初名‘肘后卒救方’。”[1]不仅如此,按裘沛然之说“这书经晋迄唐,虽然经过许多名医阅览并且称引,但没有一人提及这个书名”[2]。
3.作者
作为中医学术史上如此重要著作的作者,正史之中没有任何痕迹,这是有违常识的,因此也是最为令人生疑的。“尝考张仲景之事迹,范、陈二史,俱无专传,又并不散见于郭玉、华佗等传中。惟皇甫谧云:‘仲景垂妙于定方’。”[3]
4.成书年代
《伤寒论》的成书年代一般都以自序中提到的“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其中的“建安纪年”推算的。但也有学者提出“‘建安’之‘安’字应据《医史》作‘宁’字之误。建宁为灵帝年号,证以史志,灵帝时有大疫”[3]。如此,则《伤寒论》的成书年代又有争议。
5.卷数
因为版本的流传情况至今仍有许多未能落实的细节,卷数问题自然更是未有确数。但自宋代林亿等始,至当代《伤寒论》研究“泰斗级”人物刘渡舟、钱超尘,一再将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文中提到的“数十卷”误为“十数卷”。宋本《伤寒论·序》:“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刘渡舟《伤寒论校注》校注后记:“皇甫谧(215—282年)距仲景时代甚近,《甲乙经序》已称仲景之书为‘遗论’:‘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云:“《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只需翻检《针灸甲乙经》原著即可确认林亿、刘渡舟、钱超尘之误。当代张灿玾等《针灸甲乙经校注》[4]也为“十数卷”,但出注“原作‘数十卷’,据明抄本及《医经正本书》改”。《医经正本书》由宋代程逈撰于1176年,林亿等校注《伤寒论》时,不可能看到《医经正本书》,更不可能看到明抄本。而《针灸甲乙经》原作确为“数十卷”,林亿等未作任何校注说明径改,更大的可能就是引用错误。而当代刘渡舟、钱超尘在此文献学关键且敏感争议上未作任何说明直接引用,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刘渡舟《伤寒论校注》校注后记称:“王叔和得其遗篇编纂《张仲景方》十五卷,内含《伤寒论》《杂病论》。”学界一般认为,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为三十六卷(据《太平御览》,上文已述),此处又存争议。
6.自序
《伤寒论》自序中提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与上述关于卷数的讨论中涉及的数十卷,存明显差异。如果再考虑上文提到的“建安”“建宁”之辩以及历来对自序中“夫天布五行”以下文字本有疑义,则《伤寒论》自序的真伪也不能肯定。
医理问题
《伤寒论》属于古籍文献,学习古籍文献涉及文献学的诸多专门技能,大致包括目录、版本、音韵、校勘、训诂、注释等。其中,注释与义理问题(在中医古籍文献即为医理)关系最为密切,对注释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完整、准确地解释原文,这是建立在规范的方法学基础上的。而中医古籍注释一直以来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学,《伤寒论》的注释从属于中医古籍注释,同样存在这一共性问题。
“江户后期,对于古来多以主观意识解释古典文献现象加以批判、反省之同时,兴起医学考据学派,直至幕末,此学派之研究成果可谓登峰造极。考证学派继承清朝考证学派学风,将考据方法导入医学领域,热衷于从文献学上,客观注释整理汉方古籍……医学考证学者之业绩,远远超过同领域同时代中国学界之研究。”[5]
“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与日本江户中后期大致相当。乾嘉道咸时期的考据之学,如日中天,家弦户诵,对经传子史之研治影响非常巨大,而对医学界之影响相对较小……章太炎先生对此有所评说:‘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5]
清代考据学是追求系统、规范地注释文献的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对“朴学”(即清代考据学)有10条内容的概括,以下几条尤为重要,正是中医古籍注释中所欠缺的: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孤证不为定说;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日本汉方医家据此在“客观注释整理汉方古籍”上取得了远远高于中国医界的成就。反之,中国医界在中医古籍注释中,由于方法学上面的缺失,其客观性难以被真正的学术研究标准所认同,在《伤寒论》研究中同样如此。
义理注释,在医学文献中还涉及医理。由于中医学学术体系的特殊性,不如西医学具有直接可靠的证据,在客观性上存在不足,故而各逞其说,难决一是。一本《伤寒论》,引出万千伤寒家。其实,中医学与西医学一样,具有实在的证据。症状、体征、疗效,都是绝对客观的。只是中医学在形成中采用了“取类比象”的方法学,其中有抽象、概括的过程,但这些并不否定其客观性,最终中医诊疗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客观的,也是对所有相关中医理论、学说的验证。因此,《伤寒论》医理注释,是有据可凭的,一凭书证之实证,二凭临床之实证,二者有机结合,完全可以实现客观性。至于尚不能证明的,当明确“存疑待考”,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规范。
《伤寒论》医理阐释的问题在中医高等院校《伤寒论》教材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医院校教学《伤寒论》是采用重新编订的教材,均非《伤寒论》的原本。如当前使用的版本——王庆国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之前经典的版本——李培生主编的《伤寒论讲义》,这些教材基本体现了目前《伤寒论》学习的主流。经过编订的教材可能有助于初学者入门,但学习者不能看到著作的原貌,即无法在“一次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研判,利弊得失仍有待评估。而如若教材本身再出现问题,则影响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常见问题如下。
1.原文注释问题举例
《伤寒论》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中“脉阴阳俱紧”的“阴阳”的注释。《伤寒论讲义》称:“脉阴阳俱紧:阴阳在此指脉的部位,即尺部脉和寸部脉。脉阴阳俱紧,指寸关尺三部脉都见紧象。以句首有“太阳病”三字,知指脉象浮紧。方有执说:‘阴谓关后,阳谓关前,俱紧,三关通度而急疾,寒性强劲而然也’。”《伤寒论选读》称:“阴阳俱紧:阴阳指部位,即寸、尺部脉。指寸关尺三部脉均见紧象。”这两个版本教材的内容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学习者必定以为这是历来公认的“脉阴阳俱紧”的“阴阳”的注释。实际上,对于“脉阴阳俱紧”中“阴阳”的注释,至少有3种观点。刘渡舟《伤寒论校注》称:“对‘脉阴阳俱紧’,注家有以尺寸释阴阳者,有以浮沉释阴阳者。《难经》云:‘关前为阳,关后为阴’,故此处之阴阳,似以前说为允。”刘渡舟的注释,正是体现了梁启超归纳的“朴学”原则的规范。“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刘渡舟引用的证据是战国时期的《难经》;教材引用的是明代医家方有执)。两相比较,刘渡舟的注释明显规范、审慎。但这样有规范的注释,在近代中医高等院校教材中少有体现。由此上溯历代以来的各家注释,大多“有失法度”。中国医界是中医研究的主流,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就格外突出。关于“脉阴阳俱紧”中“阴阳”的训释,曹颖甫的《伤寒发微》,其实还提出了“左阴右阳”的观点。
2.方证释义问题举例
以下再以《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桂枝汤”为例,重点说明注释的规范对于义理阐释的重要性和教材所呈现的重大问题。
《伤寒论讲义》在桂枝汤证之上冠以“中风表虚证”,在“方义”项下称:“方中桂枝辛温,解肌祛风;芍药酸寒,敛阴和营。两药配伍有调和营卫之功。”《伤寒论选读》同样,在桂枝汤证之上冠以“中风表虚证”,在“方义”项下称:“方中桂枝辛温,解肌祛风,温通卫阳,以散卫分之邪。芍药酸苦微寒,敛阴而和营。桂枝配芍药,一散一收,一开一合,于发汗之中寓有敛汗之意,于和营之中又有调卫之功。”
千百年来,上述观点可谓“统治”了桂枝汤证义理的阐释。其实,此说经不起推敲。其中,最大的疑点或突破点在芍药这一药物的功效上。《伤寒论》112方,用到芍药的有30余方。其中,第279条、第280条最能说明芍药的功效。第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桂枝加芍药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六两,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擘),生姜三两(切)。桂枝加大黄汤方:桂枝三两(去皮),大黄二两,芍药六两,生姜三两(切),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擘)。”芍药在桂枝汤方基础上再加量至六两,针对的症状是“腹满时痛”;进一步,“大实痛”者,再加大黄二两。此处,“大实痛”已明确了属于实证,加入大黄这一公认的攻逐泻下的药,若芍药具有上述“敛阴而和营,一收、一合”的功效,则断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方中,且有六两之众。第280条,更明确了芍药确实是泻实之药:“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下利者,先煎芍药三沸。”其中,“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芍药与大黄同列,则芍药的功效属于和大黄同类,是针对实证的,绝对不是针对虚证。“宜减之”的原因也非常明确了,“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故,以此两条,已可明确,芍药非补虚药,而是泻实药。第31条也可证芍药非为“敛汗”所设:“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方一。葛根四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生姜三两(切),甘草二两(炙),芍药二两,大枣十二枚(擘)。”此条明确“无汗”,且用发汗之麻黄,故无桂枝汤证“有汗”之“于发汗之中寓有敛汗之意”之必要,方中仍用芍药,则直接可证芍药非为“敛汗”所设。再遵“朴学”中“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更多的书证有:第100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五十一。用前方。 桂枝三两(去皮),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擘),芍药六两,生姜三两(切),胶饴一升”。其中,“腹中急痛”之“急痛”为本条法眼,急痛多为实证,虚证多为缓痛,此为通则。且“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亦提示,小建中汤服用后起效迅速,可以马上判断是否对症,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多见于实证,而虚证往往起效较慢。小建中汤中,芍药同样有六两之众,应属关键用药,而应用于实证治疗,则其功效在泻不在补当非常明确。第103条:“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呕不止、心下急(一云,呕止小安),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方五十三。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升(洗),生姜五两(切),枳实四枚(炙),大枣十二枚(擘)。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此方同理,“下之则愈”,不避芍药。以上为《伤寒论》内可见之书证,按“朴学”之“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当属最强之证据。《伤寒论》以外书证,当首推《神农本草经》,该书为目前所见最古之本草著作,与《伤寒杂病论》同属中医四大经典。《神农本草经》“芍药”载:“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全无“敛阴而和营,一收、一合”之说,尤其“血痹、坚积”,是绝无可能以“敛”“收”“合”为治则的。至此,已基本可以明确以中医高等院校《伤寒论》教材为代表的对“桂枝汤证”中芍药功效的阐释是完全错误的。进而,以此芍药的功效对“桂枝汤证”进行阐释也就完全不成立了。特别是“于发汗之中寓有敛汗之意”已没有了方药的基础,“中风表虚证”的千年之说,自当无据了。桂枝汤证以“表虚证”概括之乃理论错误。
综上,《伤寒论》研习中问题重重。根本问题在于“底本未定”,且一时难以解决;其次在于“注释失范”,“多以主观意识解释古典文献”,故“学术多歧、一是难衷”的局面在所难免了。加强“注释”的规范性是解决《伤寒论》学习中出现上述问题的首要方法,如此。才能在医理阐释上更为科学、严谨,进而可以统一整个中医学术史中长期存在的重大争议,最终使中医学术去伪存真,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