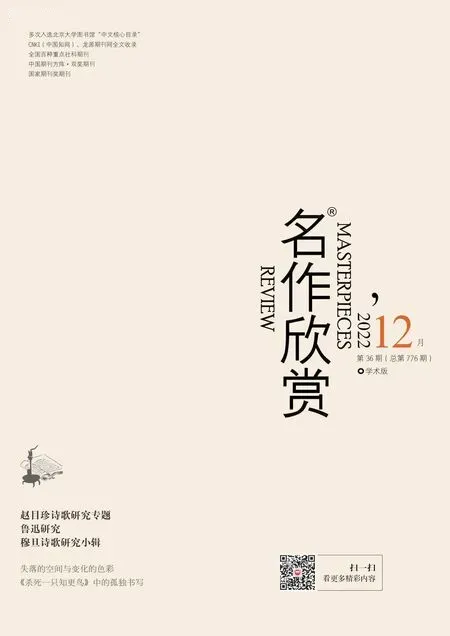论“写小说是跟人聊天”
——从汪曾祺小说中的“括号现象”谈起
2022-12-25潘西方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潘西方[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提起汪曾祺的小说观,已有研究基本可以概括为:写小说是写回忆,写小说是写气氛,写小说是写语言。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不足以完全体现汪曾祺小说的独特性。“写小说是跟人聊天”作为汪曾祺小说独特艺术风格的一个面向,却未被充分地认识和论述。这一说法出自汪曾祺1984年给邓友梅《烟壶》写的评论。汪曾祺在分析邓友梅的语言时提到,“写小说,是跟人聊天,而且得相信听你聊天的人是个聪明解事,通情达理,欣赏趣味很高的人”。这也是夫子自道。有研究者对汪曾祺的“聊天”小说观有所关注,如欧阳灿灿就“作者与语言、读者的关系”做专门论述;余岱宗在论述汪曾祺小说的“杂语气氛”时,提到汪曾祺对“离题”“闲聊”的喜爱与“聊天”的小说观相关;翟文铖在分析汪曾祺小说的口语化叙述时说到“聊天”的语式。这些论述主要在语言学领域展开讨论,显然不足以充分阐释“写小说是跟人聊天”的复杂内涵。
笔者细读汪曾祺小说,发现汪曾祺行文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却基本被忽略的现象,就是大量使用括号,通过括号内语句来增补正文。本文尝试从“括号现象”论析汪曾祺的“聊天”小说观,通过文学解读分析作家如何认知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小说功能等,进而探讨汪曾祺“聊天”小说观的独特性及其对传统文学的继承。
一、汪曾祺小说的“括号现象”与“聊天”功能
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偶尔会遇到作者为了使表述更加清楚而在行文中使用括号来加以解释的现象。例如丁玲描写莎菲看到苇弟哭泣时的心理:“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的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鲁迅在《故乡》里面也使用过括号,如:“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这种形式在废名、郁达夫、老舍、孙犁等笔下也时有见到,但通常不会引起我们过多注意。汪曾祺在行文中使用括号的数量之大、次数之多让人无法忽略,值得关注和深究。
汪曾祺一生共创作162篇短篇小说,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含有括号现象的占125篇,共使用括号635个,平均每篇近4个。行文大量使用括号,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一个独特现象。对于汪曾祺不同时期小说中使用括号的情况,笔者整理成如下表格:

从表格可看出,行文中使用括号的现象贯穿汪曾祺整个创作生涯。而有些篇目中的括号数量尤其突出,超过20个的有《老鲁》(22个)、《大淖记事》(32个)、《故里杂记》(24个)、《云致秋行状》(31个)。汪曾祺写过很多评论,却从未提到过他为何偏爱使用括号这一现象,关于汪曾祺小说的评论文章也很少讨论这一现象。①
汪曾祺小说中的括号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出现在段落之内。例如:
终于,她跟我讲和了。站起身来,伸手理一理被调皮的风披下来的几丝头发(用黑夜纺织成的头发!)。(《翠子》)
许是在一个春假里罢,(不是春假也就算是春假,何必顶真,春假是不是所有假期里最好的一个,你说?)我们两个,玉哥和我——(《春天》)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戴车匠》)
《翠子》中,作者以孩童的视角,用诗性的语言注释翠子的黑发,为的是写出此时翠子的美与她最终却要跟一个乡下跛子男人结婚的命运之间的反差,使小说更具艺术张力。在《春天》中,作者好像要跳出来和读者商量,让读者参与自己的创作,这里除了注释“春假”外,显然还有同读者“聊天”的意思。括号作为一种标点,主要用来表示文中注释的部分。徐赳赳借助西方语言学“元话语”的概念,将括号的注释功能扩展为详释功能、释疑功能、补说功能、补足功能和介入功能五个子功能。《春天》里的这个括号,我们可以将其功能理解为作者的介入。《戴车匠》是时隔三十八年的旧作同题重写,引文里的括号好像没有明确的注释对象,其实括号的使用让读者明了1981年的那次还乡是时隔四十余年的还乡,这就使小说除了表达对传统手艺没落的感慨外,还流露着作者一丝隐隐的乡愁。
第二种形式是括号独立成段,例如《同梦》《求雨》《岁寒三友》等篇中括号的使用。括号独立成段,注释的就不仅是括号前面所涉及的一些简单的词句了。例如《岁寒三友》,靳彝甫的蟋蟀帮他赢了四十块钱,然后他在如意楼请王瘦吾、陶虎臣喝酒。之后汪曾祺以括号的形式单独成段,插入蟋蟀的命运:
(这只身经百战的蟋蟀后来在冬至那天寿终了,靳彝甫特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银棺材,送到阴城埋了。)
作者用这种方式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给靳彝甫赢过钱的蟋蟀,而“银棺材”“阴城”等字眼也能使读者感受到靳彝甫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也为后来靳彝甫卖掉三块黄田接济“拥着一条破棉絮”的陶虎臣、“家徒四壁”的王瘦吾埋下伏笔,为最后三人在下雪的除夕一起喝酒时所产生的艺术力量蓄势。
本文开头所引丁玲在叙述苇弟哭泣时使用的括号主要注释苇弟年龄,这个注释有助于塑造苇弟形象;鲁迅在《故乡》中所使用的括号主要解释何为“忙月”,但客观上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为之后闰土的到来埋下伏笔。相较于丁玲和鲁迅小说中使用括号的情况,汪曾祺使用括号除了注释对象、塑造人物、经营情节等以外,还涉及主题表达、作者自白、语言经营、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等方面。可以说括号的使用使汪曾祺的小说文本面对读者时更加开放,使读者更容易进入小说、离作者的距离更近,背后所指向的则是“写小说是跟人聊天”这一小说观,以及作者对读者的重视。
二、“聊天”小说观的主要特征
“写小说是跟人聊天”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作者要通过“小说”这一媒介来与读者分享生命、生活的体验,这种分享的姿态是彼此平等的。“聊天”小说观反映出汪曾祺对读者的重视和对小说交流功能的认知。“聊天”小说观的主要特征是小说叙述中会呈现出“两个作者”。翟文铖在解读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时也注意到他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时,常有叙事者“我”的凸显。翟文铖把这种叙事方式归结为五四文学的影响,与本文论述的侧重点不同。
“聊天”和小说有相似性,它们都是交流的艺术。“聊天”时说话的双方是可以随时互动的。说话的语言变成文字落实到纸上,再由读者去接收,此时“聊天”者双方(作者和读者)的时空就发生了变化。汪曾祺大量使用括号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聊天”的鲜活性,括号这种形式承载着作者的在场感和读者的参与感。具体到汪曾祺的小说,行文中大量使用括号使汪曾祺小说中出现两个作者:一个是讲述故事的作者,另一个是与读者“聊天”的作者。我们可以从诸多实例中看到这一点。例如:
北京,大帅走进胡同,一个最红的姐儿,窑姐儿刁了枝烟,(老鲁摆了个架势,跷起二郎腿,抬眉细目,眼角迤斜,)让大帅点火。……大帅说:“俺是山东梗,梗,梗!”(老鲁翘起大拇指,圆睁两眼,嘴微张开半天。从他神情中,我们知道“梗,梗,梗”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个字实在不知道怎么写。大帅的同乡们,你们贵处有此说法么?)窑姐儿说是你老开恩带我走吧。大帅说,“好诶!”(大帅也说“好诶”?)真凄惨,(老鲁用了一个形容词。)烧!大帅有令,十四岁以下,出来。②
上述引文主要是作者在描述老鲁讲的故事,但在行文的过程中,作者以括号的形式穿插对老鲁的描述,这就把自己置于与读者并排的位置,一起来“欣赏”小说中的人物:老鲁。这里的括号就把作者与读者“对面”的位置关系,变成了“并排”的位置关系。这个故事是作者单向讲给读者的,其中老鲁这个形象却由作者和读者并排观看。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的作者是与读者并排坐着的,要和读者一起合作讲故事的。汪曾祺在写于1947 年的评论中提到“也空出许多地方,留出足够的时间,让读者自己说。他不一个劲儿讲演,他也听”。联系他发表于同一年(1947 年)的小说《醒来》,可见他小说理论和小说实践的一致性:
我想讨论一点东西:(我自以为现在已失去不少讨论的热情了,)一个军官在缅甸陷落战役中,(一次战役好了,)惠通桥断了,(随便一个桥吧,)失了归路,他得用平常不用的办法归来。
在上述引文中,作者是在和读者一起创作。这背后的态度是他也把读者当作了短篇小说家。他把写作的材料和要表达的主旨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一方面是组织故事的作者,他要讲述一个军官在一次战役中陷落,最后和少量士兵归来的故事及途中的意识变化、生存体验;另一方面是以括号的形式与读者“聊天”、与读者“合作”的作者,关于战役的名称、地点、人数等细节,要和读者一起商量。
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局限于使用括号的篇目。例如在《大淖记事》结尾时另一个与读者“聊天”的作者现身:“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相似的例子还可以在《老鲁》《落魄》等很多篇目中见到。而且那个讲故事的作者也不是正襟危坐的,而是能给读者带来聊天般愉悦的讲述者。汪曾祺曾经在1947年和1984年两次论述对读者的重视。他在1947年谈到短篇小说的本质时说:“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与沈从文交往很多,1940年8月3日曾听过沈从文题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沈从文写于1941年的《看虹录》中也大量使用括号。这些或都曾给汪曾祺理解小说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带来过启发。在1984年写的《漫评〈烟壶〉》中汪曾祺这样表达对读者的重视:
作者在叙述时随时不忘记对面有个读者,随时要观察读者的反应……写小说,是跟人聊天,而且得相信听你聊天的人是个聪明解事,通情达理,欣赏趣味很高的人,而且,他自己就会写小说,写小说的人要诚恳,谦虚,不矜持,不卖弄,对读者十分地尊重。
从汪曾祺20 世纪40 年代和20 世纪80 年代的评论与创作中,可见他对读者的重视是一贯的。沈从文在1982年复友人信中曾用“素朴亲切”来概括汪曾祺小说的特征。“素朴亲切”的背后除了汪曾祺对人事和文字应用的深刻理解,还与他对读者的重视密切相关。在现当代作家中几乎没有如汪曾祺这样重视读者的。在作者、小说、读者这三者的关系上笔者同意王柏华的看法:“读汪曾祺的文字,使你感动的……是他的感情,他对人物的那种深刻的关切和同情,以及他对读者的平等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废名、萧红,甚至他的老师沈从文都及不上他。”
三、“聊天”小说观与汪曾祺的独特性
当我们称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时,强调的是他身上传统的一面。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提到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黄子平强调汪曾祺的意义在于把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了新时期文学面前。王尧认为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有两个:一是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一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在笔者看来,“聊天”小说观作为汪曾祺创作的独特性体现,与传统文学有密切关联。
首先就古典小说叙事传统来讲,汪曾祺认为“中国短篇小说有两个传统,一是唐传奇,一是宋以后的笔记”。大体来讲,一个重视情节,一个讲究亲切。以情节取胜的古典叙事类作品中有与汪曾祺“聊天”小说观相类似的地方。例如在《史记》中,文末常有“太史公曰”;在《聊斋志异》中,文末常有“异史氏曰”。汪曾祺虽没有在小说的文末以“汪曾祺曰”来结尾,但《大淖记事》《落魄》《最响的炮仗》等小说的结尾却有类似的处理,都是以异于故事叙述者的另一种声音收尾。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作者直接跳出故事,来发表议论,与读者沟通(“聊天”)。汪曾祺在正文的叙述中也常用括号的形式展现出另一种声音,来达到相似的效果。这种形式,我们可以追踪到最初市井说书人那里。王德威认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可能就是其不断运用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我们可以将这种虚拟修辞理解为一部作品由说书人在现场讲述故事时所使用的艺术手段。这种策略的效果就是“当读者参与和说话人沟通的模拟情况时,好像他不止接受语言临场传达情况的有效性,并且也分享说话人所感觉到的‘真实’视景”。而汪曾祺在行文中使用括号也会给读者某种“真实”的感觉,使读者游走于“虚构”与“真实”之间。我们可以将汪曾祺小说中的括号与明清小说中的“说话”传统联系起来,以此作为汪曾祺衔接传统的一个中介来思考。
其次就“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而言,“聊天”小说观是汪曾祺在继承京派基础上的发展。周作人曾说废名的文章“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汪曾祺的小说,也体现了这样的随意性。汪曾祺常常以括号的形式打断自己的故事,插入相关的话题,然后再回到故事中来。例如:“有的是一道,有的是两道,有的是一个十字叉叉,那个脸红通通的小伙子,(他的棉袄是新的,鞋袜干干净净,他不喝酒,不赌钱,他是个好‘儿子’,他有个很疼爱他的母亲。我并不嫉妒你!)尽挑那种嘴上两道的。这是记认。”汪曾祺的“聊天”是随时可中断亦可接续的。他在以聊天的思维方式行文,这是与京派很多作家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汪曾祺一贯的追求,他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也与聊天的“随意性”有相似之处。
一般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可分为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时期。对于前一时期,论者多强调其作为京派尾声的代表,对其独特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作品中的技巧、风俗的描绘、文化意味等方面。对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论者多将其置于“寻根小说”的视野中来把握,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观基本可以概括为“写小说是写回忆,写小说是写气氛,写小说是写语言”。但是这种对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时期小说特点的概括也常常适用于京派的其他作家。笔者以为,将“写小说是跟人聊天”这一贯穿汪曾祺创作始终的小说观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谱系中,可见出汪氏小说的独特性。首先就现代文学来说,启蒙与革命是其主线,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汪曾祺想要通过作品来和读者“聊天”显得很是“异类”。即使放在京派的谱系中来考察,汪曾祺小说的这一特征也在严家炎总结的京派小说四个特征之外。其次就当代文学而言,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题材决定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再到新时期派别多样的小说类型,当代文学整体呈现出由“特定的文学规范如何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到这种规范与支配地位被打破,文学格局得以重组的过程。而在这一变化当中,作者与读者的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也就很难有“聊天”类小说出现。汪曾祺这种具有“聊天”效果的小说,自然有独特性。汪曾祺的“聊天”小说观可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被称为“小说怪才”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难以归类这两种说法做一注脚。
总而言之,汪曾祺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括号现象”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述形式。这种行文方式体现了汪曾祺的“聊天”小说观,是对小说的“交流”功能、对与读者平等对话的重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小说本质上是一种作者与读者推心置腹地交流人生经验或生命体验的叙事文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的“聊天”小说观传承了古典小说的“说话”传统,铸就作家融汇古今的创作特性,在当下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① 王彬彬曾经注意过汪曾祺“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句号、冒号、括号等现象,探讨的是鲁迅对汪曾祺的影响,但对括号这一现象并未展开分析。参见王彬彬:《“十七年文学”中的汪曾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② 本文所引用文字中的省略号皆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