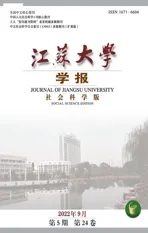民族志文化翻译与赛珍珠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
2022-12-24朱骅,原芳
朱 骅,原 芳
作为一个身处亚洲数十年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赛珍珠在亚洲的游历以及相关的亚洲书写不可谓不丰富,仅长篇小说中就有写印度的《曼陀罗》(Mandala, 1970)和《来吧,亲爱的》(Come,MyBeloved, 1953),写朝鲜半岛的《活笋》(TheLivingReed, 1963),写日本的《匿花》(TheHiddenFlower, 1952),写缅甸的《诺言》(ThePromise, 1943)等,但国际学界谈论最多的还是她丰富多样的中国书写,譬如晚清的宫廷(ImperialWoman, 1956)、皖北的农民(TheGoodEarth, 1931)、开封的犹太社区(Peony, 1948)、深宅中执掌一切的夫人(PavilionofWomen, 1946)、农民抗日游击队(DragonSeed, 1942)、走向群众的知识分子(Kinfolk, 1949)等,这其中又以她表述的乡土中国受到格外关注,正如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 1910—1986)所言,“在所有喜爱中国人,试图为美国人描述并解释中国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赛珍珠那样卓有成效,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比她那著名的小说《大地》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她为一整代的美国人制造了中国”(1)哈罗德·伊罗生. 美国的中国形象[M]. 于殿利,陆日宇,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153.。这就意味着她的中国书写以乡土中国为核心建立起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强大知识体系,人们在这个阡陌纵横的知识路径中可以检索到所需的信息。以虚构文学一己之力产生远超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赛珍珠作为知识建构者的身份必须经受住考验,其书写策略必须符合有关他者知识的生产流程,她自己对知识的有效性范围必须有恰如其分的定位。
一、 知识建构者的资质论证
正如人类学家必须告诉读者自己田野作业的经历,赛珍珠要让读者接受并相信她所提供的中国知识,就必须证明自己的代言资质,这首先仰赖出版社的营销宣传。在1931年一份标题为“作者信息”的四页小册子中,庄台出版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将赛珍珠描写为在中国度过大半人生,“从童年起时常穿中国服装,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2)LEONG K J.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26.。这些细节描述旨在强调赛珍珠的言说资质,并向美国读者承诺可以一瞥“真正”的中国。而在《大地》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后,赛珍珠向美国读者进一步证明她的中国书写的准确性。她从南京写信给当时的出版人即后来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告诉他中国读者的正面评价:“中国报章对《大地》普遍的良好评价让我开心极了。以下是一些典型评论的摘录……我给您寄送这些,是因为毫无疑问许多美国读者询问我在多大程度上真实于中国的生活,以及中国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她又补充说,“我当然会将中国读者当成我最重要,实际上也是最终评价者,所以您理解我对这些评论的满意程度”(3)BUCK P S. Pearl S. Buck to Richard J[A]. John Day Archives, Walsh, 22 July 1931, Nanking, box 36, folder 3.。
此外,她还将围绕她的身份质疑策略性地转变为一场中国文化权威身份宣传。当时在美国新诗运动中有一席之地的华人精英江亢虎,对赛珍珠的中国农村与农民书写不以为然。他在《纽约时报书评》撰文认为赛珍珠的中国知识存在缺陷,对中国民间生活并不熟悉,小说中出现不少民俗错误,此外他还认为赛珍珠夸大了中国生活的阴暗面,以取悦美国读者,农民群体不能代表中国。“他们对生活的观念非常奇特,而且他们的常识委实有限。他们虽说构成中国人口的多数,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尽管布克夫人以最普遍的方式不带偏见地描写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呈现一幅客观的中国画面。”(4)KIANG K A. Chinese scholar’s view of Mrs.Buck’s novel [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33-01-15(2).
赛珍珠在答复中首先对受到质疑的民俗细节进行反驳,特别指出,“但凡此诸点,均非重要,中国各地习俗彼此差异很大,不可能存在固定不变的风习,只能够说在我所处的地区见到的是这样。因此,我只选择自己最熟知的地方,这样至少对某一地区来说不至于失真,再加上我曾将所写内容读给该地区的中国友人听,以求印证”(5)BUCK P S. Mrs. Buck replies to her Chinese critic [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33-01-15(2).。赛珍珠所强调的是其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熟知,她接着反问江亢虎,“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6)同①.?江亢虎的质疑反过来高调地强化了赛珍珠言说中国的权威性。
赛珍珠通过赋予自己“中国性”(Chineseness),选择做一个美国的“中国妇女”而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身份。这样既避开了与男性知识分子的正面冲突,又找到了他们不熟悉中国平民大众的知识盲区,这样她的声音也就具有了知识权威的力量。此时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表述中国的西方知识体系中缺席,从而使西方必须依赖她这位白人“中国专家”?原因即在于美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少数族裔的“结构性空缺”(Structuring absence)(7)LEONG K J.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51.。
诚然,在中国的共和国初期西式教育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真正能学贯中西并进入美国知识界的中国人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剥夺了美国知识界中这些少之又少的中国学者的言说空间,即使他们偶尔获得言说机会,美国公众也只是选择性倾听,任何不符合刻板印象的言说都会被贴上“民族自卑感”或“防御性辩解”的标签,被认为不够客观而不受重视。赛珍珠选择做一个中国女人,却能被允许说话,而且有人倾听,原因就在于她明确无疑的白人种族身份和美国国家身份保证了她选择做“中国女人”策略的可行性。
赛珍珠一开始就强调她的代言对象是中国的草根阶层,这使她获得了平民思想深厚的美国大众的认可。即使之后赛珍珠邀请林语堂向美国大众介绍中国精妙深奥的雅文化,这也只能作为赛珍珠中国知识体系的有益补充,无法取代赛珍珠作为中国专家的权威身份。华人被阻挡在公共话语之外,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又使公众急于了解中国。由此“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的赛珍珠填补了这一“结构性空缺”。
二、 文化翻译的民族志策略
赛珍珠主动边缘化的身份定位、出版商对其数十年旅华身份的大规模宣传以及美国学界华人的结构性空缺等因素,将赛珍珠置于“大众中国通”(popular expert on China)的位置(8)HUNT M. Pearl Buck—Popular expert on China, 1931—1949 [J]. Modern China,1977(1):33-64.,但有这样的知识建构资质不等于说她就能自动建立起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能否建立还取决于她在特殊的国内国际语境下如何顺势而为,言说什么以及怎么言说。
在美国一战后加速海外扩张的语境下,美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兴趣日益浓厚,此时读者期待她谈论那些等待美国“拯救”和“重塑”的异教世界,但谈论的方式必须“合标”,即符合公认的知识生产方式。此时为美国读者提供有关他者知识的主渠道是刚刚兴起的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是以开明的文化相对主义面目出现的博厄斯(Franz Boas,1885—1942)。博厄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都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对他族文化的描写和表现并不是简单地将他族书面语或口语转换成本族语,而是一种对他族文化的了解、阐释和决定的过程(9)BOAS F. General anthropology[M]. New York: D.C.Heath and Company,1938:1-6.。文化异质性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他呼吁不同文化间相互尊敬和交流。文化相对主义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自我标榜的利他主义构成历史呼应,也和此时美国海外传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转向、跨国公司全球推广的在地文化适应政策相应和。
文化相对主义直接影响了人类学的终端产品之一“民族志”的撰写原则,以二手资料撰写民族志的“扶手椅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被抛弃,田野作业的参与观察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学者王铭铭认为民族志作者亲自到某一民族社区进行长期生活,参与该社区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并通过学习当地语汇和思考方式,理解当地文化,在回到自己的家园后以一定的叙述框架论说这种参与的体验和发现(10)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一个成功的参与观察者有可能以贴近文化持有者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他所研究的文化,也能够水到渠成地进行作者隐身的零度写作。
在中国长大成人的赛珍珠已经大大超出了任何一位采用参与观察法的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时间,更不用说那些短期赴华根本不懂汉语的政府官员或商务人士,即使相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著作等身的传教士如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1842—1912)、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等人,她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她能从作为母语的汉语中感知到细微而隐秘的含义变化,本能地领会并阐释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隐在的(latent)文化深层结构。
聪明的赛珍珠自然知道自己在阅读市场中的强项与弱项,强项是她对东方中国深入肌肤的了解,弱项是对美国生活与思维方式的隔膜感。要扬长避短,她就自觉不自觉地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达成视域重合与话语共谋。她需要将中国人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美国学界与普通读者能理解的话语表达。简而言之,她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文本,整体性译介进英语世界。她的写作是一个阅读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与翻译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的过程。
翻译有效与否的第一步是选择译什么。除了集体无意识驱动的日常文化实践,文化的生命逻辑更多体现在标志性的人生阶段转换中。对人生阶段的呈现,可以直观地以点带面地呈现他者的人生,象征性概览另一种生命节律。如果说中国人的人生是一条河,赛珍珠的中国书写几乎都是长河小说,尤其体现在王龙家族的生命历程中。《大地上的房子》系列从王龙鄙陋的婚礼开始,然后子女陆陆续续出生,之后是儿子们陆陆续续结婚生子,王龙夫妇去世后儿子们呼风唤雨又老去,孙子们走上前台。这样一个有纵深度的生命画卷是无论多少幅人类学专题速写也无法拼贴出来的,将这条生命链串起来并推动其绵延不绝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内核,也是赛珍珠有关中国生命叙事的震撼力所在。
赛珍珠大写特写每一个生命坐标,在生命坐标之间,填充丰富的物质(世俗需求)与精神(信仰体系)的中国文化细节,形成中国文化有机体。首先来看王龙生命历程的关键点:结婚。穷人王龙无力用锦缎、花轿、乐队和司仪标注一段生命历程的开始,但不是说就没有仪式感。赛珍珠这么描写清晨王龙为大喜做准备:
他匆忙来到堂屋,一边走一边穿那条蓝色外裤,一边往结实的腰上系那条蓝棉布腰带。他光着上身,等着烧热了水洗澡。他来到灶屋,一间挨着房子的小披屋。黎明中一头水牛从门角落里甩着头,对他低沉地哞叫。灶屋和正房一样是土坯搭的,大大方方的土坯是从自家田里挖的,盖屋顶的麦秸也是自家地里砍来的。他祖父年轻时抹了这口灶,做了多年的饭,灶烤得黑乎乎的。这泥灶上坐着一口又深又圆的铁锅,锅里注了七分满的水。他用瓢从灶边的瓦缸里舀水,因为水金贵,舀得小心翼翼。之后,他犹疑片刻,突然抱起水缸将水都倒进锅里。今天他要全身洗一遍,自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膝盖上洗澡,还没人看过他的身体。今天有一个人要看到,他要将它洗干净(11)BUCK P S. The good earth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31:3-4.。
对于水资源紧缺的农民来说,酣畅淋漓地洗一次澡,已经足够有仪式感,甚至有基督教洗礼的隐喻。更重要的是,赛珍珠不落痕迹地提供了前现代农业中国的知识,这是一个以土地为中心,人和耕作的土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微循环生态系统,即学者徐清曾经指出的中国农民的植物性生存状态(12)徐清. 赛珍珠小说对乡土中国的发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16-24.。读者们也从这样的生存境遇中看到了皖北农民的物质文化特征(土坯茅屋)、该群体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生产力发展程度(使用畜力)、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贫下中农)、衣着特点(家纺棉布)、居家用品(陶铁器具)、生火做饭的方式等等。
但赛珍珠并没有将中国农业社会扁平化,而是全面展示阶层差别,为此她精心描摹了另一场婚礼,也就是实现了阶层跨越之后的王龙为大儿子举办的婚礼,在这样的婚礼中,新娘成为财富和民俗的展台:
她们替她把身子从头到脚洗干净, 用一块新的白布裹了脚, 外面又穿了一双崭新的袜子。荷花先往姑娘身上擦了些她自己的香气扑鼻的杏仁油, 然后, 她们给她抹了香粉和胭脂。之后又替她穿上她从家里带来的嫁衣, 紧贴着她那温馨的少女皮肤的是白色的绣花绸衣, 外面是一件精制的羊毛料罩衫, 最外一层才是那件大红的缎子嫁衣。然后, 她们在她的前额上搽了滑石粉, 用一根打结的线巧妙地替她把眉毛上方的汗毛拔去。她们把她的前额梳理得又高又宽又亮。然后又给她搽了香粉和胭脂, 用眉笔在她的眉毛上画出两道细眉。她们给她戴了一顶凤冠, 披了头红, 给她的小脚穿上绣花鞋。她们还在她的指甲上涂了蔻丹, 在她的手心里搽了香水。就这样, 她默默地听任她们摆弄, 显得有点不愿意, 也有点害羞。对于一个将要成亲的姑娘来说, 她应该有这样的表示(13)BUCK P S. The good earth[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1: 274.。
和贫穷的王龙只有洗澡这唯一的仪式不一样,大儿媳在洗净的身体之外覆盖了层层叠叠细细碎碎的“文化”:性文化、祈福文化、闺阁文化等等,都在一个个细节中呈现出来。赛珍珠并未做评论,却通过婚礼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全貌: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土屋、园林、开阔的农田、封闭的闺房等,读者从繁简不同的婚礼中看到中国人自己对文化的阐释与因地制宜的实践方式,也逐渐领略到赛珍珠通过情节发展形象化地呈现她对中国人自我阐释的再阐释。
宗教信仰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最外显的精神特质,是价值观与宇宙观的核心部分,因此也是民族志文本最核心的关注点以及赛珍珠创立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点。中国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以及被宗教化的世俗儒学体系,这些信仰具有相似的仁爱观,但有不同的尊崇对象,它们下沉到目不识丁的农民阶层时已经纠缠不清。农民们理不顺不同信仰的脉络,于是他们采取功利法则,需要什么就拜什么。婚礼那天,王龙领着刚买来的丫鬟阿兰回家成亲,半路上特意停下来给自家地里的土地神上香,这是农民们最直接的守护神:
这个土地庙是座很小的房子,只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用灰砖砌就,顶上盖了瓦片。王龙的爷爷曾在这块地上耕作——现在王龙自己也靠它为生——是爷爷用手推车从城里推来砖盖起这小庙。庙外面抹了灰泥,在一个收成好的年头曾雇了画匠在白石灰墙上画了一幅山和竹子的风景……庙里坐着两尊小而严肃的神像,他们是由庙周围的泥土做的,在屋顶下受到很好保护。两尊神像是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每年过年时,王龙的父亲都买些红纸,细心地为这对神像剪贴新衣服(14)同①: 24.。
准备成亲的王龙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特地买来香烛,和阿兰一起祭拜。他们祖祖辈辈宁愿自己住在泥墙的草屋里,也要到城里去买砖砌土地庙;尽管自己穿着破旧的衣服,也忘不了每年给土地神做新衣裳,由此可见农民对土地神的敬重和恐惧。
但中国农民的神祇信仰心理又是功利的,形成一种有用则近、无用则疏、有神则拜、多多益善的信仰态度。中国农民并非仅仅信奉与之共同生存的土地神,其神灵崇拜是广泛的。希冀风调雨顺就拜“龙王爷”,盼望传宗接代就找“送子娘娘”,求富贵就供奉财神。各路神仙各司其职,依据人们的需要发挥作用。王龙致富后就转而供奉财神爷,将财神像挂在堂屋正中,买了上好的锡香台和锡香炉。待到非常富有了,就懒得再拜什么神仙,连给众神烧几炷香都不干。在农民眼中,芸芸众神多为势利贪小之辈,喜奉承,贪供品,欺软怕硬,避贱迎贵。他们烧香拜神,是幻想以贿赂求通融,以较小代价(香烛、红纸等)换取较大的实际利益(丰收、得子、祛病等),一个神灵香火盛衰直接与该神灵近期的灵验度有关。大旱之年,王龙拖着饿得虚弱的步子走到土地庙,故意把唾沫吐到土地神冷漠的脸上。
植物型生存的终极是回归土地,但回归方式却因人而异,也是重要的文化展台。赛珍珠对富人王龙的葬礼描写,无论在有关中国的民族志还是海外文学中都是空前绝后的。王龙仅一口楠木棺材就花了近六百两银子。老朽的王龙就躺在棺材边,精神好点的时候,会伸出颤抖的手抚摸那漆得铮亮的外棺(15)BUCK P S. Sons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32:4.。这种情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怪异的,但却揭露了一个传统中国大地主强烈的占有欲和对待死亡的功利性态度。另外,对这个万人空巷的葬礼,赛珍珠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以王龙的两个儿子抚慰垂死父亲的方式呈现:
我们都去给您送葬,出殡的人至少得排一里多地。您的太太、姨太太们都会去哭您,还有您的儿子、孙子,都给您披麻戴孝,村里人和您的佃户们也都去!走在最前面的是您的魂轿,里面放着我们请画匠为您画的像,跟着是您那口最体面的大棺材,您老躺在里面就跟皇上一样,装裹您的新衣服都为您预备好了。我们还租了顶绣花棺罩,深红的底,金色的花纹,可好看了,把棺材抬着走过大街时,把罩子盖在棺材上让镇上的人都能看到……我们还要请和尚念经为您超度。我们还专门雇了哭丧的和抬棺材的,穿的是红黄色的袍子,还要扛上我们为您命赴黄泉之后准备的各种东西。大厅里已经糊好了两套房子,一套跟您这里一样,另一套跟城里的那套一样,房子里有家具、奴仆、轿子、马,反正您需要的全齐了。这些纸糊的东西做得可讲究了,各色各样的,葬了您之后就烧掉它们,我敢说哪家的纸人纸马也比不上您这一套好。这些东西都得排在出殡的行列里,让人人都瞧得见……(16)同①: 5.
大地上的人和植物一样春华秋实。王龙入土为安,葬礼上焚化的彩纸做的荣华富贵亭台楼阁所腾起的烈焰,标注了一个生命轮回,灰烬中开始了儿孙们的新时代。
三、 翻译策略选择与地方性知识建构
当我们从民族志和文化翻译的角度解读赛珍珠有关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就不得不思考赛珍珠如何解决文化可译性的问题。不同民族生存境遇产生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宇宙观的表达与具体的文化专项词汇中,如中国有几十个有关亲戚的称谓名词,因纽特人有几十个有关冰雪不同样态的专属名词等。赛珍珠将中国文化作为文本翻译进西方阅读界的时候,不得不权衡直译(异化)与意译(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
从民族志的文化翻译来说,直译就是采取民族志工作者作为收集者的翻译策略(ethnographer as collector),译者尽可能保留原文化形态,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不使用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去改写资料;与之相对,意译就是采取民族志工作者作为阐释者的翻译策略(ethnographer as interpreter),译者对他族文化进行深层次阐释,将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转换成西方阅读界熟悉的表达方式,而赛珍珠实际上超越了民族志学者的这两种常规做法。
赛珍珠首先采取了“可理解的陌生感”,也就是她的文化翻译可以为西方读者理解,但又有明显可识别的中国文化特征。她将被翻译的中国人的声音在文本中释放出来,形成某种对话民族志(dialogical ethnography)的特点,这就要求在可理解与直译之间达到某种张力平衡,这尤其体现在微观的语言翻译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赛珍珠并没有采用双语引录、他族语言注释等深度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亦称厚译法)去化解可能存在的文化不可译问题。她在提供充分的有助于理解文化词汇的上下文的情况下,对中国特色文化词汇听之任之,充分陌生化,以此呈现中国认知方式的自然状态,如黄包车夫在人群中择路而行时,嘴里不断地叫borrow light(借光,麻烦让路),女人怀孕叫have happiness(有喜了)等。她对译者隐身的坚持,对文化的陌生化的无为式处理,并没有妨碍读者对文化词汇的理解,相反激发了读者对他者文化独特性的兴趣,进一步巩固了译者在知识建构中的权威性。
赛珍珠让人类学家望尘莫及的是她将自己对文化的阐释故事化和情节化,以叙事的方式展开。阐释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认为,民族志的文化翻译就是对文化持有者对本族文化阐释基础上的再阐释,通过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阐释能力,寻找他者文化的意义,建立关于他者的坚实的知识体系(17)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5.。赛珍珠在《大地》中让中国农业社会的各色人等都有表述自己文化的机会,王龙、阿兰、叔父、黄老太、荷花、杜鹃、梨花等每个人都体现“文化个性”,人物之间的冲突是文化自我阐释方式差异的具象化,在这个过程中赛珍珠成功隐身。
她的隐身并不意味着她没有观点,她的春秋笔法在于给中国文化以文学化的阐释,让不同文化元素以固有的逻辑运行方式同其他元素互动和冲突,解构与重构,合纵再连横,看似布朗运动一样无序的文化元素冲冲撞撞,分分合合,其实都是赛珍珠的阐释性配置,让文化元素在其原生态自足的关系网络中,本真而充分地展示自我。赛珍珠作为写作者隐身于观众中,但在时代的幕墙上演出皮影戏的绳子却都攥在手里,说故事是她对中国文化阐释与再阐释的方式。
格尔兹还指出,一部具体的民族志描述是否值得注意,并非取决于作者获取遥远地方的原始事实的能力,然后把这些资料像带一只面具或雕刻那样带回家,而是取决于作者多大程度上说清楚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以减少人们对在鲜为人知的背景中的不熟悉行为自然要产生的那种困惑: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18)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16.。显然,赛珍珠的小说叙事型文化翻译达到了优秀民族志所要实现的目标。如果对比在同一项皖北农村调研基础上产生的两个文本,即赛珍珠的《大地》和她的丈夫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的《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FarmEconomy,1930)这本公认的汉学研究经典,我们发现自然是《大地》对美国民众的中国观产生更大影响,而纯学术的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书只能影响为数很少的专家。
赛珍珠不仅从文化主位(emic),即局内人的视角描述中国文化,以保证文化翻译的恰当,而且低调定位自己的知识适用范围。在和江亢虎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各不相同的地方风俗的巨大国家,所以特意选择将故事中的风俗同某一地方尽可能贴近,以便至少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是精确的(19)BUCK P S. Mrs. Buck replies to her Chinese critic [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33-01-15 (2).。赛珍珠在此所强调的是她的文化阐释的地域性,一种高度自省的认知局限,拒绝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他者社会时形成的普遍性(generality)虚妄。
赛珍珠的这一反驳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理念不谋而合,尽管她的观点比后者早了近半个世纪。格尔兹认为从对特定文化阐释中获得的知识具有地域特质,未必能通约为某种普遍规则,但在把握现实的某个方面要比普遍性知识丰富和深刻,这就是他提倡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locality)不只是地理范围,而且是与普遍性相对,是阐释者选择的以退为进的学术姿态。盛晓明认为,所谓“地方性”并不是简单地就特定地域意义而言,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存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20)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 哲学研究,2000(12):36-44.。从这一点来看,赛珍珠主要呈现的是有关中国淮河流域农民(包括妇女)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却是当时男性传教士人类学家们不容易获得的。对于多数东方社群来说,只有表示亲善的女性白人才有可能被接纳,对于那些深藏在内室的东方女眷生活,只有女性白人才能目睹,白人女性对他者家庭生活的进入可以说大大推动了关于他者的知识建构。
四、 结论
赛珍珠比其他来华的西方跨国书写者高明之处在于,其白人作者的主体性存在被完全隐匿,以这样的整体性文化翻译方式与人类学达成学术共谋,将前现代中国乡村原生态呈现给现代西方读者。不同于人类学文化翻译的宏观、笼统,主题的碎片化(仪式、婚姻、宗教等),赛珍珠就像使用摄像机,全面呈现中国社会整体的有机性,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文化逻辑与集体无意识演绎生命历程(文化持有者的自我阐释),而看起来天衣无缝的情节正是赛珍珠将文化逻辑具象化,赋予主流文化和各种亚文化以生命节律来实现的。中国人对文化的自我阐释活化为人物形象刻画,赛珍珠对文化持有者的阐释之再阐释形变为情节发展。如此的文化翻译比人类学更直观,更灵动,也更具情感层面的震撼力。
另一方面,赛珍珠的文化翻译产品是小说,小说离不开活的语言,尤其是对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本地人的口头语言的文本化与转译,因此赛珍珠的文化翻译是宏观(文化的文本化)与微观(语言文化元素移译)的完美结合,这就比一般的人类学文本更进一步,读者可以从人类文明中最核心的语言层面了解他者文化。由于作者隐身,读者在似乎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通过小说阅读自主进入相对封闭的中国农业社会,在故事进程中体验他者的文化逻辑,观看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的自我阐释与表演,不知不觉中与赛珍珠通过情节表达对中国文化的阐释达成共识,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知。在阅读中国书写后,他们不知不觉成为自己与赛珍珠共建的知识体系的捍卫者,尽管赛珍珠曾经声明这只是“地方性知识”,但多数读者却已经将之泛化为关于中国的普遍性知识。从这一点来说,赛珍珠与东方主义的刻板中国观形成无奈而无法解脱的共谋。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自身的美国白人公民身份加持了她数十年的中国生活阅历,接受她刻意自我边缘化的“中国女儿”身份,使她能够在华人知识分子结构性空缺之时,相对容易地被推举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此外,在她被公认为“大众的中国通”之后,围绕赛氏中国知识所形成的学术生态抑制了中国学者甚至整个亚洲学者在美国学界的生存空间与表述机会,或者说她巨大的影响力将华人学者的声音屏蔽了,这在美国的种族歧视语境中是一个永恒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