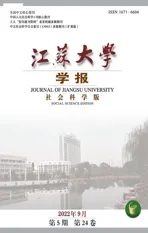赛珍珠传记作品《异邦客》中的家园政治观
2022-12-24汪文君
汪文君
“文化边缘人”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位于两个文化群体中间,同时拥有两种文化,但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的一个”(1)郝素玲. 赛珍珠:一位文化边缘人[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64-67.。自出生三个月就离开家乡被带到中国,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正如她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提到:“我在一个双重世界中长大——一个是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2)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M]. 尚营林,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9.。赛珍珠除了她自己外,一切都是双重的:她有中西两个名字,两种身份;她同时学习两种语言,面对两种文化;她有两种吃饭风格;去两种学校;有两种信仰。正因为同时在两个世界生活,她内心充满身份焦虑,她常常“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但并不置身其中,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但又不在那里生活”(3)同①.,感到自己在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归宿,既不能完全回归美国文化,也不能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始终是局外人。“文化边缘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既存在于两种文化间,又同时受两种文化的排斥,具有文化上的“双焦透视”便利,但是同时也面临文化身份归属不清的尴尬。离散造成地理位置上的事实位移,与此同时带来了文化上的错位感,也进一步引发了精神上的错位感,地域、文化、精神离散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无家”感,所以赛珍珠常常这样问自己:“难道人们必须要有根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再次扎根呢?思考一下连根拔起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4)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M]. 尚营林,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242.?离散带给作家对生存状态的深刻感悟,在离散过程中固然有许多迷茫和苦楚,但也有特殊之处,拥有的双重文化视角往往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利用文化视角的交汇,赛珍珠书写了关于中西文化融合、文化身份建构、寻根、家园建构等主题,思考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的可能。
此外,传教士父母对美国故乡的记忆以及在异域重新建设家园的过程,也深深影响了赛珍珠对“家园”的多重思考。赛珍珠的父母加入了传教士大军,来到中国传教,这个群体作为文化离散中的特殊群体,始终以边缘人的身份生活和工作,既带着对故乡永远挥之不去的思念和与祖国母体撕裂的痛苦,也饱尝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和漂泊无定的痛楚。他们既不太可能被移入国所完全接纳,也不可能与祖国彻底分离,只能在两种文化的中间状态离散地生活。带着无根漂泊的无奈和对家园的强烈渴望,家园书写成为赛珍珠写作生涯中最丰富却又最脆弱的一环,她将这样的情感融入以“家园”为题材的小说中, 如《大地》中王龙对土地的坚守、《母亲》中母亲对家庭的呵护、《同胞》中詹姆斯·梁回国报效祖国以及《龙子》中林郯誓死捍卫家园的众多故事;此外,她创办“欢迎之家”为战争孤儿找寻新归宿的事迹,都表达了赛珍珠对思念家园、寻觅家园、建构家园的努力和感悟。赛珍珠为母亲创作的传记《异邦客》,感同身受地讲述了母亲被放逐的一生以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痛楚。本文拟从地域家园、文化家园和哲性家园三个角度剖析凯丽的思乡之情,并以此进一步解读赛珍珠家园政治观的具体体现。
一、 地域家园:凯丽的美式花园
何以为“家”?广义上看,“家”表示住宅、房屋。引申来看,家还可以表示国家、社区、故乡、家人等等。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人们在土地上繁衍生息,自古以来就有“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土地情结,土地成为人最终的归宿,只有入土为安,才算真正走完了一生。人类世世代代的延续离不开土地的滋养,土地意识早已是人类的共识,对于土地的眷恋也成为“家园情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离散群体来说,“‘家园’不仅是他们出生甚至成长的地方,也是他们旅居海外若干年后仍想回归的地方”(5)李亚萍. 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36.,身在异乡为异客,正因为能深刻体会到离别祖国母体时撕裂的痛楚,所以离散群体的“家园”就是他们的“祖国”。处于地域离散状态的人,离开自己的故土,生活在陌生的国度,又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当新的环境难以适应,而旧的环境又无法回去时,他们就成了无根漂泊的人。只有离开家园的人才会有寻家的迫切感,所以“非家”的状态是离散群体心中永远的痛。
初到中国的凯丽,犹如一个拓荒者,在陌生的国度艰难地生存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强烈的思乡之情,再加上辗转搬家颠簸,更是让凯丽精神上居于崩溃的边缘。从西到东、从城市到乡村,一家人一直到处奔波,漂泊无根的生活状态让凯丽常常感到“处处无家处处家”(6)费小平. 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2。与凯丽有相同情况的,是被祖国放逐、被家庭放逐的传教士妻子这一特殊群体,她们为传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人生牺牲。她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忍受着作为边缘人的身份孤寂和长期漂泊的放逐感,对于被迫远离家乡的她们来说,故乡是她们曾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是她们血脉中流淌不息的希望,可是如今故乡只能是魂牵梦绕的远方。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散文中写道:“流放意味着一个人总在回望自己诞生的祖国,因为现在他们永远失去了它”(7)李亚萍. 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53.,“离开故土”与“漂泊异乡”构成最直接、最伤感的地域乡愁。一个人在遭遇放逐的境遇时,在行动上和心理上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寻根倾向,试图在重建过去的过程中找回安全感和归属感。凯丽日夜思念着故乡,家乡教堂的钟声、古老的赞美诗都能将她的思绪送往万里之遥的地方。强烈的思乡情绪让凯丽与自己故土的文化总是保持着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联系,她在异国的土地上竭尽全力地为家人做着重建过去的努力,所以最终在镇江安顿好之后,凯丽展现出在异国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内心激发出重建生活的激情,她不仅学会在必须建家的地方建家,而且都是美式的家。凯丽的思乡之情无处不在,既在洁白的粉刷过的墙里,在修葺平整的草坪里,在故乡带来的玫瑰里,也在她的第一座真正的花园里。凯丽建造的美式花园,满院的红的、粉的和黄色的单瓣小玫瑰,充满了思乡之情的小植物,搬到哪里就栽到哪里。凯丽的“乡愁”从原先的一个抽象概念被分解成了“花园”“鲜花”“钟声”“风景”等具体意象,这些意象在地理空间中层层叠加,形成了坚强的壁垒,将墙外的中国世界和墙内的美国世界截然分开。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家又建成了(8)赛珍珠. 异邦客[M]. 林三,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57.,从此在墙和大门之内是属于凯丽自己的一块小天地。约翰·罗斯金指出:“无论女性身在何处,均可成为家园——一个充溢着特殊品质的空间、一个洋溢着静谧与爱的港湾。”(9)同①:15.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建立起与土地和大自然的情感连接,也可以更从容地适应周边的环境并开始新的生活。凯丽的美式花园正是她每天可以回的“家”,是对故乡文化的恢复,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和对心灵的宽慰,也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用实际行动表示出的对母体文化的眷恋和回归。所以,每当凯丽爱恋地望着窗外的花园,“不管是鲜花盛开的季节,还是满园潇飒的冬天,回忆起家乡时,总是目光发亮”(10)赛珍珠. 异邦客[M]. 林三,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17.。
“家园可以分为有形家园和无形家园,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分离的两种家园,而只是同一个家园的两个层面。”(11)高秉江,卫才胜. 论有形家园[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22-27.有形家园是可以触摸到的红墙绿瓦的庭院,或者是屋后蜿蜒流淌的小河等实体意象,有形家园还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布宁笔下的庄园、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安妮·麦珂尔斯笔下的风景、叶芝笔下的爱尔兰大房子等等,“花园”的意象在西方文学中也是常见的有形家园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期待和寄托。有形的家园可以被重新建造,虽然重建后的家园无法取代最初家园的回忆和情感,但是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记忆中的精神家园,凯丽的美国花园就是这样一个被重建的有形家园。“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家是我们的庇护所,我们在家里感到很安全”(12)龙迪勇. 空间叙事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266.,凯丽在不断漂泊的生命旅程中艰难地以自己的方式活着,一边是归不去的故土,一边是飘零的异乡。对两个世界来说,凯丽都是边缘人, 但她将儿女们一点一点地与她自己的国家连接起来,她哼唱古老的赞美诗、制作美式的食物、所有的布置都还原美国的摆设,有凯丽母亲的照片、家乡的风景画等等,或许这样,“这间房子使我懂得了那安置在遥远异国他乡的家的许多细微处的意义”(13)同①:22.。“幸福的理想始终有形地表现在住宅上,无论是茅屋还是城堡”(14)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512.,凯丽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加深对家园的渴望,每失去一处房子,都是她内心刻骨铭心的痛,所以家更是“边缘人”凯丽在放逐中对生命归宿和幸福理想的寻找。房子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房子是有生命的,不仅仅是物理的空间存在,更是情感的载体,对房子的回忆伴随着凯丽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离散所造成的与祖国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得离散个体持有关于实体或者想象的故乡理想”(15)COHEN R. 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Routledge, 2008:17.,正是因为故乡的房子承载了童年远去的记忆、家人日常生活的珍贵点滴,凯丽才费尽心力地在中国还原一个美国的家。
“文学空间里的地域描写意味深长”(16)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98.,家园不仅是物理的空间存在,更是精神上的皈依之处,在一个相互关爱、充满温暖的家中生活能够让人缓解身心的疲惫和孤寂,给人一个停歇的温暖港湾。相反,如果生活在一个冷漠、疏离的家庭中,只能感到孤独和绝望。在幼年赛珍珠的印象中,父亲赛兆祥犹如幽灵般的存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乡间布道而很少回家,他和子女们仅仅像个熟人一样,对妻子凯丽更是缺少关爱,他无暇顾及家庭,也没有时间关爱孩子和妻子,导致他在家中“父亲”角色和“丈夫”角色的模糊。赛父无限的精神追求与赛母有限的安家需求形成了冲突,地理上的家园荒芜破败,凯丽精神上的家园也衰败了,结果一家人都过着“似家非家”的生活。“空间不仅在外部再生产着社会关系,还深深地嵌入家庭的伦理关系中来,对家庭内部施展力量。”(17)刘永杰. 空间的隐喻:空间理论视阈下《悲悼》中的家庭[J]. 世界文学评论, 2011(1):136-139.凯丽的一生从离开弗吉尼亚的家乡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就像赛珍珠在自传中写的一样:“亚洲成了我的真实世界,而我的故土,却成了天堂般美丽的梦乡”(18)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M]. 尚营林,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3.。从此,凯丽成了被祖国放逐的人,面对丈夫对家庭的态度,她又是个被家庭放逐的人,她只能在有限的封闭空间内——她的厨房和花园中进行着内心的抗议和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家园是给人以归宿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19)陆扬.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4):31-37.,在中国的“家”给凯丽提供了临时的住所,也重重地给她套上了精神的枷锁。
二、 文化家园:母语是一个人的民族根基
作家聂华苓自1964年从台湾赴美后,好几年都写不出一个字,她说只因不知道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因而患上了“失语症”。直至重新领悟到汉语是她的根,她才缓解了由母国至异乡漂泊所感到的内心孤独和创伤,再一次用母语与祖国对话,才解除了失语症。母语是离散群体与祖国间的血脉相连,也是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共同的想象家园,正如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就是说人不能没有语言而存在,人只有通过语词的选择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20)李亚萍. 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32.。凯丽跟随丈夫来到异国传教,之后的四十年都生活在陌生的国度,她努力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寻找安慰和寄托。离散的过程切断了语言的连接,也模糊了母语所承载的文化符号,生生隔离了与故土的联系。但在赛珍珠的记忆里,母亲凯丽总是想方设法地,甚至不惜代价地亲自教授孩子们学习英语,为他们提供美国背景,给他们讲美国的历史人物,介绍圣经故事,给予他们对美国不朽的爱。让孩子们学习母语的目的,就是不能忘记他们虽在中国生活,但身份却是美国公民,不能忘记自己国家的语言。对于像凯丽一样的异乡客来说,母语是她们身份的标签,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使他们表现出很强的身份焦虑意识,母语的阅读和使用成为弥补与母体撕裂伤痛的疗伤手段之一。他们可以沉浸在自己熟悉和安全的语境中怀念过去,为自己构建的母语环境可以暂时忘记所处的异乡环境和现实生活的折磨,内心得到安慰。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回归故土,用母语表达内心的诉求,可以一方面缓解思念故土的焦虑,也是逃离现实异乡生活世界的一个有效方式;另一方面,母语也是重新找到自己在异国身份定位的途径,不断强化异乡人寻根的渴望。在异国漂泊的生活中,因为母语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故乡记忆,传达出丰富的回忆意象,既有故土、母亲的形象,更有童年生活的影子,而这所有一切都是与祖国血脉的有力连接。
“从过去的某个中心来到现在成为他们故乡的这个地方,由于他们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联系,他们工作起来总有一种空虚感——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21)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 盛宁, 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246.对于传教士集体,尤其是他们的妻子们来说,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进行了切割——从移出国到移入国,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舍弃。异乡客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融入移入国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回归母国文化,而是处在很尴尬的“文化中间地带”。在新的国家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该国的日常生活语言,而暂时规避自己的母语,这看似平常的生活举动却意味着在离散过程中拔根而起的痛楚和移入新土时的不适应。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本·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民族的认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认同’,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而且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的东西。”(2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39.所以民族更多的是感情连接,“他们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祖国保持联系,他们的民族共同意识和团结被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极大地强化了”(23)陈爱敏. 认同与疏离:美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的东方主义视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4.。星期天的晚上凯丽总是弹着自己的风琴唱古老的赞美诗;有时候孩子们围坐在凯丽周围,听她讲述往事,讲国家的战争,讲她对故乡的回忆。“讲故事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是把往事诉诸声音,用它去影响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24)李莉.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248.讲故事还意味着是“一种互动方式,一种个体在相互关联的时间与空间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历程”(25)同④:252.。“真正的家园不是靠石砌砖垒,而是用文字和精神筑造的”(26)高秉江,卫才胜. 论无形家园[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22-27.,是语言和文字使民族的记忆延续下去。凯丽通过这种方式保留对故乡的回忆,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个人记忆和族群记忆传递给下一代,让她的孩子们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凯丽的一生,是从美国到中国,又从中国返美探亲数次,直到最后以故土再也回不去的遗憾而结束的一生。她的人生经历连接了美国和中国两个地理空间,但后半生却只能留在中国且一直生活在孤苦飘零中。作为传教事业的践行者和文化层面的离散者,异国生活的失语症容易使人陷入焦虑中,用母语生活还原母国场景或许可以帮助异邦客群体随时从语言中获得故土的感觉。用母语连接祖国的血脉,是对遥远祖国的认同,更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因为这样的“家园”是可以随时带在身上,是处于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地理空间的人们间的共同家园。
三、 哲性家园:异乡再次扎根
《异邦客》中,共有三次凯丽回美国的描写,一次是在来中国的十年后,“凯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家——家——只有它能救她”(27)赛珍珠. 异邦客[M]. 林三,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252.。这一次回国,使她从过去十年孤立的生活中走了出来,重又根植于自己的亲人中,她发现她的家人全部都在那里,欢迎她回到老家。第二次回国,已经是离开家乡二十年后,可这次“她的兄弟和姐妹已学会没有她而生活,尽管他们很爱她”(28)同①:137.。这次离开美国时,她的心中感到孤独,“她离去时已无家可归,不仅仅是肉体的分离,还开始了精神的分离”(29)同①:138.。最后一次返回美国是在第二次返美的七年后,村子的名字也改了,她已经在那儿待不下去了,“在她自己的国家已不再有她的家,她悲哀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人真正需要她”(30)同①:159.。至此,她彻底被故乡边缘化了,她在心中向美国一切的美告别,从此美国也只存在于她的心中和记忆里(31)同①:169.。在小说的最后,凯丽从美国探亲返回后再也没有回到故土,美国成为一个没有必要再回去的地方。萨义德对作为文化移民深有体会:“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32)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331.凯丽一家在中国传教的几十年中先后多次在休假期返回美国,却经历了“迫切想回归—逐渐被遗忘—最终被抛弃”的被动与故土分离的过程。对离散群体来说,这或许是比较常见的伤痛,因为从离开故国的那一刻起,故乡在不断发生变化,离散群体也在经历新的环境,而想要完完整整地如拼图般再回到那个出发的原点,显得不太实际。很多离散在外的人在多年之后会满怀希望回到故乡寻根,但往往寻到的是极度的失落,凯丽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台湾思想家唐君毅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花果飘零”和“自植灵根”的命题:“一树崩倒,花果飘零,随风而散,落入异域,若能发心,亦能自植灵根,随境所适。”(33)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第7卷[M]. 台北:学生书局, 1990:71.在每一次返美探亲逐渐被抛弃时,凯丽无形中也体会着对异乡中国认同感的与日俱增。第一次返美,凯丽意识到“根在美国,却也与中国结合在一起,因为她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某部分躺在那古老的土地上”(34)同①:99.,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过没有亲人埋葬的地方不叫家乡;第二次返美,她意识到“正是那些遥远国家的人在召唤她”(35)赛珍珠. 异邦客[M]. 林三,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138.;第三次返美,“她却把脸转向异国他乡,而且是坚定地转过去,因为那儿有需要她的人,他们为她的离去感到痛苦并急切地求她回去”(36)同①:155.,内心深处的乡愁在新的国度焕发出创造新生命的能量。从此,凯丽将中国的生活融为她未来生活的一部分,而美国作为一个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既然尝过被连根拔起的痛苦,也必然理解再次扎根的意义,凯丽对中国的态度恰恰经历了与美国对她的抛弃相反的一个过程:“渴望返美→情感初融→异乡扎根”。凯丽在家园重构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愈合,故土与异乡的关系获得了超越,当然,这一切是在经历了多年异乡生活之后才达到的。“乡愁”是种很复杂的情感,当一个人离开故土来到异国时,“地域乡愁”是最直接体会到的思乡情愫。而文字和语言(特别是方言)的乡愁却又击中了异乡客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进而升华为“文化乡愁”。一个人一旦再次回到祖国,地域乡愁和文化乡愁或许会减轻许多,更可以不复存在,相比而言,哲性乡愁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乡愁。哲性乡愁已经从简单的“两点式”思念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思考,一种理性地对生命归宿的探索。“当逐渐适应异域生活,当远离故土的伤悲逐渐消退,开始真正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氛围时,对故土的思念会转化为一种冷静的思考,甚至站在两种文化之间,理性地对待故国家园。”(37)李亚萍. 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54.凯丽在中国这片土地重新建立新的家园,她将镇江的住宅和院子再一次变成了她的家,在围墙外是另一个世界,但是她学会了认可这片生活的空间,同时在围墙内,她又深深扎下了根,建立了一片美国家庭的绿洲。
澳大利亚作家阿列克斯·米勒指出的“流放如归家,错置即正位”的境界,异乡与故土的位置互换一下,也未尝不可。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与“自植灵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在异乡的飘零放逐中能找到自己心灵的故乡,并且有能力在异乡重新找到归属感。作家拉什迪在《想象的家园》中这样写道:“像我这样的流散作家,流亡者、移居者或放逐者,心头可能总是萦绕着某种失落感,带着某种冲动去回顾过去,寻找失去的时光……但回顾过去时,我们会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我们创造的不是真实的城市或乡村,而是看不见的想象的家园。”(38)SALMAN R. 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M]. London:Granta Books and Penguin Books Ltd, 1991:10.对于离散群体来说,他们处在一个中间位置,既不完全融入新的环境,又与旧的环境保持关联。家园不一定是原来所属的国家或民族所在的地方,可以是实体的有形家园,也可以是想象的家园,不一定是落叶归根的地方,也可以是再次落地生根的地方。“她现在知道家和国在人自己的心中,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建出来”(39)同①:150.,我们有理由相信,直到生命的终了,凯丽仍思念着她所熟悉的美国,虽然这些永远是她回忆中的财富,但是她将这种思念化为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几年凯丽的家“愈来愈变成各种处境困难的人的聚集地”(40)赛珍珠. 异邦客[M]. 林三,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145.,这其中有逃荒乞讨的中国人,有患肺病的苏格兰女人,有可怜发疯的英国女人,更多的是可怜的孩子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凯丽的家,并从她健全的个性中获得援助。凯丽将自己对故乡弗吉尼亚“小家”的思念,一步步升华为美国“大家”的精神。她再也没有搬过家,扎根于此,也长眠于此,并且“将代表着家的愉快和互助的友谊带给她见到的每一个人,她给异邦客带来了家和国,她自己就是这方国土上有血有肉的美国”(41)同①:180.。凯丽的一生犹如蒲公英,离开原乡,放逐异域,只不过她不再是“无根的”,而是带着她的根,找到飞向陌生异乡的新路,将家融化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无论是地域家园、文化家园还是哲性家园,都属于家园建构的不同层面。对于凯丽来说,美国故土是她前半生生活的圆心,中国故乡是她后半生情牵的归处,她本人也成为连接东西方之间的纽带。地域的家园是承载从房到家和家之所以为家的精神之光,家园也成为赛家人内化为自身的,想象与希望同在的精神共同体。同时,赛家两代人并没有停留在离去、归来还是扎根的模式中,而是在遥望故土中思考,一边在想象中等待归乡的希望,一边又在矛盾中感慨故土再也回不去了。不管是留恋还是思考,对于他们来说,家园是离开半生、遥望半生、期待半生又温暖半生的情感共同体。凯丽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并将她的家建成了一个博爱的大家庭,再次扎根是将她的生活经历、社会责任和生活意义延续,是她对地理家园、精神家园和心理家园的延续,也是她自己身份确认的过程。凯丽在两种文化中被撕裂,也在寻找淡化、弥补这个文化边界,将自己错位的人生调正,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家乡是异乡,异乡也可以是家乡。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的家园之中,这里的家园超越了时间、空间,连接起过去与未来,走向了更深层次的价值与信念,成为承载爱、拥抱爱、给予爱的生命共同体。
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情感关联除了生命的延续,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认同过程,赛珍珠在双重文化交汇的环境中长大,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她从小和母亲一起经历着孤独感和无家感,母亲站立在异国美式花园思念故乡的孤独背影,尤其让她难以忘怀。童年的成长经历成为日后赛珍珠最具创造力的源泉,无论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她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根到底在何方。为母亲创作传记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她的一生经历着“出生美国→长于中国→回到美国→再也无法回到中国”的遗憾。赛珍珠的家园书写,既是写一个个固定的地理空间,也是写存在于记忆中的永恒家园,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赛珍珠融入身体里的精神血脉,代表着她一生无法割舍的家园情怀。除了作品中的家园书写外,赛珍珠的后半生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欢迎之家”的工作,在几十年里,她努力为五千多名孤儿和混血儿童寻找收养家庭,这是赛珍珠对思念家园、寻找家园和建构家园的具体实践。赛珍珠“家园政治”的立场,消解了不同民族的隔阂、不同文化的边界,从小家走向大家,走向民族共荣和文化融合,也将她一生中最遗憾的无家可归转换为处处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