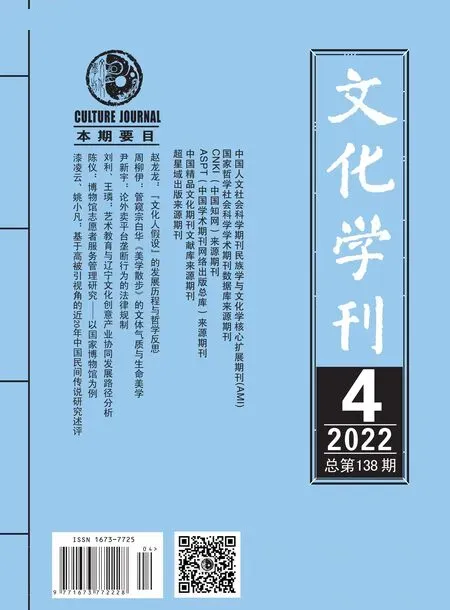动词“吃”的音义关系及其配价研究
2022-12-07李林燕
李林燕
“吃”表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行为活动,出现次数频繁,“吃了吗?”一度是人们日常对话中最常用的语句,由此,“吃”所构成的同一形式的结构模式往往蕴含多种意义,存在歧义纷争。如“吃的”这一“的”字短语结构。然而,“吃”是否自产生之初便具备饮食义,需要对其音义关系进行进一步梳理。如何分析“吃了他三个苹果”这一特殊结构形式的句式结构及判定动词“吃”的配价归属也存在争议,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吃”的饮食义溯源
吃,最初不具有饮食义,按“六书”言,“吃”属形声字,从口气声,“气”不仅表声音,其形又像弯曲的云气,表示口吃者声音不能自然直出。《说文解字·口部》:“吃,言蹇难也,从口气声。”即其本义指口吃、说话结巴。在饮食义动词“吃”还未产生时,古代汉语中表饮食义的动词多为“食”和“饮”,“食”多与固体食物的食用搭配,“饮”则常与流体食物或液体的食用搭配。汉至魏晋时期,动词“喫”出现,开始竞争“食”的饮食义,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对动词“食”的饮食义的历时替换。
宋代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收录了“喫”字,注:“喫,食也。从口,契声。苦击切。”魏晋之后,动词“喫”不仅具有“食”的意义,还兼有“饮”(现代汉语“喝”)的含义,《洪武正韵》:“喫,饮也”。唐宋时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朱子语类》等文献中,“喫酒、喫茶、喫水”等词语多有出现。现代,宁波方言等方言中仍存在“喫(吃)茶”“喫(吃)水”等说法,这也为“喫”古代兼具“吃”“喝”两种意义提供了佐证。在动词“喫”对“食”饮食义的历时替换过程中[1],由于语音的发展变化及方言的影响,“吃”被借来表饮食义,同“喫”出现混用现象,随着语言发展,“吃”成为表饮食义的主导词。
从语音特征看,“喫”与“吃”的声母、韵母均不相同。依据《唐韵》,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标注“喫”的读音为“苦击切”。而“吃”在《唐韵》《集韵》《韵会》《广韵》均注为“居乙切”,又《集韵》“欺讫切,音乞。吃吃,笑貌。”总的来说,“喫”字属于溪母锡韵入声,“吃”字属于见母迄韵入声。汉语史上,有些音同或音近的字会发生替换现象。“吃”与“喫”的混用说明,在汉语发展过程中,“吃”与“喫”的语音经历了逐渐趋同的发展过程或说两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某些读音,因此,“吃”被假借承担了“喫”的饮食义,同时,“喫”所具备的“饮”的意义又逐渐被动词“喝”分担,使得“喫”字以饮食义的身份出现在书面语中的次数大为减少,呈消亡趋势。
就语音层面看,“喫”属溪母,“吃”属见母,而“吃”在《集韵》中又有“欺讫切”一音,此音声母与“喫”声母相同,同属溪母,虽义有异,但为“吃”与“喫”的混用提供了可能。此外,汉藏对音、日译汉音及现代南方方言均存在溪母字读为见母字的用例[2],这侧面印证见母“吃”与溪母“喫”混用是可能的。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的拟音[3],入声锡韵的“喫”收“—k”尾,入声迄韵的“吃”收“—t”尾,据上古音看,两者相混的可能性极小,然而,由于语流音变的存在,并且随着入声韵尾逐渐消失,“吃”与“喫”皆变为阴声韵,两者混用不是没有可能,由此,动词“吃”才能取代“喫”成为饮食义的主导词。而后动词“吃”以饮食义为基点,引申发展出了其他义项,为“我吃了他一个苹果”特殊句式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动词“吃”的配价分析
语法包括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仅从一方面去探析配价是不完整的,陆俭明(1995)指出:“确定配价应该以意义分析为基础,同时得到形式上的可操作性”。相较而言,从语义、句法两个层面探究动词“吃”的配价归属更显合理。
(一)简单句“吃”的配价
动词所支配的“行动元”的数量决定着其价数[4]。古代汉语中的饮食义动词(如食、饭、饮、抿等)及现代汉语中的饮食义动词(如吃、喝、吞、咬、含等)主要支配施事和受事两个配价必有的语义成分,在简单句中构成基本句式:施事+动词+受事,其中施事充当主语,受事充当宾语。常见的例子如:1.他吃饭。2.我喝水。3.狗咬肉。4.她含糖。
尽管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动词“吃”在饮食义项上的配价归属,但除了饮食义义项,“吃”所具有的其他引申义项一般也只能带施事和受事两个语义成分。如:1.纸不吃墨。2.又吃掉了敌军的一个营。3.快看,那儿有一艘吃水很深的船。这里,例1“吃”有吸、吸收之义,可将“道林纸”看为施事,“墨”看为受事;例2“吃”有歼灭或摧毁之义,施事未出现,受事是“敌军的一个营”;例3“吃”有浸入水中之义,指船身入水的深度,“船”是施事,“水”是受事。因此,一般情况下,动词“吃”主要支配两个行动元,从配价角度而言,属二价动词。
(二)特殊句式“吃”的配价
唐元发、孙卉姿[5]对陆俭明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法指出“吃了他三个苹果”分析为双宾句[6]是可取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其文章认为“吃”是个二价动词,“他”可以实指,也可以虚指,整个结构组合体应看成单宾结构。
目前,学界已认可“他”存在虚化的说法[7],因此,这里从“他”作虚指成分和实指成分两个方面探究“吃”的配价。唐元发、孙卉姿指出,当“他”是虚指成分时,“他”大致相当于一个句中语气助词,不充当句法成分,因此,与“三个苹果”没有领属性语义关系,在句法结构上,只有“三个苹果”作“吃”的宾语。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在某些时候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仅起凑足音节等作用。如:
我当时饿极了,一口气吃了他三个苹果。
我当时饿极了,一口气吃了三个苹果呢!
这两个句子在语气上存在着些许差异,但是在语义表达上没有差别,均在陈述“由于我饿极了而吃了三个苹果”的事实。因此,当“他”是虚指成分时,“吃”在“我吃了他三个苹果”这种句式中确实只支配了施事和受事两个成分,属于二价动词。
然而,当“他”是实指成分时,“吃”是否仍是二价动词,便值得深入探究。唐元发、孙卉姿文章认为,当“他”作实指成分时,“他”和“三个苹果”有语义领属关系,在结构上是偏正关系,“他三个苹果”整体作“吃”的宾语。同时通过该例句与“给了他三个苹果”进行“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进行论证,认为两句之间存有明显差别,即动词“吃”的配价不同于三价动词“给”。如:
我给了他三个苹果——我把三个苹果给了他——他三个苹果被我给了
我吃了他三个苹果——我把三个苹果吃了他——他三个苹果被我吃了
进而从是否可将“他”和“三个苹果”拆开转为把字句、合拢变为被字句论证两者是否存在领属关系。这就否定了动词“吃”在此例句中所具有的三价性质。这一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并不具备周遍性。同是动词“给”,出现在其他例句中,便不能完全符合以上条件。比如:
1.我给了他一个巴掌(我给了他一巴掌)——我把一个巴掌给了他——他一个巴掌被我给了
2.我给了他一脚——我把一脚给了他——他一脚被我给了
这里的例1和例2既不可将“名①”和“名②”(1)“名①”指“他”,“名②”指“一巴掌、一脚”合在一起转换成“被”字句,也不能拆开转换为“把”字句,可见,单凭能否将“他”和后面的词组拆开换成“把”字句,合拢变换为“被”字句是不能精确判断两者在语义上是否确有领属关系的。
从语义、句法的配价角度来说,动词“给①(了他三个苹果)”与“给②(了他一巴掌)”都支配了施事、受事、与事三个成分。尽管“一个巴掌(一巴掌)、一脚”存在量化趋势,但仅从配价而言,“我给了他一巴掌”和“我给了他三个苹果”两个例句之间并无太大不同。因此,当“他”做实指成分(后面默认“他”是实指成分)时,这里的“吃”不能被简单当作二价动词。
(三)“吃”是否具有三价性质?
许多学者分析论证了“吃”等二价动词构成双宾句的可行性,那么能够构成双宾句的“吃”是否就此具有了三价性质呢?本文认为,“我吃了他一个苹果”这类句子可以算作一种特殊的双宾句,从配价角度而言,这种特殊句式中的“吃”具有三价性质,只是这种三价性质并不稳定。
陆俭明(2002)解释了将“吃了他三个苹果”分析为双宾结构的可行性[8]。他认为,从语义角度看,“他”和“三个苹果”存在领属关系,但从句法角度来说,两者并没有同“他的三个苹果”这样直接的句法关系,因此“他三个苹果”可以不看作偏正结构,“吃了他三个苹果”可分析为双宾结构。此后,他又借用“语法动态性”理论对“修了王家三扇门”这个例子进行解释说明,指出这里的“名③”(2)“名③”指“王家、他”,“名④”指“三个苹果、三扇门”既是“名④”的领有者,同时又以动词的与事论元身份出现,因而具有双重语义身份。换言之,在这类双宾结构中,“王家”“他”都是动词的与事,故其在句法层面可判定为双宾结构。
由于“词语的语义配价是句法配价的基础,并要求句法配价尽量同它相适应”[9],因此,在研究动词的语法配价时,多数学者会同时考虑语义和句法两方面,但不可能所有动词的语义配价成分都恰好与句法配价成分完全一致,为便于描写,往往只能忽略相对不明显的一方面。如,陆先生在对“修了王家三扇门”例句进行解释时,承认“王家”是具有双重语义身份的成分,同时承认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与事身份,进而将其判定为双宾结构。本文赞同陆先生的观点,这是综合考虑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配价最后选择的结果。可同理分析“吃了他三个苹果”的结构。
就“我吃了他三个苹果”这个句子来说,不能仅因为“他”和“三个苹果”存在语义领属关系就将其分析为单宾句。如“我送了他三个苹果”这类句子,“我”和“三个苹果”之间也暗含领属关系,但这并未影响动词“送”的配价数,其仍属于三价动词。两个句子句法无差别,区别在于具有语义领属关系的两者远近距离不同。
总而言之,“他”和“三个苹果”之间确有领属关系,但如同“我送了他三个苹果”中“我”和“三个苹果”存在暗含领属关系一样,这在句法上没有直接表现。因此,综合考虑语义、句法和句式配价[10]要求,“他”应当被看作与事成分。即,在“我吃了他三个苹果”句式中,“他”符合语义学上与事的定义,即施事所发动事件的非主动参与者,最常见的是因施事的行为而受益或受损者[11]。“他”没有主动参与“我”的施事行为,但确是因为“我”吃东西的行为损失了“三个苹果”。因此,可以将“吃了他三个苹果”这类句式看作拥有双宾语的句子,这就承认了动词“吃”的三价性质。
三、结语
承认动词“吃”在“我吃了他三个苹果”这类句子中的三价性质,不是指必须将其划入三价动词类别。单就“我吃了他三个苹果”例句可见,动词“吃”是在进入“我吃了他三个苹果”这一句式后产生了增价行为,具有了三价性质,但其本身未表现出这一性质。即句式的配价要求大于动词本身的配价要求,故动词在某种句式中,它的某些语法属性会发生某些变化,产生增价现象。因此,某些动词需要综合语义、句法及其在句式中配价现象以明确其在特定例句中的配价数。
尽管某些二价动词可构成双宾句,在这些句式中具有三价性质,但这时的三价是不稳定的,只有在特定句式中才会表现出来。而这些动词本身所具有的二价性质又是极其稳固,可脱离特定句式而存在,例如,在提到动词“吃”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的施事者和受事者,一般很少会考虑到与事成分。这是人们处于静态环境的思考。这与陶红印的看法相似,“动词的论元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句法语义现象,而是随实际语言运用而不断变化的[12]”。
这可适当参考现代汉语中词类的划分情况。现代汉语中,词与其所归属的词类之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对一的关系,存在名词、形容词在特定句式做谓语成分以及量词充当主语成分等情况,但最终还是要依据词的主要性质将词划分进一个词类。同样,在划分动词“吃”的配价归属时也应着重考虑它的主要价数性质,即动词静态的配价而非句式的动态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