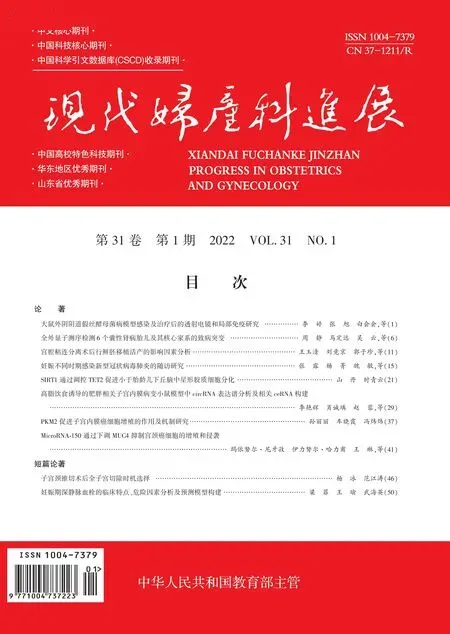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子宫内膜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2022-12-07殷爱军孔北华
殷爱军,孔北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济南 250012)
1 子宫内膜癌临床概况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欧美等国家位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之首,在中国仅次于子宫颈癌。据统计,2020年全球子宫内膜癌新发病例为417367例,死亡病例为97370例[1]。估计2021年美国新发病例为66570例,死亡病例为12940例[2]。2015年中国新发病例为63400例,死亡病例为21800例[3]。子宫内膜癌的总体治愈率较高,5年生存率在80%左右;约有80%的患者诊断时病灶局限于子宫,5年生存率可达95%,而局部转移及远处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则为68%和17%[4]。
子宫内膜癌的初始治疗主要模式为手术及根据复发风险和预后确定的相应辅助治疗。而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则多采取化学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和(或)挽救性放射治疗(放疗)等[5]。鉴于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的总体预后较差,对经典治疗的反应性较差,亟待探索新的治疗方式以改善预后。
2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概况
近年来,随着对肿瘤细胞以及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的不断深入,免疫治疗,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被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激活T细胞需要两种信号刺激:一种是通过T细胞受体(Tcellreceptor,TCR)传递,另一种是通过共刺激受体来传递,这些受体结合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cells,APC)上配体以实现信号的传递。免疫检查点通过调控共刺激(ICOS)信号以维持机体内的免疫自我耐受,防止T细胞过度激活导致的免疫损伤。肿瘤细胞则利用这一机制来逃脱免疫监视与杀伤,进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checkpointblockade,ICB)通过抑制免疫检查点活性以激活免疫细胞对肿瘤的识别和杀伤功能,从而发挥抗肿瘤的作用[6]。目前研究较为深入、应用较为广泛的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Tlymphocyte-associatedantigen4,CTLA-4)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death-1,PD-1)/PD1配体(PD-L1)抗体。
PD-1/PD-L1抗体在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的治疗中应用日趋广泛,本文将主要探讨其研究进展。
3 子宫内膜癌分型
基于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因素、临床特征及预后,1983年Bokhman提出将子宫内膜癌分为两种类型。Ⅰ型(雌激素依赖型)占比为60%~70%,常合并内分泌代谢失衡,常伴癌前病变;病变发展相对缓慢,分期较早,分化较好,对孕激素治疗有较好的反应性,预后较好。II型(非雌激素依赖型)占比为30%~40%,多分化较差,与内分泌代谢失衡无明确相关性,侵袭性较强,深肌层浸润及淋巴结转移率发生率较高,对孕激素的反应性差,预后不良[7]。尽管该分型可提示子宫内膜癌发病的高危因素及部分预后相关信息,但其无法指导新的治疗方式的选择。
癌症基因组图谱研究计划(TCGA)旨在应用高通量的基因组分析技术和综合全面的分析以探索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改变特征,从而精确地指导肿瘤的预防、诊断和治疗。TCGA将子宫内膜癌分为四种亚型: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低拷贝型和高拷贝型[8]。
POLE是由POLE基因编码的DNA聚合酶ε的催化亚基。DNA聚合酶的校正功能主要依赖于POLE的核酸外切酶区域,POLE核酸外切酶区域突变导致DNA复制过程中碱基突变负荷显著升高[6,10]。POLE超突变型占比为7%,在四种亚型中突变负荷最高,预后最好[9]。
错配修复(mismatchrepair,MMR)基因胚系/体细胞突变和MLH1基因甲基化可导致DNAMMR功能缺陷(deficientmismatchrepair,dMMR),从而引起DNA复制错误的累积,无法保持基因组的稳定性,在微卫星位点中尤为明显,从而出现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instability,MSI)。微卫星不稳定型占比为28%,其中包括MMR基因胚系突变的林奇综合征及散发性突变;突变负荷较高[9]。
4 子宫内膜癌与免疫治疗
目前,免疫治疗的分子标记物主要为两类,一类与肿瘤新生抗原相关,如MSI-H/dMMR,肿瘤突变负荷(tumormutationburden,TMB);一类与肿瘤炎性微环境相关,如PD-1/PD-L1,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lymphocyte,TIL),T细胞炎性基因表达谱(geneexpressionprofile,GEP)。
在诸多类别肿瘤中,子宫内膜癌MSI-H/dMMR的发生率最高,新诊断的子宫内膜癌发生率约为30%,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为13%~30%[9]。子宫内膜癌的部分分型(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突变负荷较高,可形成较多新生抗原[9]。此外,免疫组化检测提示子宫内膜癌PD-1/PD-L1表达阳性率高(内膜样癌40%~80%、浆液性癌10%~68%、透明细胞癌23%~69%),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的CD3+/CD8+的TIL显著升高[11]。
基于以上,免疫治疗有望成为子宫内膜癌,尤其是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的有效治疗方式。
5 子宫内膜癌免疫治疗的疗效
子宫内膜癌的肿瘤免疫原性较强,一系列研究探索ICB单独应用(表1)以及与化疗、其他免疫治疗方式、靶向治疗的联合应用。
5.1PD-1/PD-L1抗体单药治疗TCGA分型临床应用日趋广泛,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较高,新生抗原较多;分型有助于临床实践中预测可能对于ICB治疗有效的患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先后于2017年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MSI-H或dMMR的实体瘤,2020年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的肿瘤组织样本突变负荷高(tumormutationburden,TMB-H)≥10个突变/Mb的成人和儿童实体瘤患者(既往治疗后疾病进展且没有更佳替代疗法)。2021年加速批准dostarlimab-gxly用于dMMR实体瘤的成人患者(既往治疗后疾病进展且没有更佳替代疗法)。
5.1.1PD-1抗体应用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
5.1.1.1 应用于以MSI-H/dMMR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KEYNOTE-016研究,这是一项在美国开展的II期临床研究,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应用于41例既往多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及dMMR的非结直肠肿瘤的疗效和安全性,dMMR和错配修复功能正常(proficientMMR,pMMR)的结直肠癌队列的客观反应率(objectiveresponserate,ORR)分别为40%和0%,20个周的PFS率分别为78%和11%;其他dMMR肿瘤队列的疗效与dMMR的结直肠癌队列相似,其ORR为71%,20个周的PFS率为67%;共入组2例既往多线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2例疗效均达部分缓解(partialresponse,PR);初步提示肿瘤微环境、基因组改变与ICB疗效间存在的关联[12];后续该研究共入组12种癌种86例的dMMR的晚期实体肿瘤患者,其中子宫内膜癌患者共入组15例,ORR为53%;总体人群主要不良反应是皮疹或瘙痒(24%),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或垂体炎(10%),无症状胰腺炎(15%),且甲状腺功能异常仅限于dMMR组[13]。
KEYNOTE-158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多队列的II期临床研究,进一步评价了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MSI-H/dMMR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截止2020年10月,该研究纳入子宫内膜癌患者共79例,ORR为48%,中位PFS为13.1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4年PFS率为37%,4年OS率达60%,总体人群最常见不良反应是瘙痒(24%)、疲劳(21%)、腹泻(16%)等,其中11例(12%)有3~4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6例(7%)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而停药[14]。基于KEYNOTE-158研究队列D和队列K的ORR数据,FDA帕博利珠单抗作为一种单药疗法,用于治疗在任何情况下经先前系统治疗后疾病进展、且不适合进行根治性手术或放疗的微卫星高不稳定性(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GARNET研究,这是一项在9个国家117个中心开展的I/IIb期临床研究,是目前为止评估PD-1抗体单药治疗晚期/复发性内膜癌样本量最大的研究,这一亚组共入组271例,Dostarlimab(TSR-042)用于dMMR队列、pMMR队列的ORR分别为44.7%、13.4%,中位OS尚未达到;有2例(2%)患者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而停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乏力(15%)、腹泻(15%)、疲劳(14%)和恶心(13%)[15]。基于GARNET研究,Dostarlimab被美国FDA批准用于单药治疗既往含铂化疗方案治疗时或治疗后进展的成人dMMR复发性或晚期子宫内膜癌[16]。
NCI-MATCH(EAY131)研究Z1D亚组NCI-MATCH研究是在美国开展的目前规模最大的针对难治/复发性肿瘤的II期临床研究,其Z1D亚组旨在评估纳武利尤单抗治疗dMMR的非结直肠肿瘤。该亚组共入组42例,ORR为36%,中位PFS为6.3个月,中位OS为17.3个月;子宫内膜样腺癌、内膜样腺癌合并其他病理类型、癌肉瘤共17例,其中13例为子宫内膜腺癌患者,ORR为45.4%;3例CR中2例子宫内膜样腺癌;最常见不良反应是疲劳(40%)、贫血(33%)、皮疹(17%)和低白蛋白血症(17%),无5级毒性反应,3例患者发生两种4级毒性反应[17]。
5.1.1.2 应用于以PD-L1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KEYNOTE-028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Ib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共入组24例既往标准治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PD-L1阳性(至少1%的肿瘤细胞和相关炎细胞阳性或间质阳性)的子宫内膜癌患者,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ORR为13%(3/24),均为PR,其中1例为POLE突变型。中位PFS为1.8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PFS率分别为19%和14.3%;中位OS尚未达到,6个月和12个月的OS率分别为67%和51%;最常见不良反应是疲劳(20.8%)、瘙痒(16.7%)、发热(12.5%)和食欲减退(12.5%),无4级和5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例患者(16.7%)发生了8起3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18]。
5.1.1.3 应用以PD-L1&MSI状态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 一项用于评估纳武利尤单抗治疗晚期/复发性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的II期多中心临床研究,共入组22例子宫内膜癌患者,ORR为23%,中位PFS为3.4个月,中位OS为8.7个月。PD-L1阳性子宫内膜癌患者的ORR为25%(2/8),PD-L1阴性患者的ORR为21%(3/14),MSI-H子宫内膜癌患者的ORR为100%(2/2),微卫星稳定型(MSS)患者的ORR为0%(0/6);共63%的患者发生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其中19%的患者发生了3~4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19]。
5.1.1.4 应用于以TMB-H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KEYNOTE-158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多队列II期临床研究,该研究旨在探索TMB-H与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晚期实体瘤疗效间的关系,截止到2019年6月,共纳入1073例患者,805例(76%)可评估TMB,105例(13%)为TMB-H。TMB-H和非TMB-H患者的ORR分别为29%和6%;且TMB对疗效的提示意义与MSI状态及PD-L1的表达无关。其中子宫内膜癌患者为82例,TMB-H和非TMB-H患者的ORR分别为46.7%和6%;105例患者中,11例(10%)发生了治疗相关严重不良反应,16例(15%)患者发生了3~5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20]。
5.1.2PD-L1抗体应用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
5.1.2.1 应用于以MSI-H/dMMR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 一项II期临床研究评估了阿维鲁单抗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治疗dMMR和pMMR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分两阶段设计,第一阶段各组入组16例患者,若≥2例缓解或≥2例6个月无疾病进展则进入第二阶段。共入组33例,pMMR队列因未达一阶段预设疗效终点提前关组,dMMR队列入组17例患者即达4例缓解,ORR为26.7%,6个月的PFS率为40%,且疗效与PD-L1表达无关;6例(19.4%)发生了3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无4-5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21]。
PHAEDRA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多队列II期临床实验,该研究共入组71例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其初步结果提示,度伐利尤单抗治疗既往接受过治疗的dMMR和pMMR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ORR分别为43%和3%;14例患者发生了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甲状腺功能亢进6例,甲状腺功能减退6例,肺炎1例,肝炎1例[22]。
5.1.2.2 应用于以PD-L1为生物标记物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 一项Ia期临床研究评估了阿替利珠单抗用于治疗晚期/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研究,开始入组限于PD-L1阳性(至少5%的肿瘤浸润免疫细胞阳性),后不限PD-L1状态;共入组15例患者,其中5例为PD-L1阳性。ORR为13%(2/15),均为PR;PR患者均为PD-L1阳性患者[23]。
综上所述,目前子宫内膜癌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多为针对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挽救治疗。与其他瘤种不同,PD-L1的表达未能有效预测子宫内膜癌免疫治疗疗效,对于子宫内膜癌的单药免疫治疗,MSI-H/dMMR是一个较为准确的生物标志物,且目前检测较为简便,临床实践中可及性较高。
5.2PD-1/PD-L1抗体的联合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可使部分患者病情缓解,改善预后;但仍有较多患者呈现原发性或获得性耐药,免疫联合治疗旨在发挥不同机制的协同作用,提高疗效。免疫联合治疗主要包括联合化学治疗、其他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
5.2.1 联合化学治疗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协同机制可能表现为:化疗可提高肿瘤的抗原呈递及免疫原性[24]、诱导肿瘤细胞PD-L1的表达[25],肿瘤微环境中的效应T细胞可通过减弱基底层细胞介导的化疗抵抗增强化疗药物效果[26]。
BTCRC-GYN15-013研究,这是一项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共入组46例晚期/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既往可接受≤1线化疗,若为含铂化疗,需无铂间期>6个月。应用紫杉醇/卡铂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共6个周期,ORR为74.4%,中位PFS为9个月;pMMR者的中位PFS为9个月,dMMR者的尚未达到;7例患者发生了15起3-4级严重不良反应,无5级严重不良反应[27]。与既往对照相比,ORR及PFS显著改善,毒性未超预期;但尚待III期研究证实。
目前,有两项对比dostarlimab(RUBY;NCT03981796)/阿特利珠单抗(AtTEnd;NCT03603184)联合化疗与单独化疗应用于晚期或复发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5.2.2 联合靶向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常依赖细胞毒性T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而效应T细胞的激活需肿瘤特异性抗原。肿瘤靶向药物可通过增加抗原的释放、促进T细胞的浸润、逆转肿瘤的免疫抑制状态等机制以起到与免疫治疗协同抗肿瘤的效应。
5.2.2.1 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仑伐替尼是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激酶活性,及其他与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相关的受体(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受体、KIT和RET)。
KEYNOTE146研究该研究是一项Ib/II期多队列的临床研究,Ib期研究确定治疗方案为每3周静脉注射200mg帕博利珠单抗与每天口服20mg仑伐替尼,主要研究终点为24周的ORR;研究结果提示该联合治疗方案对于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疗效及安全性较好,值得研究进一步探索。该II期研究的中期分析提示,共入组54例转移性子宫内膜癌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3个月,24周的ORR为39.6%[28]。最终分析共纳入108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8.7个月,无论MSI状态,24周的ORR可达38.%;非MSI-H/dMMR者ORR可达37.2%,MSI-H/dMMR患者ORR可达63.6%。对于既往接受过治疗患者,无论MSI状态,中位PFS为7.4个月,中位OS为16.7个月;83例(66.9%)患者出现了3级和4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总共有22例(17.7%)患者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停用药物[29]。FDA基于KEYNOTE-146研究的中期分析数据加速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联合方案用于治疗既往接受系统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晚期或复发性非MSI-H/dMMR子宫内膜癌[30]。
作为KEYNOTE-146研究的验证性试验,KEYNOTE-775/Study309是首个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在既往接受过铂类药物治疗的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的III期临床试验,达到OS和PFS的双重主要终点和ORR的次要疗效终点。该研究共纳入827例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其中非MSI-H或dMMR的患者697例。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治疗能够显著延长ITT人群的OS(18.3个月vs11.4个月,HR=0.62)和PFS(7.2个月vs3.8个月,HR=0.56),且这种获益不依赖于患者MMR/MSI的状态;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治疗也能够显著延长pMMR(错配修复正常)人群的OS(17.4个月vs12个月,HR=0.68)和PFS(6.6个月vs3.8个月,HR=0.60),基于KEYNOTE-775研究数据,FDA正式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用于治疗既往接受系统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晚期或复发性pMMR子宫内膜癌(不适宜手术或放疗者)[31]。
与KEYNOTE-146和KEYNOTE-775相比,ENGOT-EN9/LEAP-001研究(NCT03884101)纳入的是未经全身化疗的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旨在对比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方案与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的疗效与安全性,且此项研究纳入了中国人群,期待近期结果的公布。
5.2.2.2 联合其他靶向药物 近年来,PD-1/PD-L1抗体的联合其他靶向药物治疗的研究逐渐增多,如与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NCT03951415、NCT03572478、NCT02912572)或靶向叶酸受体α的抗体偶联药物(NCT03835819)等,期待研究结果的公布。
5.2.3 联合其他免疫治疗方式
5.2.3.1PD-1/PD-L1抗体和CTLA-4抗体联合应用PD-1及CTLA-4均属于共刺激受体B7/CD28家族。抗原呈递细胞上的B7复合体与T细胞上的CD28受体结合是T细胞激活的必要条件。CTLA-4抗体和PD-1/PD-L1抗体均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但其作用部位、时期等存在差异。CTLA-4通路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淋巴结部位,作用于T细胞发育的早期;PD-1通路更多的是在外周发挥T细胞调节作用,在T细胞的效应阶段起作用[32]。另外,PD-1抗体主要影响肿瘤浸润耗竭性CD8+T细胞,而CTLA-4抗体除此之外还能引导ICOS+Th1型CD4T细胞的扩增[33]。
现有多项临床研究在探讨PD-1/PD-L1抗体和CTLA-4抗体联合应用于晚期/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NCT03015129,NCT03508570,NCT02982486);其中一项对比度伐利尤单抗单独或联合Tremelimumab的随机对照研究的中期分析提示单独或联合治疗的ORR分别为14.8%、11.1%,中位PFS分别为7.6个周、8.1个周,24周PFS率为13.3%、18.5%,两组的疗效尚可,患者仍在进一步招募中[34]。
5.2.3.2PD-1/PD-L1抗体和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抑制剂联合应用IDO抑制剂在肿瘤微环境中通过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激活、活化调节性T细胞(Treg)等方式等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使机体无法对肿瘤细胞进行识别和清除;与化疗、放疗、其他免疫治疗方式联合应用可能增强疗效。有关纳武利尤单抗和IDO抑制剂(BMS-986205)联合应用于既往治疗进展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研究(NCT04106414)正在进行中。
基于目前PD-1/PD-L1抗体联合治疗的临床研究,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的疗效较为肯定,尤其是对于单药治疗效果差的pMMR/MSS的患者意义较大。未来期待更多更有效的联合治疗,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6 PD-1/PD-L1抗体相关不良反应
随着PD-1/PD-L1抗体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对于其不良反应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PD-1/PD-L1抗体与经典的化学治疗的抗肿瘤机制存在差异,因此不良反应谱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分子机制尚未明确,多认为是影响机体免疫稳态所致。
PD-1/PD-L1抗体相关不良反应的主要特点为出现时间较晚和持续时间较长,可发生于治疗期间或治疗结束后的任何时间;与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的相关性尚未明确;可发生在任何器官,较常见的为皮肤、内分泌、胃肠道及肝脏等。
PD-1/PD-L1抗体单药治疗所致的任意级别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约为60%,3级以上者发生率约为10%。在与其他治疗方式进行联合应用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均有所加重,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于不良反应的管理应重视基线评估、仔细筛查、定期监测,强调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
7 结论及未来方向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癌MSI-H/dMMR的发生率高,尤其是近年来应用逐渐广泛的TCGA分子分型中的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型患者由于肿瘤突变负荷高、免疫原性好,应用PD-1/PD-L1抗体治疗子宫内膜癌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多可耐受。进一步探索与化疗、靶向治疗、其他免疫治疗方式联合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疗效,尤其是对于pMMR/MSS患者意义重大。
基于肿瘤的分子通路以及免疫微环境改变以筛选PD-1/PD-L1抗体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最优生物标记物亦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鉴于MSI-H/dMMR及TMB-H子宫内膜癌患者应用PD-1/PD-L1抗体效果较好,推荐晚期/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行相关分子检测。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分类乃至肠道菌群、驱动基因突变、患者个体化评估未来亦有可能提示PD-1/PD-L1抗体的疗效及不良反应谱。
PD-1/PD-L1抗体治疗可改善晚期/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预后,而联合治疗和生物标记物的探索有望使更多患者获得更大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