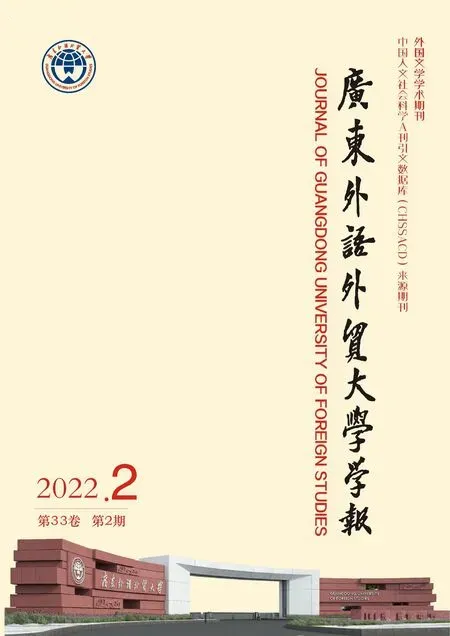创伤与异化:《士兵归来》中退伍军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2022-12-01刘胡敏房洁聆
刘胡敏 房洁聆
引 言
英国BBC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不仅以播音主持闻名于世,他高产的文学创作也给他带来不少的赞誉。他的小说多取材于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以家族历史反映社会变迁,其中聚焦于家族起源的“坎布里亚三部曲”和他自身家庭故事的“威格顿四部曲”均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塑造在现当代英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威格顿四部曲”中的首部作品,《士兵归来》(TheSoldier’sReturn)取材于布拉格的父亲在二战的服役经历,同时也是布拉格童年生活的再现,于2000年荣获英国W·H·史密斯文学奖。小说描述了英国二战退役士兵山姆·理查森从缅甸战场返回家乡威格顿后仍然饱受战争创伤的困扰,在与家人相处和再次融入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心理障碍,体现了战争创伤对士兵战后生活的巨大影响。
“受难者共同体”联结的缺失:难以回归的自我身份
战争创伤是当代创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但是人类对其危害的认知却经历了坎坷的发展。美国著名创伤研究学者朱迪思·赫尔曼(Herman,2015:21)在其著作《创伤与复原》(TraumaandRecovery:TheAftermathofViolence—fromDomesticAbusetoPoliticalTerror)中指出,直到越战之后,学界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有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着重从现代心理学、战争伦理等方面剖析创伤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而甚少将创伤与士兵身份认同相结合来分析战后士兵社会边缘化的现象。胡亚敏(2017:168)在对美国战争小说的研究中提出,“许多老兵在战后难以适应国内社会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疑惑”。 在《士兵归来》中,山姆返乡后也出现了跟许多回归士兵一样的身份认同危机,而他的身份认同危机主要产生于战争创伤。
(一)自我认知的失位
山姆的第一次创伤源自目睹同乡士兵伊恩的死亡。伊恩在一次任务中因疏忽不小心拉掉手雷的导火线,当时周围有很多战友,他无法将手雷扔到安全的区域,在紧急情况下他为了保护战友毫不犹豫地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雷,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战友们的安全。作为队长,山姆对伊恩的死亡从未停止过自责,认为是自己不够警觉才导致了战友的死亡。伊恩死后,山姆异常痛苦,他感到自己“身上很大的一部分仍然追随伊恩,以及伊恩之外不可侵扰的黑暗”(Bragg,1999:94)①。赫尔曼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士兵安全感的丧失,认为“对身在战场的军人而言,安全感存在于他的战斗小分队里”(57),一旦同分队的战友分离或是死亡,士兵的战争创伤会严重恶化。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士兵们安全感的丧失源于对他们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培养出的“受难者共同体”联结的破坏,“(他们的)自我早已融入其中,与共同体难以分离”(胡亚敏,2017:171),因此当战友牺牲后,士兵们会变得不知所措,仿佛失去的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受难者共同体”联结确保了士兵在战争环境下可以互相照应,减少牺牲,但也使他们改变了对“自我”定位的认知,习惯将集体行动置于个人行动之上,因而难以适应战后以个人行动为主的社会生活。返乡后,每当山姆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社交活动时,他总会感到“不自在”和“尴尬”(18-26),甚至当他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也会因不能适应单独行动而感到焦虑:“奇怪的感觉一直延续着,就像他正走进齐腰深的海水里,潮水不停地拍打着他,他的呼吸甚至开始混乱起来……他觉得自己要患幽闭恐惧症了”(28)。唯一让他感到高兴自如的“社交”活动是给牺牲战友的家人写信。在做这件事时,他全身心投入,以至多次忘记去接儿子放学,让儿子感到极度失望,而这也让他的妻子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和不可理解。在山姆的战后生活中,他把对妻子和儿子的责任摆在次要的位置,所有中心都围绕为战友而做的琐事,无法像从前一样融入社会,亦难以重新回归自己战前的社会身份。
(二)大同幻象的破灭
对士兵而言,“受难者共同体”不仅仅存在于同一个战斗小分队中,还可以延伸至整个军队。战争抹去了阶级和种族的差异,无差别的死亡威胁让士兵们产生一种“大同”的幻象,而战争的结束则让这种幻象破灭,返回家乡的士兵无法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到昔日在战场上的连结,因而在回到安全的国内时反而感到无所适从,沉湎于对战争的怀念并迷失自我。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在一次题为“老兵为何怀念战争”②的演讲中指出,返乡士兵怀念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杀戮,而是战争中与他人培养出来的“战友情谊”。布拉格在《士兵归来》中对这种情谊有详细描述:“那是一种超越友谊的感情,你可能甚至不太喜欢那个人,但却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因为你知道对方也会这样对待你”(187),山姆便是这种情谊的拥护者。当他回到退伍老兵的群体中时,他快速地恢复自己战时的从容状态,谈笑风生,从容组织一场大型的活动,甚至帮助战友解决心理问题。山姆与战友相处时的状态显然与他独处时迥异,也令他愈发渴望长期处于“战友情谊”的连结中。在一次退伍士兵聚会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怀念:“他曾以为自己受够了战争。现在,当他看见巴士停在卡索街博物馆的对面时,他内心平静地意识到,自己希望战争延续下去”(186)。
但是,这样的“战友情谊”是建立在战场极端残酷的环境上的,若想通过重拾“战友情谊”来寻找身份认同,老兵们必将打破战后社会的安定秩序,成为社会中异化的个体。在那次聚会中,山姆通过与多位战友叙旧,“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个完全自由的人”(188),并在聚会后放任自己参与醉酒老兵对街道的破坏行动。当他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时,他并没有为自己违反公共秩序感到丝毫羞愧,也毫不在乎别人对此事的不满,相反他“还在心里偷着乐”,认为自己是“勇士”中的一员(199)。小说中许多退伍士兵如山姆一样,把自己排除在战后社会和平民群体之外,拒绝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通过人为制造混乱重新组成“受难者共同体”,从而再次寻找自我的价值。这样虽能获得一时的痛快,但如此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将注定不被社会所接受。正如报纸上的通告所言,“从轻处罚是考虑到这群人(退伍士兵)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但他们也要提醒自己,他们已成为和平社会中的公民”(199)。
和平社会难以为退伍士兵提供他们视若生命的“战友情谊”,而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这种情谊的老兵们无法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让他们觉得回归后的自己碌碌无为,因此战场便成了山姆和其他老兵不愿走出的过往。在工作和社交上屡次受挫的山姆直言“参军对于我而言是一场教育……我喜欢上战场的感觉……我能在那儿做得比我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好”(116)。回归社会后,老兵们与所面对的规则和秩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通过诉诸暴力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缓释内心的创伤,因此他们成为给社会带来潜在危险的边缘人。在这样自我异化的状态下,山姆和其他老兵重新以战前的状态和谐地融入社会和家庭的过程注定困难重重。
异化的亲情:难以重建的家庭身份
除了回归社会外,返乡士兵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回归家庭,重新建构起他们作为儿子、丈夫或父亲的身份。“从社会伦理学来看,亲人是血缘相同的人,同时也是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最可靠、最亲近、最值得信赖和相互依托的人”(庞好农,2017:5)。如果返乡士兵能在家庭中获得信赖,这对他们重拾自信、回归正常生活将有极大帮助。然而,有着战争经历的士兵们普遍认为“没有一个平民(尤其没有一个女人或小孩)可以理解他面对邪恶与死亡的遭遇”(赫尔曼,2015:61),因此,大多数返乡士兵在面对妻儿时选择孤立自己,对战争过往闭口不谈,在失去与家人沟通机会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创伤因无处宣泄而更加严重。
(一)战争创伤的持续影响
战争创伤是每一个从战场上回归的士兵必然要承受的精神痛苦,他们在战场上经历的血腥和暴力让他们无法回归到战前的自我状态。战争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无法修复的伤害,许多幸存者只能采用“失语、失忆、缄默、不愿交流”等方式来面对自己的伤痛,而有很多人也会反复出现幻觉和做噩梦,不停见到死去的战友或敌人的鬼魂,他们回归后已然无法回到战前的生活状态了。正如维克雷(Vickroy,2002:170)所言,“创伤事件能够导致情感上的瘫痪,这些事件不是被铭记,而是会不停地重现,以至于幸存者经常不能用一种可被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叙述这样的创伤”。著名创伤理论家卡鲁斯(Caruth,1996:11)也曾经说过,“创伤是一种突发或灾难性事件带来的令人难以禁受的经历,人们对此创伤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反复重现的幻觉和其他入侵的现象”。在小说中,山姆的战友杰克在退伍后便出现了持续性的幻觉,但他无法与除山姆之外的人倾诉创伤,缺少心理协助的他最终精神失常,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疗养,给他的家庭再次笼罩上阴影。山姆的创伤虽没有杰克严重,但他也出现了“强迫性重复”的症状,战场上的画面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给他的战后家庭生活带去了严重影响,而他错误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深了他和妻儿间原本就存在的隔阂,导致家庭关系异化,失去了重建家庭身份的机会。
山姆脑海中反复出现的画面来源于他在战场上受到的另一个严重的视觉创伤。在一次侦查行动中,山姆和他的小分队发现了11具缅甸儿童的尸体,他们衣不敷体地被日军捆绑在树上,然后被残忍地用刺刀杀死。那些孩子的尸体“在树上一动不动,血液慢慢地流着,流浪狗被吸引过来,疯狂地挥舞着爪子扑向树干,但终因够不着而摔落”(224)。这一视觉创伤极大地刺激了他的情绪,他当即觉得“愤怒完全占据了大脑”(225),无法感知其他情绪。这样的画面总是不停在他面前闪现,让他反复经受创伤的“洗礼”,这种重历伤痛的方式正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被鹰叼啄心脏的痛苦一样,是一种无止境的伤痛(刘胡敏,2020:51)。受此影响,他在返乡后急于将自己的儿子乔培养成硬朗刚强、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男子汉,而不是在温室中被保护得很好,像“被包裹在棉花里的孩子”(74)那样成长。然而,他因参战在家中长期缺席,无法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陪伴他。而家中仅有两位男性陪着乔,一位是乔年迈的姑爷爷,另一位是家中的房客,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乔形成了安静腼腆的性格,与山姆所期待的“男子汉”形象大相径庭。每当儿子做出不符合他期待的举止,如哭泣、撒娇等行为时,他的视觉创伤记忆就会浮现,造成他情绪失控,对儿子实施语言及肢体上的暴力,用类似“妈妈的宝贝”(71)一类的话语来嘲讽儿子,不顾儿子较为羸弱的身体素质而强迫他做一些能证明“男子气概”的活动。山姆的妻子察觉到他的异常,试图与其沟通安抚情绪,但山姆对战争经历闭口不谈,最终变得越来越情绪化。虽然从创伤复原的角度而言,对创伤记忆的重溯有利于患者重建对记忆的自主权(赫尔曼,2015:164),但山姆的自我孤立导致其家庭生活无法安抚他创伤记忆中的极端情绪,反而加重了他与家人之间的隔阂,使他无法尽到作为父亲、丈夫的责任。
(二)身份模板的潜在隐患
除了战争创伤影响,对与山姆同时代的返乡士兵而言,他们还要面临另一个导致亲情异化的隐患。就大多数男性而言,“父亲”这一角色的身份模板来自他们的父亲。拉康在其“镜像理论”的研究中指出,“镜像阶段之后,儿童被迫认同于文化象征秩序中那个超验权威,即父亲或男根符号”(陶家俊,2006:467)。然而,在20世纪初,父亲对儿子实施家暴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被视为通向纪律的捷径,是控制力的有力体现”(73)。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男孩都面临父亲的暴力威胁,父子之间的关系可想而知。山姆的父亲是一位一战老兵,性情暴虐,由于从小饱受父亲的家庭暴力,山姆一度极力否认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且在自己的儿子出生后发誓永远不会责打孩子。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父亲的身份认同早在成长过程中就已完成,从选择踏上战场开始,山姆就踏上了“成为父亲”的道路。赫尔曼(2015:58)指出,返乡军人通常都有“在调节亲密感与攻击性上的困难”,因此战争经历让山姆与父亲越来越相像,进一步加重了他返乡后在家庭中的异化。山姆经常会因为妻子和儿子之间关系亲密而感到非常嫉妒,甚至会因此对他们怀有“敌意”,认为是他们将自己排挤在家庭之外,让他没有了容身之地。一天他回家后看到妻子艾伦又陪儿子乔躺在床上,乔的“手环绕着艾伦的肩颈,脸紧贴着她,他们似乎融为一体,连呼吸都是同步的” (122)。妻儿之间的温情不仅没有让山姆觉得欣慰,反而让他感到嫉妒和愤怒,于是“心中灼烧的嫉妒让他飞快地掀开了毯子,粗鲁地摇醒了艾伦。和艾伦一样,他也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吓住了”(122)。在与妻子和儿子日复一日的矛盾中,山姆的负面情绪逐渐积累直至无法排解,在一次与妻子的争吵中情绪彻底失控,将乔推翻在地:“他的手臂垂落在身侧,他的过去在脑海中破碎。这一刻,他变成了自己的父亲”(216)。山姆对乔的暴力给父子关系带来难以弥合的隔阂,让儿子从此见到他就感到害怕,也让妻子对他彻底失望。
由此可见,战争创伤让山姆彻底变成一个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的人了。战争创伤导致了山姆家庭身份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又反作用于山姆,加剧了他的创伤。对返乡士兵而言,缺乏沟通的夫妻、父子关系让他们与妻儿的情感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隔阂,曾经渴望回归的家庭并没有成为他们修复战争创伤的港湾,反而带来太多新的痛苦,加剧了士兵们对战后生活的排斥。最终,他们无法重新回到过去的家庭身份,这样身份重建上的失败使家庭成为另一个“战场”的延续,给家人带去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
不受认可的英雄:被遗忘的社会身份
饱受战争创伤记忆折磨的老兵们不能完成自我调节,也不能从家庭中寻找到支持,最终只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社会。尽管他们对战后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隔离,但社会也有义务接纳、帮助返乡士兵尽快适应,渡过难关。然而,战争也给社会带去了巨大影响,在剧变中,社会非常容易出现对战事的冷淡和遗忘,导致返乡士兵无法在社会中寻找到自我形象认可与文化归属,失去融入社会、获得新的社会身份的机会,彻底成为异化的群体。
(一)社会身份与自我形象
战争创伤导致二战返乡士兵们无法重新回归过去的自我和家庭身份,但是却让他们认同一个新的身份:战争英雄。在军队的教导中,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远征军士兵们作为“在亚洲大陆吹响与敌人战斗的号角”的“强大军队”(191)的成员,在战争之后已然把自己当成时代的“英雄”。高文惠(2015:95)指出,“身份问题的核心是自我形象问题,自我形象的定位决定着发言立场和价值判断标准”。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英雄”,让山姆在返乡后十分渴望听到民众对他们的赞扬,并且希望民众对这场战争做出正义的评价。然而,英国社会对待缅甸远征军的态度与士兵们的自我社会认同有着巨大偏差。远征缅甸的英国第14集团军又被称作“被遗忘的军队”,由于战争前期的溃败,他们在盟军部队中风评欠佳,国际社会也更加肯定中国和美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的贡献。即使指挥官斯利姆将军后期力挽狂澜,第14集团军的名声依然没有得到改观。斯利姆本人在回国后受到政府的“冷遇”,“连丘吉尔都把缅甸的胜利归功于蒙巴顿和哈罗德·亚历山大两人”(Hogan,2000:9)。山姆及同乡士兵返乡时,威格顿社群没有组织任何欢迎仪式迎接远征军,镇上也没有任何与缅甸战争有关的纪念设施。通常而言,实体化的战争记忆如纪念碑、博物馆等设施是社会帮助退伍军人疗伤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些设施“可以帮助他人知晓创伤事件的真相”(刘帅一,2017:95),军人们被压抑的感情会较容易得到缓解。而第14集团军的退伍士兵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这样的遗忘让山姆及其他远征军士兵意识到所谓的“战争英雄”只是自己的一个幻想,威格顿社群和英国民众根本不会承认他们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正如维克雷(Vickroy,2002:201)所言,“战斗经历让士兵和市民之间产生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市民们无法给士兵们提供必要的心灵安慰”。士兵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返乡后的自我形象认同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严重的二次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返乡士兵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发言权,无法实现社会价值的现实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抛弃家庭,逃离家乡,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小说中,大部分士兵选择离开家乡威格顿,并移民澳大利亚。山姆在多番犹豫后,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二)社会身份与文化归属
除去不受认可的自我形象之外,返乡士兵在重拾社会身份的过程中还面临文化归属的困境。如前文所言,入伍经历让老兵们对军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他们只需做好被“分配”的事情就可以获得满足感。这种令行禁止的“固态化”生活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因为他们“很容易在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容易在对生活的确定和把握中树立自信心”(赵静蓉,2015:31)。然而,当他们回国后,全民动员的战争氛围已经远离国土,返乡士兵们面对的是一个“流动的”战后社会。战后英国百废待兴,经济上需靠美国援助,政治上也面临殖民地独立的浪潮,殖民帝国形象一去不返,社会充斥着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英国社会无法为返乡士兵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稳定性与安全感,而为帝国征战过的老兵们也无法认同这样一个“衰落”的社会文化。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身份认同是“一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归属问题”(杨建玫、常雪梅,2020:34),那么当二者脱节时,便极容易造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异化。对返乡士兵而言,他们已经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赵静蓉,2015:12)。而移民澳大利亚后,老兵们拥有新的移民身份,可以在移民文化形成过程中,重新构建社会身份。因此,在山姆和其他返乡士兵心中,移民这一念头“和重新参军的念头一样,只是想一想都觉得自由”(202),在为新生活奋斗的过程中,他们依旧可以成为“战斗英雄”。
然而,完整经历了英国社会变化的士兵家属和普通民众们并不认同他们的选择。士兵们希望社会能记住战争,民众们则渴望摆脱战争阴影,重回正常生活,与他人在社会文化认同上的分歧通常会成为令老兵们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小说中威格顿的居民们常常以一种“仿佛他们刚度假归来”的淡然态度与山姆及其他士兵打招呼(27),社区工厂的负责人为了维护战后来之不易的稳定现状,更是拒绝为山姆及其他老兵们安排工作。赫尔曼(2015:65)指出,“返乡的军人总是对自己在家乡所受到的支持程度非常敏感,他们会寻找受到大众肯定的实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逃离对战争淡漠的社会环境是老兵们避免二次伤害的自我防御。虽然小说名为《士兵归来》,在小说结尾部分,山姆跳下驶向港口的列车,放弃前往澳大利亚的结局也呼应了题目,但他和妻子艾伦的关系是否能够最终得到修复,在早已将他遗忘的社群里他的创伤是否能够痊愈,都是未知数。
结 语
布拉格在《士兵归来》中将家庭作为创伤叙事的载体,以微观视角呈现了宏大的战后历史背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人后代对战争的思考。“士兵归来”体现的是老兵们对战后生活的美好幻想,但返乡后,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回归家庭生活和获得社会认可3个方面都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无法让他们重新回到过去和谐的生活,让战后生活步入正轨的幻想破碎。由此可见,和平年代对退伍军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回归社会和家庭可以让士兵得以休养生息;而另一方面也让他们面临重新融入社会的种种困境。人们通常从战争创伤心理来分析退伍军人的困境,却忽略了造成这种困境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因素。若想治愈老兵们的创伤,除了在心理治疗方面给予支持外,还需要重建他们的身份认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士兵回归社会和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战争给士兵们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创伤,士兵们战后如何成功地融入家庭和社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关心和支持。
注释:
① 小说的引文来自Bragg M. 1999. The Soldier’s Return[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此后只标明该书的页码。引文均由笔者自译。
② 演讲标题翻译引用自胡亚敏文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