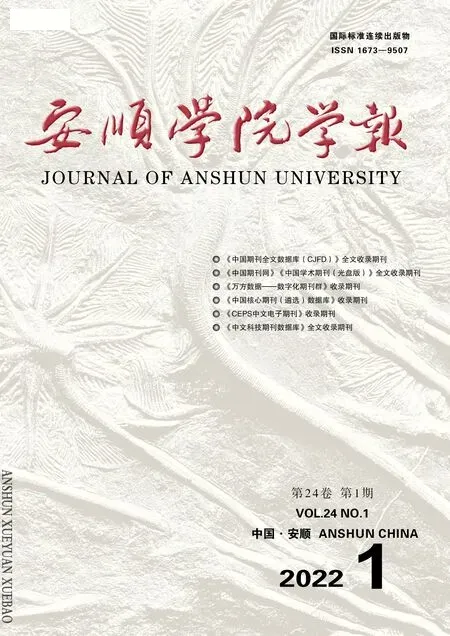阳明心学的生命哲学发微
2022-11-28王青青
王青青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何为“生命哲学”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狭义的生命哲学,指的是狄尔泰、柏格森所代表的哲学流派。广义上而言,包含以下特征的都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一、将生命意向提升为宇宙本源、本质的存在;二、关注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三、体悟生命的存在。[1]儒家对“生命”有其独特的理解,包含了生命本体、生命的存在、生命境界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哲学。牟宗三讲“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于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2]
阳明即成立儒家对于生命的理解并有所发挥,将生命与良知联系在一起。良知是生命本体,天地万物之根源,一切的存在皆在良知的大化流行中开显。阳明更注重从主体的角度与感应天地万物之一体,从内向外去体会生生之意。对于阳明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聚焦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上,而很少对阳明的生命哲学进行挖掘。笔者认为,阳明的哲学可以说是对生命问题探索的产物,生命哲学贯穿阳明的思想。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阳明心学的生命哲学进行探究,这对于心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命之本体
阳明经历从格竹之理失败到龙场悟道的长期摸索,发现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析心与理为二”。阳明经龙场悟道后大开悟,真正与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路径决裂,建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思维路径。圣人的学问即是“生命的学问”,如《论语》以仁为主,《孟子》论性善,《中庸》言“诚”“中和”“慎独”,《大学》讲“明明德”“诚意”,这些皆是不离心体,即无论如何言说,皆是对心体的多方印证。阳明历经生死、百折千难之大悟,所悟便是物与心自然归一,至此阳明对于“圣贤学问”十年困惑遂告解决,自始倡导“良知”之学。“良知”一词源自孟子,孟子认为,人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得“良知”,是人与生俱来,人之本心自发的知仁知义,即为人的良知。阳明以“良知”来综括孟子所言的四端之心。阳明“本心”“良知”“天理”作为本体超越于经验的存在,阳明谓“万化根源总在心”[3]870。良知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与此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存在,是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依据。阳明建构了一个圆融的生命体:天地万物为一体,心物之间、身心之间都是一个圆融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
在阳明看来,良知即为“天地之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源。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3]119这句话历来难以理解,究竟如何理解阳明的“生”与“成”是何意?早在先秦文献中,就从天道创生的角度讲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道,无为无形,自本自根,乃是天地万物存在着的源头。阳明也在不同场合言,良知是“道”“天”,强调“良知”与“天道”为一。故阳明说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是在言天道创造性之表现,即儒道所言之“生生”。在阳明看来人的生命存在与天地万物生命存在都是良知的开显,良知作为主宰支配天地万物,“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3]139。良知是天地万物的生命本体,生化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即是良知的流行不息。生命之构成不仅是形体上的躯壳,“精灵”“良知”“真己”才是构成生命之为生命的本质存在。
良知是生命的源泉,人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也是因人也是良知生化。阳明也继承了儒家对于人在宇宙中地位的一贯认定,即“人者,天地之心”,亦强调了人在整个大生命体中的独特地位。人之所以能够主宰天地万物就在于人心只是“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3]141所谓天地万物呈现,即靠灵明之心来实现。何为“灵明”?阳明将气分为“最粗者”“稍精”“又稍精者”“又精”“至精”。天地氤氲之气,“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122。阳明后学的王龙溪作为阳明高足,也有许多关于“精灵”“灵窍”之类的用法,于阳明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于人,而知也者,人心之觉而为灵者也。从古以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灵而已。”[4]154天地万物本身就处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故当人心这一点灵明是天地氤氲之气“至精”处,故能够自觉自身,赞天地之化育,与良知作为共同“创造者”。万物一体之“生意”才能观、可感,天地万物通过这一点灵明或显或隐,天之高、地之深、鬼神之吉凶得以如如显示。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此灵明充塞于天地万物之间,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虽然各有不同,但灵明只有一个,并非我有一个灵明而天地万物另有一个,天地万物必须要在这一点灵明涵咏之中,才能得以呈现,成天地万物。相应的,灵明亦是依天地万物而成其真实得以具体之显现。
阳明话语体系中,良知生化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与人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人是这一存在连续体中的一个环节,人心是“至灵至明”者。天地万物本身处于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当人心自觉自身,故可以感通天地,赞天地之化育,于天道成为共同“创造者”。人心一点灵明之发用,显现为天地万物。“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3]48的地位,而成为天地万物之主。
二、 生命之共感
如前所述,从宇宙创生的角度而言,天地万物与人皆是良知所化生,因此我们可以将天地万物与人看作一个完整之大生命体,此生命的主宰即是良知。因此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这一点不虚质疑。当人心自觉自身,于天道成为共同“创造者”。这里隐含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人如何自觉到自身,体会到于万物一体?阳明言“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3]141在阳明看来人心与物同体的关键就在于“感应之几”,“感应”这里的感应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刺激与反应,也不是感性的接受与被影响,而是“即寂即感,神感神应之超越的、创造性的、如如现实之”[5]感应。在感应关系中,不是心意构造对象物,而是感应关系构建起了心物二者的一体性[6]。提到心物关系,不得不提非常著名的“岩中观花”的话头: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122
关于这个话头,学界也从意义论、存在论等多种角度进行解读,但这些解读潜藏着一种“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心”与“物”必然彼此分离,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物”,这显然于阳明“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不相应。友人以“于我心亦何相关”来质疑阳明“心外无物”,友人在提问在于岩中花树作为实在之物,与“心”有何关系,产生这种疑问的根渊就在于其把“花”与“心”分为不相干的独立物。阳明所言之“物”不仅仅是的客观存在物,而是与“意”相联系在一起的“事”,是生命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阳明皆以“吾心之处”出发,物、事与心都是“一体”的,与吾心不相离。阳明用“未看时,同归于寂”“看时,一时明白”回答友人的问题,这里“寂”与“明白”的关键就在于“未看”与“看”。阳明这里的“看花”,不在于将花作为客体去认识与分析,而是去感此花,观照此花,“一时明白起来”是在神感神应之中“明白起来”的。“看花”之看,不仅仅是经验范畴的观察、观看而言的“感知”,而是这汝心与万物的神感神应,阳明言“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3]41。花之颜色“明白”实是我的“灵明”让其“明白”,“此花颜色”是我的“灵明”之“虚灵明觉”的神感神应的关照下得以开显。依这点灵明的感应之几,天地万物流行不息,即阳明所谓的良知之造化,这种造化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创生”,而是一种“开显”,当未看此花时,这一点灵明凝聚,天地万物皆入混沌无是可是,无非可非,“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来看此花时,人心一点灵明发动于窍,事而应感而动,良知由寂而感,对于天地万物显现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之作用。“此花颜色便明白起来”。所谓的“花树不在心外”,是表示我与花树俱在这一点灵明的感应之中呈现。感则俱应,寂则俱寂。
人具有独特的宇宙地位,人之所以作为天地之心,就在于天地万物之大生命虽都有良知,亦有灵明,但是只有人能觉悟到这一点灵明,即只有人能具有觉知到这良知的能力。动物与人一样皆能视听言动,然而它们并不会意识到生命的流动,也觉察不到生命本体。如果没有人心之感应,天地万物存于混沌之中,无事无非;当人心应感而动,天地万物开显,天地万物具有“生存之道”。天地万物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个体生命之流行是体会天地万物一体的基础。如果人与天地万物只是一种“二物有对”的分割状态,就如同人之手足因血气不能流贯变现出的麻痹之症,即为“不仁”。见到小孩掉入井,定会产生恻怛之心,这既是良知本心与孺子产生感应;见鸟兽哀鸣觳觫有不忍之心,草木摧折瓦石毁坏有顾惜之心,都是良知本心与物神感神应,而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这即是说无论是有生命之物,或者是草木瓦石等无生命之物,当它们受到破坏时,会自然产生感应不忍关爱之心,也即是“明德”“良知”“一体之仁”。至此,阳明通过良知感应,将人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了一起,人也才真正与天地万物有着仁爱关切,将天地万物看作是自己密切相联的一体。由间于形骸之分的小人走向与物无对之大人,这种对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追求,不仅是人生理想的追求,更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体现。 这种通过良知感应的切身体验所获得万物一体的生存上的体认,从而作出直接的道德选择,自然落实到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即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本有之“仁心”,即“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3]1067。“明德”作为本体之存在,不仅与个人相联系,也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存在,“明明德”要通向“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社会实现,自然要“亲民”,“亲民”即是把此仁心施于百姓。换言之“明明德”的道德实践必然在亲民的政治实践上展现,实现“止于至善”。阳明在《大学问》结尾处强调“是之谓尽性”,以为必须“明明德”于天下才能使吾之“性”圆满实现,尽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尽仁,尽仁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必须落实在亲民之实践,才能够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阳明通过人与物之间“感应”自觉到人与物之间的一体,这种感应并非意识层面的认识,而是源自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所产生的内在体验。这种体验自然落实到对社会的责任感与生命感。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是经验意识层面的理性选择,而是人之为人的自觉追求。
三、 生命之超越
中国文化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暂时性具有深刻体认,“不朽”是源于人类对于生命之无限性的期盼。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这种对生命之超越的追求,即是对成圣成贤的追求。如何成为圣人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圣人学问”即也是“生命学问”。阳明的学问也可以说是追求“圣学”为宗旨,以实现生命的超越。在儒家学者那里,圣人可学而成,这可以追溯到孟子“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进一步明确了学习是为圣的途径。阳明从小就认为只有读书学圣贤,才是天地间第一等事。阳明在学为圣人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之后,发觉朱子“格物”始终事物之理与吾心为二,打不成一片,进而反思,凡人究竟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自我本心、本性如何与圣人之道相印,在经过“遍求百家”“百死千难”的曲折之后,终在龙场一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之道,并不是向外求事物之理而获得,而是廓清心体之后呈现的本心真性。实言之,阳明那里,“圣人”不在是外在的权威,而是每个人具有的良知、本心。阳明将圣人理解为人人本有的良知,强调“心之良知是谓圣”。前面已经提到,良知是生命之本体,人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也是因人也是良知生化。阳明言“满街都是圣人”,实际上是抹去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界限,将圣人拉到了世俗的世界,在拥有良知良能上,圣人与愚夫愚妇是相同的。这无疑是说人人都可以去追求生命之无限性,实现生命之超越、成圣成贤。
在阳明那里实现生命之超越即是要为己与无我。为己即是使自我人格不断完满,“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3]302,“克己”与“为己”表面上是矛盾的,阳明这里通过将“己”区分“真己”与“躯壳之己”化解了此矛盾。“真己”即是本体之心,是破除私欲,达到超越善恶的本真之己,即是永恒的大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是良知;“躯壳之己”即是因“间于形骸、强分尔我”之小我。克己并非不让鼻四肢去视听言动,而是不能够“随躯壳而起念”欲享逸乐。人的生命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就在于良知,因此没有真己作主宰,躯壳也不是躯壳,而是死物。反之,有真己作主宰,躯壳便不是死物,而是活泼泼之生命,真己之显现。人如真能“常常保守这个真己本体”[3]41便是有“为己之心”,便能克己,也即是能为己。“无我”强调的是达成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只有通过无我的工夫,才能破除自我与他者的相对待,将自我融入绝对之大我,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阳明那里为己与无我可以说是同一种状态的不同角度的言说,为己之己是与天下万物为一体之真己,成己的实现即也是无我境界,破除小我之执着。
在阳明那里虽然人人具有圣人本质,但并非说人人已是圣人,只是可能性上言每一个人都是可能成圣的。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顺欲念而动,受私意所避免。圣人之心如同明镜,随感而应,在现实之中于遇到的事事物物之中落实良知;凡人则受物欲私念遮蔽使得良知隐而不露。良知自光明“皎如明镜”,物欲私欲遮蔽后变得昏暗,不能够感而必应,无物不照。只有通过“致良知”的工夫才能使良知恢复其全体莹澈、无物不照之本来面目,此过程即是追求生命之解脱与超越的过程。所以阳明强调的“致良知”即是生命之超越的关键,即能否成圣之关键。如何“致良知”实现生命之超越,延伸有限的自然生命?
首先“自信良知”。虽然“个个人心有仲尼”,但是因“自信不及”使得胸中之圣“都自埋到了”。“自信不及”就在于人们不坚信、不觉悟“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之所以这样就在于私欲遮蔽了良知,所以使得良知存而不见,如同浮云把白日遮蔽一般。王龙溪曾言“致虚则自无物欲之间,吾之良知自与万物相为流通而无所凝滞……后儒不明一体之义,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虚,不足以备万物”[4]43。良知与万物为一体,不可分为二,只是人有物欲夹杂,故有良知与万物二分,而不见良知,反而将质疑良知虚,将良知悬挂起来。信得良知就是要摆脱“躯壳之己”的限制,让“真己”得以呈现。自信良知并不是一般宗教对象化的信仰,而是对良知人人具有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即是依良知本心而行,即是让良知成为生命之主宰,冲破物欲之遮蔽,以回归广大之本体,让心之良知充塞流行。
致良知的具体方法而言,阳明所言有很多,静坐收敛、省察克制、拆穿光景、拘谨穷理、事上磨炼等,但都是指点语,总结起来即是静与动的工夫。阳明早年教人静坐,主于收敛,旨在涵养省察,隔绝习气私欲,以恢复本心。所谓静坐即是针对朱熹一派“格物”之说务外遗内的倾向的纠偏。但静坐不是槁木死灰,使之不起,而是思虑萌动的省察克治,“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寻出来”[3]18一念萌动是便克去。但别人没有阳明百死千难的求道经历,亦没有真切笃实的知行工夫,所以便“喜静厌动,流入枯槁”。阳明察觉偏境陷空的弊害,只从正面教人事上磨炼。因此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3]104。一味好静只是逃避责任的私欲,消蚀人之为人的道德责任与担当,纵使一时收敛得住心,但也是一种假定,遇到事情,便不能应事接物。阳明借用孟子“必有事焉”之说,表明良知于应事接物中发挥效用。所谓的事上磨炼也只是在日用伦常中磨炼此知行之本体,磨灭“小我”之习气,使七情所感,不过也不及恰当好处。即是教人在日用伦常中,磨灭私欲,使得“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虽然人人都具有感应天地的能力,走向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人之为人内在本质,大人或是小人都是以万物为一体的,皆有一体之仁。但是现实世界中,小人只是有些时候受私欲遮蔽而不能澄明的呈现,也即是良知障碍,这并不是说良知不存在,而是如同浮云掩日一般,良知的光明泯而不露,但只要“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3]109。
当真正能够致良知,使良知本体扩充至极全体呈露、无有亏欠无障蔽,便能自觉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即能破除小我的执着,达到无我的境界。即是在自我生命过程中,视天下国家为一家,视天下之人如一人,从而也就能够自觉地天下生命之苦乐即我苦乐,唯有解除天下百姓的困苦,才能使得良知获得满足,实现万物一体的心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倘若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3]29此即意味着自我与他者共在,个人生命意义完成过程,亦承担着对他者的伦理责任,假使有一事一物失去其安身之所,即是我心之仁有未尽处。在这个意义上人自然而然对万物都持有深切的仁爱以及关怀,将天地万物与自己生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生命关怀提供动力。换而言之,生命之超越,并不是个体能够完成的,追求生命的不朽与超越,自然而然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个体生命之超越与他者乃至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克服有限之生命,共同迈进大化流行之境界[7]。
综上所言,阳明由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之超越,即是儒家所追求的圣人之道。这种生命的超越就是良知本体扩充至极全体呈露、无有亏欠无障蔽,便能自觉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即能破除小我的执着,达到无我的境界。
结 语
生命的本质以及生命境界之探寻历来是儒家关注之重点。儒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主张在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把握生命的真谛,去认识生命、追求生命之境界,从而实现”人之为人”之价值。阳明所言之心、良知,即是孟子所言的本心,即是道心、人心。道心与人心为一,并非有两颗心分别存在,心之本体纯粹至善,谓之道心;顺气质私欲而发,则谓之人心。此心作为天地万物主宰之心,贯通内外动静、无物我之分,与天地万物同流。天地万物的生命与人之生命本为一体,只是小人因顺其私欲而将自己与万物区分开来。阳明之学,从具体而真实之良知指点本心,而本心即是天理,亦由良知之感应而建立天地万物之同体。从良知出发,归于生命的本真澄明之境,时时不忘 “尽心知性”。心之本体的“良知”应当是观照之重点,“致良知”即是良知之明觉充分呈现出来,见之于行事,以成就道德行为。这“致”的工夫是不间断的,不断扩而从之,则人的生命行为便是良知天理之流行,一切言行皆是良知的妙用,一切事物是生命的自然,于是在生命的进程中自然。生命之超越即良知本体扩充至极全体呈露、无有亏欠无障蔽,便能自觉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即能破除小我的执着,达到无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