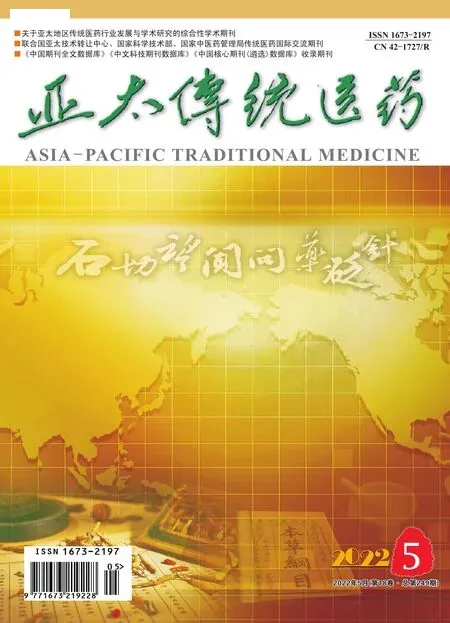曾普华基于“癌毒致病”和“方证辨证”治疗肝癌临床经验
2022-11-27李佳颖曾普华
李佳颖,曾普华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2.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为一种发源于人体肝细胞或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幅上升。全球癌症发病排名中,肝癌居第六,每年约有91万人发病,死亡数为83万,居世界第3位[1]。肝癌起病隐匿[2],初期症状难以发觉,病情发展迅猛,绝大多数患者在知晓自己患病时基本已属中期或晚期,因此常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化疗和放疗对肝癌的治疗效果并不明显,西医采用肝切除术、肝移植术、血管介入、射频消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方式来治疗肝癌,但是不良反应大[3],疗效欠佳,患者生活质量及生存率大大下降。当前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联合传统手术、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能发挥减毒增效、抗复发和转移作用,实现“带瘤生存”,提高患者远期生存率。
曾普华教授是全国青年岐黄学者,全国第一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在恶性肿瘤防治领域经验丰富,对中医药治疗肝癌有独特见解,临床疗效较好。将曾普华教授治疗肝癌相关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1 肝癌的中医病因病机认识
原发性肝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系统命名。古代有关资料曾对类似病证作如下解释,肝癌可归结为“脾积”“肝积”“积聚”“膨胀”“肥气”“黄疸”“癖黄”“癥瘕”等范畴。李春辉教授认为肝癌发生的基础为正气内虚,在人体发病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此症状,伴有湿热邪毒、过度劳累、饮食不节,七情致病犯及脾胃,终致正气亏虚,脏腑功能失调,以“扶正祛邪,重视脾胃”为主要治则[4]。王沛教授将肝癌分为肝郁脾虚证、气血瘀滞证、湿热蕴结证、气阴两虚证等四种常见证型,治疗多以滋阴柔肝为主、健脾调理气机为先,补肾消导为辅[5]。曾教授指出“癌毒、瘀血、脾虚”为肝癌的核心病机,以“清热解毒、化瘀软坚、健脾理气”为基本治法,辅之以清热利湿、清利肝胆、利水化湿、消食和胃、通利二便、补益肝肾等法。
2 方证辨证理论阐释
方证辨证又被称为“汤方辨证”,即以方剂的适应证、病机、治法、使用禁忌等作为大体方向,对疾病的表现、体征等进行深入理解的辨证方法[6]。著名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发明了“汤证”概念,如“麻黄汤证”“桂枝汤证”。此后药王孙思邈也提出了“方证”一词,他运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在《千金翼方》将方证作出了具体解释,开拓了一种类型的证、一种类型的方的方证治法研究体系[7]。清代柯韵伯《伤寒来苏集》谓“仲景之方,因证而设,此证即为此方,为仲景活法”,即为“有证便是方”。《伤寒论》中的113方被徐灵胎划分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12类,各类主证中主方为先,随后将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形成以方类证、证从方治的“方证对应”学说。如柴胡类方证表现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心烦欲呕,口苦咽干目眩”;葛根汤证为“项背强紧,无汗恶风”,而“手足不温、手足冷”即为四逆汤、四逆散方证。方证辨证简化了更深层次的思维步骤,是中医学辨治过程中的一种“黑箱理论”,其融入各大辨证体系(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是各体系的精炼与提高,在临床实践中,体现了医者的直觉思维,在辨证论治中至关重要,是方证辨证思维的更高层次。
3 方证辨证治疗肝癌
曾教授认为肝癌以“肝郁脾虚,瘀毒互结”病机为总纲,瘀毒所生,多因正虚邪盛,多种病理因素夹杂所致。癌毒作为一种有形之邪、一种异于六淫的特殊毒邪,其从无到有,从产生到不断进展是内外致病、邪气长期作用于人体的结果。“癌毒致虚”,故肝癌患者多兼有肝瘀脾虚、脾虚湿困、湿热毒结、肝肾阴虚等证;现将曾教授基于“癌毒致病”和“方证辨证”治疗肝癌的思路及用药特色介绍如下。
3.1 方证对应论治
“肝区胀痛或刺痛,腹胀纳减,面色沉闷,气弱厌语,舌紫暗,脉弦或涩”——“肝复方”主之。曾教授根据方证辨证,临床上遇到此类症状的肝癌患者,予肝复方加减,患者肝区胀痛或刺痛,伴有面色沉闷,舌紫暗,脉弦或涩,是为一派瘀滞之象,腹胀纳减,少气懒言为脾虚之证,由此辨为肝郁脾虚、瘀毒互结证。方中党参、黄芪、白术、茯苓补中益气,香附、柴胡、陈皮疏肝理气解郁,桃仁、莪术、鳖甲、软坚化瘀,甘草调和诸药,共奏健脾理气、化瘀软坚之功,是治疗肝癌肝瘀脾虚患者的主要疗法。
“腹大胀满,神疲乏力,身重纳呆,肢楚足肿,口粘,常感恶心,尿少,大便稀溏,舌淡胖,舌边伴齿痕,苔腻,脉濡或滑”——“四君子汤合五皮饮”主之。曾教授临床遇到此类患者,予四君子汤合五皮饮加减。患者脾失健运,故水谷不化,纳呆便溏;脾虚则运化失常,水液内停,则患者身重肢肿,尿少;湿性黏滞,上泛于口,口中黏腻难忍。舌淡胖,舌边有齿痕,苔腻,脉濡或滑,均为脾虚湿困的典型舌脉,故辨证为脾虚湿困、瘀毒互结证。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等健脾益气,陈皮、大腹皮、冬瓜皮等祛湿利水消肿,诸药相配,共同起到健脾益气、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肝区胀痛灼热,纳呆,脘闷,发热,黄疸,口干口苦,心烦易怒,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小便黄,大便结或粘滞不爽”——“茵陈蒿汤”主之。临证遇此类患者,曾教授选用茵陈蒿汤加减。病者湿毒瘀阻肝胆,胆汁外溢发为黄疸;湿热毒邪耗伤阴血,阴虚阳亢,则可见口干口苦,心烦易怒;湿热侵袭大肠,壅阻气机,致大便结或黏滞难忍。结合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典型湿热之征,辨为湿热内盛、瘀毒毒结证。方中茵陈、栀子、大黄清热去湿,利胆退黄,猪苓、茯苓、薏苡仁、大腹皮等加强健脾祛湿,理气宽中,共奏清热去湿、补益脾气之功。
“肝区灼痛,腰膝酸软,手足心热,心燥难寐,低热盗汗,口干,舌红少苔或光苔,脉细数”——“一贯煎”主之。临床遇此类患者,曾教授以一贯煎加减。患者肝区灼痛,腰膝酸软,手足心热,口干,舌红少苔或光苔,脉细数,实为阴虚内热,肾水无以上滋心火,心火偏亢,故见心烦不寐,阴虚内热迫津外泄,患者可出现低热盗汗,此辨证为肝肾阴虚、瘀毒互结证。方中生地、当归、枸杞滋养肝肾阴血,川楝子疏肝解郁,女贞子、菟丝子增强补益肝肾之效,生甘草调和诸药,共同起到滋阴养血、补益肝肾之功效。
3.2 专病专方专药运用
曾教授认为肝癌是由于“多因相合、癌毒内生”导致的,肝癌的主要病机应当是“癌毒、瘀血、脾虚”,在肝癌发作的整个过程都伴有相关症状,由此总结出肝癌之效验方—“固脾消积方”(其前身为“益气化瘀解毒方”)。前期研究已证实固脾消积方能对肝癌西医治疗发挥减毒增效作用,稳定瘤体,抗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改善疾病预后[8-9]。
曾教授根据“癌毒致病”理论,将2~4味可抗癌的中草药融入方证辨证中,如重楼、半枝莲、蛇舌草、龙葵、半边莲、莪术、水红花子、八月札等,常用全蝎、壁虎、蜈蚣、土鳖虫等虫类药,借其峻猛之药性,攻毒散结,剔痰通络。
3.3 辨证加减治疗
对于肝癌临床常见症状,在方证辨证上加减用药,标本同治,疗效显著。便秘者加大黄、厚朴、枳实;腹泻较重者,加炮姜、苍术、炒扁豆;腹大胀满、尿少者加枳壳、大腹皮、茯苓皮、猪苓;腹水较重者,加泽兰、车前子;疼痛甚者,加延胡索、香附、川楝子、郁金、血竭;恶心欲呕者,加法半夏、竹茹、旋覆花;肝肾不足者,加枸杞、女贞子、菟丝子;身目发黄者,加茵陈、栀子、赤芍;气闷无力自汗者,加人参、黄芪、浮小麦、五味子;低热者,加知母、银柴胡、白薇;高热者,加生石膏、知母、黄芩、银花、连翘、羚羊角;纳差食少者,加山楂、神曲、炒谷麦芽、鸡内金。
4 验案举隅
曾某,女,42岁。初诊主诉:肝肿块术后及肝动脉灌注化疗后2个月。患者于2009年7月8日行左肝肿块切除术,手术顺利,术后病检示:(肝左叶)高-中分化肝细胞癌,5 cm×4 cm×3.5 cm。肝被膜未受到癌变影响,脉管癌栓及卫星结节较少,段端未见癌,四周肝脏组织出现硬化症状。CD3(T淋巴细胞+),PD-1(+30%),PD-L1(肿瘤细胞-,部分淋巴细胞+),Ki-67(+15%),CK19(-),VEGF(弱+),CD34(血管+),GPC3(局灶弱+),Hepatecyte(+)。术后先后肝动脉灌注化疗6个周期,自2011年2月起一直于曾教授处求助中医药调治。刻下症见:肝区胀感,无明显疼痛,腹胀,厌食厌油,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夜寐尚安,二便调。舌暗红,苔白,脉弦细。既往有乙肝病史。辨证:肝郁脾虚、毒瘀互结证。治法:健脾理气,解毒化瘀。处方:固脾消积方加减,党参15 g,黄芪30 g,白术10 g,茯苓15 g,柴胡10 g,郁金15 g,鸡内金6 g,女贞子20 g,枸杞10 g,菟丝子10 g,法半夏10 g,八月札10 g,海螵蛸15 g,莪术10 g,土鳖虫6 g,鳖甲15 g,壁虎10 g,重楼10 g,半枝莲30 g,蛇舌草30 g,龙葵30 g,甘草5 g。配合肝喜片服用治疗。根据实际诊疗情况加减,并定时复查,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至今已逾10年之久。
按:本案患者既往有乙肝病史,邪毒长年侵淫,日久癌毒内生,毒瘀互结,导致肝积内生。经手术和局部灌注化疗后,损伤人体正气,肝脏受损,累及脾胃,导致肝郁脾虚。治以扶正为主,同时解毒抗癌,选择健脾理气、解毒化瘀为治疗法。方中人参、黄芪、白术、茯苓、灵芝等益气健脾,枸杞、菟丝子、女贞子等补益肝肾,固后天以补先天。炒栀子、郁金凉血散瘀,莪术、鳖甲等化瘀软坚,八月札疏肝理气,全蝎、壁虎攻毒散结,重楼、半枝莲、蛇舌草、龙葵等清热解毒,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共奏健脾理气、解毒化瘀之攻效。本案为术后、介入治疗后长期坚持中医药抗复发和转移治疗的患者,达到了较好临床效果。
5 结语
方证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简化形式,是临床医师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具有高效性、便捷性、灵活性等特点。熟练掌握其中要义,会使临床疗效获得质的飞跃。本文总结了曾教授基于方证辨证理论,从方证对应、专病专方专药、辨证加减等三个层面进行病证合参,精准论治,疗效显著。总之,如何发挥“病证结合”“方证辨证”的优势和特色,是我们临床实践中应当不断挖掘和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