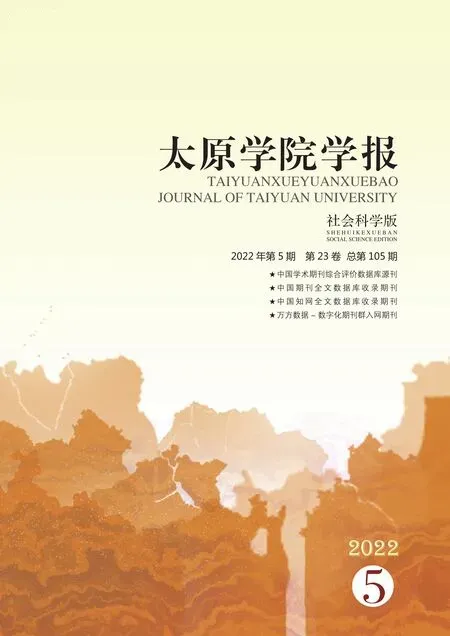扬之水“名物新证”的研究方法小议
2022-11-27周斌斌
周斌斌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扬之水(1954—),浙江诸暨人,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等系列名物考证的著作,被认为是继青木正儿之后又一名物学的代表人物。其用“名物新证”的方法诠释章句、阐释诗义,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被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称誉,“有较好的成绩,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470。她的成绩令人瞩目,她的“名物新证”的方法也应与夏传才教授所说,“当另文讨论”[1]470。
一、学界关于扬之水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辨析
学界对于扬之水研究方法所持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以谷雨芹《扬之水〈诗经〉研究小议》为代表,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扬之水采用考古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2]。在该文的研究方法专论里,谷雨芹进一步认为,扬之水是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施于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先之人,考古与文学相结合的说法在此处被注解为“‘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2]的“二重证据法”说。第二种观点,以王莜芸为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撰写的序言里所提到的“三证归一”说为代表。她认为,“作者对名物的考证和叙述,力求从实物、文献(历史记载和文学)、图象三个方面,三类线索,三条源流的交汇点上,穷尽与对象相关的资料”[3]4。第三种观点,以夏传才教授为代表。他认为扬之水把“文化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研究与传统训释考辨相结合”[1]384,暂将此观点称为“综合说”。
造成三种观点说法不一的原因,在于扬之水并未明白声明自己的研究方法。三种观点在扬之水的文章里都能找到相关的支撑材料。扬之水2004年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定名与相知》,同时也是她于2004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的主干内容,该后序内容后来在2012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合编版《古诗文名物新证》的序言部分以《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的面貌再度出现。虽然三版文章的内容有所翻新,但涉及到的方法意识并没有多少改变。总结这三版文章所涉方法论的部分,可得如下认识:第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4]1;第二,“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但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文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5];第三,新的名物研究“必须站在历史、文学、考古等学科的结合部来审视文物”[3]525。将前两条认识综合来看,扬之水是说,传统名物学以训诂和考据为方法,新的名物学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得到方法上的革新,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论将完成一种接近真实历史的叙述。这便为“二重证据法”说提供直接依据。第三条认识表现了扬之水综合历史、文学、考古、文物等多学科结合的方法意识,这也为夏传才教授的“综合说”提供了材料支撑。除此之外,在2004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文名物新证》的封底部分,印有介绍字样,“运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合处复原起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3]。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结合的说法无疑复刻了王莜芸的“三证归一”说。因此,有关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辨清。
需要加以辨析的是,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就是“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也是实物、图像、文献三重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原因在于,图像不能单独存在,必须附着在墙壁、纸卷等实物上,因此沈从文将图像统归于文物义。到了1960年代以后,因发现图像独特的证据价值,沈从文才开始区别文物为图像、实物,形成后来所讲的“三重证据法”。事实上,沈从文、孙机、扬之水三代学人的研究方法都是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但由于沈从文并未使用“三重证据法”一词,沈从文在《文学遗产》发表的多篇文章里都只提“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致使学人多误以为沈从文“文物结合文献”的方法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孙机、扬之水的研究方法也都归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是学人的误解。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有相当大的差别。孙机有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出土的文献跟传世文献”,“二重证据就是我拿着《史记》的《殷本纪》和出土的甲骨文里面记载商朝的事来比较来研究”,“现在除了二重证据还有实物”[9]。王国维认为“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思想上”[10]。因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方法和思想的现代性,史料眼光多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上。到了沈从文做研究的时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学术语境的改变,致使这一时代的学术眼光更多放在了考古文物上。考古与历史的结合,这并不稀奇,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云,“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11]303。沈从文“文物结合文献”的“三重证据法”,关键是把考古学的成果带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去。过去的名物研究,多是训诂、考据等文学内部的研究方法。沈从文“三重证据法”打通了考古学与文学之间的通道,对于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名物,不再只是探究字义,而是与考古文物相对应,从实物、图像两方面探究该名物的形制、功能、作用、演变等信息。这如同扬之水所说,“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4]5。青木正儿的名物学承接传统训诂与考据,方法上文献互证,史料上依靠真实性不高的笔记小说、谱录类书。扬之水的“名物新证”应用沈从文“三重证据法”,态度上科学实证,史料上增加现代考古学的成果,方法上是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的综合。
二、扬之水“名物新证”中的“三重证据法”
前已论及,不仅扬之水“名物新证”的题目直接来自沈从文,方法上也是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这不只是体现在扬之水学术谱系的继承上,还表现在扬之水“名物新证”的应用里。
这里试举“者舌”一例来具体说明扬之水名物研究中“三重证据法”的应用。在扬之水之前,已有学者做过“者舌”考。法国人侯锦朗在文章《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里引池田温刊本做过“者舌”研究。他指出,“‘者舌’是指一种需要确定其意义的罗表的组成部分,也出现于P.2613号写本中(被断代为873年)。池田温于其刊本(第579页)中将‘者’字改为‘赭’而又未作解释”[12]93。侯锦朗说,“者舌”是组成“罗表”的配件。但“罗表”又为何物,他没有作出解释。事实上,侯锦朗此处讲的“罗表”并不是一个词汇。侯锦朗援引的“罗表”出自伯3432号“又肆福故幢贰,杂色罗表,色绢里,高梨锦屋并舌者锦绣罗带木火珠”。此处的断句,并非侯锦朗以为的“杂色/罗表”,而应读为“杂色罗/表”,和后面“色绢/里”,一起构成“幢”的表、里两面[13]。此外,侯锦朗也无法解释池田温为何将“者”字改为“赭”字。
不同于侯锦朗“引书注书”式的研究,扬之水应用“三重证据法”进行“者舌”考,前后历经五年。2007年,第一版“者舌”考从文献出发考据“者舌”一词,发现《魏书》卷一二〇《西域传》中记有“者舌”国,是指“故康居国”,显然与这里表示帐之物件的“者舌”无关。而后,扬之水从敦煌壁画的图像考察,发现壁画中帐、幢、伞、幡的各种构件几乎可以通用,因而,她提出,“者舌”或是“蒜条”的地方口语化名称,即指壁画上绘有的犹如“蒜条”的“锦屋”垂饰。据此推测“者舌”的词源,“舌”或状其式、“者”或通假“褶”字[14]。相关的实物证据,扬之水举出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帷帐部件中,五种颜色拼合相迭的尖角图案的垂带,以及莫高窟一七一窟北壁华盖图中以五色缀为三角图案且在末端坠上帘押的蒜条。第一版“者舌”考初从文献考据,并无收获,而后围绕图像,发现“者舌”即诗词中常见的“蒜条”一词,并辅以实物资料为参证,为推论提供明证。2010年,第二版“者舌”考在第一版之上,新增了重要的文献史料。第一版在得到“者舌”即“蒜条”的认识后,反推“者舌”的词源,其中“者”为“褶”之假借的看法,是推测的结果,没有实证。第二版考证新发现了《一切经音义》中有关“者舌”的史料。徐时仪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之慧琳《音义》卷二十六“即便有娠”条,“尸仁反。怀胎也。经作身。如如盖是一,赭舌是多。者应赭字,乃是盖,四面垂綵。綵舌也”。按注本,这一段释义无法贯通。扬之水考校认为,《合刊》在此处标点有误、校注有失。实际上,该段为两条释文误作一处。“如盖是一,者舌是多”其实是另外一条辞条,释义“者应赭字,乃是盖四面垂綵。綵,舌也。”依此言可知,“者舌”即“赭舌”,指华盖周边下垂的彩带[15]。此说便为起始猜测的“蒜条”说补足了文献依据,且又解释了侯锦朗无法解释的,池田温为何将“者”改为“赭”字的问题。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王乐、赵丰2009年发表的《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从敦煌出土实物入手考证伞盖的部件,认为“者舌”其实是伞盖下面缀有背衬的三角状饰片,而扬之水讲的“蒜条”其实是敦煌文书里写到的“柱子”[16]。扬之水在此说的基础上再一次名物考证。她还是从图像出发,发现早期莫高窟的洞窟壁画里有着所谓的“垂帐纹”,帐子下面垂条饰物底端的造型犹如柱子一样。扬之水详细考察了这种柱子造型的发展演变史,得出“柱子”得名的依据其实是以形得名。“柱子”因形状为柱状而在文献中得此名称,至于“者舌”确实是伞盖下面的三角形饰片。
比较侯锦朗和扬之水的“者舌”名物考,侯锦朗从池田温的刊本出发,引书注书,不仅不能弄清楚“者舌”为何物,且由于缺乏基本的文献学功底,造成引书过程中断句错误、理解失当,其生造的“罗表”一词将研究者带入了更深的迷雾。这是传统名物研究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扬之水有言,以往名物研究的局限在于“古人受到资料的限制,比如清代考据家看不到现代考古的成果,国外汉学家则多半会受到语词多重含义的限制”[17]。应用“三重证据法”的名物考证,其基础依然是文献。文献记载的信息便于检索、且丰厚充实;物、图的信息尽管真实、形象,但材料复制的代价相对高昂,不易获取,且单一文物提供的信息也极其有限。扬之水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考据、训诂得到有用信息,再与物、图比证。这样做有效规避了传统名物研究的一些局限。从文献、图像(指壁画一类的形象性文物)、实物三重史料里比较互证,因为有多重证据的参照,可以有效发现文献史料的书写错误,确定其文字表意的具体所指,这是其一。其二,图像、实物有物无名,文献史料有名无物,三重史料的结合实质上是在做持名找物的工作:带着文献记载的、不知所云的能指符号寻找图像、实物中的所指意义,完成名、物贴合的历史还原。这样做不仅复原了历史中的物,有效解决一些历史文化谜团,同时褪去物之所属的现代眼光,还原生成物的古典况味。其三,文献书写是一种固定化的符号活动,在文献中可见“者舌”之符号名称,却难晓生成“者舌”的符号化思维过程。文献与图像、实物的名、物比证可为探索词源提供一条途径。
三、扬之水应用“三重证据法”的实绩
扬之水继承沈从文、孙机“三重证据法”的研究范式,进行系列“名物新证”,取得了不少实绩。
(一)为诗歌创作年代的考证提供依据
诗歌创作年代的考证一直是文学史上经典的话题。一般来说,判断一部作品的生成年代,有“内证法”和“体证法”两类。所谓“内证法”即“结合地下地上诸多材料”,在“诗歌的本文中寻找内证”[18]。“三重证据法”属于广义上的“内证法”。因为以往“内证法”所使用的“地上地下诸多材料”是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法”的材料范围包括且不限于文献,更重要的还有图像、实物在内的考古资料的参与。利用考古成果比证诗歌中写到的名物,同样也能为诗歌创作的年代提供依据。
沈从文最先开始尝试用“三重证据法”为诗歌断代。《木兰辞》一诗,有人说是北朝作品、有人说是唐朝作品。沈从文从考古材料出发探究诗歌创作年代的名物制度。北朝俑中有马、无骆驼,敦煌麦积山绘制的壁画图像里也证明北朝没有骆驼形象。而在唐朝,现代考古挖掘的唐墓里出土了大量骆驼形象,由此可见,出现“明驼”这一名物的《木兰辞》更有可能为唐人所作。图像、实物资料可以勾勒出成诗年代的物质背景,在此视域中观看诗中描写到的名物形象,大致能在两相契合处判断出成诗的年代。扬之水对此也有应用。《小雅·鼓钟》的创作年代,郑玄有“昭王时,《鼓钟》之诗所为作”之语,但历代对于成于昭王的说法缺少相关的佐证。这是因为西周前期的文献资料十分稀少,涉及到昭王事的论述更是含糊不清。扬之水通过出土的两周彝器,在彝器镌刻的铭文中发现数十篇涉及昭王南征的记录。这印证了昭王南征荆楚且命丧黄泉的传说。由此,联系诗中反复出现的“淮水汤汤”“淮有三洲”语,可见此诗是为悼念征伐出师而命陨三洲的将领,这便与成诗年代的背景相契合,完成了诗作于昭王时代的论证。
(二)赋予诗中名物以形象
诗歌借助于文字表现意境,这就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想象等高级思维活动来领会诗句中所表达的情境。扬之水的“名物新证”借助出土文物的形象资料,在文本形态上直接以历史图像呈现诗歌中描绘的情境。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体例不仅还原了诗中的场景,还更好地帮助了读者理解诗意。
例如,《豳风·七月》是一首描绘劳动人民一年四季农事生活的诗歌。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借助战国曾侯乙墓漆箱和西汉壁画上星象图中的大火星,让读者视觉感受到“七月流火”的时序变换;为了让读者深刻了解诗中“爰求柔桑”“以伐远扬”的场景,扬之水借用战国铜器纹饰中的采桑图来做荆桑、鲁桑的形象图解;为了让读者深入了解“八月绩麻”的过程,扬之水又图示讲解了考古出土的纺轮。这些图证是《诗经名物新证》的典型特色。文图并示的体例赋予诗歌以切实可见的形象性,延展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三)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真实地理解诗意
扬之水曾计划以李清照的生活为切入点,做《临安士人的一天,南宋日常生活二十三事》来展现真实的宋代世人生活。这个题目虽然没做成,她的“名物新证”却部分地实现了这个想法。张定浩评价其“名物新证”:“借助于名物研究,复原‘不复存在的语境’”[19]。比如《两宋之煎茶》一文,借茶物的考证还原两宋文人风雅的茶事景观。有学者言,“《新证》图文并貌,为我们打开了远古时代一个形象的、有声有色的世界,让我们走进了古代诗人的生活”[20]。
古典时代,诗中的名与物都一一相对。时间的磨损,致使词语与词语之间不断地融合、淘汰,幸存的词语又不断地衍生新义,这样一来,一类词语便脱离日常生活,变成某个历史时期的古奥记忆;另一类词语在长久的颠沛中,意义发生了多样的变化。因此,扬之水“名物新证”通过相关历史时期的图像、实物资料,拼接物的本来状况,再将物与名对应,便能破译词的本义,同时也能避免望文生义、以今解古的问题。相关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宋代毛滂《蝶恋花》有句“春愁春媚生颦笑,琼玉胸前金凤小”。有学人以为“金凤”指的是歌伎抹胸上绣着的金凤图案。扬之水通过考察大量的图像和琵琶实物,了解到古代琵琶捍拨上会绘饰山水、禽兽、人物等图像,因此诗中的“金凤”实为歌女当胸弹奏的琵琶捍拨上绘制的金凤图案。扬之水在这部分的研究实绩最为学人瞩目。
四、扬之水“名物新证”的理论贡献
沈从文提出并提倡实物、图像、文献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他的言说重心在于强调“三重证据法”应用的可能性、重要性和必要性,至于方法导向的理论范畴,沈从文言之不多。扬之水的“名物新证”在沈从文“三重证据法”导向的研究范畴里,有着自己的理论规定。扬之水以“定名与相知”的概念为“三重证据法”预设导向的研究目标,这弥合了沈从文关于此方面不及言说的缺憾。何谓“定名与相知”,扬之水有着一套清晰的理论创构。定名是研究的第一步,指“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21],即解决物之名的问题。古器物学持“物”找名、古名物学持“名”找物,实际上都是属于“定名”范畴。在“定名”之上便是“相知”。“相知”是指,“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实现名与物的还原”[21]。这里包含两个部分,第一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21],第二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21]。“物”的生命历程有两个阶段,最开始作为原初物,表现服务于人的功用目的和赏心悦目的审美目的;然后,“物”进入历史阶段成为“文物”,“相知”在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便是“文物”之“文”的问题。扬之水说,“‘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22]。概而言之,“定名”复活文物,“相知”复原文物,对文物所属的古典空间中礼仪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诗意文化的揭示与还原是“相知”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传统名物学是“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之学问”[23],“定名”是名物学赖以独立的根本任务。但传统名物学研究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所涉材料几乎围绕传世文献展开,这就难以避免历史变迁中“名”“物”分离的现象对名物学研究制造的困难。譬如说,后人讨论古代车制常举《秦风·小戎》篇为例,但古车制不存于世久矣,《小戎》篇对此的笔墨又节省到无一字可以增减,所以后人弄出了许多文字的纠葛,始终触碰不到问题的实质。“三重证据法”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有效逾越了这份障碍。例如,《小戎》有言“阴靷鋈续”,历来注释都不得要领,而扬之水通过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战马,物、文比对,始知“阴靷鋈续”是为先秦古车特有的系驾方式,而在了解这一点后,才能发觉《小戎》选取阴靷鋈续这最为关键的部件来表现这种系驾方式的语言精妙。因而,区别于传统名物学的研究方法,“三重证据法”因引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与成果而将“名物新证”带入了现代意义。现代名物学研究,“定名”还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目标,但在“定名”之上,新的方法论还应设定与之相符的、新的研究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扬之水提出“相知”的概念,可见是一种理论的更新与完善,及时为现代名物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与理论指向。“定名与相知”的提出,意味着方法与目标在理论上的统一,扬之水由此完成了她“名物新证”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