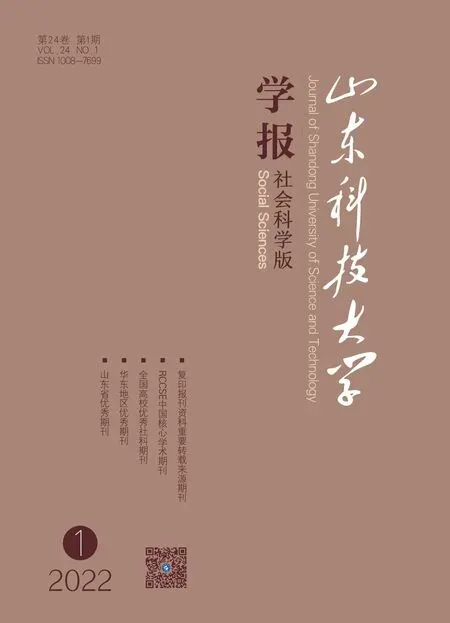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技术观视域下人的异化问题
——从“常人”到“千篇一律”
2022-11-26陆文斌陈发俊
陆文斌,陈发俊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人类在经历新型冠状病毒考验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的深度融合,进而使得社会朝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学习到工作再到家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离不开智能科技的支撑,对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需求正在极度增长。与此同时,这些智能设施也促使人对其产生了越来越高的依赖性,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诱惑性急剧地增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类更容易遗忘自身,更加无意识地成为“普通人”。所谓的“普通人”,并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是生存于同一世界中所有人的平均状态,即海德格尔所指的此在的“常人”状态。人们在“常人”的遮蔽中,日渐消散了自身的个别性,并伴随技术的深入发展而显得更加的平庸,甚至沦落为“千篇一律”的模样。然而,不论是“常人”,还是“千篇一律”,在本质上都是此在在其生存的过程中被世界所同化,背弃了本真生存状态,陷入了一种人之异化状态。对人之异化的思考最早可见于海德格尔1922年的《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现象学的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他就曾指出此在的实际生活具有如此之特性——毁灭,即“实际生活在其本身中、作为其自己、为了其自身、从其自身出发,在所有面对其本身的东西中‘践行’运动性”。[1]这种运动性所内具的引诱、安定、异化、根除为自身的沉沦营造着可能。《存在与时间》对人之异化的洞察显得更为深刻,海德格尔立足于西方的本体论视角,将形而上学视为人与自身的存在以及世界的扭曲联系的原因。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存在的哲学误解的历史,而不是虚假意识的理论。然而,他在存在论视域下为追求本体论的“深化”,却忽视“在世”的历史和社会决定因素,以至于并未发现人之常人化的真正原因。[2]虽然常人是一种人之异化状态,但是以此视角来审视人的现代化所引起的人的空心化、栖居源始性的沦丧等一系列问题,亦不失是一个破除人之现代性困境的良好路向。[3]面对当今人类社会因技术的泛滥所流行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海德格尔从“实验”“集置”“泰然任之”等概念所阐发的“技术命运论”,可视为对其强有力的反驳。[4]然而,此在如何从古代技术时代下的“常人”演变为现代技术统治下的“千篇一律”的原因还值得进一步深究。本文将立足于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常人”沉沦至“千篇一律”的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并为疫情时代下的人们如何摆脱异化状态,追求独特的本真生活,提供些许的思维指向。
一、“常人”“千篇一律”:此在对本真生存的背弃
德语中的“异化”(Entfremdung)一词,从其根源上来说源于希腊语“alienatio”,象征着事物之间的分离、疏远以及陌生化。黑格尔将其提升为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用以阐释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则将它延伸为一种主体所产生的并同主体相脱离的对象物,且这种对象物反过来束缚和支配主体。[5]马克思则更多地用它来描述资本介入下劳动本身对劳动者的压迫。在海德格尔的视阈中,“异化”是一种“此在”在生存论层面上由于受到技术的影响而产生的对自我本真生存的背离,主要体现为古代技术时期的“常人”和现代技术统治下的人的“千篇一律”。
(一)古代技术时期的“常人”
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技术的探讨还没有成为一个专题,但已经初显海德格尔对技术之本质的关注。这主要体现为他对“用具”(Zeug)的思索,在海德格尔看来,用具从不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存在物,其内涵必须依其所在的整体才能得到清楚的阐释,亦即“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6]80例如,如果我们要廓清“打印机”这一概念,就必须从由电脑、鼠标、键盘、鼠标垫、打印机、纸张、油墨、桌子、灯、窗、门、房间所构成的“印刷工具”整体来理解它。从本质上来说,打印机是一种为了作打印之用的东西,并且只有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它是什么才能得到不断的显现。换言之,海德格尔并不否认用具是一种实现人某种目的的东西,亦即用具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符合人类学对技术的定义。(1)在人类学或者工具论的视角下,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人的行为。这种观点更多地还是将技术视为人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或行为。然而,海德格尔对用具的思考也透露出一种人类学的技术论色彩。首先是技术将被视为一种为了作……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本质作进一步的深思。然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人类学的技术概念为跳板,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在他看来,对技术的思考应当减少对其物性的瞠目凝视,更多地在其使用过程中感知其特性、体察它所是的东西。以锤子为例,“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6]81易而言之,这种在操劳活动中不断涌上前来照面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称其为用具。然而,用具在存在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合用性,让其所伴随的何所用也一同来照面。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合用性就是用具所呈现的“为了作……的东西”。这种“为了作”的结构包含着某种东西指向另外一种东西的可能,用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便能指引出整个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主体世界)”,[7]而这个世界就是此在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换言之,用具在此在的操劳活动中,不断地揭示出此在寓于其中的世界。
作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简称“在世”)的此在,人既是一种“能在”,也是一种“共在”。这里的“能在”是指此在在生存论上所能领悟的关于自身生存的全部可能性。亦可理解为,此在的“主体性质”正是从自身的能在中不断得到规定,即他是他所从事的东西。从事某种东西,就是在与某种东西打交道。例如,从事粮食生产就是在与土地、天空、农具、农夫等打交道。此在的在世生存就是分别以Sorge(烦、牵挂、操心)、Besorgen(烦忙、牵念、操劳)、Fürsorge(烦神、牵心、操持)的方式,与此在的存在(本性)、存在者以及此在自身打交道。并在与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分有被抛入的世界。故而,此在的存在也是一种“共在”。然而,作为共在的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为与他人的差别而操心,即使他知道这种操心会让自己与他人的共处扰攘不宁。从生存论上来看,这种操心使得此在容易处于一种盲目跟随的状态,让他人趁其不备接管其自身,进而被平庸化为“常人”。在“常人”的掩盖之下,此在心安理得地生存于他人之列,遗忘作为个别化的“我”。从存在论上来说,“他人”在本质上就是共在世界中人的一种平均化状态,即“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6]147他就如同一件被熨烫后的衣服,在诸多此在的共同攫获下,消散了本质性的操劳,庸庸碌碌地生存着。
在日常的生活中,此在首先以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沉沦。这里所说的“沉沦”不是一种宗教学或者伦理学意义上的沉沦,不带有任何消极的评价,而是此在以闲言、好奇、两可的方式寓于世界当中。换言之,沉沦就是此在以闲言、好奇和两可的方式使自身的个性以及独特性消散于与他者共处的世界之中。“此在首先总是已从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6]204在海德格尔看来,沉沦既是此在非本真的存在方式,也是此在最为贴近的一种方式,并且此在通常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生存。著名学者陈嘉映就曾指出:“沉沦本质地属于此在,是此在不立足于自己本身而以众人的身份存在。失本离真,故称之为‘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8]沉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存在方式,让人不再从本真的自我角度来生存,而是让此在在与世内的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迷失于常人,亦即人在生存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与此同时,人的异化程度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加深,逐渐沦为现代技术统治下的“千篇一律”。
(二)现代技术统治下的“千篇一律”

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数学和物理学基础之上的精确科学的集置(das Ge-stell)。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设置的延伸,它在其追问的真理领域内开启了对正确性的谋制,任何存在于该领域内的存在者都成为了一个充满确定性的实在。[14]152-153“新时代科学放弃了事物本身,以便把它们整理成对象化的和算出来的东西以适合技术的操纵和统治。”[10]196例如,一棵开花的树,它伴随电锯的轰鸣和科研人员的来回奔走,逐渐地成为由一串抽象数字组成的有着因果关系的科学知识。然而,随着诸如此类的科学知识的不断积聚,人的思维模式也逐渐齐一化为追求可计算性和精确性的机械力学图景。并且,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谋制性日益增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区分也在逐渐缩小。[14]162自然和社会都成为机械力学图式支配的对象,事物的物性始终被人所遗忘。一切的事物都只是从与人的对峙中获得自己已经被订置的状态。莱茵河被订造为水压的提供者,空气被订造为氮料的提供者,土地被订造为矿石的提供者。人仿佛在表面上操控一切,但在实际上人也属于被订造的行列。“有关人力资源、某家医院的病人资源这样的说法就表示这个意思。”[15]在现代技术的促逼之中,人失去了自身禀有的多种可能性,被不同的目的预订成为可供驱使的持存物。以高校里的教师为例:老师在学校里教授学生知识和撰写学术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与其先辈在大学里从事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他们已经为学校所订造着。教师已经被订造到职业的待遇中去了,职业的待遇为学校的一系列要求所促逼着,学校则被递交给国家和社会安排着。在现代技术时代下的教师不论是否意识到自身已被卷入“促逼”和“订造”的解蔽方式之中,他们都已经受到了促逼和订造。同时,他也促逼和订造着世内的其他存在者。“促逼着的集置取消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人作为命运被限制在架构之中,失去了本真和自由。”[16]亦即,这种充斥着限定性和强求性的解蔽方式使人呈现为某种固定含义的持存物,消除了其本身所敞开的其他一切可能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千篇一律的甚至是冷淡的。技术的强力使人会无意志地听任作为与事物和世界的惟一的关系的机械力学图式。[10]190人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不断地受到戕害,缺乏对自己行动的审视。同时,它也使人的精神生活变成了只是对“流行文化”的刺激反应。并且,在“流行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冲击中,人精神的神圣感、世界的神秘感、生活的意义感被不断地刨除,进而造成人自身的意义缺失。人在现代技术统治下异化成无沉思性的千篇一律的持存物。
二、“常人”何以转变为“千篇一律”
在海德格尔的视阈中,不论此在是处在“常人”状态,还是处在“千篇一律”状态,本质上都是人脱离本真生活样式的异化状态,只不过技术在不同时代所引起的人之异化有所不同。在古代技术时期,人的异化体现为“此在”沉沦为“常人”。“此在”以一种“常人”的生活状态来生存,遗忘了自身的个别性和独特性。而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此在”被促逼成千篇一律的持存物,人和他者都在技术所引起的精确思维中被订置,世界和人都被压制成毫无褶皱的薄纸,人的异化状态呈现为一个持续加深的过程。那为何此在会从“常人”转变至“千篇一律”的可持存物呢?
(一)思维模式的精确化

(二)哲学沉思的边缘化
科学的强力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哲学的沉思逐渐地消退,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自16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所展现出的“强力”就似乎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并随着人的广泛使用而逐渐地覆盖了整个地球。[19]51-52这里所说的“强力”并不是指什么强大神秘的力量,而是一种在精确科学思维的指引下以数学和物理学的方式对事物的确定,它使现实成为人的表象。科学和技术所展现的强大威力也不得不使人们直呼“上帝已死”。当今的科学虽已极大地区别于中世纪以及古代的科学,但从根源上来说,它们的本质依旧同源于自柏拉图以降的那种思想——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哲学更多是被当作一种知识的汇总,它不仅需要思想具体的事物,也需要研究事物背后更具一般性的存在。然而,当一事物可被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之后,它便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地位,开始形成专门的学科来整理该事物,使其成为一种关于现实的专门的理论。于是,科学便从哲学的母腹中成长起来,并日益同其相脱离。然而,科学和哲学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在场者的自行展现,但近代科学所追求的由因果律决定的知识同古希腊人在现实中经验到的知识恰恰相反。科学在今天已经日渐远离其本质的含义,成为一种对现实具有极强干预性的整理和制造。并且,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诸如自然、人类、历史、语言等在场者都已转变为一种可测量者。作为大写的人类之学,哲学所能沉思的对象更多则集中于科学之后的那些难题,悬挂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上,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从整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内容。当代科学的蓬勃发展及其实践化导向,使人们广泛地认为“思辨”的哲学是“无用且渺小”的,只有“精确”的科学是“实用且伟大”的。哲学被迫走上了一条消退之路。“实用且伟大”的科学日渐遮蔽了“无用且渺小”的哲学,使人遗忘了它真正充满力量的东西——对现实的沉思。无沉思的人们无意志地听从科学——作为事物与世界唯一的关系——的命令,摆置着世界,也摆置着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可怕的东西并非世界成为完全技术的世界。更可怕得多的是人对这世界的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不能够沉思地达到适当地探讨在这个时代真正上升起来的东西。”[10]189人们不知疲倦地探求事物的原因与结果、必然和偶然,力图透过事物的现象迷雾寻找到事物自身的规律。每当人们追逐存在者所存在的充足律时,就已经迷失于科学所带来的不断后退的“为什么”之中,放弃了一种哲学的沉思性思想——其本身就是理由的“因为”。[10]192沉思性思想的放弃也就意味着人丢失了驻足审视自身的时间和唤醒自己独特个性的机会。人总是操劳着并为外在的异己力量消磨着自身的心灵和肉体。于是,人更加乐于以常人方式来展开自身的生存,为自己寻找到一种在家之感,进而掩盖内心的空洞。
(三)意义世界的贫困化
人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神性”被技术消散,人的思想被技术遣至“无所可思”的境遇中。在前期的哲学沉思中,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异化问题并不是由技术直接造成的,而是人在由技术所指引出的共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所决定的。作为常人的此在,“在千篇一律的人群中感到安宁”。[20]这种虚假的“安宁感”反过来又不断地引诱着此在朝向非本真的生存方式生存。换言之,它可以使此在避免“个别化”所带来的孤独和无助的“不在家”之感。作为在家状态的常人,他是一种无处不在又无处所在的人的平均化状态。它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先行描绘出可能和被容许的东西,压抑着一切挤上前来的突出状态,将此在稳定在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但此时的常人所面对的世界却还是一个充满意蕴的世界。事物仍是世界——天、地、神灵以及有死者——的汇集地。人对事物的思索同样也处在一个多样的路向中。例如,对于一个中世纪的农民来说,“他知道土地、植物与动物本身都是由神创造的,并且得自于神;对他来说,生长过程还是一个秘密,是某种不可知不可制造的东西,而只能加以支持;他把他的收获品看作仁慈的上帝的礼物。”[10]19易而言之,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的思维对共存于同一世界中的事物还保留着更多的意义。然而,事物所具有的更多含义并不先于事物本身,只有事物本身具有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时,人才会给它贴上此种意义的标签。故而,处在古代技术时期的此在所面对的还是一个饱含意蕴的世界,其本身也能获得世界给予的多重意义,即他还身处“能有所思”的境遇之中。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本的“能有所思”境域也逐渐被褫夺,世界变成了“毫无褶皱”的持存物的堆积。在尼采看来,以往的人只是从作为强力意志化身的“上帝”那里经验到自身的本质。但自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人们逐渐地将存在者获得规定的强力意志收归自身,人取代了上帝,成为一切存在者的统治者。一切事物都从与人的对峙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成为必须随时到场的可持存物,世界成为了人可进行预设的被制造者总体。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现代科学也只是伴随技术之本质——以强求和限定的方式来会集事物的展现——的必然结果。[18]303世内的一切存在者都不可遏制地成为现代技术促逼下的进行制造时所需要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了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标的人的材料。”[18]303人们努力地在“无可所思”的世界中寻找自身的意义,利用技术的成果和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但这一切,只是更换了技术的使用形式,人依旧只是技术本质促逼下的无意义的僵死格式。人在将世界表象为自己的对象物时,就已经在技术的生产中将自己通往敞开者的道路完全封闭。技术作为提供者的本质也淹没在人类有意的自身贯彻中,变成纯粹的“订造”。人在技术的使用和制造中,将世界变得井然有序,将原本充满“等级”的世界压制得“千篇一律”。[18]309世界在现代技术的刨削下,失去了自身的多样性——神性消退、物性消失、人性消逝。人既陷入一种“无所可思”的状态,也转变为一种“无所可思”之物。
概而言之,此在以一种被抛的方式进入世界,在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用具的指引揭示出此在寓于其中的世界。虽然,此在生存于世界之中,首先展现为一种非本真的常人状态,但此在在此时所面临的世界却还是一个充满意蕴的世界,其本身也还拥有诸多的可能性。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将使事物得到规定的“权力意志”收归自身,让自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地处于一种崛起的状态。同时,人也在生存的过程中训练起一种精确的科学思维,进而人的哲学性沉思被迫走上被遗忘之路。此时的技术虽然依旧是主体实现自身意志的手段和工具,但此在已经无意识地被卷入毫无沉思可言的技术促逼之中,成为现代技术统治下的可供订造的高级材料。在现代技术的强求和限定之下,常人所处的“能有所思”时代被摧毁殆尽,逐渐陷入一种“无所可思”的境域。
三、疫情之下的“技术”和“常人”之思
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人类在面对神秘和多变的新冠病毒时,也不得不采用最原始的方法——隔离和封闭——来应对它。但抗疫的成功并不是仅仅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就可以,现代技术的应用也为本次抗疫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性支持。比如,健康码的运用使得复工复产变得更加精准、科学、有序。但在疫情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技术的强力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集中地显露。这或许会使人们心生畏惧,更加奔向“常人”的生活状态,使人的异化呈现为一种现代技术促逼下的“持存物”和人之生活状态平均化的“常人”的叠加状态。但这也为人们反思现代技术、摆脱常人的支配、追求本真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契机。
(一)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观照
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集置,以一种强求和限定的方式先行摆置着一切存料,使人在集置的集聚中放弃了对事物的沉思,被技术订置为单纯的可被替换的部件,其存在成为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如果人要寻得本真的存在方式,就必须看到技术的“限定性”和“强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拾具有思辨性的哲学沉思,进而达到对技术的辩证性思索。在疫情时代下,技术所具有的“限定性”“强制性”被不断地摆置到人的面前,使人不断地经验到技术对人的压迫。质言之,在疫情的催化下,现代技术统治下的人的异化状态被更直观地反映在头脑之中为人的意识所感觉。在唐·伊德(Don Ihde)看来,技术内在包含着一种准他者性(quasi-otherness),即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有着自身所需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这就使得人们在想“掌控”技术时,不得不将其视为一种“他者”。在人与技术的他者关系中,技术成为人认识世界所需借助的一种他者性存在,并逐渐成为一种焦点性的存在,世界则被日益地弱化为一种背景式的存在。然而,在疫情中,此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技术从人认识世界时所需借助的“他者”,转变为世界认同人所需借助的“他者”,即“健康码”成为世界认识“我”的一种他者性存在,并且成为一种认识的焦点,“我”被弱化为一种背景式存在。[21]如果“我”无法提供“我”的健康码,“我”就会被排除在一个以健康码为准入条件的社会共同体之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我”因为无法提供“我”的健康码,从而被迫无法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没有自驾工具,要想到达任何地方,就必须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步行。[22]易而言之,技术所具有的“他异性”暗含着一种技术对人进行压迫的可能性。作为技术使用者,人是一个现实的人,是身处于一定群体中的人。当某种技术的使用成为一种群体性要求后,技术就限定了人们在该群体之中的展现方式,如果该群体没有容许其他的展现方式存在,那么人就将被技术强制性地排除在该群体之外。在疫情的极端条件下,现代技术对人所具有的“他异性”“限定性”“强制性”被极大地强化,急剧地从日常的隐性状态演化为疫情条件下的显性状态,呈现在人类的面前。这为人们沉思现代技术之本质提供了契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19]28技术虽然孕育着危机,但其内部也生长着拯救者。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技术性的因素,也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而是以促逼的形式让人与存在交汇,进而将其解蔽为持存物。它在解蔽存在的过程中,放弃了对存在者的守护,只是根据技术的意志订置存在者。换言之,集置在提供者的意义上,以限定和强求的方式向人提供持存物的存在的未隐蔽状态。技术的强求和限定并不是世界唯一的展现方式,它们的出现也需要人的参与。而作为世界的参与者,人们在听命于技术的同时,也可能具备另一种思维——沉思的思维,以拯救技术、守护自然和保护自身。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虽然精确的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现实和自身的沉思也同样重要。只有当人类唤醒沉思的思想时,他才会在任何可能的机会那里,对精确科学思维支配下的异化进行充分思索,并为本真生活的复归以及世界多种可能性的生长准备新的基础。然而,沉思之思并无固定的标志和概念,它唯一的基础就是对具体现象的思索。换言之,它就是对日常中已经熟知的概念和观念加以追问,以便促使人们发现事物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真正涵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对技术进行沉思时,既要按照技术应有的样式肯定它,也必须具备下一种否定性的眼光来审视它,以避免它对人和世界的本质所造成的扭曲。海德格尔将这种态度称为“泰然任之”,[23]亦即人们既要放弃从技术看待物的视角,也要看到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疫情时代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融合使疫情的防控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为全国性的复工复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让人们看到了走出疫情阴霾的希望。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疫苗的研制和使用变得更具有多样性。例如,我国目前所使用的疫苗就有三种:腺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这些疫苗使人们可以更好地避免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给此在本真的生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紧密联结为我国经济的复苏以及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在在更高层次的生存境遇中追求本真的生存方式开辟了新的空间。概而言之,现代技术在给人类诸多限制的同时,也为人的本真生存构建起了更多的可能性空间。面对如此之境遇,人必须学会辩证地对待技术,沉思其内部真正升起的东西。唯有如此,人才能摆脱技术的支配,寻回世界的丰富意蕴,进而获得复归本真之生存的可能。
(二)对常人之支配的摆脱
虽然对于现代技术的反思为人们摆脱异化状态作出了准备,但人要想复归本真的生活状态,还必须克服另一大障碍——常人对此在的支配。常人作为人的一种平均化状态,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刨除了个体所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人沉浸于庸俗化了的共在世界之中。但从根本上来说,人还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即对共在世界之中每一具体现象进行沉思的能力,只是在常人的引诱下,人遗忘了这种能力。遗忘之所以会产生,海德格尔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在借助常人对死亡之本己的掩饰,不断地逃离人的个别化,进而放弃了对死亡的沉思,阻断了良知的呼唤,沉沦于人的异化状态。亦即,作为此在终结的必然性,死亡在此在与他者共在的过程中,因公众的闲言,逐渐地具有了两可的性质,成为了常人口中“人终有一死,但自己当下还没碰上”的偶然性的东西。在死亡的庸俗概念中,人们只是将死亡作为偶然性的事件来经验,忽略了其本己性。然而,疫情之下,死亡经验的大量涌现以及封闭状态的持续悬临使得人们沉思死亡、设想以何种样态来生存成为可能。质言之,直面死亡的可能大量到来,沉思的力量开始以被迫的方式呈现在手。人们或将在封闭所带来的孤独中直面死亡、领悟死亡,进而沉思地抵达死亡的本己,在良知的呼唤中摆脱人的异化状态。
首先,直面死亡的会集。“死亡”在生物学上可被概括为有机体的一种生命现象;在生存论上可被解释为此在向着终结而生存;在存在论上将被标识为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确知而不确定的能在。它是此在不再能在的可能性。在它悬临此在之际,此在与他者在共在世界中的关联都将被解除,他将抽离个体回到存在之中。并且,“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6]288虽然常人知道死亡是难以逃离的,但他并不本真地确信自己的“死”,而是将死亡推延给他者,推迟到“今后有一天”。然而,疫情下大量他者死亡经验的直接或间接呈现,使得此在从未如此之近地感受死亡的悬临。虽然这种死亡经验依然是外在的,但是他者死亡经验如同潮水般的冲击也必将会动摇此在心中已被庸俗化的死亡概念,加之封闭所带来的无聊感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孤独感,这些内在感受的不断会集或将促使此在直面死亡,进而沉思死亡,构想此后的生存可能和存在样态。换言之,大量他者死亡经验和孤独之感的会集为此在直面死亡、沉思其本真的生活状态,进而摆脱常人的支配、成为个别化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其次,对死亡的沉思。所谓对死亡的沉思,就是在直面死亡的基础上,去设想此后的生存方式以及死亡悬临之际的应对之策,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到死亡之中。注意,这里所说的先行到死亡中并不是让我们首先亡故自身,也不是让我们整日沉溺于终结的悲伤中,而是让我们向着“死亡的可能性境遇”去生存。在此境域中,我们将明白,死亡是人之存在的最后性生存环节,它使我们解除了与外在世界的一切联系,周围的事物都茫然消失,只剩下“无”;同时,我们也将明白死亡是我们必须独自承担且不可逃脱的生存环节,它具有强大的不确定性。此在在该境遇下所展开的生存便是其自身最本真的生活样态。在此在朝向“死亡”先行之际,其自身也就被暴露在自身中产生出来的持续威胁中。[6]305此在要是想脱离常人的支配,复归本真的生活状态,就必须维护这种威胁,以警醒自身。对这种自身涌现出来的威胁进行长期维持的状态,海德格尔称之为“畏”。在“畏”中,此在凝望着自身终结的可能性境遇,领会自身最本己的存在。然而,由于此境遇下浓重的孤独感让此在觉得难以忍受,故而他选择将向死而生的“畏”倒转成畏死的“怕”,进而将死亡当成一种事件来经验,并在他人的“死亡”中不断地刨除自身最本己的可能性,使自己安心于常人的生活。然而,疫情中大量他者的死亡经验和封闭之孤独的会集促使此在在一种“强制性”的个别化中沉思地抵达最本己的可能,进而为其从常人中唤回自身作出准备。质言之,此在要想复归本真的生活状态,还需在疫情塑造的个别化境遇中不断地沉思死亡以增强向死而生的意识,进而在良知的呼唤中摆脱人的异化状态。
最后,在良知的呼唤中增强向死而生的意识。“良知”是此在从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中寻找到自己的展开状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呼唤。然而,呼唤在本质上归结为话语的一种样式,它与现身、领会以及沉沦一同构成此在的基本建构,且在其中起到纽带作用。与话语相对应的是此在的倾听,此在之所以迷失于常人,是因为他所倾听到的只是常人的闲言,或对倾听到的本真自我充耳不闻。因此,此在要想找到本真的自我,必须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阻断常人的倾听,复归对自己本真的倾听,进而领悟本真的自我。“以这种方式呼唤着而令人有所领会的东西即是良知”。[6]311易而言之,良知作为呼唤的话语,它所包含的并不是熟知的日常内容,而是“无”,它所显示出的却是此在最本己的“罪责存在”。[6]309“有罪责”就暗含着一种“不”(Nicht)的意思,亦即,“(你)有罪责”就意味着“你不应该是常人”。“不”促使此在进入决心的状态,向着最本己的自身筹划,即此在在“不”的罪责中复归本真的生活状态。但常人所具有的安慰性是巨大的,尤其在现代技术的助推下,它可能使此在更加无意识地沉浸在常人的状态中。(2)根据CCSight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短视频行业日均活跃用户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18亿,日人均使用时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分钟。因此,此在要想维持自身的本真生活状态,就必须不断地增强向死而生的意识,即在日常的生活中要使精神的“我”经常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之中,进而使此在持续地处在一种个别化的状态之中。
疫情肆虐的2020年已经过去,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物技术快速融合下的现代医疗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科技对战胜疫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科技所展现的强大力量已将人类赶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技术成为延续人生命的必经途径。[24]疫情期间,健康码、接触者追踪平台、远程医疗等相关新兴科技的出现,有力地帮助人们控制疫情的发展态势。疫情过后,生鲜到家、远程教育、SaaS协同办公等科技产品的出现也在极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迅速地恢复到日常的生活状态之中。可以说,新冠病毒的出现加速了人类从自然文明体系向技术文明体系的转变。然而,在已经到来的技术化时代中,人逐渐从古代技术时代下的“常人”转变为现代技术统治下的“千篇一律”的高级材料,人对自我本真的遗忘变得更加严重。但疫情以一种极端的状态使人大量地经验到技术的他异性、限定性、强制性,以及他者的死亡经验,为人反思现代技术、摆脱常人的支配、追寻本真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契机。疫情时代下的人们要想摆脱自我的异化状态必须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直面死亡,看到它们中真正升起的东西。除此之外,人们还应不断地沉思导致自身异化的每一具体现象,在良知的呼唤中,不断地加强向死而生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