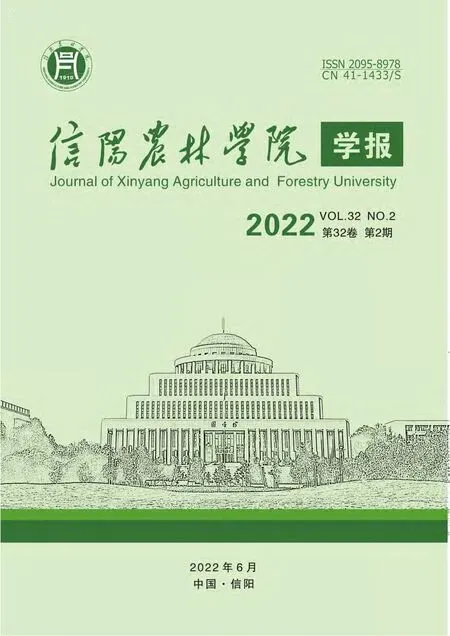自我建构与超越
——《别了,那道风景》中的多重空间叙事研究
2022-11-25沈慕蓉
沈慕蓉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1 引言
亚历克斯·米勒(Alexei Miller)是屡获澳洲文坛大奖的当代著名小说家,《别了,那道风景》(Landscape of Farewell)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位德国历史学教授在父辈大屠杀阴影中从迷失到探寻最终重构自我身份的故事。主人公马克斯·奥托(Max Otto)因其父曾参与纳粹暴行而始终生活在“共谋犯罪性内疚”与“逃避式沉默”的枷锁之下。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结识了土著学者维塔·麦克里兰(Vita McLelland)并被其说服搬至昆士兰州尼博山小镇,与维塔的叔父道佳尔德·戈纳帕(Dougald Gnapun)——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顾问同住。在倾听道佳尔德诉说的祖先戈纳帕故事并帮助他书写大屠杀的故事后,奥托逐渐正视暴力历史,走出逃避与怀疑的阴霾,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可以说,小说着眼于大屠杀、殖民等历史事件给不同族裔及后代带来的心理创伤和身份危机,不仅剖析了大屠杀产生和创伤代际传递的原因及后果,也探讨了主体的自我修复与建构历程,极具反思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出版以来,小说便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刘云秋高度赞扬内容的深度,评价米勒“微妙地鉴赏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个人的良知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1]。国外学者罗纳尔德·夏普(Ronald A.Sharp)认为文中的描写 “提供了一条穿越黑暗、忍受黑暗、不被黑暗击垮的道路,最终通向人类自我肯定的深层源泉”[2]。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分析与主旨解读,鲜少涉及米勒对空间的运用。空间叙述理论始于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他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创造性地提出“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3]。巴赫金也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形式》中强调“时空体”(chronotope)[4],认为空间和时间共同作用于文本的叙事。在《别了,那道风景》中,空间是作者阐释自己写作意图的典型媒介。大屠杀后代奥托长期以来囿于“不可言说”与“不可不说”的心灵枷锁,唯有通过静态的文字层面抒发苦痛,在空间上形成隔绝的状态。然而伴随着两位土著的介入,主人公现时与过往、自我与外部的对立状态逐步解构。奥托通过文本空间的历史重构完成与在场读者的思维交互,进而依托地域的多次位移达成人物意识与空间场所的互动式和解,这样的叙述赋予了作品独特的空间化效果。本文立足于空间叙事学,梳理《别了,那道风景》的空间线索以揭示作者利用心理空间的搭建来袒露大屠杀后代内心纠葛的处境,以文本空间的嵌套再现创伤语境与宣泄幽灵记忆,以地理空间的转换链接族裔和代际间的情感纽带,引导人物完成创伤的疗愈,进而解码小说如何借助文中的多重空间——内在心理空间、潜层内文本空间以及外部地理空间,展现主人公一步步超越自我、重构认同的过程。
2 心理空间:呈现迭代创伤
空间理论的兴起使文学研究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时间维度,而是转向文学的空间,即关注时间与空间、空间与空间等的交互,并解析文本内多层空间的特质与效用。心理空间是空间理论关注的要点之一,被认为是一种话语意识的建构与映现,吉尔斯·弗科尼尔(Gilles Fauconnier)将心理空间定义为“当我们思考和谈话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和行动之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概念包”[5]113,并揭示人们进行思考的过程“就是不断构建心理空间并对其进行语篇加工、处理及意义阐释的过程”[5]16。在《别了,那道风景》中,米勒塑造了主人公的心理空间并毫无保留地将其公示于读者面前,因而随着人物思维的映射和言语、行为的呈现,主人公的隐性创伤被全方位地展露出来。
小说选用第一人称视角,以人物的言语、意识流动和心理活动来建构兼暴露其隐蔽的内心世界,由此深入剖析了大屠杀给受害者带来的久远创伤。由于创伤给受害者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肉体、精神的双重折磨,它也成为了部分施暴者及其后代不愿触碰、甚至是不予承认的隐秘。而文本中内心空间的形成则有效地填补了这一叙述上的空缺。主人公马克斯·奥托是一位德国历史教授,童年时代的经历悉数与战争相关,暴力阴影给他造成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其实,奥托并未直接参与大屠杀行为,但因他的父亲曾服役于军队并参与纳粹大屠杀,所以明明身为史学教授,奥托却始终无法直面德国历史上惨无人道的暴行,并且刻意逃避事实。奥托的心中一直抱有强烈内疚感,认为自己是共谋的罪犯。“我们自己也许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同为人类的人群的大屠杀,而且凡是有一点理智的人都不会让孩子们对父辈的罪行负责。可是,我们自己和他们一样,同属那个参与大屠杀的人种,这就不能不使困扰我们一生的‘共谋犯罪’的想法听起来更加合理。”[6]19
此外,小说还借助人物的记忆回溯打破线性叙事,串联起过去与现在、父辈与后代,向读者展示了奥托是如何以及为何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始终恪守沉默的诺言。奥托的自我叙事经常无意识地闪回,其思绪基于回忆穿梭在不同的时间线上。例如奥托与土著学者维塔在酒馆进行交谈时,奥托的注意力先是聚焦说话人维塔的行为动作“摆弄着酒杯,脑袋向一侧歪着……”[6]27,随即意识突然停滞,陡然切换至自己面前干涸的酒杯,而后在混沌之际主观视角倏忽转向,开始刻画外界环境的喧闹“他们的笑声、叫喊声不绝于耳……节奏明快的音乐不停地播放着”[6]27。维塔的描写已经彻底退出奥托此时的内心空间。再随着思绪的逆回,由音乐的声浪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经历。此类的意识流动和时间回溯充斥于文本的心理空间内。当维塔询问奥托有关父亲的事情时,奥托的言语在此刻堵塞,肢体动作完全凝滞。但是,奥托的意识却不断流动,在心理空间中跳跃至过往,进而坦白自己的痛悔。奥托的内心饱受煎熬,几乎一生都活在怀疑的阴影之下。长辈的避而不谈让尚且年幼的他深知有些事情并不能被宣之于口。这种家族乃至族裔的禁忌话题逐渐变成子女难以启齿的痛苦源头,也导致了奥托记忆的“填补”——为减轻罪恶感而将父亲想象成一个忠于祖国的战士,但这并未让他获得精神解脱,反而导致其陷入了自我分裂的深渊。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的奥托已经无法分辨事情的本原,甚至在记忆模糊的基础上无意识地进行自我欺骗。在过去无法果敢地询问父亲的奥托,最终选择“心照不宣,对于这件事情始终保持沉默”[6]41。这里,不同的时间点由人物心理空间的囊括达成了同频。
用内心活动构筑实时的痛苦,用记忆的跳跃引出创伤的源头。通过心理空间的表现结构,文本叙事揭示了暴行的惨痛后果及创伤的闪回和延宕,袒露了大屠杀第二代的心路历程,也由此解释了后代缄默的缘由。奥托不仅是一个个体存在,他更像时代下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一个家族甚至一整代人“避而不谈”的普遍心理。但此类不能被提及的“禁区”却无时无刻不将经受者笼罩在阴影下。倘若创伤永远处于再现状态,那么,记忆覆写记忆,创伤叠加创伤,只会造成无限的恶性循环。治愈创伤的首要步骤是承认事实、直面创伤,而心理空间为奥托搭建了一个展现平台,使得整本小说变成一部饱含忏悔与苦痛的自白录。一方面,一些创伤者不愿表露心声,习惯逃避性沉默,选择闭口不谈相关事宜却饱受梦魇记忆的折磨。因此小说选择从人物内心视角切入,建构起属于其本身的心理空间,便能将无法诉说的痛苦自然地展现出来,而读者也可以明晰人物内心深处的想法。另一方面,因文本叙述视角的不同,读者所产生的阅读情感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第一视角的垄断与其它视角的消隐能够最大程度放大主人公奥托的心理阴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作为情感纳入方,也会参与到与小说主题相关联的心理空间中。当小说采用主观视角时,读者便更倾向于站在奥托的角度同情其遭遇,体验他的苦楚并与之产生共情。如此一来,心理空间叙述的意义达成了有效的输入和输出。
3 内文本空间:摹写创伤语境
就小说的文本空间而言,其关注作品的语言特色、视角结构和叙事时间线等,以及它们是如何共同作用以创造立体的、非线性的描述。而在《别了,那道风景中》,由于“我”视角的有限性,使得在一层文本空间中,立足于人物自我意识的创伤显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人公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向读者开放的。此时,作为一个单纯的文本叙述者,奥托依旧是一个封闭的个体,他的自我认同修复尚未体现出主动性。因此,米勒巧妙地采取了嵌套的文本结构,即在小说中构置了潜层的内文本空间以刻画人物填补自己的代际记忆,并通过书写的方式再现语境来倾诉创伤、努力界定自我的身份。
奥托在尼博山书写的有关大屠杀记忆的日记是小说的第一个内文本空间。多年以来,由于二战后德国盛行的集体大沉默原则,许多后代被迫背负着“遗忘的责任”,但纳粹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或“断续关联”影响并困扰着小说中的人物,造成其心理创伤和身份缺失。维塔提议的尼博山之行成为奥托最后的希望。在这里,奥托与原住民道佳尔德逐渐建立起友谊。二人虽然属于不同种族,但都是经历过屠杀创伤群体的后代,且无论是道佳尔德还是奥托,都在创伤记忆中体验了相似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即创伤在记忆断裂的基础上完成了代际呈递,而这种记忆缺失需要通过他人记忆的投射和自我想象力的投入来填补。在小说中,这种想象和创造是通过内文本空间实现的。为寻回自我,挣脱心灵的束缚,奥托主动选择通过书写日记的方式重构创伤语境以展演创伤。他在日记中反复提到一些长期困扰他的意象或记忆,如童年生活的经历、光怪陆离的梦境、舅舅农场里的窟窿和无助的吉普赛小女孩,等等。这些意向荒诞夸张,反映了创伤既真实又隐晦的特质。在他笔下的空间,奥托第一次基于自我的意识探寻创伤的根源,努力弥合记忆沟壑,这无疑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体现。
当暴力阴影很难被感同身受地理解或直言无隐地谈论时,它可以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被宣泄出来,而如何刻画后代自愿直面创伤、主动打破沉默则是文本叙事的一大重点。日记的文字空间是出于奥托个人意志的记忆书写,这种内文本空间提供了一种与隐性在场的读者进行交流的平台,是奥托逐渐从缄默转向倾诉的疗愈媒介。
小说的第二个内文本空间是奥托受道佳尔德之托而书写的土著祖先戈纳帕的故事,这个命名为《大屠杀》的故事记载着道佳尔德曾祖父戈纳帕屠杀白人殖民者的事件。较之奥托独立完成的日记文本,戈纳帕的故事创作除了融入自身想象还涉及到他人的经验与记忆,并且在奥托自愿的情况下向他人开放,所以奥托的意识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达成了外露与交互,可以说这是奥托心境变化的重要转折点。道佳尔德坦言自己无法写下曾祖父武士戈纳帕的故事,但“害怕的是历史真相被历史湮没”[6]141。因而希望奥托能够为他写下来。起初奥托十分犹豫,发现作为历史学家的自己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记录并不能写好故事。最终,奥托将自己对英雄戈纳帕的想象融入了道佳尔德的后记忆叙述中,以一种“亲身参与”的方式在内文本空间内写出了一个既属于道佳尔德,又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多洛里斯·赫雷罗(Dolores Herrero)认为“文学书写能够也必须参与创伤经验叙述,如果不能完全重复事件原貌,至少可以试图以一种疗愈性叙述把它们都说出来”[7]。从这个意义上看,戈纳帕的故事是成功的,它既带有历史的真切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又包含个人想象和描述的主观性,不仅帮助奥托完成个人身份的建构,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和精神与记忆的双重超越,“找到一种平静”[6]193,也让道佳尔德从奥托撰写的文字中释然,他对奥托“用低沉的声音,很严肃地说:‘你就像身临其境。’”[6]190通过个体创伤经验与历史创伤叙述的比对与融合,小说的描写揭示了大的历史语境离不开个体体验,而个人创伤经验也能够在创伤语境的重现中得以消解。
总而言之,大型创伤需要通过一种良性重复的纪念方式来解构其负面影响,而倾诉、书写等方式是感知与治愈创伤的有效形式。通过空间的转换和延伸,小说的内文本空间创造了一个嵌套的虚拟世界,以公开诉说的方式摹写创伤语境,书写幽灵创伤记忆,弥合了代际间与创伤经验之间的断裂和缺失,为奥托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和意愿投射的空间。道佳尔德终于了却心愿,与过去的自我和解,而奥托也有生以来第一次尽情抒写了埋藏在自己心里那种进退两难的心情,成功开解了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实现了创伤后代所追求的自我救赎。
4 地理空间:重构自我认同
在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不再囿于单纯的事件发生地,而是更进一步地帮助刻画小说的氛围、人物的心境以及主旨的表露。《别了,那道风景》里,地点与场景是一种空间的建构,也是记忆的承载介质之一,更是主人公重塑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小说章节分为四大板块,每个部分均以地点作为小标题,分别为“汉堡”“尼博山”“远征岭”和“斯克鲁特大街”。这几处地点与奥托成长或生活的经历以及自我认知的形成有着重要关联,不仅折射出地理空间内人物的生存境况,也反映了人物一步步走向外在流通空间的过程与倾向。随着地理空间的转换,奥托实现了由自我迷惘空间向自我重构空间的进阶,终于战胜了一直以来困扰他的梦魇,与自我、与他人、与历史达成了和解,重新建构起自我的身份认同。
就时间线而言,米勒采用顺序衔接手法使得地理空间的转变连贯化。从文本框架来看,米勒选取了并置和对比的叙事技巧表现地理空间的区别,以及人物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引发的意识差异,从而链接族裔与代际间的创伤记忆,赋予人物疗愈创伤的载体。故事初始于汉堡。作为奥托久居的生存空间,这里本应是一个让他充满归属感的地点,但奥托多年以来却承受着“关联性内疚”之苦,妻子的离世更是将奥托推向绝望的边缘,决意自杀。整个空间孤寂压抑,象征着禁锢着奥托身心的牢笼。同时,米勒借用奥托的记忆呈现了奥托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创伤空间——舅舅的农场。由于父亲上了前线,幼时的奥托被母亲丢至舅舅的农场生活。在奥托眼里,舅舅对土地有着疯狂的迷恋,但他怀着渴望的同时又非常厌恶土地纽带对他的束缚,其复杂矛盾的性格让奥托十分惶恐。当舅舅指责“父亲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6]93,且母亲对舅舅评论的回答避重就轻时,奥托不清楚父亲到底是“英勇作战的战士”还是“手沾鲜血的侩子手”,最终选择了缄默以对。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怀疑的痛苦只增无减。舅舅农场墙壁上的小窟窿是奥托创伤的典型表征。通过想象墙壁外可怕的战争,奥托企图外化自己心底的矛盾,种种畸形的幻像不断加重他的身份缺失,使其意识游离在分裂的临界点。在这个孤独的地理空间内,奥托被自己生活的土地放逐,成为了流亡者。可以看出,无论是少时生活的农场还是一直居住的公寓,奥托始终被囚系在一个压抑的地质空间。而自从搬来尼博山后,奥托逐渐适应新的地理空间,开始有所选择地触碰自己内心最深层的伤痛并勇敢暴露出来。对于尼博山的风景刻画,米勒给出了很多详细的直接描写:低矮的灰绿色灌木丛、不远处的海岸线和煤矿、沙砾公路、圆形小山、石棉水泥房等等。尼博山成为了奥托新的避难港湾,面对山山水水的宁静,他的心中突然涌出“一种充满期待的感觉”[6]62。终于,尼博山的地理空间拯救了奥托,让他完成了从创伤记忆之地到精神疗愈空间的跨越,收获了理解与认同。
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形成一条纽带,具有长久的延续性。倘若能把记忆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场景,或更进一步来说,当家庭、族裔历史与地理空间保持了固定的、长期的关联时,地点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即可以承袭祖先并触发与后代关联的“在场记忆”。这样一来,地理空间可以成为回忆的场域,创伤后代也能通过“重返故地”的方式有效地建立起与父辈、与历史间的联系。小说中,尼博山之旅改变了奥托的心境,而继维塔之后,道佳尔德再次作为“引导者”向奥托提议驱车前往他的家乡访问老戈纳帕,一个“想象中的、从青年时代后就没有再见过的理想之地”[6]194。道佳尔德强调,戈纳帕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这个故事在被保存下来后还应该永远地流传下去。文本再度置换地理空间,转向了“远征岭山崖”。经历了疲乏不堪的一天之后,二人终于找到了位于远征岭山崖之上的戈纳帕山洞,奥托将这面富于神性的石墙称为“古代神庙的废墟”[6]235。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远征岭一行对奥托和道佳尔德的身份塑造与认同重构有着重要的精神与实际意义。道佳尔德在代际之地与过去团聚。奥托也在目睹道佳尔德的精神朝圣后,终于理解纪念遗址维系族裔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的巨大影响及神圣意义。此处,基于小说地理空间的拓展与延伸,大屠杀的故事实现了文本范畴与历史范畴的完美交融,继而帮助奥托达成从想象层面向现实层面的升华。故事最后,奥托返回德国“斯克鲁特大街”,在家中时常怀念有关尼博山的一切。小说将地理空间切回最初的地点。空间首尾相连的循环设置更体现了人物内心的转变并映衬了创伤的疗愈,这使得文本“具有一种叙述性和述行性的进展的动感”[8]。奥托深刻地顿悟到自己已然重获新生,他下定决心探询原先的家族禁忌,将父亲经历的那场战争以文字撰写出来。至此,奥托从“心如死灰、完全被痛苦击垮的老人”[6]244蜕变为“值得相救的、充满活力的男人”[6]244,成功革新了自我认知,重构起自我的身份。
5 结语
《别了,那道风景》以个体创伤经历的展演与治愈为线索,叙说了后代在大屠杀阴影下寻回认同和重构身份的故事。透过对文本叙事的分析可以发现,米勒巧妙建构了多重空间以打破传统线性叙事,在故事进程中不再单纯依靠时空上的顺序连接,而是在保持情节衔接渐进性与流畅性的同时,采用偏重性的主观视角、回溯的叙事时间以及网状式的链接结构将创伤记忆分散在行文中,使得过往与现时不断交错、融合。小说运用心理空间的塑造来全方位展示大屠杀后代矛盾的处境,以文本空间的层叠来复刻原初语境并倾诉代际幽灵,通过地理空间的递进来填补身份认知的缺失,造就人物自我意识的重构与超越。这种多重空间的叙事模式不仅剖析了创伤的成因与表征,呈现了创伤弥合的历程,也将创伤记忆的负面影响转化为一种对历史和记忆的积极探索,为个人乃至种族和解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文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