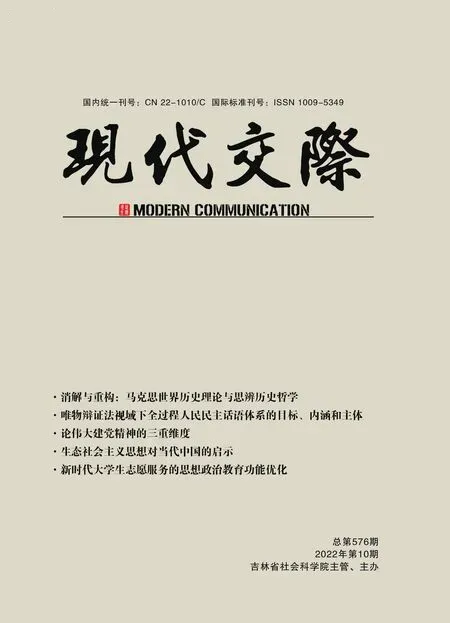论黄庭坚过境湖湘诗歌的独特价值
2022-11-25王友胜
□丁 畅 王友胜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湘潭 411201)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黄庭坚因在荆州作《荆南承天院记》,被赵挺之、陈举等以其塔记中“天下财力屈竭”等语句,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由此踏上人生中第二次谪贬旅途。对于黄庭坚政治人生与文学创作的研究,过去学界主要聚焦在到达贬地之后的诗歌创作,对其在过境湖湘写作的四十余首诗歌却鲜有深入研究。而纵观黄庭坚在湖湘所写的诗歌作品,其中既有对地域自然风景的描摹,亦有对人文景观的生动刻画;不仅有对故交挚友的酬唱赠答,亦有对贬谪心境的独特抒发。这些对人、情、物、景的多维刻画,是传播宋代湖湘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本文拟以此作为中心与重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以诗歌的生动擘画传播了鲜活的宋代湖湘文化
黄庭坚于崇宁二年十二月从鄂州启程,过洞庭湖后沿湘江南行至潭州长沙,继续循着湘江南行,由潭州而至衡州,由衡州向西进入永州地界。行至零陵,因天气炎热,酷暑难当,恐家人不能承受如此恶劣天气,只得将家眷留在零陵,只身溯湘江,先西行,再南行,经过全州、桂州,最终抵达他人生旅程的终点站——宜州。黄庭坚一路南行,他的过境、他的游历、他的心性情怀与湘山楚水摩挲激荡。在诗人笔下,湖湘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得以描绘,湖湘文化的人文景观得以呈现,并由此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1.传播了湖湘山川形胜的隽誉
黄庭坚的诗歌以其深微的艺术底蕴而使人体味无穷,同时也以其自然之美而使人流连徜徉。诗人通过游览胜地、寄情山水来转移贬谪痛苦,获得心灵慰藉。如黄庭坚在永州游览淡山岩后所写:“春蛙秋蝇不到耳,夏凉冬暖总宜人。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绿树仙家春。”[《题淡山岩二首(其一)》][1]1248诗中“春蛙秋蝇不到耳,夏凉冬暖总宜人”道出了淡山岩既免于春蛙秋蝇的叨唠,又拥有冬暖夏凉的温度。“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绿树仙家春”一句强调了淡山岩周围佛寺道观遍布、绿树成荫的环境特点,可谓游览观光之胜地。细细窥探,此时的诗人是把这里当作“隔尽俗子尘之地”,当作纾解愁绪、消磨痛苦的场所。在诗人笔下,淡山岩无论岩内岩外,其景色、温度都如此美丽宜人。又如《题淡山岩二首》其二诗中谓“石门竹径几时有,琼台瑶室至今疑。回中明洁坐十客,亦可呼乐醉舞衣”[1]1248,这里如仙境般美好,石门竹径、琼台瑶室,如此纯净圣洁、幽雅之境界能够涤荡一切尘凡俗虑。如此良辰美景,若能邀三五好友于此畅饮玩乐,应再合时宜不过了吧!诗的结句赞誉了永州淡山岩之稀有,使人心向往之。由于黄庭坚的名气,随后此处吸引了不少文人骚客探颐索隐、接踵而来。包括明代的张勉学、管大勋、王泮及清代的周崇傅等人,他们在此吟咏题刻、碑记无数,致使永州淡岩石刻的数量成为零陵之最。此外,“青玻瓈盆插千岑,湘江水清无古今”(《太平寺慈氏阁》)[1]1248、“嵌宝响笙磬,洞中出寒泉。同游三五客,拂石弄潺湲”(《游愚溪》)[1]125等诗句中,无论是“湘江水清”,还是“寒泉”“潺湲”,都是对湖湘山水清丽宜人的自然美景的书写。
黄庭坚于现实的挫折之中,能够把山水作为化解苦闷、孤寂、落寞、痛苦的载体。在贬谪的逆境之中,通过寄情山水的方式净化自己的内心,把山水作为抒发感情的载体,作为消除苦闷的媒介,从而得到心灵上的安顿,以此来消解、超越贬谪的痛苦。如《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其一)》:“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以轻松的笔调写出了诗人于贬谪期间难得一见的笑容,而这一笑也是在这山水之间所发出的。黄庭坚以山水来寄托情感,于饱览山水清音之中暂时获得心理上的放松,寻得精神上的慰藉。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当地的文化,为各处风光留下众多不朽的诗篇。
2.激活了浯溪独特的文化地标
黄庭坚在南贬宜州的途中,除了对湖湘地域自然风光的描绘,还有对人文风光的刻画。其中对浯溪独特文化的书写,影响最大的当属其《书摩崖碑后》一诗。磨崖之碑文,由元结所撰写,以言安史之乱中肃宗复京之事,全文由颜真卿书刻于浯溪畔的临江石崖之上,世人称为“中兴碑”。此后,元结文、真卿字、浯溪石作为“浯溪三绝”而享誉中外,“摩崖碑”亦由此成为当地颇具生命力的文化地标。黄庭坚南贬途径此地,见此碑刻,于是挥笔作长篇七古《书摩崖碑后》: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1]1246
这首作于黄庭坚晚年时期的作品,看似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却沉郁有余、有感而发。诗歌首言登临情景,感叹与《中兴碑》相见恨晚。次叙安史之乱的始末,对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给予高度概括,指出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因素在于唐明皇既不懂得如何治理江山,且亲近小人、远离贤臣。并认为唐明皇之所以悲剧终老,都是其自取其祸罢了。接着叙述了身为大臣的元结献计献策,杜甫见杜鹃屡次下拜。如此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贤臣,世人却看不到他们的刻骨忧伤,只见他们的华美辞藻。诗的煞尾,视角由历史转为现实,风格上平稳自然,恰与首四句遥相呼应,叙说同自己一起观览碑刻的有僧人及文士,而此时,天上的雨似乎也是想洗涤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全诗结构周密,精于格律,语迟意缓,遒劲老苍;夹叙夹议,并能洗尽铅华,归于平淡。
黄庭坚同好友接连三天徘徊在这摩崖石刻,“在黄庭坚《书摩崖碑后》的首倡推动下,同来文士和诗僧应该是有唱和的,可惜都已湮没无闻了”[2]。现如今,浯溪畔的摩崖石刻,以其独特价值而成为“湖南十大文化遗产”之一。如果说唐代文学家元结是赋予浯溪文化意义的第一人,那么宋人黄庭坚则为浯溪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间接动力。众多书法名家及诗人在这里留下工细的石刻、绝妙的诗文,创造了不朽奇迹、成就了千古奇观。
黄庭坚在其七言古诗中也有对寺庙的描绘,如《太平寺慈氏阁》:“青玻瓈盆插千岑,湘江水清无古今。何处拭目穷表里,太平飞阁暂登临。朝阳不闻皂盖下,愚溪但见古木阴。谁与洗涤怀古恨,坐有佳客非孤斟。”诗歌首先从视觉上描绘了湖湘山水清丽宜人的自然美景,极言湘江水之清澈无可匹敌;其次叙写了登临太平阁后的思想情愫;接着提及朝阳、愚溪两个永州的著名景点;最后从侧面表达出与友人曾纡同登太平阁的无限感慨。本诗一方面展现了诗人南贬途中豁达超然的心境,另一方面亦可从短短的诗句中窥探湖湘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胜景。
二、以诗歌的交游唱和丰硕了湖南文学遗产的宝库
唱和现象在宋代较为突出,“酬唱到了宋代,已经成为文人社会交往与交际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成为文人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活动”[3]。黄庭坚在湘期间,与其故交挚友、本土诗人、方外人士、著名歌妓交往密切。他们之间或题诗、或赠诗、或交游唱和,其间佳作连发,为湖湘文学和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题画赠诗:酿造诸多情意深长的诗篇
《古今事文类聚》记载:“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功者,以文鸣缙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其唱和。”[4]由此可知,李公寅与黄庭坚早在元祐年间便有交往。崇宁二年,山谷在赴贬途中,于长沙遇故友李公寅。黄庭坚十分赞赏其画,感叹不已,并为其所藏画作题诗多首。如:“髻重发根急,妆薄无意添。琴阮相与娱,听弦不观手。”(《题李亮功家周昉画美人琴阮图》)[1]1181诗人以仕女图为题咏对象,描绘画中美人薄施粉黛,正专心拨动着琴弦。整首诗并无富贵秾丽之气,字里行间透露出简淡落寂之意。李公寅除了收藏周昉的《美人琴阮图》外,还藏有戴嵩的牛图,黄庭坚观摩此画后,觉察画像与自己的处境、心事恰相契合,于是在《题李亮功戴嵩牛图》诗中写道:“韩生画肥马,立仗有辉光。戴老作瘦牛,平田千顷荒。觳觫告主人,实已尽筋力。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1]1182诗歌前半首运用对比的手法,“肥马”与“瘦牛”,“立仗”与“平田”,“有辉光”与“千顷荒”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相对照,诗人的心意也就无须赘述了。后半首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以老牛的凄苦情状、心中所愿来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慨和心愿。黄庭坚借戴嵩的《牛图》,表达自己历经政治风浪、仕宦生涯坎坷,只想远离是非、归隐田园的心态。
由前文知,随同黄庭坚游赏浯溪山水、观览中兴崖碑的除了文人名士,还有几名方外人士。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黄庭坚在衡州与僧人仲仁结识。仲仁以创作水墨梅花而著称,以浓墨挥洒成花,意境开阔。其独辟蹊径的墨梅艺术深得黄庭坚喜爱,因此结交为知己。黄庭坚欣赏其道行,钟爱其水墨画,为其水边梅题诗曰:“梅蕊触人意,冒寒开雪花。遥怜水风晚,片片点汀沙。”(《题花光为曾公卷作水边梅》)[1]1244诗歌描绘了水边之梅于严寒中傲然绽放,娇纤的梅蕊触动旁观者的心绪情怀。联想到顶风冒雪绽开的花瓣,待晚风吹过将片片散落在汀上之沙,心中不免惋惜。字里行间暗指诗人赴贬所途中孤独、凄苦的情状。此外,黄庭坚还与惠洪相互唱和。他欣赏惠洪的聪慧才智,写《赠惠洪》二首与《西江月》以赠之。黄庭坚深感于惠洪心性的旷达、超然,也以此心态来面对自己的贬谪逆境。
黄庭坚晚年在其《书赠花光仁老》中云:“余方此忧患,无以自娱,愿师为我作两枝见寄,令我时得展玩,洗去烦恼,幸甚。”[1]1265由此可见,黄庭坚主动请求仲仁为其作画,给处于忧患之中、心中郁结的自己以温慰。据文献知,仲仁身患疾病仍为其作画,而黄庭坚最后所收梅花图则是仲仁生命中最后的绝笔。其感情之真挚、情谊之深厚溢于言表。黄庭坚在经过衡阳时,与著名歌妓陈湘结识。陈湘钦慕黄庭坚精练的书法艺术,并以黄庭坚为师研习书法。黄庭坚与故交挚友的题画赠诗,以及与方外人士唱和赠酬、诗文往来创作的情谊深长的诗篇,为文学史留下了独特、闪光的一笔。
2.交游酬酢:推动湖湘文化的蓬勃焕发
沅湘文学的显盛崛起与文坛骄子的入湘、文学群体的感化,以及江西诗风的浸染密切相关。北宋时期,欧阳修、黄庭坚等著名诗人相继来湘。他们与湘籍文人士子交游唱和、酬唱往返,滋养了大批文人士子的诗词创作,产出了众多质量上乘的文学佳作,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蓬勃发展。
黄庭坚过境湖湘历时半载,其间他与湘籍士人多有接触,来往密切。沅湘文人知晓当朝诗坛泰斗来湘,不顾其贬逐身份,纷纷前往拜会。无论是与黄庭坚为同僚的诗人、书法家周寿,还是曾为其道院赠赋一首的江西道院的创办者柳平,或是被黄庭坚称为“国士”的著名经学家廖正一,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黄庭坚的浸润与影响。可以说,“他们是沅湘学士中接受黄庭坚影响最为直接且效果最为显著的几位”[5]。他以穷且益坚的人格风范、殚见洽闻的学识才学、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奠定了湖湘文坛浓郁学术氛围的基调,提升了湖湘学士诗歌创作的质量,客观上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蓬勃焕发。
黄庭坚以其卓越的诗学理论及独特的风格,成为宋代诗坛泰斗之一,其诗歌创作既汇聚宋诗的艺术特色,又凸显个人风格之奇崛。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在宋代显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诗尤其是南宋诗深受江西诗风的陶染与感化。基于这样的大气候、大背景,黄庭坚的入湘无疑会对湖湘文学产生重大影响。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浸润着湖湘的历史文化和人群,刺激了湖湘诗坛大放异彩,孕育催生了一批著名的诗人、词家。湘潭诗人王以宁、宁远诗人乐雷发及长沙诗人刘翰或隐或显都受到黄庭坚的影响,创作出风格独特的诗文集刊。如王以宁的《王周士词》及乐雷发的《雪肌丛稿》,细细品鉴他们的诗词创作,似乎能够觉察出其作品饱含着黄庭坚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对江西诗风的延续,是黄庭坚诗歌所具有的魅力与巨大吸引力,更是湖湘文学士子对诗歌价值追求探寻的充分体现。
三、以诗歌的思想外化浓缩了黄庭坚独特的贬谪心境
黄庭坚晚年南贬荒凉偏僻、距离遥远的南蛮之地,政治前途渺茫、人身失去自由,一身吊影、孑然难行。在面对打击迫害之时,人们往往会展现出迷茫无措、矛盾相向的心理状态。在赴宜州贬所的途中,黄庭坚大约写下四十首诗歌,这些诗歌既渗透着自己复杂矛盾的情感趋向,同时也寄寓着诗人对人生理想的美好向往。南贬宜州乃山谷最后的生命历程,其间虽有低沉叹息之音,但更多的是对贬谪苦难、得失荣辱的看淡,对人生命运的感慨以及卓然兀立、笑傲人世的超然旷达之情。
1.苦闷情愫:“豫愁帆风船,目极别所爱”
地域的荒僻萧索,贬谪生涯的困苦久长,诗人内心郁结着化解不开的压抑、苦闷。这种境遇除却加重了黄庭坚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感,牵绊其内心的还有好友离世的悲痛感。黄庭坚于崇宁二年十二月初从鄂州出发,其亲友纷纷赶到汉阳为其饯行。于年底至长沙,当时恰与秦观的儿子秦湛及其女婿范元实相遇,二人正护送秦观的灵柩北归。当年与友人同进同出的美好场景犹在眼前,如今亲眼目睹同门好友的灵柩,而自己又身在艰苦无望的贬谪路途,其心中的悲愁、压抑、苦闷之情可想而知。在此时期,诗人有《晚泊长沙示秦处度范元实用寄明略和父韵五首》,其诗中“逝者不可寻,犹喜二子在”及“豫愁帆风船,目极别所爱”[1]1180二句更是将诗人的无限悲愁、寂寞痛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此场景,对黄庭坚来说简直是肠欲断、心欲裂,悲痛之情亦无法掩饰。
黄庭坚在赴宜州之时,途经衡阳。当时其友孔毅甫在衡州做官,黄庭坚恰好在孔毅甫住处看到秦观所写的《千秋岁》,睹物思人,遂感慨万千,不免动容,便追和一首。相比之前黄庭坚面对困境超绝尘寰的思想性格,这首和词更多蕴含了对亡友的深切悼念之情。词曰:“飞骑轧,鸣珂碎。……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词的上阕主要回忆当年两人同朝为官的欢乐场景,“飞骑轧,鸣珂碎”一句,俨然能够看到他们意气相投、一同出游的场景。同进同出,对酒当歌的自在生活一去不复返,如今他与友人阴阳相隔,自身一贬再贬,依然在贬谪中奔波,心中的无限悲痛可想而知。词的下阕抒发诗人落寞孤寂的情怀,“人已去,词空在”的无限伤感,昔日的欢乐已不在。友人已去,谁能体会自己的哀苦之情?
政治道路之渺茫,环境之摧残,使诗人悲愁孤寂的情绪跃然纸上。尽管黄庭坚曾以“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过洞庭青草湖》)[1]1179的豁达胸襟、豪迈之气来自我安慰,实则落寞悲愁。如诗人途经衡州所作《离福岩》,诗中“不见祝融峰,还溯潇湘去”[1]1240一句暗含了诗人一路仕途坎坷、家中音信全无的无奈与怨愤。整首诗含蓄而不显露,全诗不着一字“景语”,却能于短短几句之中感受到衡山烟雾缥缈的胜景自在眼前,画面感极强,让人回味无穷,由此也可看出晚年的黄庭坚在诗歌艺术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2.超然旷达:“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
黄庭坚虽于长久的谪居生涯中表现出压抑、苦闷的思想情愫,但终究并未走上颓废一途。而应注意到的是,“在沉重忧患的压抑下,在被抛弃的境遇中,能否高扬主体意志,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新的抉择,直接关系到身处逆境的贬谪诗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走向”[6]。黄庭坚并没有选择在苦闷中消沉自己,而是对贬谪的苦难具有高度的超越意识。在诗歌中,他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对苦难的看淡,以及超越忧患的意识倾向。
在展现诗人频历艰难仍不屈不挠的作品中,以组诗《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最为精妙。这组诗是黄庭坚从四川戎州贬所回到内地,赴家乡分宁(今江西修水),途经岳阳时所作。第一首诗云“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1]1124,第二首诗云“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1]1124。前者表达了诗人遇赦归来的喜悦、欣慰之情,诗人在遭遇九死一生的艰苦磨难后仍能以豪爽的性情、乐观的心态展现放逐归来的欣喜之情。全诗意兴洒脱,短短字句间表现出诗人豁达洒脱的情怀和对故乡的期待欣幸之真情。后者写远眺洞庭湖所见,首句暗含隐语,看似写眼前的“满川风雨”,实则喻指诗人当时所处的恶劣的政治环境,然仍能以兴致勃勃的心境观赏这湖中美景,可见其倔强挺立的形象。其开阔之胸襟、心性之澄澈、豪迈之情怀,令人钦佩不已。
再赴播迁之路,黄庭坚在《过洞庭青草湖》中言“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1]1179。此句或隐或显都表露出恬淡超旷的意识倾向。诗人用较为乐观的心态来排遣内心忧虑,以期减弱贬谪带来的郁抑和愤懑。纵观诗人于湖湘所作诗歌,能够知晓赴贬所途中的黄庭坚在心态上更为平和与达观。他能够以戏谑的方式淡化悲苦、摆脱困顿,虽身处忧患却志节坚定,襟怀洒脱。如在永州所作《戏咏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驯鹧鸪二首》,这首诗以李宗古家的鹧鸪为戏咏对象,诗中“山雌之弟竹鸡兄,乍入雕笼便不惊”[1]1245巧妙地运用拟人的手法,写鹧鸪为山雌之弟、竹鸡之兄,虽进鸟笼却并不惊诧。而戏语则体现在后二句,因鹧鸪的鸣叫与人语“行不得哥哥”相似,所以才有“此鸟为公行不得”之句。整首诗以言说鹧鸪而打趣李宗古,将鹧鸪的特点表现得活灵活现、生动形象。又如:“涪翁投赠非世味,自许诗情合得尝。……老夫何有更横戈,奈此于思百战何。”(《戏答欧阳诚发奉议谢余送茶歌》)[1]1251黄庭坚作诗酬答欧阳诚发,诗歌首先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欧阳诚发的籍贯、形象及其才思敏捷等特点。次叙诗人自己与欧阳诚发以及苏轼三人之间的友情。最后写黄庭坚将好茶赠予欧阳诚发,描绘了茶之色泽、茶之香醇,从“官焙香”与“非世味”可知此茶为上乘好物。整首诗幽默诙谐、风趣有余,刻画了欧阳诚发的形象及才华,歌颂了三人真挚的友谊,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赞誉及颂扬。
黄庭坚暮年再度流放,虽承受孤寂处境,远离家乡之苦,饱经困扰磨难,却一路有唱有和、寄迹山水,足以体现诗人超越苦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其沉静内敛、超然豁达的心态,使其诗歌创作成为贬谪文学上最耐人涵泳的诗篇,也赋予黄庭坚在北宋士大夫的心理历程中超越忧患的典型意义。
四、结语
黄庭坚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及独特的诗学理论而稳坐宋代诗坛,备受研究者关注。黄庭坚在奔赴贬所途中历经多地,产出了反映不同地域、文化、人情、民俗的优秀诗词作品,其中过境湖湘所撰写的诗歌作品尤为引人驻足、品读和阐发。综观黄庭坚过境湖湘的诗歌作品,不论是以吟唱山水来寄托情感,还是以交游酬唱来广结友人,或是以戏谑方式来摆脱困顿,贯穿作品始终的是一条经受生命沉沦而卓然独立的基线,体现了诗人豁达洒脱的情怀、恬淡超旷的意识倾向。这些经典作品成为研究贬谪文化、湖湘文化及宋代文化的鲜活文字载体。
虽需思全局,但仍立一域。传统对黄庭坚诗词作品的研究方法多从其传奇跌宕的一生进行整体性描摹刻画,有粗略、泛化之嫌。而截取黄庭坚的人生片段来进行局部性精雕细琢,则有放大、细解其人生境遇之益。除了本文所截取的黄庭坚过境湖南,亦可选取其贬谪黔州、戎州等地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开展研究,实现以一域观全局,更细腻和通达地理解黄庭坚惨淡但澄澈的一生。黄庭坚是贬谪诗人的重要代表,也是受尽宋代政治打压的典型人物,与其持有相同境遇的诗人为数不少。因此,可以提炼黄庭坚贬谪诗歌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亦可考察其所处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贬谪诗歌的独特魅力,进而在百花齐放式的研究中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贬谪诗人和贬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