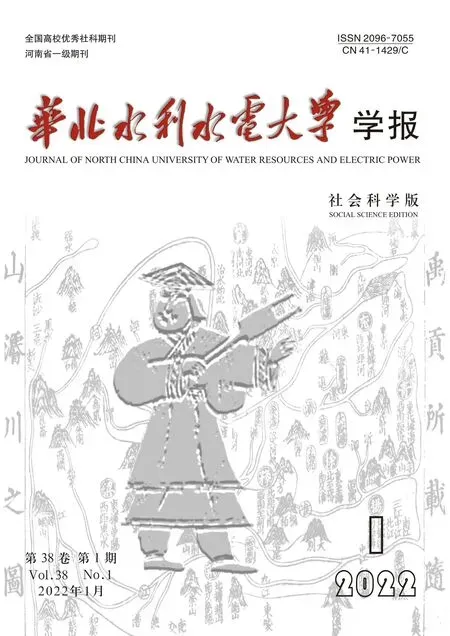沉浸式艺术:独特形式与新鲜体验
2022-11-24苗文宇卢焱
苗文宇, 卢焱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沉浸式艺术带来的体验是传统艺术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已经不再是欣赏者的幻想,而是可以实在地展现眼前。虽然目前学界对沉浸式艺术的研究多集中于新媒体传播相关或科技应用(如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部分文章中会涉及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但关于其美育价值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通过考察“沉浸”产生的背景以及对其美学特征的分析,思考这种方式之于审美教育的意义。
一、走向“沉浸”的道路——从欣赏方式到艺术形式
“沉浸”从词源来讲是有迹可循的。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有言:“沉浸醲郁,含英咀华。”[1]44即研学时应该心神沉浸,品味书中精华,“沉浸”在此已经涉及全神贯注的含义了。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艺术与美学语境中,在欣赏时进入沉浸状态是共同的追求,较之于单纯的静观默想,沉浸的欣赏方式更接近理想的审美体验。到了现代,各学科理论的完善与科技的发展,得以使它从欣赏方式演变为真实的艺术形式。
(一)一种理想的欣赏状态
在中国古典美学语境中对全神贯注的追求就是审美心胸的逐步建立,这是欣赏艺术的绝妙方式。老子认为,在观照万物时应做到“涤除玄鉴”,只有洗除内心的主观欲念,保持内心的虚静,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虽然审美心胸理论是由庄子的“心斋”“坐忘”所确立,但最早的源头还是老子。沉浸体验的目的就是使欣赏者完全融入作品之中,即使保持虚静的审美心胸,欣赏者的内心与作品之间仍存在着界限,因此仅达到全神贯注的境界还远远不够。在《姜斋诗话》中,清代哲学家王夫之认为,人们在审美感兴中可以实现情与景的统一。“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弈照耀,动人无际矣。”[2]752这不仅精妙地解释了审美意象的产生过程,也生动地描述了人们获得的丰富美感。朱光潜认为,艺术意象是超然于现实世界以外、纯粹而独立的,人在直觉中形成的意象即是进入了审美的境界,也是艺术的境界。他的意境观念在受到西方移情说与克罗齐的影响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本土化的语境改造,认为对诗与艺术的审美就在于情趣与意象的统一,而情景合一就是中国美学中的沉浸欣赏方式,如果王夫之与朱光潜的说法较难意会,那么卞之琳的一首诗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1)卞之琳(1910—2000),现当代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断章》创作于1935年10月,据作者自云,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有这四行使他满意,于是抽出来独立成章,标题由此而来。
在沉浸式欣赏中,欣赏者不再区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而与此同时,“你”作为欣赏者其实已经成为风景本身的一部分。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这种与对象相融的沉浸欣赏方式得到了更贴切的展现,人们行走在园林之中,就是进行审美欣赏之时,意境也随着“移步换景”逐渐清晰起来。这种欣赏方式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宗白华认为:“中国画的透视法是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完整的律动的大自然,他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3]110在西方艺术史的发展中,沉浸欣赏的方式也同样重要。19世纪德国作曲家瓦格纳通过“沉浸式歌剧”的实验将音乐、舞蹈、造型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这种整体观念的实践与综合艺术尝试的歌剧革命,其实就是要满足欣赏者的多种审美需求,与中国园林设计一样,各种元素的添加都是为了吸引欣赏者进入沉浸欣赏的状态。
(二)理论与科技的结合
确切的“沉浸”概念来自心理学,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研究时用“Flow experience”(心流或沉浸式体验)来描述高峰体验时的心理状态。他发现人们在工作时会偶尔进入到这种状态,以至于忘记其他事情,而只感觉到愉快,甚至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去完成当前沉浸的事情[4]4。在“心流体验”中,人们会忘记自己主体的存在,这与沉浸欣赏时的心理状态一致。由于人们醉心于这种最优体验,所以为了实现自由地进入沉浸欣赏的状态,就需要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做载体。
“沉浸”从欣赏方式到具体艺术形式的转变,得益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从欣赏方式到艺术形式的演变,直到今日才得以实现,虚拟现实技术(VR)的应用让艺术创作产生了新的方向,艺术与真实生活的关系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借助先进的手段来辅助沉浸体验的形成,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现象。多瑙河大学图像科学与文化研究系主任奥利弗·格雷乌(Oliver Grau)以一种史学的观点对“沉浸”进行考察,发现在每个时代,艺术家们都会尝试用各种手段或者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来辅助人在欣赏时进入沉浸状态,比如巴洛克时期流行的错觉空间,这种幻觉形式的历史流变对沉浸式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163。由最初的模仿现实到照相机、摄影的还原现实,再到如今的虚拟现实,艺术家们不断需求新的方式去突破传统创作技法的桎梏。除了VR,在沉浸式艺术实践中也有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技术的参与,以及5G与AI(人工智能)的普及,沉浸式艺术会有更多的可能。
先进技术的运用给予了艺术家更多的创作活力,也让受众的审美体验更加丰富。南京艺术学院王文文对沉浸式艺术做出如下定义:“‘沉浸式艺术’是一种应时代而生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它是随着媒介形态的愈发丰富,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更加走向模糊,人与媒介和环境相互融合,互为彼此之后产生的一种从物质到精神全方面参与的艺术体验方式和状态。沉浸式艺术借助着多媒介的融合,多艺术的跨界合作,将虚拟的人际关系实现了‘在场’体验,通过现场的接触,而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不再需要通过生硬的文字或者‘悬挂的日记’(指绘画)去了解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可以直接参与,沉浸其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完成各种关系的建立。”[6]22举例来说,以往的剧院、影院在如今演变成了360度全景剧场与MAX和IMAX3D影院,氛围的烘托和声光效应的共同作用,让观众在欣赏时可以专注于当前情境和作品的叙事内容。“沉浸”不仅打破了艺术文本之间的界限,也让艺术有了更多样的展现形式。2013年在纽约现代博物馆(MOMA)举办的《雨屋》展览作为沉浸式艺术实验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行走在“雨屋”中的人,身处“大雨”之中却不会被淋湿,这种违反自然常理的现象得益于科技与创意的结合。“雨屋”的设计团队运用了大量3D镜头来实时监测和定位游客们的运动信息,通过传感模拟和后台控制系统,给前来参观的人们带来了新奇难忘的审美体验,科技的辅助让实现“沉浸”变成可能。
二、“境”的实在显现与身心体验
感受到作品中的意境是审美体验的深层目的,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依靠想象力的作用将艺术作品带来的感官刺激与自身原本记忆相结合,从而在头脑中形成新的形象。可是,因为与作者所处时代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人们往往很难把握作者试图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境界。虽然有些艺术家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地创造天马行空的作品,但是如何让想象力突破这层“隔阂”,使欣赏者面对作品不再无动于衷,依然是艺术和美学的难题。此外,审美之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在人的内心形成,身与心的分离导致在审美活动中“身”总是被忽视,甚至被排斥在审美之外,而沉浸式艺术凭借新的媒介让身体回归于审美体验,呼应了当代身体美学的思潮。
(一)想象的具象化
2019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艺术家杨泳梁举办了自己的个人展《不朽之境》,在他的创作中,中国传统山水水墨画有了新的展现方式,观众们在欣赏画作时只需佩戴上VR眼镜便可轻松畅游在山水风光之间。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欣赏者若想进入审美之境,就需从最开始的审美感知开始,在由“象”到“审美意象”之间,想象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审美活动的发生在于审美心胸的建立,随后想象力才可介入并发挥作用,但是如今的审美难题已经不只是如何保持无利害的心境,而是从最开始的审美感知就出了问题。
现代人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之中,面对抽象的古典水墨画时很难在心中勾勒出审美意象,想象力在此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少人更容易对形象的西方古典油画感兴趣,而很难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感觉。传统文学作品、戏剧、音乐、电影等创造的世界,在宽泛意义上我们可将其视为虚拟现实或者虚构现实,这种“虚构”在传统艺术美学范畴中主要指发生在人的意识层面的创造性想象行为,其典型特征表现为非现实的与间接的想象中的现实世界同样可以分享虚拟现实的某些特质[7]。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杨泳梁的作品革新了“境”的形成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想象力的困境,人们在欣赏《不朽之境》时,不单能看到如仙境般的动态水墨风景和栖息在山林间的动物,还可以听见瀑布激流、昆虫鸣响与风的声音。这些本来依靠想象去补充的场景,现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帮助,使如梦如幻的意境直接显示在人们眼前。
艺术家的创作想象是使用“自在存在”的物质将意识中的想象“具象化”,受众的想象则是在获得物质近似物的信息后通过“自为意识”对信息进行转化,并通过想象“完形”信息内容[8]。沉浸式艺术试图将艺术家内心与受众审美心理连接在一起,以人与作品的交互为前提,通过引导其感官来营造意境。想象力发挥作用的时机已经不再是帮助审美意象的形成,在艺术家给欣赏者预设的审美之境中,想象力得以聚焦作品叙事本身,这样不仅减少对于作品理解的偏差,而且也能在创作者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更深刻的解读。对创作者意图的把握是正确理解作品的关键,想象力的不同使每个人的审美意象千差万别,因此才有“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可是对于不热衷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来说,哈姆雷特的意义就形同虚设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将作品创作出来了,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接下来是读者和听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再创作。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是艺术创作的继续。未被阅读的作品其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他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9]297。对作品的误读让文本的开放性失去意义,理解多元化的基础在于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的沟通和共鸣,“沉浸”使想象具象化,帮助作品更好地被人接受。尧斯认为艺术家与接受者都有各自的“期待视界”,沉浸式艺术可以被看作是“视界融合”的一种特殊情况,艺术文本被规定了接受和理解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接受者想象活动可以跨过形象的塑造,直达自由的审美境界。进入作品之后,受众再以自己的方式发挥想象,获得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审美体验。
(二)感官的合作和身体的回归
沉浸式艺术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多重感官的刺激,这在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各种技术的辅助下,人们的审美体验更接近艺术真实,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人们试图用一种假象去掩盖真实,在艺术世界中对真实感的诉求,为的是自我遗忘真实世界的心理状态,专注于艺术情境,从而满足内心的审美需求。埃塞克斯大学的罗斯玛丽·克里奇教授(Rosemary Klich)在研究沉浸式艺术时,就关注了耳机在沉浸式艺术中对于人们与作品相互感知程度的影响,她以听觉为研究起点,发现虚拟现实会带来“身体转移幻觉”。在文中,克里奇引用了利亚姆·贾维斯(Liam Jarvis)的观点,认为沉浸式虚拟现实的实践体验,会产生“本体感漂移”的现象,即用户融入了“他者”的身体意象,并将其作为自己身体图式的一部分来体验。[10]这种“本体感漂移”在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移情”理论,是一种带有身体维度的审美体验。在2017年米兰设计周上,日本建筑师村上梓与英国艺术家亚历山大·格罗夫斯(Alexander Groves)共同设计的“New Spring”装置吸引了大批游客的目光,这种具有工业化气息的高达6米的树状结构,会在树枝末端喷出白色的雾,雾气飘落时会团结成气泡,一旦接触到人的身体,气泡就会爆裂,散发出自然花木的芳香。虽然整个作品丝毫没有自然的元素,但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甚至触觉上的暗示,让观众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处在樱花林之中。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感官真实与认知理性发生了错乱,在这种奇妙的状态好似庄周梦蝶,欣赏者的心理和生理都达到了审美的境界。传统审美的观照和体验方式多是静观默想,这种接近纯精神性的审美是需要质疑的。美国学者杜威说:“感觉的性质之中,不仅包括视觉与听觉,而且包括触觉与味觉,都具有审美性质。”[11]139在沉浸式艺术中,人们感官上的动态体验与五感的合作抹除了作品与观众的距离,通过参与和互动,不仅解放了心灵也体会到了身体的自由。
身体作为感官的承载者,在中西美学中都被看作阻碍审美发生的惰性元素。“心”的优先性和高尚性与“身”的工具性形成鲜明对比,它们的对抗关系影响了艺术和美学的发展。身体的感知被认为是感性、初级且不具备可靠性和普遍性,并未真正进入美学及哲学研究范畴。直到尼采对形而上学的颠覆、福柯的解构直至梅洛庞蒂感知现象学对身体首要性的系统论证,身体在美学及审美经验的研究中才逐步重回人们的视野[12]。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论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13]引发了美学界对审美中人自身身体的关注,他用“Soma”来代替“Body”,认为人的身体是充满感知力和活力的,并不单纯是血肉以及骨骼组织的混合,身体需要的不只是营养和锻炼,排斥身体的美感体验是有悖常理的。现代艺术对身心俱愉的追求是对传统身心二元对立的重构,人们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的高度参与让身体回归了审美活动,利用现代科技协助身体“在场”,用各种手段还原人最本真的知觉感受。舒斯特曼也倡导人们通过训练增强身体的感知力,这种实践的观点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如今现代生活的紧凑节奏压缩了生活空间,让我们的身体无比疲惫,科技发展加速了身体的异化,身体上的各项功能开始逐渐被工具代替,若不对身体进行及时唤醒,不仅是审美敏感度的弱化,更可能会影响人的生命健康。沉浸式艺术带来的全新审美体验回应了身体的需求,促使当代艺术向身体美学的转向,也促使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从科学的、理性地向审美的转变。
三、“沉浸”或“淹没”的美育之思
20世纪英国心理学美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在研究审美心理时提出了“心理距离”说,他认为审美的关键在于对主体对客体心理距离的把握,太近或太远都无法使人达到审美的状态。相同的道理在审美教育中也适用,若过于贪图沉浸式艺术在感官体验上的满足就会沉迷其中,若刻意且僵硬地在艺术文本中添加教条道理,则会引起欣赏者的排斥心理。合理利用艺术性与娱乐性兼备的沉浸式体验,不仅为审美教育拓宽了道路,同时也践行了贺拉斯所倡导的“寓教于乐”理想。
(一)价值:接受、创造与情感
从接受角度看,要对传统艺术进行审美感知,就要求主体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及审美鉴赏能力,我们已经通过上文的分析得知审美之境的显现让沉浸式艺术更易被受众欣赏,所以借助“沉浸”手段对于审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博物馆游客的审美心理进行探析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具有专业素养的人之外,大部分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观的,特别是青少年本身审美鉴赏能力较成年人来说就略有不足,这些对他们来说枯燥的作品不仅无法产生教育意义,更会加重厌烦排斥的情绪。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对象,杜卫认为:“从艺术与审美的关系来说,艺术是审美的最集中和最典型形态,是人类审美文化的最主要载体。因此,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最佳途径。从儿童青少年美育的范围来看,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艺术教育应该是促进青少年审美发展的最理想途径。”[14]182因此在各种博物馆、美术馆和展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学校或家庭带孩子来参观,对于儿童或青年来说,沉浸式体验中的“趣味”元素是不可或缺的,艺术文本在新媒体中重新获得了活力,多重感官的享受让人得以自由体验,这与席勒的“游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引入游戏冲动来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矛盾,认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15]259“游戏”在这里就指审美活动,席勒试图将感性与理性在审美中统一,实现人性的完美。实际上并非青少年乐于这种游戏状态,人生的各个阶段对游戏都是敞开怀抱的,对于一些晦涩难懂的经典作品,人们如果无法接受,那么审美教育就无从谈起,沉浸式艺术改造了艺术文本的展现方式,经典的重新阐释为美育实践拓宽了道路。
从创造角度看,艺术家在创作沉浸式艺术时,可以更轻松地将自己的创作本意表达出来,同时也可以综合更多元的艺术形式,艺术文本的边界得以不断开放,创作的空间也更加广阔。在对经典的二次创作中,通过各种沉浸手段的应用,可以拉近文本与受众的距离,那些现代人本不易理解的作品和其内涵就变得更易接受。受众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与文本的互动程度远远大于其他艺术形式,环境烘托与氛围渲染让人们的参与主动性大大增加。2016年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共同打造的《清明上河图3.0》结合了舞台艺术、全息影像技术,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演绎,让它又重新“活”了起来。二次创作不仅保留了经典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也有利于审美教育的普及,许多珍贵的藏品对普通民众来说很难一睹真容,如果无法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欣赏,就很难提升个人的审美格调与审美趣味,健全人格的形成离不开审美教育,沉浸式艺术凭借新媒体的传播力,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经典,而好的参照物自然能对人的审美价值标准产生正面影响。沉浸式艺术不仅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舞台,也给欣赏者开辟了创造空间。所谓欣赏者的创造,指的是在沉浸式体验的互动中人们基于文本的创造,或在脑海对文本进行再造性想象、或在体验之后自己去动手实践。当然互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沉浸式艺术在观众介入的那一刻才算创作完成,因此人也算艺术作品的一部分,这样亲密且互补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打开了人们的感官,在“境”中的奇妙体验,使受众的审美直觉更加敏锐,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
从情感角度看,沉浸式体验更易引导人们全神贯注地去欣赏作品,情感也更易被调动起来。失去对情感的教育,美育就无从谈起,丢失情感的人会让动物性压倒人性,无序的行为和欲望的发泄也会将道德标准破坏。艺术作为审美的典型范式饱含了艺术家的情感,因此对作品的欣赏可以陶冶欣赏者的情操,但是现今社会严苛的分工和生活压力让情感变得僵化,不少人已经疲于面对经典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和快餐式的娱乐。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艺术受众的缺失会倒逼艺术家的流失,之所以探索沉浸式体验,就是为了缓解艺术的危机,在沉浸式产品中,知识、阅历、心情、境况都不是体验效果的决定因素,只要受众愿意参与,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技术手段都可以实现审美体验的“物我同构。”[16]对艺术审美的复归可以重新点燃情感,人们的精神状态逐渐平和,这正是美育所期望的结果。
(二)反思:娱乐、消费与被支配的主体
沉浸式体验带来的感官满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对这种快感会产生依赖性,由于沉浸式艺术造价一般都很高昂,所以不少艺术家在创作时都更注重娱乐性而不是艺术性,这是一种迎合市场的无奈选择,即使有观众希望从这种新形式中感受艺术的魅力,也可能会迷失在感官的刺激和快感中。在沉浸式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人们是跟着创作者的节奏观赏的,判断力和反思性暂时丧失作用,若作品娱乐性远超艺术性,那么就会对人造成误导。正是愉快的感官体验吸引了大量观众,因此对娱乐性的把控是沉浸式艺术的难题。沉浸式体验经济几乎已经渗透了所有传统文娱产业,可是文艺与文娱界限的模糊会对艺术造成负面影响,本来是审美教育的有力手段,在娱乐的遮蔽下反而造成受众的玩物丧志。许多沉浸式艺术展览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娱乐场所,以“沉浸”为噱头吸引人参观,造景供人打卡拍照,这些所谓的“沉浸式体验”失去了艺术的内核,而只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艺术创作异化成了艺术生产,滥竽充数的沉浸作品应运而生,吸引流量成了目标,这种沉浸体验在快感过后带给人的只能是空虚,很难引发受众的思考,也无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
此外,科技让沉浸式艺术创作更加多元、灵活,但随之带来的陷阱也更应警惕。姚斯认为:“强调创新似乎是现代偏见的一部分,或许与市场机制渗入美学领域有关。独创性和天才在受到青睐的评价范畴的花名册上,是个姗姗来迟者……换言之,我们对新颖独特的事物的偏好,与我们的‘视野’的关系,比起与过去时代存在的思想或期待的关系,很可能要大得多。”[17]345一部分艺术家其实已经掉入了所谓“创新的深渊”,科技元素的滥用会让一些沉浸式艺术作品痴迷于“炫技”而忽视作品内涵的表达,更有甚者打着“沉浸式体验”的旗号,其实只是僵硬地堆叠一些不相干的技术,根本无法营造让观众沉浸的氛围。对科技的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都会影响人们的审美体验,科技不应遮蔽艺术的内核,而只应作为辅助“沉浸”的手段。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存在着参观者主体性消失的危机,科技作为感官的延伸,可以服务人们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但实际应用时往往会发生喧宾夺主的情况。观众沉迷于身体感官作用下的虚拟场景和技术装置中,主观能动性受限,审美主体性弱化,他们或单纯被新奇和绚丽的场景所吸引,为了体验而体验,放弃了思考、批判和抵抗的权利。对于这样的受众来说,身心愉悦和社交体验是主要的目的,虚拟场景体验本身的意义和批判性思考被遮蔽[18]。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沉浸于迷幻之感而不不能获得审美体验,淹没在了娱乐消遣之中。造成人们丢失自我的原因不止如此,不少沉浸式艺术与受众日常生活的经验过于遥远,作品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走马灯,整个体验过程好似囫囵吞枣,在结束后除了对新奇形式的惊叹,并不能对作品想表达的内容说出个所以然。这种问题的症结在于艺术家过于追求表现形式的华丽,导致人们难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找到文本与自我相连的节点。沉浸式艺术与其他传统艺术一样,形式与内容的平衡才是创作的关键,科技与娱乐只是辅助“沉浸”的手段,注重对作品精神内涵的表达才是它的文化与美育价值所在。
四、结语
“感受美”的主体参与度是大于“欣赏美”的,在沉浸体验中的感官开放程度也高于传统艺术,对文本的一览无余让想象力有了更自由的空间,这种深度的审美体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会更加深刻。然而,“沉浸”的优点恰恰是造成它异化的因素,要想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艺术与美育价值,就应杜绝娱乐至死和消费主义,以及科技的滥用,只有将它视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敛财工具,用心创造、注入情感,新兴的艺术才不会立刻衰落,也免于沦为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