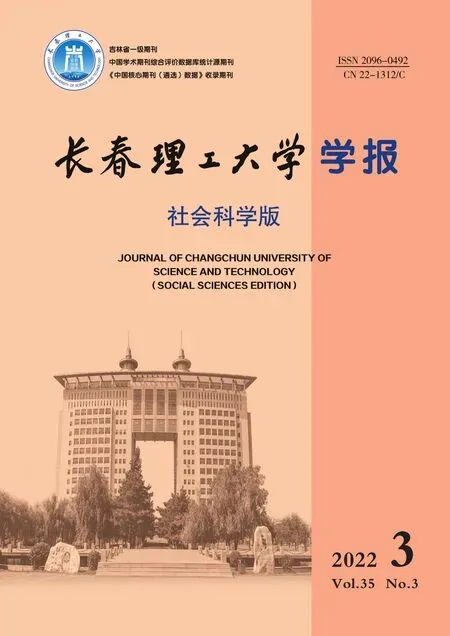论《微神》的“梦”中场域与人间之“诗”
2022-11-24杨慧莹
杨慧莹,吴 艳
(1.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吉隆坡,999004;2.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38)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微神集》以“微神”命名,如他所说:“名之曰《微神集》者,第一是因为微神这两个字倒还悦耳,第二是因为它是我心爱的一篇……”这可看出老舍对《微神》这篇小说的喜爱。但是在老舍先生的小说代表作中,多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再次创造现实情景,例如,读者耳熟能详的中篇小说《月牙儿》、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这些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生存图景、社会价值已成为老舍小说风格的标志性“旗帜”,而“爱情”的主题往往作为小说中的副线情节,并且多用于充实主线剧情的发展。因此,《微神》所具有的“突兀性”引得研究者与读者另眼相看。严家炎曾在《〈微神〉:老舍的心象小说》中对《微神》的“心象”概念进行了经典的阐释:“不但梦境属于‘心象’的延伸,即使‘梦的前方’也是一种象征化的‘心象’,整篇作品都是通过现实和梦幻交错,来展现一个内心的甚至是下意识的境界。”[1]基于对“心象”概念的理解,引起了研究者对《微神》中梦境与“心象”话题的多方面探讨,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往往被忽略,即如何“通过现实和梦幻交错”展现“内心的甚至是下意识的境界”。这不仅涉及到对《微神》的思想内涵与学理层面的追问,还可联系至短篇小说在建构时空观时所采取的文本策略,以及如何在“梦”与“诗”的对话中延展小说的思想深度,本文就此研究方面展开论述。
一、“梦”中场域与文本策略
《微神》全篇不过9 000余字,但却能够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富有张力的情节与鲜明的形象,这正是以构建“梦”中场域作为文本策略的有效方式。此方式不但延展了短篇小说的创作空间,并且悬置了“事件”真实与虚假的界限,也悬置了过去与未来的空间观。在“梦”中场域,“说”“出”“给”三者可以圆润地结合,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一)“梦”中场域与创作空间
首先从《微神》的题材进行探究。小说无外乎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情节,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短篇小说而言,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将所要讲述的故事完整地、有条理地展现出来;如何在限定的人物与“场所”内完成对整个“事件”的构思,达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效果,从而营造出“情”与“思”兼备的延展空间,这些要求具有一定的难度。由于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若想在特定“场所”内塑造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展开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是需要谨慎思考的,许多短篇小说选择开门见山的叙述方式,或以悬疑的策略突出矛盾冲突。但《微神》的叙述并非如此,而是有效地利用了“梦”中场域对小说的创作空间进行延展。
《微神》的故事情节具有张力,且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即便小说中的“她”已死,但老舍却未将小说写“死”,还由此激发了读者关于“生”与“死”的疑问与探求。这不仅归功于老舍先生妙笔生花的文字功底,也是“梦”中场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由于短篇小说在情节构思上具有挑战性,若运用全知视角叙述,小说中的矛盾冲突与悬念设置的作用会被消减,若仅运用限知视角,人物塑造的展开空间又会被限制,而“梦”中场域则可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梦”中的“异世界”,读者在理解的时候会自行带入先验认知:“梦”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突破具体“事件”的束缚,生命的进程可以在“梦”中被打破,既定的历史可以被重新认知,日常经验也可以用悖论来推翻。“她”与“我”在“梦”的场域中重遇,不仅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更跨越了生死的秩序,因此“梦”作为个人的隐私空间,其具有的虚幻性使人暂时逃离了常规秩序的束缚。虽然《微神》中的出场人物只有“我”与“她”,故事场景也非常有限,但人物与场景却在“梦”中场域环环相扣。伊藤敬一在《〈微神〉小论》中将《微神》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春天的花园;梦的前方;“我”的回忆;“她”的陈诉;尾声。[2]本文在此基础上将这五部分进一步归纳为两大部分:现实情景与“梦”中场域。现实情景包括“春天的花园”与“尾声”,而“梦”中场域则包括“梦的前方”、“我”的回忆、“她”的陈诉。
首先“我”由现实的“山坡”进入“梦的前方”,再由“梦的前方”进入“我”的回忆,接着由“我”的回忆返回“梦”中的小房子,从而推进“她”的陈述,最后伴随着“她”的消逝,“我”又重新回归到现实的“山坡”。具体而言,利用“梦”中场域,“我”与“她”可以存在于三个时空中。第一个时空是“山坡”上的现实情景,这时虽然没有“她”的存在,但从全文来看,此时“她”的缺席也证明了“她”的存在,因为“她”的缺席便是全文的起点——“她”已经逝去。第二个时空是“梦的前方”,即心中“三角”,在这个“不甚规则的三角”梦境中包含了关于“探险”与解脱的主题。“三角”所对应的三处风景中,一处是“她”曾居住过的住所,在经过“我”的回忆后,“我”又转回“她”曾居住过的小房子中,虽然“她”肉身已在现实世界中毁灭,但在“梦”的场域中“她”的精神得以保留。这里是“她”对“我”表达深情的地方,也是“我”直面悲喜之“诗”的场所,而“我”的选择则是以“探险”的方式告别这段爱情之“诗”。第三个空间存在于“我”的回忆中,这部分是由“梦的前方”引发的既定回忆,也可以称之为“梦中梦”,其中讲述了“我”与“她”朦胧的初恋往事,在“梦中梦”里有“我”的无奈与无助,“她”的不幸与冷漠,以及最后“她”因打胎而死的悲凉结局。需注意的是,虽然“我”所回忆的具体“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梦”的场域内,但“梦的前方”作为“时间不在场的诱惑”则指引着“我”去追忆逝去的记忆。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其著作《文学空间》中对回忆的“积极力量”所做的阐释:“回忆把我从以别种方式将我召唤回去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它赋予我自由地召唤它并按我现在的意愿拥有它的那种手段,从而使我获得解放。”[3]这说明“现在的意愿”意味着“我”的回忆并不能以“不在场”的“事件”作为曾经“在场”的证据,因为“梦”中场域是对陈旧记忆的重新开启与不断更新,《微神》的“梦”中场域体现出“言不尽意”的特点。犹记沈从文的名作《边城》,其对翠翠的梦境也进行过简单而又清晰的描述: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作者从旁观者视角对于梦境的柔软陈述,但转而看向《微神》,即便在“梦”中场域,其依然具有条理清晰的叙述逻辑。“我”进入“梦的前方”,并走进“她”的小房而触发了回忆:曾经年少时“我”与“她”的青涩暗恋,以及多年后“我”出国,“她”沦为暗娼,最后“她”因打胎而死。虽然《微神》运用了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技巧,但并非杂乱无章,相反,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于“讲故事”的意识流。在“梦”的场域中,陈述的逻辑是具有前因后果的叙述策略,因此《微神》不同于《尤利西斯》的破碎分离,也没有《等待戈多》中的虚妄彷徨,而是更倾向于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以假定性的情景所构建的带有黏着性与悖论性的语言。只不过在《微神》中,这个假定性的场景被定格在“梦”中场域,因为“梦”可以将时空顺序打乱而不用背负语言混乱的罪名,并可以在“梦”中场域进行文学的再次创造,“悬置”起真实与虚幻这组针锋相对的矛盾。
(二)“梦”中场域与“悬置”意义
从上文分析可知,现实的“我”与“她”、“梦的前方”中的“我”与“她”,以及回忆中的“我”与“她”,在这三个空间中存在一条清晰的因果链。这段情窦初开的感情在回忆的小房子中开始,而一切的美好以“春天埋人”的一副棺材为终结,于是“我”和“她”的“诗篇”从清丽的色调蜕变为诡谲的冷漠。而将这一切都编制在“梦”的场域之中是非常和谐的,因为在现实与梦境这两条叙事线索中,并非以真实和虚假的对立作为叙述的条件,而是以“梦”中场域来超越真实与虚假的研讨范畴。
现实与梦境如同两条重合的相交线,重合点便是“她”的死亡。在现实中,“她”因打胎而死,这是肉体的衰亡;在“梦”中场域,她的脚最终化为白骨而消失,这是精神的陨落。“梦的前方”存在的“前设”条件是回忆与现实部分的逻辑叙述,这是现实中的“死”与回忆中的“生”共同构建的“梦”中场域。如果“我”对“她”没有回忆中的情愫,“她”就无法住进“我”的梦中;如果“她”在现实中没有死亡,也就无法铸就“我”对“她”的执念,因此“梦”中场域在本质上并不是“生”与“死”的对立,而是在回忆与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超脱于“生”与“死”的话题。这不同于《罗生门》中以“死亡”为基点所展开的矛盾性叙述结构,《微神》在“死亡”的重合点后,以协调补足的叙述方式形成严密的叙述逻辑;不同于《罗生门》中各执一词的矛盾分化,虽然都对“死亡”话题保持警觉的姿态,但是在《微神》的“梦”的场域中,“我”的回忆与“她”的陈述则具有内在逻辑的真实性,“我”与“她”共同叙述了一个完整故事的前因后果。但是,因为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是以“梦”中场域作为“前设”条件的,这样能“悬置”起故事内容的真实性,但又无法否定故事内容的真实性,所以只能对此保持谨慎与怀疑,同时也正是在读者与研究者的不断推测与怀疑中拓展了《微神》的思考深度与文本价值。因此《微神》的“梦”中场域的不确定性如同一种“诱惑”,如陈嘉映在著作《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中曾说:“看似人发明了语言利用着语言,实则是人在语言中发现自己。”[4]而这填补空白的“诱惑”正是以隐秘的“梦”境作为语言的载体成为一种“召唤结构”。程亚林在总结陈嘉映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时曾说:“任何语言都对存在有一定程度的遮蔽,因而存在的敞亮只是一瞬间的事,诗人只有在‘说’而未‘出’的那一刹那间,领略到存在的真容,发现存在‘给’了出来。一当被‘说’出,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玄秘’而隐没于‘晦蔽’之中。”[5]这不仅对诗人而言如此,对所有创作者来说,“言不尽意”的困扰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作过程。对于《微神》这类以现实主义为“质”,以现代主义为“形”的短篇小说,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捕捉到“说”与“出”的临界点,并将存在的意义自动呈现“给”读者,这便需要一个特殊的媒介作为特定的“场所”——“梦”中场域。因为“梦”中场域不仅悬置了“事件”的真实与虚假的界限,也悬置了过去与未来的空间观。
需要注意的是,“悬置”不等于“消解”,“消解”是在直面问题后对二元对立状态的取消,但“悬置”是暂时的回避,将“所指”导向其他值得思考的话题,这不但在宏观思考上扩展了《微神》的理解范围,而且在微观叙事中将“梦”中场域与创作场域相连,使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原理作为引导问题意识的话语。总之,“梦”中场域的建构“悬置”了将真实与虚幻相对立的可能性,也“悬置”了话语权的争夺战。创作者在运用文本策略时,可以在“梦”中场域自然而然地将“说”“出”“给”三者相结合,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因此在“梦”的场域中,质疑作品真实与虚构的方式是无效的,而真正带给读者的是故事所“给”出的关于存在意义的思考,这也是对“爱情”本质的思索。
二、人间之“诗”“梦”“爱情”
在《微神》中,老舍先生将“诗意”与“平凡”相对,并与“色彩”相连,“色彩”则以“诗性隐喻”的手法描绘着充满欢乐与苦痛的人间之“诗”。作者最终选择了以“探险”的勇气直面“诗”的悲喜,这即是人生的悲喜,并以“梦”中场域作为“爱情”的祭奠,为取消自我憎恶提供了可能性。
(一)“色彩”中的人间之“诗”
在《微神》中,作者曾以“后设”的方式言明:“爱情的故事永远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那么,想必是世界上多数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怜的人们!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应有的趣味吧。”[6]130通过“我的故事”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这正是通过探险“梦”中场域来寻得“诗意”,而何为“诗意”?“诗意”与“梦”又有何渊源?这是在研究《微神》的“梦”中场域时容易被忽略的要点。
上述解释中,老舍先生将“诗意”与“平凡”相对,并与“色彩”相连。在对《微神》进行文本细读时,可以发现“色彩”是小说中的重要线索,并且《微神》中的“色彩”具有反常识的特性。例如深绿、浅绿、草绿等绿色色调并非仅是蓬勃生命的象征,“色彩”也是以“诗性隐喻”的文本策略通向生命“消亡”的暗示。例如“她”的“小绿拖鞋”对应的是“一支白脚骨”,而“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作着春梦”对应的是“春天也要埋人的”的死亡现实。“她”曾经的住所中的“浅绿小垫”“案上的一盆小松”“锈色比小松浅些的两方古铜镜”“快垂到地上的绿毯”皆消逝在现实时光中,后来“绿色”则成为“她”沦为暗娼时脖子上的“大绿梳子”。而曾经初恋时“腮上的两片苹果”“两颗香红的心”“小红木凳”以及她脸上红艳的花影,文中这些红色色调不仅象征着初恋的情节,在“她”沦为暗娼时“红”则成为“她”穿着的“一件粉红长袍”。这可以看出,《微神》中“色彩”的象征意义具有矛盾性:美好与痛苦的悖论。而“色彩”所象征的矛盾意义正是以“诗性隐喻”的方式体现出美学性与创新性。“诗性隐喻”的概念是由莱可夫(George Lakoff)和特纳(Mark Turner)在著作《超过冷静理性:诗性隐喻分析指南》中首次提出的。胡壮麟先生在此基础上对“诗性隐喻”的典型特点进行研究,指出“诗性隐喻”具有原创性、真实性、跨域性、美学性等特点,如他所说:“有人认为,所有隐喻在感官上应当是清晰的,如事物与事物、感觉与感觉、观点与观点、图画与图画,都不能相互混淆。这一看法是认识上的误区。它妨碍了人们去发现、理解和鉴赏最伟大的诗性隐喻……诗性隐喻,以一种可眼见、可触摸、可听到、可品味、可嗅到的方式,给读者带来思想和情感。”[7]因此在《微神》中,“诗意”所暗含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色彩”的方式将抽象意义具象化,通过“色彩”的矛盾意义暗示《微神》中“诗意”的美好与痛苦,这样的丰富性正是“诗意”所具有的不平凡的内涵。
在《微神》中,老舍先生多次对“诗”进行阐述:“我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思念也没有,可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些诗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没有声响,只有些波纹是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终也没成功一整句。一个诗的宇宙里,连我自己好似只是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符号”[6]123;“左边是一个斜长的土坡,满盖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银色而显出点诗的灵空”[6]126;“我的心跳起来了!我决不是入了济慈的复杂而光灿的诗境”[6]128;“我杀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区别?”[6]149从这些描述中可以发现,“诗”与“梦”有着某种相似的联系。首先,《微神》中的“诗”不同于海德格尔笔下“诗”与“思”的理想场所,而是包含欢乐与痛苦的“色彩”,是人间的真实与无奈,也不同于但丁《神曲》中理想的、乌托邦的、充满神性的“诗意”。在《神曲》中,但丁将“诗”以“爱情”具象化,但“爱情”却再次上升为抽象的符号,并指向宗教与信仰,而《微神》所描述的则是关于“爱欲与文明”的人间之“诗”。在《微神》的“诗”中充满着关于生与死、存在与痛苦、幸福与激动的人生必修课题,这便是人间之“诗”所具有的完整性与丰富性。人间之“诗”所传达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理想的团圆式结局,也不是西方“悲惨世界”般的痛苦命运,它具有的开放性正如“梦”中场域所具有的延展性,“悬置”了绝对统一、对立解构的命题,并以“复调”的声音在知觉中体验五味杂陈的人间之“情”。如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著作《心的概念》中阐明:“知觉活动既蕴含着具有感觉,又蕴含着在一种牵强附会的含义上可称之为‘思考’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这种牵强附会的含义上,描画、想像或幻想看到或听见某物也蕴涵着思考。”[8]那么在“梦”中场域进行着“思考的活动”,就是以“色彩”的反常识性经验展现出“诗”的“思考”所具有的变动性,“诗”中关于“知觉活动”的“思考”意义正是对生命悲喜的直视,这是打破生死一线的焦虑,也是“我”对于“心象”的“探险”。“我”在“知觉活动”中关于“诗”的“思考”激起了鲜活的生命意识,并促使“我”思考关于“爱情”的价值,这也是为何“我”最终决定“探险”的缘由。
(二)“梦”中的“爱情”——直面人间之“诗”
假设没有“梦”这个特殊的场域,也不妨碍《微神》故事情节的叙述,如运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一位清纯的女子沦为暗娼的不幸,而“我”只能无助地默默忍受这份悲凉。但在思想表达上,如果失去了“梦”中场域,则会失去一定的思考深度,即“我”对“诗”的构建。如前文所说,“我”在“梦”的场域中对“诗”的建构不同于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栖息之所,“诗”与“思”隐蔽了现实的残酷,但“我”并没有用虚构的幻想对“我”的精神场域进行庇护,而选择了以“探险”的勇气直面“诗”的悲喜,这即是人生的悲喜。
文学作品中的多数梦境是对遗憾的圆梦,如经典作品《牡丹亭》,其中片段“游园惊梦”正是杜丽娘因伤春之情而感发的云雨之“梦”,这是杜丽娘以圆梦的方式对真实生活的补足。但《微神》的“梦”却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在“梦”的尾声,“我”不想再受制约,于是坚持去看“她”的脚,可最终看到的却是森森白骨。如果之前“她”的“小白鞋”映射的是“我”对“她”的欲望,那么在“梦”中场域,“我”想要看“她”的脚的行为并非出于对欲望的满足或对遗憾的圆梦,相反,这是“我”要获得“探险”的勇气与要做的仪式性的告别。当“我”从最初的逃避:“为什么她落到这般光景?我不愿再打听。反正她在我心中永远不死”[6]142;“我看见它多少多少次了……可是我没到那个小房里去过”[6]128,发展到“这次我决定了去探险”[6]128的决定,正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转变。“我”最初以各种借口回避真实,以自欺的方式躲避痛苦,而“我”所做的“探险”的决定是试图直面这段“诗”中的“爱情”,表达出告别这段“爱情”所有的欢乐与痛苦,正如“她”最后将“我”从“梦”中场域推出,这表明“我”终结了对“爱情”的执念。
然而在“梦”的小房子里,“她”的发言到底是来自“她”的真挚情感,还是来自“我”所编织的自慰,这个问题不得而知的,因为文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断论,读者有权利猜想“她”是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真实形象,也可以假设“她”是“我”以“代偿性”的方式来补偿“我”的爱意与自尊。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对过往事情的解释是“我”对于“她”的死亡“事件”的解脱。如杨晓河在《老舍〈微神〉爱欲思想的探微》中阐明:“《微神》表面上纪念爱情,隐义是通过叙述恋人从心中离开来揭示我如何从对初恋亡人的记忆中‘解脱’出来。”[9]进一步而言,从初恋情人的记忆中解脱的不仅是痛苦懊悔的情感,更包含了回忆中心动如催的情愫,这便是人间爱情之“诗”。因此无论“她”是“我”虚构的,还是“她”确实是以超验的形态存在的,对《微神》而言都是浅尝辄止的分析,而最为精心的设计是通过“她”的解释为“我”曾经的无奈与懊悔寻得了解脱的特权,这是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的和谐运作,于是“梦”中场域作为“爱情”的祭奠为取消自我憎恶提供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微神》,不但是以“爱情”作为小说的叙事焦点,以现代主义手法凸显多重叙事方式,更将“爱情”的主题与“梦”的叙事策略相结合,将“诗”的构建通过“诗性隐喻”的方式显现在“梦”中场域里。因此在研究《微神》时,不仅需要以现代主义或象征化技巧来阐释梦境与“心象”的概念,同时需注意小说是如何运用文本策略来探讨“梦”中场域的内涵与外延意义,如何在“梦”中场域中以“诗性隐喻”来隐喻人生之“诗”,这涉及到对小说《微神》的文本策略与思想深度的探求,为在小说的“形”与“质”上获得更为深刻的思考,也为当下短篇小说的构思提供创作新意与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