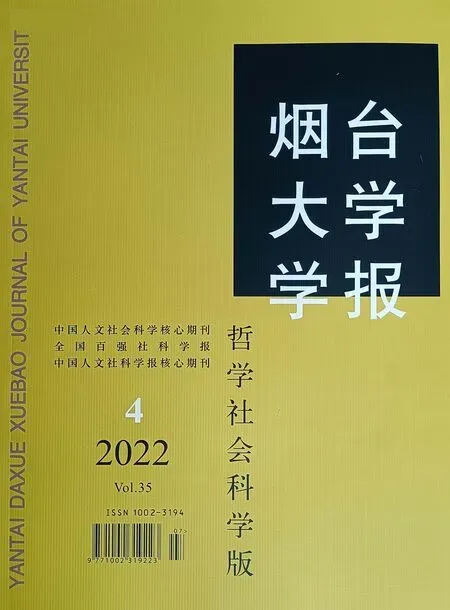《盂兰盆经疏新记》日本流传考
2022-11-23李铭敬王荟媛
李铭敬,王荟媛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宋代大智律师元照(1048—1116),俗姓唐,字湛然,为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灵芝崇福寺住持,因此又被称为“灵芝”或“灵芝元照”。元照继承了道宣(596—667)的南山律宗,以律宗中兴之祖著称,同时在净土宗一门有很高的造诣。其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释“南山三大部”(1)道宣律师常年居终南山,被后世称为“南山道宣”或“南山”。他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奠定了南山律宗的基础,被称为“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42卷、《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22卷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21卷,以及净土宗著述《观无量寿佛经义疏》3卷和《阿弥陀经义疏》1卷。(2)参见温金玉:《灵芝元照:律风浩荡九百年》,《中国民族报》2016年12月20日,第7版。此外,他还著有《盂兰盆经疏新记》(以下简称为《新记》)1卷,是唐代圭峰宗密禅师(780—841)所撰《盂兰盆经疏》的注释书,国内现已亡佚不存。
目连于七月十五日供养十方众僧而使母脱饿鬼道之苦的故事初见于西晋竺法护译《盂兰盆经》,此后作为盂兰盆会的起缘故事而广为人知。后世有不少高僧大德为之作疏,其中圭峰宗密禅师所撰的《盂兰盆经疏》尤为著名。该疏凡一卷,辑录儒释孝道要言,强调“孝顺、设供、拔苦、报恩”(3)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第506页b。。此疏历来被视作解释《盂兰盆经》的权威之作,如宋代普观的《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提到:“吾祖圭峰禅师之疏兰盆也,遂古作者,莫之与京,讲授流通,为日故久。”(4)普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1989年,第483页a。然而《盂兰盆经疏》虽广引儒释经典,引用之际却多以“儒中”“释中”等代替原本的书名,导致典籍出处模糊,初学者难以理解,望而却步。元照意识到其“传授者鲜能开诱,撰述者互有瑕疵”(5)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55页b。的问题,立志“由记以达疏,由疏以通经”(6)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55页c。,不仅详细考据了其典故、引文的出处,引经据典说明其含义,还对生僻、难懂的词汇加以注释。
《新记》鲜少得到中外学者关注,其版本和流传情况还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日本学者坪井直子曾就佛教说话集《沙石集》对《新记》中所载“孝孙元启”故事的引用进行考察,并提及日本中世(1192—1603)的《言泉集》《私聚百因缘集》《往生要集义记》《往生礼赞私记见闻》和近世(1603—1867)的《劝孝记》《童子经谚解》等文献中均可见《新记》的书名,(7)参见坪井直子:《孝子伝、二十四孝と盂蘭盆経注》,《京都语文》2016年第23期。初步梳理了《新记》在日本的流传脉络。然而坪井并未具体考察《新记》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亦未论及其对日本文学的具体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此书在日本的刊行流通和在日本文学中的接受情况,探讨其在日本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明确《新记》在中日典籍和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意义。
一、《盂兰盆经疏新记》在日本的刊行与流通
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义天(1055—1101)渡宋求法,曾至灵芝崇福寺谒元照,并请得其所著书于高丽雕板流通。义天归国后致力于宋、辽佛经的刊行与整理,编纂了佛书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录》(1091),即著名的“义天目录”,为佛教章疏目录之嚆矢。其中“盂兰盆经”条有“疏一卷宗密述……记一卷科一卷元照述”(8)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1172页b-c。一文,是可考的关于《新记》传往海外的最早著录。
而将《新记》传入日本的关键人物是京都泉涌寺的开山鼻祖俊芿(1166—1227)。俊芿号“不可弃”,常被称作“不可弃法师”。据其传记《不可弃法师传》(1244)记载,他在宋十二年,南宋庆元五年(1199)入宋,于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景福寺师事元照门下弟子如庵了宏,嘉泰二年(1202)携大量典籍和文物而还,其中包括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观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道书籍256卷、杂书463卷、碑文76卷等。回国后,他在京都创立了泉涌寺,大力弘扬南山律宗,使得泉涌寺一时成为律宗的中心。(9)参见信瑞:《泉涌寺不可棄法師伝》,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东京:法藏馆,1972年,第416页。从镰仓时代(1192—1333)中叶起,在泉涌寺主导下,佛教书籍的刻板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史称“泉涌寺版”。其早期开版书籍如下所示:
宽元四年(1246) 元照撰《佛制比丘六物图》一卷
宝治二年(1248) 《梵网经菩萨戒本》一卷
建长三年(1251) 元照撰《盂兰盆经疏新记》一卷
建长四年(1252) 道宣撰《四分律行事钞》三卷及元照撰《行事钞资持记》三卷
建长六年(1254) 《沙弥十戒法并威仪》一卷
文永十年(1273) 《教戒律仪》一卷
永仁二年(1295) 道宣撰《解释门归教仪》二卷
永仁六年(1298) 宗密撰《盂兰盆经疏》一卷及元照撰《盂兰盆经疏新记》一卷
正安元年(1299) 元照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卷(10)平春生:《泉涌寺版と俊芿律師》,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第319-323页。
可以看出,早期泉涌寺版以律宗典籍,尤其是道宣和元照的南山律宗著述为主。如划线处所示,《新记》在建长三年(1251)首刊,在永仁六年(1298)重刊,可见其受重视和欢迎的程度。泉涌寺版《新记》今已不传,仅存由净因撰写的卷末刊记,全文如下:
入宋中兴师不可弃和尚,始传此文,将来本朝,兼讲其诰,用示未闻。自尔以来,师资禀承,弘赞无绝。盖文兼内外,而音训不同;言亘众典,而起尽易惑。仍为资新学之费,切聊加短才之愚点,错谬定容多英俊更正之矣。建长四年七月日,泉涌寺首座净因谨点。
比丘尼净信舍数贯净财,开一卷新记。愿使旷劫生缘、法界群类,忏涤罪根,庄严净土。建长三年七月日,干缘比丘净因谨志。(11)平春生:《泉涌寺版と俊芿律師》,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第332页。
净因(1217—1271),字圆悟,曾师从泉涌寺二世定舜律师和三世智镜律师研习“南山三大部”,先任泉涌寺首座(12)首座:仅次于住持的僧职,掌管僧堂内部事宜,亦称上座。,后历任戒光寺和饭山寺住持,声重律苑,被门人誉为“灵芝之再生”。(13)参见卍元師蛮:《本朝高僧伝》,见《大日本仏教全書103》,东京:仏书刊行会,1912-1922年,第770页。据此刊记,俊芿不仅将《新记》带回日本,还讲论其要旨,此后代代相传。由于《新记》广引佛教内外典籍,阅读难度较大,净因特意加注了训点(14)训点:汉文佛经传入日本后,为便于理解,日本僧侣在行间加入的表示音义的日文假名。,以便初学者理解。此版《新记》是受到比丘尼净信的资助出版的,此人生平事迹已不可考。据日本“全国汉籍数据库”,有明确刊年记载的藏本包括永正二年(1505)比丘守怿刊本二册、庆安元年(1647)京都武村市兵卫刊本三册、贞享三年(1686)大坂励学堂河内屋善兵卫重刊本五册,刊年不详的藏本包括日本刊鼇头本五册、永正年间刊一册。(15)参见(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2018年4月(更新日期),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query=%E7%9B%82%E8%98%AD%E7%9B%86%E7%B5%8C%E7%96%8F,2021年10月4日(访问日期)。从中世到近世屡经刊刻,足见《新记》在日本的流传绵延不绝。
二、《盂兰盆经疏新记》在日本作品中的征引情况
《新记》传入日本后,迅速得到传播和普及。笔者注意到,日本僧人所撰的唱导资料集、说话集和佛经注疏中都有对《新记》不同程度的引用和提及。就利用方式而言,《新记》转引自其他文献的孝子故事成为唱导资料集《言泉集》的重要素材来源,而说话集和佛经注疏更多关注《新记》对汉语、梵语词汇的解释。
(一)唱导资料集
《言泉集》(约1232—1235)是安居院流唱导师圣觉在其父澄宪的《转法轮抄》的基础上编纂的唱导(16)唱导:唱导师将佛教教理以讲唱的形式加以披露的一种布教手段。按编纂目的,其内容主要分为亡者佛事、镇护国家和除灾招福三种。资料集。亡者佛事部分主要收录了祭奠亡者的法事中的讲唱素材。其中,“亡父帖”“亡母帖”“祖父养父”“兄弟姊妹”条大量引用了佛教内外典籍的孝子故事。《新记》的引用集中于“亡父帖”的“不孝罪过”一节中:
《同记》云(元照)(17)括号内为原文小字夹注,以下皆同。:“五桥,以五车系五体,纵横裂之。《三十国春秋》云:‘池汤用妻言,将母于山中杀之。秦王闻,令以五车杀之云。’”
《盂兰盆记》云:“《大报恩经》云:‘须阇太子父母被贼所算,逃逝外国,失路绝粮。乃割己肉,供须父母,令达前路。’”《同记》:“《汉书》云:‘文帝母疾病踰年,文帝目不睫,不解衣冠,汤药不掌不进。’《礼记》云:‘文王有疾,武王不脱衣冠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间谓病差)。’”
《同记》云:“《大报恩经》云:‘忍辱太子父母病重,医者云:“须不瞋人肉为药。”太子自念生来不瞋,因名忍辱,可充此药。又念国中设有不瞋者,如何取彼救我亲乎?遂自割肉充药,厥病乃愈(音抽)。’”
又云:“《唐僧传》云:‘高齐道记,往必荷担,不耻微行。经书、塔像为一头,老母、扫帚为一头,齐佛境内有塔斯扫。每语人曰:“经不云乎,扫僧地如阎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胜也。亲供母者,福与登地菩萨齐也。”至于便利,女人经理,不许人兼。或有助者,纪曰:“母,吾母也,非侘之母。形骸之累,并吾身也。有身必有苦,何得以苦劳人?所以身为苦先,幸勿相助云。”’”
释尊担棺
《增一阿含经》云:“净饭王崩,白氈棺。佛与难陀在前,阿难罗云在后。难陀白佛:‘父王养我,愿听担棺。’阿难罗云亦尔。佛念当来凶暴,不报父母,故躬自担棺。大千六反震动,释梵诸天,皆来赴丧,代佛担之。佛执香炉,前引就山云。”
孟宗抽笋
《孝德传》云:“西晋孟宗为郎中,母丧,委官而归。母性嗜筍,宗每当时供奉。母亡后,冬至欲以筍祭。乃入竹园,哀告天地,乃得以荐之。”(18)《言泉集》有金泽文库本、真如藏本和东大寺北林院本三个主要版本,金泽文库本和东大寺北林院本已出版,真如藏本尚未公开。东大寺北林院本和金泽文库本“不孝罪过”一节有内容缺失,《言泉集·東大寺北林院本》附录的内容对校中,以真如藏本补完此节内容。见畑中栄编:《言泉集·東大寺北林院本》,东京:古典文库,2000年,第442-444页。
上文“《盂兰盆记》《同记》”都指《新记》。《言泉集》转引自《新记》的佛书典籍以外的典故包括《三十国春秋》池汤事(19)《三十国春秋》现已亡佚,今存清代汤球的辑本,其中并无池汤事的记载。见吴振清校注:《三十国春秋辑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汉书》汉文帝侍母事、《礼记》周武王侍文王事、《孝德传》孟宗哭竹事,佛书典籍中的典故包括《大方便佛报恩经》须阇提太子事和忍辱太子事、《唐高僧传》道纪担母事(20)关于道纪担母事,《新记》和《言泉集》均为“《唐僧传》云”,道纪担母洒扫的故事见于《唐高僧传》卷三十《高齐邺下沙门释道纪传》,《新记》中《唐僧传》应该是《唐高僧传》,即道宣所撰《续高僧传》的略称。和《增一阿含经》佛陀担棺事,以佛教内外典籍中的孝子故事为主。从引用的数目来看,除去非孝子故事的池汤事,《言泉集》引自《新记》的孝子故事共7条,可见《言泉集》重视对《新记》所记载的孝子故事的援引。前文提及,宗密的《盂兰盆经疏》虽然广引儒释孝子故事,却多是采取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若非熟悉上下文,则很难理解,《新记》的注释弥补了这一不足。如《新记》对《盂兰盆经疏》“升棺”一文的注释为:“对举曰升。《增一阿含经》云:‘净饭王崩,白氈棺殓。佛与难陀在前,阿难、罗云在后。难陀白佛:“父王养我,愿听担棺。”阿难、罗云亦尔。佛念当来凶暴,不报父母,故躬自担棺。大千六反震动,释梵诸天,皆来赴丧,代佛担之。佛执香炉,前引就山。’”(21)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63页a。又如《新记》对《盂兰盆经疏》“儒有荐笋”一文的注释为:“儒中《孝德传》云:‘西晋孟宗为郎中,母丧,委官而归。母性嗜笋,宗每当时供奉。母亡后,冬至欲以笋祭。乃入竹园,哀告天地,乃得以荐之。’”(22)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63页b。从典故出处和故事细节两方面完善了《盂兰盆经疏》所提到的孝子故事。《言泉集》“亡父帖”收录了祭奠亡父的佛事中僧侣所讲唱的词章,主要内容包括孝子故事和歌颂父亲养育之恩的美言嘉句,《新记》中的孝子故事契合其主题,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如划线处所示,《言泉集》对《新记》的引用多有错漏之处。“五桥”为“五擿”的误写,“道记”为“道纪”的误写,“至于便利,女人经理”应为“大小便利,必身经理”。笔者推测,《言泉集》成书时,《新记》尚未正式开版印刷,依靠手抄本传播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讹误。俊芿在创建泉涌寺后,制定《泉涌寺殿堂房寮色目》,其中“法轮宝藏”条云:“教藏者,安置大宋传来律宗、台教等之教乘,永备学道者之龟鉴。为令法久住,广答四恩也。”(23)俊芿:《泉涌寺殿堂房寮色目》,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第395页。俊芿及泉涌寺其他入宋僧所携归的典籍应该都安置在此“教藏”之内。同时《泉涌寺遗嘱诰文》规定:“若寺中僧借文字时,必见长老首座之听许,方可借之。不然,勿辄借之。寺门之外,永不可出。”(24)俊芿:《泉涌寺遺囑誥文》,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第392-393页。俊芿对教藏借阅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在此背景下,《新记》有可能通过泉涌寺僧抄写传往寺外。
(二)说话集
说话集是平安时代(794—1192)到室町时代(1336—1573)流行的一系列取材自佛经和民间传说等的短篇故事集。泉涌寺版《新记》首刻六年后,净土宗僧侣住信法师所撰说话集《私聚百因缘集》(1257)卷六《风树根之事(孝与离别也)》(25)“根”为“恨”的误写,以下皆同。一文中就已经引用此书解释“风树恨”的含义:
宗密禅师《盂兰盆疏》之《新记》云:“风树根者,《鲁史》云:‘孔子出行,见虞丘子也,道中哭。孔子问其故之时,曰:“吾有三失,是以哭也。我本高其志,不事庸君,臣节不遂,是一失也。吾少而择交游,寡于亲友,老无所托,是二失也。吾少游学,周流天下,父母已终,阙于侍养,是吾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永不返者,年也;去再不见者,亲也。”云毕而死。’”(26)住信:《私聚百因縁集》,东京:名著普及会,2007年,第103页。
划线处“宗密禅师《盂兰盆疏》之《新记》”即是指《新记》。《盂兰盆经疏》序言中有“宗密罪衅,早年丧亲。每屡雪霜之悲,永怀风树之恨”(27)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第505页a。之句,《私聚百因缘集》所引内容为《新记》对“风树之恨”的注释,可见住信同时参考了《盂兰盆经疏》和《新记》。
无住道晓(1227—1312)著有说话集《沙石集》《杂谈集》《圣才集》等书,以“八宗(28)八宗:一般指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和真言宗。兼学”著称,但世人普遍认为无住是禅僧,这是由于他中年拜入临济宗寺院东福寺住持圆尔辨圆门下的缘故。《沙石集》(1283)卷八第十一条中,记载有善天狗教人真言和恶天狗劫掠僧人的两则故事。无住认为,日本的天狗相当于佛经中的鬼,其善恶之分取决于德行的优劣,并引用《盂兰盆经疏》对此进行说明:
圭峰释曰:“a傍行者曰畜生,竖行者曰鬼。”见于《盂兰盆经》之疏中。b鬼神有重重果报之优劣,c此为其行因浅深不同故。(29)築土鈴寛校订:《沙石集(下巻)》,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78页。引文为笔者所译,以下皆同。
圭峰即宗密,因其晚年在终南山圭峰坐禅,故人以圭峰称之。无住所引的内容,当属《盂兰盆经疏》下卷对地狱诸鬼不同果报的描述:
势力鬼,谓夜叉罗刹毘舍门阇等,所受富乐类于人天。b或依树,或住山谷,或居灵庙,或处空宫。a形竖而行,属于鬼趣。此等变化多端者,c繇于因地罪福不精,苦乐之因相杂作故。(30)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第509页a。
《沙石集》a处的内容与《盂兰盆经疏》a“竖行云鬼”一致,至于“横行曰畜生”,却未见相关记载,此处当是无住把《新记》的注释误以为是经疏的原文。《新记》的相关注释如下文所示:
夜叉此云轻捷,罗刹此云可畏,毗舍阇此云啖精气。a形竖行者,异于畜趣皆旁行。(31)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74页a。
佛教认为世间众生均根据生前的作为,在六道中不断轮回,其中畜生又被译为傍生,取傍行之众生意。从a处内容来看,《沙石集》同时借鉴了《盂兰盆经疏》和《新记》的描述。而b“鬼神有重重果报之优劣”、c“此为其行因浅深不同故”两处的内容化用自《盂兰盆经疏》b“或依树林,或住山谷,或居灵庙,或处空宫”、c“繇于因地罪福不精,苦乐之因相杂作故”。可知,无住在引用《盂兰盆经疏》时,还参照了《新记》的相关注释。
此外,卷一第八条中可见这样一则故事:某位上人参拜严岛神社之时,见到大量海鱼作为贡品摆在社前,深感疑惑。严岛神社的神明解释道:“接受百姓所供奉的鱼类,一方面可以减轻百姓杀生的罪孽,同时被供奉的鱼类,本来就寿命已尽,通过供奉于神明所产生的功德,亦可早日成佛。”紧接这则故事后的说理部分引用如下:
以常例论之,不杀生,踵从教义,契合戒律,奉般若妙味,方合我佛之神意。揆其因由,汉土弘扬儒道二教之时,祭以牛羊诸牲,以荐先祖。及论此,古德释云:“佛法之弘布,甚难。是以天竺菩萨,虽生于汉土,而先弘外典,令知父母之神识,诲以孝养,以为佛法之便。外典之教,乃为权教,非佛法之正者。自佛法流布,释教信众,改彼祭法,以佛法为孝养之仪。”(32)築土鈴寛校订:《沙石集(上卷)》,第43页。
《新记》对《盂兰盆经疏》“良繇真宗未至,周孔且使系心。今知礼有所归,不应犹执权教”(33)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第505页c。一文的注释如下:“佛出周时,教行西竺,故云未至。至于后汉,始流此方。若论祭法,出于往古。且取文典垂世,故推周公孔子。然而周孔皆是大权,先制礼法,使人从善,然后佛化,易可弘通。四时祭祀,非本圣意,故云且使系心。”(34)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61页c。划线处的“古德释云”以下内容显然也同时受到《盂兰盆经疏》和《新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无住之师圆尔辨圆于1235年入宋,嗣径山(今浙江宁波)无准师范,1241年携带大量典籍归国。现存《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详细记载了其携归日本的典籍书目,其中就有“《盂兰盆经疏》一卷 同记一卷”(35)大道一以:《普門院経論章疏語録儒書等目録》,见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書·家分け第二十·東福寺文書之一》,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1956年,第97页。,即《盂兰盆经疏》和《新记》。笔者大胆推测,无住利用的可能正是藏于东福寺的《新记》。
(三)佛经注疏
日本中世僧人所撰的佛经注疏中,亦可见到《新记》的书名。就结论而言,《新记》在其中多数扮演的是佛教词典的角色。下文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净土宗僧人良忠(1199—1287)晚年所撰《观经疏传通记》为《观无量寿经》的注释书,在阐释“疏”的字义和供奉父母之仪时,引《新记》加以旁证:
灵芝《盂兰盆记》云:“疏即训疎,谓疎决文意,使无壅滞。”(36)良忠:《观经疏传通记》,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7册,第498页b。
《盂兰盆疏记》云:“《僧祇律》云:‘父母不信三宝即少供,信即恣与。’”(37)良忠:《观经疏传通记》,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7册,第594页c。
虽然出处注为“《盂兰盆记》”和“《盂兰盆疏记》”,其内容却是分别引自《新记》“疏即训疎,谓疎决文意,使无壅”(38)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55页c。和“《僧祇律》云:‘父母不信三宝即少供,信即恣与’”(39)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62页c。两处。
招提寺律僧照远(生卒年不详,一说1301—1361)撰有《资行钞》(1349),为道宣撰《四分律行事钞》和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的注释书。该书解释“阿鼻”之含义时,引《新记》加以说明:
阿鼻此翻无间也。《盂兰盆新记》云:“《观佛相好经》说:‘犯逆为阿鼻因,阿鼻此翻无间。’”(40)照远:《资行钞》,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62册,第429页c。
上文出自《新记》“《观佛相好经》说:‘犯逆为阿鼻因,阿鼻此翻无间。’”(41)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63页c。一文。
东寺真言宗僧人杲宝(1306—1362)的《大日经疏演奥钞》是唐代僧一行(673—727)撰《大日经奥疏》的注释书,也引《新记》解释“觉察”和“释迦牟尼”的词义:
《盂兰盆经新记》(元照)云:“觉有二义,一者觉察,对烦恼障。无明如睡,唯圣独悟故。”(42)杲寶:《大日经疏演奥钞》,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9册,第48页a。
《阿弥陀经义疏》(元照)云:“释迦翻能仁,即大慈垂应。牟尼翻寂默,妙智冥真。合此为佛,则三身备。”《盂兰盆经疏新记》(同上)云:“俱云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以寂默故,不住生死,即法身也。以能仁故,不住涅槃,即报应也。”(43)杲寶:《大日经疏演奥钞》,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9册,第151页a。
出处注为“《盂兰盆经新记》”和“《盂兰盆经疏新记》”的引文分别对应《新记》“觉有二义,一者觉察,对烦恼障。四住如贼,唯圣觉知故。二者觉悟,对所知障。无明如睡,唯圣独悟故”(44)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58页a。和“具云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以寂默故,不住生死,即法身也。以能仁故,不住涅槃,即报应也”(45)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见《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21册,第458页a。两处。
通过考察日本僧人所撰的佛经注疏对《新记》的引用,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新记》多作为说明佛教词汇的参考资料加以使用。这是因为《新记》作为《盂兰盆经疏》的注释书,对其中难解的词汇和语句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日僧多借助训点来进行汉文的阅读和写作,学习者汉文学水平参差不齐,《新记》的注释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学习和了解佛教知识。
其二,除了律宗,《新记》还为净土宗、禅宗、律宗、真言宗等不同的佛教流派的僧侣所接受,这与泉涌寺在日本宗教界的巨大影响力有关。俊芿在宋期间,除了元照一派的律宗和净土宗外,还系统地学习了禅宗和天台宗,将之一并传往日本。如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提到:“泉涌寺俊芿不可弃法师远越波澜,入宋学法,正传台教律宗,兼传灵芝净教,即是净教相传规模。”(46)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见《大藏经补编》第32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651页a。泉涌寺建成后,俊芿设立十六观院和真言院,通过制定《清众规式》《泉涌寺殿堂房寮色目》等一系列寺制僧规,初步确立了泉涌寺净、禅、律、真言和天台诸宗兼学的宗风。天台宗慈圆、法相宗贞庆等当时各宗大德高僧都纷纷拜入俊芿座下。以此为契机,泉涌寺不仅成为当时律宗的中心,其影响力更是渗透进其他宗派中。(47)参见信瑞:《泉涌寺不可棄法師伝》,见石田充之编:《俊芿律師:鎌倉仏教成立の研究》,第413-420页。因此,《新记》在传入日本后,借助泉涌寺的影响力,在其他宗派中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三、结 语
本文以《新记》在日本的传播为例来说明域外汉籍研究对于中日典籍交流史、佛教文化传播史的意义。主要结论可以归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传播过程来看,《新记》由俊芿于1202年传入日本,1251年在泉涌寺首座净因主持下正式开版印刷,其后亦不断有刊本问世,足见其深受时人欢迎。成书于1232—1235年间的唱导资料集《言泉集》中也能窥见此书的引用痕迹,可以推测在正式开版印刷前,其手抄本就已经在寺外传播。
第二,从利用方式来看,《新记》中记载的孝子故事成为唱导资料集《言泉集》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说话集和佛经注疏则更多关注《新记》对汉语、梵语词汇的解释。
第三,从引书撰者来看,净土宗、禅宗、律宗、真言宗等不同流派的僧侣著述中皆有对《新记》的引用。泉涌寺提倡诸宗兼学,对其他宗派也具有极大影响力,促进了《新记》在佛教界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