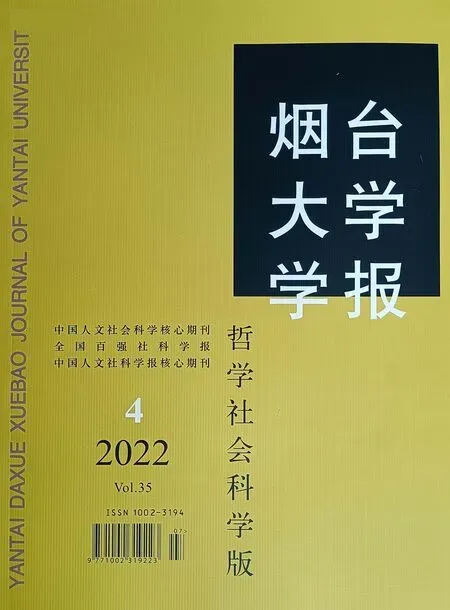走向民间:整理国故与文学史料的范畴重构
2022-11-23朱首献
朱首献,沈 阅
(浙江大学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整理国故运动是一场由胡适揭橥,以新文化派学人为中坚主体,秉持“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的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的学术运动。(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2页。在整理国故运动所批驳的诸种成见中,雅俗分野、崇雅鄙俗之旧习的偃旗息鼓以及由此催生的一股民间文化研究的热潮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学者史华慈就敏锐地发现:“在‘整理国故’这项事业中,有一个新倾向,就是人们对研究大众文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2)本杰明·史华慈:《论五四及其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黄兴涛、罗检秋译,见王跃、高力克选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在汲汲于走向民间的学术浪潮中,中国文学史的整理和书写活动也深受其影响,在文学史料的认知与择取方面,超越了以圣人文章、骈文律诗为囿的旧史料观,转而着力于提升民间文学史料在文学史著中的地位,并由此推动了中国文学史著风貌的变革。
一、雅俗平等的学术理念之提出
按照价值体系和群体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上层士绅创造并享有、官方控制教育、以政治教化为导向的正统文化,其主体内容是六经三史和载道文学;二是普通民众创造并享有、在民间自然生长、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民间文化,内容包括民间文艺、风俗信仰等。自古以来,民间文化都处于被正统文化轻视、贬抑乃至遮蔽的境地。对此,顾颉刚曾感叹道:“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民间文化史料的严重匮乏,让他在研究国史的过程中常常“感着痛苦”。(3)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5期,1928年4月17日。与其类似,董作宾也慨叹“中国两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4)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民间文艺》第1期,1927年1月1日。此类言辞虽不免激烈,但却切实地揭露了传统文化崇雅鄙俗的典型特征。
自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民主、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传统文化领域内正统与民间的分野以及由于正统文化的专制权威而导致的民间文化的失语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学人心底的普遍纠结。正是基于这种纠结,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胡适为首的新派学人开始大力倡导平等的学术理念,以期破除独尊正统文化的陈旧观念,引导学人摆脱以贵族文化和圣贤文化为学术中心的桎梏,发掘“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室之中”的民间文化传统。(5)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5期,1928年4月17日。
1923年1月,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全体同仁撰写发表了指导整理国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下文称《发刊宣言》),在这份旨在阐明国学门所持之新原则与新方法的宣言书中,胡适将平等的学术理念明确规定为研究者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该文中,胡适指出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是清学的绝大缺憾,有鉴于此,“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认清整理国故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他强调:“过去种种,上自思想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6)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5、11、14页。可见,整理国故运动要求打破一切狭陋的门户成见和雅俗分野,主张整理和研究一切过去的思想文化。同时,胡适还专就古典文学的研究谈到:“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整理国故派的眼中,“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7)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13页。此番宣言有力地打破了自古以来文人学士轻视民间文学的陈见,将以歌谣、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圣人文章、诗赋古文等正统文学一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突显了平视雅俗的学术理念。作为一份代表国学门同仁全体意见的学术宣言,(8)胡适在1922年11月9至15日的日记中写道:“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882页。胡适所彰显的平等的学术理念自然也得到了国学门同仁的共认。
揆诸史实可以发现,在这份宣言正式推出之前,平视雅俗的研究眼光已在北大校园内初步酝酿成形。无论他们在文学观念、思想倾向抑或政治立场上有何分歧,以平等的眼光观照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研究理念却得到了一致认可。以北大文科教授朱希祖为例,在文白之争中,由于文学观念稍显保守,他被新文学的支持者斥为“凡庸的折衷派”。(9)郑振铎:《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4页。然而就学术研究而言,早在1919年3月,他就已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先秦以来的文献典籍,“一概须平等看待,高文典册与歌谣小说一样的重要”。(10)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这与胡适在《发刊宣言》中的相关表述可以说如出一辙,有研究者即认为朱希祖此言是前引胡适所论之“雏形”。(1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不仅如此,这种平视雅俗的治学取向还在北大文科教授的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落实。以小说研究为例,早在1918年前后它即进入北大文科诸教授的学术视野。1917年底至1918年初,国文门研究所多次召开“小说科研究会”,(12)1917年11月底成立的国文门研究所是国学门的前身,成立后由于组织涣散,无甚成绩,于1921年初进行改组,经过一年的重建,最终于1922年1月17日正式改组为国学门。专门商讨小说研究的相关议题。在1917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刘复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小说由来虽久,以缺乏系统的研究,故进步殊形沮滞,今研究所中既设此小说一科,即当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13)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3页。这也意味着历来为文人学士所不屑于言道的小说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一门现代学术研究的主题。(14)唐德刚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曾指出:“把小说当作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笔者认为此论有失偏颇。从正文所举史实即可见出,早在胡适开始小说研究之前,刘复、周作人即已在北大国文门研究所成立小说科,有意将小说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问引入高等学术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刘复和周作人的意见还直接启发了胡适小说考证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周作人所谓:“研究小说不外历史的或个别的二方面。就一国之小说,沿流溯源,自始至终作一系统的研究,乃历史的方面;专就一书或一人或一时或一派而研究之,则入于个别的方面也。”再如刘复所论:“研究之结果宜作为论文式札记。札记不择体例,随读随作,涉及细微均录入。至于论文,或就一钜作寻其理绪,或联合一派辨其因迹,如红楼梦一书,篇页至繁,大可统其全书,单独作为一文;又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性质大致相同,可综合其性相而论次之。”具体就札记而言,刘复还主张其中应包括小说的“篇幅体材”“作者小传(或附以所处时代之文学状况)”“全书事实”等。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诚然胡适小说考证的工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创建新范式的意义,但是,小说正式成为一门现代学术研究的主题是在1917年底北大国文门研究所成立之时,远早于胡适的小说考证。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434、1433页。凡此可见,在国学门正式建立之前,以平等的眼光对待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研究理念已是许多趋新的北大学人的共识。
经由《发刊宣言》的宣告,雅俗平等的学术理念正式成为指导整理国故运动的基本原则。在它的烛照下,国故的范围被拓展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歌谣、小说、民间故事、风俗、信仰、方言等无所不包,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以经书为主体的文献典籍,而成了“全世界的事物”。(15)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京报副刊》第147期,1925年5月13日。凡此从北京各学术机构藏书的变化中即可见一斑,此前经史子集四部“就笼罩了书籍的全体”,但在平等眼光的绳墨下,北大国学门、故宫博物院、孔德学校等机构于四部典籍之外,广泛搜罗了明清档案、碑碣拓本、佛像照片、民众文艺、家谱等材料,在京师图书馆内,最为学人仰望的也不再是四库全书,而是敦煌宝卷和明清两代的地方志。(16)顾颉刚:《国立广州中大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民国日报》1927年8月10日。在这种情势下,一股乐观、新鲜的研究热情弥漫学界,顾颉刚即热情洋溢地表示:“从前人的研究的范围又极窄隘,留下许多未发的富源,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17)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这里“新的眼光”所指无疑就是平等的眼光。其实,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国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彻底摆脱了历代学人独尊正统文化、鄙薄民间文化的窠臼,彰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包容的研究理念。
二、扬俗抑雅:雅俗平等学术理念的走向
整理国故运动对平等学术理念的提倡乃是针对鄙俗的偏见而言的,这一点在顾颉刚为《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体现得尤其清晰。该文开篇就谈到,社会大众在国学门陈列馆参观时很自然地就能感到鼎彝和朝廷诏谕的“名贵”和“尊严”,而对风俗史料和歌谣表示出“轻蔑的态度”,为此,顾颉刚感到有必要重申“学术平等的观念”,他再次强调:“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18)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由此可见,整理国故派提倡学术平等观念的根本原因和直接目的就在于祛除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崇雅鄙俗的陈旧观念。
这一目的决定了整理国故派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倾向性,即他们虽则宣称平等地对待正统文化和民众文化,表面上似无意于厚此薄彼,然落实到具体研究的层面,却明显偏重于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史料,在史料诠释的价值取向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关怀和坚定的民间立场。就像梅光迪所观察到的那样:“一切主张,皆以平民主义为准则。”(19)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罗志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即广泛地发掘、整理长久地被排斥、遮蔽的民间文化传统,相对冷落原本处于正统和中心地位的经史典籍,他认为:“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20)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诚如其所言,整理国故派为彻底改变传统文化中崇雅鄙俗之旧习,在消解正统权威,表彰民间价值与地位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崇雅鄙俗的反面——扬俗抑雅。通常而言,他们认为民间文化比正统文化更能反映时代精神面貌,因此也更值得保存和研究。比如1922年顾颉刚在谈论中学国史教科书的编篡问题时就明确表示,编写国史者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各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因为在他看来,谚语、歌谣、野史笔记等“出于民众”,是民众的“实话”,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民众的生活,不像“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记录只是为了“敷衍门面”,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时代状况。故此他强调,为了真正地“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切实地“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编国史者必须将研究视野从庙堂下移至民间。(21)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20日。1924年他再次申言:“前人为学,偏信纸片之记载,偏护贵族之身分,不能发见社会真象,为矫正此偏畸之习惯计,故吾人努力搜求活的材料,以期了解各种社会之情状,尤其注意于向来隐潜不彰之下级社会之情状。”(22)顾颉刚:《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说明书》,《宝树园文存》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页。与顾颉刚精神相通,刘复也提出古本《尚书》只能帮助学人“在经解上得一些小发明”,而几首民间小唱却能帮助学人“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史,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他还因此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歌谣运动。(23)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3期,1925年10月28日。凡此可见整理国故运动有意搁置经史正典,侧重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传统的偏向。
扬俗抑雅的价值取向催生了研究视角下移的学术风气,其时趋新学人普遍将眼光从上层贵族的文化传统转移至了民间文化传统。朱光潜曾对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研究视野作过这样的概括:“数千年来,吾国学者所孳孳不辍者,首在穷经明义理,次则及于历史与周秦诸子,行有余力,乃旁及集部,习辞章以为言学应世之具。”(24)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9页。确如其所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思想学术世界由经史子集四部所囊括,而且经史子集四部不止是学术类别的划分,更是学术等级由高到低的排列,其中经学为一切学术的中心和皈依,占据传统学术的最高点。由此出发,传统读书人反复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便主要集中于经史典籍,行有余力方习作辞章,而且修炼文辞本身并非辞章学的目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穷理言学。这表明对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正统文化的注解、传承与维系构成了传统读书人学术世界的全部图景。在这幅图景之下,下层民众创造和享用的民间文化因其思想、趣味、形式等各方面均与正统文化截然异趋而被传统读书人鄙夷、排斥。大致就如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所谈到的:“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25)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页。以文学研究为例,传统经学的权威衍生出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主要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和古文,其功能是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以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为文学评价的主要标准。基于此标准,崇尚雅正的正统文人对鄙俗淫哇、滑稽恶趣的民间文学深恶痛绝、避恐不及,且视兴于民间的戏曲、小说为“君子弗为”之“小道”,至于野夫村妇口头流传的山歌民谣则更是不值一哂。对此,朱自清曾经描述道:“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26)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iv页。
这一情况在近代中国略有改变,梁启超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著名命题,(2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文集之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7页。并掀起“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风潮,黄遵宪发起“诗界革命”,提倡“我手写吾口”,积极辑录整理民间歌谣。这些举动让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要注意的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提倡更多是出于开启民智的教化目的,对民间文学本身的价值并无多少认可,故此时民间文学并未成为一门学术研究的主题,晚清的读书人也甚少对民间文学加以严肃认真的研究,他们的文学史眼光仍然局限在以经史子集为框架的正统典籍内,或认为小说戏曲为“民间无学不识者”作,斥其“识见污下”,(28)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上海:科学书局,1914年,第182页。或“以诗文为主”而仅以“词曲、小说为从”,(29)曾毅:《中国文学史·凡例》,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第2页。至于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更是丝毫未尝提及。所以朱自清说此时“俗文学”虽然“升了格”,但“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30)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第iv页。
直到学术平等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可和有意强调后,这些原本被鄙视为“小道”“异端”的东西才有资格得到与传统经学、史学一样严肃郑重的研究,即如顾颉刚所言,真正意义上以“学术的眼光”去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化是从这时开始的,“这种事情,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31)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续)》,《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11期,1925年12月23日。凡此从国学门的机构设置和学术实践中即能见出。国学门下设五个学会,除明清史料整理会和考古学会以外,其他三个学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均专为民间文化研究而设。而从国学门机关刊物刊载的文章来看,《歌谣》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发表民间文艺研究成果的园地。至于《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这两大综合性刊物所刊载的文章也以民间文化研究为绝对主体。自1925年10月14日创刊至1926年8月18日停刊,《国学门周刊》共出版二十四期,除启事、通讯、学术界消息等杂录外,刊文共计161篇,其中民俗类81篇,占全部稿件的一半。1926年10月,由于经费问题,《国学门周刊》改为《国学门月刊》,自1926年10月至1927年11月,月刊断断续续推出八期,除读者来函、学术界消息等杂讯外,共刊文92篇,其中民俗类34篇,较之周刊数量和比重虽有所降低,但仍远胜训诂、考古、历史等其他类别。(32)有关《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刊发文章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09-219页。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策源地和主阵地,国学门明显偏重民间文化研究的治学取向颇能反映该运动扬雅抑俗的整体走向。
在研究视角向下转移的学术背景下,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化传统首次得到了有组织、大规模且系统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诸如顾颉刚对吴歌和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刘复、董作宾对歌谣的整理和研究,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对古典小说的考证,茅盾、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北大风俗调查会组织的妙峰山庙会调查等,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些研究都作出了极具学科奠基意义的贡献,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史料观变革与文学史料范畴重构
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也即对民众生活和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其时文史学者对于史料的范围、判断标准、包括内容等问题有了截然不同于传统读书人的回答。新文化派学人一致认为,记载民众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史料比王公贵族的传记资料更能展示真实且完整的历史面貌。(33)1919年9月,杜威夫人在题为《历史学的研究》的演讲中基于“真正的历史,就是全体人类的生活”的认知,提出:“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不是仅仅记得几个人名地名年代的,这样的历史乃是死历史。我们所需求的是新的活历史,我们所谓的活历史,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动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的,乃是要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的。”杜威夫人看民众生活材料重于英雄传记的观念对随后整理国故运动中研究者历史视野由上至下的转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见杜威女士讲、志希笔记:《历史学的研究》,《神州日报》1919年9月13日。因此要想建构全面真实的中华文明史,必须摆脱传统史家对官方正史的依赖,转而“调头去请教那些‘民间的文献’”。(34)钟敬文:《江苏歌谣集序》,《民众教育季刊》第3卷第1号,1933年1月31日。在他们看来,正史只是极少部分王公贵族的“家谱”,内容偏狭且充满伪饰,并非可以代表时代真貌的史料;反观民间文献,不仅记载的是作为社会主体构成的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且毫不讳饰、真诚可靠,故尽可能多地掌握民间史料,就能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揭发全民众的历史”。(35)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5期,1928年4月17日。由此可见,趋新学人实际上是以流行范围的广狭作为择取史料的标准,认为广泛流行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中间的思想和文化才是历史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史料,而那些仅占人口极少数的王公贵族的生平事迹不应再占据史书的中心。(36)如胡适就曾以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为例指出:“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他甚至明确表示后者才是“真正史料”,至于传统的“谨严的史传”抑或“痛快的论赞”都是“一个钱不值的”。见胡适:《中古文学史概论序》,《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261-262页。
就文学史料而言,在研究视角下移风气的影响下,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广泛流行于平民百姓之间的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紧密,影响范围也更广泛,相较于正统诗文而言,它们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郑振铎就曾明白地指出:“三五篇”俗文学作品比“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生活”。(3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0页。郑振铎此言颇能代表时人共识。胡适也表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史料“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38)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页。由此出发,他们对中国文学史著的史料范畴作了大幅调整。
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著以经史子集为取材范围,林传甲、曾毅、王梦曾、谢无量等都是从四库典籍中搜寻与文学史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范围内,词曲既已“厥品颇卑,作者弗贵”,(3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十)》卷一百九十八·集部五十一·词曲类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0页。戏剧、小说则更是无迹可寻,更遑论诸宫调、弹词、宝卷等文学体裁。《四库提要》斥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的论调一直深刻影响着最早的那批文学史作者。(4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十)》卷一百九十八·集部五十一·词曲类一,第41页。窦警凡在《历朝文学史》中称“曲则其品益卑”,(41)转引自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6期。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斥元之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文格日卑”,视小说戏曲为下等社会的“淫书”,而不予叙录。(4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181-182页。进入民国后,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传播的深入,王梦曾和曾毅的文学史虽不至完全排斥小说戏曲,但也声明它们只是诗文之“附庸”,王梦曾更直言其对宋元白话诗词文的讲述不过是为了“博读者之趣”。(43)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编辑大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2页。至于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著的集大成者——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在1918年出版时,这种偏重经史典籍和古典诗文、轻视民间文学的择取史料的倾向仍未改变。谢无量虽在《绪言》中畅言宋元以降“不尚文雅”“苴弃德义”的“平民文学”逐渐蔚为大观的趋势,(4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38页。但在具体书写中仍偏重古典诗文,对其视为近古以来文学史之“大势”的平民文学只用寥寥数语略过。
及至学术平等的理念引起史料观向下的变革之后,中国文学史著才将选取史料的重心从上层转向民间,文学史著的史料范畴也因此重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基于平等的眼光重构史料范畴的典范之作。在引言中他自陈出版该著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45)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第3页。批判的锋芒直指早前出版的基于精英立场专叙古典诗文的中国文学史。在该著中,他反复申言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史之所以“能有一点生气”,“能有一点人味”,“全靠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强调以白话为载体的民间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中最有活力和价值的部分。(46)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3页。基于此,胡适将研究视野重点放在了长久以来被庙堂文学遮蔽压抑的民间文学上,兼及文人极力模仿民间文学创作的平民化文学。与此同时,鉴于民间文学史料历来不受重视,史料保存较少,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用大量的篇幅抄录原文,且通常都是全文征引。此举不仅向读者直观地展现了民间文学传统的原貌,更是保存民间文学史料的有益尝试。胡适保存和标举民间文学史料的成功示范推动了民间文学入史风气的形成,广泛地搜罗、排布、扩充民间文学史料成了其时文学史家的自觉意识。民间文学自此成为中国文学史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一个时期文学史的讲述倘若缺少民间文学史料即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换言之,民间文学史料的存缺、多寡在当时成了一条衡量文学史著优劣的重要标准。例如胡云翼在评述1930年代以前出版的多部《中国文学史》时就指出: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虽“自有见解,行文隽美”,但可惜“只叙及文人方面的文学,而忽视最有价值的民间文学”。他还批评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虽“叙述周密,持论平允”,却稍嫌“忽视民间文学的发展”,不能叫人满意。(47)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北平:北新书局,1933年,第3-4页。
不仅如此,历史地看,民间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还呈现出层次逐步深入、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1920年代文学史家关注的民间文学史料大多是乐府、戏曲、小说等体裁。进入1930年代以后,神话、笑话、寓言、宝卷、传奇、鼓子词、诸宫调、弹词、双簧等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开始进入文学史,民间文学史料的类型和范围得到了更广泛的扩充。这一点在郑振铎1932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表现得很清楚。在《例言》中他谈到,以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往往取材范围过狭,“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他认为“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于诗文、词曲、小说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民间文学天地,诸如“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4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北平:北平朴社,1932年,第1-2页。这些民间文学在以往出版的文学史书中都是缺席的,郑振铎称这种缺席是“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他愤懑地表示:“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罪臣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4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第1-2页。为此,郑著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网罗了佛曲、变文、诸宫调、宝卷、全相平话、弹词、大鼓、皮簧、滩簧等从未被中国文学史著注意的史料,并且为尽量全面地搜罗民间文学史料,他还远赴伦敦、巴黎查阅抄录相关的敦煌写本。郑振铎对民间文学史料苦心孤诣的搜求使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成为了当时民间文学史料类型和内容最为丰赡的一部中国文学史。鲁迅称其“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50)鲁迅:《(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可谓一语中的地点出了郑振铎以人弃我取、人略我详的态度广泛搜集民间文学史料的治学取径。其后,不仅词曲、戏剧、小说这些被正统文人斥为“小道”的文学体裁登堂入室,就连以往完全不入正统文人视野的诸宫调、宝卷、弹词、皮簧等也正式成为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统览1920—19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可以发现,在走向民间的文学史书写风气下,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民间文学史料得到了全面发掘,“活的民间诗歌、故事、历史故事诗、一般故事诗、巷尾街头那些职业讲古说书人所讲的评话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堆数不尽的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那无数的男女,在千百年无穷无尽的岁月里,却发展出一种以催眠曲、民谣、民歌、民间故事、讽喻诗、讽喻故事、情诗、情歌、英雄文学、儿女文学等等方式出现的活文学。这许多[早期的民间文学],再加上后来的短篇小说、历史评话,和[更晚]出现的更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等等”,(51)《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丰富的民间文学史料使得中国文学史著得以超越早期为经史子集所囿,以古典诗文为宗的促狭格局,通过对民间文学史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使之呈现出更为纷繁生动的文学史景况。自此以后,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史料正式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民间文学专题史的研究也蔚为大观,并最终推动了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