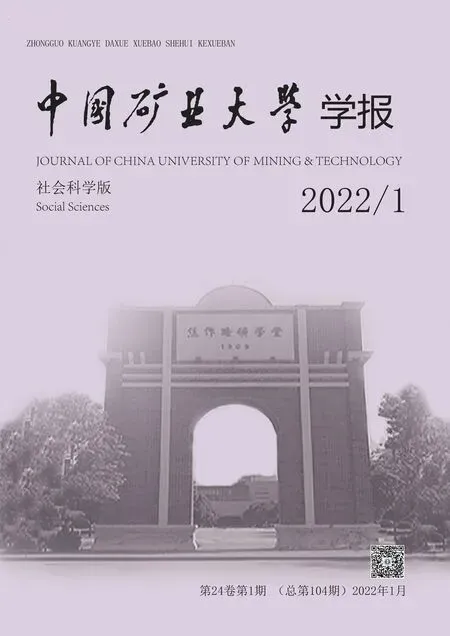国外简·奥斯丁小说的认知文学研究评析
2022-11-23杜坤
杜坤
21世纪以来,伴随跨学科研究和认知理论的蓬勃发展,认知视角的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强劲发展态势。由于奥斯丁小说的叙事技巧与认知理论高度契合——“敏锐地观察到人与人之间是如何进行心智互动的……她的见解经常与当前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同步”①Beth Lau,Jane Austen and Science of the Min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8,p.3.,她迅速成为“从认知视角分析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②Beth Lau,Jane Austen and Science of the Min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8,p.1.。对奥斯丁作品的具体研究视角从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到神经认知诗学(Neurocognitive Poetics)等不一而足。
迄今,国外已有两本专著问世,贝丝·劳(Beth Lau)的《简·奥斯丁与心智科学》(Jane Austen and Sciences of the Mind,2018)和温迪·琼斯(Wendy Jones)的《大脑中的简》(Jane on the Brain,2017),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角度解读奥斯丁的全部作品。琼斯书中的十二篇文章,分别对奥斯丁小说中人物的内在洞察力、情感控制、防御机制以及人物之间的情感共鸣、情感依恋和支持、情感调节等方面进行讨论,重点关注了读者对人物的移情和人物自身的移情体验,来“证明奥斯丁描写人性的准确性”①Wendy Jones,Jane on the Brain: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Social Intelligence with Jane Austen,London&New York:Pegasus Books,2017,p.XVIII.。贝丝·劳的专著收录的十篇文章分别阐释了人物的读心(mindreading)、心盲(mind blind)、心智弹性(elasticity of mind)、心智时空之旅(mental time travel)、认知停顿(cognitive pause)等心智科学现象,为理解和阐明小说的关注点、技巧和持久魅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已然受到研究者们极大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散见于相关认知文学研究专著或期刊中。这些“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洞见能增强我们对奥斯丁的理解,同时她的小说也提供大量详细、微妙的大脑运作信息以丰富科学发现。”②P.C.Hogan,How Authors'Minds Make Sto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xiii-xiv.本文旨在梳理分析国外学者对奥斯丁作品的认知文学研究成果,从具身体验、虚构心智、文学达尔文主义和神经认知诗学四个视角解析国外学者在研究方法、理论视角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并评估当下研究的不足,以期对未来研究有所启发,进一步拓展奥斯丁作品研究的批评空间。
一、具身体验与语言表达
读者和评论家历来特别关注奥斯丁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尤其是人物的意识、想象与身体表达。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考察小说主题,当前以具身体验为视角的研究主要观察身体与意识、情感的关系:奥斯丁对意识、情感等的表达体现了偏向心智体验性的趋势——注意思维、大脑和神经系统在感官网络中的相互作用。以《爱玛》(Emma)为例,有许多评论家同意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观点,认为《爱玛》不仅是一部心理小说,还是一部通过“感知的主客观模式对比”③Marilyn Butler,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264.来怀疑想象、批判爱玛内心世界的作品。研究者们还注意到“奥斯丁将身体反应作为道德判定标准”④Marilyn Butler,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293.,尤其心理世界的反应如何延伸到身体层面⑤John Wiltshire.Jane Austen and the Body:The picture of heal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艾伦·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指出,在《劝导》(Persuasion)中,奥斯丁从生物学和先天角度展现了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与那个时代的脑科学研究相一致,并在某些方面领先⑥Alan Richardson,''Of Heartache and Head Injury:Reading Minds in Persuasion'',Poetics Today,No.1,2002,pp.141-160.。不同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脑科学理论,小说中的描述更强调的是人物之间使用非语言表达来交流,也就是超语义的身体交流。具体展现为:奥斯丁在描写段落和间接话语片段之间自由穿梭,不仅传达了意识的流动,也传达了意识的消逝。除此之外,凯·杨(Kay Young)聚焦于小说中语言如何将人物意识表征成自我意识情感,尤其是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的自我意识充分体现在第23章中。弗雷德里克给安妮的信用现在时书写,大量使用“must”祈使句,“体现了弗雷德里克当下的具身依恋之情,而且是一直都有的感觉,它所展现的语言情感的深度是持久的,而这种情感在奥斯丁其他作品的书信中大多没有体现”①Kay Young,Feeling Embodied:Consciousness,Persuasion,and Jane Austen,Narrative,2003(1):78-92.。这种情感体验的过程是人物从外部感知并意识到情感概念再到认同的过程,进而引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可以说,在《劝导》中,奥斯丁转向了具身认识论,创新了对主人公印象的表达方式,既体现了对无意识心理活动和具身认知的新认识,也展现了一种表达意识体验变化的新模式。
研究表明,奥斯丁在《劝导》中展现的人类主观意识的体验方法并非偶然,而是她的一贯视角。例如,表达意识的语言选择和对他人心理状况的归因判断分析在《爱玛》中已然出现,并与体验主观性的早期观点类似。由于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到奥斯丁对心理学和社会戏剧(social dramas)的兴趣,却没有考察她探索具身心智的兴趣,因而也忽略了《爱玛》通过语言选择、隐喻性描述意识和情感等复杂概念时展现的矛盾心理”②Antonina Harbus,Reading Embodied:Consciousness in Emma,SEL,2011(4):765-782.。这说明在《爱玛》中,奥斯丁为解决具身意识和情感物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然做出了一些尝试。她对内在意识的分散性描述反映了彼时心理学观点、道德修辞(moral rhetoric)等一些流行观点的复杂多样背景,特别是隐喻表达,暗示了心智在根本上是基于具身体验的。例如凯·杨主张“奥斯丁描写爱玛有一种不构成主体的主观性、一种不受其他思想支配的思想、一种不受理解他人想法的冲动支配的思想”③Kay Young,Imagining minds:the neuro-aesthetics of Austen,Eliot,and Hardy,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0,p.32.,从根本上定义了她独特内在的想象力,也就是她的一种自我意识。“爱玛思维能力的两种形式——创造意义的作家和预言未来的预言家——都定义了一种想象叙事的自我意识。”④Kay Young,Imagining minds:the neuro-aesthetics of Austen,Eliot,and Hardy,p.45.爱玛最终认识到身边的世界,不是她的设计,也不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从以想象为基础的自我意识转变为以经验为基础的“延展意识”(extended consciousness)⑤Kay Young,Imagining minds:the neuro-aesthetics of Austen,Eliot,and Hardy,p.48.。
琼斯注意到,除了思维和情感的隐喻表达,《爱玛》中也包含了很多视觉隐喻。虽然视觉词语无法把爱玛与视觉本身联系在一起,但视觉作为一种感知,“就是理性、智力和理论的转喻”。“对感知的性别化(和非性别化)的历史主义解读与神经科学的范式相重叠,并且后者肯定了奥斯丁将移情理解为一种基本的、中性的(gen⁃der-neutral)感知机制”⑥Wendy Jones,Emma,Gender,and the Mind-Brain,ELH,2008(2):315–343.。爱玛学会移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自省的,同时爱玛试图唤起读者的某种反应,也将感知和反应的过程具身化。除了视觉隐喻,“《爱玛》和《劝导》是研究非语言交流和面部表情的代表作”①Alan Richardson,Facial Expression Theory from Romanticism to the Present.Lisa Zunshine(ed.).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pp.65-83.。也就是说,奥斯丁讽刺性喜剧小说的特色就是使用非语言交流,通过肢体动作来揭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从而读者可以体悟其中所蕴含的情感。
“18世纪的情感叙事往往取决于人物对情感的投入,包括人物自己的情感投入和对他人的情感投入。”②Joel P.Sodano,Semblances of Affect in the Early English Novel:Narrating Intensity.Stephen Ahern(ed.),Af⁃fect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A Feel for the Text,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9,pp.65-82.在《爱玛》中,女主人公爱玛意外坠入爱河,意识到自己对奈特利先生的感情时呈现出一种虚拟感觉,从而激发了自我认知。在这样的时刻,叙事被情感强度所束缚,“情节的推进变得缓慢,描述变得厚重,专注于捕捉受影响身体的手势和颤抖(tremulations)”③Stephen Ahern,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Affect Theory Reads the Age of Sensibility,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2017(3):281-294.。而《诺桑觉寺》中呈现了另一种情感形式,即对“失望”的体验:一种具身的、情感跌落的体验。主人公凯瑟琳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虽然期望通过浪漫幻想重新塑造精神和身体活动,但情感弧大幅下降,经历了令人不安和沮丧的情感冲击。那么,读者如何体验这种“失望”,也就是“失望阅读(disappointed reading)的社会性”以及“奥斯丁对失望感受的判断是如何影响读者的”④Carmen Faye Mathes,Reading and the Sociality of Disappointing Affects in Jane Austen.Stephen Ahern(ed.),Affect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A Feel for the Text,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9:85-103.,都是她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以及对读者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一种具身表达。
这些研究还具有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折射出在奥斯丁创作时期,英国人对思维意识与身体关系的看法正在发生转变:个人的思想品质到底是教育和社会经验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先天的生物学和遗传因素,奥斯丁也显然受到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争论的影响。正如认知文学研究者所讨论的,奥斯丁在创作中对心智的书写(隐喻表达、自由话语、“身体”描述等)、理解和体验似乎表明她接受了生物学的观点,也认可了在人类现实经验中身心关系的普遍观点,暗示了心智在根本上是基于具身体验的。尤其是奥斯丁的后期作品更为全面地展示了心智的生理基础概念,揭示出“现代的、后笛卡尔式的整合心智概念——认知的、情感的、具身的、关联的(relational)”⑤Kay Young,Imagining minds:the neuro-aesthetics of Austen,Eliot,and Hardy,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0,p.4.。
二、虚构心智与叙事技巧
据国外学者统计,“心智”(mind)一词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出现了160次,在《爱玛》中出现了135次,在《理智与情感》中出现了104次,在《诺桑觉寺》和《劝导》中各出现了69次,在《傲慢和偏见》中出现了64次①Tarpley,J.K.Constancy and the Ethics of Jane Austen's Mansfield Park.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10,p.57.。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心智”在奥斯丁小说中所占的分量。国外学者特别强调奥斯丁作品中“思想的、言语的两种自由间接表征形式用于不同的目的”②Wolfgang G.Muler,Irony in Jane Austen:A Cognitive-Narratological Approach.Jan Alber&Greta Olson(eds.),How to Do Things with Narrative.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018,pp.43-64.,认为她对自由间接话语(FID)的使用是对虚构心智物理特殊性的考察:“FID不是进入他人思想的手段,而是一种检查自己的工具”③Angus Fletcher&Mike Benveniste.A Scientific Justification for Literature:Jane Austen’s Free Indirect Style as Ethical Tool,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2013(1):1-18.等等,这些从认知叙事学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都将作品对虚构心智的建构研究推向纵深,尤其是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和认知叙事学的结合研究,表明奥斯丁对虚构人物心智的创新书写不仅揭示了她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兴趣,也不仅只是“对18世纪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心智思想的编码”④Merrett,Robert James.''The Concept of Mind in Emma'',ESC,1980,No.1,pp.39-55.,而是更全面地反映了她如何创新地将“心智”表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叙事特征。
乔治·巴特(George Butte)认为18世纪的英国作家已经开始描绘人物的多层次且相互反映的主观性,即深层主体间性(deep intersubjectivity)。在笛福、菲尔丁等人的小说中,人物“与他人的接触从来没有超越两层的‘交换’,而是涉及多重的判断和感知”,在奥斯丁描绘的场景中,“观察的观察”表达了“一种塑造叙事的新方式”⑤George Butte,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Know:Narrating Subjects from Moll Flanders to Marnie,Co⁃lumbus:The Ohio University Press,2004,p.59.。从这个角度看,奥斯丁的作品在虚构心智建构方面具有深刻创新。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同意巴特的探索:“把他的讨论放在认知理论的背景下,可以说他指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关键点:(18世纪晚期)虚构主体的塑造从心智嵌入的第二、第三层次发展到第三、第四层次,作者(奥斯丁)完成了这一转变。”⑥Lisa Zunshine,Why Jane Austen Was Different,And Why We May Need Cognitive Science to See It,Style,2007(3):273-297.巴特的研究没有建立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但他的论证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在许多方面也与认知文学批评所依据的理论立场是相容的。
在巴特的研究基础上,詹塞恩引入心智理论,对小说中深层主体间性模式产生的层次化场景和虚构人物心智做了极好的解读。将心智理论引入作品分析,使得读者愈加关注文学人物潜在的欲望、意图和感受。由于人物心理状态的归因模式是由元表征能力决定的,“对元表征的研究也有助于读者对文学叙事‘真实’问题的持久关注,以及对‘历史’与‘虚构’的区分”⑦Lisa Zunshine,Why We Read Fiction: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11.。例如《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开篇第一句话的讽刺效果就来自于它作为表征和元表征之间的博弈,激活了读者两种不同的信息处理策略。在人物思维结构明显完成之后,将额外的“心智叠加”(mind plus)①Lisa Zunshine,Mind Plus:Sociocognitive Pleasures of Jane Austen's Novels,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09(2):103-123.到场景上的策略也是奥斯丁叙事创新的另一个标志。这是构建有洞察力的女主人公的一种叙事方式——“她”就是添加在这个看似完整场景的核心要素。除此之外,詹塞恩认为“具身透明性(embodied transparency)也是运用‘读心’(mind reading)解读小说的众多方式中的其中之一”②Lisa Zunshine,Getting Inside Your Head:What Cognitive Science:Can Tell Us about Popular Cultur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24.,通过身体语言读心可以不断地减少误读的可能性。例如达西第一次求婚,伊丽莎白感到“糟透了”(dreadful),在这种时刻,她依然能看出达西努力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震惊,但是在此刻产生的透明度是相当短暂的。
与詹塞恩研究领域相似的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也一直致力于研究虚构心智和叙事技巧的关系。他指出“奥斯丁充分创造虚构意识假象的能力常常被视为她的标志性叙事技巧”③Alan Palmer,The Construction of Fictional Minds,Narrative,2002(1):28–46.。在研究《爱玛》时,他认为重建爱玛虚构心智的活动和理解虚构心智所处的叙事范围的活动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不同心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成功地将其理论化,以及如何将目前存在于其他领域的理论整合到一个新扩展的虚构心智叙事学中,他在《虚构心智》(Fictional minds,2004)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详细阐释。帕尔默还将经典叙事学以及言语范畴(The Speech Categories)与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等理论视角结合起来,以《爱玛》和《名利场》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分析虚构心智时,既要关注虚构心智的传统内在层面,也要关注心智运作的故事世界的社会和物理语境。进而,他在《小说中的社会心智》(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2010)中构建了一个考察特殊虚构心智的理论框架,即连续意识框架(continuing-consciousness frame),并在框架内分析了《劝导》中安妮的社会心智如何在故事世界的心际网络(intermental network)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展现了安妮心智的心际本质。
理查德森赞同詹塞恩和帕尔默关于奥斯丁发展了表征意识的新叙事技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奥斯丁对深层主体间性的创新性描述置于浪漫主义时代语境中,分析了《爱玛》中人物展现的一系列人际行为。理查德森认为奥斯丁将人物置于一种迫使他们反复猜测对方意图、信念和情感状态的情境中,展示人物普遍依赖社会认知策略。为了“读”彼此的思想,他们必须特别注意彼此的身体——“眼睛、面部表情、手势、声调和血液在皮肤下的运动以及监控自己的‘内在’的感觉(intero⁃ception)”④Alan Richardson,The Neural Sublime:Cognitive Theories and Romantic Text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p.81.。霍根(P.C.Hogan)更进一步指出,在《爱玛》中,奥斯丁不仅错误地模拟了人物的思想,她也模拟了读者对这一过程的模拟,从而可以分析出读者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误解人物未被揭露的内在想法。“这些复杂的模拟引导着奥斯丁对叙事的细化,使得整篇作品极有可能达到她所期望的情感效果。”①P.C.Hogan,How Authors'Minds Make Sto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26.
然而,娜塔莉·菲利普斯(Natalie M.Phillips)则认为,“丽莎他们倾向于从微观方法分析多个片段或段落。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多重人物的相同时刻,它们的作用似乎截然不同……奥斯丁创造的人物网络,不是为了模拟多重主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mutuality and reciprocity),而是为了争夺叙事空间和认知丰富性的稀缺资源。小说中的主体间性(以及相互观察的交流)场景,展现了一种明显的反互惠的(anti-reciprocal)、主体内在性的人物塑造过程”②Natalie M.Phillips,"Distraction as Liveliness of Mind: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haracterization in Jane Aus⁃ten",Paula Leverage,Howard Mancing,Jennifer Marston William&Richard Schweickert(eds),Theory of Mind and Literature,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11,p.105.。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巧妙地调整她的叙述,用玛丽的死板执著和精神上的麻木凸显伊丽莎白的敏捷,用以加大读者的注意力跨度,使得读者对伊丽莎白的探索意识产生了范围和深度上的错觉;同时通过精心设计的分散注意力的场景来展现伊丽莎白的创造性活力,使得人物之间的含蓄对比能够迅速传达,进而使读者也可以捕捉伊丽莎白的认知敏捷性与心智活力。
综上所述,当前国外学者对奥斯丁作品中虚构人物心智的叙事表征研究与以往评论家们注意到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对比③Christopher Brooke,Jane Austen:Illusion and Reality,Woodbridge&Suffolk:D.S.Brewer,1999.,或是人物“认识到概念和真实之间的差异从而进行自我认知”④Thorell Tsomondo,Representation,Context and Cognition;and Jane Austen,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985(64):65-75.的观点大不相同。认知科学的视角,如“心智理论”的引入,更进一步帮助读者对虚构人物意识活动的理解以及对作者叙事技巧的进一步阐释。可以说,奥斯丁对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叙事关注和人物“读心”意识的目的感的清晰描述,不得不使我们把她“看作一位早期的心智理论学家”⑤Alan Richardson,The Neural Sublime:Cognitive Theories and Romantic Text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p.81.。
三、文学达尔文主义与文化语境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以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将“人性”即代表人类典型特征的动机和情感作为核心思想与研究对象。其代表人物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教授曾多次戏称《傲慢与偏见》在文学史上就像一只果蝇,如科学家发现果蝇是研究遗传学的优秀物种一样,文学达尔文主义批评家也发现奥斯丁的作品是进行认知进化研究的优秀语料。文学达尔文主义研究者将奥斯丁的作品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和基本的进化原则——生存、繁衍、亲属关系、社会活动等方面来解读作品中男女不同的生存和择偶策略,女性在一夫一妻制伴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物性格如何根据所处文化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同时,研究者们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关注作者—作品—读者的相互适应关系,旨在揭示由文本体现的社会-文化关系,促使进化人类学家意识到文学的实证研究为解决心理学的重大问题指出了新路径。
卡罗尔以《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等五部小说为语料,分析基本性格(elemental dispositions)、物种-典型性规范(species-typical norms)、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和个体意义结构(individual structures of meaning)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傲慢与偏见》和《德伯家的苔丝》一样,“二者有着普通和基本的动机结构,创造了清晰、完整、连贯的结构意义,呈现出非凡的文体风格用以凸显主题,人物角色也饱含着丰富的人情味”①Joseph Carroll,"Human Universals and Literary Meaning:A Sociobiological Critique of Pride and Prejudice,Villette,O Pioneers!,Anna of the Five Towns,and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Literary Darwinism:Evolu⁃tion,Human Nature,and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2004,p.144.。他还指出《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展现了人类最高层次的意识组织,即对获取资源和成功交配的首要需求的认识,以及与协调认知行为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②Joseph Carroll,"Human Nature and Literary Meaning:A Theoretical Model Illustrated with a Critique of Pride and Prejudice",Joseph Carroll(ed),Literary Darwinism:Evolution,Human Nature,and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2004:185-212.。其他研究者也认为这个观点在《傲慢与偏见》中体现得最为清晰。“从表面上看,《傲慢与偏见》可能显得保守,但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生活中压倒一切的、无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将我们的基因传递下去,那么看似保守的婚姻实际上是解放了。”③Michael J.Stasio&Kathryn Duncan,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Jane Austen:Prehistoric Preferenc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Studies in the Novel,2007(2):133-146.可以说,进化的心理机制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奥斯丁时代人类的心理机制以及文化表达。每个人物都想在进化理论的共识范围内结婚:女人想要男人拥有财富和地位,男人想要女人拥有青春和美貌。但小说中体现个人品质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男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一基本共识,并在性格和思想上具备优秀品质,这就是奥斯丁为女性在进化中取得成功创造的必要稳定性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女主人公的婚姻解放。
如果我们赞同奥斯丁的小说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婚姻解放,那至少表明了她的小说领域是“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性别选择领域:选择伴侣并被选择”④David P.Barash&Nanelle R.Barash,Madame Bovary's Ovaries:A Darwinian Look at Literature,New York:Delacorte,2005,p.23.。女主人公与雌性动物一样,选择伴侣的要求有三个基本特征:“优质基因、品行良好和财产丰厚”⑤David P.Barash&Nanelle R.Barash,Madame Bovary's Ovaries:A Darwinian Look at Literature,p.43.。选择的结果就是与相同或上层阶层的人结合,这种“高嫁”(marrying up)⑥David P.Barash&Nanelle R.Barash,Madame Bovary's Ovaries:A Darwinian Look at Literature,p.45.就是一个普遍目标,甚至可能是一个规则。在选择与被选择的同时存在着同性之间的竞争以及男女之间的竞争,这是人类交配动力的四个核心因素,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任何社会政治语境和环境条件都会影响这四个因素的表达,但是“奥斯丁小说中的生态环境极其稳定,每一部小说都建立在一个良好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群体中,小说开始或叙事过程中都没有受到战争、环境灾难或其他破坏力量的根本性挑战”①Nacy Easterlin,A Biocul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240.,因而交配动力在一系列常规的社会活动中发挥着作用,这些女性人物的选择特征为人类交配动力带来了客观的例证。
研究者将理论与文本结合分析的同时,将现代实证研究方法与进化心理学的发展观点和文学达尔文主义研究相结合,文学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也可以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和线索。卡罗尔团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人物动机、情感、性格特征和婚姻伴侣偏好的模型,用该模型分析一些特定的文学文本和读者对文本的反应,将产生的数据信息量化,用来检验对文本的特定假设,契合了“三个层面上分析文本意义”②J.Carroll,J.Gottschall,J.A.Johnson& D.J.Kruger,Graphing Jane Austen:The Evolutionary Basis of Lit⁃erary Meaning,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10.。他们在问卷中列出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201部英国经典小说中大约2000个人物角色,包括奥斯丁所有作品中的人物。全球519名英语系教师以及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专家对435个人物完成了1470份问卷。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者以《傲慢与偏见》和《爱玛》为例,把研究重点放在“竞争结构”上,针对作品中的主角和反派角色,具体分析人物的动机、择偶标准、性格因素、情感反应等方面,在竞争和性别对立、男女性作家的男女性人物、竞争结构的适应功能这三个方面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认为“竞争结构应被视为一种模拟情感反应的社会互动体验”③J.Carroll,J.Gottschall,J.A.Johnson& D.J.Kruger,"Agonistic Structure in Victorian Novels:Doing the Math",Joseph Carroll(ed),Reading human nature:Literary Darwi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1,p.173.。研究人员还将奥斯丁作品中的56个人物分成不同角色,分析了动机、性格与意识形态、性别关系、女主人公的情感反应以及读者反应。统计数据表明,奥斯丁压抑了男性的欲望,将男性的动机女性化,以积极的情感基调体现了女性的家庭精神。可以说,“在小说所隐含的社会视野中,更强大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和培育女性的家庭精神”④J.Carroll,J.Gottschall,J.A.Johnson& D.J.Kruger,Graphing Jane Austen:The Evolutionary Basis of Lit⁃erary Meaning,p.96.。
除了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有的研究以作品中对女性性格有实质性评论的段落为分析对象,依据进化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以及人物在社会关系和恋爱关系中的实际行为,设计出一系列描述行为和趋势的题目,进行问卷调查。以《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例,通过互联网对美国中西部两所公立大学的本科生(332人,226名女性)完成匿名调研,研究人员认为奥斯丁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可能是因为“奥斯丁的人物描述提供了与现实人物的低成本、低风险的替代体验,并促进读者对他人动机和行为的理解,以适应性地调节自己的行为”①Daniel J.Kruger,Maryanne L.Fisher,Sarah L.Strout,Shana'e Clark,Shelby Lewis,&Michelle Wehbe,Pride and Prejudice or family and Flirtation?Jane Austen's depiction of Women's Mating Strategies.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2014(1):114-128.。换句话说,当代读者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中很容易就能看出人物的择偶策略,并能准确地将人物与所描绘的实际行为相匹配。可见,奥斯丁对女性择偶策略的描述揭示了她的许多洞见类似于现代进化心理学家所佐证的观点。
四、神经认知诗学研究与阅读的神经机制考察
神经认知诗学研究是对读者在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身体反应和大脑神经机制的实证调查分析。不同于基于访谈、问卷调查的行为研究方法,研究者探讨的是文学文本的阅读模式、情感体验等方面的神经机制。按照首创者阿瑟·M.雅各布斯(Arthur M.Jacobs)教授的定义,广义而言,“神经认知诗学就是对通过眼或耳的(诗歌)文学接受,包括它的神经基础,进行跨学科的实证调查,并对之理论化”②Arthur M.Jacobs,Neurokognitive Poetik:Elemente eines Modells des literarischen Lesens(Neurocognitive Poetics:Elements of a Model of Literary Reading),Munich:Carl Hanser Verlag,2011,pp.492-520.,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运用如事件相关电位(ERPs,Event-Related Potentials),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视线跟踪技术(眼动技术,Eye Gaze Tracking Technology)等神经科学新技术,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大脑加工语言的机制,研究文学阅读时激活的脑区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文学阅读的情感、审美和移情等的神经机制,为文学阅读的情感和审美的阐释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国外对奥斯丁作品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有两篇。菲利普斯等人采用fM⁃RI和眼动技术来研究细读和休闲阅读两种阅读模式下读者的文学关注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专业背景(英语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的被试,在阅读《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时,认知模式会有何不同。研究者认为,在欣赏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画、电影等艺术作品时,我们的聚焦风格和聚焦度决定了我们对作品的参与方式,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主观的审美体验上,还体现在认知层面上(独特的神经活动模式)。③Natalie M.Phillips,"Literary Neuroscience and History of Mind:An Interdisciplinary fMRI Study of Atten⁃tion and Jane Austen",Lisa Zunshine(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55-81.
实验分析表明,读者阅读作品时,会自然而然地在细读和休闲阅读两种模式中相互切换,对手中的文本进行无意识地调节。两种阅读模式激活的脑部区域既有重叠部分又有各自的特征,而且模式切换时表现出了强烈的认知差异(比预想的差异更显著),整个脑部的血流输送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细读模式几乎激活了大脑所有区域,调动的脑部区域远远超出了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相关的区域,说明细读过程不仅涉及注意力和关注点,还有其他认知活动。
研究者们注意到,奥斯丁时代阅读和聚焦的历史环境和当今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被试者阅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时的脑成像与19世纪的读者应该有重要的差异,重要原因在于“细读”不是那个时期读者的阅读习惯。“当今读者虽然与历史读者具有特定的认知共性:对文本中角色的情感反应、对长难句(歧义句)的加工负荷、阅读时激活的核心神经网络。但是,当今的文化参考、识字普及率、打印技术、教育实践等因素已经使我们大脑中与文学关注点密切相关的神经生理网络变得更加复杂,灵活度也比历史读者有了很大提高。”①Natalie M.Phillips,"Literary Neuroscience and History of Mind:An Interdisciplinary fMRI Study of Attention and Jane Austen",Lisa Zunshine(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55-81.实验结论意味着,认知文学研究者在思考历史与认知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认知的历史语境,同时也提醒文化历史批评家也要意识到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历史性变异。
埃里克·瑞齐勒(Erik D.Reichle)等人则研究了“无意阅读”(Mindless Read⁃ing),即眼睛正在看书或文字,但是心理却发生了游离(俗称走神)的现象。他选取了4名在校生(3女1男)阅读整部《理智与情感》,采用经验采样法以及眼动追踪技术,通过分析行为指标(被试的阅读时间、回答问题的正确率、自我捕捉走神的数目以及探针捕捉走神的数目)和眼动指标(正常阅读、自我捕捉无意阅读、探针捕捉无意阅读下的四个指标:首次注视时间、词间的回视时间、词的注视时间、文本外注视时间),揭示了正常阅读和无意阅读两种模式下眼动的差异。
他们发现:
“自我捕捉和探针捕捉无意阅读时,注视时间指标比正常阅读中长,并且这些差异早在捕捉到无意阅读前60秒到120秒时就很明显,并且这样的模式在自我捕捉的情况中更明显;在捕捉到无意阅读前10秒到30秒时,注视时间指标受正在进行的词汇和语言加工过程的影响,比相同时间间隔的正常阅读时少;被试在刚刚自我捕捉无意阅读前2.5秒的时间间隔内做到首次注视、词的注视或词间注视(这些都表明正常文本加工),不论是比探针捕捉无意阅读还是比正常阅读中的可能都要小,被试更可能用看其他地方代替阅读文本。”②Erik D.Reichle,Reineberg,Andrew E.&Schooler,Jonathan W,"Eye Movements during Mindless Reading",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9):1300–1310.
研究表明,若能在无意阅读发生时实时识别,将有利于改善人们的阅读困难问题,而且研究无意阅读可以促进对意识本质以及阅读的认知加工过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神经科学实验将文本、视点跟踪和脑成像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读者阅读反应差异的变量及其在神经层面的反应。虽然研究者选取的都是奥斯丁的作品,但实验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技术手段,所要探究的文本内容激活的认知或审美活动过程有所差异。目前依据神经科学技术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由于受技术、经费限制,大多研究集中在较少的几个科研机构,而且研究者很少对单词、短语、句子之外的文本进行研究,因而成果数量少。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零散,研究的一些问题也可能缺乏统一的认识和阐释,但是已然表明,文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描述和解释,而是开始对语言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深入挖掘,对文学作品接受的情感和审美研究给予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实验数据支撑。
五、结 语
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奥斯丁作品的认知文学研究有逐步深入和拓展的趋势。依据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奥斯丁对人类心智、身体、情感的描写,揭示了她笔下人物心智和情感的展现方式是具身的。在奥斯丁的小说中,人类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心智或意识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简单联系,她对人物的洞察和思考具有社会文化性、具身性和生物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奥斯丁专注于人物情感和感知过程的描写,使得读者也能够迅速通过人物情感和具身体验进入文本空间来感知人物的心理特征。
但同时又必须承认,目前现有成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研究盲点较多,分析视角狭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成果,等等。为了进一步推进研究,笔者提出如下三条路径作为参考:
1.给予作品整体观照,提升研究的系统性。现有的研究观照到《爱玛》《傲慢与偏见》和《劝导》较多,其余三部也有少量涉及。目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成果只有两部专著。未来的研究可将奥斯丁创作的作品全部纳入考量范畴,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双重层面上提升研究的学术层次。
2.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扩展研究深度。现有研究成果大都聚焦于作品中人物的虚构心智、具身体验以及与叙事技巧的关系等论题,若要使研究在纵深上有所突破,就需要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开辟新的途径。适当借鉴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女性主义、认知空间批评、认知生态批评、心智美学等多维视角深入发掘作品内涵,或是配合问卷、访谈的行为研究和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认知文学批评视域。
3.考察奥斯丁作品与媒介表演之间的关系。从认知文学视角对戏剧表演艺术的研究可谓是不胜枚举,比如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研究不断深入。历年来奥斯丁的作品不断地被改编为影视剧作,若从认知文学研究视角探究其作品原著与影视剧改编或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互通关系,势必有助于深化奥斯丁作品研究的深度。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国外奥斯丁作品的认知文学研究成果的批判借鉴,不仅可以丰富研究的学术史料,也为国内学者提供研究起点,开阔研究视野,形成国内外研究互动交流、平等对话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