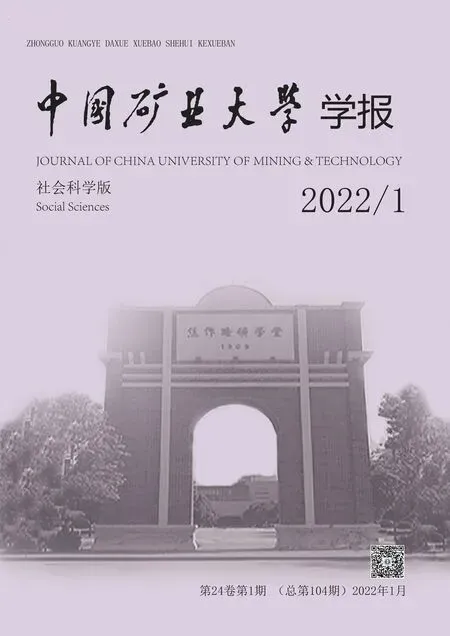从拟真到致幻
——“一镜到底”的美学探索
2022-11-23曹桐曹红军
曹桐,曹红军
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是长镜头系统论述的源头。巴赞认为段落长镜头能够使影像时空与现实时空得到完整统一,从而起到再现物质现实的效果。长镜头从理论化初始,便被置于现实主义和纪实美学的框架中。而“一镜到底”电影的出现,使得影片可以由独立的长镜头连贯呈现,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影像本体的物质性色彩。
“一镜到底”所展现的连续时空与人的视觉感知一致,呈现出了独特的沉浸性、游离性与绵延性特征。相较于物质现实的真实,其效果更加贴近于“知觉的真实”。随着现代电影美学和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一镜到底”的美学效果逐渐向着超现实、心理化的写意美学发展。通过延续诗电影的美学手法,丰富长镜头对于内部时空的再造,“一镜到底”呈现出了虚幻的梦境效果,在美学和哲学范畴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数字影像时代,“一镜到底”更是拓宽了传统类型电影的表现疆域,在沉浸性影像和游戏化电影中取得了突破。
如今,关于“一镜到底”电影的评论仍更多基于影视艺术实践的角度,对于其理论研究也多着眼于拍摄方法和技巧层面。“一镜到底”电影的美学追求究竟为何?其美学特征具有哪些发展趋势?通过梳理“一镜到底”电影在各时期的美学特质和表现手法,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一、拟真:对制作工艺和艺术形态的极致追求
历史上第一部采用“一镜到底”概念呈现全片的电影是1948年由美国导演希区柯克拍摄的《夺魂索》。希区柯克早期作品风格多脱胎于苏联蒙太奇学派及德国表现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含义丰富的剪辑、风格化的摄影、布景等,营造紧张悬念,塑造惊悚氛围。而《夺魂索》却突破性采用克制的长镜头结构全片,以纪实性的手法表现了一场连贯的戏剧事件。该片所呈现的风格转向,不仅是希区柯克对个人导演类型的突破,更是对电影本体形态的实验探索。
20世纪20年代,由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苏联电影人创立了影响深远的蒙太奇学派,“他们认为画面本身并无涵义,涵义是由蒙太奇射入观众意识的。”而高举纪实美学旗帜的后来者安德烈·巴赞则批判蒙太奇手法,认为“蒙太奇是典型的反电影性的文学手段,把单一的意义射入观众的意识,观众永远只是被动的接收者”①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页。。巴赞提倡的影像本体论基于现实主义视角,将影像的本质与物质现实相同一,认为长镜头是最能体现现实的多义性与暧昧性的镜头语言。强调在不进行主观介入的长镜头里,能呈现出表现对象的真实、空间时间的真实以及叙事结构的真实,从而创造可再现世界原貌的“完整电影”的神话②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页。。巴赞的影像本体论与长镜头理论对电影语言的探索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深刻影响了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等著名导演。后人以大量的影像实践探索着巴赞的理论,诞生了众多以长镜头美学为标志的纪实风格电影。
《夺魂索》“一镜到底”手法的横空出世,是在“蒙太奇”与“长镜头”两大学派博弈中,长镜头形态的首次极致化应用。长镜头赋予了《夺魂索》与众不同的现实感,在绵长的镜语里,文本的矛盾与悬念呈现于琐碎的细节中,以克制的节奏和冷峻的旁观视角展现了案件全景。影片开头就揭露了案件凶手及藏尸线索,由此埋下核心悬念——来宾何时发现凶杀真相。长镜头以大量细节延宕戏剧悬念,如通过镜头调度多次表现了女仆收拾藏尸箱子,却未发现尸体的行为动作。以克制的调性,围绕悬念元素展开铺陈叙事,在生活流中模拟真实在场的紧张感。高密度的戏剧矛盾与绵长镜头形成了强烈反差,构成了文本与形式间的反向张力。
不过作为“一镜到底”的首次呈现,该片在表现形式和美学内涵上尚存在较多瑕疵,并未达到巴赞理论中“完整电影”的美学神话效果。首先在表现形式上,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该片“一镜到底”的效果实际是8个长镜头分段拍摄,经由黑场、跳切等手法模糊剪辑点拼接而成,并未达成对现实时空的完整摹写。其次,在美学呈现上,为了实现连贯拍摄的效果,导演采取封闭空间与线性时序,使内容近似于古典“三一律”式的舞台剧,缺乏了灵活的调度空间。长镜头仅起到了对场景、细节的勾勒突显作用,并未与叙事文本产生有机的内在联系。整部影片如同在景别与视角不断变换中呈现的实景舞台剧,整体表现并不出色。但倘若脱离与叙事文本的关联,纯粹分析“一镜到底”的本体形式与审美效果,“一镜到底”视听语言的若干独到特征便显现出来。
(一)沉浸性
“一镜到底”连绵的影像时空贴近人眼的真实感官,极易带来沉浸式的主观体验,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知觉的沉浸中,长镜头又将人物、事件置于不断变化的画框与景深之中,其表达意义的含糊性、开放性,会引发观众自主的思考,带来心理的沉浸。在知觉、心理的双重沉浸作用里,琐屑的环境细节、纪实性的人物互动、连贯的空间运动,构成了“一镜到底”生活流叙事中的核心要素,写实主义风格得到了充分体现。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一论,来源于对于造型艺术起源的心理分析——艺术家们对于造型艺术的创作本能,可追溯到“木乃伊情节”,即人类渴望还原、保留现实物质的原始冲动。而电影的出现,使得物质现实得到了完美再现。“影像的纪录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的痕迹,不再受到不可逆的时间的影响。”①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页。而“一镜到底”的出现,则不仅仅是对物质现实的还原,更是对人类真实视听感知的拟真,是对人类内心与外部世界联结通道的再造。影像的“造梦”与致幻功能在连绵的视觉中被放大到极致,以其独特的沉浸体验,将影像视觉、作者视觉和观众视觉三者形成了深度连接。
(二)游离性
苏联电影理论家吉加·维尔托夫,以“电影眼睛理论”提倡电影工作者应当以摄影机机械的眼睛,而不是人的眼睛去看世界②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3页。。即通过摄影机独特的还原现实方式,反映人眼所无法捕捉、突出的现实内容,从而重新解构与认识现实世界。“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通过镜头调度,使画面角度、景别、画幅产生变化,在连贯镜头内部也可实现蒙太奇效果。丰富的视觉形态,使运动镜头与人类视点存在的差异在熟悉化的连贯视觉中形成陌生化体验。观众时而处在全能的上帝视点,时而又可能“附身”于片中人物的视觉中,形成多变观感。如《夺魂索》在展现凶手防备他人上门时,镜头先以客观视角跟拍凶手背影,随即凶手出画,镜头由客观变为主观,模拟了凶手视角缓缓向门走去,暗示其忐忑心理。而接着凶手持左轮手枪的手忽然从画幅左侧入画,再次由主观变为客观视角。长镜头连贯地实现了由窥视至沉浸的主客观变化过程,形成客体与主体无缝转换的镜头语言。“一镜到底”的电影眼睛以独特的观看方式打破了连贯视觉的习惯与沉浸性,呈现出特有的间离效果。
(三)绵延性
“一镜到底”的运动镜头构成了“物随景移、移步生景”的画面效果。绵延的镜头运动构成了影片空间与时间的整一性。
巴赞认为,“银幕仅仅是把事件的局部显露给观众的一幅遮光框。当人物走出画面时,我们认为他只是离开了我们的视野,而依然如故地继续存在于背景中被遮住的另一个地方”。这段话强调了电影银幕像窗户一样,展现的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全貌,画框在空间上具有向外延伸的特性。克拉考尔对此回应:“它的边框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界限,它的内容使人联想起边框之外的其他内容,而它的结构则代表着某种未能包括在内的东西——客观的存在。”①徐丛丛、吴冀川:《电影长镜头学派的现象学思想解读——重识巴赞与克拉考尔》,《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绵延的长镜头将画框内外的世界构建成整体,除了画框内的画面,外延出去的影像世界,也在绵延的势能下具有“存在”的张力,在每一个影像瞬间,都具有外延至下一时刻的动能,而外部世界的未知与模糊,又构成了戏剧性的悬念。
巴赞在《一部柏格森式的影片——毕加索的秘密》一文中曾这样评价过影像的内容:“毕加索笔下的每一个线条都是引发新内容的一种创作,它不像是一个原因导致了一个结果,而更像是一个生命孕育了另一个生命。”②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04页。这一论述包含了对于柏格森的“绵延”概念的理解——时间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各个阶段互相交融、渗透,汇合成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中的运动过程。“一镜到底”将长镜头所绵延的空间与时间贯穿始终,既包含了对于时空连续的现实性指射,也暗含了始终处于未知的悬念延宕,建构了具有独特形式的完整意义宇宙。
当长镜头作为影像整体,其沉浸性所蕴含的对观看心理的召唤,游离性所呈现的特异视角下的间离效果,绵延性所体现的独特的整一联系,综合成为无限接近现实而又区别于现实的幻觉形态。巴赞曾经将理想的现实主义电影称为“现实的渐近线”,那么“一镜到底”则更像是“知觉的渐近线”,是对于现实认知与心理感受的写真。
二、虚幻:现实空间与幻觉镜像的超文本结合
经典长镜头理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空间与时间的还原,本质在于借长镜头的客观性进行写实表现。而在现代电影中,超现实风格与主观思想表达同样是电影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向。电影语言的形象符号建立在回忆和梦境的基础上,是一种凭借本能对现实物象进行视觉读解的语义系统。除了客观的纪实外,长镜头下的物象作为主观的符号能够呈现丰富的下意识的、非理性的表意内涵。
(一)长镜头与诗电影
意大利导演皮耶·保·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一文中曾经指出:当电影运用诗的语言特征进行表意时,会呈现出“自由的、间接的”话语特征①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78页。。如安东尼奥尼对于心理世界的外化表现、贝托鲁奇对于极致细节的呈现、戈达尔通过物象的联结创造新的语言……蒙太奇对于物象的表意是直接而清晰的,通过对物象的联结能够形成主观式的隐喻功能,这也构成了苏联早期的蒙太奇诗电影风格。而具有现实本体性的长镜头,客观冷峻的视角呈现出了现实的含糊与暧昧性,在表现主观化的诗意影像时,具有天然的朦胧感,其冷静的客观形式与幻想内容的糅合会迸发出独特的美学张力。
俄国著名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如诗如梦的意境美学闻名于世。在继承了苏联诗电影传统的同时,他尤为擅长在长镜头中营造超现实的梦幻场景,塑造如梦境、倒影般的影像时空。在《乡愁》《潜行者》等电影里,文本内的时间常失去线性意义,过去、现在与未来交融于一个长镜头中。如《乡愁》中,长镜头跟随一个秉烛男人将烛火从墙的一角移至另一角,在这个绵长的境语里,作者传达出了人从出生至死亡的抽象隐喻。长镜头作为塔可夫斯基“自由的、间接的”诗性话语,具有一种深沉的内省特征,能够在沉缓节奏中将人物的情绪与表达放大。在长时间的段落镜头中,时间长度更象征着生命的密度,喻指着时间的凝结和生命的转瞬即逝。正如其“雕刻时光”的电影理念,“没有其他哪种艺术能像电影这样,可以凝固时间,因此电影是什么?它是时光雕刻的镶嵌画。”②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二)运动镜头与超现实穿越
《俄罗斯方舟》是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一镜到底”影片。全长99分钟的影片,动用总计450多名演员,历时7个月排练,在经历了3次失败后最终才连贯拍摄完成③吴婷:《一镜到底的艺术特色》,《艺术科技》2016年第20期。。而除了技术上的突破外,《俄罗斯方舟》更具突破性的在于打破了“一镜到底”完整视觉内部的时空连续性。
该片是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2002年拍摄的一部历史影片,讲述了一位当代电影人穿越进圣彼得堡的古老宫殿里,见证了俄罗斯千百年历史的奇幻漫游故事。影片将“一镜到底”的沉浸性充分发挥,镜头全程喻指主人公的主观视点,引领观众与剧中人物“直接”对话,在移步换景的穿越中,“亲身”游览俄罗斯200多年间的文明景观。在景观式的长镜头里,观众会发现俄罗斯历史中的文明瑰宝,伟人先贤不断跨越时代,汇聚在这座时空不明的宫殿中。连贯的画面里不断涌现着超现实的视觉讯息,糅合成具有现实感的幻觉体验。
超现实时间感的塑造,得益于长镜头对内部空间真实性的消解。运动镜头向量具有前后、上下、纵深、左右等方向维度,当长镜头呈现方向感、目的性不明确的物理空间时,这类迷幻的真实空间配合长镜头的运镜方式,则可构成银幕空间的假定性,将空间抽象为视觉符号,形成独特的“穿越”心理暗示,将真实空间跨越为主观空间。《俄罗斯方舟》拍摄于俄罗斯国立美术馆。从空间功能上看,博物馆的每一个子空间都具有时间标记功能,从空间造型上看,博物馆复杂的回廊、门厅,都给空间转场提供了契机。所以,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穿行于回廊中,每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就会“穿越”进历史的某个时刻。在线性的游荡画面里,镜头之眼亲历了伊朗使节造访沙皇的仪式,巧遇尼古拉斯以及革命前夕末代沙皇一家最后的晚餐,并在1913年末代皇室的最后一场盛大的华尔兹舞会上结束了他们的“旅程”。在连贯的电影时空中,长镜头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与文明的梦幻旅程。时间仿佛是一场线性的景观,散状陈列在宫殿内,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国文明、人物以现实物象的形式与超自然的梦幻感相统一。
(三)德勒兹与“一镜到底”的梦境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曾提出,影像中的时间是同时包含着过去(回忆)、当下(正在发生,且立刻成为过去)以及未来相同一的形态,称其为时间的晶体。我们可以精简理解为影像中的瞬时既包含着过去的一切,又将同时导向未来的一切。德勒兹还认为,在所有现实影像的背后都映射着一种潜在影像。某种程度上其理论与克拉考尔的电影本性论不谋而合,“电影通过可见世界(日常情景或虚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隐藏在思想中的动机”。但对于现实与潜在影像的双重张力关系,他做出了更深入的剖析,“潜在影像不是一种心理状态或一种意识:它存在于意识之外,存在于时间之中”,“就现实而言,没有不变成现实的潜在,同样,也没有不变成潜在的现实。这是可以自由置换的反面和正面”①应雄:《德勒兹〈电影2〉读解:时间影像与结晶》,《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影像文本中具有引导观众进入回忆和梦幻的势能,从物质的现实指向想象的虚幻,而潜在影像又会进一步指向回现实,呈现为记忆、想象和思维的扩展、循环与反射,直至现实与幻境的边界模糊重合。
长镜头以照相性特征作为美学本体,其富有现实性的沉浸知觉条件为潜在影像与客观影像的双向流动创造了前提,使得作者的主观想象与作品的客观形象进一步贴近,从连贯而完整的物质景观之中,升华出梦境与幻觉的质感。《俄罗斯方舟》中的宫殿,如同德勒兹理论中的晶体空间,将时空的侧面融合。“一镜到底”的纪实性将文本构建的历史回忆与现实物象相同一,正如该片的主题一样——方舟,意味着虽然俄国璀璨的文明历史已留在了过去的时代,但是它们深深印刻在了俄国后人的精神与血液里,如晶体般熠熠永存。
如果说《俄罗斯方舟》借“一镜到底”使非线性的时间元素展现出超现实效果,那毕赣的《路边野餐》和《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则完全沉溺于对梦境体验的模拟。作为新生代的华语导演,毕赣的创作方法和美学理念深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在其处女作《路边野餐》中,导演在叙事文本中引入了大量诗歌元素,使得情感密度在长镜头的时间密度中充分涌现。长镜头跟随着乡间医生在名叫荡麦的小镇遇见了他逝去的爱人和未来的侄子,过去、现在、未来的多重时间维度杂糅在荡麦这个晶体空间里。最接近现实的纪实长镜头,与最梦幻的诗关联在一起,呈现一种巨大的张力,使司空见惯的现实突然有了陌生化的色彩,那些被日常生活抹去了的激情、梦幻和诗意,在观众观看电影过程中,纷至沓来,在荡麦这一虚幻空间中得以集体释放①王杰、肖琼:《寻找飘逝的乡愁——关于〈路边野餐〉》,《上海艺术评论》2017年第2期。。
继《路边野餐》后,毕赣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再现了“一镜到底”的梦境演绎,并以更加丰沛的梦境元素将“一镜到底”推向更极致的幻境。
首先,该片从观影方式上加入了浸入式交互的巧思。《地球最后的夜晚》前半段用2D放映讲述了主人公的现实经历,而在后半段“一镜到底”的梦境则采用3D放映,在进入此段落时,观众需要主动佩戴3D眼镜进行观看。这样一种设计,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将“一镜到底”的沉浸性体验进一步放大,通过增设“戴眼镜”这一观影过程中的交互媒介,一方面形成了一种间离效果,在形式上主动将影片的现实与梦境段落相区分;另一方面,利用了沉浸性影像对于观众的召唤性心理,通过观众主动参与的仪式感,强化在观影潜意识中对于梦境文本和“一镜到底”形式的接受度,从而进一步突出“一镜到底”的造梦感。
其次,该片在长镜头中更有意识加入了符号化的物象,强化了物象对想象的能指作用,在开放的长镜头中塑造了符号化的隐喻迷宫。《地球最后的夜晚》将大量场景、物象作为隐喻文本,对应着主人公罗纮武的潜意识而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梦是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而成的”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71页。。在影片中,相同的人物与物象在现实时空与梦境长镜头中分别出现,构成所指与能指的互文关系。现实中的好友白猫在梦境里成为一个打乒乓球的少年,而现实中追寻的神秘女人在梦境里成为凯里县城一个普通女子。形象的双重意义在铆定了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镜像关系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梦境叙事的功能,隐喻主人公现实中的遗憾并逐步与之和解。
2)高原4月整体、E区(喜马拉雅地区)及G区(高原东南部)与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呈负相关性,其中E区(喜马拉雅地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最多。因此,喜马拉雅地区4月感热通量可以作为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预测的因子之一。
《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以经过剪辑的段落作为现实时空,“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段落象征梦境,彼此在时空和文本意义上构成镜像式的互文。该种结构如同前文论述的德勒兹理论中现实影像与潜在影像的关系。在可见的前半段现实中,人物的情感与回忆作为不可见的潜在影像以隐性的张力存在于现实叙事中,而本应朦胧不可见的潜在影像则在后半段以物化的长镜头形态展开,这种构作使得现实时空中含蓄的能指有了清晰的所指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一镜到底”的梦境既作为现实的潜在影像,同时又作为以长镜头为本体的现实影像。因此,梦境又以自身为“现实”,将梦的潜在影像指涉回了真正的现实,形成了德勒兹理论中“自由置换的正反面”。同时,现实与梦境中物象的意指作用也发生了颠倒,梦境与现实互为彼此的能指和所指。
之所以用“一镜到底”强烈的物质性来表现梦境,正是基于作者意图模糊现实与幻想边界、淡化二者从属关系的创作初衷。柏格森认为物质自身对外部发生作用、发射光,而接受了这种作用和光的人即产生了物质的“像”。“像”就如同物质和精神的一个共同的参照平面,介于纯粹物质和纯粹精神之间。而影像就是一个知觉机器所截留、所接受的来自物质的作用和光。德勒兹在伯格森的基础上,把影像和哲学中的“像”连接起来,将影像看作是理论上不同于人脑的光学、声学机器所得到的物质作用和光(波),同时他广泛采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学,认同了影像的物质性,仿佛物质的“火”变成了影像的“烟”①应雄:《德勒兹〈电影2〉读解:时间影像与结晶》,《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一镜到底”的梦幻原理,与“像”的哲学逻辑十分相似。连贯的知觉形态最为近似现实世界,却只是现实世界的倒影,是夹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共同参照面。是极度逼近真实、却又无法抵达物质现实的海市蜃楼,如同物质之鳞片在宇宙中反射出的点点光泽,触手可及,又触不可及。
三、共情:数字技术下的界限模糊与物我两忘
随着长镜头美学和影视工业技术的不断完善,“一镜到底”在商业电影领域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字技术的成熟,更是以虚拟现实替代了影像的物质现实,在虚拟的造梦幻觉中呈现更深层的沉浸效果。
(一)“凝视”与自我投射
在商业类型片领域,“一镜到底”更多运用于聚焦个体命运,将影片时间等同于文本时间,通过沉浸性、游离性、绵延性放大戏剧氛围,提升对人物情绪的体现。如《寂静的房子》《余命85分》《于特岛7月22日》都截取了个体在极端境遇下由高浓度情绪主导的一段生命时间。2015年德国导演塞巴斯蒂安·施普尔执导的惊悚片《维多利亚》是该类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一部犯罪悬疑电影,《维多利亚》前半段以铺陈琐碎的细节,讲述了维多利亚与4个青年邂逅相知的过程。在你来我往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影片推向柔和平淡的日常纪实风格。然而故事从中段急转直下,维多利亚和4位青年卷入了黑帮事件,受胁迫抢劫银行。在激烈的犯罪、逃亡段落中,长镜头通过运动镜头、跟拍、晃动等所具有的游离视点,产生极为丰富的在场感。“一镜到底”的绵延性,让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反转事件具有强大的张力。前半段缓慢积攒的人物共情,不断为后续的悬念蓄力。当观众已沉浸于平淡的日常性节奏,反转张力突然爆发。使“一镜到底”表现出的日常性升华为一种反常态的惊悚感,强烈的现实感粉碎成了幻灭感。
《维多利亚》等商业类型片采取的美学路径与“一镜到底”的开山鼻祖《夺魂锁》相同——将“一镜到底”的纪实性形式与强戏剧性文本结合,形式的真实性与内容的假定性碰撞出反差张力。影片采用写实主义风格,维持影像时间与客观时间的一致,还原物质现实的真实。更丰富的镜头调度,更极致的戏剧冲突,让“一镜到底”的沉浸性呈现出高度聚焦于人物的个体感受。连贯的镜头下,人物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丝表情、每一个动作起伏都被细微地捕捉到,观众能够更充分地共情人物。“一镜到底”对于知觉的深度模拟,对人物的极致贴近,使得观影行为更像一种连贯而真实的“凝视”。
萨特引用“凝视”这一概念强调人作为主体与他人的辩证关系,在注视中,自为的存在性得以真正建立。而拉康在萨特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凝视”的边界。他引入“镜像”概念,认为人在自我的建构过程中,通过注视行为将他者的形象作为自我形象构建的重要途径。并且,主体在“看”的过程中,也具有一种潜在的“被看”的指射,这份潜在的“被看”映射出的是主体自身携带的欲望。“凝视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是一种与想象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但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①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30页。凝视所诱发、携带的幻想,是欲望的投射,观看主体希望沿着欲望的缺席到达欲望的在场。
在“一镜到底”的沉浸体验中,观众通过对于电影人物的连贯聚焦,形成了一种长时间的“凝视”,将自我意识投射于被“凝视”的他者,形成了心理上对角色的“扮演”。同时,“凝视”行为也指射出观众内心的潜在欲望,在《维多利亚》中,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超日常刺激性的渴望,对危险和反叛的追逐。影片前半段细碎的日常中,暗示了维多利亚的潜在人格阴暗面以及对庸常日常的厌倦。文本层面的欲望呼唤与观众“凝视”行为的潜在心理形成了暗合,进一步强化了观影的带入感。使得观影行为成为一份沉浸式的欲望投射。观影中,“凝视”并不是一种代偿的欲望满足,而更像是将主体的潜在欲望透过他者得到显现的存在,是对深层自我的认知,如同“镜像”般,实现着对自我的照见。
(二)数字技术下物质与精神的相融
随着数字摄影技术及虚拟合成技术的不断成熟,二进制代码构建的影像彻底改写了影像与物质现实的同一性,让“一镜到底”有了更加自由丰富的表现形态。荣获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鸟人》就是好莱坞工业体系下“一镜到底”作品的成熟典范。超过100分钟的长镜头实际由多个分镜头通过CGI技术拼接而成,看似连贯的场景也是在不同场地拍摄的。数字技术的成熟发展真正实现了人工技术创造的虚拟现实与物质现实的融合。《鸟人》讲述了一位过气电影演员企图通过进军百老汇挽救自己事业和生活的故事,长镜头将主人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交融,展现了其荒诞而可悲的内心挣扎。虚拟数字技术下的“一镜到底”既呈现出了巴赞长镜头美学的物质现实属性,又表达了作者的虚拟想象,进一步将长镜头创作从物质本体迈入想象本体语境。
《鸟人》的第一个镜头运动就奠定了全片超现实的风格基调——镜头由主人公的面部特写拉至身体全景,展现了人物漂浮在半空的状态,通过后续的情节,观众可以得知这是主人公独处时内心意识的外化。后续进入主人公内心的犹豫与挣扎时,代表他人格负面的鸟人会在长镜头中出现,带着男主进行一系列超现实的行为活动。数字技术将人物超现实的意识世界通过虚拟技术实现,再以长镜头与现实叙事连贯贴合,进一步模糊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使得人物的心像能够更自然平顺地外化。
塔可夫斯基、毕赣等人以情入境的长镜头,是通过镜头内部的隐喻、符号、调度塑造出的梦幻效果,在诗性的镜头语言中对物质现实进行的象征性改造。而《鸟人》则通过数字技术直接对画面所呈现的物质景观进行重塑,一反传统长镜头将精神世界物化的方法,而是将物质精神化,使得影片无论在文本还是素材层面都得以高度主观化。在高度发达的长镜头技术下,虚拟与现实的影像层次上有了更清晰的区别,观众能够更精准地区分在连贯镜头内何为真实何为幻想,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更加模糊,真实与幻想在特效中紧密缝合,虚实交融的奇观跃然银幕。陌生化的奇观中暗含的是对梦境的写真,“一镜到底”对于现实知觉的拟真得以更进一步在幻想的觉知中开拓天地。
(三)“一镜到底”与游戏化电影
随着新媒介的多样化兴起,电影的形式正被愈来愈多的媒介形态复合、混杂。尤其电子游戏的流行,让电影的游戏化特征愈发明显。纽约大学媒体研究者亚历山大·盖洛威在他的著作《游戏化:论算法文化》中指出,新一代的电影摄制者开始自觉探索将游戏形式融入电影制作,并创设“游戏化电影”这一术语。“游戏化”电影在具体的形式表征上主要体现为时空设定游戏化、情节结构游戏化、视觉呈现游戏化①施畅:《游戏化电影:数字游戏如何重塑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9期。。2020年由萨姆·门德斯执导的战争电影《1917》,就是一部以游戏化风格为主导的“一镜到底”电影。
该片讲述了一战时期,英军在进攻兴登堡防线的最后关头发现是德军陷阱,为向前线传递“停止进攻”指令,特派两名英国士兵冒险穿越敌境,拯救1600名英国士兵的故事。该片在情节结构与视觉呈现上做了充分的“游戏化”处理。“一镜到底”的连贯时空搭配冒险闯关式的叙事情节,使得整部影片效果近似RPG类的战争游戏。在第三人称开放式RPG游戏中,玩家能以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俯瞰并操作人物完成任务,线性闯关。《1917》中画面始终以跟随镜头拍摄主人公,时而搭配主观镜头模拟人物的第一视角,充分模拟出RPG游戏的视觉体验。这样的设定一方面唤醒当代观众潜在的玩游戏经验,生成玩游戏的假定性与嵌入性;另一方面激发观众在视觉观看的基础上混合身体动觉,增强观众在电影院的体感经验。
此外,“一镜到底”的连续性拍摄所引导出的影像空间,近似电子游戏视角下具有空间导航功能的镜头调度,起着从视觉上召回观众游戏经验的引导作用。形态各异的战争景观如同开放游戏地图中的不同版块,角色在每个场景中遭遇不同的挑战,每一个立体空间都似一道精心设计的游戏关卡。随着主人公的行进,布满尸体与残骸的铁丝网、废弃的炮车“墓地”、夜色中燃烧的教堂接连呈现,在探索视角下都具有一种持续的悬念感,共同营造出惊奇性和探险性兼具的战争景观。
导演萨姆·门德斯有意识地选择了“一镜到底”作为该片的主体形式。“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选择,这必须有一种发自内心、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式是为了让观众尽可能接近那种体验。”①撩撩电影呗:《〈1917〉要玩新花样,110分钟一镜到底》,https://baijiahao.baidu.com/?id16461775956593806 13&wfr-spider&for-pc,2019年10月1日。在《1917》中,战争被呈现为一种景观,同时更被放大为一种体验。电影虽无法呈现电子游戏所具有的交互形式,但通过模拟电子游戏的视觉和文本形式,可以将沉浸性与交互感进行深度的勾连,从而唤醒观众的体感经验,模拟出心理上的触觉体验。美国学者詹妮弗·巴克尔在《触觉之眼:触摸与电影体验》一书中提出:电影体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深层的触摸──电影与观众间的感官交流,这种交流超越了听觉与视觉,深入皮肤之下,并在体内发出回响②Jennifer M B,“The Tactile Eye:Touch and the Cinematic Experi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April 2009,p.7.。当镜头跟随主人公在布满荆棘的战壕中被割伤,在萦绕苍蝇的尸堆中挣扎作呕,同时又在战场边缘的樱花树下驻足,在林荫中的士兵颂歌前聆听,观众的触觉和动作感知也随之唤醒。在“一镜到底”的景观设置中,影片将唯美诗意的自然意象与残酷肮脏的战争景观提纯并置,在强烈的美丑、生死二元对立中,主人公的行动具有了更鲜明的抒情性。电影与游戏的混合使得“观看”不仅转变为“知觉”,更转变为一种“象征性的交互”。
美学理论的兴起都与其时代主题具有相近的潮流方向。从长镜头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来源于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观察与思考,本质是通过现实主义影像对于战后社会的美学反思;塔尔可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等电影大师所发展的诗意美学长镜头,受到法国新浪潮等现代电影运动的深刻影响,源头在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电影的浸入;而“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美学,诞生于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壮大发展于数字影像时代。沿着前人所应用过的长镜头美学语境,逐步探索出从拟真到致幻的美学发展方向。如今,“一镜到底”的应用范围广泛,除电影外,广告、游戏、VR、互动电影等新兴媒介中都能看到其姿态。但在多数情况下,“一镜到底”仍被视作一种在主流影视形态之外的新奇样式或是过度炫技的包装。实际上其致幻般沉浸性的媒介形态,与数字时代主题十分趋同,即深度的沉浸形式与数字控制论下的赛博格幻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作为兼具数字时代技术风格与美学特征的视听形态,“一镜到底”仍在发展与探索的阶段。其既需要融合新的媒介形态拓展其应用边界,又需要进一步延伸其诗意的幻想性,深化其美学的沉浸性。